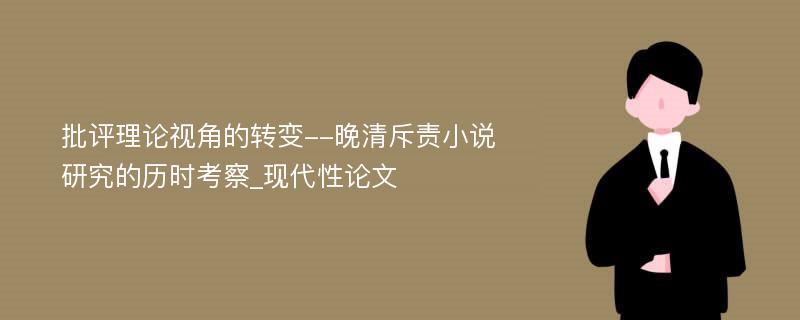
批评的理论视角变迁——晚清谴责小说研究的历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述评论文,视角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2008)02-0105-05
晚清谴责小说自产生以来,研究者论述甚多。从丰富的研究著述中,笔者概括出以下几种研究模式。这种总体模式概括具有共时性色彩,但每种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历时性研究特点。从这些研究模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学批评在现当代的理论变迁。
一、类型学批评模式
这是一种整体研究模式,即把谴责小说看作一种文学类型,揭示这一小说类型特有的题材特征、艺术规则以及其文学传统渊源。
这一批评模式最早滥觞于鲁迅的研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中第一次将以李伯元创作的《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揭露晚清社会丑恶现象的小说标目成“谴责小说”,使之与同时期的晚清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区别开来。鲁迅概括了这种小说类型的艺术规则:首先是内容题材的批判性特色,“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其二是语体特征,“词气浮露,笔无藏锋,以合时人嗜好”。其三,谴责小说是文学历史上讽刺小说的变体。在《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中,鲁迅首先界定了讽刺小说这一类型:“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有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然而,他认为晚清的这类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四,鲁迅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曾朴的《孽海花》作为谴责小说的代表作进行了具体解读,奠定了这四部小说经典文本的地位[1]。鲁迅的这一研究模式初步奠定了谴责小说的历史地位,对后来者也影响重大。其后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刘大杰和郭箴一在各自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及《中国小说史》中,都沿用了鲁迅的“谴责小说”这一类型概念。
建国后最初三十年,国内学者大都延续了鲁迅关于谴责小说的类型界定。80年代以后,类型学研究模式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对谴责小说这一类型概念的适用性上。部分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较早的以裴效维为代表,他在《试论中国近代小说的兴盛和演变》一文中指出,谴责小说这一称呼并不能涵盖整个晚清小说的思想容量,合适的概念应为“资产阶级小说”[2]。近年来,杨联芬又对鲁迅的这一概念界定进行理性反思。一方面她承认“鲁迅批评眼光的准确和语言的善抓特征,都使‘谴责小说’这个概念被广泛接受”,同时她又认为“我们对于晚清小说的研究和评价,大大受制于‘谴责小说’的概念和鲁、胡等大家无意中设置的藩篱”,“‘谴责小说’中具有鲜明个体特征的作家作品被淹没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共性中”[3]。其次,在谴责小说与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小说的类型区别、历史继承上,研究者多有挖掘。齐裕焜、陈惠琴合著的《中国讽刺小说史》中,将晚清谴责小说列为近代讽刺小说而多有论述。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将晚清谴责小说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四大名著拓展到《桃杌萃编》等其他以往不被重视的作品[4]。庄严在《论晚清谴责小说中的爱国题材》中说,谴责的艺术是由古代讽刺艺术演变而来的一种亚种,是谑化的讽刺[5]。著名学者陈平原在这一问题上见解深刻。他认为“‘谴责小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类型,只能说是讽刺小说的变体”,这种变体“未能满足于含蓄的讽刺,也不愿温和地滑稽”,“于是选择了鲁迅称之为‘谴责’的特殊表现风格”。值得注意的是,陈平原先生并没有把眼光仅仅停留在此,他深入挖掘“谴责”文体背后的根源,因为这“单从艺术天赋或者个人才能角度似乎无法解释”,进而从“说书风格的滞留、政治小说的影响以及引笑话入小说的倾向”三个角度展开论述[6]148。陈平原没有纠缠于“谴责”与“讽刺”两种类型的的价值判断,而追溯其各自的存在根源和文化内涵,无疑其研究给人启迪。但其对谴责小说创作主体文化心理分析的缺失及对“谴责”背后诗性精神的忽视又是促使谴责小说研究深入的关键所在。
一直以来,港、台及许多国外学者都保持着对晚清谴责小说的关注。从类型学批评模式看,台湾的孟瑶在她的《中国小说史》、林瑞明在《晚清谴责小说的历史意义》中对谴责小说的类型界定都沿用了鲁迅的说法。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在《晚清小说概观》一文中,将谴责小说界定为“写实主义的社会小说”,与同期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小说”和“娱乐小说”相区分[7]。但这些类型研究大都从题材入手,忽视文本的语体特征,无实质突破。韩国学者吴淳邦的《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和朴捧淳的博士论文《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艺术研究》倒值得关注。二人都把谴责小说归限于讽刺小说类别中,着力对“讽刺”概念进行了系统全面地梳理,并将它提升为一种文体。尤其是吴淳邦的论著严谨细致地考证了研究对象的具体范围,将之归结为九部作品。但他们仍简单地将晚清谴责小说等同于传统的讽刺小说,未能揭示出谴责小说的独特审美属性和文化精神。
类型学批评模式确立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历史个性,使之从晚清小说的整体中凸现出自己独特的体裁特征和艺术规范,并强调了与传统文学的历史渊源,是一种体裁诗学的研究范式。只是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大多从题材内容界定其类型特质,尤其对其语言风格阐释不够。
二、传统社会学批评模式
这种批评模式受传统文学社会反映论影响,曾长时间成为国内谴责小说的主流研究模式。它既有整体研究,又兼及单篇作品,着重从外部社会历史环境中揭示这类小说的形成原因、主题特征和思想意义。具体来看,晚清谴责小说传统社会学批评模式体系纳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外部分析。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第一次对谴责小说作了较为全面的社会学分析。他认为谴责小说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生活,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抨击社会与政府的工具,“其命意在匡世”,有着充分的现实意义。鲁迅的分析奠定了谴责小说的研究基调。胡适在《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更是把谴责小说称之为“社会小说”。在《官场现形记序》中,他肯定了该书在暴露晚清官场方面的史料价值。但胡适过分强调了谴责小说的艺术缺陷,对其思想意义,除指出它具有对社会现实的“讽刺的作用”外,没有更深入的论述。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胡适等人说谴责小说的结构形式“都是学《儒林外史》”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论断。阿英从外在的社会因素补充了两点,即新闻事业的出现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无疑。阿英的论述较为全面客观。
第二,政治工具论分析。建国以后的三十年内,对于谴责小说的内容特点,北京大学《中国小说史稿》(第16章第1节)、《中国文学史》(第9编第4章第1节)、复旦大学《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第3章第1节)都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们归结为:紧密配合政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以及暴露批判当时的丑恶的社会现实。对于谴责小说的总体评价,随着越来越浓的政治气候的影响,除了阿英、时萌和向儒等写的少数几篇文章给谴责小说较高的评价外,其余研究都对其大力鞭笞。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章培恒1964年发表于《学术月刊》的《论晚清谴责小说的思想倾向》、1966年江东阳发表于《光明日报》的《论晚清谴责小说中的揭露和谴责》等。政治斗争的干预使这一时期的研究没有什么突破。
第三,社会文化的历史分析。这一阶段最值得注意的一篇论文是林岗的《官场与民俗——谴责小说研究》[8]。该文第一次把晚清谴责小说中的批判精神与前代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作了认真的比较。文章把中国古代文学中批判现实的创作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儒林外史》以前,以杜甫、白居易及元杂剧等作家作品为代表。批判中渗透着强烈的感伤情绪,批判现实的态度有所保留。《儒林外史》可谓第二阶段。吴敬梓感受到时代氛围的最新变化,把政治批判和道德谴责的文学创作推向新的高度。谴责小说的群体出现是批判文学新的标志,它的批判重点是官场和官僚们,其批判深度已达到传统观念所允许的极限,是对以往批判文学“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突破。这篇文章视角新颖,点出了谴责小说批判精神的特点,但仍是社会学的外部分析,难以深入到作家的文化心理及文本形式,削弱了理论的深度。
第四,社会心理学研究。相比较于大陆学者,台湾学者则更重视从创作主体的社会心理来探讨谴责小说的主题和思想意义。林瑞明的《谴责小说——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实质收获》一文和专著《晚清谴责小说的历史意义》[9] 的重点都是对四大名作的考察。他指出,这些小说的作者处在新旧思想激荡的转型期,写其阅历,以抒其郁闷之情,抒发感慨,表达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有着特殊的进步意义。孟瑶在《中国小说史》中认为谴责小说思想境界不高,因为其作者身处危急时刻多满怀悲愤之情进行创作,缺少“冷静的距离”,没有反映出“现实的永恒处”,只是对当世的一味谩骂。
国外学者也有此类研究。他们比较重视谴责小说中的吴趼人和刘鹗的作品。代表性的如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试论〈老残游记〉》,阐释了作者刘鹗的“大同和睦”的思想世界观[10]。麦生登美江的《吴趼人》着重论述了吴趼人的思想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哈罗德·谢迪克在《老残游记》英译本前言中揭示出作者刘鹗的“尊重人类自然愿望”的道德观和“反对极端教条与暴力革命”的政治观[7]。这些研究以哲学思想作为背景,观点新颖而深刻,但大都离开文本的具体语境,强调作家的社会思想经验,稍显玄虚。
传统社会学模式在谴责小说的研究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叙说了谴责小说基本容貌,使它走进民众。很多社会学的资料分析翔实可信。只是这种研究极易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破坏了研究的客观公正性,而且与文本疏离,艺术审美性揭示不够。
三、叙事学批评模式
这是一种借用叙事学理论对文本内部作具体解读的研究模式,可分为中国叙事学研究模式和西方叙事学研究模式。中国叙事学研究模式主要从结构安排、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等方面对谴责小说作些随笔性的、直观性的局部揭示,主要体现为传统的作品艺术形式的审美分析,常常点到为止,不够系统深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对《官场现形记》的结构分析作了点评,“头绪既繁,角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篇,即千篇一律。”而对于《孽海花》则评价为“结构工巧,文采斐然”。
建国以后很多学者大多把目光投注到谴责小说的主题意义等思想评价,只是有少数论文提及到它的艺术结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祖献在《论谴责小说的产生及其发展》中指出,《官场现形记》无中心人物、故事,吴趼人和刘鹗的作品已有了中心人物,结构渐趋紧凑;到了《孽海花》,结构进一步改进,改变了谴责小说无主干的松散结构。可以看出,上述研究对谴责小说的形式结构等艺术价值从整体上都评价不高。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分析。
真正从叙事学视角研究的代表是当代学者杨义和陈平原。在《中国叙事学》中,杨义在阐释其中国小说的叙述视角理论时,对《孽海花》作了例证分析。他认为,《孽海花》在叙事中有时采用“全知视角内含着某些流动的角色视角”,即虽有呈现式的全知视角,但流动的角色视角乃是构成本文的呈现式的基础。在论述叙事聚焦问题时,又采用了《老残游记》中的一些片断来分析。如他认为第二回中,老残游千佛山的描写是一种“聚焦于‘有’”,即聚焦中已渗透着人的感情趣味和价值选择;而第一回白妞演唱的描写是“聚焦于‘无’”,即达到了一种充满悟性的幻觉境界,是“有意味的空白”[11]230。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集中探讨了中国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方面的转换,理论内涵深厚,但较少涉及谴责小说的文本分析。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则具体分析了晚清小说,尤其是谴责小说的叙事特征。他们的研究吸收了国外的新鲜理论,结合对中国小说的自身领悟理解,使人耳目一新。
随着西方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起以来,由于它将注意力从传统的外部研究转到内部研究,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已成为西方理论界解读文本的重要工具。于是,一批对中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的外国学者纷纷利用这一理论解读中国的叙事作品,包括晚清的谴责小说。其中的代表作有捷克的米列娜主编的《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12]、美国学者韩南的作品集《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13] 以及捷克的普实克论文《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小说叙述者作用的变化》等。米列娜的著作中收集了她和她的学生们关于晚清小说的叙事研究论作。如米列娜在《晚清小说情节结构的类型研究》中通过“串联”类型原则和语义分析原则来描述晚清小说的三种情节结构:线式情节小说、故事组小说和单一情节小说,其中前两类都与谴责小说有关。根据分析,她表明晚清小说(包括谴责小说)“是按照特殊的统一原则组织的”,“应该摒弃以往认为中国传统小说结构混乱的看法”。在《晚清小说的叙事模式》一文中,她从叙事方式分析了《老残游记》、《孽海花》,把这两部作品归结为“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方式”,而《官场现形记》和《文明小史》属于“第三人称评述叙事方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是“第一人称个人叙事方式”。由此,她得出结论:“中国现代小说中范围广阔的个人叙事风格是晚清小说中已经开始的这些趋势的继续。”韩南在其专著中对吴趼人的小说从叙事者角度进行探讨,其目的在于考察这些小说中的叙事者或意识中心,并解释它们是怎样为吴趼人的社会批判的特殊目的服务的。在他看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海游骖录》都有一个天真质朴的主人公,这样的主人公不得不从这个世界中以各种方式获得教训,从这过程中,很多讽刺批判的信息就可以很自然地传达给读者。另外如普实克的论文着重探讨了四大谴责小说中叙述者的安排对小说思想意义、人物塑造、情节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全面来看,虽然西方学者极力阐发谴责小说的叙事内涵,但单纯地把它当成冷冰冰的客观物来分解,在科学化、理性化的同时也导致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四、文化学批评模式
这是一种从文化学视角全方位地阐发晚清谴责小说的思想内涵和人文精神的研究模式。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研究者从现代性的视野去挖掘谴责小说的文化意义。当代学者王一川在其专著《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中,论述生活世界与现代性体验关系及现代性体验类型时指出《文明小史》对中国现代性发生时段的社会转型状况作了全面而生动的描绘,几乎涉及了包括社会政治、精神情感、物质生活等诸多层面,“可谓一幅处于古典型与现代性之交的中国文化的‘清明上河图’”。对于《老残游记》,王一川教授突出了小说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老残为什么一方面对时局充满伤悲感慨,另一方面又拥有观赏美妙风景的闲情逸致?通过细致而深入的分析研究,他认为,这个矛盾正揭示了老残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一种“回瞥式”现代性体验,而这种体验就是《老残游记》中所生发出的文化精神之一[14]。王一川对两篇谴责小说的现代性文化揭示紧紧抓住“体验”这一文学性审美特征,见解独到精辟,令人信服。国外学者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王德威和哈佛大学的李欧梵在多篇论文中更是力挺晚清小说(包括谴责小说)的现代性精神品格。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等文章中[15],王德威通过对包括谴责小说在内的多部晚清小说解读,认为这些作品在写作方式、表现内容及精神理念中表现出极为丰富的“现代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往往不被容纳进后设的现代性标准模式中。在他看来。晚清小说“才是作家追求、发掘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指标”。李欧梵在《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16] 等文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国外二位学者观点新颖,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学理念的一种叛逆感。但理论过于抽象,主观夸饰性明显。
王德威在《“谴责”以外的喧嚣》[17] 一文中对谴责小说尖酸泼辣的讽刺现象作了富有新意的阐释。他以“闹剧”模式来重新定义晚清谴责小说的文化意义。他认为这种“闹剧”模式是俄国批评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精神的一种体现。这样的闹剧性作品所汇集的是一股桀骜不驯的创作力量,而且于五四以后如老舍、张天翼的小说中显现出来。可以看出,文化研究者在关注新旧观念杂糅的新小说给今人留下晚清社会史料意义的同时,更多去挖掘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一旦有与之相应的文化理论,便迫不及待地拿来,与之匹配。从狂欢化理论揭示谴责小说的文化精神,与现代性视角相比,这一研究紧扣住谴责小说强烈讽刺的语体特色和情节模式,抓住了谴责小说的独特写作方式,但又有削足适履之嫌。毕竟在话语情节相似的背后,谴责小说在文化精神层面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还有很大的差异。
文化学研究模式拓展了谴责小说的精神空间,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谴责小说的研究价值。但如若缺乏细致深入的文本解读,容易流于抽象理论和精神概念的粘贴。
从类型学批评、传统社会学批评再到叙事学批评、文化学批评,晚清谴责小说的研究见证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视角变迁。无论哪一种理论视角,都彰显了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和文学价值追求,也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文学理论并非只是理论的抽象概括和空洞的玄思,而应植根于文学创作的实践。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理论必须与文学文本相结合,在文本中感受理论,在理论的视角下去体验作品。
收稿日期:2008-02-15
标签:现代性论文;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论文; 小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小说史论文; 文学论文; 官场现形记论文; 晚清论文; 文化论文;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儒林外史论文; 老残游记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叙事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