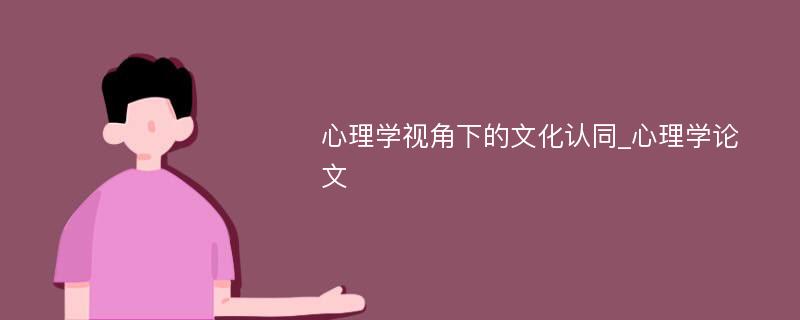
心理学视野中的文化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视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4)01-0068-08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国际间地区间交流的不断深入,移民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也很少有单一民族国家的存在。现代性和传统性、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而文化是贯穿其中的核心要素。虽然对文化的定义还存在争议,但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文化影响个体的认知方式和行为表现(彭凯平,王伊兰,2009)。面对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群接触的不断深入,如何维护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能保持和增进国家认同,是摆在各个国家面前的首要任务之一(韩震,2010)。因此,文化认同逐渐成为多学科交叉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者或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对文化认同进行宏观分析,或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视野对文化认同进行个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体现出不同领域的学者对文化认同问题多维度、多方向和多层次的思考。但从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以思辨和理论探讨为主,多是从“应该”的维度进行泛论性阐述,缺乏由数据支撑的实证性支持。
心理学一直强调,外部的客观现实必须通过个体内部的心理活动才具有价值,对文化认同的研究也不例外。心理学家更擅长选择核心的变量,设计严谨的实验来考察某一群体文化认同的现象,建立理论模型,从而探究原因,预测行为,为理解文化认同的本质提供实证支持。目前,文化认同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在移民现象比较普遍的国家中进行,研究对象主要是移民、难民等。第二,在有多民族存在的单一国家中进行,研究对象主要是不同的少数民族。尽管第一类研究较为普遍,但很多心理学家也开始关注第二类研究,因为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的频繁接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融合,进而引发了研究者的兴趣。我国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条件造就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为心理学家研究文化认同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因此,本文旨在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文化认同的相关理论和影响文化认同的因素。从理论上讲,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利于理解文化认同的本质,为拓展并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认同理论奠定基础;从实践上讲,也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使其全面发展、良好适应。
一、文化认同的概念和结构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当今心理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但是对于这个概念,不同领域的学者还没有形成共识。国外对文化认同的理解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强调文化认同的个体层面,如文化认同是与一个文化族群相关的个体的自我主观意识(班克斯,2010),是处于某一文化群体中的个体对自我知觉和自我定义的反映(Schwartz,Montgomery,& Briones,2006)。而另一种则关注文化认同的社会层面,如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个方面,是个体与文化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Padilla & Perez,2003);是个体对特定民族和特定国家的归属感和心理承诺,具体包括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Phinney,1990)。我国学者认为,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某种文化的认同程度,具体是个体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与某种文化中多数成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相同或相一致的程度(郑雪,王磊,2005);是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陈世联,刘云艳,2006);或者是对不同文化特征的接纳和认可态度,具体包含认知、情感及行为等三个部分(雍琳,万明刚,2003)。
可见,国内外学者对文化认同的理解已经形成一些共识。第一,从宏观上来说,文化认同由两个部分构成,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即民族认同和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即国家认同。第二,从微观上来说,文化认同具有多维的特征,它包含对特定群体的态度、认知、情感等内部心理过程。不论研究者从哪个角度来定义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建构都会落实到个体的心理层面。它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建构自我的过程及作为群体中的个体社会意义的体现(Berry,1999)。我们也认为,文化认同既存在于社会层面,也存在于个体层面,它是个体在不同的情境和群体中进行文化态度决策和自我定位,从而进行社会适应的过程。
国外很多研究都将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视为同义,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分并不清晰。Phinney等人(2001a)认为,文化认同既包括民族认同也包含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比民族认同的内容更广,更具有包容力和概括性。崔新建(2004)指出,虽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属于不同的层次,但两者都是以文化为基础的聚合体,文化认同是两者的本质内容,也是两者的核心纽带。此外,对不同的群体来说,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含义也略有差异。对移民群体来说,民族认同是指对移民前国家或民族的认同,国家认同则是指对当前移民国家的认同。对单一国家内的少数民族群体来说,民族认同是指对本民族的认同,而国家认同是指对自己所在国家的认同。
尽管文化认同包含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但总体来说民族认同被广泛而大量地研究,国家认同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且两者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聚焦的话题之一。传统的单维模型认为,民族认同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国家认同的水平,反之亦然。近年来更多的研究者都赞同双维模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互独立,个体能同时建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提升不会削弱国家认同(Bourhis et al.,1997)。虽然在理论上两者相互独立,但在不同国家对不同群体的实证研究结果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正相关(Berry et al.,2006)、负相关(Birman & Trickett,2001)和不相关(Nesdale,2002)。我国学者对藏族(王亚鹏,2003),苗族、壮族以及彝族(史慧颖,2007)和维吾尔族(王嘉毅,常宝宁,丁克贤,2008)等的研究普遍支持“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呈正相关”的观点。
二、文化认同的相关理论
在心理学背景下,文化认同的多数研究是在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等领域中展开的。尽管这三种视角在对文化认同的理解上有重合的地方,但他们强调的重点却有所差异。
(一)基于发展心理学视角的文化认同理论
发展心理学家一直关注个体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建构过程。文化认同的发展理论可以追溯到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或者同一性理论。埃里克森认为,民族认同是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的一种认同形式,对青春期个体的自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Erikson,1968)。在同一性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行为探索和情感承诺两个维度,玛西亚提出了民族认同状态模型(Marcia,1980)。她把认同划分为四种:分散(既没有行为探索也没有情感承诺)、排斥(没有行为探索但有情感承诺)、延缓(有行为探索但没有情感承诺)、成熟(既有行为探索又有情感承诺)。尽管这两种理论或模型都试图强调积极认同的作用,但它们没有体现出个体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和动态变化。
Phinney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认同发展的三阶段模型(Phinney & Ong,2007):未验证的民族认同阶段、民族认同的探索阶段及民族认同的形成阶段。在“未验证的民族认同阶段”,个体并不知道民族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对民族认同的感知大多源自父母、社区或者更大的社会群体。在“民族认同的探索阶段”,个体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积极参与本民族的文化活动,从而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到了“民族认同的形成阶段”,个体对本民族的知识有了更深入的掌握,他们更自信、也更愿意接纳自己的民族身份。虽然这三个阶段是用概念的形式予以表达,但它们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
已有研究表明,文化认同的建立始于儿童期。此外,个体通常会在青春期前期对自己的民族进行探索,并在青春期晚期,大约17岁左右,形成较为稳定的民族认同(Pahl & Way,2006; Whitesell et al.,2006)。即使到了成年期,个体也不会停止对本民族进行探索的过程。我国的研究也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少数民族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程度逐渐提高,对民族文化的识别能力也逐渐增强(陈世联,刘云艳,2006)。但这个过程复杂多样,并有巨大的个体差异。秦向荣(2005)发现,11岁青少年民族认同的水平最高,然后呈下降趋势,20岁时有所提高。而维吾尔族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水平随年级的升高呈现递增趋势,民族认同则随着年级的升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王嘉毅,常宝宁,丁克贤,2008)。
可以看出,个体文化认同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充满着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但从总体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儿童青少年能够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化认同水平,这主要和他们日益增长的认知能力密不可分。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目前对文化认同研究的新趋势是将文化差异和发展过程结合起来(Phinney,2010)。Oppedal(2006)就指出,儿童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的发展问题。这是因为,移民或少数民族个体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适应时,既要面对文化差异的挑战,又要面对个体的发展任务,两者紧紧交织地在一起,很难区分出哪些是文化认同过程,哪些是个体的发展过程。受到生态系统理论(戴蒙,勒纳,2009)的启发,一些学者试图将不同的领域进行整合,从而建立解释力更强的模型。文化认同、自我及家庭关系等个体必须经历的发展任务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这些内容在个体正常的发展变化中因为文化适应的因素而变得格外复杂,同时这也给心理学家开展实证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Sam和Berry(2010)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应对发展任务或者文化适应的体验影响其完成发展任务时,这些移民或者少数民族儿童青少年能否被看成普通、正常的群体,而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二)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的文化认同理论
文化认同也是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中社会认同理论是研究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社会认同理论有三个核心内容:第一,动机的作用,如个体有获取积极社会认同的需要;第二,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地位差异;第三,作为独立的个体或某个群体中的成员,个人如何解决认同问题(Turnet & Reynolds,2001)。人天生有种分类的需要,倾向于将自己划分到某一群体中,与他人区别开来,并用这种群体中的成员资格来建构身份,从而获得自尊、提高认知安全感、满足归属感和个性发展的需要(Tajfel & Turner,1986)。民族是一种天然、重要的分类,如果移民或少数民族个体对自己的民族有积极评价,就会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建立安全的民族认同,从而获得高水平的自尊。因此,社会认同理论非常强调群体分类和自尊的关系。已有研究也支持“强烈的民族认同和自尊呈正相关”的结论(Liebkind,2006)。此外,对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的评价、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自尊,进而影响他们的认同状态。
社会认同理论还认为,生活在价值观、规范等差异很大的文化背景中时,个体文化认同的建构和发展就会面临挑战。因此如何在这种情境中作出选择,更好地进行社会适应就成为个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移民或者少数民族群体能学习当地的语言,参加当地的社会活动,增强对移民国家的文化认同,他们就能更好地进行社会适应。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可能并不能帮助他们获取有效的自我发展的能力。随着在移民国家居住时间的增加,个体对移民国家的文化认同逐渐提高而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逐渐下降(Tartakovsky,2009)。
社会认同理论在理解移民或者少数民族群体文化认同的模式方面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根据个体对自己所在群体的地位来预测个体或者群体的行为。但该理论被认为有很强的种族优越感。首先,它只强调了移民或者少数民族群体在文化适应中的单一选择,即放弃本民族文化,融入主流文化,而忽视了他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已有研究表明,在移民国家居住时间的长短和移民的文化认同关系不大,即使这些人有丰富的生活技能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但这也绝非以牺牲他们的民族认同为代价(Jasinskaja-Lahti & Liebkind,1999)。其次,尽管不同群体间的分类和比较会影响个体的自尊,但Phinney等人(2001a)则认为,如果这些消极态度和评价没有内化到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的内心深处,就不会对他们的自尊产生不良影响。
(三)基于跨文化心理学视角的文化认同理论
在跨文化心理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文化适应理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指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群体及成员之间持续的接触所引起的文化和心理双方面的变化过程(Berry et al.,2006),包括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群体层面的文化适应主要有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等内容的改变。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是指个体价值观、态度等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从而对新环境能够最终适应的过程(Berry,2005)。心理学家更为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现象。尽管在文化适应中接触的双方都会发生变化,但Berry(2005)认为,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所面临的挑战更大。他们不仅要学习新技能、新知识,从行为上应对不同文化规范的要求,进行社会适应,同时也要对不同文化进行甄别从而在心理上形成归属感。可以说,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传统的单维模型表明,移民或者少数民族群体对一种文化的适应就会对另一种文化不适应。而文化适应的目的就是同化,即大家都说同一种语言,持有相似的价值观和态度。但目前的两维模型对文化适应的理解更为有效(Berry,2005),即对本民族文化的适应并不会导致对主流文化的不适应,二者是独立的。这就引发了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第一,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价值吗?第二,和其他民族接触有意义吗?对于这两个问题,有四种可能的答案:整合(对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都很适应)、边缘化(对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都不适应)、分离(不适应主流文化而适应本民族文化)和同化(适应主流文化而不适应本民族文化)。这四种答案表明了个体在文化适应中所持的不同态度及采用的不同策略。大量研究都表明,整合是移民或少数民族个体选择最多的策略,也是一种良好的适应手段,而边缘化是则是个体选择最少的策略,同时也是一种较为不良的适应手段(Berry et al.,2006)。
文化适应理论为理解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对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个体也有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等四种态度。整合是对民族和国家都很认同,分离是认同本民族而不认同国家,同化是认同国家而不认同本民族,边缘化是对本民族和国家都不认同。
由于文化适应的过程复杂多样,因此并非所有的个体都能采用相同的策略来经历这些过程,即使是来自同一文化背景中的成员。首先,个体会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使用不同的策略。如,进入学校后,先会采用同化策略,接着使用分离策略,最后可能用到了边缘化的手段。其次,个体会根据不同的情境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如在家庭中使用分离策略,在工作中使用同化策略,在学校里使用整合策略。相对于学校和单位等公共场合,个体在家庭等私人场合中有更高水平的民族认同。可见,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会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不断尝试各种策略来应对环境所提出的要求,从而形成整合的文化认同状态。
尽管很多文化认同的研究是在文化适应的背景下展开的,但二者的关系却存在着争议: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是否考察了相同的内容?Phinney和Ong(2007)认为,文化认同是文化适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适应比文化认同所包含的内容更多,范围更广。此外,文化认同更多地强调个体的内心情感、体验和态度,更具有内在性。那些对本民族有强烈归属感的个体可能很少参加本民族的文化活动,而那些参与本民族活动的个体可能并没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因此,文化认同可能是一种独立于行为而存在的内部结构,外在的行为表现应放在文化适应的领域去研究,这样才能区分出文化认同本身的意义和相关行为的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研究者对文化认同的考察会有不同的理论取向,但却达成以下共识: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或者更大社会的情境因素,个体会和所处的环境不断磨合、碰撞,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化认同状态,最终达到良好适应的目的。
三、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
影响文化认同的因素有很多,如社会、文化、政治、历史和经济等宏观外部因素。移民或少数民族的人数、居住范围、所享受的权利和资源以及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等因素对文化认同也都有不同的意义。本文则聚焦在与个体层面相关的、影响文化认同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方面。
(一)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口统计学指标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话题,这包括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通常,女性似乎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比起男性,她们有更高水平的民族认同,但这个结论在不同国家、不同移民群体和不同民族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Phinney,1990; Berry et al.,2006)。年龄是影响文化认同的重要指标,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文化认同的水平也在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在文化认同中的作用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主要问题。Syed等人(2007)的研究表明,来自经济地位较低家庭中的移民学生在一年的大学生活中强化了自己的民族认同,而来自较高经济水平家庭中的移民学生既没有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行更多的探索,也没有区分民族和社会阶层,所以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到主流校园文化中去。我国学者也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李志英等,2008)。来自收入较低家庭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比来自收入较高家庭中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更为重视、赞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水平高间接地增加了这些学生对外交流的机会,因而能对本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形成整合的文化认同。
(二)文化差异
通常来说,两种文化的差异越大,个体文化适应的过程就越困难,进而影响其文化认同。语言就是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也是文化认同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语言和文化认同的关系一直没有定论。国外以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为对象,在考察语言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对文化认同有积极的影响作用(Phinney et al.,2001b)。Imbens-Bailey(1996)对亚美尼亚裔美国儿童的研究表明,懂得本民族语言和英语的双语儿童比只懂得英语的单语儿童有更高水平的民族认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语言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不大(EdWards & Chisholm,1987),即使本民族的语言消失了,个体依然会有较高水平的民族认同。
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基本上持以上两种观点。巫达(2008)考察了彝族的语言发展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本民族的语言使用和身份认同没有关系,那些不会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个体依然有较高水平的民族认同。马戎(2004)也认为,中国的回族、满族虽然已经使用了汉语,但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但王远新(2009)对青海同仁土族的研究发现,使用不同语言的土族群体之间相互认同度不高,民族认同趋于弱化。祖力亚提·司马义(2009)对新疆维吾尔族“民考汉”群体的研究发现,语言可以形成个体对两种文化的双重认同。万明刚和王亚鹏(2004)、雍琳和万明刚(2003)对藏族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学习汉语的时间、学习汉语的方式,如双语教学和汉语教学等与语言学习相关的变量对藏族大学生的藏、汉文化认同都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不同的结论是因为,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历史不尽相同、各种语言在现代社会中的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存在差异、各国所实施的语言政策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此外,研究者所采用方法、手段及选取对象的不同也使语言在文化认同的作用出现了以上这两种结果。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可以在更多不同的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中进行,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语言在文化认同中的意义。
(三)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应对压力、提高适应的重要资源,主要包括父母和同伴。首先,父母能够对个体的文化认同产生影响。个体的民族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父母那里学到的。对那些文化认同水平高的儿童的父母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父母都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他们在努力培养自己的孩子,使其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并发展得更好(Ward,Bochner,& Furnham,2001)。我国学者也发现,父母的教育水平(万明钢,王亚鹏,2004;秦向荣,2005)、民族身份(万明钢,王亚鹏,2004)等因素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有重要的关系。但从发展的趋势来看,父母对移民或少数民族儿童青少年文化认同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对不同文化的学习和掌握程度远远超过他们的父母,因此就不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取全面的帮助(Schwartz,Montgomery,& Briones,2006)。在这种情况下,同伴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友谊和文化认同有相关关系,那些和本民族同伴建立友谊关系的青少年有更高水平的民族认同(Phinney et al.,2001b)。国内的研究也表明,汉族朋友的数量是影响藏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万明钢,王亚鹏,2004)。
综上所述,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文化差异及社会支持等因素在个体的文化认同中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并非是单独起作用,它们往往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对个体文化认同的建构和发展产生影响。
四、对文化认同研究的反思
尽管目前国内外关于文化认同的心理学研究很多,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研究态势,但有些问题还需要不断完善。在理论方面,首先,研究者对文化认同的理解不同,这就造成了在研究设计、进而在研究结论上的差异。其次,文化认同所依赖的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及跨文化心理学等理论背景既有相似点又有差异点,但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背景下诞生的,关注的主要对象是移民,因此在解释我国少数民族群体文化认同问题时需要区别对待。此外,对于这些理论本身的不足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如文化适应理论与族群接触的关系是什么?其中有很多交互作用都需要进一步的梳理和挖掘。这就需要各国研究者一方面要检验理论的普适性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具体的国情和研究对象,拓展并完善相关理论,从本土现象中归纳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认同原理,体现出理论发展的创新性。例如,我国香港学者以香港人的双文化认同为研究内容,验证了社会认同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增补了原先理论中的一些不足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赵志裕,温静,谭俭邦,2005)。最后,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一些学者对于文化认同理论的发展又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第一,全球化使我们每个人在心理和行为上更为一致还是更为不同?第二,是否我们每个人都能形成一种全球认同(global identity),而不论我们身处何方(Sam & Berry,2010)?这些都是值得研究者不断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研究方法方面,多数文化认同的研究都采用问卷法来探索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文化认同是个发展的过程,这就需要心理学家更多地使用纵向研究来考察文化认同现象,尽管它比较费时、费力,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去作为的理由。纵向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认同的变化过程、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从而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开展实践研究,促使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更好地进行社会适应。虽然我们呼吁更多的纵向研究,但并非完全否定了横断研究的价值。跨地区、跨民族的对比研究是当前更为需要的研究类型,因为它能使研究者更为有效地掌握文化认同的普遍规律和特殊差异。第三,加大质性方法的使用。Chirkov(2009)就认为,我们无法在量化研究中看到“文化”的作用。因此,用参与观察、开放式访谈、聚焦小组和生活叙述法等质性手段来考察民族价值观、民族传统等文化现象可能更为合适。此外,这些分析又可以在家庭、学校等不同场合中进行,从而能更深入地了解个体、环境及两者的交互作用。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始使用神经科学手段,如fMRI,ERP,TMS,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中自我和社会加工过程并取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结论(Hong et al.,2010)。当然无论选取哪种方法,目的都是为了引发出更多有意义的关于文化认同的想法,促进理论的发展,为更有效地理解文化认同提供支持。
[收稿日期]2013-10-28
标签:心理学论文; 文化认同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群体心理学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移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