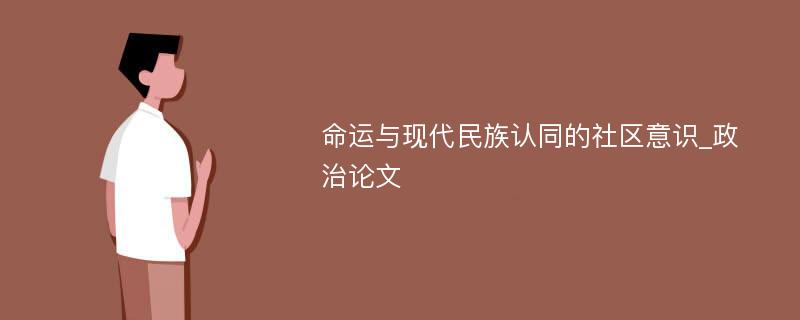
命运共同体意识与现代国家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意识论文,命运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8-0066-08 不管现代政治学教科书中如何强调地方性社群、阶级(阶层)或“普遍公民身份”对于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性,但仍不可否认的是,民族(ethnic groups)①依然是现代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建构和维护国家认同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以地域、语言、传统、宗教或血缘等为标识的文化共同体,民族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是那个“主宰我们的生命、建构我们的政治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之一[1]。作为一种历史生成的文化共同体,民族的强大感召力来自对共同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是源于外部的社会逻辑,也不是源于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的分析”[2]5-6,而是源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内在共同理解,这也是那些试图看似合理的用经济发展思维解决族群国家认同问题的方式,在实践中却往往难以奏效的主要原因。正如在多元族群社会中,城镇可以通过集市将附近的人们聚集起来,但却无法通过经济和商业的繁荣,消解族群间文化的多样性一样。在当代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确存在着认同张力,这种张力一经与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就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带来族际冲突,危及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做到既支持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体现国家对少数族群作为差异性文化共同体的尊重、包容和团结,又能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危及国家的同一性,克服共同体内部民族主义情绪在煽动民族情感、制造民族疏离、破坏社会团结甚至阻碍国家认同的偏激性行动。笔者认为共同体意识对于形成和建构人们的身份认同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唯有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创建一种基于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族群联系纽带,才能较好地塑造、巩固和强化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为此,本文将通过阐释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进一步探讨多民族国家如何塑造、巩固和强化现代国家认同。 一、“共同体意识”对认同建构的意义 共同体(community)是伴随着18世纪以来西欧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变化,思想家为理解城市公共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特别是因工业化、城市化所形成的陌生群体道德感和公共精神缺失而建构出来的一种分析性概念。早期对共同体的思考是建立在“城市与乡村对立”[3]基础之上的,认为共同体是一种“以亲密情感、道德承诺、社会凝聚力以及长时间延续存在的”[4]人类集合体。这种集合体区别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偶然性的、松散的、可选择的和出于便利考虑而达成理性同意的人类聚合体。②在当代日常生活中,共同体也是一个被广泛嵌入不同语境使用的复杂概念体系,人们总是在不同场合随意地、甚至“含糊而空洞”③地使用它,如“科学共同体”“产业共同体”,甚至“创意共同体”等等。④这种在语义上对“共同体”与“聚合体”不加区分地使用,使得原本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蕴含丰富内容的共同体概念,不仅在内涵上被简化,而且使其所附着的价值和意义也被部分侵蚀掉。本文所指的共同体,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严格定义的共同体,是指那种经历过“持久而真正的共同生活”、具有传统的自然感情、紧密相连的人类交往有机集合体。说共同体是一种紧密相连的人类交往有机集合体,是因为成员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把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和目标当作自我生存的价值与目标[5]54。杜尔凯姆认为,这些准则一旦被削弱或消解,就会引发混乱,引发孤独、隔阂甚至失去意义的感觉[6]。所以,共同体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本质上不是个体的自我创造、自我独白或自我承认,而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交往体验和发现。鲍曼指出,在人们的心中,“置身于共同体”总是美好的,尤其当我们提及自我所属的共同体时,不时会呈现出那种萦绕内心的无限荣耀、美好与舒适的景象。共同体的价值就在于它不仅能为我们遮风挡雨,还能化解我们周遭的不安与焦虑:在这里,我们不用时刻绷紧审视和警惕的神经,想象出那陌生的潜伏危机;在这里,不仅有我们熟悉的历史记忆,而且还有我们共同的心愿指引,即便争吵也释放出应有的善意;在这里,我们不仅相互依靠、相互信任,而且也没有人会因为我们的失误而幸灾乐祸,人们总是满怀同情地倾听、相互坦诚地谅解,没有怨恨与报复,只有真诚支持与帮助[2]2-3。 从鲍曼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出那种由共同体铸就的共同体意识,是人们从观念上把共同体视为一个历史生成、不可分割的总体,一个具有自主价值的人类群体,一个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精神家园。共同体本身就蕴含着一体化、相互承认、确定性和保护等方面的价值。总体上,不论我们如何阐释共同体,共同体意识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基于历史的相互承认和基于主观感觉的紧密联系性。共同体意识对形成和建构人们的身份认同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共同体基于历史的相互承认,有利于揭示和塑造成员的身份构成。在揭示和塑造每个个体的构成属性上,共同体的力量要远超过单纯的社会聚合体。“共同体所描述的,不只是他们作为公民拥有什么,还包括他们是什么;不是他们所选择的一种关系,而是他们发现的一种依附;不只是一种属性,还是他们身份认同的构成部分”[7]。正是在与他者(其他共同体的成员)的交往过程中,人们发现了自身依附于共同体的身份特征,这些鲜明的特征构成了人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每个人的国家认同,从表面看是对“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的自我回答,实质上却是个体对构成其群体生活的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的判断,“除非我们与某个(或多个)共同体建立联系”,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的命运如何?”[8]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家认同就是个体对所属政治共同体(国家)的一种稳定的归属感。这种稳定的归属感,不是单纯基于个体的法律身份或出生地,而是基于形成其认同感的生活经历、自己视之为与共同体相关联的本质上共通性和一致性的自我识别(self-identification)。自我识别的要素,包括诸如语言、宗教、饮食、音乐、文化价值观等等。这种识别,既是一种基于他者承认的自我识别,更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内在化识别,因为这样,它才与普遍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存在着微妙的差别。普遍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反映的是生活和交往的客观社会关系。一个人的公民身份与其说是自己选择的,倒不如说是由于自己身处的某个境地,被社会的整体网络定格的;而基于他者承认的自我识别,更多地意味着对自己所处共同体的归属性认同想象。一个人的公民身份通过法律规定就可以形成;而基于承认的自我识别,则需要借助个体对共同体想象的内在化才能生成[9]。总之,个体内在化的自我识别和认同想象是揭示和塑造共同体成员身份构成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共同体基于主观感觉的紧密联系性,有利于成员的内部团结,焕发个体对集体的忠诚感和认同感。共同体内部的紧密联系性,即共同体成员生活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10],形成“在一起”的生存状态。滕尼斯指出,“在一起”是在“对共同体相互依赖状态彼此确认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共同体富于生命力的心灵和灵魂”[11]。由此看出,基于主观感觉的紧密联系性,是建立在共同体成员相互依赖状态确认基础之上的。这种确认是成员对共同体内部共享要素的确认(共享要素包括土地、历史记忆、生活方式、语言、血缘、传统文化、仪式和制度等等);这种确认不是个体单纯追逐利益的合理算计,而是内部行动者归属于同一共同体的主观感觉。韦伯清晰地指出两者之间差别:共同体的紧密联系性是“主观感觉上的”,“非建立社会关系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基础上的[12]。也就是说,相互依赖的主观性,不是相对客观性而言,而是相对于合理性而言的。滕尼斯将之称为“直接的相互肯定”的“本质意志”,它与“理性化”的社会“选择意志”形成鲜明对比[5]43。这种“主观感觉上的”相互依赖,客观上构成了共同体内部团结和忠诚的源泉,这也是共同体本身可以为个体参与集体行动提供强大动力的原因:一旦政治共同体遭遇困难或面临外部威胁时,每个成员可以根据自己与所属共同体的关系,修正自己对各种行动方案的思考,选择最有利于维护共同体的那种行动方案。成员对共同体基于主观感觉的紧密联系性的把握,体现为共同生活历史所形成的和共同习俗所延续的价值和观念。它的存在,不仅使共同体可以指导成员的个体行动,而且也是当共同体成员发生冲突时内部可以取得一致性解决方案的基础[13]。可以设想,一个缺乏主观紧密联系性的社会,即使引入了民主,也无法带来必要的认同、团结和忠诚。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民主充其量只是为自由争吵带来更大的空间,甚至连长期的争吵都难于持续。民主可以解决发言权的问题,但最终却无法解决共同体的内部价值和观念分歧。一个政治共同体,如果价值和观念分歧都达不成相互理解,民主反映的只会是弥散的共识或意见。现实表明,没有融合、没有理解、没有倾听的社会是可怕的。泰勒指出,失去“在一起”的主观紧密联系性,即使再先进的民主体制也无法成功运转[14]。 总之,在紧密联系的共同体中,每个人“都与他人共享一种认同,与他们一起感受团结:都认为我们亏欠其他人某些特殊的东西,并深信这些东西不能指望其外人以他们的方式来完成”[15]。这种紧密联系性的共同体意识所带来的“守望互助、唇齿相依”的总体忠诚与内部团结,是政治共同体认同建构的基础,有了它,共同体才能避免内部分裂之忧。 二、“认同性危机”与现代国家认同 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做到像今天这样将民族、地区、宗教等不同形式的亚共同体和作为大型政治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种不同类型的亚共同体在有效建构内部认同的同时,也在不同的共同体间制造神话、设置区隔,甚至寻求分离。现实表明,由民族、种族、语言、宗教等等因素所激发的分离主义的认同裂痕,即使在成熟的多民族国家中也屡见不鲜。因此,在现代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的过程中,有效管控“认同性危机”是异常艰难而重要的一步。先有人民对国家的认同,然后才有政权的合法性等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后续问题,这已逐渐成为政治学者的共识。⑤诚然,由于民族主义的泛滥、境外极端势力的诱导或国内民族政策的失误等因素,也会导致国家建设进程中产生新的认同性危机。所谓认同性危机,是指原先认同于部落、地区或其他亚共同体的成员,承认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公民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冲突性危机表现。一般来说,一国之内亚共同体形成更大规模政治共同体认同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会快速或自动地实现,通常会伴随各种摩擦、冲突甚至战争边缘的危机状态。历史经验一再提醒人们,是国家认同建构在前、政权合法性建设在后,而不是相反。那种把国家认同与政权合法性纠葛不清的观念,既不利于正确厘清各种亚共同体(尤其是族裔共同体)的认同意识与现代国家认同的区别,也不利于正确认识和分析现代国家所面临的认同性危机。鉴于文章的主题,笔者将重点分析族裔共同体(民族)与现代国家的内在联系,以厘清民族认同(ethnic group identity)与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区别,分析现代国家认同的聚焦点。 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形式,现代国家就是民族国家。现代国家是一种近代现象,是伴随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族人民反抗教会和君主的专制统治,争取平等、自由、安全和自治的民主运动的产物;在当代,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国家还是广大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产物。现代国家的成长与民族主义不可分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运动,民族主义一开始就与现代国家建构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认同的意义就在于人们可以通过一套由民族主义建构起来的、凝聚民族文化价值的象征和话语体系,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民族是一个整体,并诉诸族裔共同体意识以实现族类政治团结,进而通过集体的力量实现民族独立或民族自治。民族主义为民族认同提供了精致的系统化理论表达,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声称族裔单位应与政治单位相一致,主张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没有民族,就应该创造出一个民族来。正统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民族与现代国家共同成长,现代国家所塑造的民族认同应区别包容和团结政治共同体所有内部族裔,或者称之为国族。总之,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许多国家都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族裔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使国家建构陷于“认同性危机”。 当今世界大部分民族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只有少数国家(如希腊、冰岛、朝鲜、蒙古等)可称之为单一民族(mono-national)国家。单一民族国家不是说这个国家中不存在多民族的构成成分,而是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历史上持续存在的具有民族主义国家建构要求或强烈“内部民族”(nations within)认同意识的族裔共同体。事实上,由于信息化、全球化及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几乎每个国家内部都居住着来自不同民族的公民,他们区别于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的是,这群人从不声称国家某一片领土是本民族长期生活的历史家园,也较少面临多民族国家中狭隘民族主义所焕发的民族同化、民族仇视、民族隔离、民族清洗甚至民族分裂等族群政治冲突。显然,单一民族国家可较好地容纳民族主义者所声称的民族自决权问题,但其内部仍然存有一种特殊而复杂的认同政治冲突,比如对于如何理解本民族的习俗、妇女的地位、宗教信仰,如何行使民族自决权以应对外来移民的流入,如何保护本民族免受外来民族的威胁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刻分歧。这些民族内部的认同分歧,也常常困扰着单一民族国家的政策选择、甚至危及一个国家的内部团结和经济发展。总之,民族和民族国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不论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所有这些涉及认同与承认的政治问题,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即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之间如何融合、生存、维护和发展的问题。 从政治共同体的视角来看,现代国家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共同体而言的。波拉德(Albert Pollard)在论及欧洲社会发展史时,提出三种典型的(predominant type)政治共同体形态:古代是城邦国家(city-state)、中世纪是世俗或教会的普世国家(secular or ecclesiastical world-state),近代以来则是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16]。此外,还有东方专制主义王朝国家(帝国)形式。不同类型的政治共同体在应对国家建构的认同性危机上,其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城邦国家是典型的同质性政治共同体,城邦公民是相对于外邦人和奴隶而言的,其本身就是一个紧密联系的血缘团体,并在语言、宗教和习俗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典型城邦国家都是小型政治共同体,其威胁主要来自于强大邻邦的外部征服,而不是城邦公民的内部认同性危机。普世教会国家是以宗教信仰的力量凝聚不同的族群,因为宗教的强大感召力使族群共同体意识被大大地缩小,人们甚至很少关注族裔共同体的认同建构问题,在普世教会国家模式下,被放大的是世俗权威与教会权威间的冲突,而不是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幅员广阔的东方专制主义帝国则采取了一种分而治之的模式,帝国统治者关心中央权威的存在甚于地方族群的内部治理,帝国有边陲(frontiers)而无边界(borders)[17],身处边陲的族群基本上长期处于一种内部治理的自治状态;相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帝国并没有强烈的主权和领土意识,帝国权威所至,主权和边界就辐射到那里,帝国的权威消弭,主权和边界就会自动萎缩。 现代国家是以主权、领土和人口为明确法律标识的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质是强化国家对主权、领土和人口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国家强化对边界内领土的管辖、中央权威自主性的提升和对地方协调能力的增强等[18]。现代国家建构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国家建构的承认维度,使辖内外所有人都承认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主权和领土的统一性;二是国家建构的能力维度,要使政府权力可以渗透到主权管辖内的所有团体和个人,这种能力体现为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法律的强制能力和社会的协调合作能力等。现代国家认同性危机源于国家建构的承认维度。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认同是政治共同体所有人或团体对国家主权以及由主权延伸的制度和领土的认同。尤其是领土认同的存在,让人们归属于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心理感觉被凸显甚至无限放大。领土认同是人们对国家管控所辖边界的承认,人类天然的群体边界意识,使民族和国家共同体都成了具有认同情感的领土共同体,“领土国家”几乎是现代国家的代名词。在这里,领土(边界)成了聚合人们集体意识、表达集体自治意愿、实现族类政治和精神团结的地理标识。领土不能定义民族,但有助于民族人格的形成,它在民族的认同生产和再生产中具有突出的空间意义,是一个民族不可消除的印记。领土不是自然形成而是人为制造的存在,它体现人们的行为与思想,正是领土的边界意识让民族加入到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来。 当一个民族共同体认同其生存的领土,想全部拥有或控制它时,民族认同就实现了从强调群体归属向强调领土归属的转移,从而赋予了领土以政治上归属识别要素。也正因为这样,以前俄罗斯是指俄罗斯人生活的地方,而现在俄罗斯指的是生活在俄罗斯的人们。在人类历史上,现代国家的出现使“边界普遍化”,第一次使每个人被精确地划定在国际上彼此承认的领土版图中,第一次使每个人有了一张“在全世界有效并被全世界承认的籍贯证和个人登记卡”[19]。但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一个民族的边界和人们所处国家的领土并不总是吻合的,一个国家包括多个民族,但一个民族分散在不同的国家中,也是不争的事实。现代国家的领土和边界也并非是完全依据民族生存的自然文化空间划分的,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诸多的历史偶然因素,包括战争、殖民和历史协议等等[13]162。事实上,许多非洲国家的边界都是基于殖民统治的便利而(按经纬度)划定的。民族共同体与现代国家的冲突就在于,国家为了在领土内行使完整的主权,总是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方式修改民族的文化边界,以实现内部文化的同质性,最大限度地避免由文化异质性而引发内部或外部冲突。⑥况且,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也在挑战和改变一国居民的同质性。所以,在由多民族构成的现代国家中,如何应对境内多元文化和族群的异质性,如何建构一个更具包容性、团结和发展的政治共同体,始终是现代国家认同的关注焦点。 三、“命运共同体”与现代国家认同 多民族国家在面对现代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出现的“认同性危机”时,通常有三种应对策略:同化主义建构策略、多元主义建构策略和“超民族的”(supranational identity)国家认同建构策略,后一种策略也称之为“泛国家的认同”(pan-state identity)建构策略。同化主义建构策略是指将主流民族(dominant national group)认同提升为国家认同,用主流族群的民族认同同化其他少数族群的民族认同;这种策略还主张弱化少数族群的民族认同,或将其纳入公民生活的私人领域。同化主义建构策略包括:否定或割裂少数族群的认同联系,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或制度,推行主流民族的民族认同(如公民资格和语言政策、取消地方自治、推行主流民族的公共文化政策,甚至包括采用偏向主流民族的考试和选拔机制等等),这种策略在早期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中曾被大量使用。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人们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少数族群逐渐形成了各自精英层,他们借助于互联网影响国际舆论,取得相同族群邻国的支持,进而拥有更多的内部资源和外部盟友捍卫自身的民族性,这客观上使得这种带有强制性的认同建构策略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20],不少国家甚至形成了“反抗性民族主义”(reactive nationalisms),带来民族冲突的升级,这种策略逐渐为大多数国家所放弃[21]。多元主义建构策略是指国家承认内部民族认同的多元性,对多元民族认同给予平等的公开承认,推行更具包容性的多元民族政策。多元主义建构策略是对同化主义和熔炉理论(the melting pot)的回应[22],它不仅假定少数民族具有权利,而且把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合法的[23]。这种策略包括:推行地方自治,尊重多元信仰,使用多种官方语言,废除带有明显族群歧视的排斥性制度、体制和政策等。多元主义建构策略的目标是通过容纳、而不是诉诸冲突升级的手段来解决民族认同的多样性。这种策略同样也会面临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民族自治的界限和民族识别的标准等复杂的制度难题。超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策略试图建构一种超越现有民族认同多样性的新认同,以形成一种基于总体的超民族认同或泛国家认同。这在结束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曾一度盛行,其目标是“消灭部落、建立国家”,将所有族群融入一个新的国族认同之中。这种建构策略的目标是培育一种各部族都拥护的超民族认同,以建构一种更大范围的、稳定的国家认同感。在欧美成熟的现代国家,泛国家认同建构策略通常是将其作为多元主义认同建构策略的补充,而非替代,目的是减少对多元主义认同建构中“反抗性民族主义”的阻力。诚然,无论是被多数国家使用的多元主义认同建构策略,还是尝试使用超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策略,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内部民族与现代国家的联系,化解和超越族群认同的区隔,建构一个更具代表性、获得更多承认和更大支持的命运共同体而做出的努力。 共同体天然排斥隔阂,共同体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能有效化解区隔,还能为建构认同提供动力。当然,“并非每一种隔阂的境遇(situation of estrangement)都会产生政治问题,但政治问题大多数是由隔阂造成的”[24],在涉及国家认同这类具有强烈情感取向的问题上尤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建构现代国家认同是一种消除族群隔阂、达成民族和解和建构更大规模现代国家的政治艺术。在当代多民族国家中,通过尊重族群差异、增进族群交流、扩大族群共识、促进族群合作,在族群间建构以包容、团结和发展为特征的命运共同体,不失为一种消除族群隔阂和族群疏离现象、化解各种竞争性民族主义和次生民族国家建构的认同性危机的重要策略。以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建构现代国家认同,既要超越多元主义认同建构策略只重视包容和多元价值的局限,又要克服超民族的国家认同策略中“轻理解(understanding)、重共识”(consensus)的一体化偏差。我认为,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够超越多元主义和超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局限,是因为命运共同体的联系纽带不仅有对多元族群建构策略中基于理解的包容性的平等承认,更有超民族国家认同中注重一体化团结和发展的价值追求。理想的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可以让内部族群切实感受到他们是价值相通、历史相承、行动相连的共同体,“多元一体化”⑦是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基本原则。 在单一民族国家,尽管不同政治派别在如何界定本民族的民族性上有分歧,⑧但在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认同等涉及国家认同的关键性议题上并没有多大分歧;而在多民族国家,不仅存在族群间认同的文化差异,还可能在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上,甚至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和制度认同等国家认同的核心议题上存在着争议,导致各种竞争性民族主义或次生民族国家建构危机相伴丛生。这些竞争性民族主义和次生民族国家建构危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国家认同建构策略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族群没有在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做出合理的区分,有意或无意地把主流民族认同的特征复制或投射到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上;而在一些追求以超民族的国家认同策略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国家中,也因为对一体化认同的刻意追求而忽视对族群权利的尊重和理解,把普遍性个体的权利识别当作所有族群自主人格的承载体,没有慎重地为族群文化差异预留合法的权利空间。命运共同体所主张的多元,既要认真对待普遍个体的权利多元性要求,更应对族群的多元文化权利诉求给予合理而充分的回应。之所以强调应给有群体差别的多元文化权利预留空间,是因为普遍的、平等的、整齐划一的个人权利,在实际政治操作过程中可能对少数族群带来机会和结果的不平等,进而造成对少数族群利益表达的压制[25]。因此,在促进少数族群融入更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避免族群排斥并寻求族群自我保护的过程中,尊重少数族群的集体文化权利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26]。 以命运共同体建构现代国家认同,还应在尊重族群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族群间交流和融合,使多元的族群认同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交叉性共识,从总体上使族群认同趋于一体化,即呈现出明显的国族特性。比如在英国,就是要在保证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等多元文化族群权利的同时,建构出一种总体的(国族层面)英国民族,使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内在化地意识到自己同时也是英国人,而非将英国人与苏格兰人(或其他内部民族)对立起来。这种一体化的民族建构,既可以是历史形成的(通常伴随国家间战争形成的),也可以是技术和制度建构上的“想象的共同体”,通常是两者兼有。我们知道,民族天然就是命运共同体,民族的生命叙事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历程,正是共同的经历和磨难造就了一个民族。同时,民族也将历史本身谱写成命运,铸造了共同经历、共同文化、共同利益和共同记忆。尽管不是所有的命运共同体都是民族,但所有的民族都是命运共同体,没有命运共同体就没有民族性的形成。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为族群的过去与将来搭建起一种具体而形象的联系[27]。族裔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常常提醒着族群的边界意识,揭示着人们的族群身份,焕发和凝聚着成员对民族的向心力和自豪感。一体化的努力就是试图在更大规模的共同体内实现族群团结,提升共同体意识在建构认同中的积极意义。一体化不是要抹杀各自族群的历史,更不是以主流民族叙事改写少数族群的历史。在此意义上,一体化建构的原则就是要在尊重和融合各个族群历史的基础上,塑造一种基于相互理解和承认的共享观念;一体化的过程也不是要刻意回避民族的文化边界,而是要在尊重族群文化边界的同时,打造出族群间共同价值的联系纽带,以规模共同体的价值优势(如发展、安全和秩序等优势)形成强大的认同吸附力,促进共同价值的形成。研究表明,族群文化差异并不是缺少联系、缺少流动和缺少信息共享造成的,通常是由封闭的政治与社会系统形成的社会排斥所造成的[28]。因此,一体化还应重视制度建设,意在打破族群间对抗性的文化边界,鼓励少数族群以自身的模式参与到民族国家的总体建构中来,倡导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政治体系以容纳族群的多元文化特性。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一体化,是一种基于理解、包容、平等和发展的一体化,是一种以更大规模共同体价值的体量优势(如规模经济的发展优势、国家安全的和平优势、文化繁荣的多元优势等等)推进各民族团结和发展的一体化。 总之,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现代国家认同,应遵循“多元一体化”原则,以培养一种共同体内部族群基于历史的、相互承认的认同归属感,增强成员基于主观感觉的紧密联系性为基本目标。认同归属感的培养是通过叙述、传播和诠释的方式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历史的”、区别于他者的共同体想象。这些想象、叙述和诠释的方式,既可以是空间层面的(如国家公园、乡村博物馆、国家海洋馆等空间文化建设)、历史层面的(如历史教科书、历史原址地、历史纪念碑、民族民俗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建设),也可以是文化层面的(如语言、仪式、法律和国家制度等制度文化建设)。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作为一套意义系统的国家认同,正是通过不同层面文化想象被不断塑造出来的,国家也只有通过基于历史、空间和制度等多层面的文化指示框架,才能创建出一体化的、稳定的心理归属感和共同体符号系统。当然,通过想象创建的符号系统不是随意的、虚构的,它只是借想象的力量建构起来的,想象是多民族创建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和渠道[29]。同时,以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现代国家认同,还必须在成员与共同体之间培养一种感同身受的内在联系性,这种内在联系性应具有超越想象的现实切身体验,是相互包容、尊重和理解的产物,而非争吵、讨价还价的妥协和简单共识。因为任何一种妥协和简单共识都意味着分离因素的一直存在,只有相互理解的内在化了的价值共识,才是铸就统一力量的源泉。我们要通过公开、坦诚和平等地对话,在彼此承认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把握族群的共通性,经由共通性价值共识建构出更具包容性的、平等参与的共有制度和价值体系。 ①本文赞同用ethnic group而非nation来指称民族,主张将nation翻译成“国族”,以区别ethnic group作为国族之下的族群或族裔。参见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6页。 ②正因为如此,斐迪南·滕尼斯在谈及共同体与社会(聚合体)的区别时指出,“在共同体中,尽管有种种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参见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52-54页。 ③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共同体’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含糊而空洞地使用着,以至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已经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参见Eric J.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1914-1991.Pantheon Books,1995,pp.428. ④针对这种复杂的使用状态,Howard Newby甚至抱怨道:“什么是共同体?……我们将看到,这可以解析出超过90个共同体的定义,而它们之中的唯一共同要素就是人!”参见Colin Bell & Howard Newby,Community Studi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the local Community,George Allen and Unwin,1971. ⑤现代国家建构一般要依次经历五个重要的危机阶段,即“认同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和“分配性危机”。参见罗斯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35-36页。 ⑥现代国家形成以来,各种在外部边界划分上的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内部行政区划分上的族群隔离、种族清洗、选区分割变动,乃至行政区划分、重命名等等,都是人们有意识地通过修改民族的文化边界以增强国家领土主权的表现。类似的例子还有国家实施的有意识的民族迁徙,如普鲁士议会在1886年通过一项法律,鼓励德国农民向波兰人居住的波森省进行人口转移,使波兰人地区“日耳曼化”,以便“生产”出一个民族的空间,进而最终有助于控制一块德国人明显居于少数的领土。参见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版,40-49页。 ⑦1988年8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作Tanner讲演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解释,中华民族认同的主要内容是一种“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多元一体格局中的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本文仅从一般意义上阐释以命运共同体建构国家认同中的多元一体化内涵,而不是从具体层面探讨中国的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问题。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比如在葡萄牙,保守派以保证天主教信仰和民族纯洁性定义葡萄牙的民族性,主张用军事独裁的方式来应对内部和外来威胁;改革派则以多元、开放和世俗的姿态来理解本民族的特性,倡导用民主的现代治理手段应对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