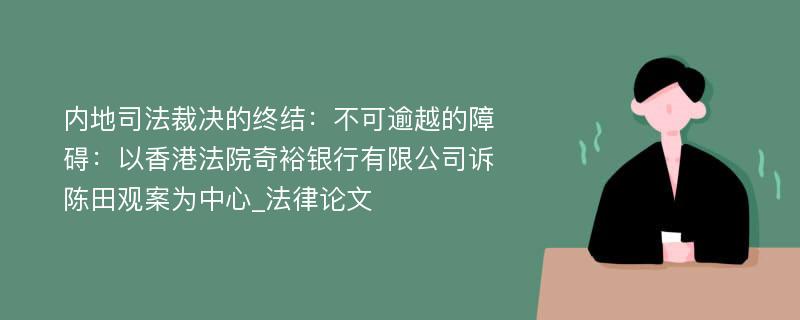
内地司法判决终局性:难以逾越的障碍——以香港法院Chiyu Banking Corp Ltd v.Chan Tin Kwun案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判决论文,司法论文,障碍论文,法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自香港回归,内地和香港间的经贸往来不断深化和发展,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日益凸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诸如区际管辖权、民事司法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等重要领域,两地间的法律协调却举步维艰。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近十余年来,内地多宗民商事判决被香港法院认定缺乏终局性,无法在香港顺利得到承认与执行。内地司法判决缺乏终局性的观点,在香港法律界似乎已经根深蒂固,“总体而言,内地法院所作出的任何判决,不论其是一审还是二审,甚至是在审判监督程序下产生的,都不具有终局性,最多只是一种半终局性的判决。因为如果需要,它将受制于可能的再审程序。”① 终局性问题似乎构成了内地司法判决在香港获得承认和执行难以逾越的障碍。
尽管“终局性”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内地法学界的讨论,但目前提出的意见和方案似乎很难超越成文法思维的藩篱,过多地将目光投向香港法院判决的最终结论并纠缠于两地不同的法律概念之中,忽视了香港法院在“遵循先例”制度框架下从先例提炼判决理由并将其类推适用于特定案件的司法过程。立基于此的解决方案可能只是自话自说,难以构建香港和内地在不同法律文化和法律体系的语境下进行交流对话的有效平台。在目前中国多法域并存的情势下,普通法的基本理论和运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智识的来源和学术的素材,更有可能成为我们分析解决内地和香港之间民商事法律冲突的视角。本文将通过对香港法院相关判决的梳理, 指出Chiyu Banking Corp Ltd v.Chan Tin Kwun② (以下简称为“Chiyu案”)案确立的内地司法判决终局性的判断标准为香港法院随后的一系列判决所遵循,Chiyu案从而具有先例的性质。然后以“判决理由”确定理论作为出发点,将普通法其他法域在终局性问题上的晚近发展作为参照,尝试对Chiyu案的司法过程进行批判性分析,从而对香港法院终局性标准的妥当性提出质疑。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提出终局性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而更多的是寻求不同法域间法律协调的新思路。
二 内地“终局性”问题解决方案简评
针对内地司法判决因终局性问题无法在香港顺利获得承认和执行的境遇,内地有观点认为,“中国法院的判决是可供执行有法律约束力的确定判决,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且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也承认在原审国上诉的域外判决并非是没有终局性的,所以香港法院不能因为审判监督程序的存在而“得出内地法院的判决不是终局性判决的结论,更不能以此作为推翻承认和执行内地法院判决的理由”。③ 的确,根据香港法院遵循的普通法规则,终局性要求“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没有上诉的权利。外国判决有可能在上诉审中被推翻,或者上诉审正在该外国进行这一更为直接的事实,并不能构成(在国内)提起承认和执行的障碍”。④ 但是论者似乎未注意到,在Chiyu案中, 上诉制度与再审制度的区分构成了香港法官逻辑推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官在考察了《民事诉讼法》抗诉和再审程序的相关规定后,在判词中认定,内地以审判监督为基础的再审机制并不是简单的上诉程序,因此不适用针对上诉判决的例外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能指责香港法院“甚至违反自己的法律”。更为重要的是,内地判决“确定性”的概念见诸“中国与三十多个国家缔结的司法协助条约中”,是缔约方在平等协商后达成的一致与谅解,这些条约并不必然适用于香港;内地和香港在民商事法律领域又是平等关系,因此简单直接地要求香港法院放弃自己在普通法制度下的终局性规则而接受内地民事诉讼判决的“确定性”概念,似乎很难奏效。
另有方案提出,应该借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订的《民商事管辖权与外国判决公约(草案)》第7条作为解决终局性问题的思路, “该条从判决在原审国与申请国的效力的角度出发,认为一个判决在被申请法院不能有比原审国更优先的效力,并对问题的处理提倡的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给法院一种自由选择的幅度,对复审中的判决可以没有偏见的中止或终止。”⑤ 然而,香港法院并不是像论者认为的那样,简单地“拒绝承认和执行中国内地的判决”。实际上,他们在一些判决中行使的恰恰是以上解决方案建议的裁量权,裁定中止以承认和执行内地判决为诉因的诉讼而且不是终止诉讼。⑥ 该解决方案似乎不能解决目前的终局性困境, 反而有可能为香港法院目前的做法提供正当性依据。
以上解决方案的思路似乎可以归结到成文法体系下的思维惯性。一方面,在论证的出发点上,论者所关注的是香港法院“终局性”规则的字面意思及法院在判词中做出的“内地司法判决缺乏终局性”的最终结论,而香港法院赖以评判内地司法判决的基本标准似乎并不在论者的视野之中;另一方面,在论证方法上,论者采取的似乎是规则的比较和演绎方法,在引用香港相关法例的具体规则、其他法域法院做出的结论以及相关国际公约的条文的基础上,将香港法院的“终局性”要求与内地的“确定性”概念以及其他法域的相似概念进行比较,然后在此基础之上采用规则演绎方法,推导出内地判决不应被认为缺乏终局性的结论。在这样的论证过程中,香港法院如何采纳终局性标准并将其适用于评判内地判决的司法过程,也就不在论者的考虑之中了。然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如果仅仅关注规则的字面意思,我们与香港法律界进行沟通寻求解决问题的努力就有可能落空。我们不妨转换思路,首先确定香港法院评判内地判决终局性的标准,然后再在香港法院具体司法过程中探究该标准的正当性。
三 香港法院Chiyu案司法过程评论
(一)Chiyu案简要介绍
在香港法院针对内地司法判决终局性问题做出的一系列判决中,Chiyu 案可以说具有先例的地位。一方面,在该案的判词中,法官援引了英国贵族院1889年Nouvion v.Freeman⑦ 案(以下简称“Nouvion案”)并从中归纳出判决理由,将“原审法院是否能改变业已做出的判决”作为判断内地司法判决终局性的标准;在以后的多宗判决中,香港法院不再专门讨论终局性标准的渊源、根据及其正当性,而只是简单地沿用Chiyu案采用的标准作为类推适用的逻辑出发点。⑧ 另一方面,在晚近的判决中,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除强调Chiyu案判决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外,还指出Chiyu 案对内地司法判决缺乏终局性的认定可以作为证据在以后的相关案件中直接提出。⑨ 这意味着, 被申请承认和执行方只需要在香港法院的相关诉讼中引用Chiyu案作为内地判决缺乏终局性的抗辩依据, 而无需承担内地特定判决缺乏终局性的进一步举证责任,就可得到法院的支持。
由此,内地民事诉讼法中审判监督制度的抽象存在,已然构成了内地判决一般性地缺乏终局性的初步证据。如果香港法院顽强坚持“原审法院能否改变业已做出的判决”这一判断标准,可以认为,除非内地完全废除民事诉讼法中的再审制度,否则,内地判决的终局性将无法获得香港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终局性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普通法上终局性要求本身,而在于香港法院采用的评判标准。确立该标准的Chiyu案的基本司法过程的确值得我们关注。在Chiyu案中,原告在福建省某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为“中院”)提起诉讼,法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但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即在香港提起诉讼请求执行内地判决。与此同时,被告在内地请求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该检察院后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被告遂在香港法院以避免双重诉讼为由请求中止以承认和执行内地判决为诉因的诉讼。香港法官在考察了案件事实情况以及当事人提出的诉求和抗辩后,确定该案的真正争论点在于内地司法判决是否具有终局性。在讨论了内地民事诉讼法抗诉制度的运作以及承认和执行域外判决的普通法规则以后, 法官在判决中援引了英国贵族院百余年前审理的Nouvion v.Freeman一案作为先例, 判定“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虽然(经过上诉为两审终审判决)不能再上诉,并能在内地执行这一意义上具有终局性,但是该判决并不能满足在香港法院承认和执行(域外判决)所应具备的最终和不可推翻的条件。根据沃诚(Watson)法官的说法,该判决‘在原审法院并不是最终的和不能更改的’。如果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抗诉,判决在再审中容易被中级人民法院变更。在抗诉情形下——即使发生几率微乎其微——中国法院也必须重审案件,这意味着它明显地保留着改变自己做出判决的权力。”⑩ 香港法院由此否定了该内地判决的终局性。
(二)对Chiyu案司法过程的批判性分析
如果将Chiyu案的判词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 我们不难发现法官的审判过程实际上带有三段论推理的明显特征。法官首先引用了英国先例并从中提炼出判决理由作为评判域外司法判决终局性的标准;同时,法官也注意到普通法规则中该标准的例外情形,即适用于上诉程序的限制;然后,法官考察手头案件牵涉的事实,强调内地基于抗诉的再审程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上诉程序,例外规则因此无适用空间,前述标准可以适用于内地判决并得出该判决缺乏终局性的结论。
然而,立基于形式逻辑推导的司法过程的说服力取决于论证前提的可接受性,在Chiyu案中,法官论证的前提却不能令人信服。香港法官在Chiyu案中援引了作为先例的Nouvion案中两位法官的部分意见后, 便摘录沃诚法官判词中的一句简洁话语作为终局性判断标准,即:一个判决如要满足终局性的要求,它必须“在做出该判决的法院是最终的和不可变更的”。香港法官并未揭示出他做出如此选择的判断过程和理由。更为重要的是,普通法下类推适用法律规则的前提条件是案件事实的相似性。虽然香港法官论述了再审程序和上诉程序的不同,强调终局性标准的例外情形不适用于内地司法判决,但同时却忽略了该标准本身适用于内地司法判决的妥当性:他既未提及Nouvion案的事实构成, 更没有进一步关注该先例针对的域外判决与内地司法判决是否存在差异。我们能否就此得出结论,香港法院从Nouvion案中提炼的法律规则能够脱离特定的事实基础而具有普适性呢?这些疑问可能导致进一步的追问,在普通法的司法过程中,法官能否脱离法律规则产生和适用的社会历史条件,忽略法律追求的价值而作出纯粹的逻辑推导呢?香港法院在Chiyu 案司法过程的妥当性由此在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质疑:
1.判决理由确定缺乏事实的支撑
在普通法遵循先例的原则下,并非法官在构成先例的司法判决中阐述的每一个观点,都构成应当在呈现相似情形的日后案件中予以遵循的权威性规则。只有那些从早期判决中提炼出的被称为案件判决理由的观点,才能对以后的相似案件施加拘束力。判决理由的形成,并不是法官脱离案件的特定事实纯粹抽象思维的产物。英国学者阿瑟·古德哈特(Arthur Goodhart)认为,“案件中的法律原则只有考虑以下两点的情况下才能找到:(1)法官认为是实质性的事实,(2)法官基于该事实做出的决定”。(11) 沃克(Walker)认为,判决理由就是“在考虑案件的实质性事实或在案件事实的语境下裁判案件的法律规则”。(12) 因此,法官是否考虑先例的特定事实以及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发现和剪裁该事实的构成要素,将直接决定判决理由的构成并影响它以后的适用范围。
在Chiyu案中,作为先例的Nouvion案的具体事实的确无足轻重,香港法院可以完全予以忽略而只需援引先例中些许的抽象法律意见就可以提炼出该案的判决理由吗?我们不妨简要回顾该案事实。在Nouvion案中,英国贵族院所面临的问题是确定西班牙法院做出的一种“remate”判决(13) 是否具有终局性。该判决通过一种简易诉讼获得,依据原告提供的初步证据,法官无须事先通知被告就可决定扣押他的财产,扣押决定随后会通知给被告,被告可选择是否出庭抗辩,但抗辩的范围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这种简易诉讼中败诉的原告或被告有权在同一法院就同一标的提起普通诉讼并可提出所有的抗辩,“remate”判决对普通诉讼没有既判力的效果,法院可以在普通诉讼中重新审理争议的所有争点。
与香港法院不同,Nouvion 案的事实在普通法系一些国家的司法过程中得到充分关注。法院在审理申请承认和执行域外判决的诉讼,面对被告依据Nouvion 案提出的抗辩时,并不是简单地从该案法官所阐述的只言片语出发,而是基于该案特定的事实来发现和提炼案件的判决理由。在Lewis v.Eliades and Others一案中,英国法院认为,Nouvion 案中法官是围绕着这样一种事实做出决定的:所涉西班牙判决并不是一个可以提出所有抗辩并考虑了所有争点的判决,而沃诚法官的意见并不能仅仅从字面含义上进行理解,而“必须参照该案的特定事实和其他法官的意见”。(14) 法院进而认为,手头案件所涉域外判决已裁判了所有争点,在当事人之间创设了债权债务关系,可以认为具有终局性。无独有偶,在Skaggs Companies Inc.v.Mega Technical Holdings Ltd.案中,加拿大法院同样认为,将“域外判决必须在原审法院是最终并不可更改”认定为终局性标准是“误导性的,因为援引的话语是有选择的”。(15) 法院在考察了历史上一系列相关判例后采纳了他们对Nouvion案的理解,即基于涉及金钱的外国司法判决而提起的诉讼,其诉因确立的条件是“就(金钱)债务的存在方面而言,该判决在原审的外国法院是最终和不可推翻的”;“终局性是指债务是否存在而言,而不是该判决是否会被撤销”。(16) 香港法院所归纳的标准,即“判决只有在原审法院不能再对其进行变更时才是终局性的”,针对的显然是在Nouvion 案中只具有临时性的特定判决:该判决中的被告无权提出所有的抗辩,法院也未审理双方当事人的所有争点。
2.判决理由确定缺乏对规则演进历史的考察
普通法法域的上级法院特别是贵族院法官做出的冗长法律意见并不仅仅意图去制定僵硬的法律规则,他们在判词中的陈述更可能着眼于对如何获得法律规则过程的描述、解释和论证。在有两位或更多的法官发表意见时,他们的观点应彼此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但即使如此,在细致考察了案件的事实后,要在充满睿智的众多意见中进行取舍,归纳出判决理由作为裁判当下案件的规则,并不是一件易事。所幸的是,法官在探究法律规则时,面对的通常不是一个孤立的先例,而是一系列潜在的相关先例群。从一个判决中可能衍生出多个可能的解释,但是如果能将特定判决与针对相同或相似争点的其他判决联系起来,洞察规则产生和发展的脉络,便有可能限制法官对先例的任意剪裁并为他们提供裁量的框架。因此,有意见认为,一个先例只有结合所有其他的相关判例群才能得到适当的解读。(17)
在被援引作为先例的Nouvion案中, 虽然贵族院做出了所涉西班牙判决不具备终局性的一致判定,但有四位听审的大法官就该结论做出了不同的论证,各自发表了详尽的法律意见。Chiyu案中的香港法官并未在其司法过程中阐述或论证, 他们何以在该先例纷繁芜杂的法律意见中直截了当地引用一位法官的简洁话语作为终局性判断标准而舍弃其他法官的详细论证。在Nouvion案之前的一个案件中, 法院认为,任一具有适当管辖权的域外法院做出的判决都能构成提起承认和执行诉讼的基础,除非败诉一方已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撤销该判决。(18) 而在Nouvion案之后,法院对Nouvion案的理解是,该案中的西班牙判决之所以被认定缺乏终局性, 是因为该判决并没有最终和不可推翻地创设债权债务关系。(19) 域外判决的终局性取决于被告是否采取了实质性步骤予以变更的事实。在Chiyu案中,面对Nouvion案纷繁复杂的法律意见,香港法官既不从总体上比较各种意见的异同,又不将该先例置于相关规则演进的历史中予以考察,而只是从援引的一个孤立案件的寥寥数段话语中不加论证地归纳出终局性的判断标准,这种简单形式化的司法过程会在相当程度上减损终局性标准的正当性。
3.司法过程忽视价值的考量
国际民商事交往领域和范围的深化和拓展,使得一个法域的法院要经常面对其他法域迥然不同、各具特色的诉讼程序。以上列举的其他法域的晚近判决相当一部分指向的是西方民事诉讼中较为常见的缺席判决。如果采用“原审法院能否改变其业已做出的判决”作为衡量终局性的标准,这些缺席判决由于存在原审法院事后变更的可能性而无法得到承认与执行,它们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将漂浮不定,这无疑会减损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同时,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在具备适格管辖权的法院合法获得的判决可能仅仅因为另一方当事人简单的诉讼策略即不出庭,而变成一张永远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实际上,早在百年前就有法官对简单地从Nouvion 案判词的只言片语中归纳硬性规则的做法提出批评,“如果我们说缺席判决可能被原审法院撤销而不具备国际诉讼所应有的终局效力,我们实际上就认为,原告的理由越清晰,它所获得的域外判决就越没有用处”。(20) 在晚近涉及终局性的判决中, 不论是考察原审法院是否已经审理了当事人间的所有争点,还是关注当事人是否采取了实际步骤撤销原有判决,其他法院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围绕域外司法判决是否真正创设了债务关系来确立其终局性标准的。这实际上可归结于普通法上承认域外司法判决的理论基础即“债务说”。“债务说”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司法判决。其核心内容是,有合格管辖权的域外法院判定由一方当事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给另一方当事人后,该支付金钱的义务就成为法定义务,可以在被申请执行地通过提起清偿此债务的诉讼予以执行。(21) 债务说蕴涵了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即确保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在一国依法取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会随着国界的跨越而化为乌有。在此意义上,其他法域的晚近判决并不是对Nouvion案的颠覆,恰恰相反,它们更像揭开了时空距离遮盖在Nouvion案上的面纱,将它的真实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
与以上司法实践相对照,在香港法院Chiyu案及其以后的一系列判决中, 严格适用技术性的终局性标准对于参与两法域间民商事交往的当事人是否公平合理,两地间日益频繁和深化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能否由此得到保证和促进,这些因素未能纳入到法官的司法过程之中。对硬性规则的遵循和形式逻辑自恰性的追求似乎隔绝了对当事人正当利益和商事交易稳定性的考量。
实际上,以上从不同角度对普通法司法过程的考察,只是出于便利分析阐述的考虑。不论是从特定的事实还是从规则的演变中提炼判决理由,这两种方法在晚近其他法域的司法过程中不是非此即彼、相互隔绝,而是相互依托,浑然一体的。在这样一种积极的司法过程中,法官既将Nouvion 案放置于数个相关案例形成的锁链中从外部考察,又从该案的事实中予以内部的探究,而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正是法官对当事人正当权利和民商事关系顺利流转的深切关注。虽然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4条的规定,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司法判例在香港法院审判案件的过程中只是具有参考作用,但是其他法域涉及终局性问题的司法过程,无疑给香港法院提供了自我审视的视角。也许我们可以用卡尔·卢埃林(K.N.Llewellyn)的评论作为对香港法院Chiyu案司法过程的总结:
许多法官都不愿意对那些被认为是有关早期判例做认真且深刻的考察,以确定早期法院所制定的原则——按其表述的确切形式——对于裁定当下案件来讲是否真的必要。他们往往抓住某些见诸于先例中的主要用语,并视其为“该案之规则”,而不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思考,以发现这一被确立的规则的范围是否同那个由早期法院裁定的问题的范围一样广。(22)
四 结语
通过上述Chiyu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法过程中, 香港法院未能探究先例Nouvion案的特定事实, 只是将先例在特定语境下形成的法律意见无限制地扩张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规则,就越过了将内地司法判决与先例中的特定事实进行比较,从而决定先例规则能否类推适用这一重要环节;只是简单地不加分析地罗列先例判词中的数段话语,就确定了一种完全技术性的僵硬的终局性标准,而不是在对不同法律意见整体性的把握中寻求判词的内在关联性,更不是将近百年前的先例放置到规则演进的历史中考察。香港法院排除了对现实正当权利的期待,隔绝了民商事法律关系稳定和安全性要求,其建立在一种纯粹文字推演基础上的司法过程的合理性和妥当性由此发生动摇,由形式化司法过程创设的终局性标准的正当性无疑也遭到质疑。虽然普通法其他法域晚近的判决对香港法院只具有参考意义,而且这些判决针对的也是不同于内地判决的其他类型的域外判决,但是,我们以上关注的与其说是这些法院对终局性标准作出的发展,毋宁说是这些法院展现出的积极的、更具说服力的司法过程。对先例事实构成的把握,对规则演进脉络的探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回应以及对正义的追求,这些要素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其他法域晚近司法过程的共同特征,并最终导致了各具特色的现代终局性标准的创设。
如果香港法院能够在其司法过程中注意到其所采用的终局性标准实际指向的是Nouvion案中只具有临时性质的特定判决, 关注到终局性标准的历史演进轨迹及作为理论支撑的“债务说”,敏锐感受到香港内地间不断深化的民商事法律关系对公正和安全的内在要求,那么,在内地有权机关还未实际启动再审程序之前,已经裁判了当事人间所有争点并创设了债权债务关系,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内地司法判决的终局性是不应受到质疑的。香港法院似应展开一种积极能动的司法过程,建立灵活弹性的终局性标准,终局性问题不应成为内地司法判决在香港寻求承认和执行的障碍。
也许,难以超越的正是我们的法律思维习惯。终局性问题可能只是冰山之一角,伴随内地和香港经济一体化过程而引发的资本、货物、人员的频繁流动,两地间在诸如管辖权、法律适用等诸多领域的法律冲突会日益凸显和激烈。宏观至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法律思维模式,微观到法言法语、法庭礼仪,香港和内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彰显出巨大差异。就香港法院而言,如果像Chiyu 案那样展开一种建立在形式逻辑上的司法过程,顽强地坚持某一特定的技术性规则,那么,由两地间法律差异所带来的法律冲突的解决似乎是无法企及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拘泥于成文法的思维惯性,纠缠于两地法律概念的字面差异,忽视香港法院在普通法下由先例归纳法律规则再将其类推适用的有机司法过程,我们就无法有效地与香港法律界建立沟通对话的桥梁。由此,超越原有思维习惯的束缚,以一种宏观和开放的视野去探究和把握其他相关国家和地域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并能敏锐地观察和分析不同法域间与经济融合形影相随的民商事法律冲突,提出建设性的协调方案,将是香港和内地同行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注释:
① Nanping,Liu,“A Vulnerable Justice:Finality of Civil Judgments in China”,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Spring 1999,p.83.
② [1996]2 HKLR 395.
③ 董立坤:“内地与香港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中的‘终局性问题’”,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9期,第18—19页。
④ PM North,JJ Fawcett,Cheshire and North'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13th,Butterworths,1999,p.428.
⑤ 董立坤:“内地与香港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中的‘终局性问题’”,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9期,第19页。
⑥ 在Chiyu案中,法官判定“搁置该案的法律程序,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有关抗诉作出决定”;在Wuhan Zhong Shuo Hong Real Estate Co Ltd v.Kwong Sang Hong International Ltd [2000]2 HKLRD H5.案中,法官判令“搁置申请执行的程序六个月”。
⑦ Nouvion v.Freeman(1889) 15 App Cas 1.
⑧ 参见Wuhan Zhong Shuo Hong Real Estate Co Ltd v.Kwong Sang Hong International Ltd[2000] 2 HKLRD H5; Tan Tay Cuan v.Ng Chi Hung[2000] HCA 5477;林哲民日昌电业公司诉林志滔案,民事上诉案件2001年第354号。
⑨ 林哲民日昌电业公司诉张顺连案。原香港高院民事诉讼案件2000年第9827号,民事上诉案件2001年第1046号(宣判日期为2002年7月12日)。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在该案聆讯中援引了香港法例第八章《证据条例》第59条的规定,即凡在特定法律程序中获裁定的香港以外任何国家或地区关乎任何事宜的法律的任何问题,可以在任何民事程序中接纳为证据,以证明该国家或地区关乎该事宜的法律。法官由此认为,虽然在该案中,当事人并未提交有关“抗诉制度”的证据,法庭也可以采纳Chiyu案中对内地司法判决终局性的认定,判定“根据香港法律,该法院(指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并非一最终及不可推翻的判决”。
⑩ [1996]2 HKLR 395.
(11) A.Goodharte,“The Ratio Decidendi of a Case”,Modern Law Review,Vol.22,No.2,March 1959,p.117.
(12) M.Sander,The Law Making Process,(1994),Butterworths,p.263.
(13) “remate”应为西班牙语,原意为“拍卖,通过拍卖出售”等;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还有“在强制执行中将物移转给债权人”的含义。参见Woerterbuch der Rechts-und Wirtschaftssprache,Spanisch-Deutsch,4.Aufl.,C.H.Beck Verlag,S.1058。大概由于“remate”判决在英国相关司法制度中不能找到精确的对应概念,在作为先例的Nouvion v.Freeman案和以后的一系列有关终局性的判决中对该词加以引号后直接使用。判决性质可以通过下文对其取得条件及效力的描述加以把握。
(14) [2003] EWHC 368 (QB),[2003] 1 All ER (Comm) 850.para.53.
(15) 2000 Alta.D.J.720; 2000 Alta.D.J.Lexis 730.para.29.
(16) 2000 Alta.D.J.720; 2000 Alta.D.J.Lexis 73.para.33,34.
(17) William Twining and David Miers,How To do Things With Rules,4th ed.,Butterworths,1999,p.335.
(18) Vanquelin v.Bouard (1863) 15 CB (NS) 341,143 ER 817,at 828.
(19) Boyle v.Victoria Yukon Trading Company (1902) BCR 213,at 223.
(20) Boyle v.Victoria Yukon Trading Company (1902) BCR 213,at 223.
(21) Russell v.Smyth (1842) 9 M & W 810.
(22) 转引自[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