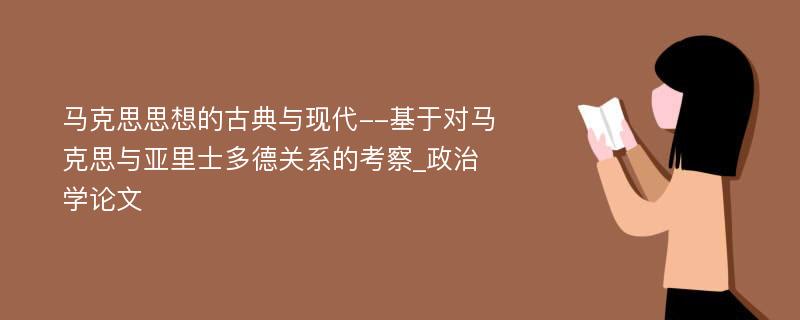
马克思思想中的古典与现代——基于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关系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亚里士多德论文,古典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4-0007-10
一、马克思的“自在体系”与古人的关联
1857年至1858年间,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两封信中,谈及拉萨尔的著作《赫拉克利特》。在1857年12月21日的信中,马克思写道:
谢谢你的《赫拉克利特》。我对这位哲学家一向很感兴趣,在古代的哲学家中,我认为他仅次于亚里士多德。[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①
1858年5月31日,马克思谈道:
我在病中细读了你的《赫拉克利特》,并且发现,根据保存下来的零星残篇而恢复起来的体系作得很高明;而机智的论战也使我感到不小兴趣。……你在写作中必须克服的困难,我尤其清楚,因为十八年前我曾对容易理解得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进行过类似的工作,也就是说,根据一些残篇阐述了整个体系。不过,我确信这个体系,赫拉克利特的体系也是这样,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只是“自在地”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即使在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象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②
在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明确如下两点:其一,马克思对古代哲学家的兴趣并非仅限于《博士论文》期间,“一向很感兴趣”的自述隐藏着某些仍待省察的东西;其二,马克思认为,某些思想家内部的结构与其体系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斩钉截铁地“确信”,其在《博士论文》中通过残篇阐述伊壁鸠鲁的体系是存在的,但这一体系是“自在地”存在着。
由此,引发了这样两个问题:其一,古人在马克思的思想谱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其二,马克思思想谱系中是否也存在一个他本人未曾明确表述(甚至是本人未曾察觉到)的自在体系,而这一自在体系和古人又有何关联?
针对第二个问题,日本学者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认为,马克思的上述洞察“同样适用于马克思的作品本身”③。也就是说,马克思思想内部同样存在一个与其自觉采用的体系形式不同的结构,亦即存着一个外形的“马克思”与一个“内部结构”的马克思。
马克思对正义的暧昧态度也恰好揭示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关于马克思是否存在正义理论的争论一直是众说纷纭,杰拉斯(Norman Geras)在梳理了晚近几十年此方面代表性文献的争论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确实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但他不认为他自己是这样想的。”④认为马克思反对正义以及认为马克思赞同正义的双方都可以援引马克思的文本为自己的立论作辩护,以至于杰拉斯不得不反思:“对同一作者的意思,居然存在两种如此截然相反的解释,且每种解释显然被大量对其著作的直接引用和推理所支撑,面对这一局面,我们最好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仅仅参考马克思的文本,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⑤怀特(Stuart White)则认为,这一现象正是“一个极力避开基于正义批判和倡导的‘正式的’马克思与一个仍然默默地卷入正义话语的‘非正式的’马克思之间的分歧”⑥。
事实上,马克思这一思想特质愈为人们所感受。从第二国际的决定论思想和以卢卡奇契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决定论的反叛及对自我能动性的彰显,⑦以及晚近波普尔关于此方面的讨论,⑧都可以看得出,立基于马克思的文本,却可以得出两种异质甚至是对立的思想,该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呢?
就此,阿伦特认为,这种矛盾正是马克思作为一流思想家的标志。在二流的思想家中,“一种根本性的、公然的矛盾很少出现”⑨,“而在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中,这些矛盾通往他们作品的核心,并且提供了真正理解他们的问题以及他们全新洞见的最重要线索”⑩。在阿伦特看来,马克思这一矛盾源于传统与现在的紧张关系。当马克思试图在思想中反抗传统,同时又采用了传统本身的概念工具时,则不得不陷入绝望与悖谬之中。(11)
显然,阿伦特的这一判断有一定的依据。从教育经历来看,深受古典教育的马克思与古人确实有着亲密的联系。另一方面,身处现代的马克思又面临着与古人不一样的社会世界。然而,马克思是站在古典批判现代,还是站在现代反观古典,抑或在这两个世界来回穿梭?马克思从古人那里汲取了什么样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是否正是马克思“自在体系”的内核,而现代又给马克思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是否正是这些现代问题赋予马克思所“自觉提出体系”的外观?进一步说,马克思思想内部的张力是否真的是古典与现代的对峙?
这些问题应该得到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越来越注重对马克思的学理性分析。“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与马克思同行”之类的主题依然方兴未艾。无疑,无论是通过文本的细致解读,考察马克思的真义,还是以当代问题重思马克思的理论,抑或是对马克思的比较性研究,都可以拓宽对马克思的理解。通过立体式(也常常会是相互冲突)的解读,马克思的形象虽显得越来越复杂,但对于打破一言堂式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如果仅把马克思的文本抽离出来,从外形的体系性或片断性孤立考察、强行肢解进行当代解读,则不免落入了麦卡锡(George E.McCarthy)批评北美近几年关于马克思与伦理学研究中的窠臼:“在它们当中,大多都存在这样一个毛病,即那些问题都是从一个文化真空中提炼出来的。虽然它们都展现了严密的诠释学问,只可惜还是没能深入去考察马克思思想发展所立足的哲学背景与传统。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研究仅流于对马克思话语的泛泛之论,而遗漏了赋予其话语以意义和关切的潜在精神。”(12)
因此,回到马克思首先要有一个自觉,这种自觉意味着必须先理解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文化氛围、马克思自身的教育背景,及马克思对各种批判所作的“本体论承诺”,亦即必须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理论批判中所依据的标准。任何批判必定基于一定的标准,只是这些标准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自在的。自觉的标准往往在文本上“明码标价”,直接写明。自在的标准则散存于各文本之中,必须从文本隐喻、整体的含义来厘清。作为资本主义最好的学生,也是最激烈的批判者,马克思必定是依据一定标准来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只是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极少可以直接看到他本人关于这方面的直接论述,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则是把马克思依据的标准重构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澄清马克思与古人的关系以及其本身潜在的关切。
二、古典人文主义运动对马克思思想旨趣的形塑
一个人的阅读旨趣、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决定他的学术取向。马克思与古人的关系无疑和他所受的教育紧密相联。马克思一生有大量的藏书,据布鲁诺·凯撒(Bruno Kaiser)的研究,马克思的书房藏有89卷古希腊和古罗马作者的书(48卷为原文)(13)。从高中到大学,马克思一直沉浸在古典文化和哲学的氛围中。“从他最初对希腊罗马的历史与神话学的兴趣,到他完成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物理学的博士论文,古典哲学构成了他理智生命的核心。”(14)到晚年,马克思依然保持着对古典文化的热爱,并且将阅读古典文化当作一种放松的方式。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及各种琐事使他无法安静从事研究时,曾说:“晚上为了休息,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15)
马克思对古典文化的沉迷与当时德国的文化氛围紧密相关。梅维斯(Mewes)认为,古希腊文化在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humanism)中占据无可争议的重要位置:“就人文主义的这种一般精神的关键成份在马克思中得到保存来说,就有理由去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与希腊人的关系,尤其是研究他与某种特别是德国对古希腊的解释的紧密关系。”(16)
古希腊文化对德国的全面影响始于17世纪的教育改革。1703年,腓特烈大帝登上普鲁士王位,标志着德国启蒙运动的开始。启蒙运动时期,经格斯纳和海涅的努力,学习希腊文在大学和中等学校受到重视。“人们在这时已经感到还有比对一般功利更为高尚的兴趣;感到‘人性’以及知识分子的全面教育,在它们本身都具有绝对的价值。就这方面而论,则不能认为还有比探索希腊知识和熟悉希腊文学更加重要的事。以传授最高文化为目标的教育,若想抛开希腊语文于不顾,似乎是不可能的。”(17)1737年公布的德国高等学校规章更是明确地规定:“凡确定从事学术工作者不可不攻读希腊语文,否则将遇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凡欲从事任何研究工作者,为求以后工作进行顺利,莫重于事先掌握希腊语文。”(18)
18世纪70年代之后,新人文主义运动在德国文化教育领域取得支配地位,新人文主义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复兴古希腊文化,其基本任务就是论证德国人和希腊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具有密切关系。因此,“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按照古希腊的模式塑造青年一代,即使不能在体格和容貌上如此,至少在心灵和精神上应该如此。就是说,应该用希腊人所具有的情操、寻求真理的勇气和能力、反对内外敌人的坚定气概以及对善与美的热爱,来培育青年的心灵”。(19)
德国精神与古典文化的亲和性在卢卡奇的《歌德与其时代》一书中也得到阐释,卢卡奇认为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的德国文学是建基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膜拜的基础上的,是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意识形态所做的准备工作。(20)
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氛围成长起来。在波恩大学早期时日里,马克思的研究集中围绕着希腊罗马的诗人和哲学家,他还加入一个叫做“邦纳诗人”的团体,这一团体的兴趣点在于希腊美学理想的复兴,特别是美与和谐的理想。(21)1836年,即柏林大学成立26年后,马克思进入该校学习。(22)1837年,马克思开始研究黑格尔。黑格尔曾被称为德国的亚里士多德,(23)其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典范。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深情地讲道:“假使一个人真想从事哲学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更值得去做的了。”(24)黑格尔是最早同时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以及密尔(James Stauart Mill)、弗格森(Adam Ferguson)、休谟、斯密、萨伊(Jean-Baptiste Say)和李嘉图等人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方面著作的现代理论家。(25)在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那里,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是统一的。马克思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在1837年致父亲的信中,马克思谈到自己的一个转向:“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26)这一转向使他重新钻回黑格尔的大海里。与费希特不同,在黑格尔那里,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是统一的:“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27)古希腊的魅惑力不仅通过黑格尔,还通过温克尔曼(Winckelmann)、莱辛、诺瓦利斯(Novalis)、歌德、席勒等人的想象而进入马克思的思想世界。(28)这种思想魅惑不仅集中于文学与艺术领域,还渗入德国的政治与经济理论,直至其伦理学与社会理论。(29)
可见,古典文化几乎垄断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文化精神,巴特勒(E.M.Butler)在《希腊对德国的专制》直截了当地指出:“希腊文化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现代文明的大势,在一切地方影响她的思想、她的标准、她的文学形式、她的想象、她的视野和梦想。但是德国是她胜利的精神统治者的最高的例子。德国更忠心地模仿希腊,更不可自拔地被它迷住了,德国人比任何一个种族都更少地消化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最大的影响是在德国。”(30)
因此,抛开古典文化来理解马克思,不可避免将遗忘其思想得以奠基的传统。“古典遗产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对受教育阶层的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和无处不在,以致我们不必再问古典是否影响过马克思和他的阅读和写作,相反我们应该问马克思是怎样阅读古典和理解古典的。”(31)
三、政治动物与古典城邦的自然性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阅读和理解古典的呢?马克思从古人那里继承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
晚近的大量研究表明,马克思在此方面受惠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理想社会的实际情形与雅典城邦国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其关于最好社会形式的理想,“与其说它们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如说它们再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经验模式的、雅典城市国家的政治社会状况”(32)。洛维特同样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依据的是黑格尔的亚里士多德的样板:城邦;城邦的人是一个政治动物,其自由就是在他在中与自身同在”(33)。古典的城邦理想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对完整、自由、和谐的人类社会的洞见。麦卡锡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在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产业资本主义以及权力和权威的社会关系背后,隐含着一种对希腊城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传统之批判性因素的恢复和回归。”(34)
古典城邦的理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详细的论述。亚氏无疑是马克思最感兴趣也是最尊敬的哲学家。《博士论文》一开头,马克思尊称亚氏为“希腊哲学中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35),在《资本论》中,亚氏被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36)。作为一位一生从事“无情批判”的思想家,马克思此番赞誉绝非随口之词。“马克思甚至一度考虑撰写关于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博士论文。”(37)而卡弗(Terrell Carver)就认为,如果马克思能够一直关注(或从事)哲学研究,那么亚里士多德也应该是一个研究候选人。(38)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39),麦卡锡认为,这一命题“贯穿于马克思的著作,它尤其表现于马克思对人类本质和自由问题的思考”(40)。然而,细致的考察将会发现,亚氏的这一命题包含进一步诠释的空间。
凯特(David Keyt)在1987年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三个基本命题》中,认为亚氏的对于城邦的定义与后来的霍布斯明显不同。亚氏认为城邦就像人和动物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而霍布斯则认为城邦是人为约定的结果。然而,凯特指出,按照亚氏认为城邦是实践理性的产品的政治学原则,亚氏应该会同意霍布斯的结论。因此,在亚氏的政治学中存在着悖论:即亚氏一方面认为城邦的形成和延续依赖于立法者或统治者以及各项法律,因而,统治的“技艺”暗示了城邦本身是人为的产物;另一方面,亚氏又宣称城邦是自然的产物,而在《物理学》中,自然的东西本身内部已包含着自己变化。(41)
当然,亚氏的这一矛盾早已被人察觉到。但是普遍的做法是消解这一矛盾,即通过认为亚氏“设置了一种潜在的人性冲动,必须受到外在于人的来源的主动刺激,这种冲动才能被认为并且得到实行”(42)。而凯特显然拒绝这种做法,后来亚氏的注疏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43)笔者认为,内德门(Nederman)依据亚氏文本提出解释方案值得借鉴。内德门通过援引《论灵魂》、《论动物运动》,以及两个版本的《伦理学》的思想资源,试图证明“城邦对人而言是自然的,人是政治动物”,(44)“只有在城邦中,人才能充分地过道德的生活,因为只有城邦(通过城邦领导者和城邦的法律)才能提供人作为人而进行选择——即好好选择——所必需的教育”。(45)但是,内德门这一解决方案仍缺乏一个关键环节的论证,即如何证明城邦的运动就是人的运动,城邦是自然的产物如何正是人道成肉身的结果。在这一点,我们须回到质料与形式,潜能与现实的关系上。
在亚氏看来,任何事物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虽然亚氏没有明确使用过城邦的质料与形式这一用语,但是,如果按照亚氏的理论逻辑,这一用法是合法的。因为城邦也是事物,并且是自然物,因此,也必然存在着质料与形式的区分。那么,哪些部分是城邦的质料?哪些部分是城邦的形式呢?
城邦存在的基础是疆域和人口。柏拉图在《法律篇》曾论述过,制定法律时,需兼顾疆域的大小和居民两个要素。(46)亚氏同样认为,在城邦的各种条件中,公民的数量和土地是最重要的。(47)他以织工和船匠为例,在制造之前,如果能够准备好愈上乘的材料,那么,制成的作品则愈佳。同样,一个理想的城邦所需要的人口和疆域也应该恰到好处。“政治家所需要的原料首先是众多的人口,自然他必须考虑人口的数量和性质,然后照此考虑疆域的数量和性质。”(48)在亚氏看来,城邦的人口不是越多越好,疆域也不是越广越佳,两者皆要遵从适度原则:“人们知道,美产生于数量和大小,因而大小有度的城邦就必然是最优美的城邦。城邦在大小方面有一个尺度,正如所有其他的事物——动物、植物和各种工具等等,这些事物每一个都不能过小或过大,才能保持自身的能力,不然就会要么整个地丧失其自然本性,要么没有造化。”(49)可见,人口和疆域是城邦的载体,两者可以划分为城邦的质料。
但是人口和疆域并不能说明城邦的本质,决定城邦本质的是政体。“正如城邦是某种共同体,其公民共同参与某种政体,一俟政体的属类发生了变异,形成了与原先不同的政体,就可以说城邦已不复是昔日的城邦了,好比我们说悲剧的合唱队与喜剧的合唱队已然不同,尽管成员往往并没改变。”(50)一旦城邦的政体变化,则城邦的性质就发生变化,所以《政治学》才花大量的篇幅讨论何为最佳的政体,何为最合乎现实的政体。政体作为城邦居民的某种制度或安排,决定了城邦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说政体是城邦的形式。
质料与形式的结合体现为潜在与现实的运动关系。质料是潜在,形式是现实。(51)运动意味着“潜在存在作为潜在存在的现实”(52)。在亚氏看来,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区分为现实的和潜在的。潜在意指着事物可能的但尚未实现的状态,例如作为雕像的青铜、可建成房子的建材。现实(entelekheia)或实现(energeia)(亚氏经常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作为潜在的对立面,意指不同种类的潜在的实现或满足。如此一来,很容易将运动视为一种从潜在到现实的过程,陈康先生和罗斯代表这一观点。(53)然而柯斯曼(Kosman)对此提出质疑。(54)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先生对此方面作出了精彩分析。李猛先生认为,导致这一问题在于混淆亚氏考察运动的两个阶段。亚氏对运动考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回答“运动是什么”,而对这问题的解决,是充分理解“自然”的前提,须注意的是,在第一阶段的考察中,亚氏并没有讨论运动与连续的关系以及运动与时间的关系,这部分的关系是在运动的第二阶段分析中才被纳入考察的范围。第二阶段考察运动作为连续的东西,但对运动的考察的困难不在于说明连续的含义,而是澄清“变动”本身意味着什么。(55)“潜在存在作为潜在存在的现实就是运动”,这是亚氏对运动的第一定义,但在这一定义中涉及的不是一般意义的潜在,而是作为潜在的存在。运动不意味着潜在从缺失状态进入成全的状态,而是指潜在状态的完成。运动是质料对形式的渴望,是“‘形式自然’对‘质料自然’的凯旋”(56)。
笔者认为,李猛先生对运动分析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探明了质料自然与形式自然的存在关系,并通过“自然上先于”运动的潜在与现实来界定运动,从而突破了人们对亚氏运动循环定义的指责,并进而证明人工之“工”,仍需以自然为基础和目的。质料是可运动的质料,其标示着与通过运动获得的“形式”的存在关联。“潜在作为雕像的青铜,能够刻成赫尔墨斯的木头,能健康或也能得病的体液,可建成房子的砖头,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运动并不是在这些基底上武断任意地添加一种新的形式,而毋宁说是对基底潜在存在性质的成全。一位亚里士多德式的技艺大家,就是因为能够从现成的东西中洞察到这些‘处于潜在的东西’或者‘可运动的东西’,从而比普通人更深地触及到了存在的‘原因’和‘本原’。”(57)
对运动的考察,可以发现处于潜在状态的存在标志着质料具有接纳形式的内在倾向,而实现意味着这一内在倾向被置入形式之内。形式作为与质料相异的他者必须在质料的自然本性上发挥作用。质料与形式之间的潜在与成全关系已经蕴含在处于潜在状态的存在的“内在倾向”之中,人工与自然的区别在于,“在自然的情形中,这种倾向本身确保自然物足以通过自身运动,而在人工的情形中仍然必须倚靠思虑作为外在的本原”(58)。
人作为城邦最重要的质料,作为处于潜在状态的存在,其不仅具备这样一种通过联合的方式成就自身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足以通过自身来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氏在提出“城邦显然是自然的产物”(59)命题后,紧接着马上指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60)。城邦与人的同构关系在此可见一斑,人所谓的“技艺”恰恰证明城邦的自然。凯特以城邦是人缔造的结果来反对城邦的自然,等于把城邦掏空,将人从城邦中驱逐出去,而事实上人是城邦的质料自然。
城邦与人的同构关系进一步表现为,政体(城邦的形式)的设计应着眼于人的能力和德性发展。“城邦的任务在于促进人的能力从一种水平跃迁至另一种水平。”(61)其功能不仅在于满足人的生活,还在于让人过上好的生活。这种好的生活意味人的德性的实现和品质的完善。在这个意义上,城邦与人的关系才能如内德门所说:
立法者以某种方式培育宪政和法律,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促进邦民的福乐和道德上的善;政治家则应用并扩展法律以实现城邦的最终目的。他们的活动都没有使城邦成为人造物,城邦总归是要出现的,就因为它是人类欲求和选择的对象。立法者和政治家只是运用他们的实践智慧,以确保所出现的城邦成功地达到善的目的,而这善的目的正是一切城邦社会中的成员活动的“动因”。(62)
四、古典与现代
“城邦是自然的产物,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表明城邦与人的关系是内在的。只有在城邦中,人才能实现自身的潜能,实现德性,选择善行,发挥自身的禀赋;在城邦中,人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人的自由在他中与自身同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了同样的理念:“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3)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灶在于,在政治领域中,国家对于人而言,是一个抽象物;在经济领域中,物的发展以人的贫困和蠢笨为代价,共同体始终与人处于外在、对立的状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的粗糙论述奠基在亚氏对城邦与人关系的洞见之上。
然而,马克思比亚氏走得更远,他看到了古典城邦的自由是以牺牲整个奴隶阶级的不自由为代价的。在多个场合,马克思极力痛斥这种奴役制度。(64)古典的自由只能是少数人的自由。在自由、平等的启蒙之风席卷的现代世界里,马克思希望实现的是普遍的自由。
其次,马克思意识到,古典的自由仍是一种依附性的自由,真正意义的个人在古代没有形成。在古代,个人被束缚在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者这些个人发展了人”(65)。在过去冒充和虚幻的共同体里,“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这样的自由无疑戴上了幼稚、偏见的面纱。(66)
个人之所以不能呈现,之所以笼罩在共同体的纱幕中,是由于个人的利益被包含在由神性和封建宗法思想主导的集体利益之内。离开共同体,个人就没有独立的生存意义。作为集体组织成员的个人,随时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因此,“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67)
由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评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的“鲁滨逊”虚构,他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68)
在过去的时代,个人作为集体的附属,其属性和需要都来源于共同体。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这一状态,它推动自我意识的普遍发展,在整个社会生活层面形成了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观念框架。马克思看到,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创制活动的物质生产劳动中,彰显了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劳动,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对象世界。“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69),“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0)。个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主观意识与客观条件的根基。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一个体的发展仍是畸形的,它并非真正个体潜能的发展,相反,在物的支配下、在货币拜物教的笼罩下,个体过着双重的生活。现代社会分裂成两极:“一个要求自身利益、竞争和个体论,另一个则强调政治共同体、总体福利和普遍论。”(71)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都无法调和这一矛盾。自由主义对个体私利的强调只能导致愈演愈烈的个人间的对立,社群主义对国家的推崇则未能看到现代国家是一虚假的普遍性。
当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仍寄希望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制定管理社会的法则来实现共同体与人的真实关系:
参与立法权就是参与政治国家,就是表明并实现自己作为政治国家的成员、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因而全体人员都希望单个地参与立法权,这无非是全体人员都希望成为现实的(积极的)国家成员,或者赋予自己以政治存在,或者表明并有效地肯定自己的存在是政治存在。……因此,市民社会希望整个地即尽可能整体地参与立法权,现实的市民社会希望自己代替立法权的虚构的市民社会,这不外是市民社会力图赋予自己以政治存在,或者使政治存在成为它的现实存在。市民社会力图使自己变为政治社会,或者市民社会力图使政治社会变为现实社会,这是表明市民社会力图尽可能普遍地参与立法权。(72)
麦卡锡据此认为,在马克思人生的这一时期,他相信理性的权能和选举权的普遍化将会克服公共与私人、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分野。但是,经过莱茵报时期的社会实践后,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市民社会的真理不存在于政治领域,而存在于经济领域当中。由此,标志着马克思一个重要的转折,即将注意力转向研究市民社会和政治经济学。不过,即便在后期的著作中,马克思从未排斥早期所强调的民主、人本主义以及个体自由与权利。(73)
在笔者看来,虽然后来马克思思想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但是,古典城邦的理想并没有消失。这一理想可从1843年《评部颁指令的指控》的文章中,马克思总结了他在“莱茵报时期”所致力的工作中得出:“《莱茵报》从来没有偏爱某一特殊的国家形式。它所关心的是一个合乎伦理和理性的共同体;它认为,这样一种共同体的要求应该而且可以在任何国家形式下实现。”(74)而一个合乎伦理和理性的共同体正是亚氏《政治学》的主题。(75)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还未够成熟,但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1871年,即便已到垂暮之年,马克思仍然非常革命般地热情欢迎巴黎公社,尽管它的爆发与他的一切理论、一切预言相抵触。”(76)而巴黎公社的政治民主本身就是失落了的希腊自由理想的复活。(77)因此,古典城邦的理想——人是一个政治动物,其自由就是在他在中与自身同在——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追求。“在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那里都带有一种强烈的目的论人观,以及与此相应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观点,作为该目的表达和实现在起作用。”(78)随着现代工业体系历史发展以及社会世界的改变,“现代世界远远大和复杂于Polis的事实更昭示着现代生存的反讽性、自悖谬性”。(79)马克思必然与古人有众多的分歧,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与理想期待,古典传统融入马克思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并得以具体化。当马克思站在古人与现代人、过去与未来之间思考时,则不可避免呈现各种思想的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是马克思思想的魅力。
注释:
①马克思:《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957年12月21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7页。中括号处为手稿缺损。
②马克思:《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958年5月31日)》,同上,第540页。加粗字体为笔者强调。
③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④诺曼·杰拉斯:《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7页。柯亨(G.A.Cohen)和埃尔斯特(Jon Elster)也持这样的观点,可参G.A.Cohen,Review of Karl Marx by Allen W.Wood,Mind,XCII,No.367,July 1983,pp.443-444; 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62-205页。
⑤诺曼·杰拉斯:《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5页。
⑥斯图亚特·怀特:《需要、劳动与马克思的正义概念》,载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9页。
⑦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的纷争也恰好印证了一这点。以弗洛姆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倾向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倾向也体现了这一张力。
⑧国内学界最近关于历史决定论与主观能动性张力的讨论,可参考郭奕鹏整理并综述:《聚焦历史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载《现代哲学》2012年第5期。关于马克思思想中的张力亦可参见徐长福:《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及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开显》,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2期。
⑨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⑩同上,第20页。
(11)同上,第21页。
(12)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13)Bruno Kaiser,Ex Libri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Dietz Verlag,1967,pp.221-222; 转引自Michael DeGolyer,The Greek Accent of the Marxian Matrix,in Geroge E.McCarthy eds.,Marx and Aristotle.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Classical Antiquity,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2,p.115.麦卡锡主编的《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一书由郝亿春等合译,近期将出版,笔者参与其中一篇文章的译校,在此特别感谢郝亿春老师提供全书的译稿,下列的引文涉及此书的均来自此译稿,部分术语作调整。
(14)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5)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59页。
(16)Horst Mewes,Karl Marx and the Influence of Greek Antiquity o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 Thought,in Geroge E.McCarthy eds.,Marx and Aristotle,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Classical Antiquity,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2,pp.22-23.
(17)鲍毕生:《德国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18)同上,第89页。马克思在中学期间,已经具有较好的古典语言修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32页。
(19)鲍毕生,《德国教育史》,滕大春,滕大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
(20)Lukacs,Goethe and His Age,London:Merlin Press,1968,p.12.
(21)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26页。
(22)作为“古典教育”的缩影,柏林大学成为当时对古典名著评注性版本编辑、评注性评论,以及词典编纂学文献、哲学文献、考古学文献和历史学文献的中心。可参见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51-171页。
(23)Steven B.Smith,The Origins of the Dialectic,in Geroge E.McCarthy eds.,Marx and Aristotle,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Classical Antiquity,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2,p.77.
(2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84页。
(25)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3页。亦可参见Ritter,Hegel and French Revolution,MIT Press,1982,p.70.
(26)马克思:《给父亲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27)同上,第11页。
(28)马克思在这一期间还摘录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卢登的《德国史》,并且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一部分,见马克思:《给父亲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16页。
(29)George E.McCarthy,eds.,Marx and Aristotle,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Classical Antiquity,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2,Introduction,p.1.
(30)E.M.Butler.The 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Cambridge,1935,p.6.转引自Michael DeGolyer,The Greek Accent of the Marxian Matrix,in Geroge E.McCarthy eds.,Marx and Aristotle,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Classical Antiquity,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2,p.116.
(31)DeGolyer,The Greek Accent of the Marxian Matrix,in Geroge E.McCarthy eds.,Marx and Aristotle,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Classical Antiquity,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2,p.118.
(32)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33)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212页。
(34)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35)马克思:《博士论文》,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36)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9页。
(37)David J.Depew,The Polis Transfigured:Aristotle's Politics and Marx's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in George E.McCarthy eds.,Marx and Aristotle,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Social Theory and Classical Antiquity,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2,p.40.
(38)卡弗:《政治性写作: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形象》,张秀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39)马克思:《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40)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
(41)David Keyt,Three Fundamental Theorems in Aristotle's Politics,Phronesis,Vol.32,No.1(1987),p.54.
(42)内德门:《政治动物之谜——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中的自然与人为》,载刘小枫主编《城邦与自然》,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
(43)例如查恩(Joseph Chan)试图通过区分城邦的类型与城邦的形式来化解其中的矛盾,这种做法虽然有吸引力,但在亚氏的文本却难得找到依据,见Joseph Chan,Does Aristotle's Political Theory Rest on a “Blunder”?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3,Summer,1992,pp.196-197; 对这一问题的洞察和讨论还可参看:R.G.Mulgan,Aristotle's Doctrine That Man Is a Political Animal,Hermes,102 (1974),pp.438-445; David J.Depew,Humans and Other Political Animals in Aristotle's “History of Animals”, Phronesis,Vol.40,No.2 (1995),pp.156-181; 阿莫伯勒(Wayne H.Ambler):《亚里士多德对城邦自然性的理解》,载刘小枫主编《城邦与自然》,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83-108页。
(44)内德门:《政治动物之谜——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中的自然与人为》,载刘小枫主编《城邦与自然》,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
(45)同上,第114页。内德门的相关论证请参看此书第114-133页。
(46)柏拉图:《法律篇》,载《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1-462页(卷四704-709)、第506页(卷五747D)。
(4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1325b40。
(48)同上,第236页,1326a5-6。
(49)同上,第236-237页,1326a29-40。
(5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6页,1276b1-5。
(51)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秦典华译,载《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三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页,412a10。
(52)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徐开来译,载《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8页,201a10-11。
(53)陈康:《论希腊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60页;另见W.D.Ross,Aristotle's Phys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p.359.
(54)L.A.Kosman,Aristotle's Definition of Motion,Phronesis,vol.14,no.1 (1969),pp.40-46.转引自李猛:《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义:一个存在的解释》,载《世界哲学》,2011年第2期,第158页。
(55)李猛:《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义:一个存在的解释》,载《世界哲学》,2011年第2期,第162页。
(56)同上,第183页。
(57)同上,第178页。
(58)同上,第178-179页。
(5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1253a3-4。
(60)同上,第4页,1253a3-4。
(61)Nartha Nussbaum,Nature,Function,and Capability:Aristotle on Political Distribution,in George E.McCarthy eds.,Marx and Aristotle,pp.175-176.
(62)内德门:《政治动物之谜——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中的自然与人为》,载刘小枫主编:《城邦与自然》,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64)比如1864年11月,马克思致信祝贺林肯再度当选美国总统,指出:“如果说反抗奴隶主的权势是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留有余地的口号,那么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口号则是:让奴隶制死亡。”见马克思:《致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页。在对“思想巨人”亚里士多德和经济学侏儒巴师夏的对比中,马克思不无遗憾地指出,亚氏在评价奴隶劳动也难免发生错误,参见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
(66)同时代的研究者布克哈特从文化的角度表达与马克思同样的洞见,他认为文艺复兴之前,“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庭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见〔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马香雪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68)马克思:《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6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黑体为原文所加。
(70)同上,第310页。黑体为原文所加。
(71)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4页。
(7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黑体为原文所加。
(73)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5页。
(74)马克思:《评部颁指令的指控》,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6页。黑体为原文所加。
(75)克诺斯(G.E.M.de Sainte Croix)在《古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一书中讨论了马克思与亚氏的相似之处,并指出1843-1845年,马克思集中阅读了《政治学》,这一阅读经历对马克思后来的阶级斗争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可参见Nartha Nussbaum,Nature,Function,and Capability,p.211,note 47.
(76)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77)Horst Mewes,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in the Early Work of Karl Marx,Social Research,Vol.43,No.2,(SUMMER 1976),p.291.
(78)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
(79)刘森林:《实践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