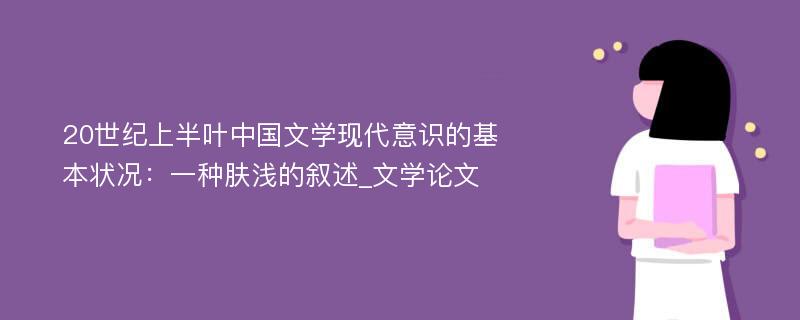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情形———种表面的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情形论文,表面论文,意识论文,半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实处境和传统文化的危机已经暴露无遗,作为危机的一种焦虑式反应,域外新说特别是西学的引进,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大热情从事的一项工作。除严复、梁启超等以外,更为年轻的王国维于此用力甚深,有研究者统计,他署名和未署名的译篇字数以百万计,广及13个方面,而以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为大宗。(注:佛雏:《王国维引进西学述略》,为《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一书的附录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00— 406页。)尤为突出的是他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译介和运用,从他早期一系列个人色彩极浓的哲学、美学论文和文学批评,乃至诗词创作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叔本华和尼采学说的深刻印记,而且他把外来的思想融入了自我个体生命的内部,使之从外在的东西变为感同身受的切己内容。1904年,27岁的王国维撰《红楼梦评论》,立脚于叔本华的理论,通过对一部中国古典名著的全新解释,勾画了一幅由意志、欲望、痛苦、解脱等诸要素环环相生、节节相扣而其中又有绝大之疑问存焉的人生图景。
稍晚一些时候,1907年,鲁迅作《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发表于次年的《河南》月刊;这一年的《河南》还发表了没有写完的《破恶声论》。这3篇论文和2册《域外小说集》集中体现了辛亥革命前鲁迅的现代思想意识。《摩罗诗力说》所述的是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派”,在思想和艺术风格上大多可归为浪漫派或“前现实主义者”,可是鲁迅却程度不等地为他们涂上了尼采的色彩,做了接近现代思想意识的变形,而且这篇文章的题记就出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文化偏至论》则直接介绍西方现代文化,论述了斯蒂纳、基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易卜生等。其中尼采思想对早年鲁迅产生的影响最为突出,一如在更大的范围里,此前此后一段时期内介绍过来的西方哲学家中,尼采对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是最大,新文学初期的其他重要作家,如郭沫若、沈雁冰、田汉等,也或著文或翻译,宣传和张扬尼采学说,形成思想热点和冲力。(注:田汉译《说尼采的〈悲剧之发生〉》,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沈雁冰的长文《尼采的学说》,连载于《学生杂志》第七卷第1至4号,1920年1至4月;唐俟(鲁迅)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载《新潮》第二卷第5号, 1920年9月;郭沫若译《查拉图斯屈拉》第一部和第二部共26节内容, 分26次连载于1923年5月至1924年2月的《创造周报》。)
除了尼采的个人主义意志崇拜和建立在批判传统文明与市侩主义基础上的超人哲学,对中国新知识分子现代意识的形成产生过相当大作用的,还有柏格森的反理性的直觉主义和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1914年,《东方杂志》介绍了柏格森的学说,随后又有《教育杂志》、《新青年》、《民铎》等刊物推波助澜,(注:钱智修译《布格逊学说之批评》,载《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4号,1914年9月1日; 钱智修:《法国大哲学家布格逊传》, 载《教育杂志》第八卷第 1 期,1916年1月20日;刘叔雅:《柏格森之哲学》,载《新青年》第四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柯一岑:《柏格森精神能力说》, 载《民铎》第三卷第1号,1921年12月1日。其它介绍柏格森的文章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民铎》第三卷第1号为柏格森专号, 上举柯一岑的文章还由柏格森学说介绍了“意识流”(Conscious Stream)的概念。)张东荪译释的《创化论》191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21年《民铎》第三卷第一号推出柏格森专号(其中的作者和译者有严既澄、柯一岑、蔡元培、张东荪、李石岑、吕澂、瞿世英、冯友兰、杨正宇、范寿康、梁漱溟、张君劢等),柏格森思想的传播已达高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柏格森学说差不多同时介绍进来,到20年代,出现了系统细致叙述其理论的长文,如朱光潜的《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注:朱光潜:《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载《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14号,1921年7月25日。), 而且出现了将精神分析运用于文学批评和人物考释的实际尝试,其中有名的例子,如郭沫若1921年作《〈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注: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收入《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以证文艺创作源于性欲的升华;到1923年,他又发表《批评与梦》(注:郭沫若:《批评与梦》,载《创造》季刊第二卷第1 期,1923年5 月。),更以自己的创作来验证精神分析学说。再如潘光旦1924年发表的《冯小青考》(注:潘光旦:《冯小青考》,载《妇女杂志》第十卷第11期,1924年。后来潘光旦又对此文“重加厘定,于其性心理变态,复作详细之探讨”,充实成《小青之分析》一书,1927年9 月由新月书店出版,再版时书名改为《冯小青》。),以弗洛伊德的“自恋”、儿童性欲说对一个中国明末女子作典型的精神分析,堪称绝妙佳例。鲁迅也坦言他的“故事新编”《不周山》,是取弗洛伊德之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注:《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41页。)。例证繁多,不胜枚举,事实是从20 年代一直到40 年代的文学创作,弗洛伊德的影响不绝如缕,在在可见。 这其中有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令人注目,那就是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明权选择连载于《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21年1月16日至22 日),而后又有“未名丛刊”鲁迅的译本和“文学研究会丛书”丰子恺的译本,鲁迅译本至1935年已经印到12版。(注:《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本列入“未名丛刊”,新潮社1924年12月第 1版,北新书局1928年8月第5版,1935年10月第 12 版;丰子恺译本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1925年3月第1版,1932年9 月国难后一版。)这部书的作者创造性地综合了柏格森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对文艺的起源作了现代主义观念的解释,强调生命力的冲动和创造,这一思想不仅波及创作,而且渗透进中国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中,直到40年代胡风的文艺理论,仍然可见其活跃的冲击力。
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认同和共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还有,作为另一种相反的力量——对吸引、认同、共鸣的抗拒——又将怎样表现出来呢?这样复杂的问题当然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不过我们却可以通过具体的事例略窥一斑,想见彼时的情境和思想、心灵深处的惶惑及其复杂的表现。
民国初年在舆论界影响甚大、同时也应被视为新文学运动先驱人物的黄远生,曾作《想影录》,刊于1916年2月的《东方杂志》, 该文主要是摘译日人大住啸风所著《新思想论》,揭示和宣泄“过渡时代之悲哀”和“现代思想之烦闷”(这是文中的两个小标题)。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之前,黄远生已于1915年末在美国旧金山遇刺身亡。与他有所交往的年轻朋友梁漱溟读了《想影录》,深受刺激,他觉得黄远生带着绝大的困惑苦恼而去,而他本来是有法子帮他解除这绝大的困惑苦恼的:“余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濆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愿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这亟草而成的,就是《究元决疑论》,发表于同年5、6、7 月的《东方杂志》。《究元决疑论》针对人“陷大忧恼病苦”、于世间“恐怖犹疑不得安稳而住”的生存境遇而发,也就是说,梁漱溟基本上承认黄远生和西方近现代诸家所揭示的诸多文化和精神症候,他在这篇不算太长的文章里引述西方新说颇多,间采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康德、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的思想为己用,甚至赞叹说,“柏格森(Bergson 即《想影录》之别克逊)之所明,尤极可惊可喜。”可是他最终要说的是这些西方新说都不能解决问题,“如所谓‘现代思潮不以宗教伦理为目的’者(远生《想影录》),正此有漏非真之穷露,而不复为人所信。”他认定和开出的药方是佛法,所以十分痛心于“如来大法近在眼前,而不知求(《想影录》所译《新思想论)无一语及佛)”的社会趋势。(注:梁漱溟:《究元决疑论》,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1—22页。)
梁漱溟后来承认这篇东西“荒谬糊涂”(注:这是1933年5 月梁漱溟为这篇文章写的“附记”里的话,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21页。),不过他似乎仍然没有讲出其中的一个要害就是他用佛法来“究元决疑”,很大程度掩盖了现代社会文化症候和现代人精神痛苦的现代特性,细心的读者从行文中不难感受到,这种带着强烈现代特性的症候和痛苦同样体现在当时的梁漱溟自己身上,但却被他以佛法的无时间性(似乎任何时代、遭遇任何问题,都可以用佛法来“究元决疑”)压抑了。但是在黄远生的文章中,这种现代特性却充分地突现出来。他说到本国“思想界之枯窘”,所以要择取域外著作“道着痛痒触人心脾者”译录介绍;而域外“今日文明国人,亦多苦于思想之烦闷,及不统一,”“产业益进,机力愈伟,生活愈难,神经刺激,较吾曹更甚。今日吾曹不新不旧,不中不西,青黄不接,与彼相同而所以致其苦痛者,家国之故,较彼更深,自哲人视之,其为身世之感,人生之忧,则一也。”(注:黄远生:《想影录》,《远生遗著》卷一,商务印书馆1984年5 月增补影印第1版,第160—161页。标点为引者试加。)而在此之前,1915 年11月发表于《东方杂志》的《忏悔录》中,黄远生却基本不涉“家国之故”,集中剖露个人精神的黑暗面和分裂冲突。“吾之一身,有如两截,一为傀儡,一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灵魂。吾之灵魂,实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其二方其梏置之初,犹苦槛兽羁禽,腾跳奔突,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从狱隙之中,稍冀须臾窥见天光。惨哉天乎,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而已。”(注:黄远生:《忏悔录》,《远生遗著》卷一,第124—125页。标点为引者试加。)黄远生的好友林宰平曾经说:“我刚读他《忏悔录》,就像读卢梭和托尔斯泰《忏悔》的时候,受了很大的感动。远庸没有卢梭的胆力,又没有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所以他格外苦。”又抱憾道,“我闲时常想着,若使远庸没有死,今日必变为新浪漫派的文学,他本是个极富于感情思想的人,又是观察力最强不过的人,自然会与现代最新文艺的潮流相接近了。”(注:林宰平:《〈远生遗著〉序》,《远生遗著》,第14、11页。)
黄远生这样一个突出人物的事例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般情形,但是,他真诚披露的内心苦闷却也并非孤绝的个例,其时代性症候倒不妨视为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苦闷的象征”。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倾向,使得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更具吸引力。
二
从西方现代哲学文化思潮的吸引力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吸引力,这之间几乎不需要什么过渡,实际上它们差不多就是并行于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萌生和建设期的。在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中国文学界介绍波德莱尔、王尔德、史特林堡、梅特林克、安德列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勃洛克的热情决不低于介绍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左拉、雨果的热情。据陈思和统计,在1925年以前,以当时介绍外国文学最有影响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诗》、《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20余种的篇目为例,系统介绍西方写实主义(或称作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著译文章约有9篇; 系统介绍现代主义(包括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具体流派)思潮的著译文章约有12篇;介绍浪漫主义思潮的著译文章不过四五篇。现代主义居首位。如果同时考虑到对具体作家作品的介绍,并与对文学思潮的介绍加以对比的话,我们则可以发现,写实主义思潮和作家的介绍篇目居多;浪漫主义思潮介绍篇目少,作家介绍篇目多;现代主义思潮介绍篇目多,作家介绍篇目相对少。从这个情况大致可以看到,中国作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趣不在于具体技巧,而在于现代主义文学反映的现代意识。(注:陈思和:《七十年外来思潮影响通论》(上篇),《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43页。)
粗略地说起来,在30年代之前,现代主义文学中多被注意和译介的主要是一些早期的现代主义者或称现代主义的“根子”作家,如波德莱尔、王尔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到三四十年代,兴盛期的现代主义作家如弗吉尼亚·伍尔芙、T·S·艾略特、奥登等,他们的作品或以汉语译文或直接以原文的形式在中国年轻的知识者中产生实际的作用。甚至在30年代前期的杂志中,我们都能读到对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介绍评述,(注:凌昌言:《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载《现代》第五卷第6期,“现代美国文学专号”,1934年10月1日。)不过其具体的影响就不可考了。
或许可以通过选取关联性较为密切和明显的俄、法、英美文学的几个重要的方面,来看看进入汉语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意识错综复杂的情形。
如果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主义忽略了在俄国特殊发展的一部分,那么在考察现代主义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时将会留下很大的遗憾。俄国文学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一些具有强烈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除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安德列耶夫、阿尔志跋绥夫、梭罗古勃、勃洛克等人的作品也对一些新文学作家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颇有意思的是,这特殊的吸引力往往被统一在“为人生”的大前提之下,仿佛是“无派别的人生的文学”,接受者既认同其与社会现实的紧张性关系,又包容和吸取了各种“非写实主义”的艺术处理方式。譬如早在1918年就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的周作人、(注:[英]W.B.Trites著,周作人译《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载《新青年》第四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1922年发表万余言长文《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的沈雁冰,(注:沈雁冰:《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载《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1号,1922年1月10日。)都基本不脱“为人生”的论说框架。可是这样的论说框架毕竟不可能框住作品具有的非凡穿透力和读者可能产生的全部感受与认知。1926年,鲁迅坦言,统论陀氏人与作品之全般非能力所及,可是他的管窥之说却令人吃惊地发现他个人的阅读感受异常丰富和强烈:陀氏不仅把他作品中的人物施以精神的苦刑,还同时将自己也加以精神的苦刑,而且,“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出灵魂的深。”(注:《〈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04页。)这个印象一定非常深刻,以致于10年后, 鲁迅又重复说道:“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伟大的残酷甚至使鲁迅“常常想废书不观”。(注:《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11—412页。)另一位小说家阿尔志跋绥夫,也刺激鲁迅产生出异常强烈的感受,并且还费力“几乎是逐字译”出了《工人绥惠略夫》,他说阿氏的《赛宁》写出了“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这一种倾向,虽然可以说是人性的趋势,但总不免便是颓唐。赛宁的议论,也不过一个败绩的强者的不圆满的辩解。阿尔志跋绥夫也知道,赛宁只是现代人的一面,于是又写出一个别一面的绥惠略夫来,而更为重要。”绥惠略夫“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来。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终身战争,就是用了炸弹和手枪,反抗而且沦灭(Untergehen)。”“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包围的书。”(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全集》第十卷,第167、169页。)鲁迅对这两位俄国作家的议论,显然不是无关己身的现实境遇和精神状况的客观介绍,换句话说,如果鲁迅从他们那里读出了现代意识,那么这种现代意识也同时是从他自身的境遇和状况中读出来的。
象征主义应该算是在中国新文学中产生了广泛和深入影响的流派,如果开列一份传输译介者的详尽名单,这份名单会显得过长而令人一时难辨轻重。不过至少这两个人的名字十分显眼:李金发和梁宗岱。可是这两个人带给中国的象征主义差异甚大,这主要倒不是因为他们呈现象征主义面貌的方式不同:李金发主要以自己的诗创作,梁宗岱主要以相关的理论探讨和诗的翻译,各展所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取向的各有偏重:法国象征主义从波德莱尔发轫,嗣后经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瓦雷里相继承传,转折光大,李金发所取以波德莱尔为重点,梁宗岱所向以瓦雷里为核心。但这也只能是一个大概的说法,细究起来恐怕要更复杂一些。不过以在汉语情境中所起的实际效果而论,李金发在诗界内外造成了惊世骇俗的震惊性反应,以艺术上的不羁体现出反抗庸俗社会的强烈现代意识,他在诗中模仿了波德莱尔及其追随者所实践的通常称之为“波希米亚”式的姿态,这种艺术和生活的方式“有时也用一个更加简单化的词语‘épater le bourgeois’(‘使墨守陈规者惊异’)来表示”(注: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现代百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52页。);而梁宗岱则是潜心于诗艺内部中西诗学的融会贯通,可谓取精用宏,苦心孤诣。1934年,《文学季刊》第2期发表的《象征主义》一文, 不仅仅是介绍一个西方的思潮和流派,更是深入地探求中西诗学沟通的可能性,显见深的修养和大的用力,至今仍不失为这方面的力作。这也难怪倾心于诗艺求索的卞之琳会产生出这样的比较性评价:他先已从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的译介和仿作中接触到了象征主义,“但他们炫奇立异而作贱中国语言的纯正规范或平庸乏味而堆砌迷离恍惚的感伤滥调,甚少给我真正翻新的印象,直到从《小说月报》上读了梁宗岱翻译的梵乐希(瓦雷里)《水仙辞》以及介绍瓦雷里的文章(《梵乐希先生》)才感到耳目一新。我对瓦雷里这首早期作的内容和梁译太多的文言词藻(虽然远非李金发往往文白欠通的语言所可企及)也并不倾倒,对梁阐释瓦雷里以及里尔克的创作精神却大受启迪。”(注:卞之琳:《人事固多乖:纪念梁宗岱》,《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 期。)而且梁宗岱本身是诗人,以诗笔涉理论,常常意象纷披,不惟开启思路,而且诉诸深切的感受性,譬如论说象征之道在于契合,不禁思接千虑、神游无极:
当暮色苍茫,颜色,芳香和声音底轮廓渐渐由模糊而消灭,在黄昏底空中舞成一片的时候,你抬头蓦地看见西方孤零零的金星像一滴秋泪似的晶莹欲坠,你底心头也感到——是不是?——刹那间幸福底怅望与爱底悸动,因为一阵无名的寒颤,有一天,透过你底身躯和灵魂,使你恍然于你和某条线纹,柔纤或粗壮,某个形体,妩媚或雄壮,或某种步态,婀娜或灵活,有前定的密契与夙缘;于是,不可解的狂渴在你舌根,冰冷的寂寞在你心头,如焚的乡思底烦躁在灵魂里,你发觉你自己是迷了途的半阕枯涩的歌词,你得要不辞万苦千辛去追寻那和谐的半阕,在那里实现你底美满圆融的音乐。(注:梁宗岱:《象征主义》,《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6页。)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立基于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李金发和梁宗岱的不同,也许正可以看作同一种认同危机的不同的诗性反应。这种认同危机的不同反应也极可能在同一个诗人身上表现出来。譬如闻一多,按照叶维廉的说法,他的很多首诗表达的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死亡的欲望”,像早期的《烂果》和著名的《死水》,但“烂”、“死”之后就一定会出现新生吗?在被誉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里,闻一多写道:“给我一个奇迹,/我也不再去鞭挞着‘丑’,逼他要/那分儿背面的意义;实在我早厌恶了/那勾当,那附会也委实是太费解了。/我只要一个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闪着/宝光;我要的是整个的,正面的美。 ”(注:闻一多:《奇迹》, 《诗刊》创刊号,1931年1月20 日; 此处引自《闻一多全集》第一卷,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61页。)他对现实的世界无能为力,就用文字创造出一个理智、经验、传统和想象“结晶”的世界,当“奇迹”出现时,显身的不是世间的事物,而是文字升华出来的造物。“这几乎是象征主义者马拉美所说的:‘我说一朵花,不是地面上或花铺里看到的花,而是一朵由文字里音乐地升起的花!’闻一多和马拉美两者所面临的历史需要和条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亦没有看到闻一多研究象征主义太多的痕迹,但在不同历史不同空间里,由于完整性受到破坏的危机(尽管马拉美的文化完整意念和闻一多想的完整意念是不同的)而有了相似的对艺术的肯定。”(注:叶维廉:《语言的策略与历史的关联》,收入《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年1月第1版,第223—225页。)
正如同是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的诗风差异很大,同是新月派理论家的叶公超和梁实秋,其理论趣味和文学观念的不同也相当显著。叶公超对当下西方文坛的关注和他特殊的现代敏感,使他成为30年代介绍英美现代主义的重要人物,特别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譬如关于T·S·艾略特,虽然早在20年代就提到过他的名字,(注:如1923年8月27日出版的《文学》周报载玄(茅盾)的《几个消息》, 说艾略特为英国新办杂志Adelphi的撰稿人之一;1927年12 月《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12号载佩玄(朱自清)译R·D·Jameson 的《纯粹的诗》,把艾略特作为代表纯诗趋向“激进的作家”予以介绍。)但系统深入的评述还要等到叶公超的《爱略特的诗》和《再论爱略特的诗》(注:分别载《清华学报》第九卷第2期,1934年4月;《北平晨报·文艺》第13期,1937年4月5日。后者为赵萝蕤译、上海新诗社1937年初版《荒原》的序言。另外,叶公超主持的《新月》“海外出版界”专栏在 1933年3月1日出版的第四卷第6期上介绍了美国F·R·Leavis的《英诗之新平衡》一书,其中论述到艾略特和他的《荒原》。),除此之外,还有一篇译文《T·S·艾略忒与布尔乔亚诗歌之终局》(注:〔俄〕D·S·Mirsky:《T·S·艾略忒与布尔乔亚诗歌之终局》,罗莫辰译,《文季月刊》第一卷第3号,1936年8月1日。)也可称得上是有份量的文章。 叶公超的学生卞之琳翻译了《传统与个人的才能》,载1934年6 月的《学文》创刊号;另一位学生赵萝蕤翻译了《荒原》,1937年由上海新诗社印行。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受到当时任教的英国诗人和批评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影响,一些学生诗人热衷于学习和讨论艾略特、奥登等的作品,同时把自己在中国严酷现实环境里的个人感受激发和磨砺得更加敏锐,孜孜以求复杂的现代意识的文学表达,从而形成一个自觉的现代主义诗创作的群体,而且造就出穆旦这样的中国新诗史上的杰出者。
不过,如果要说到中国诗人对英美现代诗的回应,特别是对艾略特作品的回应,早在西南联大那群青年诗人之前,就出现了不同凡响的创作:那就是也属于新月圈子的孙大雨的长诗《自己的写照》。这首诗写于1930年间的纽约、俄亥俄的科伦布及诗人回国之初,原计划写1000余行,实际完成的也有近400行。(注:孙大雨:《自己的写照》, 分别载:《诗刊》第2期,1931年4月20日;《诗刊》第3期,1931年10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9期,1935年11月8日。 )长诗的主角是现代文明的巨子、庞杂而畸形的纽约城,借用李振声的评述,“下坠的堕落与向上的活力、罪孽与救渡、排斥与迷惑,各种相异的力量,在诗中神奇地彼此缠绕。缠绕得如此诡巧和密不可分,以至我们就像抒写者一样,无法公然将它们厘分清楚。纽约城粗俗的活力构成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引领抒写人四处追诘,以便对它内藏的生命玄机作出寻索。尽管长诗最终未能完成,以致它意欲对纽约生命玄机作出反诘、置疑和反讽的一番勃勃雄心,最终不得不付诸阙如,但即便就它现存的残篇格局来看,它那赋予混乱的世界以一种秩序的气度,以及笼络、驾驭、吞吐、消化现代都市的雄健精力,这方面能与之相匹俦者,却是至今依然罕见其人。”长诗第一部分写“纽约日常情景:嘈杂的街衢,川流不息的轮轴,做着黄金梦的投机家,汗臭,蝼蛄争逐的人群,震动总量足以轰坍任何一座高楼的打字机声,汇聚自整个世界的肤色各异的痛苦,以及苟且的性……。抒写者似乎在力图暗示,现代世界真正的奇异和神秘不在别处,而就深藏活跃在日常情景之中。麇集在抒写者四周的嘈杂语声,那些茫无头绪、杂乱无章的对白和呓语般的潜对白,则折射出源自粗俗物欲的活力以及尘埃般盘根错节万众杂沓的生态和心态。诗行的推进,是对飞驰在黑暗中的地铁节奏的模拟,迫使我们的思路作出理智难以为继的跳越,使人在阅读的被动中,隐隐感受到一种不可解释却异常有力的诗对现实的涵盖和统摄。‘大站到了,大站到了’的地铁催促声,不由使人联想起艾略特《荒原》中的‘时间到了,请赶快/时间到了,请赶快’,二者异曲同工地泄露出川流不息的知觉所意识到的现代时间带给生命的压抑和紧张。在这个疯狂运转的都市里,人的地位已被悬置。在更多的时候,并非人在操纵物,而往往是物,准确点说是物欲在驱迫着人行动。速度在追杀一切,从肉体到灵魂,一切都转瞬即逝,人在无限增长的速度面前正在渐次丧失自己的本质。”(注:李振声:《孙大雨〈自己的写照〉钩沉》,《小说家》1999年第3期。)
大约就在孙大雨凭借一个异域的都市批判地勾勒现代人错综意识图像的前后几年,在中国上海,这个奇迹般崛起的充满异国情调的现代都市,也正有一部分诗人和作家在表达着他们都市经验的特殊意识和感受,其中以邵洵美等为代表的颓废——唯美的小团体、以穆时英和刘呐鸥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成为20年代后半期到30年代前半期上海都市文学引人瞩目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这些作品所呈现的放松地享受感官快乐或焦虑地为现代欲望所困的都市情境当中,我们不无迷惑地发现,都市魔幻般地失去了客观的现实性,它不是一个等待主体去把握的对象,它自己就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主体,在极端的情况下,置身于都市空间内的人反倒成为吸附在这个巨大主体身上的细微的存在,乃至于只是这个巨大主体的感觉器官。
可是,现代都市所激起的意识、感受和经验的文学表达并非只是如此,就在同一时期,冯至500 行的长诗《北游》就显示出相当明显的差别。这首诗在1928年开始的头3天时间里一气呵成, 为另一种异国情调的北方殖民地化都市哈尔滨绘制了一幅复杂迷离的立体画。在这首从头到尾写满了“阴沉,阴沉……”的长诗中,冯至把对现代畸形文明的批判和叙述者个人的精神痛苦、反省、追问互相交织起来。耳闻目睹,象征着神圣的“礼拜堂”躲在无人过问的角落,“巍巍的建筑好像化作了一片荒原”,“啊,这真是一个病的地方,/到处都是病的声音”,“这里的人把猪圈当作乐园,/让他和他的子孙同归腐烂!”而反诸自身,“我心中有铲不尽的泞泥”,“我全身的血管已经十分紊乱,/我脑里的神经也是充满纠纷”。处在一种普遍的现代困境和个人的精神危机之中的叙述者,却无法用颓废——唯美的方式来缓解焦虑:“我思念,/世纪末的诗人——/用美人的吻来润泽他们的焦唇,/用辛辣的酒浆灌溉他们憔悴的灵魂。/我呀,灵魂憔悴,唇已焦躁,/无奈我的面前美人也不美,醇酒也不醇。”“我只能这样呆呆地张望,/望着市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各各的肩上担着个天大的空虚,/各各的肩上担着个天大的空虚,此外便是一望无边的阴沉,阴沉……”(注:冯至:《北游》,北平沉钟社1929年第1版。此处引文据《昨日之歌》, 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47至66页。)
冯至的诗,要到40年代的《十四行集》才达到最高的成就。在战乱频仍的4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经由不同类型的作家,得到了差异性巨大却也不妨视为互相映照的表达。其中尤为突出者,可以举出沦陷区上海张爱玲的创作,国统区重庆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小说,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在张爱玲饮食男女浮世悲欢的低调曲折叙述中,我们会突然遭遇到人生的虚无和整个文明毁灭的重创,似乎是无端地涌起了洪荒的恐怖。胡风一贯强调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其理论的基本框架也确实可以看作是融入了“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但是我们从他那诗一般的语言的表述中,分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框不住他从自身的情境中生发出的强大的感性力量,框不住他在窒闷庸俗的现实中所体验到的压抑、紧张和精神撕扯、“肉搏”的痛苦和欢乐;而胡风的理论和路翎的小说创作之间的互相激发、互相调动,也应该有助于佐证胡风理论中的现代主义因素。路翎小说铺张的高密度的心理因素和超强度的生命能量,以及常常飞奔在理智与疯狂边缘的狂热叙述和异端形态,更不可以统统纳入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下来,即便是胡风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也有力不能及的地方。西南联大的学生诗人中的几个,在抗战胜利以后,又组合进一个先后围绕着《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松散的创作团体中,这个团体以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与同期的其它诗歌创作相区别,到80年代初,其中的9位诗人——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 唐祈、 唐湜、袁可嘉、穆旦——合出一本诗集《九叶集》( 注:《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而得名九叶派。
三
随着40年代的结束,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世纪的上半期逐渐成形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并没有随着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结束而寿终正寝,在以后的历史变迁中,它还会寻找到合适的时机,产生深远的影响。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创作的兴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即可以看作是这一文学现代意识的延续。1936年和戴望舒、徐迟集资创办《新诗》的路易士(纪弦),于1953年2 月创办《现代诗》杂志,1956年拟定“现代诗社”六大信条,大张旗鼓地提倡现代主义。1956年9月,夏济安主编《文学杂志》,到1960年8月休刊共出版了八卷48期,大量译介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理论和批评,同时着力扶植青年作家的成长,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等一批作家都是台大外文系夏济安的学生,他们在《文学杂志》停刊之后创办了《现代文学》,造成浓烈的现代意识氛围。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夏济安的《文学杂志》其实是他10余年前在上海参与编辑的《西洋文学》(注:《西洋文学》编辑同人共6人:张芝联、夏济安、柳存仁、徐诚斌、林葆园、林憾庐。后二者是挂名的,前4人是撰稿、组稿的主要力量。 参见张芝联《五十五年前的一次尝试》,《读书》1995年第12期。)的复活。《西洋文学》1940年9月创刊,维持到1941年6月,共出10期,以翻译为主,其中出过詹姆斯·乔易斯和叶芝的特辑,每辑包括作家小传、原著选译、评论等,如乔易斯特辑就有诗选、短篇《一件惨事》和《友律色斯(Ulysees )插话》三节、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的《乔易斯论》等内容。这份短期杂志差不多把威尔逊《阿克塞尔的城堡》的大部分内容都翻译过来了。大陆70年代末80年代提倡现代主义创作、翻译介绍现代主义作品和理论,也大大得力于一些前半个世纪里就受此熏染或致力于此的诗人、批评家、翻译家,我们可以举出徐迟、袁可嘉等人的例子。翻开曾经在80年代产生过广泛影响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4册,每1册又分上下2 本,各册初版时间分别为:1980年10月、1981年7月、1984年8月、1985年10月。),在译者当中,会看到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艾青、卞之琳、冯至、查良铮(穆旦)、杜运燮,等等。《外国文艺》1980年第3 期发表艾略特的《荒原》,就是赵萝蕤对40多年前旧译的重新修订。这种现代意识重新活跃起来的情形,真应了一句话:落地的麦子不死。
还想再说一个例子,以唤起一段流落在文学史角落的记忆:法国文学翻译家王道乾文革后翻译兰波的《地域一季》,原也是重拾几十年前的旧梦。年轻时候的王道乾是一个诗人,他1947年赴法学文学,同船去学艺术的一位朋友还保留着他当年的一首诗,这首诗有没有标题不清楚,两段文字是全的,转抄在这里,(注:转引自熊秉明《我所认识的王道乾》,《东方》1994年第3期。 )重现巨大的社会变局和急剧的个人转化来临前夕,一个中国青年诗人思想和感受中翻腾不息的现代意识——
深夜车子在街上驰过,
这是运走我的信号。
手伸出枯萎,碎成灰粉,
瘫在面孔上,一本书上,
一片杂沓荒唐的理智上;
耳下涌起水波汹涌之声,
地狱在我心里,人群惊慌,
集聚在庙前,世界大改变;
永远渴;这城是黑夜性格的陈述,
城在灯下聋而愚沉入湿凉树荫,
房屋是滞重的做物,房屋;
饱食及沉睡的宗教,政治希望与教育。
我飞入清凉的原因里
并不引来结果;明澈的一条线
永不重复不修改,绝对精敏机智的线
在数目中在昨天昏乱的理性中升至无限;
惊扰我,你这秩序,伪秩序,
毒我,希望毒我,我的肉体,我的知识;
最后一朵花,最后一次试验;神秘的结婚。
淼茫古代,湮远的知,最初绝对的理想,在我肉内动摇,
风在肉缝里吹,吹,吹,吹,吹,预知的风,吹,吹,吹……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荒原论文; 柏格森论文; 忏悔录论文; 新青年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梁宗岱论文; 黄远生论文; 诗歌论文; 象征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