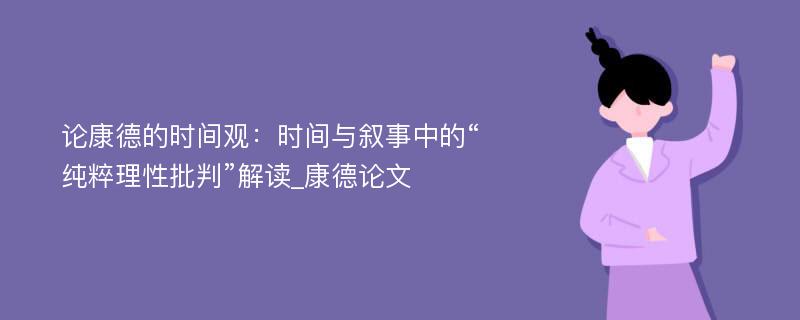
利科论康德的时间观①——试述《时间与叙事》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时间论文,理性论文,利科论论文,试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6)02-0168-06
毫无疑问,胡塞尔是对利科的哲学生涯影响最大的人,正是通过阅读胡塞尔并发展了胡塞尔的思想,利科才真正开始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现象学家和诠释学家的生涯的。1950年,利科出版了载有他评论的胡塞尔《观念Ⅰ》的法文全译本,开始了其作为一个胡塞尔评论家和批评家的生涯,并且作为一个现象学的领军人物而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而我们认为,也正是通过对胡塞尔《观念Ⅰ》的译注,利科才真正关注起时间性问题的。利科于1983—1985年间完成的3卷本巨著《时间与叙事》(Temps et récit)就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史上一部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利科在此书中通过对多位给后世西方哲学带来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康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时间理论之“疑难”(apories)的深入反思,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叙事时间(temps raconté)理论。而本文只限于讨论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为建构其叙事时间理论而对康德时间观所做的批判性解读。
一、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时间观
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让康德的时间观与胡塞尔的时间观相“对质”(confrontation),以此作为他对西方哲学传统时间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的一个重要阶段。利科指出,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对“内时间”所作的种种分析,大都被奠基于对客观的或世界的时间之先天的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试图把外部世界置于括号中,然而它却依靠与那个世界相关的语言和理解。这样,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计划之核心中就存在着一个悖论。按照利科的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目标最终与每一种其它的关于时间的现象学一样:从内时间中导源出或构成客观的时间。然而,在胡塞尔的情形中有一种相当反讽的循环性。他把他想要构成的真正的事物悬置掉了!利科声称这种方法论上的荒谬导致了在一系列关系上优先位置的前后颠倒。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利科开始了对康德时间观的考察。
这里,还是让我们先循着利科的思路简要考查一下康德论述时间性问题的相关文本,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利科的“解读”。在1781年,康德发表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详细考察了空间和时间,对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分别做出了形而上学阐明、先验阐明与解说。他认为,当外物作用于感性而产生感觉时,必须依照空间这种直观形式,才能得到秩序与排列(大小、形状、位置关系等),形成存在于空间中的感性对象;而感性对象出现于意识之中,又必须有其先后顺序,这就要遵守时间这种直观形式,因为时间本身是内心知觉(内感觉)的直观形式,外部知觉也是在内心中进行的。总之,“空间是一切外部直观的纯形式,它作为先天条件只是限制在外部现象。相反,一切表象,不管它们是否有外物作为对象,毕竟本身是内心的规定,属于内部状态,而这个内部状态却隶属在内直观的形式条件之下,因而隶属在时间之下,因此时间是所有一般现象的先天条件,也就是说,是内部现象(我们的灵魂)的直接条件,正因此也间接地是外部现象的条件。”[1] (第37页)在康德这里,空间和时间既不是自在之物的规定,也不是它们关系的规定,而是我们感性的主观条件;空间是外部直观的纯形式,时间是内直观的纯形式,我们只能认识到自在之物在我们感官面前所呈现的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本身。
而关于时间在构成知识方面如何起作用则是康德在后面,特别是在“原理分析论”——包括“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和“经验的类比”——中要阐明的。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和“经验的类比”部分,康德集中讨论了时间在构成知识中的作用。在这两部分所探讨的焦点问题是直观如何通过判断过程而被归摄到关于范畴或概念的规则中的。对康德来说,首要问题是去理解判断如何能够组合这些作为概念和直观的不同质的“项目”。因而,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中,他质询道:“但现在,纯粹知性概念在与经验性的(甚至一般感性的)直观相比较中完全是不同质的,它们在任何直观中都永远不可能找到。那么,把直观归摄到那些概念之下、因而把范畴应用于现象之上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个如此自然而又重大的问题真正说来就是我们必须建立一门判断力的先验学说的原因,为的是指出纯粹知性概念如何能一般地应用于现象之上这种可能性。”[1] (第138页)在康德看来,为了使“归摄”或者说“判断”产生,这种存在于概念和直观之间的异质性就必须被克服。因为那在根本上说来的不同质者是不可能被组合或统一的。
由此而来,康德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中继续演示说,必须要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与现象同质,并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之上成为可能。康德写道:“时间作为内感官杂多的形式条件、因而作为一切表象联结的形式条件,包含有纯粹直观中的某种先天杂多。现在,一种先验的时间规定就它是普遍的并建立在某种先天规则之上而言,是与范畴(它构成了这个先验时间规定的统一性)同质的。但另一方面,就一切经验性的杂多表象中都包含有时间而言,先验时间规定又是与现象同质的。因此,范畴在现象上的应用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而成为可能,后者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对于现象被归摄到范畴之下起了中介作用。”[1] (第139页)在康德看来,一种先验的时间规定,由于它既是与范畴同质的,同时又是与现象同质的,因而它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对于现象被归摄到范畴之下起了中介作用。毋庸置疑,对康德来说,在一种起调解作用的“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的帮助下,这些纯粹知性概念能够被运用于先天综合判断。
而在“经验的类比”中,康德则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不可见的时间”(temps invisible)之看法。他指出,一切现象皆在时间中,只有在作为基底(作为内直观的持存形式)的时间中,同时并存也好,相继也好,才能被表象出来。所以,现象的一切变更应当在时间中被思考,这时间是保持着并且没有变更的。“就是说,持存的东西是时间本身的经验性表象的基底,只有在这基底上,一切时间规定才是可能的……因为变更所涉及的不是时间本身,而只是时间中的现象(正像同时并存也不是时间本身的一个样态一样,因为在时间中根本没有任何部分是同时存在的,而是一切都前后相继的)。”[1] (第171页)上述这段引文,对我们理解康德的时间观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在这里,康德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只有在作为基底(即作为内直观的持存形式)的时间中,一切时间规定(即时间本身的经验性表象)才是可能的。变更所涉及的不是时间本身,而只是时间中的现象,因为时间(本身的变更)并“不可见”,那可见者只是时间中现象(的变更)。这正是利科所谓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
二、利科对康德时间观所作的批判性解读
在上文中,我们循着利科的思路简要考查了康德论述时间性问题的相关文本,这里我们主要来分析他对康德时间观所作的批判性“解读”。我们上面已经提到,利科让康德的时间观与胡塞尔的时间观相对质,以此作为他对西方哲学传统时间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利科不满意内在于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困难,由此,他开始了对康德时间观的考察。
首先,利科阐明了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经验对象的先决条件(présuposition)。利科强调指出,那种存在于奥古斯丁关于心灵(l' ame)的时间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学(physique)的时间之间的对质并没有穷尽关于时间的全部疑难。所有这些内在于奥古斯丁时间概念的困难还仍然没有被澄清。正是因为带着这样的思考,利科觉得有必要让胡塞尔与康德的时间观相对质,藉此以进一步深化对叙事时间理论的探讨。利科提到了他质问胡塞尔的原因:“对我来说,这是缘于这种去呈现他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特征的主要抱负,也就是说,通过一种适当的方法让时间自身呈现出来……然而,这种让时间如此(per se)呈现的抱负遭遇到了从根本上说是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在前面篇章中,以物理时间的名义出现,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又以客观时间(temps objectif)名义出现——那就是说,时间被暗含在关于对象(objets)的决定中。对康德来说,客观时间——在一种先验哲学中关于物理时间的新构形——从不如此呈现出来而总是作为一种先决条件。”[2] (第37页)我们觉得,上述这段引文所描述的胡塞尔与康德在时间观上的对质,实际上是一种“直觉的时间”(temps intuitif)与一种“不可见的时间”之间的对质。而结合上文中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时间”的具体阐述(如“时间是所有一般现象的先天条件”),便可知这种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被暗含在关于对象的决定中即是指这种“不可见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经验对象的先决(先天)条件。很显然,按利科的理解,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作为一种关于经验对象的先天(先验,超验)条件,已经迥然有别于前康德哲学对时间之不同的“见解”,因为无论是“主观的”理解(如奥古斯丁的)还是“客观的”理解(如亚里士多德的)都属于“内在的”理解而不属于“超越的”理解,可见“时间”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开始了“本体”(先验,超验)化的积极尝试。
其次,利科从他的叙事时间建构的视角进而阐明了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只是一种宇宙学的(cosmologique)时间。利科指出:“那最明显地使康德相对立于胡塞尔的,是在所有对时间的主张中之关于非直觉的(indirect)性质的主张。时间根本就不呈现:它是一种关于呈现的条件。”[2] (第68页)因而,对利科来说,康德保持在一种对时间反思的宇宙学维度内,尽管时间被归属于内感觉——这似乎标识了一种在康德与奥古斯丁之间的密切关系——但那种感觉决不是一种自我—知识的源泉。可见,从利科的叙事时间建构的视角来考察,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只是一种宇宙学的时间,毫无疑义,康德仍然没有完成时间彻底本体化的任务,因为他忽视了现象学的(phénoménologique)时间反思维度。
再次,利科具体分析了康德之“不可见的时间”建构与一种现象学方法的内在逻辑关联。利科宣称,他不希望一种对康德的回复将会提供一种对胡塞尔的反驳:“在这方面,康德所拒斥的不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分析本身而是它们的声称:即在关于客观时间的全部指称之外而通过直接的反思去获得一种被净化于全部先验意向的时间性(temporalité)。回过头来说,我将显示,如果不借用一种从未被如此表达过的暗含在时间中的现象学,康德自己不可能建构起这些与一种它自身从不如此呈现的时间相关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们被他的先验的(transcendantal)反思方式所隐藏。”[2] (第68页)这里,根据利科的阐释,如果康德想真正建构起这些与他的“不可见的时间”相关的先决条件,则必须通过借用一种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的分析方法。
按利科的说法,贯穿《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始终之非主题化的现象学的含意在关于内心(esprit)的指称中被发现。在“先验感性论”中,内心首次被讨论到,但康德并没有诉诸它的自我—证明。他的论证总是通过反驳前面的假设而间接地推进。因而,他总是强调了关于时间属性之非直觉的特征。而这种强调又总是关于时间的任何主张之先决的特征。这就是为何“先验感性论”的话语(discours)是关于先决条件的而不是关于实际经验(vécu)的:“这种回溯法的(régressif)论证总是胜过直接的洞察力。这种回溯法的论证,回过头来,悖理地假定一种论证的优先形式。”[2] (第71-72页)于是,在利科看来,《纯粹理性批判》的悖论在于:它的特别的论证方式不得不隐藏暗含在支配空间和时间观念性(l' idéalité)演示的思想实验(l' expérience de pensée)中的现象学。
既然时间本身不可能被知觉,那么我们只有通过这种在那持存者与变化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在一种现象的存在中,方能觉察到这种本身不流逝而在其中每一种事物都流逝的时间。因而,利科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结论是:如果不打破在关于时间构成与关于对象构成之间两可的联结,它的暗含的现象学就不可能被清楚地表述出来。假使这种断裂被实现,我们将被引导到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然而,利科让康德与胡塞尔相对质导向了同样的绝境(impasse),无论是现象学的途径还是宇宙学的(先验的)途径都不是充分自足的。每一种都回过来指称另一种。但这种指称又在相互排斥的条件下展现了相互借用之似是而非的特征:“一方面,只有把康德的问题置于括号中时,我们才能够进入胡塞尔的问题;只有通过借用客观的时间(它在其主要的规定中仍然是一种康德的时间),一种关于时间的现象学才能够被清楚地表述。另一方面,只有从对任何内意识(其将重新导向一种关于心灵——这里,在现象与事物之间的区分自身被悬置了——的本体论)的所有求助中排除出来,我们才能够进入康德的问题;这些规定(通过它们,时间不再只是一种量)必须被奠基于一种暗含的现象学(它的空白点明显地处于先验论证的每一个步骤中)。”[2] (第87页)由此,利科强调,康德与胡塞尔在时间观上的对质同样不可能获得理论上的解决,而只能通过诗学的(poétique)方式部分地被调解。按利科思路,要理解时间,上述两种“视角”都是必需的。而一种诗学的设计——其中提出了第三种关于时间之调解的“视角”即“叙事的时间”——能够克服在上述这两种反思的立场之间的“歧异”(gap)。
最后,利科还讨论到了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与前康德哲学时间观的渊源关系。利科指出,这种把奥古斯丁与胡塞尔联接起来的密切关系是容易被看到的,关于这一点,胡塞尔自己在他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开场白中有明确的交代。而要去觉察或接受一种在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联系则是比较困难的:“通过在‘先验感性论’中声称关于空间和时间之先验的观念性,难道康德不是更接近奥古斯丁而非亚里士多德吗?难道先验的意识(conscience)不标志着关于一种曾由奥古斯丁所开创的主体性(subjectivité)哲学之完成吗?假设如此,那康德的时间又怎样能引导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呢?但这将会遗忘这种关于康德的先验的(事物)之含义(sense),因为它的全部的功能在于建构起关于客观性(objectivité)的条件。”[2] (第88页)这里,按利科的提示,这种康德的主体,我们可以说,整个地担负起了让对象存在于那里的任务。时间,除了它的主观性的特征,是关于自然的时间——而它的客观性在整体上却又由关于意识的范畴系列所决定。由此可见,关于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与前康德哲学时间观的渊源关系非常复杂,同样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利科论康德时间观引发的几点思考
如上所述,我们简要梳理了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为建构其叙事时间理论,对康德时间观所做的批判性解读。由此,引发了我们的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从“时间的本体化”视角来看康德时间观的重要理论贡献。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集中阐述了他的时间观: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认为,时间是所有一般现象的先天条件,也就是说,是内部现象(我们的灵魂)的直接条件,正因此也间接地是外部现象的条件;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部分,康德讨论到了时间在构成知识中的作用。他认为,范畴在现象上的应用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而成为可能,后者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对于现象被归摄到范畴之下起了中介作用。正是在一种起调解作用的“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的帮助下,这些纯粹知性概念能够被运用于先天综合判断;而在“经验的类比”中,康德则进一步阐述了他对“不可见的时间”之看法。康德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变更所涉及的不是时间本身,而只是时间中的现象,因为时间(本身的变更)并“不可见”,而那可见者只是时间中现象(的变更)。而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主要从“时间的彻底本体化”(这里指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作的主要工作)的深入视角来解读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首先,利科阐明了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是一种关于经验对象的先决(先验,超验)条件,标明“时间”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开始了本体(先验,超验)化的积极尝试;其次,进而阐明了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是一种宇宙学的时间,它忽视了现象学的维度;再次,通过分析康德之“不可见的时间”建构与一种现象学方法的内在逻辑关联,从叙事时间理论建构的视角指出了康德之“不可见的时间”所面临的理论疑难。因而,从上述康德关于“时间”的种种表述与利科的“解读”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康德那里,时间开始了本体化的积极尝试,但由于他忽视了现象学的时间反思维度,因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时间”(本身)并“不可见”,所以康德仍然没有完成时间彻底本体化的任务。由此,我们不妨循着康德尝试将时间本体化而把其带入形而上学的思路,来考察现当代西方哲学对时间性问题的探讨。我们知道,时间的彻底本体化这一工作,是由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中完成的,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在对时间性问题的探讨上直接受到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将“时间”先验或超验化思路的影响与启发。至于利科“叙事时间”的建构工作,可以被看做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之存在论现象学时间性理论对时间的彻底本体化问题探讨的深入,而且带有明显的当代法国哲学“问题意识”特征(如对“永恒”或“他者”维度的强调)。甚至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目前正做的将“空间”本体化的工作,其实质仍然不过是“时间”被本体化之后将“空间”的“时间”化。由此来看,只要我们循着“时间的本体化”问题这条主线,我们似乎就可以比较清楚地把握到从康德到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在对时间性问题的探讨上的大致思路。而康德对“时间”做哲学思考并尝试将其本体化、从而把其带入形而上学的开创之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其二,从康德的“不可见的时间”与前康德哲学时间观的渊源关系来看康德时间观的重要学术价值。由利科的上述批判性“解读”可知,关于康德的时间观与前康德哲学时间观的理论联系同样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如关于康德与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在时间观上的理论联系在目前学界一直是一个非常受争议的课题。我们觉得,康德在对“时间”的哲学思考上同时受到了古希腊传统和犹太—基督教两大传统的影响,如他开始将“时间”本体化的尝试就似乎主要受到了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对“(意志)自由”问题讨论的启发,但在其它方面又似乎仍带有亚里士多德时间观的痕迹,因而从康德时间观出发,回溯前康德的哲学家们关于“时间”的不同见解,可能会有助于澄清在此方面的诸多疑难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康德时间观又是探讨前康德的哲学家们时间观的重要思想坐标,因而康德的时间观建构在西方哲学史中之承前启后的特殊贡献亦可由此窥见一斑。
其三,从康德之“不可见的时间”建构与一种现象学方法的内在逻辑关联来看康德时间观的重要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自近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以降,对“时间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主题化、专门化,到20世纪更是出现了多部关于“时间性问题”的巨著,如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柏格森的《关于意识的直接材料》(英译本名为《时间与自由意志》)、普鲁斯特的《寻找逝去的时间》(又译为《追忆逝水年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勒维纳斯的《上帝·死亡和时间》、利科的《时间与叙事》,这似乎表明一部独立的“现代西方时间哲学问题史”开始形成。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几部关于“时间性问题”的巨著都与“现象学”有关,并且在对“时间本体化”问题的研究上显现出前后相续、层递深入的态势。而由利科的上述“解读”亦可知,康德要真正建构起与他的“不可见的时间”相关的先决条件,已经暗含了一种关于时间的现象学方法的需要,如1905年就有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问世。而我们也可以循着这样一种“现象学”时间性理论的内在逻辑,以进一步从“时间的本体化”视角揭示出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的本质特征。由此看来,康德将“时间”本体化的尝试似乎同时预示了一场现象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革命,而这一点也进一步说明康德时间观之理论建构对后世西方哲学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我们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谈到利科论康德的时间观引发的思考,从而充分彰显出康德时间观之理论建构在西方哲学史中之承前启后的特殊贡献。设若我们能再转换一下“视角”,即当我们把康德的时间观建构之“问题意识”带入对西方哲学之时间性问题的研究中时,我们将能更深刻地理解康德在对时间性问题的探讨上所作的创造性工作。而学会像康德那样“思考”并“提问”,岂不正是我们从事哲学工作所要致力的目标?
注释:
①谨以此文纪念保罗·利科(1913—2005)逝世一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