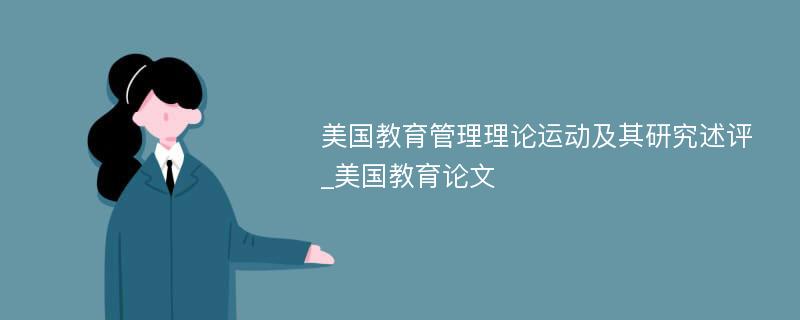
美国教育管理理论运动及其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美国论文,教育管理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09)07-0056-05
一、20世纪50年代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转向
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是美国教育管理思想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时期,一般教育管理著作都称之为“社会科学时期”(Social science approach)或者“行为科学时期”(Behavioral science approach)①。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相当多的美国教育管理学家,试图从各种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中吸取一些适合于教育管理的知识和思想,来建构教育管理的理论体系[1](P30)。这种集体的努力及其众多成果,形成为美国教育管理思想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理论运动”(Theory Movement)。
在此之前,美国教育管理思想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形成为两个特征极为明显的阶段:即“科学管理时期”(Science management)和“民主管理时期”(Democracy management)。第一个时期,大约从1910年前后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泰罗所倡导的“科学管理”理论对美国教育管理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育管理领域凸显出对效率的崇拜,这一特征,被坎贝尔称为“效率的幽灵”[2](P56)。20世纪30年代前后,由于科学管理自身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逐渐被民主管理思想和人际关系学说所取代,民主参与学校管理迅速成为美国教育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关于组织的民主管理和人际关系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反映到学校管理实践中去,很难加以确定。这主要是因为有关民主管理的概念不确定。此外,民主的和人际关系的管理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实践脱节。美国著名的教育管理学家坎贝尔(Roald Fay Campbell,1905-1988)指出:“无论是民主管理和人际关系学说,都未尝制定改革学校实践的严密计划;相反,这些思想就其本身而言更多的是提出一些改革主张。”[1](P197)即使有一些实践民主管理成功的例子,也都只是在规模较小的城郊学区进行的,因为在那里比较容易维持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状况大大限制了民主管理和人际关系学说影响的范围。
20世纪50年代前的美国教育管理思想体现在许多教育管理著作之中,但就其学科水平而言,大都处在经验描述的框架与水平之上,缺乏理论上的概括[3](P19)。这种在学校里教授管理经验,没有科学理论根基做基础的教育管理研究,被昆宁汉(Luvern L.Cunningham)称为“传说故事”(Folklore)[4]。许多学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教育管理的教学同现代学术思想和研究的主流脱节所造成的。甚至在颇负盛名的大学里,教育学院与工商业学院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管理课程一直由担任过督学的教授讲授。他们的专业知识主要来自多年在“第一线”工作中辛辛苦苦获得的经验。因此,教学内容集中于“怎样去做”这些实际问题,依靠的是过去管理者所积累的经验,并不是经过实证的系统知识。虽然他们现身说法,提出许多管理的原理和原则,充其量也不过是成功管理人员的观察或体会的心得[1](P25)。
对此状况,美国著名教育管理学家欧文斯(Robert Owens)曾明确地指出;“20世纪头五十年,教育管理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现存问题的情况或是收集意见。除极少数人例外以外,在教育管理方面,没有什么研究是对尚待解决的理论问题进行考查,事实上,没有一项研究包含了行为科学家提出的见解与研究方法。”[1](P26)另一位著名教育管理学者米勒(Ward Miller)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指出,那个时候“管理的大量研究实际上对做了什么或正在做什么一直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考虑一下,如此之多的管理经验已是今非昔比、变化很大,但对其科学地进行研究却如此之少,这真使人感到吃惊”。不过,他接着说,这种状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的转变,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教育管理已成为一个研究、发展的领域和一种专门的职业”[5]。
的确,20世纪50年代前后,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格里菲思(Daniel E.Griffiths,1917-1999)所说的:“教育管理的研究趋向,已着重于理论的探索,不再单纯从实用的观点而把科学原则排除在外。”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理论的探索“已经不再是个别的摸索,而已经通过全国性的组织从事集体的研究”[3](P19)。这种由美国教育管理学家们集体努力的结果,后来被称之为教育管理的“理论运动”。“教育管理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演进,……明显走向不同的方向。当‘理论运动’开始被人们当作一种新的方向来称呼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为学术与实践的分离奠定了基础。这场运动是在那些希望将教育管理地位提升到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大学教授的主导下开展的,该运动的支持者们把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了教育管理之中”[6](P106)。
对这一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美国著名教育管理学家卡伯特森(Jack A.Culbertson)曾清晰地描述说:(1)在许多管理系的学生中,流行清晰而敏捷地鉴别、描述管理行为的文章和描述管理行为的人,但对目标则解释的多,劝戒的少。(2)一些学者已极其明显地从管理的经济效果转向了这些现象的社会心理方面。(3)管理虽然发生在各个不同的组织中,但其过程大体是相同的,这个观点是被大家所公认的。(4)通过经验研究,包括理论的测试和发展,能够增进管理基础知识的观点,已经日益被学生所信。(5)越来越多的像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这样一些学科的学者参与了教育管理学的研究[7](P5)。
二、关于理论运动的起止点
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起点比较明确。美国教育管理学界一般都把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起点定为1946年至1947年间[8]。美国教育研究会(NSSE)出版的1964年鉴报告说,就在1946年至1947年,美国教育管理研究领域在组织工作上发生了三个重大事件,强烈地影响了美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发展,并进一步形成了“理论运动”。这三个重大事件是:“第一,凯洛克基金会(W.K.Kellogg Foundation)收到该基金会教育咨询委员会的一份建议书。建议书认为,学校管理是一门学科领域,应该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第二,美国学校管理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AASA)的计划委员会,在规定协会的目标中,提出要对督导制度进一步专业化进行研究,并开设课程;第三,教育管理学教授们建立了一个组织(即美国全国教育管理学教授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Professor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NCPEA),专门对管理、领导原理以及对学校管理者在培训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9](P11-12)这三个事件使人们认识到,教育管理需要专业化。韦恩·霍伊(Wayne K.Hoy)等人也明确指出:“由于全国教育管理学教授大会、教育管理合作计划和大学教育管理委员会的努力,使教育管理的发展能与其他管理学齐头并进,并且使教育管理学得以独立成为一门科学,并为未来厘出一个研究与发展的方向。”[10](P18)
从美国教育管理理论发展的进程看,教育管理理论化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顶峰,但是以后的进展并不十分顺利,甚至有人断言理论运动失败了②。真正的猛烈的批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来自加拿大的格林菲尔德等人。其重要的标志是1974年和1975年。1974年在英国布里斯托(Bristol)召开的“国际互访计划(International Intervisitation Program,IIP)”第三届年会和1975年在美国哥伦布市召开的大学教育管理委员会年会,成为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急转而下的分水岭③。许多教育管理学家感觉到,在经过轰轰烈烈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迷惘和困惑,而不知在学术上应如何发展。在坎贝尔的退休会上,昆宁汉指出:“70年代,教育管理领域在学术上有些困惑,并正在寻求确定近期的研究方向或指出未来的适当选择。”[11]时任大学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卡伯特森认为,“教育管理理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疲惫不堪”,“基本假设的重新验证已经开始”。1979年,格里菲思承认教育管理领域的“学术困惑”和“要奋起批判”。他说:“这似乎是对我一生中所接受的所有理论进行挑战。”[11]他指出,要自己考虑脱离与其一起生活,甚至对其作过贡献的准则,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至少在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教育管理已陷入难以预料的境地。
在随后十多年间,以加拿大教育管理学家格林菲尔德(T.Barr Greenfield)、福斯特(William Foster)[12]和贝茨(Marilyn Bates)等人对“理论运动”进行了长时间的全面批判,形成了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史上著名的“格林菲尔德革命”(Greenfield Revolution)。格林菲思(Daniel.E.Griffiths,1917-1999)等人也奋起捍卫理论运动的领地和学者的尊严,出现了“两格论战”的热闹场面。直至1988年,格里菲思才对1974年和1975年的那两篇具有巨大杀伤力的论文作出最终的反应。综上所述,把格里菲思发表以上总结性论文定为美国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结束的标志,比较符合史实。
在确定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之后,再来考察其发展的整个脉络。这一时期,美国的教育管理学,也像管理科学出现的“丛林”局面一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学派,可谓是五彩缤纷。由于学派林立,观点冲突激烈,有人形容说这简直是一个“真正的疯人院”,这种说法未免失之偏颇。应该说,这是适应当前科学技术发展和教育发展的需要,管理走向多元化的必然结果。但就理论运动而言,其主流思想是引导教育管理朝着建立理论、着重研究和运用行为科学、社会科学方向发展,尤其是在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巨大影响下,教育管理学者注重于教育管理的理论构建,并将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教育管理的研究和指导教育管理实践。教育管理研究发生很大变化,从注重民主倡议转向分析性的系统阐述,从一个研究领域发展到一门研究学科,从纯观察转向理论研究,从较窄的思想发展到包括多学科的研究和理论。
纵观理论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美国教育管理理论运动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7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理论运动的发轫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格里菲思、哈尔平(Andrew W.Halpin)、盖茨尔斯(Jacob W.Getzels,1912-2001)等人。第二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理论运动转向主张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的观点。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弗斯(Paula F.Silver)、霍伊(Wayne K.Hoy)和米斯克尔(Cecil G.Miskel)等人。第三阶段从1974-1975开始直至1988年,是以格林菲尔德等人对理论运动批判为特征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教育管理理论运动发生在20世纪50年至70年代的美国,然后逐渐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受其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3]。
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美国及西方教育管理学界对理论运动的评述颇多。格里菲思作为始作俑者之一,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毫不言讳。1988年,他亲自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诺曼·博扬(Norman J.Boyan)教授主编的《教育管理研究手册》(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编撰“理论运动”一章,全面介绍和阐述了美国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影响[14]。作为这场运动的见证人,卡伯特森也给予理论运动高度认可。他曾于1988年发表《对一个世纪教育管理知识基础的探寻》(A Century's Quest for a Knowledge Base)一文,对一百年来美国教育管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其基本概念作了系统分析。他把1951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的教育管理研究称之为“提升为一种管理科学”阶段。并指出格里菲思和哈尔平等以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为基础发起了旨在建立一种教育管理科学的理论运动。此后,也就是1967-1985期间,受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 )提出的“范式”(paradigm)概念以及批判理论的影响,格林菲尔德、福斯特和贝茨等在内的当代教育管理学家对“理论运动”进行了全面猛烈的批判。1996年,霍伊和米斯克尔(Cecil G.Miskel)则把教育管理思想发展分为古典组织理念时期(classical)、人际关系、社会科学方法和新出现的非传统方法[15]。其中“社会科学的方法”在重视社会关系和正式组织结构的作用的同时,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中吸收一些主张,如巴纳德(Chester I.Barnard,1886-1961)、西蒙(Herbert A.Simon,1916-2001)、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等人的理论观点。以上这些观点构成了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从总体上说,我国教育管理学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对美国教育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盛行25年之久的“理论运动”知之甚少。许多教育管理学著作,“不仅对上述哈尔平、坎贝尔、卡拉汉等人的教育管理著作不作介绍,而且对发生在战后美国并对整个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运动’也是只字不提。以至于某些从事教育管理学科教学的教师,至今仍对理论运动的起因、目标、功绩、缺陷、所招致的批判以及理论运动的历史意义不甚了了”[16]。笔者曾在中国学术期刊网(http://www.cnki.net)上输入相关主题词进行全文搜索,统计结果恐怕难以令人满意。1994-2004年期间发表的教育管理类论文,包含“理论运动(含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主题词的文章仅6篇,包含“格里菲思(含Griffiths等)”为7篇,包含“哈尔平(含Halpin、哈尔品等)”为8篇。不仅如此,这些主题词主要集中在其中的七八篇文章中。更有甚者,在不少教育管理学著作中,还出现了诸如断章取义、以讹传讹、空穴来风等一些严重阻碍教育管理学发展的现象。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教育管理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和困境,并作出一些努力尝试改变。根据现有资料,国内最早提及“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论文是黄志成的《近期国外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1995)。该文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给教育管理带来了许多新思想和新观点,促进了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入了教育管理理论的构建阶段。20世纪70年代,在众多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教育管理理论,形成了教育管理理论运动[11]。
笔者曾在拙著《美国现代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2000)专列一节,概要介绍了“1950年以后美国教育管理思想的走向”[17](P191-193)。指出,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转向理论化。南京师范大学张新平在所著《教育组织范式论》(2001)中用较大篇幅评述理论运动。他在该书中指出:“教育管理理论运动大致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美国出现的一种力图将教育管理构建在实证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管理科学’运动。”[18](P140)华南师范大学黄崴在《20世纪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及其模式的发展》一文中,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是西方教育管理思想发展史中一段极其重要的时期。“它兴盛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至今仍然是教育管理领域的主流理论之一”[19]。该文还把理论运动归于“理性为本模式”,并指出其占支配的观点是把教育管理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理论基础则是逻辑实证主义和行为科学。广州大学教育系孟卫青发表的《20世纪西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回顾与反思》(2002)[20],一文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限,把理论运动分为初步形成时期和发展成熟时期两个阶段。前一个时期主要数格里菲思、哈尔平和盖茨尔斯贡献最大;后一个时期则以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为主调,代表人物以波拉·西弗斯、霍伊、米格斯等人影响较大。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蔡怡在发表《西方教育管理运动述评》(2003)[21]一文又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作了进一步的勾勒,其中反映了当代教育管理学者,如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皮博迪学院教授菲力普·海林格(Philip Hallinger)对这一运动的评述。
总的来说,开展20世纪40年代末至80年代的美国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研究,不仅可以对这个教育管理思想上的重大事件进行一次全面详细的剖析,而且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以来美国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做一次全面的梳理。通过正本清源,增进和改善我们的教育管理知识,最终促进我国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9-04-20
注释:
①美国当代教育管理学家欧文斯(Robert Owens)把美国教育管理思想分为科学管理时期(1910-1935)、人际关系时期(1935-1950)、组织行为时期(1950-1975)和新的组织理论时期(1975至今)四个阶段(欧文斯著,孙绵涛等译:《教育组织行为学》(第2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0页)。霍伊(Wayne K.Hoy)和米斯克尔(Cecil G.Miskel)则把以上这段历史分为古典组织思想时期(classical organization thought)、人际关系导向时期(human relations approach)、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期(social science approach)和非传统观点时期(non-traditional perspective)四个阶段(见Hoy & Miskel.Educational Admistration:theory,research and practice.McGraw-Hill,inc.1996.p.9)。伦伯格(Fred C.Lunenburg)等也持类似的观点(见Lunenburg,Fred C.& Ornstein,Allan C..Eucational Administration:Concepts and Practices.Wadswprth Publising Co.2000)。
②坎贝尔等著:《现代美国教育管理》,第266页。早在1965年,也就是在理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希尔斯(Jean Hills)就曾非常含蓄地批评说,“在理论运动开始以来的20年里,与其说教学和研究发生了实际变化是一个事实,倒不如说是一个神话。”
③在1974年国际互访计划年会上,格林菲尔德递交了一篇论文,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评。为此,格里非思描述说,这种对组织理论的批判是“彻头彻尾的”(from the petty to the profound)。在1975年的哥伦布会议上,艾里克森发表论文,提出要转变教育管理研究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