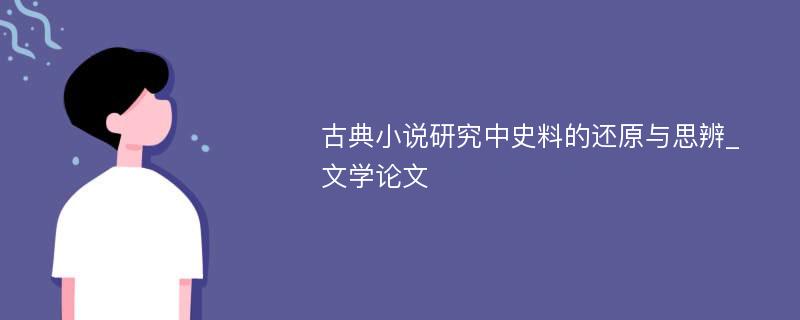
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辨论文,古典小说论文,史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古典小说特别是明清通俗小说领域,“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之间的关系常困扰着研究者。孰轻孰重,无所适从。甚至这两派迥异的批评范式还曾各领风骚并影响过一代学风。从治学思路上溯源考察,小说批评中无论是较为注重史料钩沉的索隐派、考证派还是偏向于思辨分析的批评派,就其根源来讲,它们与中国传统经学史上的三大流派“西汉今文学派”、“东汉古文学派”、“宋学派”一脉相承,都有着各自的源流谱系;如果我们广开思路,再做些横向比较研究,就不难发现,西方的“传记式文学批评”与我们指向作品的索隐及指向作者的考证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我国当代的“社会历史批评”,一方面直承“宋学派”的侧重微言大义而来,但更重要的是与“五四”以来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有关。各种批评范式只不过是一些人文表征,它们的背后隐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所以,单纯的线性描述或简单的肯定与否定,都不能圆满解释批评范式兴衰与转换的复杂原因。从前,由于受单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对某些缺陷明显的批评范式进行了否定,尽管硕果仅存的社会批评派在当时得以“一枝独秀”,但实践证明,它并不能解决好也不可能包办古典小说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应该承认,不同批评范式对作品的解读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为其它范式所无法取代;但同时,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虽然这些偏差又能被其它范式所补救。研究者从不同的价值尺度、评判标准出发,往往就会造成对同一文学现象褒贬悬殊、抑扬失实的情状。因此,简单地指出某些批评范式的长处与缺陷,还仅是停留在表浅的研究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应在不同学派的冲突与磨合、影响与反影响、渗透与反渗透的张力中寻求突破的契机。一个学人,一个学派,能客观地看到别人的长处并冷静地反观自身,才是学术上成熟的表现。索隐派也好,考证派也好,包括后来成为时代骄子的社会批评派,恰恰在这方面不够冷静,它们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后故步自封,作茧自缚,从而使得它们后来的发展越来越走向创立之初那种元气充沛的反面。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进行学术反思,才深刻醒悟到:只有多样化的研究格局互补且不断拓展创新,才有可能使研究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飞跃。营造一个众声喧哗、思想多样、畅所欲言的宽松学术环境,对于新世纪古典小说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些问题的正确处理,一言以蔽之,仍然还是“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两者关系如何进一步臻于完善并朝这一方向努力。
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关于古典小说中“材料”与“文本”的关系问题就有过不同意见。如某位研究专家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
几乎五四以来,像以胡适为首的一些“权威”们所做的那些工作,说起来是研究“文学”,其实却始终不曾接触到“文学”本身。他们“研究”作家,只是斤斤计较于作家的生卒年月;“研究”作品只是考订作品有多少种版本;充其量,也不过是对某一作品的故事演化,或对作品内容中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进行一些无关宏旨的考据。他们的历史考据癖好像很深:比如研究《红楼梦》,就专门钻研曹雪芹的家世,考证这位伟大作家到底是不是壬午年死的,以及他和贾宝玉究竟是否同为一人;研究《水浒传》,就专门比勘七十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的异同。至于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如何简直很少谈到。……既然以考据代替了研究,就很容易形成材料第一的“研究”方式。①
材料的考证与文本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该文指出了一些考证文章的通病,是有意义的;但以上论述,也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轻视考据的印象。发展到后来,另一位小说研究专家将考证工作藐视为“不过把以前的旧说从较为冷僻的书上找来放在一块儿”,甚至认为“所谓辨伪存真,并非对于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必要或重要的”,②这其实乃是一种对小说考证的偏见和误解。其实,古代小说研究同样需要有文献学、版本学的功底,否则,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的“其他的工作都如筑室沙上,不能坐牢”,③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考证不是目的,科学的考证以及有用的史料能更好地为研究作品本身服务。如《红楼梦》,这部作品的成书过程异常复杂,如哪些是出自曹雪芹手笔,哪些是后人妄改,何者为脂批,何者为正文,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哪些异同,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不能分辨清楚,红学就失去了稳定的研究对象。再如《水浒传》,版本有繁简之别,根据容与堂百回本、袁无涯百二十回本以及贯华堂七十回金圣叹腰斩本去分别研究,得出作者创作企图的结论就大相径庭。与此相联系,作者问题也很重要,如《水浒后传》的公案,有人曾因为“序”上存万历字样,遂断为明人所作,还有人据题署的“古宋遗民”和内封上的“元人遗本”,又将此书定为元代作品,其实关于作者的年代,在《南浔镇志》中是可以找到相关线索的。倘若不进行必要的“史料还原”工作,而去盲目论《水浒后传》的社会背景,肯定是要闹笑话的。也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强调重视作品的思想、艺术性或“回归文本”并没有错,然而如果没有“史料还原”作为研究基础,那么“文本”研究岂不成了空中楼阁?研究这些,不能说与“回归文本”没有关系,应该算是有价值的考证。我们可以指出某些考证对古典小说研究有没有用,有没有效,但却不能指责考证本身。
但是,也不能绝对化。真理再往前走一步也会变成谬误。说考证是“回归文本”的基础或前提,就其终极意义而言,这种表述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的地方,但这个大前提里往往蕴藏着一些危险的判断,表现在机械地理解文本与文献的关系,把上述命题绝对化并作为一种凝固的戒条去束缚研究者的手脚与灵魂,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具体分析。如果说文本研究有了版本和作者考证做基础,其研究成果会更扎实深入、更严谨,这话本来大体不错,但绝不能说没有版本、作者的考证成果做前提,文本研究就寸步难行。很多古典小说作品研究也不可能等待专家们拿出考证成果后再去入手。这里笔者无意贬低考证的价值,也承认材料是任何学问的必要条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话固然不错,但诚如钱钟书形象比喻的,“能列出菜单未必能烧一手好菜”,我们同样可以说,掌握了深厚的文献学知识,也未必就一定能写出石破天惊的研究精品。学术文章的“炒冷饭”关键还是思想的贫乏、理论的滞后。
传统小说索隐研究范式的最大毛病就在于它非要在文本意义诠释领域中进行“史料还原”,以为这样的“还原”才算解读了作品,其实,不管那些作品里存在着多少真实历史信息,而这些信息一旦进入小说艺术整体中,它们就会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从而被构造成为新的意义单位,而考证派的症结也在这里与索隐范式殊途同归。由于考证派旨在提供更多的作家和时代背景知识,就其研究对象研究过程而言并不属于文本研究的范畴,所以它对作品的解读很有局限。仍以《红楼梦》为例,我们必须承认,单独的曹学也仅限于作者的研究,而不能代替文本自身,亦即新批评派的所谓“文本外部研究”。这种外部研究,立足点的偏差在于过分地将《红楼梦》与曹家史实一一对应,而其具体解决问题的途径则是通过考察曹雪芹的身世来阐释《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这比较符合我国古代“知人论世”的传统,也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从而将《红楼梦》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文学毕竟不同于科学,心灵感悟的东西单靠科学是难以得到圆满解释的。如果强调过了头,有时这种“科学意识”反而还会成为“创造”的劲敌,即艺术与科学的“二律背反”现象。
三
与“史料还原”的研究范式比较,“思辨索原”是我们进行研究的根本目的。人们提出“回归文本”,恐怕并不是嫌真正的考证做得差不多了,而是离作品愈来愈远。正如汉学发展到后来,繁琐日甚,始于考据,止于考据,“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④因此,为了对索隐尤其是考证之末流进行反拨,强调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思辨索原”,也就在情理之中。
由于考证派远离文本这个轴心并且在研究理路上存在严重缺陷,特别是发展到末流,那种无关宏旨的一事一考、一字之辨,同时伴随着琐屑、苍白,使许多重大的文学现象往往有意无意地被置于脑后,在很大程度上确实遮蔽了作品的审美视线,同时鼎革之际新的时代又要求一种新的治学范式,这样,内外因的综合作用,以“典型论”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历史批评派便在上世纪50年代初应运而生。对“时代背景”的深入考察,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的重要贡献,不容抹煞。因为如果离开历史、社会而仅仅从作品本身去寻找答案,那么人物形象也就变得难于理解甚至解读流于随意性,这恰恰是“典型论”对考证派的可贵反拨。很多人对这一派过分强调社会政治而颇有微词,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甚至认为这一派是“根据政治的需要产生的”,而不是学术发展的必然逻辑归宿。其实作为一种可能的研究角度和认知方法,“社会学”也并不外在于古典小说研究的内在逻辑,而恰恰是对胡适考证派治学范式所做的重要补充,因而对理解作品来说也是合理的、必要的。当然,这种范式并不是惟一正确的,事实上它也不可能穷尽作品的全部。从动态的文学观来考察,《镜与灯》一书的作者Abram曾提出文学四要素说,即“世界—作者一作品一读者”,认为只有从这四个维度去诠释,才有可能较全面地把握一部作品。但以“典型论”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历史批评范式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对世界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看得过重,这就不但诠释过度而且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赏鉴的审美视线。
当代西方新批评派提出文学“本体论”,认为研究作品,无须研究作者的传记,无须研究历史背景等,这实际上是强调文学四要素中的作品,即要求对作品进行主体价值学诠释,这种由外向内的诠释维度的转换,正是对传统庸俗社会学治学偏向的反拨,虽然在提法上陷入片面但又不失其深刻。对比传统索隐派的犯呆犯傻、考证派的自结牢笼特别是社会历史批评派发展到末流后那种一般性的思想、艺术分析,新批评派的品格也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不错,“史料还原”式的索隐、考证以及社会历史批评派能告诉人们古典小说中“有什么”,但“有什么”并不等同于“是什么”,况且,即使考证清楚作者的身世或者真的索隐出什么历史事件来,也未必就能穷尽作品中的一切。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主体性哲学在中国大陆演成主潮,以主体价值学诠释为特征的新批评派也就为不少研究者所乐于采用。应该承认,新批评这种研究范式,让人们把目光聚焦于作品,并将这一局部显影放大,使人们看清了它的详细构造,尤其是以心灵妙悟和文化融通为旨归,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去审视作品,体现出一种高层次的哲学思辨和文化关照,这对以往的任何研究范式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超越,对很多古典小说的主体价值方面的诠释也确实比以往更深入了一层,但如果夸大认为这是研究了作品的全部,那就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特别是新批评派不惜割断“世界一作者—作品一读者”中的三个重要环节,只剩下“作品”一项,更显出“见木不见林”的形而上学。倘若我们把作品经过新批评派那样的微观显影放大后,再吸收考证派、社会批评派的研究成果,将作品放置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上去进行宏观考察,追溯作品之所以在此时出现的根由,岂不是看得更清楚,分析得也更加圆满、得体、到位么?
由于摆脱了以往政治功利观念和话语霸权的影响,在文化开放、价值多元的文化语境下,古典小说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现在研究者的批评视野更加开阔,这种新批评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也就有了本质的区别,因为在社会学的诠释下,那些曾经出现的作品仅仅被视为记录一定历史时期的文本材料,而新批评派强调从艺术结构上去把握作品的美学价值,特别是关注作品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哲学思考,就更难能可贵了。不错,同以往的研究范式一样,新批评派也并没有达到完美境界,有所恃必有所失,在学理上它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但这一派由于立足点颇高,境界不俗;从前景上看,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应该抱着尽量宽容的态度。对有缺陷的新事物的涵容,往往能使我们走出平庸的怪圈。
注释:
①吴小如《我所看到的目前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见《文艺报》1954年第23、24期。
②聂绀弩《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辨伪存真’》,见《人民文学》1955年1月号。
③见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宝玉喝汤”条。
④见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与汪龙庄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