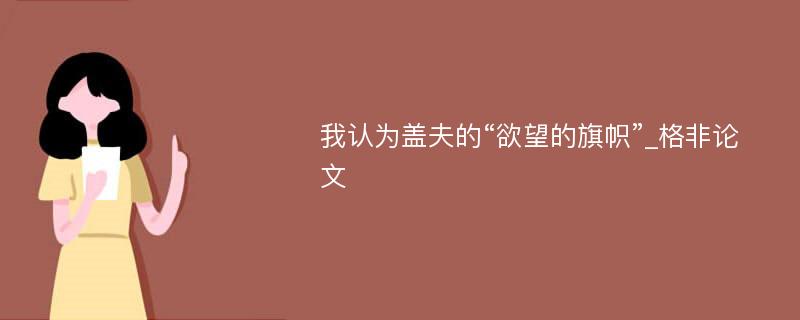
我看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看论文,旗帜论文,欲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陷井》、《褐色鸟群》、《青黄》到《大年》、《锦瑟》,格非一直在一个遥远的时间,陌生的空间里编织着流畅的想象。我们已习惯于读到一个完整的故事如1+1=2那么简单,可在格非的世界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一个的人,飘着莫名的思想,说着玄妙的话,看到在所有季节里雨都在疯落,搅乱正常的秩序,正常的情欲,看到大段大段的空白、拼贴、错位,世界充满偶合和生生死死的宿定以及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孤独、隔膜、猜疑。格非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便在思想意识更加复杂的知识分子所聚焦的环境——大学校园的背景上展衍开来,书中的大多数人物,又有着与作者自身最接近的身份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学生、讲师、教授等。作为一个敏感且充满了“先锋意识”的小说家,格非是如何构建这个微妙复杂的一处?他企图传达什么?我想,在《欲望的旗帜》(以下简称《欲》)中,我们首先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象牙塔里的荒诞剧
象牙塔是个进口的词,代表清明的情感和纯洁、光明、智慧,宛然建构了一个远离凡尘的庸俗之乐、情欲之嬉,游渺于常人生活之外的世外桃源。《欲》中的绝大多数人便居于这塔内。贾兰坡是著名的教授兼博导,曾山、宋子矜为其门阀,张末是大学毕业的中学教师,老秦等与会人物都是大学老师、教授……这是一群应有着精妙思想与言论的学者,生活和往来于有绿树有草坪有整洁的专家大楼的“举世闻名的花园大学”内。然而在崇高的学府之地,格非以敏锐的智慧,娴熟的语言演绎的是一出荒诞异常的闹剧,令人在读其文字时,捧腹不已。梳理其脉络,荒诞之处有二:
(一)学术会议的荒诞。《欲》全文分为六章,附尾声。除第四章标目为“欲望的旗帜升起”与尾声外,其余五章都与会议有关,如“预备会……”,“会议再次中断……”,“会议闭幕……”,可以说,全文情节由学术会议始,由学术会议终,以学术会议为大的茎干,而牵扯出人事之变。学术会议在高等学府召开,是极正常的,但我们若细审之,便不禁哑然失笑了,这哪是学者们召开的严肃会议,纯粹是一群大人玩的劣质的“过家家”的游戏罢了。首先,除了作者反复强调这是一次重要的哲学问题的会议外,会议实质讨论的内容我们一无所知,或者说与会者没有一个是真正关注会议的实质的,而是籍此希望获得各种不同的利益,本末倒置。人在其中各行其事,唯一被忽视的是哲学。如曾山沉溺于贾教授死的疑虑和对张末的回想中,宋子矜奔波于女研究生的打胎和迎接妹妹的到来,老秦则神秘莫测地酝酿着有关大计划。其次,会议的得以召开是凭了一名制造假药的商人——邹元标的赞助,而这名商人称这次赞助是“与那帮知识分子开个玩笑”。邹元标中途被捕,会议陷入危机……与会的人还沉浸在一惊一乍的情绪中,旁观的张末已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酝酿已久的哲学讨论会即便算不上一个恶作剧,也会给人荒诞的滑稽感”。总之,这个重大的学术会议如何的庄严、肃穆,我们不得而知,倒是会议中一些吃喝的细节,与会者们世欲的心灵,内心欲望的膨胀,在这里得以曝光,使得迂腐的学究们大出洋相。老秦终究凭此奠定了他成为青海教授、博导的地位,而纺织女工与唐彼得的婚姻是会议的意外收获,它永远证明肉体比精神来的实在。学术会议实际上成了一出荒诞剧上演的契机和舞台。
(二)人物命运的荒诞。命和运,在中国文字里透着莫测和天数。格非表叙的特征之一便是干脆放弃对命运的探索,直接去描绘命运的表现。这表现在生活中异常琐屑,蕴藉在点点滴滴的细微感受中,却总是偏离了原来的要求、愿望和出发点,由此产生晕眩又迷乱的荒诞感。而格非“先锋”的文字特点:大段的空白、错位,叙述角色的替换,时空的零乱组合……更是加剧了这种荒诞感。如贾教授悴死之谜,在《欲》文中它是无解的,慧能法师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曾山觉得他是智慧可亲,而宋子矜和老秦以为他有如鹰隼的眼,其身世之谜也是无解的。这些可以说有些神秘主义,是冥冥中不可名说的荒诞。但曾山、宋子矜、张末命运的荒诞则不在于神秘,而在于追求不得的失败和无奈,是命运对于现实的捉弄或者现实对于命运的捉弄,这又以宋和张更加突出。以张末为例,我觉得张末是作者最为钟爱的一个人物,他小心翼翼的从各方面来完成她命运的流程。可以说,张末的一生是追求爱的一生,而又永远处于精神之爱与肉体之爱的矛盾里,这是知识女性特有的心理。“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张末就开始了对于爱情的憧憬与向往”,“一个面目模糊的男人向她走来说‘我们回家’——一幅充满纯真与美好的画面,这个画面缠绕了张末的一生并指引着她寻找归宿。然而,现实总悖离她的心灵,第一个偶像音乐老师对她不屑一顾”;药剂师引发了她心中欲望的朦胧渴望,却与母亲私下相好;曾山是个有着哑铃脸型的憨厚男子,他给她以安全感,更因为他是第一个主动热烈追求她的男子,张末终于筑下了爱情的巢,最终却离婚了;邹元标是张末生命中最奇异的人,偶然的邂逅,双方却都产生了不可压抑的激情,这完全是情欲的魔鬼,是一种生命本能的吸引,但张末强大的理智每一次都保护了她。张末只能隔着很远的距离来想念曾山,她甚至企图抛弃知识的体面……然而张末需要的简单的打动永远只能在梦幻中发生。“怎么会这样?”她一遍遍的反问着自己,她流着“忧伤的泪水”要“回到她一度遗弃的生活中”,命运是如此荒诞,经不起推敲。
格非是一位善于将机智切入作品的小说家。这种机智在《欲》文的荒诞性中得到了极大的延伸,他自如地想象和编织,将我们带入缭乱的画面。这是一个表面的感性世界,具有直觉的特性,而我们总力图依据感性的事物进入理性的世界,力图找出作者心中或自我心中的心理建构:为什么格非笔下的净土竟产生如此多的荒诞?他或它的寓意何在?我以为,这二者的答案是一致的,那就是:
真实的分裂
真实是一个需要界定的词,因为它有歧义。有人说:“我生活在不真实中”,别人立即反驳:“你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第一个真实是指内心的真实,第二个真实是指物质的真实,存在的真实,譬如虚假的眼泪还是眼泪。人总在希望和追求着内心真实的世界——格非也隐晦地寓言式地描绘着他笔下人物的这一心理真实层面。这真实又依了时代的不同和个人的教育、经历、悟性的差异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而当内心的真实愈来愈远离存在的真实时,荒诞便在这二者的差距中产生。
格非开篇便交代了《欲》文的背景:20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这是一个观念正在转型,人的思想意识发生巨大变化或受到巨大冲击的阶段,太多的商业因素侵入世界,物质和金钱在价值的天平上重起来,知识和思想迅速瘪缩下去——尤其是在哲学这块无法和商业融合,只有孤独地徘徊在精神园地的领域里。于是,我们看到了哲学面对金钱的焦躁不安,以致于不得不扯下致远淡泊的君子面目来:哲学会议在没有赞助的情况下无法召开,贾兰坡时刻充满了哲学系被取消的危机感,副校长亲自去欢迎赞助商人并计划聘请其为荣誉教授……毫无疑问,金钱将知识分子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历史夹缝。然而,它面对的毕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从贾教授到曾山、宋子矜、张末,这些哲学界的精英们,他们都早已构建了一个有着相当纯净的理想色彩的内心世界,并一直在锲而不舍的追求,不轻易放弃。于是我们眼前便呈现了他们在被金钱困顿的存在里永无止境的冲突、挣扎。他们的行为本来具有高尚的动机,在这个社会里却只能显得滑稽可笑。
曾山的内心一直充满了对诚实的生活和幸福平静的家庭的渴望,对精神和肉体和谐的渴望。我们不时地看到他笨拙而可爱的举动:为了寻找张末而常常出没于几个舞厅;奇怪的分析下巴的作用;因在黑板上写到“末”字而兴奋得休克过去;看电影时蠢笨地坐在张末的后面只为了“更清楚地看她”,还有那些令人喷饭的道歉信。这些都表明了他迂腐而又真挚地企图去抓住那“怎么也抓不住的”幸福的纯净。曾山对他人亦是如此,他执拗地写《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以致顶撞导师,他在老秦的批判会上为老秦鸣不平,他给慧能法师写信要查十几遍哲学辞典,他热切的希望宋子矜能对他讲真话……总之,他努力地让外在的真实达到内在的真实,他一直苦苦思索导师悴死之谜,也是这“求真”的本性在发挥作用,但他失败了;他和张末总处在错位中,婚姻终于破裂。他悟到“没有任何人会去关注别人的内心”……这宣告了这个世界对内在真实的忽略,人和人之间谎言的障碍始终无法越过。他所追求和希望的离他日益遥远,他全部的生活只是一块“肮脏的布”。格非甚至好几次暗示了曾山有精神失常的征兆,这是两个真实相距太甚而造成的人心理的崩溃。然而曾山的天性憨厚宁静,他理想的平和是恪守自己的信心,不多为世俗的名利所束缚(他以为老秦在很多问题上并未想通),但又清醒地没有脱离尘俗,只希望真诚地与人沟通——这保障了他最终没有走向失常的境地。慧能法师最终留给曾山的话是“生活在真实中”。它洞彻了曾山的亦是宋子矜、张末的所有烦恼之源。这个真实是外部的真实,要人索性放弃内心的抵抗,归同于表面的真实中,这样便单纯地消灭了矛盾,以一种妥协的消极态度。曾山能否做到呢?
宋子矜和曾山又是不同。曾山若是说还在存在的真实中积极地追寻内心的真实,宋子矜则无法生活在存在的真实中。“与其说子矜成天在说谎,不如说他根本就无法再分辨真实与幻觉的区别。诚如他自己所说:‘在写作中,你的意识会不知不觉地被上帝或撒旦控制住。你分不清哪些事是真,哪些事是虚构出来的’”……这个困境更甚于曾山的困境。宋子矜向往灵空,内心充满了感性和浪漫的色彩。他的渴望中排除了信念,那是多余的,生活也是多余的,一切都自然、纯净,一切是多么的安静,“感到自己已经远离了尘嚣”……内心真实便被宋子矜抽象成了一种感觉,而不是曾山的平实,因此愈发脱离了现实。子矜的内心宛如一只脱线的氢气球,永远再无法回到地面,而现实的子矜就像一个还稚气的孩子,放纵的游戏在成人的园地,但注定了要遭罹毁灭的磨难。我们看到,子矜在所有的活动中都自行其事,他和导师的“情妇”作爱,他在学术会议期间带着女研究生去杭州“打胎”,他变幻的关于屁股上的烙斑的叙述……人们总以一种对待孩子的宽容宠溺了他。可子矜仍然得不到那种感觉……子矜真是个孩子,希望存在的真实里能“生出”他的梦幻来给予他。他失望了,只有和曾山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的妹妹,他和妹妹一起坐在江边上看芦苇,看船,看棉花、灯塔,“那儿是多么安静啊!就像台风的风眼”……而世上所有能够发出光亮的东西拼揍在一起,与她眼睛的纯净与透亮相比,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宁静的感觉永远只在记忆里闪烁”,这个记忆,是妹妹带给他的。子矜远远缺乏行动的能力和责任感,他的生活实际是一团糟,但居然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维持了平衡,只是这种平衡本身隐含了太多的隐患,处在了正常与失常的交界。而妹妹真实的到来,使得他连回忆的安慰也成泡影了,因为妹妹长大了,有了许多陌生的变化和陌生的言语,因为妹妹将亲眼逐步看清他的生活……掩在博士和小说家头衔下的生活。这本来还需要一个过程,却偏凑巧地他肉欲的放纵在此时受到了世俗的惩罚,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毒打……这两件事摧毁了子矜精神世界的最后防线,他终于彻底地崩溃了。他回到了家乡,正常的时候,“他也会独自一人悄悄的来到江边,在高高的坝上坐上一整天,看着江边过往的船只发愣。”子矜在疯狂的状态中获得了真实。
我们不能忽略了老秦,他代表了知识群体中的媚俗者。这些人积累了一些世故,但又不是很圆滑,学业上不是功成名就,生活却是拉家带口,于是非常实际地立起了对名和利的向往,内心理想化的世界变质而与外在的真实具有了一种相同的特性——世俗。知识成了攫取名利的工具,商业因素的掺入,更加强了对这种世俗名利的认同。老秦就这样不自觉地听信了贾兰坡的话,写了篇“在整个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导致“一遍又一遍地写检讨”,并取消了副教授的职称,他为了进入理事会甚至背着再次触怒校方的危险,只因为“他已经一无所有了”,“几乎什么事都没来得及做,就要面临退休了”,最后“好不容易替自己找了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可哲学系又不取消了”,未免自己也感到悲哀……然而最后,他终于摘到了他精心孕育的世俗的果实,荣冠了“新一代学术领袖”的称号……这与其说是老秦的胜利,勿宁说是现实对于理想的胜利,世俗对于精神的嘲笑。曾山、张末、宋子矜的愿望必然永远漂流,高不可及。格非是一位少有的,几乎完全意义上的“校园作家”,他所处的环境帮助他能比较深入地了解、透视各种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以娴熟的技巧表露出他们在the end of the world的生存困境,而贯穿着这些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行动的,只是一个极单纯的词:
欲望
在这个世界里,欲望囊括了一切:哲学、神学、宗教、爱情、理想,人人在欲望中行动着,人人身不由己地受着欲望的牵引,以致要瓦解理性与道德的约束。譬如苏辛会津津有味地讲述自己如何地享受欢娱,贾兰坡会在桌子底下踩张末的脚,张末会沉醉于邹元标的淫秽话语中……老秦对名利的向往是欲望,曾山、宋子矜对真实的渴望,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欲望”。“欲望的旗帜升起来了”,高举和张扬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曾山的最平实的理想,竟成了“奢侈”的欲望,这是曾山的悲哀。他因“怎么也无法抓住它”而愈发迫切地想抓住:加速离婚,追求张末、结婚……到又一次离婚,可他永远也抓不住它。他的生活就像他永远在修的那只闹钟总零散开来用报纸遮盖着。最后曾山只能在女儿玩的丢手绢的游戏中感到了平静,他感到他有些爱他的女儿了,这是一次欲望的转移,是以父爱的亲情来冲淡自己对于生活的失望。
宋子矜空灵的理想,更是无法触及的“欲望”。我们无法得知宋子矜的理想怎样地受阻,因为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已经放荡不羁的了,一方面游戏在哲学与小说的空间,一方面放纵于与各种女人的交往。子矜的心和他的眼睛一样脆弱,害怕触及拆散的闹钟零件……“因为它使他想起大脑的结构”……更确切地说让他想起生活的实际。这实际强制地压抑了子矜的理想,使子矜无法捕捉到“那种感觉”,得到对自我真实的肯定和确认。于是他索性“放弃”了期待,而陶醉于性的刺激中。这是比曾山更为偏激的欲望转移。子矜处于两个点的极端上,企图以放纵的肉欲来获取生活的信心,来代替空灵的理想。而当人只能通过如此的方式来确认自我的价值时,他已经迈向了疯狂。精神上所失去的,肉体上永远不能给予。宋子矜注定了在这欲望的循回中走向毁灭。
欲望的旗帜升起来了。格非的声音冷静,嘲讽又颇悲哀的悬浮在象牙塔的上方。而塔外的世界,又何会不然?欲望成了现代人头顶的得摩克利斯之剑,凛然地令脖子后面生出嗖嗖凉风,而又不得不为之驱使奔跑。门在哪儿?格非没有指出。或许,他和其它许多的人一样,还在努力地思索。门到底在哪儿?让我们一起去追求、反思、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