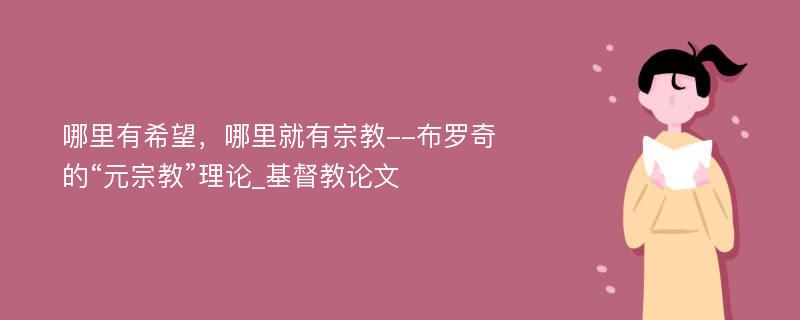
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宗教——布洛赫的“元宗教”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洛赫论文,宗教论文,就有论文,有希望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 年代开始的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 使布洛赫( ErnstBloch)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的哲学对希望神学及其形形色色的政治神学起了一种酵母的作用。他对宗教抱着同情的理解的态度,其出发点与结论和传统研究者大不相同。为此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哲学及元宗教观。他的希望哲学及元宗教观主要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圣经和教会历史。同样,他的哲学和元宗教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并没有产生多大反响,反而在基督教神学中找到回音并开花结果。他的学说进入了基督教思想的宝库而没有进入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但他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边缘或离心的一翼。
布洛赫,也不是站在基督徒的虔诚的立场捍卫、宣扬并阐述基督教经典和教条,他力图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立场出发阐明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态度和关系,阐明无神主义者如何看待宗教。
一、“还没有”的本体论与人类学
“布洛赫把末世论的希望改造为哲学,以便制定希望的教条,是前无古人的,也是独一无二的。”〔1 〕他的“还没有意识”的人类学和“还没有存在”的本体论把实际可行的范畴带到未知的希望领域和未知的世界进程的领域。
布洛赫之所以富有魅力,有两个原因:第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公开的无神论者,布洛赫对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启示文学内容非常感兴趣,他早年的一部著作赞扬了激进改革家托马斯·闵采尔的生平和思想。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帝和弥赛亚耶稣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出现。千禧年派的信仰和伦理遗产比官方基督教对他更有吸引力。他对中世纪弗洛尔的约雅金及其按时间顺序依次出现的圣父、圣子以及即将到来的圣灵时代的理论极有兴趣。据说约雅金把彼岸世界的天国移植到历史之内:“约雅金的选民是穷人,他们带着肉身而不仅仅作为灵魂进入天堂。”〔2〕第二, 布洛赫以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阐明其末世论观点的意义,而不乞灵于精神性实体的超自然的方面。在他的人道主义唯物论中,错层次思维方式受到拒斥。他的解说只限于平面式。“超在”是根据我们前面的未来认识的,而不是按照“我们之上”或“我们之中”的实体来认识的。“向前看代替了向上看”〔3〕。 这包含了为克服现状和为实际乌托邦而奋斗的革命使命的必要性。肉体与精神的需要在实际乌托邦中得到满足。
布洛赫阐明了两个基本观念:一、人的希望的品性;二、彻底开放的未来的作用。第一个问题涉及人类学,第二个问题涉及本体论。希望意味着可能性,它是未来的基础。未来是“还不存在”,是某种“还没有意识”的事物,“还没有产生”的事物。人生活在前意识的盼望之中并通过盼望创造新的社会。布洛赫认为希望的人类学和未来本体论这两个基本概念在耶稣的教训中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新的国度和新的生活的动力。这使耶稣的教训同古代文明中其它宗教区别开来。
人类学构成布洛赫哲学的基础。《希望的原理》一开始是一大段对人类主观性的分析,它与海德格尔及弗洛伊德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海德格尔企图把人自我的本质置于焦虑和虚无的威胁之下。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在对过去的力量的认同中寻找人的“正身”。“无意识”被说成是“不再有意识”。布洛赫断言,人类学的基础是我们对未来的盼望意识。“无意识”应当是“还没有”意识,这种意识具有乌托邦的效果。布洛赫说的希望并不是对未来结局的轻率信念。“还没有”可能导向全部,也可能导向虚无。结局是不能保证的,但可能性却是给定的,并且所期望的未来在当前发挥着创造力。这样,在布洛赫的本体论中,正常的因果关系是颠倒的,“真正的创世不是在起初,而是在结局”〔4〕。
布洛赫认为,一切现实都是从可能性的海洋中升起的。从这个可能性的大海中一次又一次浮现出现实的新片断。世界不是一座预制的房屋,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同样,人还没有自己的真实的存在。他还不知道确切地是什么。因此,人百虑一致地寻找真正人性的故乡。人和世界的未来得以决定的场所是现在。这个现在是未来的前线。只有我们了解我们期望和渴求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在现在的前沿得到未来,否则我们就会错过它并毁坏它。未来可能带来无所不有或一无所有,带来天堂或地狱,生命或死亡。因此,未来是充满救赎也充满危险的。
在布洛赫看来,末世论的希望把自己同“还没有”的领域里历史活动的可能性联结起来,而对未来新事物的盼望又同人所能做的联结在一起。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新奇”的观念是一个中心题目。
二、宗教的共同本质是希望
布洛赫的希望学在其“元宗教”理论中达到极致。所谓“元宗教”(meta-religion),即“承传的宗教”〔5〕。布洛赫相信,从一切宗教中继承的真正基础是“整个希望”〔6〕。“哪里有希望, 哪里就有宗教”。基督教的末世论的意义就在于提醒人们,正是在这里,宗教本身的真正性质才最终显示出来。如果我们要继承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我们就必须继承其末世论的盼望。为此目的,我们必须上溯到宗教由以出发的本体论基础。布洛赫认为,“那导致宗教产生的渴望,那被压迫的受造之物对快乐、幸福和家乡的欲求,其根源正在于孕育着宗教的人的二元分离之中——人的当前的现象与其还没有出现的本质的分离”〔7〕。
这种对宗教的看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评和通常的解释。如果宗教是从人的分离中产生的具有二重性的希望的瑰宝的话,那么,仅仅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上对它加以解释就是表面的、肤浅的。宗教如果就是希望,并保存着希望,则它就不是从恐惧、愚昧和教士的欺骗中产生的。宗教就它是希望而言,其原因就在于人与世界具有过程的特点。费尔巴哈说,人对人是上帝,这句话的意思是,性爱中的我和你互为上帝。布洛赫在下述意义上采用了这一术语:那还没有被发现和还没有彻底完成的未来的隐蔽的人是现在的人的上帝。上帝和未来的全部画像越来越迫切地影响着人类和宇宙的看不见的身份——作为人的隐蔽动力的生存的核心及作为世界的隐蔽动力的世界基础——向它展现出关于彼岸世界的更精密、更人道的图像。
这就是说,在布洛赫那里,作为人的形象和偶象的上帝不是被简单化为人的感性的存在,也不仅仅被简化为人类的疏离的、对抗的社会环境,而是“尚未被发现的、未来的人类”。“上帝”被看作是“乌托邦式实体化了的未知人类的理想”。
布洛赫试图制订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基督教理论,以此拯救基督教的合法遗产。他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希望说成是继承了基督教的遗传。基督教千禧年主义的革命神学代表了初期社会主义的幼稚梦幻,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第一次把这梦幻变为现实。布洛赫提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即历史上,几乎所有基督教的造反活动都乞援于旧约。他认为,如果从经济基础看问题,那就可以看到,基督教同其它一切宗教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压迫者的宗教。原始基督教起初不是统治的工具,而是渴望自由的表现。基督教的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使它优越于别种形式的宗教。尽管它采取梦幻的、神话的、甚至幼稚的形式,但它自觉地与穷人解放的历史运动认同。而这当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科学地予以解决并具体地加以实现。当天国试图跳到地上,或当内心生活试图跳到外部世界时,则在主观因素中,就会出现一个新的转折——不是鸦片而是无可比拟的炸药,渴望就在此处建立地上天国。当对彼岸世界的盼望开始在地上世界起作用时,它就变成炸药。布洛赫注意到这种盼望所引起的革命激情,是抽象的、神话般的,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感。它仅仅给改造世界的主观渴望以羽翼,而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促成这些变革的方法。布洛赫宣称:“人在上帝的本质中所表达的,不是别的,而是所盼望的未来”〔8〕。
三、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继承
布洛赫同马克思主义中的通俗作家的反宗教宣传实行了决裂。他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宗教加以肯定性的批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受到恩格斯、尤其是列宁的影响,断定宗教是应当加以废除的幻想和迷信。布洛赫认为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幼稚的。他强调,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宗教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类本质的幻想的实现,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只有当人同人、人同自然的关系变得合理、变得可以理解时,宗教才会消失。布洛赫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不仅仅是幻想,而且是对所需要的事物的幻想的表现。如果宗教是使人束缚于锁链的鸦片,则当务之急就不是废除宗教,而是废除宗教的社会条件,以及实现宗教以虚幻的形式表现的“真理”。布洛赫进一步对宗教作出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前无古人的解释。他承认宗教是幻想,它假定了一个神话实体,它经常使人同不公正的社会条件妥协,并且是一种压迫的形式。但是问题在于,很长时期以来,宗教在几乎所有文化中都居于支配地位,尽管宗教所指向的世界并不是象实际可见的现实那样明显地存在。在布洛赫看来,宗教的这一“非现实性”对它的意义和重要性来说就是一把钥匙。
在布洛赫的观点中隐含着这样的看法,宗教不仅仅是幻想,而且只要所盼望所追求的事物还没有实现,它就是健康的、正常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废除的。布洛赫认为,宗教体现了“还没有意识到的知识”。这种“尚未意识到的知识”应当成为预见的对象。宗教是充满乌托邦精神的,“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宗教。”〔9 〕一切伟大宗教所希冀的是绝对的或完全的希望。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以面向实践的态度来对待宗教。
布洛赫详细分析了世界主要宗教,把宗教历史解释为人类不断地把我注入宗教奥秘的内容的过程。他在琐罗亚斯德教、佛教、道教、儒教、巴比伦和迦勒底的占星术、埃及和古希腊的古代宗教以及伊斯兰教中,发现了“还没有意识的知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创立一门新的宗教人类学,以便解释宗教渴望中的深度和强度;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创立新的宗教末世论,以便解释宗教领域所假定的完善存在的目的。
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真正的无神论,它主动地继承了宗教所希冀的内容及其具体乌托邦的哲学概念。它并不是对宗教的否定,因为宗教是希望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是积极的人道主义,它设法在现实中实现宗教的“希望珍宝”〔10〕。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元宗教可以继承宗教的某些功能,包括爆炸性的,与事实相反的希望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元宗教继承了宗教以神秘方式提出的生命的意义问题,把它作为理论实践的任务。它承认宗教的想象力即使在世界完全摆脱魔法之后也不能全部清除掉,因为它包括了“还没有意识的知识”以及对一个比现存世界更好的世界的期望。
四、“元宗教”理论对神学的影响
布洛赫试图把他的马克思主义元宗教理论同俄国造神派及寻神派的宗教虔诚区别开来,但人们仍怀疑他把马克思主义同实质上与宗教毫无二论的“投射元宗教世界观”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可以继承宗教的乐观希望的某些成份,但必须对这一希望加以限制,不致使自己成为某种形式的宗教。布洛赫声称他的马克思主义元宗教不是“宗教”,但他的元宗教似乎常常被认为是宗教的代用品而不是真正的元宗教。他的“还没有实现的人类”的提法很有宗教的味道。
与其说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发展,不如说他为基督教作出了贡献。布洛赫为神学家们提供了“后有神论”时期和“后个人主义”时期对基督教重新进行定义的典范。未来主义成为信仰的范例,希望成为最高的神学美德,上帝成为人前方的未来并以未来作为自己存在的方式。“希望神学”运动的主要著作——莫尔特曼的《希望神学》(1964)就是在布洛赫的影响下写成的。莫尔特曼并且进一步把布洛赫的观念吸收到《人,基督教人类学》和《试验的希望》两本著作中。正因为布洛赫帮助基督教发现了其末世论的内核,所以他被称为“无神主义神学派”或“半个神学家”。
布洛赫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新教神学,他也促进了当代政治神学的发展。约翰尼茨·麦茨(Johannes Metz )经典的政治神学著作《世界神学》,就受到布洛赫的影响。后来,布洛赫的思想被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家们如博尼诺(Bonino)、古铁雷斯(Gutierez)、 阿尔夫斯(Alves)和塞贡多(Segundo)所采纳。通过他们, 布洛赫的影响波及到非洲和亚洲,在那里,布洛赫的著作与向着共同拯救与社会正义的神学方面发展的基督教政治化结合起来。它也直接帮助基督教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一些国家中的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起了促进作用。希望哲学的逻辑结构的特点是对现成的现实发出挑战,它能够预见并创造一个新的历史现实。在希望神学和政治神学中,布洛赫所起的作用和亚里斯多德在过去的神学中所起的作用相同。除了布洛赫以外,德国政治神学也常常援引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
布洛赫被公认为西方卓越的思想家。在他的思想被莫尔特曼和德国其他神学家吸收以后,他的声名传遍世界。和海德格尔、布尔特曼一样,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神学思想家。布洛赫被“神学化”,这使他的声誉在马克思主义圈子中受到伤害,但他的思想在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对话中却具有实践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更是如此。
应当强调,布洛赫不是唯心主义者,也不是有神论者。他把近代无神论当作希望原理的基础。布洛赫也许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他认定,没有无神论,弥赛亚的救世希望便失去了地盘,因而无神论是一副解毒剂。尽管他主张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宗教,但他的核心命题却是“没有超验性的超越”,即没有上帝的人的自我完成。在基督教神学家看来,正是布洛赫拯救了基督教的内核。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之间没有也不应当有一条天然鸿沟。他们彼此完全可以建立谅解和交往的关系。
布洛赫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继承容易受到严肃批评。他并没有对宗教心理学和方法论提出真正的评论。他的目的旨在重新解释宗教的基本原则——不过是以乌托邦的或唯物主义的方式进行。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解释宗教、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内容,但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什么摩西发明了“出埃及”的上帝的观念,为什么恰恰是耶稣“使上帝成为人”。
布洛赫提出“还没有实现的人”意味着道德主义者与最高纲领主义者的价值处于不自主的优先地位,而他关于受辖制的概念,便成了“不朽”的代名词。布洛赫对善恶观念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宗教性的。他赞扬耶稣强调爱穷人、爱卑微者。这意味着,在瞬间的神秘主义背景下,这种爱最终会产生某些效果。他也承认,宗教设想的最大的恶是价值的,像阿道尔诺一样,他认为奥斯威辛表明假定一个彻底的恶的撒旦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形而上学才不致失去其深度。
布洛赫把耶稣描绘成社会变革家,是穷人利益的代表者。这与原始基督的性质不符,也不是从圣经中逻辑地导引出来的结论。基督宗教的普世性表明它超越阶级、民族和党派利益之上。近代有不少革命者反复申述耶稣是革命家的道理。他们为了现实的需要,把耶稣塑造为“爱国者”、“民族主义起义战士”,领导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造反派”,企图在地上建立平等公有的社会新秩序的“革命家”。对此,笔者持截然不同的立场〔11〕。
布洛赫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试图压制人类的宗教需要是有害的。我们的内在性不允许在一个“前历史时代”彻底扬弃宗教。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也可以起到过渡性的作用。他认为,当想象力与之联系的各种社会条件仍存在时,试图压制想像力的各种外在表现是一个错误。他强调在被压迫的社会阶层的斗争中,宗教观点具有潜在的作用。显然,把宗教的作用和地位归结为“异化的自我意识”是不恰当的。同样,把宗教的作用和地位归结为掩盖阶级利益的由社会而决定的副现象也不恰当。但是,布洛赫以现代主义的方式如此处理宗教,不论是对宗教的意图,还是对宗教意图之外的理性进步的可能性都不公平。可以说,当前迫切需要的是要承认这一“后经验观念”仍对我们有意义,而不是承认以未来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性”。
注释:
〔1〕布洛赫:《独立自主的人》“序言”,1970年纽约版,第20页。
〔2〕〔4〕〔5〕〔6〕〔7〕〔8〕布洛赫:《希望的原理》,1959年法兰克福版,第592、1628、1521、1404、1520、1402页。
〔3〕〔9〕〔10〕布洛赫:《基督教中的无神论》,第265、303、316—317页。
〔11〕参见安希孟:《关于原始基督教的性质》,《基督教文化评论》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原始基督教不是社会政治运动》,《欧美史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