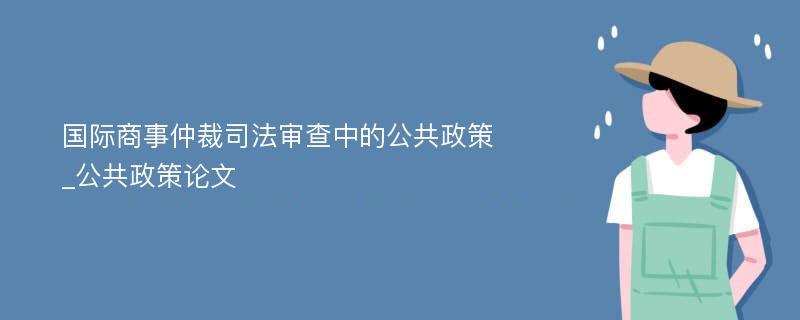
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商事论文,司法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国际贸易逐渐成为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环节。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发展既关涉民生,也关涉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在国际贸易中,尽管国家利益作为一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是考虑国家间战略关系的最高准则,但国际贸易活动的主体毕竟主要是私人或者经济实体,因此,国际贸易主要是不同国家间私人或者经济实体利益的博弈。这种利益博弈大多体现为合作,但现实中也存在大量不合作的情形,并直接体现为当事人之间的国际民商事争议。近年来,跨国贸易的增长使我国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实现了内在统一,但在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或国际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利益冲突中如何确定和坚守国家利益的底线,则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法院处理国际民商事争议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国际民商事争议的个案大多体现为个体利益间的冲突,在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的法律原则下,法院对个案中利益冲突的处理不仅要尊重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也要坚守一国的根本利益。在国际民商事活动中,这一底线通常称为“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在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中,公共政策的适用主要存在于法律选择、域外送达、域外取证、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等领域。本文之所以选择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首先,仲裁庭作为当事人约定的争议解决组织,通常只关注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的解决,很少顾及一国的国家利益或公共政策。一旦仲裁庭作出裁决需要法院承认和执行时,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将不得不对案件中的利益冲突或国家的公共政策进行考量。其次,在法律适用、域外送达、域外取证、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领域,我国法院鲜有适用公共政策的例子,①仅有的适用主要存在于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领域。最后,近年来,受合同条款、法律背景、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我国企业海外仲裁大多以败诉告终,海事纠纷仲裁尤为严重。②一旦外国仲裁机构作出不利于中方当事人的裁决,外方当事人就会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作为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中国负有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义务,③除非外国仲裁裁决违反《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的理由。在该条所规定的理由中,公共政策作为一国重大利益的维护者,是各国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兜底条款或者利益维护的安全阀,是一国利益转让的底线。在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领域,④公共政策也发挥同样的功能。 可见,考察我国国际贸易活动中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进而研究国家利益底线的确定和维护,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无疑是最佳选择。不同于《纽约公约》第5(2)(b)条“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表述,我国法律对公共政策有着多种表述,⑤其中,“社会公共利益”是最普遍的表达。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在第7(3)条同时使用“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表达同样的含义。我国立法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公共利益”取代“公共政策”概念。⑥由于“社会公共利益”侧重于“利益”,常被误解为“经济利益”,⑦一些学者主张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采用“公共政策”取代“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⑧为便于比较和研究,除特别说明,本文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公共政策”与“社会公共利益”。 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主要是在涉外法律适用领域讨论该术语的内涵以及相关立法规定。⑨学者的结论通常是应慎用公共政策。⑩然而,公共政策作为具体的法律制度,需要运用于审判实践中。因此,在法院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对这一制度所维护的核心利益和基本秩序作出适当鉴别,确定相关识别方法,不仅有利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而且对我国的涉外民商事审判有着重要价值。 一、公共政策在我国司法审查中的适用与问题 公共政策在实践中的适用问题主要反映在我国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考虑到当事人主张和法院认定标准的不同,本文设定如下范围和标准选取案例:(1)选取我国法院司法审查中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既包括外国仲裁裁决、中国涉外仲裁裁决,也包括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裁决。(2)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上实行报告制度,(11)本文统计的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案件,尤其是200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12)发布的代表性案例。(3)由于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直接涉及当事人利益的分配,被申请人经常以公共政策的理由拒绝执行仲裁裁决,而实际上案件并未涉及公共政策因素,类似案例在统计中予以排除。 根据前述标准,1992—2012年,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领域共有19个案件涉及公共政策的适用。在这些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以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仅2件,即1997年美国制作公司等申请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案(美国制作公司案)(13)和Hemofarm DD等申请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13464/MS/JB/JEM仲裁裁决案(Hemofarm案),(14)前者是我国涉外仲裁裁决涉及文化管制,后者是外国仲裁裁决涉及司法主权。由此可见,公共政策的适用只是极其例外的情形,亦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韦斯顿瓦克案中表明的观点,即对公共秩序应作“严格解释和适用”。 (一)公共政策的适用标准 关于公共政策的适用问题,存在主观说与客观说(又称结果说)的纷争。最高人民法院则强调,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结果是否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并不是裁决推理的方法或仲裁裁决表述的内容与中国法律不一致。例如,在2010年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申请承认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7—11号仲裁裁决案(2010年江苏中天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关于公共政策问题,应仅限于承认仲裁裁决的结果将违反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损害我国根本社会利益情形。”(15)在2012年韦斯顿瓦克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英国仲裁裁决案(韦斯顿瓦克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只有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将导致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我国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危及我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才能援引公共政策的理由。(16) 另外,中国法院在适用公共政策时还采用了唯一性标准。在前述19个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对其中4个案件没有讨论是否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主要原因是存在其他理由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或者下级法院不主张使用公共政策的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在2010年江苏中天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存在其他得拒绝承认情形,不宜再适用公共政策原则拒绝承认涉案仲裁裁决。”(17)在2009年荷比卢家装投资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洛桑12330/TE/MW/AVH仲裁裁决案(荷比卢家装案)、(18)2008年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申请承认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5-03号仲裁裁决案(天津鑫茂案)、(19)2008年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申请承认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4-05号仲裁裁决案(2008年江苏中天案)(20)和2007年邦基农贸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仲裁裁决案(邦基案)(21)中,尽管当事人以公共政策理由抗辩,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中并未对案件是否涉及公共政策进行讨论。由此可见,一旦案件存在其他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将不再讨论公共政策问题。 (二)公共政策的适用方法 1.肯定性方法。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讨论相关案件时开始列举公共政策的内容。例如,在2010年江苏中天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将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限于违反“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损害我国根本社会利益”。(22)在韦斯顿瓦克案中,援引公共政策的理由主要限于“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我国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情形,(23)在早期案件中则没有这些界定。这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试图采用肯定性方法对公共政策这一模糊的术语进行界定。 从现有案例看,最高人民法院列举的公共政策内容包括:法律基本原则、社会根本利益和善良风俗。(24)前两个方面体现在多个案例中,而善良风俗则主要体现在美国制作公司案中。1997年,美国乐队违反合同约定的演唱美国乡村音乐的内容,演出未经中国文化部审批的重金属歌曲。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执行该裁决将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一裁定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中国对文化演出市场的严格管制。这一案件提醒我们,公共政策有着明显的时代背景,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公共政策的内容也可能不尽相同。而且公共政策并不仅限于经济利益,社会基本的道德、宗教以及社会标准也应是公共政策的内容。(25) 2.否定性方法。除上述积极界定公共政策的范围外,最高人民法院更多采用否定性方法排除下列不属于公共政策的情形:(1)仲裁结果显失公平。在韦斯顿瓦克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以仲裁结果显失公平,违反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对涉案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不当。”(26)在2009年GRD Minproc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并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案(GRD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能以仲裁实体结果是否公平合理作为认定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标准。”(27)(2)争议事项的不可仲裁性。在国际社会,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经常被视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28)但是,在吴春英申请承认及执行蒙古国家仲裁庭作出的74/24-06号仲裁裁决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未提及公共政策。(29)(3)错误理解法律。在2010年路易达孚商品亚洲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油、种子和脂肪协会作出的第3980号仲裁裁决案(路易达孚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本案仲裁员认为中国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实践中的适用存在明显差距,但该错误认识并不会导致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违反我国公共政策。”(30)(4)案件涉及国有资产。德宝(远东)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案(德宝案)(31)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合肥市市容管理局申请不予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案(市容管理局案)(32)涉及国有投资1.05亿元设备闲置,但最高人民法院均否认公共政策的适用。(5)强制性规则。在众多涉及中国强制性规则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否定性方法限制公共政策的适用。 (三)公共政策适用中的问题 上述实践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采用严格限制公共政策适用的立场和方法,并且对下级法院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在适用公共政策上依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使用了不同的模糊术语界定和描述公共政策。在2010年江苏中天案中,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是指违反“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损害我国根本社会利益”的情形。(33)在GRD案件中,公共政策是指中国的“社会根本利益、法律基本原则或者善良风俗”。(34)在韦斯顿瓦克案中,“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我国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危及我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才能援引公共政策予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35)由于这些术语本身比较模糊,相关的含义和范围不清晰。 其次,在确定一个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否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时,中国法院通常会迅速得出相关结论,但缺乏推理和具体理由的解释。在2003年ED&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伦敦糖业协会第158号仲裁裁决案(ED&F案)(36)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从事境外期货交易。被申请人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行为,依照中国法律无疑应认定为无效。之后,就直接得出结论:“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能完全等同于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法院直接表达其观点,但没有解释这个观点的理由。在前述统计的大多数案件中,法院均采用此种处理方式。 再次,在前述19个案件中,有12件涉及我国的强制性规则,但无一起适用公共政策。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的区分已是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一个基本原则,但缺少区分的标准和规则。 更重要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可能会对下级人民法院适用公共政策产生压抑性效果。司法实践表明:最高人民法院严格限制公共政策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并且,仅涉及部门或者地方利益不构成适用公共政策的前提。(37)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鼓励法院不适用公共政策,即使适用也极有可能被推翻。长久如此,公共政策有可能变成一个单纯的学术理论,而丧失其在制度层面的生命。 在国际上,公共政策始终缺少详尽的界定,(38)各国对其认识不一。英国法官Borrough说:“它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旦你骑上它,你不知道它将带你到何方。”(39)为协调各国对待这一概念的差异,国际法协会组建专家组调研,并于2000年发布《关于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临时报告》(Interim Report on Public Policy as a Bar to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以下简称《公共政策临时报告》);2002年发布《关于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最终报告》(Final Report on Public Policy as a Bar to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以下简称《公共政策最终报告》)。(40)在《公共政策最终报告》中,公共政策被分为三个方面:法律的基本原则、公共政策规则和国际性义务。(41)本文借鉴此种分类,分析相关概念在中国现实语境下的含义。 二、公共政策与法律的基本原则 (一)公共政策与实体法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学界关于公共政策的界定中,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内容,(42)同样的术语也出现在韦斯顿瓦克案(43)和GRD案(44)中。公共政策下的“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构成一国根本性或基本性的法律制度。在确定法律的基本原则上,一些外国法院(例如瑞士法院)认为,这一概念指那些普遍意义上的法律原则,而不是具体的立法条款。(45)在德国,这一概念特别适用于宪法制度,特别是违反宪法基本权利或者违反民法基本原则的情形。(46)仅违反或者与当地法不兼容,并不构成违反德国的公共政策。(47)借鉴此种方法,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的实践,我国法院可以考虑公共政策维护的是宪法层面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例如,人民主权、民主、法治和人权原则。进一步说,下述内容应成为我国公共政策所维护的基本制度:四项基本原则;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原则。 对于实体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例如,《合同法》第一章规定的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等,不宜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公共政策范畴。在2003年香港享进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裁决案(享进案)(48)中,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的仲裁裁决违反民商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强制执行的结果既侵害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又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回复中否定了两级法院观点,认为不宜适用公共政策拒绝执行该仲裁裁决。 对于一般实体法律所规定的原则,因为其在各国是否成为根本性法律制度上存在差异,因此,要考察国际社会是否存在明示或默示的共识,(49)以寻求一致性的裁判结果。这一方法要求广泛考察外国法院的实践、相关评论员的评论、法律规则的起草背景以及其他法律资源。(50)在《公共政策最终报告》中,实体法的基本原则的示例有:有约必守原则、禁止滥用法律原则、禁止无偿征用、禁止歧视和保护无行为能力者等。(51)考虑到《公共政策最终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际社会共识,我国法院可以考虑这些原则是公共政策的范畴。当然,在具体的案件中,还要考察案件的国际性质以及与中国法律的联系程度。 (二)公共政策与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在《纽约公约》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中,第5条第1款所规定的程序性审查事项,诸如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的约定不符或者裁决不具有约束力等,经常与公共政策交织在一起。在德国和瑞士等国,违反正当程序可以构成公共政策的违反。(52)在《公共政策最终报告》中,程序性公共政策例子有:仲裁庭不公正;裁决是因欺诈或受到了贿赂的诱使或影响而作出;违反自然正义;仲裁员的任命中当事人地位不平等;仲裁裁决与另一个在申请执行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或仲裁裁决相冲突(即既判力问题)。(53)在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公共政策的有关报告中,程序性公共政策包括贪污、贿赂、欺诈以及其他类似的严重情形。(54) 我国法院对程序性事项适用公共政策一直持审慎态度。在2008年江苏中天案和天津鑫茂案中,即使仲裁程序违反正当法律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因此讨论公共政策问题。在享进案(55)中,仲裁协议未经被申请人授权,是第三人通过欺诈手段订立的。尽管该案因为仲裁协议的问题被拒绝承认和执行,但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证实欺诈构成公共政策。该案意味着仲裁协议中的欺诈不能成为公共政策。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2001年英国嘉能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仲裁裁决案。(56)在2010年江苏中天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明,一旦案件存在其他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将不再讨论公共政策。(57)但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否认公共政策的程序性内涵。在市容管理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社会公共利益不仅是为了维护仲裁程序上的公平,而且还担负着维护国家根本法律秩序的功能”。(58)鉴于此,前述《公共政策最终报告》和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公共政策的有关报告中有两个问题尚待明确:一是仲裁程序中的贪污和贿赂行为;二是既判力问题。 首先,贪污和贿赂行为。在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11/2003号仲裁裁决案(59)和百事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第076/2002号仲裁裁决案(60)中,由于涉案中国仲裁员在两起案件仲裁过程中受贿并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一些学者主张以公共政策的理由拒绝执行这两个外国仲裁裁决。(61)但由于相关受贿事实缺乏认定,这一主张没有得到最高人民法院认可,最终以仲裁程序与仲裁协议不符的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然而,在中国,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在此高度上,仲裁过程中的贪污和贿赂行为,尤其是对案件处理结果产生影响的贪污和贿赂行为,应构成中国的公共政策。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公共政策的报告认为,国际社会无疑存在如下共识:即如果某一仲裁裁决受到贪污的诱使或影响,该仲裁裁决应被拒绝承认与执行。(62)1965年《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第52(2)条也规定受贿是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63)在澳大利亚、(64)法国(65)和美国等国家,(66)这方面的仲裁裁决均被认为违反公共政策。因此,如果国际商事仲裁中存在贪污和贿赂行为,又没有其他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则可以适用公共政策。 其次,既判力问题。既判力的问题存在于2010年江苏中天案、天津鑫茂案和2005年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申请承认与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060/1999号仲裁裁决案(三井物产案)中,(67)最明显的是2008年Hemofarm案,但我国法院均未讨论该问题。Hemofarm案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最高人民法院以公共政策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的外国仲裁裁决。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中国法院就租赁合同纠纷裁定对合资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并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国际商会仲裁院再对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在此案中,仲裁裁决否认中国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正当性。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法院对财产保全行为拥有排他性的管辖权。(68)而且,审判权是国家司法主权的一部分。因此,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裁决否决了我国法院的管辖权,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进而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 然而,这一结论引发了争议。侵犯一国的主权通常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公权力机关之间,属于国际公法的事项。而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裁决的作出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仲裁庭是根据当事人约定成立的解决争议的私人组织,这样一种民间机构不可能实施国际公法上侵犯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为。在Hemofarm案中,仲裁庭的裁决构成对中国法院生效判决的否决,无疑违反了中国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实际上,在一个仲裁裁决与执行地国法院生效判决或者已经被法院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相冲突的情况下,既判力原则能够构成公共政策的内容。(69)在此方面,埃及有明确的立法,(70)英国(71)和印度(72)有既判力问题构成公共政策的案例。因此,在Hemofarm案中,运用既判力原则确定公共政策的适用,比侵犯“国家司法主权”更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在公共政策与法律基本原则的关系上,有以下标准可供使用和借鉴:一是法院地法律制度和国家利益的根本性;二是裁判结果的一致性,即考察国际社会是否存在明示或默示的共识。 三、公共政策与强制性规则 (一)强制性规则与我国法院的司法审查 作为我国法院适用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区分公共政策与强制性规则这一方法是在案件报告制度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并已成为仲裁司法审查领域统一司法尺度的重要工具。(73)在前述19起案件中,强制性规则所涉公共政策问题有12个,我国法院的处理可分为五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仲裁裁决违反我国的强制性规则,但法院未适用公共政策。 1.进出口配额。1992年开封市东风服装厂和大进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案(东风案)(74)是第一起这类案件。本案中被申请人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以国家规定三资企业不得使用出口配额为由,拒绝继续按合同向合资公司如数提供出口配额,并扣留了合资公司出口结汇款。然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理由是“依据国家现行政策、法规规定,如予以执行将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影响国家对外贸易秩序。”由于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此类裁定可以上诉,申请人将情况反映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仲裁裁决的执行将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影响国家对外贸易秩序为由,裁定不予执行,是不正确的。” 2.期货交易的限制。在ED&F案中,双方当事人利用期货炒作牟取投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依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从事境外期货交易。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行为,依照中国法律无疑应认定为无效。但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能完全等同于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因此,本案不存在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情形。(75) 3.外汇管制。在2005年三井物产案中,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在未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外债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对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直接承担债务,违反了中国有关外债审批及登记的法律规定和国家的外汇管理政策。(76)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对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强制性规定的违反,并不当然构成对我国公共政策的违反……本案仲裁裁决不应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77) 4.外国投资。在天瑞酒店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仲裁裁决案(天瑞案)(78)中,申请人天瑞公司与被申请人签订一份关于酒店商标的特许经营协议。为了规避中国对外国公司从事特许经营业务的审批制度,申请人将该特许经营协议分拆为两份合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外资准入中的备案制度属于行政法规之强制性规范中的管理性规定,不影响当事人之间民事合同的效力。仲裁裁决对本案所涉协议的处理不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规定,更不构成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情形。(79) 第二种情形是中国的强制性规则不适用于系争货物。这一情形主要存在于进出口限制领域。在路易达孚案和邦基案中,尽管案件涉及中国海关关于货物进出口限制的行政禁令,但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表明违反该行政禁令是否构成违反中国的公共秩序,主要原因是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相关行政禁令并不适用于当事人系争货物。(80) 第三种情形关涉公共健康和行政命令,但没有证据证明系争货物将产生严重的安全卫生问题。在舟山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申请不予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裁决案(舟山中粮案)(81)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由于该批货物符合进境检验检疫要求,因此不在禁止入境的货物之列。此外,并无证据表明该案所涉货物会带来严重的安全卫生问题,也不存在有损公众健康的事实。因此,执行该仲裁裁决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在路易达孚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也作出类似认定。(82) 第四种情形是案件造成严重后果,但当事人在仲裁中没有主张相关强制性规则的适用,因此,仲裁裁决并未涉及中国的强制性规则。这一情形存在于环境污染领域。在GRD案件中,系争设备在运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物质,导致5位一线职工在对系争设备进行调试生产时因发生铅中毒而住院。被申请人提交仲裁,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全部已付货款和赔偿损失。由于仲裁裁决并没有涉及环境污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答复中也没有澄清环境污染是否构成中国的公共政策问题。(83) 第五种情形存在于倾销领域。在2010年江苏中天案、天津鑫茂案和2008年江苏中天案中,所涉货物被商务部认定为倾销货物,被申请人因此主张适用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在此3个案件中没有对此作出认定,因为有其他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84) 上述案件中,真正涉及中国强制性规则的是第一类情形的5起案件,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些规则均不构成中国的公共政策。舟山中粮案和路易达孚案等,由于案件特殊,并没有明显违反中国的强行法。而在倾销领域,由于有其他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没有讨论。因此,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规则的区分虽是最高人民法院实践的一个原则,但如何区分尚无标准。 (二)公共政策与强制性规则的区分方法 每一个公共政策规则都是强制性的,但并不是每一个强制性规则都能够构成公共政策。(85)在涉外案件的处理中,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界定了构成强制性规定的几个条件:(1)强制性规定是涉及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或行政法规;(2)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强制性规定的适用;(3)强制性规定无需冲突规范的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4)强制性规定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有:劳动者权益保护、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反垄断或反倾销以及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前述讨论中,区分公共政策与一般性强制性规则已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公共政策的一个原则。然而,到底什么样的强制性规则能够构成公共政策,需要进一步澄清和界定。在此问题上,下述三种方法可以为我国法院考虑。 一是考察案件与中国法律的联系程度。如果案件争议并没有涉及或直接违反中国的强制性规定,则我国法院应尽量不适用公共政策制度。前述的路易达孚案、邦基案和舟山中粮案均属于这类情形。 二是考察国际体制的需要,即分析强制性规则所蕴含的外部政策和内部政策。外部政策和内部政策的区分方法,现在越来越多地为一些国家法院适用。例如,在Scherk v.Alberto-Culver Co.案(86)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国内公共政策不同于国际公共政策。同样,在证券、(87)反托拉斯(88)等领域,美国法院认为,国际公共政策是提升国际贸易和世界和平的必要元素,应优先于国内法所体现的国内公共政策。(89) 最高人民法院也指出,前述2012年司法解释的“强制性规定”与中国合同法中所谓效力性或管理性强制规则不同,“一定是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那类强制性规定,对此要从立法目的上考察”。对于“强制性规定”的理解应当严格、谨慎,否则会折损国际私法的积极作用,甚至带来消极后果。(90)因此,构成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规定,应是那些能够适用于国际层面的强制性政策。在实践中,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否定违反中国商品期货交易的限制和外汇管制等的规定构成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可以推论,最高人民法院已注意到法律规则外部政策与内部政策的区分。这一区分应构成判断某一强制性规则能否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权衡因素。 三是注重客观说,即对于违反中国强制性规则的情形,如果认定构成违反公共政策,则必须违反中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损害中国的根本社会利益。在2010年江苏中天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强调“关于公共政策问题,应仅限于承认仲裁裁决的结果将违反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损害我国根本社会利益情形。”(91)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强制性规定是国家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在国际私法领域中的一个突出表现。例如,反垄断法、外贸管制法、价格法、社会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般旨在保护本国经济秩序或对某类利益进行特殊保护。(92)这些领域与《公共政策最终报告》所列举的公共政策规则的示例十分相似。在此情形下,中国法院可以考虑那些违反上述领域的强制性规则的情形,认定其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但需要指出的是,规则的违反本身不是适用公共政策的理由。这种违反的结果必须是侵犯中国社会根本利益,损害中国基本的法律制度。借用社会“根本”利益和“基本”法律制度(93)的标准,旨在区分一般性的强制性规则与构成公共政策的强制性规则。 四、公共政策与国际义务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得出,在一个国家内,公共政策主要维护的是一个国家根本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在国际社会,国际公共政策维护的不应是个别独特的、非国际性的制度,而应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可、并作为整体接受的一些根本性的制度。与国内社会相比,国际社会更难形成一致认可的强制性制度和“国际公共政策”规则。但任何法律秩序不可能只含有任意规范,还应有强行法规则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服务,并体现整个国际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任何国家均有遵守这些强制性规则的义务。(94)因此,作为国家的国际义务暗含国际公共政策的因素。 在国际法上,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义务是指国际法主体在国际交往中,依据国际法规定所应遵循的义务。在此方面,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了国家遵守条约法的义务,2005年联合国《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以下简称《国家责任》)将国际义务分为双边义务和多边义务,多边义务进一步可分为对国家集团的义务和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95)在国际义务层面,能够为国际社会整体接受的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它维护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利益。这种义务不以国家的同意为前提,是国际社会共同认知的一些根本性制度。而双边义务和多边义务中的对国家集团的义务主要体现为国与国之间关系或一国与国家集团的关系,其更多由国际条约或协定确定,以国家明示或默示的同意为前提。 1.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 根据《国家责任》的规定,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主要是指严重违背依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则承担的义务。(96)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则始得更改之规则。而且,遇有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则产生时,任何现有条约之与该项规则抵触者即成为无效而终止。(97) 尽管国际法强制规则体现为整个国际社会所需要保护的公共政策,但这种规则主要是国家间的义务,在国际民商事关系领域很少发生。即使发生,当事主体之间也不可能在事前和事后达成仲裁协议并提交仲裁。但其确有间接存在的可能,例如,如果执行一项裁决,将会使相关资金流向一个外国公司,而该外国公司曾资助某一国家或机构从事违反国际法强制规则的行为,就可以构成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另外,在国际法强制规则中,国际人权法是最有可能被适用的。但现有国际人权公约中很少具有一般国际法的地位,大部分个人人权仍属于国内法调整的范畴。在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中,国际人权法主要体现于正当程序的要求,尽管在外国有被认为属于公共政策问题,但在我国却很难成为公共政策的范畴。 2.对国家集团的义务 现代国际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国家集团,有的是全球性或区域性组织,如欧盟;有的是因条约而形成的国家集团,如裁军条约或无核区条约等。由于国家集团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且义务本身不具有确定性,很难说违反该义务就构成公共政策的违反。在具体案件中,不仅要考虑义务的性质,还要权衡相关法律后果。 在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诉法国航空公司案(98)中,两个航空公司于1972年达成法航帮助利比亚航空维修航空器的合同,并达成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规则进行仲裁的协议。在1988年洛克比空难发生后,安理会在1992年通过第748号决议对利比亚实施禁飞和武器禁运。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法航认为已不可能继续履行合同。1995年,利比亚航空提起仲裁,仲裁地为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法航认为,该案中的争议具有不可仲裁性,违反了国际公共政策。但该主张被仲裁庭的临时裁决所否决。2003年,法航以违反国际公共政策为由先后向魁北克的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申请撤销该临时裁决,均被拒绝。 在此案中,公共政策因素应是一个考虑的理由。首先,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为应付威胁和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的严重争端或情势,可作出对联合国一切会员国均有约束力的决议。(99)而且宪章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与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可见,联合国宪章的普遍约束力和优先地位赋予安理会上述决议的强制性效力。其次,在国际法协会《公共政策最终报告》中,安理会的决议是作为国际义务中构成公共政策的示例。(100)但这一认识并没有得到上述法院的认可。 如果上述案件的最终裁决需要在我国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0条,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该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可见,我国法院可以执行有关裁决将违反我国条约义务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但考虑到《联合国宪章》的普遍性效力和安理会决议的强制性效力,我国可以灵活确定是否适用“公共政策”条款。 3.双边义务 双边义务主要是指一国对另一国所负有的国际法义务。双边义务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双边条约;由许多双边关系构成的多边条约,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中的许多规则以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等;特定的单方面行为,如一国对另一国所作的允诺或承认即产生对另一国的义务;规定第三方权利的条约以及国际法院的司法判决,等等。考虑到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中均有国际条约适用的规定,实践中应以尽量不援用公共政策为原则,但值得关注的是国家主权与财产豁免领域。 在《民事诉讼法》第282条中,国家“主权、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并列,(101)但二者并不是平行的概念,后者应该包含前者。由于前者过于重要,立法者在起草该条时将这两个因素专门列举。(102)国家主权和安全应构成该国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但在现代国际社会,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受到挑战。有学者指出,绝对主权观念与强行法理论在本质上就是一对矛盾。后者进入国际法体系就是为了限制前者,前者也只有在后者的限制之下才能正确实施。倘若两者共存于同一法律制度中,整个国际强行法体系就会毁于这一根本性矛盾的冲突中。(103) 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代表着当前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发展趋势,中国也签署了该公约。公约不仅规定了国家豁免的明示和默示的放弃,(104)而且确认了国家司法管辖豁免的限制。(105)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一国如与外国一自然人或法人订立书面协议,将有关商业交易的争议提交仲裁,则该国不得在另一国原应管辖的法院有关下列事项的诉讼中援引管辖豁免:(1)仲裁协议的有效性、解释或适用;(2)仲裁程序;或(3)裁决的确认或撤销,但仲裁协议另有规定者除外。(106)然而,与国家援引管辖豁免存在诸多限制相比,一国在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方面具有更多的“绝对性”。公约第18条和第19条规定,除非一国明示同意放弃执行豁免,或者该国已经拨出或专门指定某项财产用于清偿对方的请求,另一国法院不得在诉讼中对该国财产采取判决前的强制措施,亦不得采取判决后的强制措施。也就是说,在执行豁免方面,国家豁免的放弃只存在明示放弃的形式,而不存在默示放弃的形式。因此,如果没有得到一国的同意,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又涉及一国及其财产的,该国就可以公共政策的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 总结前述的讨论,国际义务是否能够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公共政策,取决于相关的义务能否成为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而对于对国家集团的义务和双边义务,如果存在国际条约,则可以违反国际条约为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在不存在条约的情况下,则视相关国际义务的性质来决定公共政策是否能够适用。 五、结论与思考 分析至此,在方法层面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通过权衡以下六种因素确定公共政策的适用:(1)案件的国际性质以及与一国法律的联系程度;(2)法院地法律制度和国家利益的根本性;(3)国际体制的需要,即分析法律制度所蕴含的内部政策和外部政策;(4)裁判结果的一致性,即是否存在国际共识;(5)损害结果的客观性和严重性;(6)国际义务的性质,即是否属于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上述因素体现了适用公共政策的国际化趋势和标准,体现了国际社会或国家间“合作”的因素。 然而,在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领域,本地法的权威性与当事人既得权的保护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为缓解二者之间的冲突,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均采用狭义公共政策概念,严格限制公共政策的适用。这种自觉的自我限制有很多解说,理论上体现了斯托雷所言的“国际礼让”。(107)当然,从政府利益的角度,这种自我限制的实质是希望通过国际合作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因合作而取得,因此可称之为“合作利益”;而对于国家因适用公共政策所维护的自我利益则对称为“非合作利益”。 合作利益在公共政策领域体现为国际公共政策概念的扩张。19世纪末,瑞士学者布鲁歇(Brocher)开始强调国内公共政策与国际公共政策的区分。(108)法国和葡萄牙的立法已采纳国际公共政策的概念。(109)在国际法协会《公共政策最终报告》和最终建议中,国际公共政策取代公共政策,成为正式术语。在我国公共政策的研究中,国际公共政策受到一致认可。但在当代,国际公共政策的概念已完全不同于布鲁歇时代的国际公共政策,其至少包含两层内容:一是国际公法上的公共政策,即国际法强制规则,维护的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二是布鲁歇及很多学者所称的国际私法上的公共政策,该公共政策虽然常被称为“国际公共政策”,但“国际”一词徒有虚名,其本质上属于国内公共政策,不过,其程序性的指导效能的确超出一国纯粹国内法制度的范围。(110)但这种公共政策毕竟不同于第三种公共政策,即完全适用于一国之内的内国公共政策(internal public policy)。例如,外汇管制在国际民商事关系中不能成为我国的公共政策,但在纯粹国内的民商事关系中,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当事人必须遵守。整体看来,“国际公共政策”的提出和应用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对合作利益的维护,是对“非合作利益”的限制。 不可否认,国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反映整个国际社会普遍愿望和利益的公共政策。而且由于人类在一些法律制度层面的趋同,“国际公共政策”在实践中适用的空间将越来越大。(111)然而,就像有的学者曾用康德关于“非群性之群性”理论说明国家的双重本性那样,被人格化的国家与个人一样有渴望自由的一面,也有寻求群体的一面。因为乐于群体,各国有承认并遵守国际秩序的意愿,(112)从而有利于形成国际一致的价值和准则;因为追寻自由,各国又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常常是一国独特的制度或文化,它们构成一国必须保有的非合作利益。 主张在国际民商事关系中适用国际公共政策,而不是国内公共政策,这种观点与各国对于公共政策的期望不符。各国在参加《纽约公约》或在国内立法中规定公共政策,更多考虑的是本国独特的制度和价值能够在国际商事交往中得以维护,这种独特的制度和价值不可能成为国际公共政策的范畴。与传统上认为公共政策旨在维护一国根本利益的认识不同,上述独特的制度维护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或贸易制度,它所维护的利益更多地体现在一国独特的价值、文化和体制方面。正如亨廷顿所言,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他们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仅受其内部价值和体制的影响,也受国际规范和国家体制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那些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存在共同的利益。(113)这种价值、文化和体制方面的内容,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根本的政治架构,也决定了当今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文明的多元性。因此,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国家根本利益的安全阀,也是一个国家价值、文化和制度的守护者。正是在这意义上,欧盟和加拿大坚守“文化例外”原则,即在国际自由贸易体制下,基于文化商品和服务的双重属性,将其排除在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之外,不适用有关的自由贸易法律体制。(114)自由贸易中的文化例外也应成为我国在自由贸易谈判中的保留举措,以传承中华文明,维护中华文化的安全。因此,文化利益应该是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 除了文化利益外,国家利益还有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关涉国家的生存、主权和发展,而经济利益则体现为经常性利益。(115)从国际商事活动中公共政策的适用看,公共政策所维护的非合作利益应主要体现在安全利益和文化利益领域。而对于经济利益而言,除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交叉领域的经济主权外,其绝大部分领域应属于国际自由贸易中的合作利益,无需适用公共政策范畴。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的大国不断输出其价值、文化和体制,合作利益的内涵将越来越丰富。在国际关系处理上,合作利益不仅是国家利益维护的应有之义,也是大国战略决策的首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言,合作利益的模式决定了应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司法层面,合作利益的广泛性决定了公共政策的适用将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公共政策也体现为一国合作利益与非合作利益的博弈。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中,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利用公共政策这样的法律制度维护自己的利益底线。毕竟非合作利益是一国的立国之本、生存之基,也是对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文明的保护。 责任编审:张芝梅 注释: ①相关情形可参见何其生:《域外送达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7—228页;高晓力:《国际私法上公共政策的运用》,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 ②参见何欣荣、贾远琨:《中国海事纠纷迭起境外海事仲裁败诉率高达90%》,《经济参考报》2011年12月13日,第8版;张维:《语言不通程序不熟费用昂贵理念迥异 中国企业海外仲裁十案九败》,《法制日报》2011年8月8日,第6版。 ③到2013年底,《纽约公约》有149个缔约方。公共政策规定在公约第5条第2款第b项。 ④在我国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中,公共政策主要存在于三个领域: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以及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 ⑤例如,《民事诉讼法》第282条的相关表述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第274条第2款则使用“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 ⑥例如,《合同法》第5、52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5条均用“社会公共利益”取代“公共政策”。 ⑦Kelley Brooke Snyder,"Denial of Enforcement of Chinese Arbitral Awards on Public Policy Grounds:The View from Hong Kong,"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42,no.1(Fall 2001),p.342; Michael Moser,"China and the Enforcement of Arbitral Awards(Part 2)," The Journal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vol.61,no.2,1995,pp.50-51. ⑧参见张宪初:《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中“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韩健主编:《涉外仲裁司法审查》,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377页。 ⑨参见金彭年:《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研究》,《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金振豹:《国际私法上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之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6期;孙建:《对国际私法上公共秩序问题的探讨——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中的公共秩序问题》,《南开学报》2005年第2期。 ⑩ 高晓力:《国际私法上公共政策的运用》,第323页。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法发(1995)18号)。 (12)该套出版物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万鄂湘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编,至2013年底,已出版25辑。为精炼起见,本文所引《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的案例省去责任者、出版地点和出版社。 (13)1997年12月26日,经他(1997)35号复函。 (14)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8辑,2009年,第124—134页。 (15)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1辑,2010年,第122页。 (16)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4辑,2012年,第116页。 (17)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1辑,2011年,第122页。 (18)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9辑,2010年,第111—125页。 (19)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7辑,2009年,第81—102页。 (20)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6辑,2008年,第38—59页。 (21)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5辑,2008年,第24—30页。 (22)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1辑,2011年,第122页。 (23)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4辑,2013年,第116页。 (24)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5辑,2013年,第154页。 (25)关于善良风俗的讨论,参见Parsons & Whittemore Overseas Co.v.Societe Generale de l'Industrie du Papier(RAKTA),508 F.2d 969(2d Cir.,1974); Julian D.M.Lew,Applicable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Minneapolis:Oceana Publications,Inc.,1978,p.532. (26)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4辑,2013年,第116页。 (27)《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8辑,2009年,第135页。 (28)参见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Towards a Uniform Judicial Interpretation,Alphen Aan Den Rij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81,p.360; Herbert Kronke et al.,eds.,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A Glob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Alphen Aan Den Rij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10,pp.348-350. (29)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9辑,2010年,第97页。 (30)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2辑,2012年,第181页。 (31)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3辑,2013年,第68—72页。 (32)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2辑,2006年,第46—50页。 (33)《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1辑,2011年,第122页。 (34)《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8辑,2009年,第135页。 (35)《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4辑,2013年,第116页。 (36)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7辑,2004年,第12—17页。 (37)参见杨弘磊:《人民法院涉外仲裁司法审查情况的调研报告》,《武大国际法评论》第9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9页。 (38)Deutsche Schachtbau-und Tiefbohrgesellsca hft mbH v.R' As al-Khaimah National Oil Company[1988] 2 Lloyd's.Rep.246 at 254. (39)Richardson v.Mellish,(1824) 2 Bing 229,252. (40)http://www.newyorkconvention.org/Publications/ full-text-publications,2014年3月1日。 (41)参见《公共政策最终报告》,第6页。 (42)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黄进主编:《国际私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43)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4辑,2013年,第116页。 (44)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8辑,2009年,第135页。 (45)Robert Briner and Paolo Michele Patocchi,"National Report for Switzerland(2008)," in Jan Paulsson,ed.,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Supplement no.51,Alphen Aan Den Rijn:Wolters Kluwer,2008,p.37. (46)OLG Thuringia(Thuringia Court of Appeal,Germany,2004),ICCA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33,2008,pp.500,503. (47)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Towards a Uniform Judicial Interpretation,p.360. (48)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7辑,2004年,第36—40页。 (49)参见《公共政策最终报告》,第9页。 (50)参见《公共政策最终报告》,第9页。 (51)参见《公共政策最终报告》,第6页。 (52)Syrian Claimant v.Defendant,Hanseatisches Oberlandesgericht Hamburg,March 12,1998,ICCA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29,2004,p.663; Italian Party v.Swiss Company,Berzirksgericht Zurich,February 14,2003,ICCA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29,2004,p.819; A SA(Switzerland) v.BCO.Ltd.(British Virgin Islands),Tribunal Fédéral(Federal Supreme Court,Switzerland),December 8,2003,ICCA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29,2004,p.840. (53)《公共政策最终报告》,第7页。 (54)"Report of the UNCITRAL Commission,Commenting on Public Policy as Understood i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and Model Law," UN Doc.A/40/17,paras.297,303. (55)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7辑,2004年,第36—40页。 (56)参见万鄂湘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编:《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与研究》第1卷,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67—76页。 (57)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1辑,2011年,第122页。 (58)《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2辑,2006年,第47页。 (5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四他字第41号复函。 (6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四他字第42号复函。 (61)参见邓莉莉:《解析:百事仲裁案》,《大经贸》2006年第12期。 (62)"Report of the UNCITRAL Commission,Commenting on Public Policy as Understood i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and Model Law," UN Doc.A/40/17,para.112. (63)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March 18,1965. (64)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1974,S.19(a); D.Miller,"Public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Australia,"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vol.9,no.2,1993,p.167. (65)European Gas Turbines SA v.Westman International Ltd.,Cour d'Appel,Paris,September 30,1993,ICCA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vol.20,1995,p.198. (66)Biotronik Mess-und Therapiegeraete GmbH & Co.v.Medford Medical Instrument Co.,415 F.Supp.133.140(D.N.J.1976). (67)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1辑,2006年,第109—112页。 (68)参见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92、258条。 (69)《公共政策临时报告》,第29页;Herbert Krone et al.,eds.,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A Glob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Alphen Aan Den Rij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10,p.393. (70)Art.58(2)(a) of the Law concerning Arbitr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71)Vervaeke v.Smith,[1983] 1 AC 145; E.D.& F.Man(Sugar) Ltd.v.Haryanto(No.2),[1991] 1 Lloyd's Rep.429. (72)Renusagar Power Co.Ltd.v.General Electric Co.,AIR,1994 SC 860. (73)参见万鄂湘:《〈纽约公约〉在中国的司法实践》,《法律适用》2009年第3期。 (74)参见宋航:《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31页。 (75)《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7辑,2004年,第12页。在仲裁裁决的审查过程中,被申请人及下级法院均认为,该裁决认可了双方通过规避中国期货交易管理法规从事境外期货交易所取得的非法利益,违反中国法律强制性的规定,构成对中国公共政策的违反。 (76)参见高晓力:《国际私法上公共政策的运用》,第258页。 (77)《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1辑,2006年,第109页。 (78)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2辑,2012年,第175—180页。 (79)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2辑,2012年,第175—180页。当时,外国公司在我国境内从事商业特许经营业务,必须经过行政主管机关的审批。但在案件提起仲裁时,仅需要事后向行政主管机关备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申请人将特许经营合同故意拆分成两份协议,试图规避我国对外国公司从事特许经营业务的准入制度,可以认定违反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80)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2辑,2012年,第181页;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5辑,2008年,第24页。 (81)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8辑,2009年,第143—147页。 (82)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2辑,2012年,第181页。 (83)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8辑,2009年,第135页。 (84)参见《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1辑,2011年,第122页;《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7辑,2009年,第81页;《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16辑,2008年,第38页。 (85)《公共政策临时报告》,第18页。 (86)Scherk v.Alberto-Culver,417 U.S.506(1974). (87)Shearson/American Express Inc.v.McMahon,482 U.S.220(1987); Rodriguez de Quijas v.Shearson/American Express Inc.,490 U.S.477(1989). (88)Mitsubishi Motors Corp.v.Soler Chrysler-Plymouth,Inc.,473 U.S.614(1985). (89)Gary Born,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Cases and Materials,New York:Wolters Kluwer,2011,pp.430-438. (9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答记者问,2013年1月6日,http://www.court.gov.cn/xwzx/jdjd/sdjd/201301/t20130106_181593.htm,2014年3月1日。 (91)《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第21辑,2011年,第122页。 (9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就《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答记者问,2013年1月6日,http://www.court.gov.cn/xwzx/jdjd/sdjd/201301/t20130106_181593.htm,2014年3月1日。 (93)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March 28,1955,UN Doc.E/2704 and E/AC.42/4 Rev.1,para.49. (94)参见《李浩培文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02、513页。 (95)《国家责任》第42、48条。 (96)参见《国家责任》第3章。 (97)《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4条。 (98)La Compagnie Nationale Air France v.Libyan Arab Airlines,2003 CanLII 35834(QC CA). (99)参见《联合国宪章》第39、41条。 (100)参见《公共政策最终报告》,第11页。 (101)《民事诉讼法》第282条。 (102)徐宏:《国际民事司法协助》,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1页。 (103)万鄂湘:《国际强行法与国际公共政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104)《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7—9条。 (105)《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10—16条。 (106)《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17条。 (107)关于斯托雷的国际礼让理论,参见黄进主编:《国际私法》,第213页。 (108)关于布鲁歇的公共政策理论,参见黄进主编:《国际私法》,第212页;J.Kosters,"Public Policy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Yale Law Journal,vol.29,no.7,1920,p.752. (109)法国1981年新民事诉讼法典第1498和1502条;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第1096(f)条。 (110)Jacob Dolinger,"World Public Policy:Real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in the Conflict of Law,"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17,no.2,1982,pp.172-173. (111)参见李双元、徐国建主编:《国际民商新秩序的理论构建:国际私法的重新定位与功能转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7—269页。 (112)阿·菲德罗斯等:《国际法》,李浩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18页。 (11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114)关于文化例外原则,参见何其生、张喆:《国际自由贸易中的“文化例外”原则》,《公民与法》2012年第5期。 (115)高伟凯:《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利益原则》,《国际贸易》2007年第3期。标签:公共政策论文; 法律论文;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论文; 司法审查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申请执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商事主体论文; 商事登记论文; 最高人民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