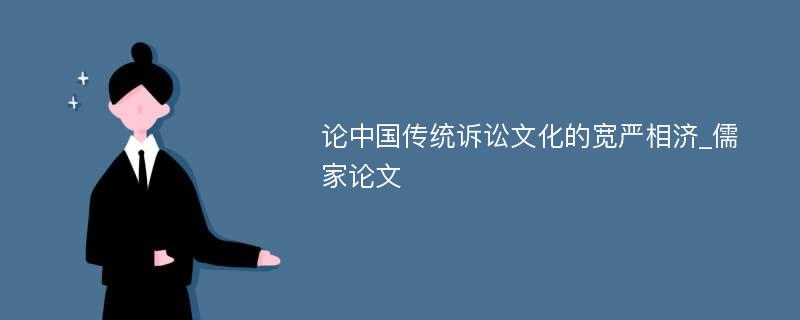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宽严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迥异于世界其它诉讼法律文化,呈现浓厚的伦理性表征,别具特色。同时,它也和其他诉讼法律文化一样,有其固有的诉讼理论基础和理论要素,而其理论基础和要素又强烈地体现着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下的诉讼法律文化个性。概括起来主要为:诉讼理论指导的“德”耶、“威”耶?司法审判的“宽”耶、“严”耶?刑罚施用的“轻”耶、“重”耶?而且,传统诉讼中的德威、宽严、轻重问题往往又显现出一种即此非此,即彼非彼,彼此间既同又异、既异又同的较为复杂的关系。因此,在探寻、把握传统中国诉讼法律文化时,必须对德威、宽严和轻重关系做一番实质性研究,(注:《德威之辨:传统诉讼法律文化理论概观之一》,载《湘江法律评论》第2卷,湖南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关于“轻重之辨”将另文专论。)方能揭示长达数千年之久且内容极其浩繁复杂,同时发展又颇具规律性的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化的真谛。本文仅就宽严关系试作探讨。
一、法宽与刑严
传统法律的工具性功能,决定了社会对法与罚的须臾不可或缺性的法律认识:“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注:《四库全书总目·按语》)统治阶级深深懂得立法是重要的,用刑更为重要。然则传统立法与用刑施罚往往不相统一,常生矛盾。这种矛盾首先在立法中显露,而立法的矛盾又必然带来司法的龃龉。大家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成文法传统,历朝建统后首先是制定普遍适用的基本法典,而在基本法典的制定上,由于起码受到西周以来礼治和儒家宽仁思想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汉代儒家思想开始被确立为法律的主导思想后,所以无不强调立法“务在宽简”,(注:《旧唐书·刑法志》)标榜“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注:《旧唐书·刑法志》)但实际上,历代统治者在制定基本法典以外,大量的敕、格、诰、例等其它法律形式又不断地被创制。由于其它法律形式和法律规范缺乏一体性,而且其法律效力甚至大到可以“代律”、“破律”之程度,加之不少司法官又偏爱乐用这些律典以外的法律规范,因此,司法中宽严的不稳定态势必然出现,进而形成一种诉讼文化模式。完全可以说,它不仅体现为个别和暂时的现象,而且铸成为一种传统社会的诉讼心理。如商朝制有“汤刑”和“官刑”,此外,诸如醢刑、脯刑、炮烙刑等法外刑(多为酷刑)又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如果说,商代之情形或不带有普遍性,那么在汉武帝时儒家思想被官方认可为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思想后,德主刑辅思想和“恤刑”制度形成后的封建诉讼就更能体现其属性了。故此,我们试举几个事例或许最能说明问题。例一,汉代有一著名中央司法官杜周,身居廷尉之高职,在司法审判中不惟法律,只秉皇帝之意旨,“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注:《汉书·刑法志》、《汉书·杜周传》、《汉书·循吏传》、《汉书·食货志》、《汉书·杜延年传》)或有人质问批评之,他却理由十足地说:“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注:《汉书·刑法志》、《汉书·杜周传》、《汉书·循吏传》、《汉书·食货志》、《汉书·杜延年传》)杜周之论,可谓一针见血。例二,宋代以后,以敕破律,以例更律现象更是盛于前朝。王安石利用神宗之敕,而不依《刑统》之律判决“阿云之狱”(注:《宋史·许遵传》、《宋史·刑法志》)就是典型。例三,朱元璋偏爱《大诰》,重典治吏惩民,强调犯罪者如有《大诰》可减一等处刑,无《大诰》者则加重一等施
罚。只要知此数端,其中奥妙就可一目了然。
其次,立法与司法相矛盾。如前所述,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往往有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即立法的相对被动性和司法的相对主动性。众所周知,制定成文法典的程序是比较严格的,而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如历史上《北齐律》经16年而成,《明律》甚至“三十年始颁行天下”(注:《明史·刑法志》)就是证明。然而客观事实是,在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关系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异常活跃,由于缺乏规范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律,于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法律的“盲区”出现了。而作为国家或统治阶级从维护自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秩序”出发,必然不能容忍社会违法犯罪的肆意横行,势必频出措施,或援用旧有法律,甚至是已经被废的法律;或功利性地创设临时性法规,甚至是法外重法酷刑。如历史上奴隶制五刑在汉初文、景二帝时被废后,新的封建制五刑在隋唐始立的数百年中,历朝屡兴“肉刑兴废论”,其参与争论者不仅包括一般的司法者,而且集合了不少著名的政治法律思想家,乃至明君圣主。是不是诸如班固、杜预、韩愈等人的认识落后于文、景二帝而酷爱残肢害体之刑?恐怕不能简单做出如是之结论。其真正的、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为了有效地在“盲区”内“除恶塞源”、“止奸绝本”,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国家统治而不惜用旧法重刑。虽然在长达数百年的肉刑“兴废之争”中,奴隶五刑始终没有正式恢复,但是个别刑种的复现却又是历史事实。因此,由于上述几种矛盾的存在以及其矛盾运动的结果,决定了中国传统诉讼法律文件中宽严理论的不定式状态的客观、长期存在,也正是这种诉讼宽严理论的不定式恰好成了后人认识上一个难解的谜。
二、执法时宽时严
执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执法适中,宽严适度。这个“中”和“度”应是一种符合科学认识的法定,而不是一种随意的不定。然而事实是,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经济结构、伦理背景、专制传统,因此传统诉讼中往往宽严因时而异,也因人、因情而不同,于是历史上执法时宽时严的现象十分突出和非常流行,其理论实践的价值表征就是目不暇接的不可思议的宽大或严酷难定的司法审判。然而,诉讼实践,其宽也好,其严也罢,皆是宽严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一个个自圆无缺的环,而且环环相扣,接成了中国古代一条长长的宽严随时的诉讼之链,真乃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诉讼景观。
在中国古代第一次明确提出诉讼宽严理论的思想家,当为春秋时期的郑国子产。他的宽严理论是:“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注:《左传·昭公二十年》)作为当时新兴力量思想家,子产直面现实中执法宽严不同带来的后果,颇有感慨。故以形象的比喻而道出了其思想主张:诉讼宁严勿宽。对于子产的理论,如果我们将它置设于历史的逻辑发展的情境中,确乎费解。子产之前,商朝法律(立法与司法)严酷,这为公认的历史事实;西周宽仁,这也属不争的时代定论。而且,商严亡国,周宽强世,作为一条可贵的历史经验,一直为后继者所领悟和津津乐道。子产如是主张,似乎有乖常识。但是如果从子产的理论产生的背景中,更从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上洞察问题,那么就不足为怪了。众所周知,无论殷商、西周都实行奴隶制法——一种“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秘密法。它与新兴地主阶级的制订法,主张法“布之于众”的理论,要求显明刑罚的社会作用的思想大异其趣,而作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思想家子产,他敢于在历史上率先打破旧的传统,公布成文法,当然也会无畏地蔑视奴隶制法。特别在当时,西周之礼业已瓦解,新的法律体系尚处初创之时,社会在转型之中。过去那个被动、盲从的社会,已经出现思想的解放、束约的消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家们,为了自身阶级的利益,敢于直面社会、正视现实,运用新的法律治世,因此悟出一个重要的诉讼宽严理论。尽管子产理论颇显直观、浅薄性,但它毕竟具有“荜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真正给宽严理论以浓墨重彩,涂上辩证色调并对中国社会影响声宏响巨的思想家,当属稍后的孔子。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孔子之言:“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里,虽然孔子同意子产宽法难治的观点,但是最精彩的尚不在此,而在孔子认识到了严法的不可绝对强调,也许一味严刑带来的结果比宽法造成的影响更恶劣和消极,因此,主张严宽济用,才是理想的治世之道。对于此,或许我们可以放言:孔子思想,真乃善之善者也!
的确,孔子之后的数千年的诉讼历程,无论其诉讼实践和诉讼理论都有力地证实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确实使人反观到任何时期一味严刑,无不都是严刑者自食恶果的道理。嬴正的秦王朝如此,明朝的朱姓皇帝亦如是。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孔子具有生命力的诉讼理论,乃是一种建立在进步的“仁者爱人”民本思想基础上的理性认识,无疑,它在历史上闪耀过眩目的光亮。难怪几千年后的清朝雍正皇帝也深受其思想的影响,认为“但能利民,则宽严水火皆所以为仁,而劳怒非所恤。如不能利民,则刑名教化皆足以为病,而廉惠非所居。益谬拘臆见,薄务虚名,不以民事为事,不以民心为心,固未能奏效者。”(注:《皇朝纪世文编》卷十五)至此,中国古代宽严在理论层面上确立了一种“正态”的诉讼理论指导观。
但是,当我们打开汗牛充栋的史籍时,就不难发现宽严理论在“正态”实际运作时的“负态”标显。这样,理论和实践的二律背反就显得十分的耐人寻味。尽管它早已成为一个古老的、有趣的历史话题,但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值得我们破解其谜。因为宽严诉讼理论不仅于当时,抑或在今日,甚乃至明天都将是一个困惑人的难题。这样说来,昨天密码的破译,实乃具有今天法律文化建设中经验的获取,本土资源的利用价值。因此,总结数千年诉讼文化理论(宽严理论为其中一个重要理论)乃现代法制建设之必需。顺此思路,我们又不能不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寻找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
(一)宽严理论的惯性伸张
有如前述,中国古代社会宽严理论自春秋子产提出,孔子趋于完善,似乎完成了其理论发展的全过程,而且其理论发展呈现出连续性和层面性。连续性系指几千年间理论的不断升华,指导的日益见重。层面性系指由于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专制结构的基因制约,诉讼的宽严理论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即总体说来,随着君主专制体制的越来越强化,“法者,帝王之具”的认识愈来愈根深蒂固于统治者,宽严问题从理论层面上越来越主宽,而在实践层面上越来越从严(当然也有不少从宽的时期和实践)。宽严的二律背反规律,终于形成历史发展阶段上一个接一个的宽—严,严—宽;整体上宽—严—宽或严—宽—严相间的诉讼实践怪圈。这是总的趋势,如果能如是认识问题例可见怪不怪了,而且能梳理出一些实质性的东西。故此,我们有必要剖析之。西周时期“新思想兴、新制度兴”,诉讼“中罚”观的确立,开始形成诉讼法律文化发展中“明德慎罚”法律观,以宽为主导的诉讼实践也开始启动。正如周公所说:司法要“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显民。”(注:《尚书·康诰》)《尚书·无逸》也要求司法官“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同时,在西周诉讼中规定了区分故意、过失、惯犯和偶犯的司法审判原则。即所谓“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时乃不可杀。”(注:《尚书·康诰》)还规定诉讼中要慎察犯人供辞,防止发生冤狱错案,等等。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出现,实乃当时审判慎罚,诉讼主宽的表现。
然而,西周“美景”不长,旋即天下汹汹,礼崩乐坏。值此春秋战国之际,各种诉讼思想有如汹涌的波涛,诉讼宽严理论首次以多元形态凸现于世。如前所述的子产主张、孔子思想,还有法家理论、道家见解……,各显峥嵘。特别是孔子儒家宽严思想更具有影响力,它一方面继承了西周的诉讼理论,另一方面又直接启蒙了汉朝正统诉讼思想,而且,自此以后,其基本主张就成了封建诉讼的一个似乎万难逆改的理论指导。翻开历史,耳熟能详的现象是,无论司法官或思想家,甚乃封建皇帝,总是口念宽严之经:“务从宽恕”,(注:《后汉书·陈宠传》)谨戒“严刻”。汉代思想家不就开始高唱“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注:《汉书·刑法志》、《汉书·杜周传》、《汉书·循吏传》、《汉书·食货志》、《汉书·杜延年传》)的宽平曲吗?封建统治者为了体现这一思想主旨,甚至把汉兴以来的严法峻刑降至最低程度。如当时汉律有“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条,有似“秦之繁法如脂”,于是最高统治者命“三公、廷尉严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注:《后汉书·陈宠传》)至隋唐之世,隋文帝“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注:《旧唐书·刑法志》)唐代是公认的一个诉讼从宽的时期,特别在前、中期。据《旧唐书·刑法志》说:唐之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并强调“治狱当以平恕为本。”(注:《资治通鉴》卷193)即使在诉讼趋严的宋代以降,各朝也总是喋喋不休地伴唱诉讼从宽的理论歌,不敢轻易悖违传统的诉讼主张。甚至连好用折杖法、刺配刑和行廷杖的宋太祖也常说:“禁民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近朝立法,重于律文,非爱人之旨也。”(注:《宋史·许遵传》、《宋史·刑法志》)尚严重罚的明太祖朱元璋,也同样不忘“法贵简当”,且以宽平精神更定《大明律诰》5条。到明成祖朱棣时还敕令全国:“为治之道,在宽猛达中。……勿恣情纵欲,干犯国典常刑。必钦必敬,慎勿以身试法。”(注:转引自单远慕、刘益安:《中国廉政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清朝在明代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完备、定型的会审制度最能体现统治阶级的诉讼主张,如其中的秋审、朝审之制,从主观上看就是为了贯彻诉讼从宽的思想。正如雍正帝所言:“用刑之际,法虽一定,而心本宽仁。”(注:《大清会典事例》卷846。)因此,在一年一度的秋审、朝审判决时,
出现诸如停勾、减等、留养承祀做法,其目的在于存法外之仁,戒峻酷之刑,以昭慎重。故提倡“凡情可原者,务在缓减”,并以此标榜“宽严之用,备在得中。”(注:《大清会典事例》卷846。)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诉讼从宽理论似乎长期一以贯之。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在探讨问题时还不能不注意到另一面,即诉讼宽严理论的实践面的特点和个性。
(二)宽严实践的凹型标显
宽严诉讼理论,从实践的阶段性上看,大致可以认为,封建社会前期主要特点是诉讼从宽,后期逐渐从严(以唐中期为界限)。我们知道,宽严理论之所以首先提出于春秋子产,而不是西周著名思想家周公,这决非偶然,它是当时深刻的时代变革和思想转型的产物。众所周知,西周以“惟仁之亲”为认识前提,以明德慎罚为法制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促成了西周的一代之治,重礼尚德成为一种适合的治世理论和规范。虽然当时尚未及时提出诉讼宽严理论,但它已是一份后世不可不继承的优秀法律文化遗产,同时,也为春秋子产理论的提出准备了思想资料。自春秋礼崩乐坏,世乱频仍,以力相并局面形成后,怎样执法才能有力调整和指导复杂的诉讼关系,统治阶级在思索,政治思想家们在探讨,以什么作为诉讼理论指导问题就成了当时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而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制订、公布成文法的子产,当然是深思熟虑在前。因此,他曾对继任者说,诉讼宽严的理论指导要以严为主。进入战国之际,尽管有人主严(典型代表为法家),有人主宽(典型代表为儒家),二派争雄,各执一端,也难分高下。但自汉代儒家思想主导后,至隋唐盛世时,诉讼理论最终结束儒法两争,宽严执法,以宽为主,且逐渐成为一种法律文化和社会诉讼心理。据自汉至唐各代史籍记载的从宽执法的思想和实践基本成为一条主线,至于以宽执法的循吏良官、典型事例,可谓俯拾皆是。这里,我们仅举一个“中性”或许颇具异论的案例为证,可能会更有力地深化主题。据《幽闲鼓吹》卷2记载:唐代法官张延因办一起大案,组织缉捕罪犯。有一天公案上出现一张“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的条纸。第二天,又有一张“钱十万贯,乞不问此狱”的条纸。张延见后,果然不再过问此案。当人问他原因时,他说:钱十万贯,已可通神,我是怕因此得罪于神而遭祸报,故不敢再办此案了。张延停办此案,固然是官吏贪赃枉法的典型表现,但我们如果从法律文化和社会诉讼心理上对此做更深一步分析,那么或许更能了解古代法官办案从宽(即诉讼从宽)的文化内蕴和实质性因素。从本案分析所引发的一个问题,即古代浓厚存在的“福报”观念问题,它是了解诉讼从宽的一个不可不特别注意的因素之一。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受佛教文化影响,“不杀生及因果报应观念深入人心以后,执法官吏多斤斤于福孽之辨。以为杀人系造孽行为……为了怕诛及无辜,报应自身,往往以救生为阴德,不肯杀戮,一意从宽。”(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
局1981年版,第260页。)甚至“官吏遇有可以开脱之处无不曲为开脱。”(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0页。)对此,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代名幕和廉吏的汪辉祖,更是有其亲身体会,且说得更加淋漓尽致:“州县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昭昭然造福于民,即冥冥中受福于天;反是则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余自二十三岁入幕,至五十七岁谒选人,三十余年所见所亲牧令多矣。其于阳谴阴祸亲于其身,累及子嗣者,……天之报施捷于响应。是以窃禄数年,凛凛奉为殷鉴,每念及,辄为汗下。”(注:汪辉祖:《学治臆说·学治说赘》)因此,“今之法家感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人罪以福报。”(注:《朱文公政训》)原因之二是依情从宽。同时,也会因“情判”带来的种种结局而感到啼笑难止。“情”在中国古代确乎是一个不定的变数,可谓“风情”万种,当它一与“法”结合时,诉讼便显得千姿百态,宽也由“情”,严也由“情”,宽与严在“情”中犹似一块可以任人捏揉的小泥团,一时是人,一时又是鬼。关于这方面的实例的确太多,我们仅举一例说明之。据《汉书·薛宣传》记载:薛况之父薛宣因遭申咸“诋毁”,薛况为父报仇则教使杨明报复申咸,结果申咸被杀伤。按照汉律规定,杨明、薛况应处死刑,但因“情”却减等处刑。原因就是“子复父仇”是为“孝”,“孝”又是一种最大的“情”,而“原情定罪”又是诉讼中的一条铁则,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注:《盐铁论·刑德》)(这里所指之“志善”、“志恶”即“情”之善恶的代名词)。像薛况、杨明此类案件判决因“情”从宽的情形,在古代诉讼中可谓不胜枚举。故清代张船山总结说:因历朝“以仁孝治国,凡遇仁人孝子,无不曲法施恩”,(注:《清朝名吏判牍》)执法从宽。就此,雍正皇帝概括为:“凡情有可原者,务从缓减。”(注:《大清会典事例》卷846。)
当然,除此以外,也还有其它原因,决定了从汉至唐诉讼从宽的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
自宋开始,执法从严的主线逐渐显现。虽然正统儒学确立以后,儒家思想主导,但由于封建社会进入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君主个人独裁极端发展,阶级矛盾,社会关系更趋复杂和激化,作为“工具价值”的法律,更显示出其赤裸裸的镇压刑处功能。宋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口头上总是不停地哼着宽仁的曲子,但实际上高悬霸主的鞭子,屠杀的刀子。正如宋代思想家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天下大乱,民遭陷溺,亦与以权授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注:《孟子集注·离娄上》)朱熹这里所说的“权”是指“严”,“正道”是指“宽”。因此,他明确主张治国“以严为本”,(注:《朱子语类》卷108)甚至还上书皇帝“要深于用法”、“果于杀人”。(注:《朱文公文集·戍申延和奏札一》)由此宋朝凌迟刑的法定,明朝在《明律》外产生充满血腥味的《明大诰》,特别是明代“厂卫”涉讼,剥皮刑的确立,更是诉讼从严的火中浇油。至清朝军流刑的完善,文字狱的勃兴,更使封建社会诉讼从严达其极致,标显出封建社会后期执法的愈来愈严。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试举“断狱程限”为例,就足可为证。唐中期以前,法律没有法官破案、审狱的期限规定,相反,为了防止冤、错案件,特别在慎重死刑方面,为了不错诛无辜,宁可延长时日,实行“复奏”制度。实行“三复奏”还虑恐谨慎不够,又行“五复奏”制度。司法官深深感知到对于案件的侦查审结,特别对于大要案件的侦审颇费时日和精思,如果不适宜地要求司法官在规定期限内完案,最容易使用刑讯逼供,轻信口供,演成冤错,这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郑克在《拆狱龟鉴》卷2《王利》中说得很中肯:“治狱贵缓,戒在峻急,峻急则负冤者诬服;受捕者贵详,戒在苟简,苟简则犯法者幸免。惟缓于狱而详于捕者,既不失有罪,亦不及无辜,斯可贵矣。”到唐代宪宗时期开始有对司法官审断案件的期限规定:大理寺检断案件不超过20天,刑部复核不超过10天,由刑部发回大理寺重审为15天。后又对审案期限进行修正,区别大中小案件,分别规定在35天至20天。宋代初期仿行唐制,后数经变动后,规定大案为12日,中案为9日、小案为4日,而且规定诉讼标的价值20缗为大案,10缗以上为中案,10缗以下为小案。明代规定对于缉捕期限,以事发日开始1月内破案,越过期限者,捕役笞20,越过期限愈长受刑愈重。案件事实基本搞清后,司法官必须在3天内作出判决,判决后10天内执行。违限3日者笞20,每3日加1等,罪止杖60。如因拖延案件造成在押被告死亡者,*
被告为死罪,法官处杖刑60;为流罪者,法官处杖刑80;为徒罪者,法官处杖刑100;为笞、杖罪者,法官处徒刑1年。清朝审案期限更为严格,规定州县案件(笞、杖刑案件)20日内结案,人命案件,州县在3月内初审完结,将被告和卷宗解府,府限1月内解省按察使司,按察使司1月内解督抚,督抚1月内奏报皇帝,并将案卷移送刑部。另对强盗案件、抢劫案件、徒罪案件、凌迟案件都有严格的层层上解审案规定。(注:参见郭建:《古代法官面面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1页。)
应该说,法律规定断狱程限是必要的、可取的,它对防止狱讼淹滞等司法弊端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规定得不科学、脱离实际的徒具形式的“严立程限”,恰如真理向前一步就成谬误一样,不仅不能体现其积极作用,反而会遗害种种。对此,请注意宋理宗时任监察御史的程元凤的批评:“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唯恐其速。奏案申牍既下刑部,迟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详,又复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动涉岁月。省房又未遽为呈拟,亦有呈拟,亦有呈拟而疏驳者,疏驳岁月又复如前。展转迟回,有一二年未报下者,可疑可矜,法当奏谳,矜而全之,乃反迟回。有矜贷之报下,而其人已毙于狱者;有犯者获贷,而干连病死不一者,岂不重可念哉!”(注:《宋史·许遵传》、《宋史·刑法志》)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唐以前也有诉讼从严的实践(秦朝最为典型,这里以汉为始点,但即使在汉唐间,也有尚严时期),宋以后也不乏诉讼从宽的表现和实际运作。我们所指的宽与严只能相对而言,断不可绝对化。如是认识问题就清楚了从秦经汉唐至明清诉讼宽严理论发展和实践的严—宽—严的凹型图式结构。第二,出现宽严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对于其中重要原因之一的“因情”宽而严的问题,无论前期或后期都是一个既可让司法官上下其手,又可使其身处两难境地的较普遍性问题。如清朝蓝鼎元曾审理一宗广东潮阳县武装“抗税案”就很能说明问题。此案判决如果从严,山门城赵姓一族约千人“罪当死”,当然会害及“案内无辜之人”。如果从宽,又怕有玩法轻纵之嫌。结果只好熟练地操起情判法:“你们罪名可大啦!现在为自己扬名,对你们残暴行刑,我不忍心;但叫我把法律放在一边,对你们宽赦,我也不能这样做。如今姑且暂时把你们羁押监狱,待你们收积欠粮米补交完毕,不再行审理,好吗?”这样,蓝鼎元果然因情“从宽审拟,枷号一二人,余皆薄责”。(注:蓝鼎元:《鹿洲公案·山门城》记载:蓝氏与赵佳璧为首抗税人对话,“余曰:‘噫,汝等既来,吾亦不忍杖杀也。升平世界,焉有颠倒谬戾之人如汝等所为哉!吾恨不早缚汝曹,尽尸诸市。所以姑容至今,虑汝有冤情耳!今日有冤,宜即申说,并所以抗拒之故,一一为我言之’。赵佳璧等皆叩首曰:‘我等实无冤情,亦不敢抗拒,止乡愚无知,积习固然。其初视若儿戏,其后畏罪日深,莫敢向迩,是以迁延自误,至于此极。今已知罪当死,但悔不可追,望垂宽恩,留一生路。’余曰:‘汝等罪名大矣!酷虐吹求,我不忍;宽者废法,我亦不能。今姑暂置之狱,俟将积逋粮米补纳全完,方行审拟,可乎?”)此案明确地表明,当司法官在传统的因情而判的法律文化影响下,难免走入宽严的两难境地,但一旦从宽判决后,又是感到何等的自慰。正如蓝氏判决此案后感慨的那样:“执法严而用法宽,想见仁人君子之像。”(注:蓝鼎元:《鹿洲公案·山门城》)
因此,在回眸中国古代数千年悠久诉讼法律文化时,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犹如一座偶尔露峥嵘的高山险峰,有时在风和日丽下,亮现出一道道诱人的灵光,有时在雨蒙雾罩下,又徘徊着一个个吃人的魔影,真乃难识庐山真面目。
三、宽严相济辨
实际上,中国古代诉讼严也好,宽也罢,都不是依法断狱,它与科学的诉讼观是相背离的。因为古代任何的宽与严往往都只会给诉讼带来无尽的消极影响和灾祸。如上所述的唐以前的从宽带来不少诉讼实践中“淹滞狱讼”的弊端,而宋以后的从严,又是诉讼中大量“兴盛刑讯,顿生冤案”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历史上众多政治法律思想家总是不断地在理论上主张既戒宽缓又避峻严。因为“宽”则多纵罪,是为不可取;“严”则伤民又危国,亦为不足训。正如唐代陆贽所言:如果“禁防滋章,条目纤碎,吏不堪命,人无聊生,农桑废于征求,膏血竭于笞箠,市井愁苦,家室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宁矣。”(注:《陆宣公翰苑集·论述适幸之由状》、《奉天论赦书事条状》)如果说这是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安宁的伤民表现,那么更为严重者则是危及封建君主和国家,即所谓“刑谪太峻,禁防伤严,上下不亲,情志多壅,乃至变生都辇,盗据宫闱。”(注:《陆宣公翰苑集·论述适幸之由状》、《奉天论赦书事条状》)但是在诉讼实践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要真正做到又何其难也。于是更多的思想家则主张诉讼宽严结合,交替使用,相辅而行,这就成了一个封建诉讼的经典理论。自孔子总结出“宽猛相济”理论后,历代政治法律思想家都对此津津乐道,视为传统诉讼理论上的圣言铁则,努力将它贯彻到法律实践中,且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首肯,少有真正的批评反对者。
关于孔子总结的诉讼宽严理论主张,虽不正式见于《论语》,但载于其它文献者有两处。一是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二是见载于《礼记·杂记》:“子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确,孔子诉讼宽严(即其宽猛或文武之道)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唐朝思想家吕温谈及执法宽严时,仍不厌其烦地重复孔子的思想,主张宽严并用:“宽则人慢,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施之以宽”,因此要“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注:《唐人三集·吕衡州集》卷10)可谓完全继用,少有异议和新诠者。
直至明末清初之际,大概只有王夫之才对这个理论转换视角,重新审视,并赋予它全新理论意义。王夫之认为孔子的“猛”不是“严”,而是一种执法走极端,而且认为“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不是宽严相结合,而是两个极端手段的交替使用,其结果不会带来“政是以和”,而只会出现“行之不利而伤物者多矣”的可怕局面。并且进一步说:“夫严犹可也,未闻猛之可以无伤者。”(注:《读通鉴论》卷8、卷28)“猛则国竞而祸急……其以戕贼天下无穷矣!”(注:《读通鉴论》卷8、卷28)王夫之则认为:“严者,治吏之经也。”执法“严”,即指严惩贪吏:“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簿尉胥隶,皆喙息而不敢逞。”(注:《读通鉴论》卷8、卷28)在这里不难看出,王夫之对“严”的界定是严格的,也是全新的。一是过严不为“严”,“严民”不为“严”。王夫之的宽严主张实际上是“宽以养民”,“严以治吏”,不走极端。二是宽严关系应该体现“宽以养民”和“严以治吏”的价值目标实现上,并且认为“宽以养民”以“严以治吏”为保证措施,只有这样的“二者并行”,不“以时为进退”、“无择于时”而行,才能真正达到政是以和。可以说,王夫之是站在朴素的民主思想的立场上,从批判性地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高度上宏发此论的,它不失为传统的宽严理论注入了活力和带来了生机。但是,尽管如此,他的宽严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在这里恕不赘述。
理论指导实践,特别是当一种被社会接受,并且具有影响的理论形成后,它便使社会的实践者自觉不自觉地信条般遵循着,传统的宽严诉讼主张便为如此。因此,它无可避免地演绎出一幅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宽严理论实践的历史长卷,其实践的价值既表征着积极的意义也凸显出消极的影响。
三国时期魏国贾逵为豫州刺史时,由于“天下初复,州郡多不摄。……长吏慢法,盗贼公行”,天下真乃一片混乱。他到官数月中,“考竞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注:《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贾逵以严治郡,而不以宽主政,成绩斐然。故此曾得到魏文帝的高度称赞:贾逵“真刺史也”。并且“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注:《三国志·魏书·贾逵传》)同时,他又能“惠施于百姓”,颇得百姓之誉。对此《三国志》作者评曰:贾逵“精达事机,威恩兼著,故能肃齐万里。”(注:《三国志·魏书·贾逵传》)可见,执法宽严相济确不失其有效性和事功性。
自然,针对具体情况,不同世态,执法严有严的收获,宽有宽的得益,宽严相济更不失其整肃、治世之功。同时也都不漏其百出的弊端。众所熟知的秦朝尚“严刑峻法”、“督责益严”,不仅没有带来秦朝的国祚长享、社会安定,相反,在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下很快出现“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可怕局面。(注:《汉书·刑法志》、《汉书·杜周传》、《汉书·循吏传》、《汉书·食货志》、《汉书·杜延年传》)不几多时,赫赫事功、强大统一的王朝迅速走向暴亡败国的绝路。这显属以严执法败国之典型一例。相反,汉初反思秦亡之教训,刻意宽缓,先无为而治,但是在“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之际,“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因此,诸侯坐大,吴楚七国作乱,内患屡兴;匈奴频侵,高祖困厄平城,外祸顿起。终于造成社会“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奉,百姓抚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注:《汉书·刑法志》、《汉书·杜周传》、《汉书·循吏传》、《汉书·食货志》、《汉书·杜延年传》)的混乱局面,带来王朝亟亟可危的可怕情境。这又是诉讼从宽的一个绝好的注脚。(可惜往昔之观点,往往只看到反秦政后的“安定”和“繁荣”,却忽视了这一点。)况且,每当一严或一宽后,势必出现严后的畸宽或宽后的畸严,并且它已成为带规律性的东西。如秦朝严刑酷法(畸严)后即出现无为而治(畸宽);无为而治(畸宽)后紧接着的是汉武帝时的“有为而治”(畸严)。据史籍记载。武帝承汉初之弊,不得不推行高度的政治统一、思想统一和法制统一;信奉近于法家思想的“公羊”儒学,颁行严令,推行峻法,重用酷吏。这种“畸严”局面,直至昭帝时期还仍然保持“武帝时形成的严刑峻罚的风气。”(注:高恒:《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所谓社会无不“颇言狱深,吏为峻诋。”(注:《汉书·刑法志》、《汉书·杜周传》、《汉书·循吏传》、《汉书·食货志》、《汉书·杜延年传》)正如《汉书·黄霸传》所载:“昭帝立,……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那么宽、严执法,究竟孰是孰非?思想家们在注目观之,潜心研之,因此,在汉昭帝时终于爆发了一次著称于史的“盐铁会议”之争。实质上它是一场关于宽严治国的手段和法宜宽平还是法宜严酷的理论之辩。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主严派,从汉初“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的认识出发,认为治国理民要靠立严法、施严刑。即他们主张的法律不能不严密,执法不可不严厉,因为*
“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从督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注:《盐铁论·刑德》)他们针对贤良文学派主张的立法简、执法宽,犹如康庄大道之说,用心良苦地以汉初疏于立法,宽于执法带来的“弛道不少也,而民公犯之”的事实加以驳斥,果断地主张“立法制辟,若临百仞之壑,握火蹈刀,则民畏忌,而无敢犯禁矣。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今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败子,则惑矣。”(注:《盐铁论·刑德》)相反,贤良文学派则主张约法省刑,因为法律制订多,反而“民不知所辟”,不仅是人民,连官吏也“不能遍睹”,其结果官吏断案,不是“疑惑”,就是“或浅或深”。这样,不仅不能严法治国理民,反而是“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注:《盐铁论·刑德》)因此,他们同样也是颇有心计地以秦朝立法“繁如秋荼”,执法“密于凝脂”而迅速亡国的历史教训说明之;以汉初高祖“约秦苛法”而“泽流后世”的事实佐证之。可见,汉之盐铁会议之争,两派都围绕着诉讼宽严理论的辩难,各执一端,针锋相对,不失为传统理论的一次冲突和深化。但是,可惜的是,汉之“盐铁会议”之争,并未从诉讼理论上解决宽严问题,反之,历史的传统在反复地演绎着。
如上所述,执法从宽,其后则必趋严;执法从严,其后又必是宽。总之,宽、严执法都为极端执法,即使是宽严相济,也是两个极端手段的结合连用,其严重后果,势必引起众多政治思想家们更深层次上的认识。如《唐律疏议·进律疏》在总结以往历代王朝执法经验的基础上,深刻领悟到“轻重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的道理。确乎,斯言美哉!宽严求平才是不少思想家和有为统治者真正追求实现的境界,尽管它是历代统治者难以真正做到的历史事实。在这点上,可以说直到清朝,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多少个严而宽,宽而严,宽严相济的圆圈运动后,也在目睹耳闻了多少由此带来悲剧和喜剧后,清朝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才比较冷静地悟出一个值得肯定的道理。认为儒家的“恤刑”、“慎罚”并不是一味讲宽;自宋以来的繁法重刑也不是盲目地主严,而是历朝都不忽视宽严适“平”。即所谓“从来帝王用刑之际,法虽一定,而心本宽仁。”(注:《大清会典事例》卷846。)以宽仁之心行严格之法,以严峻之举体宽仁之心,无论宽严,“失出失入”皆失平。同时也强调“失出失入皆如律”,这样,它既能防止司法官的过严残民,又能杜绝司法官的过宽纵罪,诉讼达到“渐为平允”的目的。我们知道,清承明制,与以往唐宋执法比较,严其所严,宽其所宽。即使在其“严”刑之中的死刑监候案件,经秋审和朝审后,一方面有“情实”的判决(关押一年后仍执行死刑),也有“缓决”、“可矜”和“留养承祀”的宽处。无论严至死刑,轻至宽宥,都必须经皇帝、大臣们集议会审,目的在于尽量做到执法持平,尽量不失宽严,尽管事实上难以做到而流于形式,但理论上仍不失其积极意义。正如《大清会典事例》卷846记载的几朝皇帝所说的那样。雍正帝认为:“凡情有可原者,务从宽减,而意非主宽;凡法无可贷者,便依斩绞,而意非主严。”乾隆帝也津津乐道:“应酌情准法,务协乎天理之至公,方能无枉无纵,各得其平,……朕毫不存从宽从严之成见。”又说:“朕临御万机,乾纲独断,宽严之用,务在得中。”连嘉庆帝也强调司法审判“不得预存从宽、从严之见,用昭平允。”
应该说,历史上几千年之久的宽严诉讼理论,至此终于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思想。虽然这种认识,其来也晚,其行也难,但是总结历史经验,无疑对后世乃至今天仍有其理论和实践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