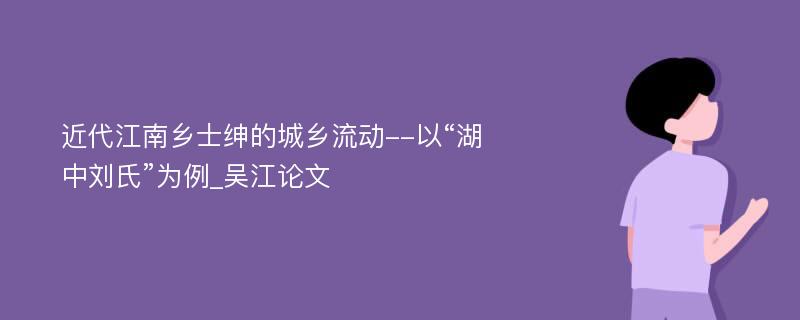
近世江南乡居士绅的城乡流动——以分湖柳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居论文,士绅论文,近世论文,江南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1—0107—09
近世江南乡居士绅向城镇的迁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费孝通称其为“社会浸蚀”现象。伴随着士绅如水土流失一般迁出农村的“社会浸蚀”现象而至的,是近世乡村社会中固有的精英阶层出现资源枯竭,基层组织核心力量难以为继,城乡关系脱节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相继有学者对士绅群体的城镇化现象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了包括近世士绅群体涌入城市对城市与乡村发展的不同影响,乡居、镇居、城居士绅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的差异,士绅居所的变动与士绅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诸多问题。①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其关注的大多为士绅群体迁居城镇对自身及社会的影响,而对士绅群体的城镇化流动本身的进程涉及不多,偶有论及,也多归因为近世社会剧变而产生的冲击所致。②那么,在近世社会变迁的外因刺激之外,士绅的城镇化流动是否还存在着其自身发展的内驱力?影响或制约其城乡流动的要素是什么?其迁移活动是否有迹可寻?士绅与非士绅的城乡流动有什么差别?士绅向城镇的流动是否等于“社会浸蚀”?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士绅的家族发展历史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从中探求可能的答案。本文将以吴江分湖柳氏为研究对象,从这一百年大族的发展轨迹中重现其城镇化之路。以期对有关士绅居地流动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 分湖柳氏及其迁移
分湖柳氏的居住地北厍位于吴江的东南部,镇区距吴江城区50里。吴江始建于后梁开平三年(909),乾隆《吴江县志》载:“梁开平三年,从吴越王钱镠请,割吴县南地置吴江县,县之置自此始。”③雍正四年(1726),“分吴江西偏地置震泽县,其东偏地仍为吴江县”,吴江县境“广八十一里,袤一百里,周三百六十里。自治东至松江府青浦县庄(一作章)练塘界八十里,西至西城内河震泽县界一百五十步,南至嘉兴府秀水县王江泾界七十七里,北至元和县七里桥七里,东南至汾湖中嘉兴府嘉善县界五十四里,西南至烂溪钱马头北首斜港秀水县界八十里,东北至元和县姚城江界三十里,西北至吴县灵岩乡界三十里。”④1912年,震泽县仍并入吴江县,此时县境东西长90里,南北宽80里,东为青浦县,东南为浙江嘉善县,南为浙江秀水县,西南为浙江乌程县,西为太湖,北为吴县。县治松陵镇位于吴江县北部,北距苏州16公里。
吴江是在太湖东南沼泽地上发展起来的,县境之内交通并不便捷,相互阻隔的交通导致了吴江县内各聚居地自成体系的发展局面,形成了吴江的七大镇,北有松陵、同里,南有盛泽,东有芦墟、黎里,西有震泽,平望居中的格局。七大镇中,县治松陵始建于唐,是全县的政治中心,同里、震泽兴于宋,平望、黎里成于明,芦墟、盛泽建于清。盛泽是吴江的第一大镇,以丝织业著称于世,平望是交通枢纽,同里、黎里、芦墟、震泽都是区域性经济重镇,其中同里、黎里在吴江还以文化发达著称。在七大镇的周围,各自有次级市镇呈众星捧月之势。分湖柳氏的聚居地北厍东靠芦墟、南与浙江嘉善隔湖相望、西南接黎里、西依八柝、北联金家坝。境内有分湖,亦名汾湖,距县治东南60里,为吴、越两国的分界线,故名。相传分湖曾是吴、越两国的重要战场,吴越战争时伍子胥曾在此领兵袭击越军,分湖边还留下了子胥滩等古迹,明人王庭润诗云:“斜日胥滩吊子胥,英灵千古岂真无;云开山口如吞越,潮怒江心似恨吴;甲冷鱼鳞埋雪苇,带销龙气堕烟芜;三忠祠近须停棹,拟把椒浆奠一壶。”⑤由于此地为吴、越两国的分界之处,因此在历史上有“吴根越角”之称。分湖柳氏之名亦取之此湖。处于太湖东下咽喉走廊地段的北厍,境内地势低平,河道纵横,湖荡密布,共有大小湖荡46个,最大的荡名“东长荡”,面积1572亩。全境有圩127只,最大为汾湖村的大富圩,面积1430亩。⑥北厍镇区三面临水,分别是三白荡、李公漾、元鹤荡,进出极为不便。因此,北厍虽地处苏州、嘉兴、上海三地的中心地带,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仍然属于偏僻地区。⑦由于地形特殊,北厍成为躲避战祸的好去处,当地有较高名望的张氏、柳氏、梅氏等家族都是在王朝更易的战乱年代迁居北厍的。
分湖柳氏迁入吴江是在明朝末年,为躲避战乱,始迁祖春江公偕弟慕江、云江从浙江宁波府慈溪县祝家渡移居到吴江东村(今北厍南东村)。经过了所谓的“潜德不传”的前四世后,到五世祖君彩公柳仲华的时候,柳家已经度过了迁移之初白手起家的艰辛,从“或遇凶岁力为周恤”⑧这样的溢美之词可以想见柳家已经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柳仲华共生有五子二女,这五个儿子后来分门立户,形成了分湖柳氏的五大房派,从明末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近二百年的时间内,分湖柳氏繁衍十一世,“子姓之可按图计者及吾目中有一百十有九人”,⑨40年以后的光绪七年(1881),分湖柳氏繁衍至十三世,“现丁之可会者自一百十有九衍至百五十余人”,⑩据民国《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的记载,分湖柳氏自明末迁居吴江至1923年共有男子421人,其中士绅88人,在经历了数代人近百年的奋斗后,分湖柳氏最终发展成为当地的望族。
表一 分湖柳氏各房支人数统计表
支系世系 端人公支端士公支端书公支端明公支
师孟公支
六世1
1
1
1
1
七世2
2
2
2
2
八世2
6
7
5
9
九世6
8
15 4
11
十世15 11 31 9
25
十一世
26 8
26 8
23
十二世
33 3
36 6
19
十三世
22 0
0
3
11
十四世
12 0
0
1
0
总计
119 39 118 39 101
资料来源:《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民国十二年镌,胜溪草堂藏版。五房支合计记载男子416人,另前五世共记载5人,总计记载男子421人。
分湖柳氏中的88名士绅在各支系中的分布并不均衡。师孟公支人数最多,计39人,占人口总数的38.6%;端人公支计33人,占人口总数的27.7%;端书公支计14人,总人口总数的11.9%;而端士公、端明公支最少,均只有1人,占人口总数的2.7%。根据各支士绅数量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分湖柳氏各支分为士绅化支系、半士绅化支系、非士绅化支系三类:端人公支、师孟公支为士绅化支系,端书公支为半士绅化支系,端士公支、端明公支为非士绅化支系。之所以这样区分,是为了更好地剖析分湖柳氏的迁移活动,探究其地域流动的特点,展示不同种类的支系在迁移中的表现。
从谱牒记载可以看到,分湖柳氏自始迁祖春江公迁居吴江东村后,前后出现的人口迁移共有28人,迁移32次,其中5人曾两次迁移。迁移人口数占总人口的6.7%,迁移频率为10.7%。换而言之,平均15人中有一人外迁,平均9.4年出现一次人口迁移。
表二 分湖柳氏人口迁移世代表
世系 人数 迁居地数
三世1 1
六世1 1
七世1 1
八世1 1
九世2 3
十世1 2
十一世 1215
十二世
6 6
十三世
3 3
资料来源:《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民国十二年镌,胜溪草堂藏版。
从表二可以看到,分湖柳氏在入居吴江的前十世迁移频率较低,六世分房后的数世中都只有零星的迁移,从十一世开始,外迁的数量迅速上升。而从表一中可以发现,分湖柳氏在十世时出现了人口的骤增,可见人口数量的变化对外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如果说人口的增加诱发了外迁,那么哪些人更可能实施外迁、影响外迁地选择的因素有哪些,只有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才能对士绅阶层的地域流动有更客观的认识。
分湖柳氏各支系在外迁上的比例并不均衡。如表三所示,除分房前三世的外迁,六世分房后外迁的27人中,师孟公支12人约占44.5%,端人公支7人占25.9%,端士公支6人占22.2%,端书公支2人,占7.4%,端明公支无人外迁。其中,士绅化支系的端人公支和师孟公支占外迁人口的70.4%,可见士绅化支系在人口迁移上较其他支系更为活跃,具有更高的迁移性。
表三 分湖柳氏迁移人口支系分布表
世系
支系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合计
端人公支 0 01/10 00 3/3 3/3 7/7
端士公支 0 0 02/3
1/2 2/21/1
0
6/8
端书公支 0 0 0 0 0
2/2 00
2/2
端明公支 0 0 0 0 00 000
师孟公支 1/1
1/10 0 0
8/11
2/2
0 12/15
资料来源:《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民国十二年镌,胜溪草堂藏版。
说明:斜杠前数字为迁移人数,斜杠后数字为迁移次数。
就个体而言,27人中士绅有9位,占迁移总数的33.3%,占士绅人口总数的10.2%,非士绅18人,占迁移总数的66.7%,占非士绅人口总数的5.5%。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相对于非士绅而言,士绅具有更高的迁移性。从表四还可以看到,士绅的迁移在世系中的分布较广,这表明近世士绅的大量迁移固然有受到近代社会突变的影响,但也有其传统性的因素,换言之,士绅在传统社会中原来就是人口迁移中的活跃人群。而传统社会中的士绅之所以具有相对其他人群更强的迁移性,是与其所具有的相对较高的社会身份密切相关的,而这种社会身份使得士绅拥有更广阔的社会交往空间,进而使得士绅获得更多的地域流动的机会和选择。
表四 分湖柳氏迁移人口身份表
身份
世系
人数 士绅 非士绅
六世1 1 0
七世1 1 0
八世1 1 0
九世2 0 2
十世1 0 1
十一世 12 4 8
十二世
6 2 4
十三世
3 0 3
资料来源:《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民国十二年镌,胜溪草堂藏版。
从迁移者对迁居地的选择来看,27名迁居者中,以城镇为迁居地的有20人,占总迁居数的74.1%,这表明在地域流动中,从乡村向城镇的流动占据了主要的部分。从比例上看,士绅为66.7%,非士绅为77.8%。可见近世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迁移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无论是士绅还是非士绅,事实上在迁移活动中,实施迁移的非士绅迁移者甚至比士绅迁移者更倾向于选择城镇,比例上要高出11.1%。虽然士绅的迁移性较强,但非士绅更高的城镇移居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迁移性较弱的影响,士绅的迁移率为10.2%,比非士绅的5.5%高出约85%,而迁居城镇的士绅占士绅总数的6.8%,迁居城镇的非士绅则占非士绅总数的4.2%,仅高约62%。换而言之,士绅对于城镇的迁移取向被人为放大,这也许是因为迁移城镇的士绅在社会活动中更为活跃,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 地域流动与婚姻圈
想要探究士绅地域流动的情况,婚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因为对家族婚姻圈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家族人口在地域间的流动情况,进而了解其城乡流动的特点。在六世分房后外迁的27人中,1人无婚姻资料,其余26人婚姻30次,其中2人继配1次,1人继配2次。下面我们就利用这些婚姻资料来考察这些外迁者地域流动的情况,探究其迁移行为与婚姻之间的互动关系。
表五 迁移人员婚姻简况表
总数女方身份女方居地迁居地 契合度
士绅 非士绅城镇乡村城镇乡村同地异地
士绅 9/98 1
6
3
6
3
2
7
非士绅17/21 10 11 14
7
14 3
8
9
资料来源:《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民国十二年镌,胜溪草堂藏版。
说明:斜杠前数字为迁移人数,斜杠后数字为婚姻次数。端书公支十一世外迁者1人无婚姻资料,未列入统计。
从表五我们可以发现,迁移者对于迁居地的选择与人群身份并无必然关系,而与其婚姻对象的居住地却有一定的关联。就个体婚姻对象看,9名迁居士绅中,婚姻对象6人居于城镇,3人居于乡村,而其迁居地的城乡选择完全与婚姻对象状况相一致,亦是6人迁居地为城镇,3人迁居地为乡村;非士绅的情况也基本上与婚姻对象的居住地情况相吻合,在非士绅17人21次婚姻中,婚姻对象14人次居于城镇,7人次居于乡村,而迁移者中有14人次选择了城镇为迁移目标地。可见迁居者对迁居地的选择与婚姻对象的居住地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迁居地与婚姻对象居住地的契合性上看,26人中有10人的迁移地与婚姻对象的居住地有着最直接的关联,即其迁居地为女方居住地,占迁居者总数的38.5%。如此高的比例表明婚姻是诱发迁居行为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而在迁居地契合的10人中,迁居城镇的有9人,仅1人迁居乡村,也就是说,在迁居城镇20人中有45%是迁居到婚姻对象居住地,而迁居乡村者此项比例仅为16.7%,这表明在因婚姻关系而直接引发的迁居活动中,城乡间的迁移是其主要类型,同时也可见婚姻关系在乡村迁居城镇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迁居城镇人员居住地选择的契合性上,士绅为33.3%,非士绅为57.1%,这表明在城镇迁居地的选择上,一方面婚姻关系是乡居士绅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相较于非士绅,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士绅具有更多的选择空间,拥有更大的迁移半径,而非士绅则因缺乏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对因婚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具有更大的依赖性。换而言之,乡居士绅比非士绅拥有更多的城镇化路径。
表六 分湖柳氏迁居地支系分布表
迁居地支系 人数 城镇 乡村
端人公支7 6 1
端士公支6 3 3
端书公支2 2 0
端明公支0 0 0
师孟公支
1210 2
资料来源:《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民国十二年镌,胜溪草堂藏版。
从家族婚姻圈层面看,表六显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从个体身份上看,不同人群的迁居取向基本相同,但是从不同支系来看,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其中士绅支的端人公支和师孟公支外迁的19人中,迁居城镇的有16人,占84.2%,半士绅的端书公支外迁2人,(11)皆迁居城镇,非士绅支的端士公支外迁6人,迁居城镇者3人,占50%,士绅支系入居城镇的比例明显超过非士绅支系。这说明影响迁居地选择的因素除了个体因素外,还有家族因素的存在,具体到婚姻关系,就是除了个体的婚姻因素外,还有家族婚姻圈所形成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士绅由于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复杂的社会身份而拥有更广泛的社会交流,拥有更宽广的地域交往空间,表现在婚姻上,士绅家族婚姻圈的地域范围较普通家族显得更广,从而使其家族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挣脱原居住地的束缚,实现更大范围的地域流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分湖柳氏士绅支与非士绅支的婚姻圈对比中得到印证。
表七 部分支系婚姻圈比较表
人口数 女方居住地居住地
迁移数
城镇乡村不详城镇乡村 城镇乡村
师孟公大胜支31/49 34 11 4
11 20 9/12 2/2
端士公支 29/39 13 22 48 21 3/3 4/5
资料来源:《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民国十二年镌,胜溪草堂藏版。
说明:师孟公支分大胜支和大港支两个分支。人口数斜杠前数字为有婚姻记录人数,斜杠后数字为婚姻次数。迁居次数斜杠前数字为迁移人数,斜杠后数字为迁移次数。
表七是分湖柳氏士绅支中的大胜支与非士绅支中的端士公支的婚姻圈概况比较。大胜支31人婚配49次,女方居城镇者34人,占69.4%,居乡村者11人,占22.4%,不明者4人,占8.2%。女方居吴江县境外12人,占24.5%,其中11人居于城镇。女方来自士绅家庭者41人,占83.7%。端士公支29人婚配39次,女方居城镇者13人,占33.3%,居乡村者22人,占56.4%,不明者4人,占10.3%。女方居吴江县境外者1人,占2.6%,来自士绅家庭者2人,占5.1%。比较这二组数据可以发现,在传统婚姻门当户对的原则之下,士绅支系的家族成员由于婚姻对象大多来自士绅家庭,因此必须在更大的地域空间中寻求婚姻对象,近1/4的婚姻属跨县婚姻、近七成的婚姻对象来自城镇都说明了这点。相比之下,端士公支则有超过半数的婚姻对象来自周边乡村,婚姻对象居城镇者比例不足大胜支一半,跨县境婚姻比例更是只有大胜支的1/10,而且13次与女方居城镇者的婚姻中有5次来源于家族中的城镇居民,惟一的跨县境婚姻亦然。这充分说明乡居的非士绅支家族的婚姻圈在空间范围上要远小于士绅家族,考虑到非士绅的城乡流动更多地依赖于婚姻关系这一纽带,因此相对狭小的婚姻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由乡村向城镇流动的速度。而士绅家族地域范围较广的婚姻圈则为士绅家族成员实施乡村向城镇的迁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换而言之,在以婚姻关系为介质的乡城迁居中,非士绅家族基本上只用依靠个人的婚姻资源,而士绅家族成员除个人婚姻资源外,还可以借助家族婚姻圈的资源优势实现乡城间的迁移活动。
从不同支系的迁移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婚姻圈的差异的对他们各自的迁移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士绅支的大胜支迁移11人14次,其中9人迁居城镇12次,人数占81.8%,迁移数占85.7%,2人迁居乡村2次,人数占18.2%迁移数占14.3%;迁居城镇的9人中,8人属从乡村迁居城镇,占88.9%,1人为城镇迁居城镇,占11.1%。非士绅支的端士公支迁移6人8次,其中,3人迁居城镇,人数占50%,迁移数占37.5%,迁居乡村4人5次,(12)人数占66.7%,次数占62.5%;迁居城镇的3人中,1人从乡村迁居城镇,占33.3%,2人为城镇迁居城镇,占66.7%。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迁移人数还是迁移次数,士绅支都远高于非士绅支,而差距更大的则是迁移的内容,从乡村迁居城镇这一组数据的巨大反差表明非士绅支在摆脱乡土束缚的能力上远逊于士绅支,在家族总人口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其初迁城镇的比例仅为1:8。虽然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原本社会交往资源就相对贫乏的非士绅家族在婚姻圈中亦无法获得足够的有助于其进行地域流动的资源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而地域流动的缺失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士绅家族的社会流动,使其社会地位难以得到有效改善,因此周而复始构成恶性循环。而社会交往资源原本就较为丰富的士绅家族在婚姻圈中得到了更多的有助于地域流动的资源,加强了其在地域流动中的能力,尤其是由乡村向城镇的地域流动能力,这种向区域中心地的地域流动又推动了其社会流动的能力,提高了士绅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的提高又进一步增强了地域流动的能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大胜支的发展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分湖柳氏中的柳以蕃晚清咸同间以文学驰名乡里,与同邑中“不可一世”的人物如凌莘庐、凌退修、费吉甫、费芸舫、吴望云、李辛垞等人齐名,大胜支中的柳树芳则与桐城派姚鼐的弟子吴江郭麐、娄县姚椿等人关系密切,获益良多,大胜支最终与莘塔凌氏、雪巷沈氏并称为分湖三大世家。值得注意的是,大胜支与这些地方望族的婚姻关系非常密切,据柳亚子先生回忆,他的曾祖母邱太夫人来自黎里望族邱氏,祖母凌太夫人来自莘塔望族凌氏,是吴江名士凌退修的姐姐,母亲来自吴江的簪缨旧族费氏,是名士费吉甫的女儿,其叔父的原配是凌退修的侄女、继配则来自雪巷沈氏。(13)大胜支仅娶莘塔凌氏就有5人,此外地方望族如黎里汝氏、黎里蒯氏等亦屡屡成为大胜支的婚姻对象。这些与地方望族的婚姻无疑提升了大胜柳氏在当地的社会声望,也为其地域流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此可见无论是士绅的个体婚姻关系还是家族婚姻圈,都对士绅实现城乡流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 迁居地的选择与社会交往
士绅家族的婚姻圈为其家族成员的地域流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表五的数据我们也可以发现,士绅的迁居地与婚姻对象居住地的契合率在各人群中是最低的,那么士绅对迁移地的选择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呢?
迁居地选择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对个体还是家族而言,迁移的目的是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为“有了地域的流动就会有新的接触,受到新的刺激,从而为社会关系、职业、收入、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地位的改变铺平了道路。一个人要靠接触别人的经验来扩充和发展自己。当他走进一个新世界的时候,他会遇到他所羡慕和尊敬的人,这些人有的可能成为他的朋友,有的可能是他社会晋升的典范。他得到新的目标,新的价值观念和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14)对于士绅而言,地域流动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实现新的社会流动,而这种社会流动的取得有赖于通过地域流动而带来的社会交往的新资源。士绅的地域流动与社会流动是互为表里的,因此其地域流动必然会受到社会流动需要的影响,简而言之,士绅在迁居地的选择上,还会考虑是否更有利于提升其社会地位等因素。我们就以大胜柳氏为例,分析其对迁居地选择的取向。
表八 大胜支婚姻与迁移关系表
盛泽 黎里 同里 莘塔 芦墟 平望 吴江 苏州 金泽 章练 吴县 枫泾 合计
婚姻 4 9 3 5 1 0 1 3 5 1 1 1 34
迁移 0 2 0 0 4 2 0 1 0 0 0 09/12
暂迁 0 1 2 0 0 0 0 0 0 0 0 0
资料来源:《分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民国十二年镌,胜溪草堂藏版。
说明:人口数斜杠前数字为迁移人数,斜杠后数字为迁移次数。暂迁指迁移两次者前一次迁居地。
表八是大胜柳氏城镇婚姻对象的具体分布及其迁居地选择的情况,其婚姻对象居地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吴江县内各镇,占64.7%,二是吴江县的上级城市府城苏州,占8.8%,三是邻县青浦、嘉善各镇,占26.5%。而其迁居地则基本集中在吴江境内各镇,占91.7%,府城苏州占8.3%,无人迁居到临县城镇。从迁移路径看,大胜柳氏是循着乡村迁市镇,市镇迁城市的渐进式迁居,如11世柳受恒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迁居同里,后迁黎里,其子柳炳伦从黎里再迁居至苏州。从迁居地选择与婚姻对象居地的比较可以发现,婚姻关系较密切的盛泽、黎里、同里、莘塔、苏州、金泽等城镇中,只有黎里、苏州成为迁居地,同里成为暂迁地,而婚姻关系较少或无婚姻关系的芦墟、平望则成为主要的迁居地。
黎里、同里成为大胜柳氏的迁居地是比较合乎情理的。首先,这两个镇都是与柳氏通婚较多的,柳氏已经进入了当地的士绅婚姻圈,与当地士绅集团的关系较为紧密。其次,从北厍的交通状况看,这两个镇与北厍的联系较为便利,日常交往比较频繁,相互之间的认知度较高。再次,在吴江的各市镇中,黎里、同里均以文化发达著名,如同里从宋淳化三年(992)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就先后出过38个进士、80个举人,(15)因此是士绅的聚居之地,这对士绅选择迁居地也是有吸引力的。而黎里与北厍相邻,是地域中心市镇,其吸引力较同里尤巨。
平望能够成为大胜柳氏钟情的迁居地与其在吴江市镇中的独特地位有密切的联系。在吴江县的七大镇中,平望地处交通枢纽,位于苏州、杭州的南北通衢和上海、湖州间东西要道的交叉点,沟通着苏、浙、沪、皖等地,在宋代已是“大商巨舶,物货充溢”,明初时“兹地为八省通衢……居民千家,百货凑集如小邑然”,到清代更是“居民数千家,物产毕陈,商贾辐凑比于苏之枫桥,时人称曰小枫桥。且人文炳蔚,景物清华,地虽一隅,可与通邑大都等量齐观也”。(16)在整体交通不甚便利吴江地区,平望称得上是吴江面向外部世界的门户。或许正是这一原因,平望成为士绅乐于选择的迁居地,毕竟身处地域交通的中心,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多的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机会。
大胜柳氏舍婚姻关系更密切、地域距离更近的莘塔而以芦墟为主要迁居地,是由两者的区域空间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芦墟是这一区域空间中的中心市镇,而莘塔、北厍从市镇的规模、市镇的发育成熟度等方面基本相当,均远不如芦墟,同属芦墟的次级市镇。这从民国时期吴江县改划自治区域过程中爆发的冲突中可以得到印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实行乡村自治制度,于1929年对县以下行政区域进行调整。吴江县政府拟将芦墟、莘塔、周庄三乡合并,结果引发区公所驻地之争,莘塔、芦墟互不相让,争执的结果是将芦墟、莘塔、北厍、周庄四区并为一区,区公所设在芦墟。县政府给出的理由是:“佥以芦墟面积宽广,户口众多,商业繁盛,地势冲要,教育发达,交通便利,均在莘塔、北厍、周庄之上,考查历史,向为各该自治区之重心。以固有界线言,与莘塔相距六里、周庄十八里、北厍十二里,今合组一区,管理原有各区一切行政事宜,均极便利。”(17)从这份公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芦墟在区域空间中的地位。从柳氏的迁居地选择可以看到,莘塔在区域市镇体系中仅居于次级市镇地位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士绅的迁居兴趣,希望通过地域流动提升社会地位的士绅最终选择了身为中心市镇的芦墟而非家族交往更密切的莘塔。
综合大胜柳氏对迁居地选择,可以看到,其范围基本处于婚姻圈覆盖范围之内,在12次迁移中有10次迁居到有婚姻关系的市镇,占83.3%。而在婚姻圈覆盖范围内,侧重选择与原居地交通便利、交往较频繁,对于自身发展能提供较大上升空间的上级地域中心地,可以说是突出反映了士绅在迁居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也就是注重地域流动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希望地域流动能带来更多的社会交往的资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士绅的地域流动是伴随士绅家族发展而共生的现象,散见于其发展历程的各时间段,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近世社会转型期,换而言之,士绅向城镇的迁移具有常态的、稳定的特点,是一种传统行为。当然,近世城镇的迅速扩容提供了更多迁移的空间,加速了城乡间的流动,无论就群体和个体而言,士绅比非士绅具有更强的流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士绅向城镇流动的规模。在地域流动的取向上,由乡村向城镇的流动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士绅的地域流动大多遵循着由乡村而市镇、由市镇而城市的规律,一代一代向更高等级的区域中心地流动。但是,这种迁移取向并不仅限于士绅,非士绅迁居者由乡村迁居城镇的比例甚至比士绅更高,表明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乡居人口向城镇的流动是全社会的流动。婚姻关系是士绅阶层构建区域空间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途径,其所构建的婚姻圈对士绅地域流动的流向选择有重要的影响。在具体迁居地的选择上,非士绅对婚姻圈的依赖更强,而士绅的地域流向选择同时还受到其社会流动需求等多方面的影响,这使得士绅的地域流动能够在更广阔的地域内展开。从近世士绅地域流动的规模看,其速度虽然略快于其他人群,但这一特点与传统社会并无本质区别。近世乡居士绅资源枯竭,从表象上看是乡居士绅向城镇的迁移,实际上士绅向城镇的流动,并没有削弱其在乡村的力量,而是顺应江南市镇化的倾向强化士绅在基层社会力量的必然趋势。造成“社会浸蚀”的根本原因是清末的废科举,从而使乡居士绅补给线的割裂,并加剧了士绅离乡的运动。从柳氏家谱所记载的十三世成员的情况可以看到,柳家子弟接受教育的场所从传统社会中的乡间私塾演变为吴江各城镇甚至上海、苏州等中心城市的新式学校,这就意味着乡村社会的准精英们不得不以离开乡村为代价来继续他们的精英之路。也是就说,科举废止后,随着乡村社会再生产士绅的功能丧失,乡村社会失去了精英补给的来源,这最终导致了乡居士绅无以为继局面的产生,直接形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精英阶层的“社会浸蚀”局面。
注释:
①参见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洪璞:《乡居·镇居·城居——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安涛:《论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及其制约因素》,《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
②如余子明认为士绅的城居化有二大原因,一是追求新的人生价值,一是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而这两个原因之所以产生正是基于近代西方势力的入侵所造成的社会变革。
③④倪师孟、沈彤:《吴江县志》卷1,乾隆十二年刻本。
⑤柳树芳:《分湖小识》卷1,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⑥《北厍镇志》卷2,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⑦吴江有轮船客运始于清同治二年(1863),北厍有轮船客运始于1923年,吴江轮船公司开辟吴江至章练塘新航线,北厍设停靠站,但不久即停航。1931年,苏州农工局轮船公司开辟自吴县浒墅至黎里的航班,北厍镇区设停靠站。1941年,新开至八柝的客轮途经北厍。1946年,往来于苏州与浙江西塘的苏州恒记轮船公司的四达班轮、永利轮船公司的洽记班轮在北厍停靠。当时北厍尚没有轮船停靠码头,依靠镇西元鹤荡畔乾泰木行的木排解决登船问题。
⑧柳兆熏:光绪《分湖柳氏重修家谱》卷9《家乘一·曾大父君彩公事略》。
⑨柳树芳:道光《分湖柳氏家谱》,《家谱自序》,道光辛丑年镌,胜溪草堂藏版。
⑩柳兆熏:光绪《分湖柳氏重修家谱》,《重修家谱后序》。
(11)端书公支外迁2人情况较特殊,1人无婚姻资料,1人为出赘。
(12)端士公支中有一人迁居乡、镇各一次。
(13)柳亚子:《五十七年》,《柳亚子文集》之《自传·年谱·日记》,第39-49页。
(14)周德荣:《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页。
(15)《吴江县志》卷2,第83页。
(16)(清)翁广平纂辑:光绪《平望志》卷1,《沿革》。
(17)吴江县政府训令第52号:《令莘塔乡政局长令知第六区区公所改设芦墟之理由》,《市乡自治区域状况调查卷》,吴江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204-3-510,第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