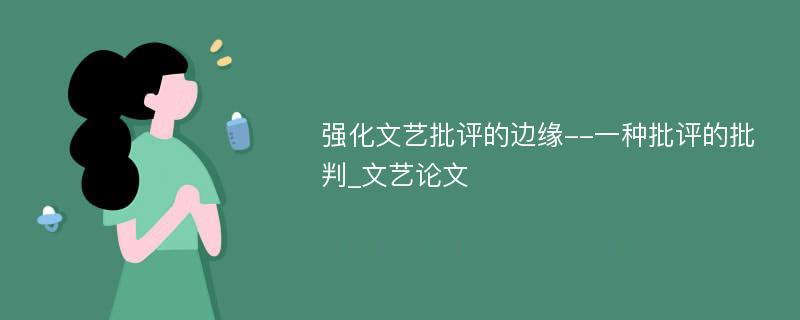
磨砺文艺批评的锋芒——对一种批评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批评论文,锋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有些很不错的批评家认为当前一些中国小说是异化性质的单向度的写作,他们尖锐地批判了当前文学的一些病态现象。可以说,这种把握是相当准确的。但是,这些批评家对这些病态现象的批判却相当乏力。也就是说,他们的批评武器还不够锋利。
在2005年《文艺研究》第9期中,李建军以“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为题认为:“批评是一种揭示真相和发现真理的工作。虽然进行肯定性的欣赏和评价,也是批评的一项内容,但就根本性质而言,批评其实更多的是面对残缺与问题的不满和质疑、拒绝和否定。是的,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意味着尖锐的话语冲突,意味着激烈的思想交锋。这就决定了批评是一种必须承受敌意甚至伤害的沉重而艰难的事业。”显然,李建军对文艺批评的根本性质的这种把握是片面的。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对于对立的两方执非此即彼的观点“好的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坏的是绝对的坏,一切都坏”。破或立,否定或肯定,在文艺批评中,不同的批评家可以有所侧重,但是不可偏废。即使文艺批评有时承担了清道夫的重任,也是为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那种以否定为文艺批评的根本性质的文艺批评不过是“用头立地”,因为它所建立的理想王国是根本脱离现实的。这种只是否定而没有肯定的文艺批评就是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这种文艺批评以人类某一个理想状态为标准臧否现存事物,它只看到现存事物与这个理想状态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它们二者的联系。因此,它看不到现存事物是实现人类这个理想状态的必要阶段,而是彻底地否定了现存事物的存在。当前文艺批评存在两种类型的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一种类型是误诊,即它所批判的对象根本就不存在它所批判的病态现象;另一种类型是确诊,即它准确地把握了它所批判的当前文学的病态现象。但是,这种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却彻底地否定了它所批判的对象,在倒脏水的时候连婴儿也倒掉了。对这种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人们往往只是注意到了一些批评家对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失之偏颇,而忽视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局限。当前不少相当活跃的批评家就是犯了这种错误。他们虽然准确地把握了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但在解剖和批判这个对象时却不够深入和有力。
在2005年7月3日《文汇报》上,洪治纲以“信念的缺席与文学的边缘化”为题指出:“从文坛的整体格局上看,我们还不得不承认,虚浮苍白且焦躁不安的功利性写作依然广泛地存在着;借助各种反自律性的表达手段,通过暧昧性的感官迎合,让作品谋取市场利益的情形依然屡见不鲜;尤其是一些新崛起的青年作家,精神格调与审美眼光普遍不高,创作热情却是异常高涨,感官化、粗鄙化、表象化的率性之作大量出现。这种看似热闹实则平庸的创作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表明了某些作家为了重新谋求社会核心价值代言人的身份或世俗化的物质利益依然在进行各种突围表演,而并非是真正边缘化了的作家在艺术自律性上的自觉努力。”的确,洪治纲看到了当前文学的一些病态现象。不过,当前中国文学之所以出现洪治纲所说的这些病态现象,不是因为洪治纲所说的文学信念的缺席,而是因为有些作家在价值取向上的迷失,即这些作家从根本上不相信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的存在。
有人为了肯定那些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的文学,提出了粗鄙存在观。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具体的人也是人,这就如白马也是马。坚持白马非马的高论与坚持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也仍然是人。有真痞子也有佯痞子,正像有真崇高也有伪崇高。动不动把某些人排除于“人”之外,这未免太缺少人文精神了。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他们认为,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是消灭大部分作家。这种典型的粗鄙存在观漠视价值高下的判断,它不是追求更好的,而是肯定更坏的。也就是说,它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它只承认人的存在,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粗鄙存在观因为有些作家可能成不了伟大作家,就放弃了任何努力,甚至消解神圣,自甘堕落。这种颠是纳非的思想倾向从根本上否定了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严重地造成一些中国作家在审美理想上的迷失。其实,当前文学创作出现低俗化倾向曾经受到文艺批评界有力的批判,但是这种有力批判在颠是纳非的多元论喧嚣中遭到了抵制和消解。
洪治纲也看到了“文学多元化”的危害。但是,他所提出的“高迈而卓越的文学信念”是无法根治这种危害的。洪治纲认为当前中国作家缺少哈金所强调的文学信念和略萨所说的文学抱负。洪治纲认同哈金所说的,“目前中国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他和哈金一样,倡导并要求所有中国作家都应该建立起“伟大的中国小说”之信念。洪治纲认为略萨所说的文学抱负和哈金所强调的文学信念其实是同一个命题。所谓的文学抱负就是“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像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对作家来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洪治纲认为当前中国文学创作之所以日显平庸,主观原因是高迈而卓越的文学信念的缺席,向“伟大的作品”冲击的文学抱负的匮乏。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使那些躲避崇高的作家,也渴望跻身伟大作家的行列。有些作家躲避崇高,不是否定“伟大的作品”,而是亵渎现实生活的神圣。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作家在向“伟大的作品”冲击中所取得的进步,而不是全盘否定或彻底打倒。洪治纲要求作家坚决、彻底和深入地拒绝和批评现实生活也是不正确的。正如马克思在挖掘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时所指出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即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也就是说,作家的批判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就是真正的批判。鲁迅以“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题在肯定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时指出:陀思妥夫斯基“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作家的拷问和批判不仅揭示真相,即“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而且否定罪恶,肯定洁白,即“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陀思妥夫斯基的拷问之所以深刻而有力,就是因为这种拷问和现实生活的拷问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如果说洪治纲是从总体上对当前中国作家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中国小说”的信念,那么,李建军则是在小说批评实践中以一些“伟大小说”为标准裁剪当前中国的小说创作。
在2002年《南方文坛》第4期上,李建军以“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为题深刻地指出:“在贾平凹的几乎所有小说中,关于性景恋和性歧异的叙写,都是游离性的,可有可无的,都显得渲染过度,既不雅,又不美,反映出作者追求生理快感的非审美倾向,也可见出他在审美趣味已堕入病态的境地。”他认为:“伟大的文学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它在艺术形式上是美的,还因为它在道德上是健康的、纯洁的。我们的写作是蔑视道德的写作。我们只用所谓的‘才华’或‘才气’来评价作家,而不问他的才华下面是什么。天长日久,我们就习惯于以一种褊狭的甚至是反文学的态度来对待文学,以至于丧失了对文学的真伪、美丑的分辨力。”在2005年《文艺争鸣》第4期上,李建军又以“是高峰,还是低谷”为题指出了贾平凹倾向于乐此不疲地叙写人的欲望层面的生活内容、渲染人的动物性的原始、粗俗的野蛮行为和毫无必要地加进了许多对脏污事象与性景恋事象的描写的两个原因:“一是作者过高地估计了包括性在内的本能快感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他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生理快感和心理美感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的深刻的道德体验和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意义。”的确,李建军看到了贾平凹的小说作品存在的病态现象,但是他没有找到这种病态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贾平凹等作家乐此不疲地叙写人的欲望层面的生活内容、渲染人的动物性的原始、粗俗的野蛮行为和毫无必要地加进了许多对脏污事象与性景恋事象的描写绝不是李建军所说的过高地估计了包括性在内的本能快感的意义和价值,没有认识到生理快感和心理美感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的深刻的道德体验和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意义。的确,生理快感和心理美感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美感也包括必要的生理快感。美国美学家桑塔耶纳指出:“虽然一件衣服、一座大厦或一首诗的感性材料所提供的美多么次要,但是这种感性材料之存在是不可缺少的。”“假如雅典娜的神殿巴特农不是大理石筑成,王冠不是黄金制造,星星没有火光,它们将是平淡无力的东西。在这里,物质美对于感官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刺激我们,同时它的形式也是崇高的,它提高而且加强了我们的感情。如果我们的知觉要达到强烈锐敏的最高度,我们就需要这种刺激。举凡不是处处皆美的东西,绝不能销魂夺目。”而贾平凹等作家片面地突出生理快感,是因为他们没有挖掘更深层的美的内容。
其实,李建军在贾平凹的小说作品中所总结的这些病态现象在其他作家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就是我们曾经深入地批判过的眩惑现象。我们认为这种眩惑现象在当前中国文学创作中大肆泛滥,不是缺乏纯洁的道德感,而是作家审美理想的迷失。李建军批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引起作家的强烈反对,恐怕就是因为没有把握《秦腔》的病根。有人在比较《秦腔》与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时指出,《故乡》开头是“回去”,最后是“告别”,准确地说,一开始就是为了告别而回去,虽然有回归和告别双重主题,但总的心态是“告别”;而《秦腔》虽然对故乡有深情的回忆,但主要是无可奈何的“告别”。这是极不准确的。鲁迅的《故乡》即使是“告别”,但也是怀有希望的“告别”。鲁迅“告别”的是他和闰土的隔膜,还是“希望”后代宏儿和水生“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而《秦腔》“是歌颂,还是批判?是光明,还是阴暗?”则非常矛盾,可以说是绝望的“告别”。而贾平凹之所以陷入绝望,是因为他看不到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所以,贾平凹不能真正开掘现实生活中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不能挖掘沉重生活中的真善美,即不能以真美感动人,就只能以眩惑诱惑人心。
李建军从文学史上的一些伟大小说中抽象出一些标准衡量当前中国一些文学作品。显然,这是一种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不过,虽然李建军的文艺批评是一种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但是,它与有些虚无存在观文艺批评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李建军所批评的对象的确是值得批判的。因此,我们在大力肯定李建军的文艺批评锋芒时绝不能忽视这种文艺批评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