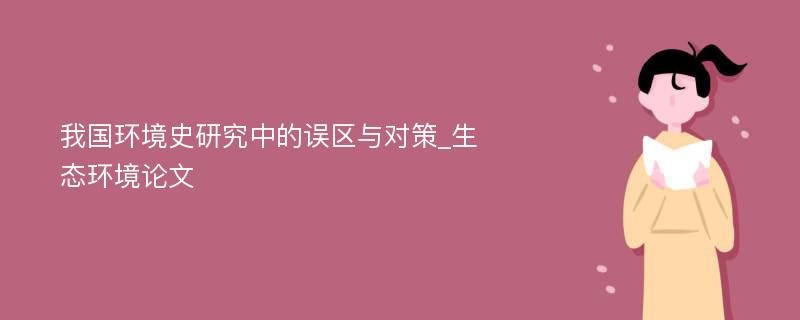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误区论文,史研究论文,环境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8-0122-06
中国环境史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20年来,相关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投身于这一领域的学者日渐增多,环境史的理论架构与研究范式等问题也都得到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国内接连召开了两次大型国际环境史会议,出版了两部较有份量的论文集。① 在2009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十多位中国学者步出国门,直接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2010年,《历史研究》又专门推出一组环境史笔谈,朱士光等6位学者对环境史的构建模式与发展方向做了进一步探讨。这些都表明环境史日渐壮大,逐渐成为历史学科中重要的研究热点。不过,人们对环境史的认识还存在若干误区,② 笔者近来做了一些思考,特撰此文进行初步的探讨,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环境史与环境变迁史之关系
为环境史下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一直是诸多环境史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美国学者罗德里克·纳什、莱斯特·比尔斯基、唐纳德·沃斯特以及休斯等人都对环境史的定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③ 国内学者也做了较多的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④ 但是就笔者所见,诸多学者的定义都没有对环境史与环境变迁史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把环境史等同于环境变迁的历史,相当多的环境史著作其实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完成的。近年来环境史方面的专著层出不穷,有些含金量还颇高,⑤ 但这些作品大都集中于一个区域或一个时期的环境变迁,未能彰显出环境史的特色和学术理念,自然与历史、环境与人类也并没有被很好地整合到一起。
为什么会出现环境变迁史一统天下的格局呢?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目前的环境史在学理上并没有突破历史地理的束缚,投身于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大多具有历史地理背景,他们主要运用的仍然是历史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得多数成果给人以借环境史之新瓶装历史地理之旧酒的感觉。要想扭转环境变迁史取代环境史的趋势,就要突破历史地理的藩篱。
毋庸置疑,生态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极为密切,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环境史就是在历史地理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多年来,学者们对两者关系进行了较多探讨。⑧最近,参与《历史研究》笔谈的几位学者又对两者的关系做了进一步解构,但历史地理学者与非历史地理学者之间仍存在较多分歧。朱士光认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念——人地关系极其重要,应当也贯彻到环境史的研究中;[1]邹逸麟主张多学科的合作,但其提及的几个应该关注的领域仍处于人地关系的框架中;[2]蓝勇对区域环境史的思路有较多论列,着眼点也仍在环境的变迁上:[3]王利华则认为环境史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厘清历史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与环境史研究之间的区别。[4]
笔者以为,人地关系应该是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但不应该将其视为环境史的全部内容,更不应该将人地关系理解为环境的变迁。历史地理学为环境史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后者若受到前者过多的牵制就会导致研究主题狭隘、研究方法单一和生态学理念缺位等若干问题。此外,学理难有突破和思维惰性增长等问题也会接踵而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环境变迁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抽去了环境变迁的部分,环境史也就丢掉了安身立命之本;但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环境变迁史绝不是环境史的全部。若只把注意力聚焦在环境变迁上,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环境史将会陷入僵化呆板的困境。要突破困局,当前要做的主要工作是拓展领域和转换视角。
(一)领域拓展——环境与社会并重。从研究领域来看,环境变迁固然是环境史探究的对象,社会的变迁从未逸出环境史关注范围之外。笔者认为,环境史所关注的变迁,实际上就是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塑造与被塑造关系,大致有四种类型:其一,环境的自我塑造。亿万年来,自然环境有其自身的演变机制与脉络,人类未施加影响的情况下,自然界中的海陆进退、气候冷暖干湿交替、地表的升降和地貌的侵蚀搬运等变化进程一刻都未停息过。其二,人类对环境的塑造。人类诞生以来,不断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自然界,引起了植被状况、水文条件、动物分布等的变化。其三,人类的自我塑造。人类通过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不断改变自身的物质与精神面貌,也可称之为自我驯化。其四,环境对人类的塑造。环境状况也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族群差异、发展方向、社会结构等等无不受到环境的制约。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已有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类型,即人类对环境的塑造作用。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地质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已对环境自我塑造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直接为我们所用。唯独环境对人类的塑造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方面,学者们用力仍明显不足。而这缺失的部分也恰恰是环境史最有价值的部分,缺失了这部分内容,环境史将会变得极为空洞。
因此,生态环境史应该将以上四种类型全部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环境变迁之外更应考究社会变迁,关注环境与人类之间纷繁复杂又生动鲜活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同样会在我们的观察范围之内。环境史将会是真正的整体史,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通过对自然与社会进行高度整合而开创出许多更新的领域。
(二)视角转换——变与不变兼顾。从研究视角上看,我们应该具有动静兼备的观察方法,探究环境状况时不仅要注意到“变”,也要注意到“不变”。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量:其一,从质量关系上来看,前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虽也有变化,但人类受制于环境又反作用于环境的表征与后果大体上是前后一致的,所以文明演进历程是量变、质变兼有,而以量变为常态。因此,我们在探究传统时代的物流与能流状况时,注意到量变的同时还要注意到质变。其二,从时间跨度上看,长时段的环境与社会都是变动不居的,此为变;而短时段的一切又近乎静止不动,此为不变。其三,从空间区域上看,传统时代的农耕区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非农耕区不断地演变为农耕区,此为变;而某一地区一旦成为农耕区后,地表景观的变化也是很微小的,此为不变。
为了更好地切入所讨论的问题,就有必要引入一种“不变”的视角——“准静态”的视角。所谓“准静态”,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动中有静,静中又有动。在这种准静态下,我们分析各个生态要素是如何布列的,这样的布列状况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人们又如何调适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应对这种特定的生态状况。准静态视角在以下两种情形下适用:1.较长时段但生态状况并无根本性的变化,如史前长达百万年的时间里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早期农业时代数千年之久的人与环境之互动,都可从准静态切入进行深入剖析。2.探究某一时代某一区域的环境状况与人们生产生活之关系时,相当于从历史演进的胶片中切下某一断片,变化可能是极其微小的。以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平原地区为例,当森林、草地、沼泽、湖泊、湿地都开发殆尽后,明清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其实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放在特定环境条件限制下的人们的生产生活。这时更多采取“准静态”的视角,就能更好把握环境与人之间的互动调适关系。
总之,通过引入“准静态”视角,可以使环境史实现“动静兼备”,从而大大彰显环境史的特色,帮助我们改变过分关注环境变迁史的现状。
二、环境史与环境保护之关系
近年来环境史理论方面的论文层出不穷,但似尚无学者对环境史与环境保护史的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一些非环境史学者往往把环境史等同于环境保护的历史,圈内学者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倾向。标有“环境保护”字样的历史论文非常多,其中尤以关注先秦环保理念的文章为多,⑦ 在不少学者的笔下,先秦是中国环境状况的黄金时代。关注其他朝代环保状况的文章也不少,仅2010年笔者所见到的就有4篇。⑧
毫无疑问,环境史是在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兴起的,其产生发展与环保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环境保护也天然地就是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内容。[5](P36-40、113-114)但是,环境史却不能简单地界定为环境保护史,其研究范围要广阔得多。一言以蔽之,环保史从属于环境史,而环境史却不等同于环保史。只围绕环境的破坏与保护做文章,对环境史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主要的消极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1.环境史的内涵极为丰富,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方面面都为其所囊括。上文已指出,人对环境的塑造作用只构成环境史研究的一部分,人的塑造作用包括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保护又只是积极塑造作用中的一种类型。这么看来,环境保护也只是环境史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眼光只盯着环境保护这一小块,就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认识错误,环境史断难取得长足发展。2.环保思潮是上世纪中后期才兴起的,古代也曾有些具有环保色彩的政府与个人行为。但传统时代的环境问题并不如工业社会严重,相关的行为只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况下出现,数量非常少,不具有自觉性和现代的环境意识,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的真正觉醒可能更要晚至上世纪晚期。若只关注环境保护的话,我们会发现可研究的问题少之又少。此外,若用环保思维去探讨中国古代环境史,可能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摒弃激进的环保意识形态,奉行生命中心主义。环境史学者大都有着强烈的环境忧患意识,时时牵挂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更多悲天悯人的情怀。可以说,强烈的环境诉求与批判意识正是环境史的灵魂所在。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量避免激进的环保主义立场。过分强调环保意识形态,会有趋于偏激而背离客观真实之虞。过强的环保意识,往往导致环境中心主义的立场。站在这一立场看问题,会发现人类诞生以来一直在对环境施加恶的影响,最终推导出的可能是颇有宗教意味的原罪论。
其实,环境无时无刻不在自我演变。而生命出现以来也积极地对环境施加干预,人类诞生后只是使得干预作用进一步强化。不对环境产生任何干预,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人类也不例外,所以环境中心主义的立场是不足取的。我们要批判对环境的过度开发,但这不意味着就要盲目推崇完全无人力干预的荒原。那么我们该采取怎样一种立场呢?王利华最早引入的生命中心主义的立场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他曾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场合中表明这一立场,他认为环境史“应当转向对人类与自然协同演进关系的系统思考,‘环境史’应当成为一种既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又具有深刻历史哲学思考和生命价值追求的特殊事业。”[4]站在生命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观察问题,既纠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与自大,又避免了环境中心主义的偏激与悲观,从而可以写出真正客观公允的历史来。
(二)规避衰败论定势思维。学界过多关注环保历史,与衰败论的盛行有关。环境史学者在开展研究前往往已抱有一种先验性的认识,即环境在不断衰退,而衰退的罪魁祸首是人类。于是,多数的研究都是在为这一先验性的结论作注脚。这样的研究模式当然也有其合理之处,却也导致了偏离客观真实和僵化思维的弊病。要走出认识误区,就应纠正这一定势思维。
1.要避免机械决定论或过度联系论,不要把任何自然灾变都与人类对环境的干预扯上关系。将环境的变迁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但过于夸大人类的影响力——特别是传统时代——则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有史以来环境的自我变化是惊人的。太阳活动状况、地质变动、洋流与气团异动等自然现象,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如此,在传统时代人类更是无能为力。所以,把传统时代环境变迁的原因过多归结到人类身上未必合理。
2.避免唯自然论,不应盲目崇拜不加任何干预的“纯自然”。实际上也并不存在真正的纯自然,我们知道生命诞生以来一直在对环境进行积极的干预。生物在大气组成、物能流动、地质结构、土壤成分、地表形态等方面的变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诞生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自然的干预。如果去掉所有的干预,整个自然环境将变得死气沉沉。我们要对人类的干预作用加以调控,以便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相处,而非彻底抹去一切干预,那样不惟人类无法生存,所有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
3.避免作简单量化的对比,不应无视史料留存数量的差异,而直接进行量化对比。人们总是对自己生存时代的信息了解最多,而对历史上的信息了解相对要少,于是总容易产生当代灾难要比先前时代多的感觉,从而形成衰败论的观点。如有学者喜欢统计历史上的灾害记录来做量化分析,由此来探讨灾害的发生和变化规律,结论都是自古至今自然灾害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他们很少注意的是,某时代文献遗存数量与距今时间的长短呈负相关关系。越是晚近文献越丰富,关于灾害的记载也越多,反之亦是。这意味着统计分析时样本的选取就是不合理的,其分析的结果往往也经不起推敲。跳出简单的量化分析模式,我们会发现环境状况并非呈线性恶化趋势。
三、环境史与传统史学之关系
国内不少学者对环境史并不完全认同,他们一则以疑,一则以惧。疑的是环境史能否在史学中站稳脚跟,惧的是环境史是否会给传统史学带来致命的冲击。那么环境史与传统史学的关系该如何梳理呢?
把环境史视作洪水猛兽是没有道理的,环境史之于传统史学,并不是完全的决裂与背弃,两者之间继承的色彩颇为浓厚。环境史归根结底是立足于传统史学之基础上的,且天然地与传统史学密不可分。历史地理、农业史、考古学构成了环境史重要的本土渊源,而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人口史、灾荒史等史学分支也为环境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没有传统史学提供的丰富营养,也就不可能有环境史的茁壮成长。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一切事项也都在环境史的关注范围内,环境史只是力争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谋求新的更合理的叙述形式与阐述模式,其真正旨趣在于“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⑨ 通过对新旧史学的更好整合,新课题和新领域将不断涌现,笔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不同类型的研究可以分别冠名为社会生态史、生态社会史、政治生态史、生态政治史、经济生态史、生态经济史、文化生态史、生态文化史、军事生态史、生态军事史、生活生态史、生态生活史、性别生态史、生态性别史等等。⑩
与其说环境史是要颠覆传统史学,不如说是要引入新思维新视角更换新鲜血液来改造传统史学。我们的叙述模式与阐释方式都会有所变化,但我们的根基依然在传统史学。环境史为史学引入了新视角、新理论和新方法,是对传统史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的补充,而非彻底推翻。
从研究对象来看,我们是要纠正重人事、轻自然的史学传统,为以往的历史研究添加更多的自然元素。环境史将人类历史舞台拓宽并添加更多的非人“道具”与“演员”,以求更全面更客观地叙述并解释历史;同时让人类回归到“芸芸众生”之中,以更谦卑的态度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概括起来说,其研究理路为“自然进入历史,历史回归自然”。[6](P2)在环境史架构下,自然环境不再是史学可有可无的背景与点缀,而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环境史要“将环境因素纳入历史解释主体范畴,认为环境—人以外的其他生物、大的自然发展进程与人一样,是创造历史的重要因素之一”。[7](P36)这样,在重视自然因素作用的同时,也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从而勾画出更为立体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图景。
从学术理念来看,环境史把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史学研究,搭建起了生态—社会二元一体的研究模式,从而改进了传统史学的社会一元单线条模式。如何在研究中践行生态学理论并探究生态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学者们做了较多的思考。王利华较早把“人类生态系统”概念引入了环境史,他认为环境史“将人类及其周围环境视为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即‘人类生态系统’,考察这个生命系统的历史结构、历史功能及其时代演变,主要着眼于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特别是生命系统的延续与保护,探讨不同系统要素尤其是人类因素与自然因素之间的历史关系,揭示系统演化的历史动力机制”。[8](P10)王建革近年来接连推出了两部专著和一系列文章,在环境史的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方面颇多建树。他最近推出的《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11) 在探究晚近时期社会对特定环境的适应状况时分析精当,运用生态理念和生态分析更好地整合了环境与社会两个层面,书写手法令人耳目一新,值得学习。
让学界对环境史产生疑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史似乎在鼓吹“环境决定论”。这种疑虑并非毫无道理,国外学者克罗斯比、贾雷德·戴蒙德等人的著作中环境决定论的色彩就非常明显。(12) 而国内学者在阐释环境史理念时,也或多或少会有环境决定论的倾向。那么环境史究竟如何看待曾大行其道又因遭受猛烈攻击而式微的环境决定论呢?应该把环境的作用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首先,要认识到环境决定论有其合理的一面,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不容忽视。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来,无数的生物学资料证明在生物的演进过程中,环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地,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的丰富资料可以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被深深地打上了环境的烙印,某种程度上说,人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深刻地决定了他们是什么人。所以,传统史学过多关注文化与社会作用而轻视环境作用的倾向应该扭转。
其次,在重视环境影响以弥补传统史学缺陷时,应避免矫枉过正,不能无限放大环境的决定作用,重视环境作用的同时不应对文化作用选择性失明。人类社会的演化历程中有两个机制在发挥作用,一是自我驯化机制,一是被动驯化机制。传统史学更多关注人通过社会与文化而进行的自我驯化,冷落了人在环境影响下的被动驯化。我们要把后者的地位摆到与前者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对文化决定与环境决定一视同仁。正如休斯所言,“虽然对一个学者来说不偏不倚总是比旗帜鲜明要难,但很多环境史学家发现他们自己还是持折中的立场”。[5](P116-117)
初创阶段的环境史标新立异在所难免,但我们绝不能狂妄到把传统史学彻底踩到脚下,也不应过分拔高环境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只有自信而又不失谦虚地面对传统史学和文化决定论,化解非环境史学者的成见与敌意,环境史才能健康发展。
注释:
① 1993年12月13日-18日,在香港召开了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会后推出的论文集为《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由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于1995年出版,英文版则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2005年8月17日-19日,在南开大学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为《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由三联书店于2007年出版。
② 杨庭硕先生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陷阱与误区进行了探讨,可参见氏著《目前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陷阱和误区》,《南开学报》2009年第2期。
③ 相关情况可参见包茂红:《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④ 侯文蕙、包茂红、高国荣、梅雪芹等世界史学者都有大量译著和评述,不一一列举。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史学者的文章有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李根蟠:《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⑤ 就笔者所见到的有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元林:《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颜家安:《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有关区域与断代研究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王玉德、张全明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则是大尺度长时段的相关研究。
⑥ 朱士光:《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景爱:《环境史续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辑: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学术渊源问题》,《南开学报》2009年第2期;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王琳:《紧张与亲密: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⑦ 袁清林:《中国环境保护史话》,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朱松美:《周代的生态保护及其启示》,《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罗桂环:《中国古代的自然保护》,《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崔德卿:《秦汉时代山林树泽的保护与时令》,载《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版;陈朝云:《用养结合:先秦时期人类需求与生态资源的平衡统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6期;吴晓军:《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为了复兴的反思》,《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⑧ 孙冬虎:《论元代大都地区的环境保护》,《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徐岩:《论郑州商都时期先民对环境的保护及其初步治理》,《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阿茹罕:《试论古代蒙古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毛丽娅:《道教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及其实践》,《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1期。
⑨ 王利华对“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网”的学术目标所作的概括,见该网:http://www.sino-eh.com。
⑩ 这里所做的构想深受王利华的影响,社会生态史和生态社会史由其最早提出,见氏著:《社会生态史——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社会史研究通讯》2000年第3期;《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另外,对新领域的命名用“环境”代替“生态”会更符合主流意见,但窃以为称“生态”更合适些。
(11)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版。
(12) 克罗斯比著,许友民、许学征译:《生态扩张主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贾雷德,戴蒙德著,江滢、叶臻译:《崩溃:人类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