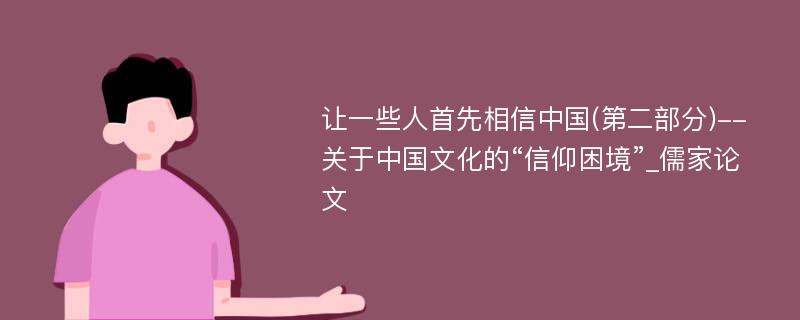
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下篇)——关于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局论文,下篇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天不生‘信仰’,万古长如夜” 遗憾的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情况却全然不同。“先信仰起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在中国都未能引起关注。 当然,这一切都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拒绝“求新声于异邦”,而只意味着:在“异邦”的“新声”中,却往往未能敏锐觉察到“信仰”的存在。 诸多学者归咎于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然而,在中国,其实始终并不存在被“救亡”压倒的所谓“启蒙”,而只存在被某一种“启蒙”所压倒的另一种“启蒙”。具体来说,在中国始终存在的,都只是“法式(乃至作为其变种的‘俄式’)启蒙”对于“英式(乃至作为其变种的‘美式’)启蒙”的“压倒”。 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成功,根源于两大选择,其一,是教会的作用;其二,是人权与契约意识,可以将它简单地概括为“信仰启蒙”和“个体启蒙”。英国之所以最后走上宪政的道路,之所以实现了改良,之所以成为世界的带头老大,正是因为两大启蒙的同时实现(所谓有神论和个人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有神论的唯心主义”)。它所开创的现代化模式,被称为:“盎格鲁圈”。但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却不然,它们仅仅只有一个启蒙——“个体启蒙”。而对于无神论的提倡,对于唯物论的提倡,所谓“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却使得这些国家既不承认上帝的伟大,也不承认人的渺小。结果,对于英国而言的“应该成为的人”就变成了对于法国而言的“本能自然的人”,而且,误以为只要强调个体解放,只要尊重人,就可以实现现代化。于是,另一个启蒙——信仰启蒙,却因此而令人遗憾地被忽视了。 然而,无疑是因为宗教传统的匮乏,中国天然地规避开了英国的现代化道路,从而也天然地规避开了西方现代化的真正源头,并且转而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以法国为代表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尽管五四时代的中国言必称“科学”、“民主”,但是却极少推崇“宗教”,更不要说对于“信仰”的推崇。 并不是没有觉悟者。一百年前,“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等口号的提出,无疑都意味着对于西方的“先基督教起来”的觉察,可是,因为这些觉悟者有意无意地把“先基督教起来”与“先信仰起来”相混同,因此在正确意识到基督教对于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以及无法把基督教直接引进到中国之余,却没有能够意识到西方基督教通过否定“教权”以高扬“神权”,再借助“神权”以高扬“人权”这一根本奥秘。一则误以为否定“教权”就是否定宗教,二则误以为可以越过“神权”去高扬“人权”,因此,也就没有能够意识到在西方基督教背后的“信仰”的出场。于是,动辄希望以美育、哲学、道德去“取代”宗教,可是,却偏偏忽视了必须要犹如基督教的高扬“神权”那样去高扬“信仰”。结果,中国的没有“信仰”的“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 “以道德代宗教”……就都仅仅只是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式”的而不是北部欧洲的“新教改革式”的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都没有能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人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以及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观念,总而言之,“人是目的”的观念,也并没有被真正关注到。 还有一些觉悟者,应该说已经察觉到了“先信仰起来”的重要性,可是,却又转而将之与中国文化等同了起来,并且认定:所谓“信仰”,在中国文化中古已有之。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所谓“内在超越”说。 所谓“内在超越”,是海外新儒家的一个发明(如牟宗三、余英时)。它是对西方基督教强大压力的某种反弹,也是对“无宗教而有伦理”的传统的迷恋,以致完全无视中国文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先天不足,偏偏转而认定在中国文化中也同样存在成熟的“宗教(性)”与“信仰维度”;而且,与西方相比,其中的“超越”属性是完全一样的,区别仅仅只有“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不同。 遗憾的是,这一说法尽管为众多学人所支持,但却于理无据。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内在”,确实有之,但是,中国文化的“超越”,则其实无之。作为一种境界性的文化,中国文化无疑存在着从低到高的提升,诸如从自然境界到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直到天地境界等,但是,这仍旧是人之为人的自我提升,而且是此岸的提升,但却并不存在从“人”到“神”的提升。显然,在这里存在着的,是“心”的维度,而不是“灵魂”的维度。因此,也只是一种“无神论的唯心主义”。但是,西方的“先信仰起来”却是一种“有神论的唯心主义”,针对的是“灵魂”的维度。在其中,所谓“灵魂”,也就是自由存在的精神世界。它具有绝对的意义。也因此,西方的所谓“超越”,就意味着对于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的孜孜以求。这终极价值远在彼岸,人之为人,只有不断而又不懈地穷尽自己,才可能逐渐逼近目标,于是,在对象世界的创造中不断地确证自己、见证自己,甚至去拼命地完善自己、实现自己、发现自己、创造自己,也就成为西方的一种必须的生存方式。由此,无限的创造力、无限的创造能量都得以被激活。可是,中国却不然,因为认定真善美都在自身人性的此岸,只要“反身而诚”,就可以发现“万物皆备于我”,自然也就不会去在对象世界的创造中不断地确证自己、见证自己,甚至去拼命地完善自己、实现自己、发现自己、创造自己。最终结局,却是生命的无限的创造力、无限的创造能量的日渐泯灭。无疑,这是一切试图借助回到人的自然本性来提升人性的文化选择都难以幸免的尴尬境遇。 由此看来,所谓“内在超越”,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偏偏是遮蔽了问题。中国文化中“信仰”的匮乏,就恰恰被遮蔽了起来。 综上所述,取径“法式启蒙”却是为了躲避“英式启蒙”;“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却是为了回避“信仰”;以“内在超越”去取代“外在超越”却又是干脆认定“信仰”本来在古老的中国早已有之,总之,与西方的旗帜鲜明地大力弘扬“信仰”截然相反,中国却往往是在羞羞答答地拼命躲闪“信仰”。 然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信仰当然并不是万能的,但是,离开了信仰,却又偏偏是万万不能的。对于“先信仰起来”问题的忽视,恰恰意味着中国的深深陷入于“信仰困局”。因此,马克斯·韦伯本人所发现的: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①无疑很有道理。 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今天我们可以说:“天不生‘信仰’,万古长如夜。” 百年之后在中国,“信仰”建构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也就成为必然。 十、真正过去的东西,一定在未来与我们相遇 然而,“信仰”的建构,在中国也并不轻松。 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构“信仰”绝无可能,唯一良策是:另起炉灶,即全盘引进西方文化。无疑,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信仰的困局”。但是,对此我却无法苟同。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犹如我们置身其中的空气,绝不是率意就可以全部“清盘”的。我们之无法离开中国文化,就犹如我们无法拽着头发离开地球。而且,在未来的中国必将得以建构完成的信仰,也必须是和只能是“说汉语”的。舍此则无疑别无他途。 信仰的建构,无疑并非中国文化的强项,也确实是中国文化之不足,但是,却也绝非中国文化之不能。固然,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局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信仰的建构都未能引起中国文化的高度重视,但是,中国文化也并非就与信仰问题格格不入。“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在中国更并非就永远水土不服、永远刀枪不入。信仰,在中国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个“多与少”的问题,但是,却并不存在一个“有与无”的问题。 世界之为世界,当然存在包括东方、西方在内的诸多的多样性,但是,却更存在共同性,也就是所谓“共同价值”,它是全世界发展道路中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最根本公理。换言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东西,一旦走出蒙昧,一旦幡然醒悟,毫无例外的,都必然体现为对于“信仰”的追求,也就是都必然体现为对人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以及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共同价值的追求,对“人是目的”的共同价值的追求,这就是人类现代化道路中最大公约数、最根本公理。②在此之外,任何一个拒绝接受共同价值的无论什么“特色”的“钉子户”,则都无疑是根本无法进入现代世界的。 中国亦然。人们之所以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构“信仰”绝无可能,往往都是仅仅着眼于中国宗教的现状。而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不同,中国自古就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有信仰地进入文明社会,而是君权天授(民授),并且是没有信仰地进入文明社会。也因此,中国未能将夏商时代萌芽的“昭事上帝之学”③进行到底,而是长期停步不前。于是,中国的宗教,也就都往往并非西方基督教那类的启示宗教,而仅仅只是前启示宗教。其中,有时是“信”或有之,“仰”却没有,有时候则是“仰”或有之,“信”却没有,还有的时候,则是既没有“信”也没有“仰”。其实,这实在不能被称作“信仰”,而只能被称作“崇拜”。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把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与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都归之为低级的宗教,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可是如前所述,“信仰”的建构不但可以借助宗教,而且还可以借助哲学。即便在当代西方,我们也不但看到了基督教所带来的信仰建构,而且还看到了非基督教所带来的信仰建构。例如朋霍费尔所提倡的就是“非宗教的基督教”、“世俗基督教”,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他仍旧是在从事着信仰的建构。中国文化也如是。以儒家为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把它看做“非宗教的信仰建构”,但也正是中华民族的原初信仰内在地构成了儒家。这就是所谓“无神论的唯心主义”。④在其中,像“以仁为本”,就正是对于“人是目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价值恪守。至于“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行一不义不为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更是透露出儒家坚决反对把人视同工具性价值的坚毅努力。⑤这一切,当然都是人类“共同价值”的体现,也都与全世界发展道路中的最大公约数、最根本公理彼此吻合。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信仰的建构竟然逆道而行,也就是说,信仰的建构不是越来越被关注,而是越来越不被关注,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信仰的因素也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从春秋到唐宋,到明清,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经三次沦落,更历经唐宋前的“集权”发展与明清开始的“极(君)权”发展,走过的不是弃恶扬善的道路,而是弃善扬恶的“劣币淘汰良币”道路。与此相应,中国文化也日益从钻石蜕变为石墨、从雄鹰蜕变为土鸡。本来,在早期的中国文化那里,例如在原始儒家、原始道家那里,就已经是“上帝死了”,但毕竟还存在着一个中华民族的“生命共同体”,存在着信仰的生命基因,可是,在后期儒家、后期道家那里,尤其是在那些俗儒、俗道的手上,中华民族的“生命共同体”也颓然倒地,信仰的生命基因更丧失殆尽。人逐渐不成其为“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逐渐“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⑥。越是低级的东西越是被强调,越是高级的东西越是被扼杀,越是正面的东西越是被否定,越是负面的东西越是被褒扬,保护的是本来不该保护的东西,打击的也是本来不该打击的东西。人,被逐渐变成他所不是,而不是逐渐变成他所是,“崖山之后,已无中华”、“明清之后,已无华夏”,这些话固然偏激,但是也绝不是毫无道理。⑦“哲人其萎乎”?就后期中国文化而言,答案是肯定的。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内部,也存在着深刻的思想悖论。以原始儒家为例,孔子终其一生,都处在某种深度的思想悖论之中:一方面是“天下为公”的“仁者爱人”观念,另一方面却是“天下为家”的“孝亲至上”观念;一方面是“仁爱恻隐”的大同之道,另一方面是“孝治天下”的小康礼教;一方面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另一方面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一方面是“以仁为本”,另一方面却是“忠孝为本”;一方面是“大道之行”,另一方面却是“大道既隐”。而在中国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孔子乃至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之中的这一深度思想悖论必须加以审慎关注。因为此后的孟子荀子,尤其是程朱陆王等后期儒家,就是从这里令人遗憾地日益完全沦入了原始儒家的深度悖论所构筑的陷阱之中。这就是所谓“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爱非仁,爱之理是仁”(《朱子语类》卷二十)、“人也只有一个父母,哪有七手八脚爱得许多”(《朱子语类》卷五十五)。由此,原始儒家的积极意义尽失。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尽失,唯余工具性价值。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却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无解,也不应该遮蔽我们前行的方向。关键在于,我们必须以“正本清源,释放中国文化中的‘活东西’”作为中国文化的信仰建构的逻辑前提,以“不破不立,清除中国文化中的‘死东西’”作为中国文化的信仰建构的基本保证,并且以“创造转换,激活中国文化中的‘真东西’”作为中国文化的信仰建构的根本途径,⑧并且,去毅然直面中国文化的“信仰的困局”。 海德格尔曾殷切提示:真正过去的东西,一定是在未来与我们相遇。⑨诚哉斯言!只要我们去毅然直面中国文化的“信仰的困局”,中国文化,也一定会在未来与我们相遇。 十一、到信仰之路:“信仰困局”的破解 不过,直面中国文化的“信仰的困局”又绝不意味着仅仅就是回到中国文化的过去,例如,回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这是因为,如同人类的一切真正的思想,即便是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也依旧一定是在人类自由与尊严的理解上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深度的思想。其中蕴含的,也正是人类借以安身立命的共同的终极价值,这就是“人是目的”。因此,而今我们在建构信仰之际,就没有必要去依靠所谓“儒家复兴”、“道家复兴”,而只需去弘扬其中的全人类共同存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对于人作为终极价值的信仰、对于“人是目的”的信仰。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大哉问”,也是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 同样,直面“信仰的困局”,也绝不意味着仅仅就是“宗教复兴”。这同样是因为,人类的一切真正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作为“宗教中的宗教”,在其孜孜以求的超自然力量背后,蕴含的依旧一定是在人类自由与尊严的理解上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深度的思想,即所谓“人是目的”。因此,而今我们在建构信仰之际,也同样就没有必要去依靠所谓“宗教复兴”,而只需去弘扬其中的全人类共同存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对于人作为终极价值的信仰、对于“人是目的”的信仰。⑩ 更何况,现在也已经没有了西方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孕育而出的温床的特定条件。在西方,由于科学在当时的不发达,基督教的问世堪称适逢其时,因此不但得以独霸一时,而且更以无可置疑的强势推动西方完成了信仰的建构。现在,情况却全然不同。宗教的神秘以及它自身的魅力都已经被“祛魅”。即便是在西方,“上帝”也已经从世界退出,徐徐回到了十字架之上。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现在“世界已经成年”。因此,即便西方的基督教信徒在思考的也已经是“非宗教的宗教建构”。这样,我们即便是还想再去重走西方的借助宗教以建构信仰的老路,也已经绝无可能。 而且,当今之世,还已经从对于“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批判进入到对于“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批判。(11)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的“神”的生存与作为“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虫”的生存都已经不复是人类的理想。就西方而言,不单单要走出异化为“神”的“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而且还要走出异化为“虫”的“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已经在从“神”的生存、“虫”的生存回到“人”的生存,无疑,这就更加加剧了信仰建构的极度复杂性,加剧了“信仰困局”本身。 因此,设想通过重建上帝的方式来完成信仰建构,已经此路不通。众多的中国学者特别服膺海德格尔的宣言:“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12)可是,这宣言却恰恰证明即便是连海氏这样的硕学大哲也仍旧没有在人类创造上帝的智慧中有所彻悟。海德格尔没有意识到:所谓“上帝”,无非就是人类的弱点的折射,也是人类对于自身的智慧毫无信心的结果。它是人之为人在建立和推进对象性关系时折射而出的理想特质,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形式”。(13)“上帝”,当然是一种“超人”的“神圣形象”,但是其中委婉表达的,却是人类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是人类希冀借助“神圣形象”去为自身存在赋予某种神圣意义,因此,是信仰成就了上帝,而不是上帝成就了信仰。 而“人类已经成年”,则不仅仅意味着要走出一切的旧神,而且意味着要走出一切的“新神”,不是“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而是再没有一个上帝能够救助我们,不是重返神学的形而上学,而是回到形上之思。而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与把握人类自身的走出“信仰困局”的能力,从回到“上帝”到毅然而然地“站出来”并且“去存在”。因为本然的超自然超现世的精神力量事实上并不存在,灵魂与肉体、有限与无限也无法截然分开,更没有一个本然的灵魂与无限事先就存在于世界,只有人类自身的自我扬弃、自我否定的生命过程及去伪存真、弃恶从善的过程,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既然人性的进化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够揭晓,那最初的一切规定,诸如“上帝”,就是没有根据的。唯一重要的,当然也就不是去建构一个“上帝”之类的目标,而是在充分展开自己的全部可能性的基础上,去不断地揭晓一个目标。这就正如弗洛姆所说:“存在方式的信仰首先不是一种对特定观念的信仰(尽管也可能是),而是内心的一个目标,一个态度。也许这样说更恰当,人在信仰中存在,而非占有信仰。”(14) 而从所谓“信仰”来看,它应该是从“信赖”到“信念”再到“信仰”的提升。从“赖”之到“念”之到“仰”之。最终,只有人类生存中的终极价值,只有人类生存中那些亟待恪守的东西,才会逐步递升而出,成为信念之中的信念,信念之上的信念,并且被“先天性判断为真”。信仰应该“把自己给与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给与比他的个人生命更伟大的观念。”按照泰戈尔的说法,“这种伟大的观念能使他从所依附的全部财物中解放出来。”(15)同时,从“赖”之到“念”之到“仰”之,还应该是一个逐步远离“物”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并且转而融入“心”的世界、精神的世界的过程,一个从“自然的本能”向“精神的本能”提升的过程。由此,人类得以无限地去开发自身的精神能量,并且无限地去趋向自身的终极价值。这就是罗素将之称为“最‘心理的’事物”(16)的原因,也是卡西尔把它命名为超出了“人的直接实践需要的范围”、“人的经验生活的范围”的“人的符号化的未来”的“一个绝对命令”的原因。(17)由此,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最‘心理的’事物”,这个“绝对命令”,无疑也就应该隶属于人类的共同价值,也就是:人是目的。 也因此,中国文化的信仰建构并不需要从乞灵于“上帝”开始,而应该立足于“非宗教的信仰”和“无上帝的信仰”。总而言之,应该立足于“人是目的”。是否坚持“人是目的”,是否以人作为终极价值,才是真正通行于全世界的根本追求,也才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共同的公分母,人类所必须共同尊奉的共同价值。 鲁迅说:“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18)这意味着: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要“先信仰起来”,首先“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同样,在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上,要“先信仰起来”,首先也向中国“所要的是‘人’”。因此,在中国首先实现“人是目的”的意识的觉醒、人作为终极价值的意识的觉醒,并且努力将这一意识作为全民族的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也涵盖一切的一个前提,一个底线,一个思想文化共识,作为全民族的不仅适用于此时此地、彼时彼地而且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为所有人所“发现”而且也为所有人所“坚信”的终极的世界之“本”、价值之“本”、人生之“本”,并且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也就至关重要。 首先,“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自由起来”。人是生而自由的,每个人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存在的目的本身,因而每个人不但对他自己来说是自己的目的,而且对他者来说也是自己的目的,而绝对不是他者的工具。 所以,当我们面对西方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亚马蒂亚·森的总结时,会感到格外亲切:“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19)当我们面对中国的严复的大声疾呼时,也会由衷赞同:“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20) 其次,“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爱起来”。信仰的直接呈现,众所周知,首先就是爱,马克思在谈到爱的时候,就曾经指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21)而这当然就是“人是目的”的实现。因此,“先爱起来”,就是“先信仰起来”。 最后,“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就是“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美起来”。美,是自由的结晶,也是爱的结晶。美之为美,也无非就是“人是目的”的现身方式、就是“人是目的”的情感显现。而美丑之辨之所以能够与真假之辨、善恶之辨三峰并立,也就恰恰因为它洞开了人类与世界之间联系的根本纽带——“人是目的”。更何况,作为人类理想的最终实现,“人是目的”,其实还更多地只能是作为一种呼唤、一种理想。于是,它不但只有借助于被创造的美好形象才是可能的,而且,也只有在被创造的美好形象中,也才可能把“人是目的”的世界乃至自由的世界、爱的世界直观地呈现出来。 总之,一个“先自由起来的”、“先爱起来”、“先美起来”的人,必定是一个“先信仰起来”的人;一个“先信仰起来”的人,也必定是一个“先自由起来的”、“先爱起来”、“先美起来”的人。 这无疑就是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的破解。 人们常说,真正重要的不应当是河流,而应当是——河床!“人是目的”,以及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自由起来”、“先爱起来”、“先美起来”,就正是这样的“河床”。在此基础上,作为“河流”,“让一部分人在中国先信仰起来”,当然完全是可以预期的。而且,作为“河流”,一个充分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自在生活与发展的“在灵魂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当然也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十二、“一大事姻缘出现于世” 1923年,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道:“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事姻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姻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22) 而熊十力不但把释迦牟尼的出现慧眼独具地称为“一大事因缘出世”;还曾勉励他在当年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弟子唐君毅等人云:“大事姻缘出世,谁不当有此念耶?”(23) 王夫之也曾自题座右铭云:“吾生有事”。(24) 而今,“信仰”,也“为一大事因缘出世”。 因此,“谁不当有此念耶?” 因此,“吾生有事”! 本文所期望的,只是呼唤!倘若更多的人能够因此而意识到“吾生有事”,并毅然直面“信仰”这“一大事因缘出世”;能够因此而意识到必须从自己开始先“有此一念”,并毅然成为在中国大地上“先信仰起来”的那部分人;能够因此而意识到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外,“信仰是生产力的生产力”,而且,在“中国人已经站立起来”之后,“‘人’在中国也要站立起来”;进而,还能够因此而直面中国文化的“信仰困局”,并毅然踏上中华民族的到信仰之路,那么,本文的目的,也就已经达到了。 注释: ①于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②有美国人曾说:我们不怕中国人学习我们的科学与技术,但是却害怕中国人学习我们的《独立宣言》,这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个道理。 ③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译著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④“无神论的唯心主义”,对于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化极为重要。例如,在中国文化与佛教的对话中,为什么因此而生的宗教形态会是禅宗?又为什么因此而生的哲学形态会首推心学?只有从“无神论的唯心主义”出发,才能够彻悟。 ⑤与此相关,还有老子的“慈”、墨子的“兼爱”、庄子的“性命之情”,限于篇幅,对于同样存在着的道家、墨家的宗教向度,本文暂不作讨论。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1页。 ⑦元朝与清朝,两个少数民族的统治是中国文化激剧蜕变的“深水区”。例如,清朝固然编纂了《四库全书》,但是销毁的书籍却是《四库全书》总数的10倍。因此吴晗才会感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遗憾的是,在两者之间的明王朝,就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也是激剧蜕变的276年。 ⑧限于篇幅,这三个方面都只能俟日后另文专门予以讨论。 ⑨张祥龙:《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⑩既然“敬神”的目的是为了“敬人”,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去直接“敬人”?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是不能拒绝宗教精神;可以拒绝信教,但是不能拒绝信仰;可以拒绝神,但是不能拒绝神性。在我的著述中多次讲过的这几句话所表述的,是我从世纪初以来就始终固守的最为核心的信仰建构的思路。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2)参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中的《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熊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4页。 (14)转引自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43-344页。 (15)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宫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6页。 (16)罗素:《心的分析》,贾可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3页。 (14)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18)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2页。 (19)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20)《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2页。 (2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2页。 (23)转引自吴昊《天下无我这般人》,《东方养生》2012年第10期。 (24)转引自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载《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74页。标签: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信仰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基督教论文; 四库全书论文; 宗教论文; 灵魂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