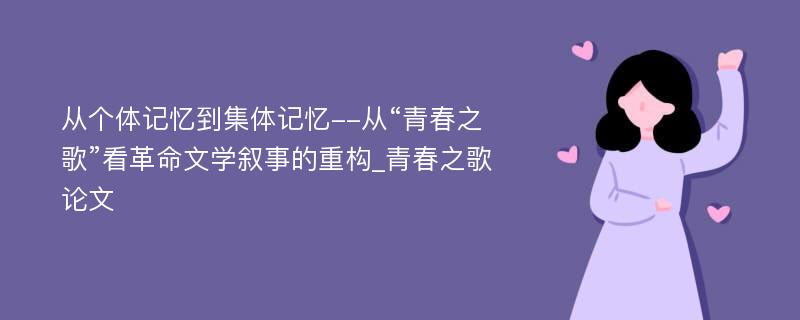
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从《青春之歌》看“革命文学”叙事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之歌论文,重构论文,集体论文,青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春之歌》是一部自传色彩较浓的小说。这不仅因为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故事同杨沫的自传相接近,更重要的是作者将自我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即她的“个人记忆”揉进了她所讲述的故事中。然而,与90年代女性小说不断把个人记忆从集体记忆中剥离出来相反,《青春之歌》是一部经过作者修改,从自我想象到自我否定,将个人生活经验缝合进宏大叙事的文本,它不仅试图陈示个人主义皈依集体主义的必然性,而且极力指证这种必然性的唯一合理性。因此,这部小说不单是一部个人成长史,它更关联着一种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革命文化的实践。
《青春之歌》的重要情节发生在30年代最初几年,背景是1935年北京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故事的一些片断来自当时学生运动中的实事,有些则来自作者的见闻和亲身感受:“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我生活在北京的学生群中。他们中有我的许多朋友。所以,他们当时的苦闷、希望和欢乐我能体会到一些。”[1]更重要的是,从作者的自传中可以了解到,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闪现着作家自己的影子。早年的家庭生活带给杨沫的不是幸福的记忆,而是原始创伤性记忆:父亲是前清举人,靠办教育发了财,长期“花天酒地、嫖妓女,娶姨太太”的生活,使他堕落了,母亲开始还和他吵架,后来也灰心了,不再关心儿女。杨沫17岁那年,为反对母亲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投奔北戴河的兄嫂,但受到冷遇,差一点投海自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结识了一个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并由相爱发展到同居。
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悲剧性家庭故事,有多种语义的可能性,具有多重叙事发展的方向,如,反抗旧家庭、恋父弑父等等,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讲述。在强势意识形态话语笼罩和监控下,杨沫最终选择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重构早年的生活经历,把它写成了一个“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2]的故事。基于此,从一开始,作者笔下自我形象的建构(包括人物经历、心理活动、行为方式等等)是通过虚构不断地朝向某种外在理念认同的过程。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杨沫在林道静的血缘中注入佃农的血统,使其带上了被压迫阶级的烙印,于是作者的个人体验被提升到“普遍性高度”:林道静生母秀尼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揭示了林家的罪恶,隐喻了整个社会的黑暗,从而把林道静对家庭背叛的个人意义转换成对旧中国反抗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也为林道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是一种革命叙事,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以政治意识形态把家庭、个人的不幸和仇恨演化为阶级对抗,并汇入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中,通过个人生活流程与革命斗争历程相一致的概括性想像,叙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这种叙事框架中,零乱、破碎乃至隐秘的个人记忆已被某种文化共同记忆筛选,即把自我融入到“一个固定的、抽象的同一体”[3](P84)中(比如“无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青春之歌》因此而被纳入主流文学。
然而,正如研究者李扬所说:“在叙事的阶段,我们的国家本质尚未真正建立,叙事的意义就在于将各种自然状况组织到话语状况中来。因此,叙事的文本让我们完整地看到这种组织过程的不自然性。无论多么高明的艺术家,在拼装这两个世界时不可能不留下痕迹。”[4]尽管杨沫把自我成长的经历纳入到宏大叙事的框架中给予讲述,但当时及后来的“明眼人”还是敏锐地看到了作品主题的分裂状态,即在成为“革命者”的林道静的身上藏匿着的“小资产阶级”自我及其情调。如果说,《青春之歌》所讲述的是以满足主流思想文化为目的的知识分子奋斗史,那么透过文本的表层,我们却看到了与主题不相和谐的差异和异质。试以林道静与三个男性的关系为例。从某种意义上说,《青春之歌》是一部关于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悲欢离合的,即非常传统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的故事。在第一章,林道静一出场就给人留下冰清玉洁却软弱无力的可爱形象: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萧、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意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置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5](P1)
这段美化自我的矫情描写实在很俗,但却是小说真正具有原始叙述动力和阅读魅力的基本原因——弱女子的无助引来一个或几个陌生男子的帮助,展开一个跌宕起伏、泪眼纷飞、引人入胜的情爱故事。因此,《青春之歌》在当时引起“轰动”,并不完全是政治因素,还有另外一些非政治因素,它满足了读者潜在的心理欲求。
从林道静的生活经历来看,小说是一个十足的“小资”故事。虽然一开始杨沫竭力突出她的悲惨遭遇,但她的生活理想和趣味却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在北戴河寻找表兄不得,险遭小人暗算,欲投海自杀,却被北大读书的“新青年”余永泽救起。余非常爱慕她的美丽和浪漫,而林道静在特殊的情况下也顾不得许多了,况且余永泽还投其所好地用海涅的爱情诗打动了她,此时两人间的印象相当美妙:在林道静的眼里,余是“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在余永泽眼里,林是“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啊”。如果小说就此结束,显然是一个没有什么新鲜感的“才子佳人”的老套路,而且仅停留在“感情戏”阶段,是不可能完成革命文学叙事的任务。“所幸”的是,林道静注定是一个不安分的女性,这使小说获得了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如果林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贤妻良母,小说该怎样发展?)。就在余永泽离开北戴河不久,另一个更为优秀的革命青年卢嘉川进入了她的视野。卢嘉川的冒险、坚毅、果敢的性格以及不俗的外貌(小说中多次用“英俊而健壮”、“多情地”“黑眼睛”描绘卢)反衬余永泽的持重世故,不问政治,埋头读书,甚至几分怯弱。可问题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余不仅先来,而且对她有救命之恩,怎么好背叛他呢?然而,林道静毕竟不甘于“平庸”的日常生活,她要过更为刺激的“革命”生活。于是她用心良苦设计种种摩擦,用“自私”、“不爱国”、“不革命”、“没有阶级感情”指责余永泽,夸大两人间的裂痕和对立。其实,小说中的林道静与卢嘉川的关系已经接近婚外恋,他们每次见面谈“革命道理”根本就经不起推敲。这样余永泽当然要反对,反对则必然在他两人间产生更大的缝隙。卢嘉川的被捕,直接导致两人分手。然而,这还不是这场感情戏的最高潮。林道静在事实上还未获知卢嘉川牺牲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另一个“革命党人”江华的怀抱,她的“小资”式用情不专的感情方式就此昭然于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林与江的感情戏路如同她与卢嘉川的翻版,换句话说,“革命”把林道静的不道德行为合法化了,其情感路上的道德焦虑最终被高于道德伦理的政治理念所克服。
正如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指出的:“与大量的人物相比,功能的数量少得惊人。”[6](P27)《青春之歌》无意中契合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也非常“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因为它的故事讲述是按照中国古典叙述模式来演绎的。对作者来说这可能是她无意中落入了窠臼,但对小说而言,它却得益于这个窠臼——读者真正喜爱和为之激动的原因可能不是别的,正是这种俗套的演绎。然而,无论是“才子佳人”还是“英雄美人”,它们都不具备现实合法性。早在20世纪初,以“才子佳人”为基本模式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因为和启蒙叙事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就遭到“五四”激进知识分子的批判。进入“当代”之后,传统侠义小说中的“英雄”也被具有更高政治道德伦理品格的“时代英雄”所取代。当然,从“英雄”到“革命者”只有一步之遥,即便是草莽英雄也只需稍加装扮就可以,如《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红日》中的石东根、《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等等。《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江华显然不完全是传统小说意义上的“才子”、“草莽英雄”,准确的说,他们应该是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时代英雄”,即现代中国的“革命者”。这种身份使得一场感情戏很自然地被接纳于革命文学的叙事结构、方式、体系之中,从而非常有力地支持了林道静的人生之路和性格成长的合理逻辑,反过来,林道静虽然活动于感情戏中,但由于她的情感世界被植入了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解放的集体革命斗争的崭新内容,因此,小说不仅像传统感情戏(如“鸳鸯蝴蝶派”小说等)那样对读者很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也使杨沫个人性经历和体验升华为政治转喻,或有关政治集体记忆的一个注脚,从而达到革命历史小说的“教谕”目的。(注:林道静的原型是作者杨沫,余永泽的原型是学者张中行。可参阅张中行《流年岁月》第224—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说,《青春之歌》更像一部披着革命叙事外衣的情爱纠葛故事,或者说,是30年代“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也许正因为这样,小说的叙事方式遭到了一些人的尖锐批评。郭开认为,小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表现来进行创造的”,与此相反,小说不仅“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而且也“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思想斗争……”[7]与此同时,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却对小说持肯定意见。他们认为小说描写的内容符合历史事实,“是一部优秀的成功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8],“整个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符合于毛主席的论断的。”[9]肯定的意见在客观上起到了对《青春之歌》及其作者的支持和保护作用,使小说不至于被打入冷宫。今天看来,这场论争虽然本质上并无根本冲突,双方都是站在政治角度、阶级立场谈论作品中传达出的教育意义,但这也表明建国后在革命文学叙事的问题上,文学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在顽强地坚持自30年代以来革命知识分子独有的文学叙事,另一种意见则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企图压制和排斥知识分子话语在社会主义文化空间中的生存。”[10]
为了适应建国后的文化功利目标,杨沫决定对小说进行修改。从1959年9月开始,杨沫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青春之歌》修改完毕。修改工作主要是结合争论中提出的焦点问题进行的:为了突出卢嘉川英勇献身的革命者形象,作者设置了他带领北大学生去南京请愿,与国民党坚决斗争的情节;为了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修订后的《青春之歌》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工作的八章(第二部7—14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第二部34、38、43章);另外,作者还修改了其他一些地方,如戴渝的死、林道静的一些心理活动等。这样,小说由最初的1958年版本30余万字扩充为修订版的40余万字,于1960出版,1961年再版。显然,从叙事的角度看,修改只是手段,重构才是目的。也就是说,《青春之歌》是想重构这样一个叙事方式:林道静从封建家庭中出走,结识余永泽,营建个人小家庭;在共产党人卢嘉川、林红、江华的指引下,思想得以升华,成为共产党员,领导学生运动。这样,一个普通的恋爱故事被置换为走向革命的故事。本来,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方式在晚清以来中国各种文学本文中已司空见惯,但通过与主流话语的刻意结合,就成为证明革命历史选择正确性的一个合法的叙事规则。因此,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林道静是如何由寻求个性解放走向“革命”的,更在于“它呈现了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它负荷着特殊的权威话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投身于党、献身于人民,才有真正的自我的生存与出路(真正的解放)。这并非一种政治潜意识的流露,而是极端自觉的意识形态实践”,[11](P148)对此,作者杨沫也承认:“想通过她——林道静这个人物,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过程,来……表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2]这样,小说就从传统侠义小说、30年代“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剥离出来,成为建国后革命文学叙事中的一个经典代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走向革命的一个范本,它极大地凸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的强烈诉求。
由是而知,“革命文学”叙事重构,不是一个仅仅关联着形式的小问题,更是一个隐含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根本性问题。它昭示了一条从最初革命的思想启蒙者,到跌落为“革命同路人”直至成为“革命对象”的悲剧性历程。这样一个命运的转折所导致的,就是知识者不得不“自愿”放弃自己的知识优越感、叙事方式,转而追求更崇高、更神圣、更纯洁的理想。类似《青春之歌》这样的修改现象在17年时期并不是个别的,像《创业史》(第一部)、《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欧阳海之歌》等这些出版、再版、重版的一批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本都经历了“修改”的命运。当然,这种命运的结果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自虐到受虐,乃至最后发展为集体无意识的过程。《青春之歌》正是知识分子完成了思想改造后,对自己思想改造必由之路的确认并通过个人的心路历程得到确证的一个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无意中书写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