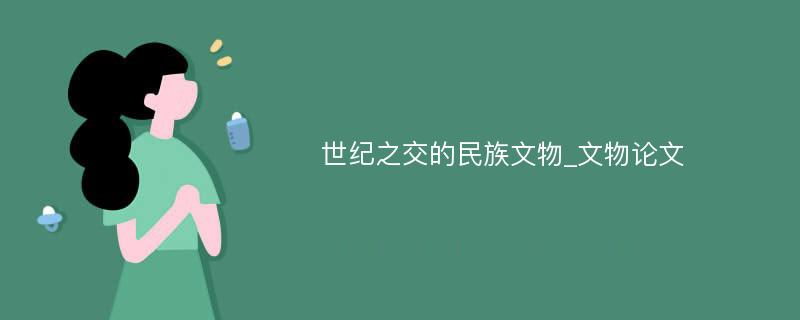
世纪之交的民族文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文物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回顾过去,民族文物工作半喜半忧,留下不少遗憾,展望未来,民族文物肯定是下世纪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世纪之交,更感到抢救民族文物的迫切性。
什么是民族文物?目前争论较多。笔者认为,民族文物是文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民族文物是自民族产生以来,各民族所创造的、具有一定民族文化信息、又有一定历史阶段、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遗物。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态形象,看得见,摸得着,是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遗留下来的文物也具有多民族的内涵,这正是中国文物的重要特色。具体来说,民族文物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指自古而今的民族文物,后者指清代以来或近代民族文物,我所说的抢救民族文物,主要是指后者,因为这类民族文物处于几不管状态,是文物工作的薄弱环节,而古代民族文物早已列入考古文物工作的范畴。
民族文物也具有文物的一般特征,如不可再造、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等。但是近代民族文物有其独具的特点:第一,古代民族文物多埋藏于地下,有地层保护,近代民族文物多裸露于地上,最容易受到损坏;第二,古代民族文物多为无机物,近代民族文物则以有机物质为主,文物保护难度较大;第三,古代民族文物欠完整,近代民族文物较完整、信息量大,不但结构完整、功能明确,还有种种传说;第四,古代民族文物基本为国家所有,近代民族文物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私人所有,这给征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一、从三个实例谈起
1961年夏天,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承担史前史研究和陈列设计,但是再现史前史仅凭考古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于活生生的民族学资料,于是我在六十年代初做了三次比较重要的调查,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
(一)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文物。
1961年夏天,几位著名的史学家赴内蒙古考察,认为民族文物极其珍贵,应该抢救。翦伯赞教授就提出:“将来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新馆时,陈列厅应该设中央走廊,两侧为对应展厅,一侧陈列地下的考古遗物,为‘死化石’,一侧陈列民族文物,为‘活化石’,互相印证,历史就说明白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对上述意见很重视,立刻派我们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族自治旗调查,我在托扎敏居民点生活了两个月,一边调查,一边征集文物。该族以渔猎为生,不知农作,住撮罗子,食肉衣皮,用桦树皮器皿,驾驶桦皮船,信奉萨满教,传统文化依旧,各种文物齐全,我们顺利地征集了一千多件文物(注:兆景:《中国历史博物馆征集一套鄂伦春族文物》,《文物》1962年2期。)。 还随猎人在林海雪原中狩猎。事后又赴黑龙江十八站地区征集数百件鄂伦春文物。在北京举办了《鄂伦春族文物展览》,受到学术界好评。鄂伦春族文物的可贵处,有两点:一是该族为一个狩猎民族,对研究狩猎文化经济类型有重要价值;二是该族在五十年代初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以地缘组成的游牧公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私有观念淡薄,这些对探讨文明时代前夜的历史有重要借鉴。三十年后,1991年初冬,我又二访鄂伦春自治旗,该族社会面貌大改,住砖瓦房,着汉装,种地养猪,连家具也汉化了。如果没人说他们是鄂伦春族,我肯定误认他们为汉族了。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由于汉族只准生一个孩子,鄂伦春族生育不限,不少汉族姑娘嫁给鄂伦春族小伙子,而汉族小伙子也喜欢娶鄂伦春族姑娘,这样有许多鄂伦春族家庭是由鄂、汉两个民族组成的,第二代又随鄂伦春族了。表面看,鄂伦春族人口剧增,其实汉族血统充斥其中。当时该旗建设了一座漂亮的民族博物馆,但文物奇缺,最后只能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借文物,复制展品,甚至有关狩猎生活的照片也都是从博物馆印制的。
(二)西双版纳傣族文物。
1962年,我们又转赴云南西双版纳,当地以傣族为主,还有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克木人和基诺族。五十年代初傣族尚处于封建领主社会,当地的“召片领”,相当于西双版纳的国王,他占有全部土地和农奴,为了进行有效地统治,下设议事厅和各级官吏,还有法律、军事组织,对山区少数民族也有一套统治方法。但贫富分化不严重,故有“穷不讨饭,富不过万”之谚。傣族稻作农业发达,有一套专门的灌溉制度,流行竹制干栏建筑,陶作、竹作、木作发达,还有树皮布、造纸等手工艺,服饰已礼制化,由于使用傣文,文书档案极其丰富。我们调查组,分散在各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共征集一万多件文物。此外,还在澜沧江两岸进行了考古调查,曾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注:宋兆麟:《景洪访古》,《云南日报》1962年11月10日。)。当时西双版纳有一个文物室,收藏大量文书。我们曾组织傣族知识分子复制了大批傣族历史档案和各种政令。后来在北京举办了《西双版纳傣族农奴制文物展览》,由于当时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没开几天就把门关上了,至今未与广大观众见面。事过三十年,即1992年,我第二次到西双版纳采风,当地的民族文物已今非昔比,过去顺手可拾的传统工具、服饰、贝叶经已经不见了,连当地收藏甚丰的文物室也已空空如也,据说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四旧”焚烧了。1992 年该州举行自治州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也举办一个“傣族文物展览”, 居然寻找民族文物无门,其展品基本是从北京和昆明各单位借用的。
(三)泸沽湖摩梭人文物。
1963年,我们又转赴泸沽湖地区。先乘车抵达丽江,从丽江到泸沽湖是步行了11天,日出而行,日没而息,露宿野餐,辛苦异常。但是一踏上泸沽湖的土地就感到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湖周围有三十六个村落,基本为摩梭人,也有少量普米族和纳西族。摩梭人流行走婚,盛行母系家庭,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注: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关于泸沽湖地区母系制的存在,清代已有记载,道光《盐源县志》:“盐源恶习,女多不嫁。”盐源县属四川,位于泸沽湖东岸。1930年庄学本在《良友》“新西康专号”上以《么些》为题,发表摩梭人一组照片,并说明“婚姻尚自由,但一般女子多不嫁,不赘,两性交往极乱。家庭以母系为本位,财产之继承亦为女子,故有女儿国之称。”真正对当地母系制进行调查的,是从60年代初开始的,但当时只注意社会形态、家庭婚姻,对物质文化不够重视,其实,摩梭人在物质文化上也有特点,如以二牛三夫犁地,在湖区以弋射雁,还有井干式民居、独木舟、麻纺、信仰达巴教、喇嘛教。我们在调查摩梭人母系制过程中,也尽力搜集文物。除了美国人罗克外,我可能是第二个到当地搜集民族文物的人,当时文物很多,居民家有,乡政府也有。在开基乡政府的仓库里,堆积不少土司头人的衣服、档案、用品,乡政府正要当垃圾处理,我们一次就征集到几百件文物。又如我去金沙江边托甸乡,搜集到成驮的东巴经、汉规经(普米族巫师),其中的《图语书》、《路票》都是极其珍贵的民放文物。最后我们雇了四十头骡子,才把文物运出泸沽湖。按原计划,我们也想举办一个《泸沽湖摩梭人女儿国文物展览》,因种种原因也被搁浅了,只好把文物闲置起来, 转向案头工作, 先后出版了《永宁纳西族母系制》(文物出版社1983年)、《共妻制与共夫制》(上海三联1989年)等专著。又是30年后,我第四次采访泸沽湖时,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拖拉机取代了二牛抬杠,摩梭人穿上了化纤,传统的麻纺已经成了历史,本来寺院是保存传统文物的安全场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灭顶之灾。总的印象是:摩擦人走婚还在走,传统的文物已经消失了。
以上是我六十年代初征集民族文物的三个地点。当时民族地区生态完好,传统生活基本保留,民族文物丰富多彩,云南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民族博物馆,当时搜集文物应有尽有,不费举手之劳,三十年后再访其地,这些民族已接受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农机、汽车、卡拉OK,也应有尽有,传统生活正在改变,古老的文物制度面临土崩瓦解,征集文物难上加难。头两年昆明建设一座豪华的云南民族博物馆,硬件不错,陈列的文物却有许多新的复制品,这是令人悲哀的。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原因是很多的,有随着社会进步而出现的自然淘汰,有过去极“左”政治运动的摧残,有当前商品经济的冲击,还有缺乏一套抢救、保护民族文物的机制。如在文物管理机构中,人员众多,机构庞杂,就是没有一个民族民俗文物管理机构,甚至一个专职民族文物干部都没有,如此这般,怎么能有效地保护民族文物?其实应该有一套保护民族文物的法规,从法律角度加强民族文物的保护工作。文博界不重视,民族学界也不重视,他们在野外调查时,对民族文物视而不见,见而不识,热衷于研究社会形态,不重视物质文化研究,有少数民族学工作者,连民族文物的基本知识都没有,怎么能研究民族文物呢?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民族学界。当然,有些文博单位有志于征集民族文物,但没有经费,最后还是无法抢救民族文物。
二、抢救任务的繁重性
前面所举的例证,绝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有相当的代表性,也就是说,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类似现象。
应该指出,在社会发展与文物抢救的关系上,我们首先应该肯定社会发展是人类的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原来留下来的文物发生变异、消失,也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历史上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如此。不过,我们应该在这种变革中积极地把文物抢救下来,使上述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为子孙万代留下更多的文物遗产。尤其在当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抢救民族文物更是刻不容缓。
到底有多大抢救任务?这是应该明确的。首先应该肯定,由于我国过去搜集民族文物较少,底子差,现在又很急切,任务是很艰巨的(注:宋兆麟:《民族文物通论》,紫金城出版社1999年。)。
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55个,还有几个未经识别的民族群体。这些少数民族有多少民族文物,应该说底数还不清楚,现在征集到手的民族文物有多少?也无精确的数据。据粗略统计,全国馆藏近代民族文物约20万件左右,而且多为工艺品,不成龙配套,可以说挂一漏万,尚有大量的民族文物没有搜集上来。
搜集近代民族文物,应该有一个目标,总的来说,应该为每个民族搜集几套文物,一套留在地方,一套留在省(区),一套留在中央。这就要有三套,如果加上外出展览的需要,则在三套以上。这是第一笔帐。不过,有许多民族内部又分若干支系,如藏族、蒙古族、台湾土著族、黎族、壮族、瑶族、苗族、布依族、傣族、哈尼族、彝族、纳西族、白族、景颇族等都有这种情况。各个支系不仅有自己的起源传说、风俗习惯,还有自己的文物制度。如果我拿一件苗族衣服请您鉴定,您回答说:“这是苗族衣服”,这只答对了一半,还要回答是什么地区什么支系什么人穿的衣服,因此,民族支系对文物工作极为重要,如同考古学讲究区系类型一样,这是民族文物的基本理论和工作方法。
以苗族而言,据我接触的十几部《百苗图》册页来说,贵州苗族多达数十种支系,该省对苗族服饰进行了普查,共有90种苗族服饰。如果把湖南、广西、海南、云南、四川和重庆等省市苗族统计在内,其服饰不下百种之多(注: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又如彝族的支系也不比苗族支系少,这一点在《滇南夷情汇集》中看得很清楚(注:宋兆麟:《云南民族生活画卷——滇南夷情汇集介绍》,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1期。),这是指云南的彝族,如果把四川、贵州、广西等地的彝族考虑进去,彝族支系也不下百种之多。事实告诉我们,征集民族文物不仅要注意族属,还要重视各支系的文物制度。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的抢救任务就不仅仅是55个少数民族的文物,还应该包括各民族各支系的文物,也就是说,我们的征集对象不是55个单元,可能是300或更多个单元。如每个单元一套文物为1000 件,三套则为300件,300个单元则为90万件。这是第二笔帐。这一估量是可观的,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抢救、收藏90万件民族文物并不为过,甚至应该抢救更多的民族文物。抢救民族文物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这一点已无疑义,问题是如何落实,笔者认为应该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国家应该有专项拨款。在各类文物收购中,民族文物的花费是较低的,因此抢救民族文物未必花很多钱,但是必须当个事业来抓,有专项投入,专款专用,保证收购民族文物的基本经费。其来源可由中央出一部分,省(区)出一部分。云南省花一亿五千万元建一座云南民族博物馆,这是很大气的,也很有远见。常言说“牵牛要牵牛鼻子”。一个省区要牵住“牛”(民族文物),最好的办法是筹备民族博物馆,好象抓住了“牛鼻子”,省里的民族文物就有单位抓了,又有专门的展示和收藏场所,能有利地推动民族文物工作。所以云南民族文物工作开展较好。海南省也是这样的。那么其他民族省份为什么不积极效仿呢?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二是在全国要有一个规划,要有责任制,分片包干。落实到省区,必须为每个民族建一座博物馆,并落实民族文物抢救方案,全国做出抢救规划,分期分批加以完成。必须抓紧、抓紧,再抓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从事抢救还是可行的,还有不少文物可以征集,如果贻误战机,拖拖拉拉,抢救工作就被动了,必然再犯历史性错误,为后人所唾骂!
三是将搜集文物与民族调查结合起来,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这是有形的,比较好抓,可以通过文物认识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但是,伴随民族文物还有许多无形的文化,也应该同时抢救、调查。因此,不能以搜集到文物为满足,还要以民族文物为切入点,进一步调查与文物有关的民族历史文化,征集者应该是调研员,不作采购员。只有这样,民族文物才能得到抢救,为将来研究文物奠定基础。可以说,抢救民族文物,不仅能搜集一大批民族文物,还会造就一大批民族文物专家。
三、目前需要抓好三件事
为了有效地抢救民族文物,有以下问题必须认真研究:
(一)做好民族文物鉴定。
当前,除积极征集民族文物,还应该把现有的馆藏民族文物进行鉴定,否则无法使用,也不知其真正的价值。1995年笔者去三峡考察民族文物,在巴东县文管所看到一大包水陆画,外边贴一张封条,书曰:“迷信文物”,打开一看,画技高超,皆为清代绘制,可列入民族文物,但已经长霉、虫蛀,我问为什么眼巴巴地让这些文物毁坏了呢?管理人员说:“一般文物我们还注意,一听说是迷信文物我们就避而远之了。”事后,我在山西阎锡山老家——河边民俗博物馆也看到一大箱子道教绘画,画技更好,也没有当回事,令人痛心。人类所经历的古代社会,就是一个迷信的时代,很多文物都打上了宗教烙印,包括远古岩画、三大石窟、天坛等建筑,不能因有迷信色彩就打入另册。问题就在于没有进行鉴定。有些专家否认民族文物为文物。个别博物馆曾尝试鉴定民族文物,但因为缺乏明确的鉴定标准,多将民族文物列为等外品或参考品,对民族文物的真正价值把握不住。根据上述情况,应该解决三个问题:
1、民族文物鉴定标准。我们根据一般文物标准鉴定, 还是另外拟订一个民族文物标准,这是可以争论的问题。笔者倾向不另外制定民族文物鉴定标准,但要解决一些具体操作问题,如一片有刻画符号的彩陶片,定为一级文物,而且类似陶片出土数以百计,那么台湾土著民族的鹿皮画,不过只有几件被保留下来,定为几级?藏族的唐卡、佛像、经典,具有多种社会价值,在世界艺术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不比汉族的明清文物逊色,又怎么定级?对此应该认真探索,求得共识。
2、积极探索民族文物研究的理论框架,这是至关重要的。 过去过分用一种理论模式,使民族学研究趋于僵化,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理论探索是每个学者的责任。以民族文物鉴定来说,仅仅根据56个民族的文物特征去鉴定是不够的。严格的说,中国民族的划分,是政治性的,科学意义上说,还应该重视民族支系的研究,事实上,中国有许多民族,内部有很多支系,所以民族文物鉴定应按地区、按支系进行,因为民族文物有明显的地域性、族系性差异,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制度,一个民族内部的不同支系也有不同的文物制度。因而民族文物鉴定操作起来相当困难,能鉴定藏族文物的,未必能鉴定东北民族文物,能鉴定云南民族文物的,到新疆不一定行得通。所以民族文物鉴定专家都有一定局限性,难以成为通才。鉴定时按地区、按支系进行较为适宜,这是民族文物鉴定工作的特殊性。
3、尽快设立民族文物鉴定机构。 国家文物局下设一个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其中设有许多鉴定组,如青铜器、书画、玉器、钱币、陶瓷、杂项等,只有民族文物鉴定未被列入,连“杂项”都不够格。这是一大漏洞,也是很不公平的。其实,民族文物数量大,鉴定难度不小,任务急,应该尽快设立有关鉴定机构,集中专家,把这项工作抓上去,进一步推动民族文物的抢救工作。
(二)民族文物的应用问题。
抢救民族文物,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保护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也就是说要充分应用民族文物。
第一、要积极妥善地发展民族博物馆,这是应用民族文物的最基本渠道。因为民族博物馆不仅是民族文物的收藏场所,也是研究和展示民族文物的中心。七十年代前只有几所民族学院设有民族文物陈列室,没有一座民族博物馆。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博物馆象雨后春笋迅速地发展起来。目前全国已有民族(含民俗)博物馆五六十座,多为州县级的,也有省区级的。说明民族博物馆发展很快。但是问题不少,有的仅挂牌,有名无实,个别省区号称有几十座民族博物馆,伸着巴掌建馆,缺乏拳头式的博物馆,水分大,既缺乏管理人才,也没有业务骨干。笔者认为,应该努力为每个民族建设一座象样的博物馆,重点放在省区、地州两级,有些小民族的博物馆也可建在县上,这些就是重点,决不能遍地开花,县县建博物馆。不要以数量取胜,要集中人才、物力和财力建好重点博物馆,布点一定要合理。
第二,民族文物要开放,更要广泛地为社会服务。现在馆藏民族文物利用率很低,不仅展览少,向社会提供也不积极,有的馆宁可使民族文物不见天日,也不向社会提供,有少数人自己不研究,也不让人家研究,垄断文物资料的现象严重。我年轻时搜集的文物都移交给库房了,这是正常的,但我再进库研究自己搜集的文物就难以上青天,自己只好做其他研究,反正案头工作忙不完。其实,在民族文物保护和使用上,应该解放思想,向社会开门。某些保管制度应该改进,决不允许个人霸占,把活文物变成死文物。
第三,应该关注民族文化村的建设。目前文物部门虽然没钱搜集民族文物,但许多企业家却视民族文化为宝,一窝蜂似的建设民族文化村,作为民族文化的景点,以适应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有成功的,如深圳民族文化村,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很好。有些是失败的,还有些是不死不活。其中有不少问题:首先,有些民族文化村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忽视软件设计,凭一时想象建园,许多设计人员文化素质太低,以想象代替民族文化事实,景点缺乏文化品味,生搬硬套,简陋粗俗,令人看了乏味。其次,不考虑时间、地点和条件,这样难免不出问题。认为深圳民俗文化村成功了,自己也会成功,重复建设,追大求全。北京南口搞了一个“老北京微缩景观”,游客到北京真景都看不完,怎么会到远郊去参观老北京的模型呢?结果是门庭冷落,最后关门了事。第三,单位追求经济效益,有些主持人为了门票效益,歪曲民族文化,假造“民族文物”,如什么图腾柱、生殖崇拜以及令人生畏的人头架,这种做法虽然能有一时的效应,赚到一些门票钱,但他是以低级趣味迎合某种社会需要,因而它是缺乏生命力的,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声誉,伤害了观众,其负面作用不小,产生误导,歪曲了民族的形象,对此我们不能放任不管,应该在软件设计上加以指导,同时在民族文化宣传上进行打假(注:宋兆麟:《民俗博物馆发展的新动向》,《民俗博物馆学刊》1995年1 期。)。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是人造旅游景点必须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二是文化含量要高,追求高品位;三是充分利用高科技;四是要注意综合效益,力争在经济效益、娱乐、教育诸方面都获得成功。
此外,应该从民族文物中吸取营养,进行积极的开发,如旅游产品的制作、服饰艺术的展示和表演等等,都大有文章可做。
(三)民族文物干部的培养。
为了抢救文物,发展民族博物馆事业,开展民族文化旅游,我国需要一大批民族文物专业干部,但是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一方面缺乏有水平的管理人才。从全面形势看,民族文物、博物馆管理人才少,素质相对较低。有些民族博物馆的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馆长水平低,不懂业务,使这些单位死气沉沉,缺乏活力。馆长自己不懂业务,也不放手让业务人员从事研究,于是出现不少业务人员从事第二职业。因此必须迅速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管理人员,不应该把其他单位不称职的干部摊给博物馆,否则民族博物馆难以办好。
另一方面缺乏专业干部。现在民族博物馆不少,但很多博物馆缺乏独挡一面的业务骨干,更缺乏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象藏族文物丰富多彩,内涵博大精深,但我国缺乏唐卡专家, 缺乏藏佛鉴定专家。 笔者1984年在罗马参观东方艺术博物馆,该馆有许多唐卡,但他们也没有进行认真鉴定。该馆馆长请我从中国找几位唐卡鉴定专家,整理鉴定唐卡,但是回国后多方联系,也无人敢于问津,说明国内民族文物专家乏人,反之,西方倒有不少这方面的专家和专著。所以我国急需培养民族文物人才(注:宋兆麟:《加快抢救民族文物的步伐》,《中国博物馆》1998年1期。)。
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已招收民族文物研究生,北京大学也成立了考古文博学院,在高校培养民族文物本科生、研究生,这是一条主要途径,应该加大力度,抓早抓好,但目前高校也缺乏民族文物方面的师资,严重限制了专业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力同文博部门合作,并抓紧民族文物师资的培养。
还有一种方式也很重要,即短期训练班。五十年代初期,基建繁忙,考古人才奇缺,现培养又来不及,当时从在职文物干部中抽调一大批人员,由北京大学举办短期考古培训班。强化考古专业训练,然后分赴各省考古工地。这批学员后来绝大部分都成为各省区考古队伍的骨干,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民族文物专业人才培养也可采取上述方式,每年举办一些民族文物培训班,可按民族分布地区举办,如南方、西南、西北、东北等,分期分批进行。课程要突出民族文物,既要有足够的讲授,又有一定时间的田野实习,操作动手能力要强。这一点与考古学一样,光上课不实习是不行的。民族文物专业也不例外,田野调查是根本的学习和工作方式,是民族文物学的基本功。中外学术史告诉我们,一位有作为的民族学者或民族文物专家,都是从调查找到学术切入点的,必有深厚的田野作业功底。根深才能叶茂。我们应当丢开浮躁,深入到边疆去,认真做好田野调查,为抢救民族文物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