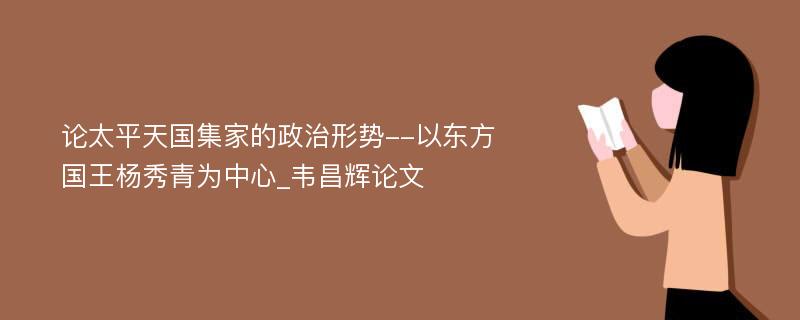
太平天国癸甲政局述论——以东王杨秀清为中心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政局论文,中心论文,王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六朝古都南京。随后,太平天国定都于此,改南京为天京。定都之后的头两年,太平天国的政局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最终形成了基本固定的权力格局。其后,不到两年,这种权力格局就导致了天京事变。因此,定都之后头两年即癸丑年和甲寅年(在天历中为癸好年和甲寅年,简称“癸甲”)的太平天国政局演变,对太平天国前期的发展具有奠基性作用。对此问题,地主阶级文人的各类记载显得扑朔迷离,而学界又迄未有专题成果进行深入的揭示和解剖。笔者不揣谫陋,以东王杨秀清为中心,对太平天国癸甲政局演变的基本轨迹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学界方家。 据张德坚《贼情汇纂》记载,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在“号衣”、“腰牌”、“宫室”、“服饰”、“仪卫舆马”、“诏旨”、“告示”以及老兵地位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①。总体说来,定都之后的最大变化是太平天国政制的变化,即职官有了“内外之分”,或“分朝内、军中、守土为三途”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张德坚分析说:“初贼所破州县,皆掳其财物,残其人民而去,未尝设官据守。自窃占江宁,分兵攻陷各府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伪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监军、总制皆受命于伪朝,为守土官。”③在政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太平天国政局的变动值得关注。政局的变动往往伴随着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或内部权力的斗争。笔者通过研究太平天国的文书机构发现,在定都天京以后的癸好(1853年)、甲寅(1854年)两年中,一些文书机构的服务对象发生着从天王到东王的转移。这就表明太平天国的权力逐渐集中到东王杨秀清身上。 但是,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在记载太平军进攻南京城及定都天京的情形时说:“时贼中凡攻战、守御、黜陟、调遣诸伪政,悉出自伪东王杨秀清。”④张晓秋《粤匪纪略》在介绍洪秀全时说“贼务皆杨秀清主之,秀全受成而已”,在介绍杨秀清时又说“贼务巨细皆专之”,而在介绍韦昌辉时则言其“尊惮杨逆惟谨,无他能也”⑤。该书记太平天国事至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夏止,张晓秋可能是太平天国重要人物衙署的书手,所观察和了解到的情况多是内幕。因此,他所说杨秀清“专”、“主”“贼务”,洪秀全只是“受成”,而韦昌辉“尊惮”杨秀清“惟谨”,应是对太平天国在乙卯年夏之前权力格局的基本反映。从李圭和张晓秋的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从其攻城始至乙卯年夏止一直都没有变化,其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中。 然而,笔者通过仔细阅读太平天国史的相关文献认为,军政大权集中于东王的权力格局是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以后在癸丑、甲寅两年期间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初期的权力格局并非如此,这样的结果是东王杨秀清不断地运用其所掌握的权力资源通过权谋争取来的。对此,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说:“东贼旧托天父下凡以惑众,谓天父之言,藉传于东王金口,兵机政要,皆由天定,人莫得违。及破南省,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⑥太平天国甲寅年正月杨秀清即借天父之口,说自己“为天下万郭军师,大权尽归掌握”⑦。由此看来,杨秀清所掌握的权力资源就是代天父传言,而其所争取的权力就是“兵机政要”的决策权。“兵机”(或“军务”、“军事”)和“政要”(或“政事”)构成了“贼务”的主要内容,或“众权”的核心内容。 李圭所记为太平军攻城时的权力格局,为了适应战事的需要,权力相对集中到东王身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太平军攻克南京以后,奠都天京初期的权力格局是有变化的,总体而言,天王是不管事的,东王主政事,而北王主军事。当时太平天国实行的是虚君制下的军师负责制,早期所任命的四位军师只剩东王、北王,他们各主其事。 关于虚君制,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则说:“至洪秀全自入城后,即督署为巢穴,入焉,加砌高墙,从未一出令人窥见面貌,故从前曾有讹传洪逆本系木偶,并无其人。然该逆在内,或数日出一伪诏,或作一诗发出,贴于照壁……大概杨逆之恶更甚于洪,在逆等以伪称为天王,宜享天福,是事皆不过问,权柄应诿于军师便宜行事,殊不知洪实杨之傀儡也。”⑧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和张德坚《贼情汇纂》中亦有类似的记载⑨。这些记载说明,奠都天京以后的一段时间,洪秀全似乎并不过问世俗的事务。 关于东王主政事,《李秀成自述》中言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初期的情况说:“开立军伍,整立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出城门去者准手力孥,不准担挑。妇女亦同。男与女不得交谈,母子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故癸好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东王令严,军民畏。”⑩ 关于北王主军事,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说“初入城,军事由北贼”,这种情况由当时的望楼系统及其运行可资证明。张汝南介绍北王韦昌辉说:“其居前建望楼,高四五丈,顶为平台,竖旗鸣角即于其上,如某门有兵来,由其门望楼竖方色旗递传至此楼,由此遍传合城,则凡所谓朝官典官悉率馆人来会听令……或派若干人赴某门接战,余或回馆,或在某门左右暂驻听后令。”(11)初期望楼运行使用的是四色旗信号制度,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记载说:“又贼匪初起望楼时,各楼遍贴伪示云:如遇东方兵来,则于楼上麾青旗,南方兵来麾红旗,西方兵来麾白旗,北方兵来麾乌旗,即黑旗;如须城内之兵出城帮同拒敌则麾黄旗。如城外大兵攻急则于旗尾加拖乌布数尺。又于楼上吹螺击鼓,由城外传至城头,由城头串至城内各街巷,以至伪北王红更楼处。伪北王处如须调北门外之兵添赴东门帮同拒敌,则于红更楼上麾黑旗;如调南门之兵赴东门,则麾红旗。其余类推。”(12)不难看出,整个军事指挥系统是以北王为中心的。 东王主政事,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即面对随着政务而来的大量文书,不识字的东王如何处理政务呢?《金陵省难纪略》载杨秀清初入城时,丞相向他禀事情形:“伪丞相入,三跪呼然后起白事。丞相皆广西人,不识字,必携书手入读奏章。东贼自言:‘五岁丧父母,养于伯,失学不识字,兄弟莫笑;但缓读给我听,我自懂得。’故书手往往得见贼与其居。”(13)可以确定的是,张汝南此处所说的“丞相”是指东殿丞相,而所携“书手”即是簿书。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前后,东王、北王、翼王各府设有丞相职,称为诸殿丞相,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介绍东、北殿丞相说:“各一贼,皆广西人,为贼主办文案。”在介绍东、北、翼殿簿书时又说:“不知若干人,两广两湖之贼,归伪东、北丞相所系,亦系写贼文者。”(14)李滨《中兴别记》载:“司伪文檄者曰簿书,伪王以下曰掌书。”(15)佚名《粤逆纪略》亦载:“各书记,伪王府则曰簿书,自伪丞相至指挥,则曰书使,以下则曰文史、办史。”(16)簿书相当于各王府丞相的书记,为级别较高的文秘人员。东殿丞相“主办文案”是由东殿簿书完成的(17)。 东王杨秀清不会满足于与北王各主其事的权力格局。如果能够贬抑天王的威权,那么,控制北王就是轻而易举之事。因此,他不断地贬抑天王的威权。他的这种做法早已开始,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介绍杨秀清即说:“至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与天贼倡乱,渐揽天贼权,自广西至金陵,悉听其指使,故伪谕旨皆署其伪号,天贼尸位而已。”(18)奠都天京以后,天王洪秀全虽不管事,但贵为至尊,其威权仍在。所以,《贼情汇纂》载:“初至江宁,杨逆日朝洪逆所。”(19)而且,在一些重大的场合,天王威权的显示还是很隆重的。这种重大场合,主要是朝会和天台礼拜(20)。事实上,洪秀全也会管理一些世俗的事务。《金陵杂记》介绍照壁时则说:“每于洪逆发伪官黄榜时,其榜即钉于此壁。”(21) 然而,洪秀全的威权和世俗权力常受到东王杨秀清的挑战。《金陵癸甲纪事略》载杨秀清说:“好杀人,必先假天父指出某甲某乙某事当杀,使贼众惊为神,故又自号劝慰师圣神风。杀必请于天贼,然天贼曰杀,东贼必不杀,曰勿杀,东贼必杀之,谓出天父意也。故尝假天父语,杖天贼四十。又杀西贼父、北贼兄及东贼兄杨元清妻,以示威。”(22)张晓秋《粤匪纪略》则较具体地记载说:“杨贼造天父下凡邪说……洪逆曾杀一人,未尝商知杨逆。一日,杨逆作天父下凡语,责洪逆三十板,当欲俯受,以他贼恳情代受之。”(23)此事原委,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详载说:“东贼并托天父挟制洪贼,前有掳来乡愚,娱窥贼居遽杀之,后东贼伪为天父下凡,至洪所谓曰:‘你与兄弟同打江山,何以杀人?不与四弟商议,须重责。’洪跪求,北翼愿代受责,再三始罢。既上奏章云:‘二兄性气太暴,王娘有孕,不宜用靴踢;虽是天父性气本暴,二兄行为果像天父,但须学天父有涵养。幼主性气亦像天父,然小时须教导,不宜由他毁坏物件,怒骂王娘。’”(24) 洪秀全的威权受到更大挑战的也是在重大的场合,如东王朝见之时。《贼情汇纂》载:“秀清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造言既毕,其为君臣如初。”又载杨秀清“每数日必朝洪秀全所,立而不跪,往往据洪秀全之座,诡称天父下凡附体,任伊造言煽惑。自秀全以下,各伪王伪官,皆长跪听受,敷衍毕,仍朝洪秀全,然后归伪第……然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为首,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25)。这就意味着,杨秀清时常利用代天父传言的权力资源,代替洪秀全主持朝事,剥夺了洪秀全主持朝政的权力。 在贬抑天王威权的同时,杨秀清的出行或入朝却盛陈威仪,摆足了威风。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东王出行事,说:“其出也,惟至天贼伪府,或登城,他勿往也。出则贼众千余人,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采鸟兽数十对,继以洋绉五色龙,长约数十丈,行不见人,高丈余,鼓乐从其后,谓之‘东龙’。乐已,大舆至,舆夫五十六名,舆内左右立二童子,拂绳捧茶,谓之仆射,舆后为相,及众贼官等百人从焉。又继以龙如前状焉,行乃毕。”(26)《贼情汇纂》则有更详的记载(27)。如是入朝,快到朝房时的场面如何呢?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则载:“每入朝北翼先候于朝房,未至朝房数十步便驻轿,轿中有二童持扇护贼出,北翼趋接跪于道,贼前掖起之,乃随之行惟谨,两旁又黄伞数柄,拥遮至朝房。洪贼已使二美妇艳妆至,不知向贼云何,贼随美妇至朝门,又出二美妇持扇分护入,其外之伞扇候于门,比出轿直至朝门前,群贼拥之登,北翼复跪送乃各去。”(28) 东王不满足于当时权力格局的进一步行动,就是逐渐地取得对军事的主导权,努力形成与北王共主军事的局面。《贼情汇纂》在介绍韦昌辉时说:“凡军务,群下具禀昌辉、石达开,谓之禀报,昌辉揣度可行,则转禀杨贼,谓之禀奏,杨贼若准,始转奏洪贼,以取伪旨,其实其事已由杨贼施行。凡紧要奏章若无杨贼伪印,洪贼不阅,故一应奏章必先送杨贼盖印,虽昌辉自奏亦不能迳达。”(29)又说:“其所属伪官及分扰各省之剧贼,当封赏遣发时,必颁给杨逆将凭一张,用黄洋绉写好,钤盖双印,准剧贼在外先斩后奏;若无杨逆将凭,而在外杀人者,以故杀论抵。”(30)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亦说:“至是凡欲言于东贼者,必先告之(指北王)为转达焉。”(31)这种格局,在涤浮道人看来,就是“杨秀清、韦昌辉主谋”的格局,所以他的《金陵杂记》即载:“其在省城抗拒官兵,布置党羽,裹胁百姓,分窜各省,并掳掠沿江府县,类皆杨秀清、韦昌辉主谋,秦日纲等附和设计。”(32) 东王、北王共主军务的情形,也反映在两人对武科的重视上。《贼情汇纂》载:“甲寅[癸丑]二月陷江宁省,因佐将乏人,故又开武科,以四月初一日为多试,遍贴伪示,令投考者先期五日赴伪诏命衙报名。届期佐天侯赴教场校阅,先试马上箭五枝,次试步下箭三枝,无后场,技艺当日完场,应试者三百余人,皆各衙牌刀手,取中谷光辉等一百四十七名为武举。十五日韦贼赴教场校阅,谓之会武试,加试马上炮三声,取中刘元合等二百三十余名,为武进士。韦贼因陈贼所取人数过隘,复出伪示,命不中者,亦一体会试。五月初一日杨贼复试于教场,遂奏请洪逆,以刘元合为武状元,职同指挥,谷光辉、周得三为榜眼探花,职同将军,余二百余人皆职同总制。”(33) 虽然军务总体上由杨、韦主谋,但他们在军务上有一定的分工,对此,《金陵杂记》载:北王府“对门谭宅内,系韦逆统下伪承宣官所居,其中高搭红望楼一座”,“每遇官兵攻城时,贼即登此楼顶,日则吹角摇旗,夜则悬灯以传伪令,通城之贼,皆觇此楼之令,先奔至韦贼门前,听候分遣各门拒敌。城中诸首逆遇有分派股匪窜扰各处时,皆杨逆诡谋,在韦逆处传布伪令分遣贼目也”(34)。也就是说,天京城防仍由北王韦昌辉负责,而京外战事则由东王杨秀清主导(前引“将凭”的史料亦表明这一点),韦只是“传布伪令”。然而,韦昌辉负责天京城防的权力在逐渐地受到削弱。一是,从望楼系统来看,城中望楼不全是他派兵看守的,《金陵杂记》反映说:“贼于城中设望楼甚多,通城大街小巷无处不有,可以大街设数望楼,亦有数巷共一楼者,有系伪北王所调各军伪圣兵看守,亦有系附近贼馆派人看守,如官更民更之分别也。”二是,望楼运行的信号制度由四色旗转为九通鼓,但九通鼓制度常常出现问题,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又记载说:“迨后逃散者多,内中人少,又有伪令,定为九通鼓之说云。一闻城外吹角,伪北王处即起鼓,定为一通鼓,各馆伪将使、听使均须起身预备拒敌;二通鼓即须齐至伪北王处听候伪令;三通鼓听伪令分出各门拒敌。又因各馆往往不到,或人数不多,逆等又定为各馆均立一小牌,所有馆中人名,均须开列,一闻角响,即带牌齐至韦逆处,到彼听候按牌查人,短少者即时记名,重斩轻责。”(35) 在东王分取北王军权的同时,北王亦在谋求东王的政务权力,似乎也形成了东王、北王共主政务的格局。《天父下凡诏书二》开始即载“(癸好)十一月二十日是礼拜之辰,北王与顶天侯及丞相等官到东府请安,并议国政事务”(36)。所谓的“并议国政事务”,反映了北王与东王共主政务的基本史实。太平天国的官凭和门牌的形成和格式印证了这一点。关于官凭,《贼情汇纂》载:“癸丑六月,杨逆始议每伪官各予官凭一张,谓之官执照,由韦逆定稿画式,先禀杨贼,后奏洪贼,取伪旨颁行。”每份官执照都有与之相连的底簿,底簿在左,官执照在右,中间骑缝加盖印章。前期官执照“中盖杨逆伪印,于编号骑缝处盖韦逆伪印,半钤照上,半钤底簿”(37)。关于门牌,《贼情汇纂》介绍说:“贼中初无门牌之设,癸丑六月,讹言有官兵混入江宁城,举国若狂,韦贼始倡议设立门牌,逐户编查,以尺许白纸,先书伪官名姓,次列给役之散贼,后列伪年月,钤盖韦贼伪印,印旁编号,以‘天父鸿恩广大无边’八字,每字千号,每贼馆各一张。若门牌无名或未领门牌者,均指为妖杀之。”“乡卒门牌,即照乡官所造家册填写,户各一张,乡民多糊于板上,悬挂门内,庶官兵至便于藏匿,贼如复至,仍可再挂。”(38)从重要性而言,官凭要超过门牌。官凭的形成和格式更能反映当时的权力格局。从官凭形成过程看,东王“始议”而北王“定稿画式”,而从官凭格式看,官凭上盖着两人的大印,都证明了两人共主政务的情形。门牌的使用更具广泛性,虽然由北王“倡议”,上面盖着北王的大印,但门牌以“天父鸿恩广大无边”八字编号,也维护了代天父传言的东王的权威。在太平天国的上上下下昭示了北王、东王共主政务的局面。 当时的门牌具体是由诏书衙管理的。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二》载:“贼令尤严男女之辨,行军所掳,男归男营,军帅统之,妇女则别置后营,粤西老蛮妇统之。至金陵设馆,钤束更甚。行营间有混迹女馆,逐日搜查,立门牌,以馆长出名统其下,月送册伪诏书馆核数,虽粤西老贼,亦不敢乱群肆行强暴,闺秀得恃以自贞。”(39)李滨《中兴别记》和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有与此相似的记载(40)。盖着北王大印的门牌由诏书衙管理,那么,诏书衙对谁负责?没有明确的史料对此回答,但从张继庚叛乱事件的有关记载中不难寻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张邴原金陵内应纪略》载:“君见某守,长揖曰:‘上元禀生张继庚谒见大公祖。’某跼蹐焉。讯状,君厉声曰:某事,劳黄丞相兼旬之神,未供一字,今值大公祖下询,当具以白。某非通官军者,通官军者某悉知之,顾人众,不悉记忆,必调名册,而后可指出。某守白北贼,从之。伪诏书衙,靳不发册,某守曰:就所记者先言之。”(41)这里所载情形,在胡恩燮《患难一家言》中亦有详细记载(42),罗尔纲先生认为张继庚所要的名册即是官册(43)。李滨《中兴别记》卷十三说:“人众不悉记,必欲我言,请许我检册。伪官册掌于伪诏书衙,胡贼白韦贼,调册,掌册者持重不与。”(44)当时北王韦昌辉负责张继庚叛乱案件的审理,他同意审讯者调阅诏书衙管理的官册,而诏书衙的“掌册者”竟能“靳不发册”,“持重不与”,这是为什么呢?这固然有“掌册者”的职业操守在起作用,但也说明韦昌辉对诏书衙并不具有掌控权。在等级苛严的权力体制之下,诏书衙的“掌册者”“持重不与”是有杀身之祸的,因此,“诏书衙靳不发册”应另有相应的权力后盾作支撑。事实上,东王杨秀清对诏书衙有着相当的掌控权,作为一个成立较早的机构,诏书衙的服务对象总体上正在从天王洪秀全向着东王杨秀清转移,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关于诏书衙的对联:“诏出九重天那怕妖魔施毒计,书成一统志岂容狐兔竟横行。”(45)这里的“九重天”是指东王府。在这种情况下,诏书衙没有服从北王的指令而“靳不发册”就是可以理解的。可能后来在东王的允许之下,诏书衙又同意“发册”了,所以,《金陵张炳垣先生举义文存》之卷首《事实》载:“继庚欲剪其心腹死党,使自相屠戮,佯曰:‘我受刑甚惫,不能尽记,得尔官册,则可一一指’。册至,每指一人,贼辄杀之,横尸于东门者三十五人。”(46)由此我们可看出北王、东王之间确实存在着争权夺利的现象。这表明东王、北王共主军务、政务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在由东王、北王各主其事向东王、北王共主军政事务的转变过程中,东王处理军政事务的方式和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太平天国有一套完整的女官制度,凡男性所具有的官职,女官制度中都有相应的官职,如女军师、女丞相等。因此,太平天国也有女簿书的设置。奠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更为严厉地推行男馆女馆制度,初期只有天王、东王、北王、翼王四人享有夫妻团圆的权利,在这些王府中为诸王服务的多为女性,《金陵杂记》载东王府“门外并有大鼓一面,有事无论大小,皆于门前击鼓,内中即有妇女出问”(47)。因此,男性簿书的活动越来越不便,而女簿书的作用便逐渐凸显出来,她们接过了男性簿书曾经从事过的工作。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在介绍杨秀清时说:“贼目禀事,(东贼)交女伪簿书,盖逼取民女通文墨者为之,计数十人,意出东贼,批出女簿书。”(48)关于女簿书,谢介鹤还有专门的记载:“女簿书,东贼逼取民女识字者充之,以代己批判。”然后,他叙述了关于傅善祥和朱九妹的故事。傅善祥本是深受东王宠信的女簿书,因“恃宠骄傲”而被“枷发女馆”,后设法逃走。朱九妹“有姿色,能诗文”,东王颇费周折地从女馆发现,以之代傅善祥充女簿书。她入府后竟以砒霜谋害东王,事泄被杀(49)。经历过傅善祥、朱九妹事件之后,东王当不再实行女簿书制度了。于是东王废簿书,而置六部尚书。实际上,各殿丞相同时被废除。因此,癸丑十月、十一月间,各殿簿书纷纷改职,或升任各殿六部尚书,或升任六官丞相。必须指出的是,那些升任六官丞相的,仍然在原来的王府里从事文书工作。曾水源是“凡东贼事代批代行,每晨见东贼议事者”。罗秘芬是“凡北贼事代批代行、每晨见北贼议事者”。而黄再兴则是“凡翼贼事代批代行、每日见翼贼议事者”(50)。这样,东王府的文书批判权遂由女簿书转到东殿六部尚书和部分六官丞相手中。《贼情汇纂》载:“伪批式,凡禀事由伪丞相拟批送进,准行发出交伪尚书录批粘于首逆头门。”“凡其下具禀奏杨逆阅后发出,交伪丞相拟批,伪尚书誊批,伪侯以次则由所属六部书六部掌书拟批誊批,然所批字不誊于原禀之后。”(51)东王府的议事权亦转到这些人身上,所以,《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说,杨秀清“每日早坐伪殿,伪相一人,伪尚书二人,伪承宣二人,伪指挥二人,以次侍见论贼事”(52)。此处的“伪相”不再是东殿丞相,而是指六官丞相。 从太平天国当时对外交涉的情况亦可看出东王处理政事的机制和权力格局。据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载:“又夷人去岁至省数次,与长毛贼意皆不合,夷人意思甚抗,贼又故作不惧之状,实则真怕。去岁冬初,夷人又两次入城,夷船一到,合城皆惊,入城后夷人与伪丞相等会晤,带有通事,先投一说单……夷官在省,并欲见洪杨两逆,诸贼未肯,夷人语句中大概甚抗,且多讥诮,而斥粤匪之教不真,并有欲见天父之言,是明知贼匪平日欺诈愚人也。迨后夷人开船后,又闻杨逆传伪令唤集伪丞相等商议云:‘夷妖生气回去,恐其再来,欲在大江筑一大坝,拦堵夷船’等语。”(53)东王先是令丞相与“夷人”会晤,后又传令“唤集”丞相“商议”,由此可以说明,一些六官丞相不只是在东王府批判文书,在太平天国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亦得到东王的重用。 东王在废簿书、置尚书的过程中,北王、翼王亦得以设置六部尚书,特别是北王与东王共主军政事务,其设置规格仅次于东王(54),是领导集团实实在在的第三号人物,其地位和势力均不可小视。因此,如何处置北王,则成为东王在集权道路上进一步权谋思考的问题。 洪秀全僻处深宫,足不出户,与其说是他安于当时的权力格局而做出的自觉行为,勿宁说是杨秀清“一切专擅”,逼使他不得不如此的被动选择。杨秀清利用代天父传言的至高权力,随时都能控制住贵为天王的洪秀全。至于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等,则更是在杨秀清的掌控之中,任由拿捏,连石达开在其《自述》中都说:“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55)以石达开的身份道出韦昌辉“屡受其辱”,说明了韦昌辉的当时境遇是异常憋屈的,也更说明了在韦昌辉身上的确还有东王所需要的东西。韦昌辉受辱可举两例:一是体现在甲寅(1854年)三月的水营事件。《贼情汇纂》载此事件说:“甲寅三月韦贼令张子朋上犯湘潭,因封船只,激变水营。杨贼得知,先差亲信之人,赴唐正财所,以好言抚慰,将韦逆重杖数百,张子朋重责一千,并出伪示,晓谕水营,人心始服。”(56)二是体现在甲寅五月韦昌辉带兵外出事。《贼情汇纂》载:“咸丰甲寅五月,杨贼命昌辉上犯湖北,令下多日,杨贼私属群下禀奏挽留,佯作不准,濒行忽改韦俊、黄再兴等。八月复令昌辉赴湖北、安徽,行次采石,杨贼下令调回,改遣石达开往。”(57)《金陵癸甲纪事略》亦载:“甲寅五月,东贼闻湖南及黄河贼为官兵破灭,欲使北贼前往,又恐北贼去而不返,乃以日纲为伪燕王,伪称千岁,天贼又加其伪号为霜师,使代北贼上游之行,去后因[我]红单艇船在三山营上下冲击截杀,乃率众贼急返金陵。”(58)两则史料记载韦昌辉之行的目的地有所不同,方向则基本一致。韦昌辉之行,不只是这些记载,还有韦昌辉发给黄再兴和石凤魁的诫谕为证,他在诫谕中要求黄、石两人分巡湖北各郡县,“遇妖即诛,见民必救”(59)。在韦昌辉已有出行准备的情况下,又改令他人,这不只是视军令为儿戏,更是对身为北王的韦昌辉之挫辱。 在太平天国的权力体系中,自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战死后,仅次于东王地位的就是北王韦昌辉了。“屡受其辱”的韦昌辉如何应对杨秀清的“专擅”呢?《贼情汇纂》载:“昌辉位下杨贼一等,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故杨贼加意防范。”(60)又说:韦昌辉“小有才,为杨秀清所忌,虽封伪王,事杨贼惟谨”。看来,“事杨贼惟谨”,即“阳下之”,是表面现象,“阴欲夺其权”才是韦昌辉的真实目的,“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构成北王应对东王“专擅”的实际策略。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北王由“事杨贼惟谨”发展到“事东贼甚谄”,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也就是说,他将“阳下之”的表面现象做足了文章。《金陵癸甲纪事略》介绍说:“(‘东贼’)舆至(‘北贼’)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北贼’)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其兄忘其名,与东贼妾兄争宅,东贼怒,欲杀其兄,发北贼议罪,(‘北贼’)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61) 从上述引文可知,由于北王韦昌辉“小有才”与“奸诈”,东王杨秀清对他的态度是妒嫉加防范。妒嫉的极端表现就是屡辱其身,而防范的做法则主要是分其权力。防范的实际操作就是将北王的权力转移给地位次于北王的翼王石达开。《金陵癸甲纪事略》又说:“凡贼取物,(北王)请盖其伪印为信。其统下伪相、伪承宣、伪尚书稍有权。其伪参护、伪典舆统下,共约千余人,东贼以此疑忌之,故分其权于翼贼。”(62)在杨秀清心目中,石达开是可以令他稍稍放心的权力棋子。《金陵癸甲纪事略》说石达开“其谄事东贼,与北贼等,东贼藉其资倡乱,亦恕其行事”(63)。《贼情汇纂》则载:“达开铜臭小儿,毫无知识。每见杨贼诡称天父附体造言时,深信不疑,惶悚流汗,尊奉洪杨韦三贼若神明。杨贼喜其诚慤,故屡委以军事。”(64)这样,“屡委(翼王)以军事”的结果,就是东王剥夺了北王的军权,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说,“自翼贼由安庆回,遂委以军事”。《金陵癸甲纪事略》亦载:“贼之打仗,伪令先吹号角齐人,至北贼伪府听令。后又改在翼贼伪府。”(65)与此相应的是,望楼的运行再次发生变化。张汝南对此记载说:“有不可解者,各门距翼楼,远者十余里,近者亦四五里,如某门有兵来,即就近某门之馆,亦须赴翼楼听令,不得径接应某门。其派贼出寇,则于望楼竖黄旗,吹角一次,合城望楼逐渐照式竖旗,亦吹角一次,各馆闻角齐人预备赴会,翼楼角三次则俱齐集听令,倘赴某州某县,即日即行,不准稽滞。”(66)张汝南发出“有不可解者”的疑问,是因为他不知道此时的军权已委于翼王石达开。 重用翼王管辖军务,而翼王倚重的是其岳父夏官正丞相黄玉崑,这种现象似乎也得到东王杨秀清的认可。《贼情汇纂》载,黄玉崑“办理军务,颇合杨贼心计,遂重任之,令伪官自检点以下俱至伊处听令”(67)。对此,《金陵杂记》亦有记载,但稍有不同:“伪夏官丞相黄玉崑先居四条巷,后移居淮清河东首察院……该伪衙同住之贼亦多,有伪检点指挥侍卫等名目,共五六人,此处群贼又称为检点衙……每晚通城各伪官贼目,皆须来此听贼伪令,均在该处起坐听候伪检点衙中传呼方入。定更时皆到,二更后无事各散,逐日如是,即遇风雨亦来,贼谓该处为首逆等理事之所也。”传令之外,黄玉崑似乎还负责出入天京城门凭证的发放,《金陵杂记》又载,“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窜,特是贼于城门稽查甚严,非有贼之伪凭不能出入,其在城外者,尚可设法奔窜,若在城内者,必须借重贼凭。其凭系伪夏官丞相所发,按数月间忽然更换,上盖伪戳,难于假造,各伪职馆中皆有此凭以便出入”(68)。由于军务事繁,黄玉崑办理军务还有副手,《金陵癸甲纪事略》介绍胡海隆时,说他“副黄玉崑理贼营事。及加伪侯,乃以海隆分理贼事,转达伪侯伪王”,在介绍林锡保时,又说他“由伪典硝授伪检点,因海隆事繁,以锡保同理其事”(69)。黄玉崑升封侯爵以后其责权未变,仍然承办军务,所以,他的继任者何震川只得兼办军务。《贼情汇纂》在介绍夏官正丞相何震川时说,他“与(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等删改六经,兼办军务”(70)。 石达开从安庆返回南京以后,杨秀清在委以军务管理的同时,亦令其参与政务管理,政事处理方式再次发生变化。《贼情汇纂》载:“初至江宁,杨逆日朝洪逆所;近则洪杨诸贼深居不出,妄拟垂拱而治,必有大喜庆事,方设朝会。如杨逆有事要见,亦必请伪旨批定日时,大抵午未时居多。”又载:“逮甲寅年贼踞江宁日久,为声色所迷,思无为而治,所有政事悉由伪侯相商议停妥,具禀于石逆,不行则寝其说,行即代杨逆写成伪诰谕,差伪翼参护送杨逆头门,将值日伪尚书挂号讫,击鼓传进,俄顷盖印发出,即由伪东参护送韦逆伪府登簿,再送至石逆处汇齐,由佐天侯发交疏附官分递各处。”(71)《金陵省难纪略》载:“贼伪示多出自东贼,北翼间见,亦或出自西南,洪贼则决无。”(72)与此相应的是,东王告示(亦称诰谕)的承办也形成了一定的程序,这种程序也反映了东王“无为而治”的原则:“一示之成,更易数回,由伪侯定稿,呈于石逆,准行则送伪诏命衙缮写,写成交石逆判朱,送杨逆处盖伪印,转交伪宣诏官发贴。”(73)反映在刑罚上,“其踞江宁,刑人必问供且禀伪侯王,层层转达以取伪旨,洪逆批准,由伪翼王交伪翼殿刑部尚书盖印,赴伪天牢提人屠杀。贼初无此制,是皆江宁充吏胥者为之筹办,其意靡他,亦不过欲缓须臾,乘推问禀奏之时,尚可设法救人耳”(74)。由此看来,政务重心似乎也集中到翼王身上。 从诰谕(东王下行文书及告示均称诰谕)的承办情况来看,所谓的“垂拱而治”或“无为而治”,是让石达开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对外文书的承办亦体现了这一点。甲寅五月,东王以答复并质问英人的诰谕全面宣示了太平天国对内对外的各项政策,重申了太平天国“视天下一家,胞与为怀,万国一体”的理念,并宣布了“万国皆通商”,而“立埠之事,候后方定”的政策(75)。为什么会有东王的这份对外诰谕呢?《金陵癸甲纪事略》载:“五月洋人至,东贼不准入城,乃自入城,书问东贼,言尔我同教,何以尔分男女馆。尔言天父下凡,请问天父肉身木身,可能一见?如此类者数十条。先是癸丑四月,洋人至,入城,东贼媚以银数十万,嘱勿打仗。十一月又至,劝和。东贼怒,洋人遂去。至是乃有此书候东贼。东贼使翼贼与黄玉崑闭户三日,作伪谕答之,不知所言。”(76)不难看出,即便是对外宣示政策的诰谕,石达开和黄玉崑亦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东王剥夺北王军政权力的过程中,北王仍有部分军政权力在手中,做着争权的努力。从有关诰谕承办的史料来看,作为下行文书的诰谕在“分递各处”前有到北王府“登簿”的程序,而作为告示的诰谕则无此程序。从后文所叙的牧马人事件可知,北王尚有较大的刑罚权力,但后来刑罚大权亦交由翼王负责。这些情况反映了北王掌握部分政务权力的实际和政务重心向翼王转移的态势。在军权方面,这种情形同样存在,以对天京城防的管辖权为例,有更明显的表现。《贼情汇纂》载:“甲寅三月,江宁监生吴维棠在城谋为内应,事泄,维棠走免,城内一日十惊,与谋者逃散殆尽……事既未成,维棠又走免,贼恨愈深,将剪发之人屠杀净尽,并令合城之人,无论新贼老贼,俱赴韦正伪王听令,未经剪发者给印据一张……三日又传令验据,无据者立杀之,统计验发验据所杀不下万人。”(77)这说明,北王对天京城防的安全仍负有一定的责任,掌有一部分权力。当然,也许在经历了吴维棠事件后,负责天京城防的权力也转移到石达开和黄玉崑手中。 在东王、北王共主军政事务的权力格局之下,东王将部分军政事务委诸翼王,以分北王之权,但北王手中仍掌握着部分军政权力。这就给人一种太平天国军政事务是由东王、北王、翼王三人共同主导的假象,所以,《贼情汇纂》就说:“其军旅各务,皆杨韦石三逆密计妥协,大事则登伪朝面奏,小事即具伪本章入奏,亦有时事过方奏,或竟不奏者。”又说:“贼巢百务亦皆杨韦石三逆议奏施行,在外贼目大小事件,纤微必禀。”(78)笔者以为,对这些说法,治史者应有正确的认识,应深入考察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细微变化。 当然,迷恋于权力、热衷于“专擅”的东王不会对任何人完全放心,他对翼王也早就有所防范。《金陵癸甲纪事略》载:“癸丑五月,安庆再陷,秋,东贼命翼贼往守,翼贼稍易东贼苛制,皖民少受害,东贼闻,惧其得皖人心,[急]趣之归,调燕贼秦日纲往替。诡言北贼劳心甚,使翼贼代北贼事,藉分北贼权,使翼贼亦不得专制于皖。”(79)《贼情汇纂》亦载,石达开于“癸丑八月奉伪令赴安庆一带安民,十一月回江宁,以伪燕王秦日纲代之”(80)。因此,军务、政务委于翼王石达开也不会持久,随着石达开的军权被剥夺,黄玉崑的军务权力也不复存在,军务大权最后就集中到东王杨秀清的身上。关于这一点,《贼情汇纂》在介绍杨秀清时即说:“属下伪官,惟奏谢恩赏,径达洪秀全,其余军务,悉禀奏秀清,听其裁处转奏,以取伪旨。”(81)与此相应,望楼(更楼)管理的最高点归于杨秀清,张晓秋说:“贼于城上设更楼七十二座,伪侍卫每日稽查,彼此互相考核,如甲到一处更楼,即问乙曾到否;乙到更楼询问,亦如之。问后即开单呈杨逆处,核其勤惰,而加赏罚焉。”(82)这就意味着,在军事上,东王拥有最终的决策权。甲寅年,就岳州战守事宜,翼王石达开给秋官又正丞相曾添养曾有训谕,明确指示说:“弟等在外,俱要事事灵变,加意隄防,如若城池十分难守,弟等可即退赴下游,坚筑营盘,静候东王诰谕遵行,毋得旷误。”(83)就坚守圻州问题,燕王秦日纲给殿右拾叁检点陈玉成的诲谕要求做好士兵的思想工作,并强调说:“其余军务一切,仍宜凛遵东王诰谕而行。”(84)在镇守田家镇并攻取汉阳等处的问题上,关于如何在田家镇安簰置炮,东王都曾给秦日纲有过诰谕,发出明确的指令。他在给国宗韦俊、石凤魁、国相石佐邦等人的诰谕中也强调说:“其余军务一切,俱要凛遵本军师前回颁行诰谕而行可也。”(85)在田家镇之战前后,秦日纲上东王的禀奏也较多,反映了东王统一管辖军务大权的实际。 《贼情汇纂》载:洪秀全“自知诈力不及杨秀清,一切军务皆委之,任其裁决”(86),“一切军务皆由杨逆主裁,仅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与之计议。凡有令则交佐天侯传至检点林锡保、胡海隆处,各伪官日至检点衙听令,虽佐天侯等有时燕见,一月之间亦不过二三次。其一切文书不能面白,故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87)。看来,军务决策权收归东王,能够参与决策的是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二人,而执行权也发生了变化,负责承办的黄玉崑退出了,而转至佐天侯陈承瑢,具体传令的则仍是胡海隆、林锡保。 同样政务权力也逐渐地集中到东王身上,东王府的六部尚书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东殿六部尚书中的李寿春、侯谦芳等人尤其得到东王的重用。《贼情汇纂》介绍李寿春说:“癸丑二月封东殿簿书,嗣改为吏部一尚书,在杨贼头门接发伪文书。杨贼有机密事,皆与寿春及侯谦芳秘计。十月封恩赏丞相。”在介绍侯谦芳时又说:“癸丑二月封伪天朝总宣诏书,职同指挥。七月封恩赏丞相。甲寅三月调为东殿吏部二尚书,杨贼信任之,同恶相济,凡有机密事,皆引谦芳及李寿春计议,权势在韦石二贼之上,伪侯相为之侧目。”(88)“权势在韦石二贼之上”的说法表明了太平天国政务权力结构的又一次变化。张晓秋《粤匪纪略》载,杨秀清“不识字,文案至,人诵而听断焉”(89)。因此,这里所谓的“人诵而听断”应是李寿春、侯谦芳在里面起主导作用了,政务大权最终也集中到东王杨秀清身上。如刑赏大权,《贼情汇纂》介绍杨秀清时说:“贼中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伪东王’)皆专决之,洪逆画诺而已。”(90)再如用人大权,《贼情汇纂》又说:“伪官铨选,不由吏部,所谓天官丞相,仅有其名而已。丞相、检点、指挥皆各举其属,列名具禀,呈于伪北王、翼王,转申于伪东王,伪东王可其议,始会名同奏于洪逆,以取伪旨,榜示于伪朝堂,俾使周知,乃颁给印凭,而授职焉。”(91)为了加强他的政令畅通,杨秀清还完善了文书传递制度,《金陵杂记》载:“从前伪疏附送递文报,并无期限,去夏有伪疏附监军某贼船过桐城宗镇,行劫典铺,掳得银钱,自行表分……随后杨逆等又定为船行上下水日行里数,每船下水顺风定以每日行可以二百四十里,上水顺风日行可百余里,上下水无风各若干里,逆风不行,令各船逐日沿途登簿,每日何风?舟泊何处?行程若干?到省时先在正伪疏附衙查对逐日风簿,不对不收。”(92) 为了防范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也成为东王的权力棋子。秦日纲在太平天国起义酝酿时期就享有很高的地位,只是到永安封王建制后,才仅次于翼王石达开。虽未够得上洪秀全称“胞”的地位,但到定都天京以后,他基本上也享受到了“胞”的待遇,一是洪秀全金龙殿赐宴,二是他得以婚娶并喜得贵子,三是在永安封王之后他最早被封为王。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缘故,秦日纲成为东王防范翼王的棋子。《金陵癸甲纪事略》载秦日纲事说:“(癸丑)十二月,因翼贼得皖人心,加日纲伪号真忠报国顶天侯,使往代翼贼守安庆,少变翼贼所行。然新虏亦二千余人,东贼以此忌之,乃调罗大纲往替。日纲归,东贼分取其统下伪将使等为伪东参护、伪东典舆,以少其众。”(93)由此记载可知,东王在利用秦日纲防范翼王的同时,也防范着秦日纲。这里所言东王“乃调罗大纲往替”的原因,只是秦日纲“新虏亦二千余人”。其实,这说的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应是,秦日纲仍旧沿袭了翼王的政策,而且秦日纲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安庆期间,秦日纲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四年二月初四日,1854年3月2日)发布了一则告示(94)。从告示内容看,秦日纲是萧规曹随,沿袭了翼王石达开的政策。至于秦日纲在安庆期间的影响,《贼情汇纂》载:“俘获伪奏章稿内有增议太平刑律多条,又伪燕王秦日纲所出告示,亦载应斩罪多款,谓之律则。群贼尊奉,又统谓天令,夫令所以驭军,律所以制民而兼制军者也。”(95)为什么利用罗大纲防范秦日纲,在《贼情汇纂》中亦有所反映,张德坚介绍罗大纲说:“甲寅二月调回江宁,令与胡以晃等上犯和庐,三月踞守安庆省,遂扰建德东流等处。”并指出:“罗大纲慓悍机警,贼中号为能者,然因非粤西老贼,功在秦日纲上而不封侯王,心甚怏怏。”(96) 东王的防范,导致了秦日纲一定的离心倾向,他表现得似乎不太听话,《贼情汇纂》载:“癸丑十一月,(秦日纲)代石达开守安庆。甲寅四月,调回江宁,封燕王。杨贼再令北犯,日纲往扰凤阳、庐州一带,不愿北行。禀奏杨贼云:‘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续伪奉旨,仍往安庆抚民,日纲遂遍扰安池各属邑。”(97)因此,在杨秀清看来,对待秦日纲,除防范之外,更要挫其锐气。甲寅四年的牧马人事件,使燕王、翼王倚重的岳丈黄玉崑以及陈承瑢等人都领受了东王的淫威,虽然他们有所不满,但最终都不得不屈服。《金陵癸甲纪事略》载:“甲寅四月,燕贼牧马某甲坐门前见东贼同庚叔未起,东贼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贼,未及问,又送付玉崑,意欲玉崑加杖。玉崑谓既鞭可勿杖,转相劝慰,东贼叔愈怒,推倒玉崑案,诉于东贼,东贼怒,使翼贼拘玉崑,玉崑闻而辞职。伪兴国侯陈承瑢、伪燕王秦日纲闻之亦相率辞职,东贼大怒,锁发北贼杖日纲一百,承镕二百,玉崑三百,某甲五马分尸。玉崑杖后,夜投水救起,削去伪侯为伍,嗣使入翼贼伪府,办理贼事。”(98)《贼情汇纂》记载,甲寅二月,黄玉崑升卫国侯。“三月因事革职,重责数百,交罗苾芬监押,玉崑羞忿,乘间投水,苾芬遣人救之,密不声张。盖贼之伪令,凡自尽遇救,亦必斩首,玉崑与苾芬厚,故待之如此。”(99)黄玉崑因何事被革职,从《金陵癸甲纪事略》的记载找到答案。前文已叙,黄玉崑是翼王石达开的岳丈,翼王倚其处理军政事务,他处理军务还“颇合”东王心意。牧马人事件似乎是由他引起的,如果他顺从东王叔的意愿,枷杖牧马人,就不会引起三人辞职的政坛风波。辞职三人受到杖刑,达到了挫辱燕王的目的,同时还警示了翼王等人,可谓是一石数鸟,使东王的威权得到足够的张扬。 甲寅年,对太平天国来说,最重要的战役是田家镇之战。这年八月,清军围攻武汉,并于下旬攻陷,黄再兴、石凤魁、侯裕宽等人退至田家镇。在武汉危急的情况下,杨秀清令石达开往援,又令秦日纲往湖北一带稽查河道,密拏奸宄。田家镇之战发生在十月,秦日纲指挥此战,但此战以太平军的失败而结束。田家镇之战后,秦日纲退至九江等地,随后又在湖北黄梅与清军激战。黄梅之战后,秦日纲即被调回天京,受到杨秀清的处罚。张晓秋《粤匪纪略》载秦日纲:“咸丰四年冬,领贼众犯田家镇、黄梅县等处,数为我兵剿败。杨逆锁回欲杀之,嗣贬为奴,犹得与闻贼务。”(100)秦日纲受此处分,在一段时间内当较驯顺,不能违逆东王的威权了。 奠都天京以后,整个政局演变的态势就是东王的集权。东王在贬抑天王威权的同时,首则夺北王之权,继则以翼王代北王,以燕王代翼王,又以罗大纲代燕王,最终将所有权力收归自己,显示了东王防范领导集团内部成员的基本轨迹,因此,癸甲年间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也就经历了一个从东王、北王各主其事,到东王、北王共主军政,再到东王分北王军政权力而委诸翼王,最后到东王独专军政大权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国政局常现波谲云诡之态,东王处理军政事务的程序和机制不断地发生相应的变化(从使用东殿丞相和东殿簿书,到宠信东殿女簿书,再到任用东殿尚书和部分六官丞相,再到重用翼王和夏官正丞相黄玉崑,最后到专宠李寿春和侯谦芳),身处政坛中人,其命运也呈一波三折之势,笔者曾以曾水源为例,做过相关专题的探讨(101)。 军务、政务权力都集中到东王杨秀清身上,他以防范为作为掌控领导集团内部成员的手段,而对“群下”,他以两手维持自己的地位:一是“秀清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逻察群下”;二是“阴察有才能可任者,以恩结之”(102)。为此,他应有庞大的为他处理军政事务的具体职能机构,如东殿六部尚书和诏书衙就是这样的机构。关于诏书衙,笔者已有专文研究过,它是一个多职能的机构(103)。如果说诏书衙是东王管理太平天国文教、档案的中心,那么,东殿六部尚书则是东王管理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中枢。关于东殿六部尚书,《贼情汇纂》介绍说:“所属衔系东殿,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每部十二人,共七十二人,主分受伪官禀奏、封赏吏部、钱谷户部,以下类推。如六房所掌,以广西识字义人为之。承宣二十四人,主发号施令……其六部尚书,又各有六部掌书,如胥吏,但冠带而给印,伪东王权重事繁,故属官视他人以倍。”(104)又说:“凡伪王侯丞相检点指挥,有六部尚书、六部书、六部掌书诸名色。其六部尚书所属,又各署六部掌书。六部书、六部掌书又各有掌书书理。惟伪东殿各尚书之掌书,颁给印信,其余掌书书理六曹执事,若吏胥而已。”(105)为使军政事务处理有序,东王府还设有专门的东殿尚书挂号所(106)。 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东王身上,如何继续对待和处置领导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能够更好地防范和掌控他们,就成了东王维持集权必须更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虽可利用代天父传言的权力资源,随时处置他们,但只有在派令外出与安置朝中之间取得平衡才是长久之策。洪秀全深处内宫,并不太多地过问世俗的权力,似不构成太大的威胁,而翼王、燕王早就可以随时派令外出或调令回京,也不易形成过大的势力。令东王担忧的还是北王,他贵为军师,在军师负责制之下,他本应享有大权。让他呆在朝中,他会随时争权,集结势力,成为与东王暗中抗衡的力量;让他外出带兵,他又可能招兵买马,扩大影响,形成以兵力为基础的尾大不掉局面,最终威胁的也是东王的集权。因此,到底是让北王呆在朝中,还是让他外出征战,东王曾有过反复的权衡,也曾有过多次的试探(参见前文关于北王外出带兵事的两则史料)。对北王来说,呆在朝中,他会隐忍图谋。只要有外出带兵的机会,他就会有更大的争权资本。癸甲年间,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一年多之后,这样的机会来了,东王令其统兵赶赴江西战场,他取得了权力资本。有了资本,他才会在天王、东王的较量中站到天王一边而对东王及其势力大开杀戒,并滋生了更大的野心,使天京事变升级,最后也葬送了自己。葬送自己,就是集权者和权力野心家的最终命运。这个规律,无论是对东王,还是对北王来说,都是适用的。 收稿日期 2014—03—12 注释: 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164、175、179、190、217、292页。以下简称“《太平天国》”。 ②③《太平天国》第3册,第106、77页。 ④⑤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47~48页。 ⑥⑧(11)(12)《太平天国》第4册,第702~703、611、711、631~632页。 ⑦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⑨《太平天国》第4册,第651、667页;《太平天国》第3册,第45、192页。 ⑩《太平天国》第2册,第791页。 (13)(14)《太平天国》第4册,第705、620页。 (1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页。 (16)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页。 (17)在定都天京前后,东殿丞相、东殿簿书的任职者见诸记载的并不多。揆诸现存文献,各殿簿书任职的情况为:曾水源于咸丰二年(壬子年)十二月始任东殿簿书、李寿春于咸丰三年(癸丑年)二月始任东殿簿书、李寿晖于咸丰三年(癸丑年)三月始任东殿簿书、卢贤拔于咸丰三年(癸丑年)七月始任东殿簿书、黄启芳于咸丰二年(壬子年)八月在长沙始任北殿簿书(后改为右二簿书)、罗秘芬于咸丰二年(壬子年)十二月始任北殿簿书、刘承芳至江宁始封翼殿簿书。而各殿丞相的任职情况为:东殿丞相二人曾由曾水源与曾钊扬担任过,咸丰三年(癸丑年)四月,曾水源又由检点升职东殿左丞相,曾钊扬也由右掌朝仪升职东殿右丞相,职同检点。北殿丞相一人曾由罗秘芬担任过,咸丰三年(癸丑年)四月,他由北殿簿书升北殿丞相,而翼殿丞相一人则曾由刘承芳担任过,咸丰三年(癸丑年)八月,他由翼殿簿书升翼殿丞相,职同指挥(《太平天国》第3册,第53页、57~60、64、67~68页)。 (18)(21)(22)(24)《太平天国》第4册,第667、627、668、720页。 (19)《太平天国》第3册,第171页。 (20)关于朝会和天台礼拜的盛大场面的记载可参见《太平天国》第3册,第171~172、262页;《太平天国》第4册,第706页。 (23)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第55页。 (25)(27)(29)(30)(33)《太平天国》第3册,第45、46,179~180,48,192,113页。 (26)(28)(31)(32)(34)《太平天国》第4册,第668、715、669、611、628页。 (35)《太平天国》第4册,第631~632页。 (36)《太平天国》第1册,第23页。 (37)(38)(45)《太平天国》第3册,第232,237、241,247页。 (39)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6页。 (40)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6页;《太平天国》第4册,第655页。 (41)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4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3~354页。 (43)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4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89~2691页。 (4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216页。 (46)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4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703~2704页。 (47)(48)(49)(50)(52)(53)《太平天国》第4册,第628、667~668、663、672~673、668、626页。 (51)《太平天国》第3册,第200页。 (54)关于诸殿六部尚书,东殿设72人,北殿设36人,而翼殿只设6人。 (55)《太平天国》第2册,第781页。 (56)(57)(59)(60)(64)《太平天国》第3册,第69、48、195、48、48页。 (58)(61)(62)(63)(65)(66)《太平天国》第4册,第670、669、669、670、658、711页。 (67)(70)(71)(73)(74)《太平天国》第3册,第52,60,171、192,218,266页。 (68)(69)(72)(76)《太平天国》第4册,第630、624,675,712,664页。 (7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9~307页。 (77)(78)(80)(81)(86)(87)《太平天国》第3册,第237,192、202,48,46,45,172页。 (79)《太平天国》第4册,第670页。 (82)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第69页。 (83)(84)(8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76、178、179页。 (88)(90)(91)(95)(96)(97)《太平天国》第3册,第67~68、102、100、227、61、50页。 (89)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第47页。 (92)(93)(98)《太平天国》第4册,第632~633、670、671页。 (94)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99)(102)(104)(106)《太平天国》第3册,第52、46、102、165页。 (100)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第48页。 (101)朱从兵、张蕾:《太平天国前期高层文书人员的命运——以曾水源为中心》,《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 (103)朱从兵:《太平天国诏书衙考辨》,《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00年第2期转载。 (105)朱从兵:《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再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标签:韦昌辉论文; 洪秀全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杨秀清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丞相论文; 军师论文; 太平天国运动论文; 远古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