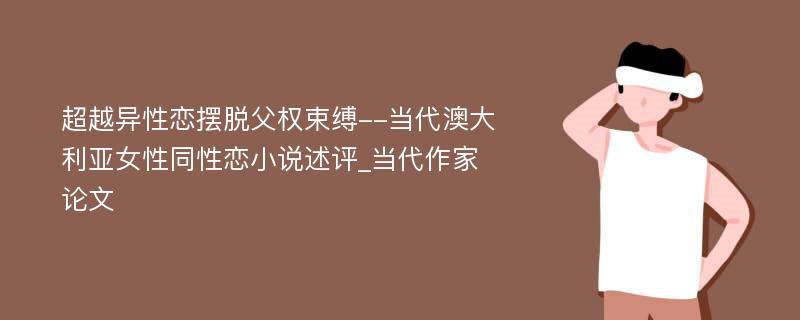
超越异性主义 摆脱男权枷锁——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小说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男权论文,澳大利亚论文,述评论文,枷锁论文,同性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同性恋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法律上赢得了许多权 益,但以异性主义为主导的各国主流社会对同性恋妇女的认识和歧视在很大意义上并未 得到根本的改变,作为一种激进女权主义存在,同性恋妇女在许多国家依然同时面对来 自男权社会和普通女性的疏远和猜疑,所以走出封闭、表现自我成了同性恋妇女无可回 避的迫切任务。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少理论家从严格区分男、女同性恋出发,重新界 定妇女同性恋,一方面批判男同性恋作为极端的厌女主义者的反动倾向,另一方面对妇 女同性恋行为的叛逆意义进行了大力的宣扬;不少妇女同性恋作家拿起笔来展示自己的 真实生活,通过自己的创作,努力向世人展示了迷蒙在神秘面纱背后的女性天地。妇女 同性恋话语的存在值得国内女性文学研究界关注。
一
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表现女性同性友谊和依恋的作品久已有之,但是表现自觉意义 上的妇女同性恋生活的文学至20世纪60~70年代才姗姗来迟。1963年,杰西卡·安德森 (Jessica Anderson)在其出版的处女作《一个普通疯痴》中写了一段同性恋恋情;1966 年,雪利·哈泽德(Shirley Hazzard)在她的小说《了望塔》中表现了一对姐妹因环境 变故而产生的一种生死相依的成年感情;1975年,伊利莎白·莱莉(Elizabeth Riley) 的出版商则明确以“一部女同性恋爱情小说”为副标题出版了她的《那一切虚假的教诲 》。一般认为,20世纪60至70年代出现的公开表现妇女同性恋关系的文学作品,从很大 意义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澳大利亚公众在性问题上逐步走向开放,但是伊恩·麦克尼尔 (Ian MacNeill)认为,从上述作家所表现出的对于妇女同性恋的态度来看,早期妇女同 性恋作家和男同性恋作家一样面对着来自主流社会的巨大压力,因为她们在创作中大多 潜意识地遵从着来自外界或者早已内化了的对于同性恋的审查制度[1](PP4~5)。的确 ,莱莉在出版《那一切虚假的教诲》时回避了自己的真实姓名(Kerryn Higgs)。她认为 ,出版商使用那样耸人听闻的副标题只能使人们怀疑小说的严肃主旨。玛格里特·布拉 德斯托克(Margaret Bradstock)也确信,莱莉在一部表现妇女同性恋生活的小说中其实 更关注的是一种成长中的女权主义意识[2](P45)。
在一个公众舆论对妇女同性恋行为嗤之以鼻的时代,妇女同性恋文学的崛起过程是艰 难的。20世纪70年代中叶,随着全国同性恋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越来越多的妇女 同性恋者从个体的黑暗中走了出来,在她们中间开始形成一种群体意识,文学创作也随 之从个体行为逐步演变成了集团行为,但由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 作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依靠由男同性恋组织创办的通讯、报纸和杂志①来发表自己 的作品,因此早期的妇女同性恋文学时断时续,难以维系。1988年,黑色金合欢出版社 (Black Wattle Press)创办了一个专门登载同性恋的文学杂志,名曰《货物》(Cargo) ,虽然该刊物仍然同时面向男女同性恋作家,但是,自那以后,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作 家毕竟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表园地。在短短数年中,《货物》杂志推出了一大批作家 的小说作品,其中包括前文提到的玛格里特·布拉德斯托克、露易斯·威克林(Louise Wakeling)、简妮·庖赛克(Jenny Pausacker)、戴·布朗(Di Brown)、安杰拉·米斯特 里科(Angela Mysterico)和弗吉尼亚·奥卡里克(Virginia O'Carrick),而正是因为这 样一个作家群的出现,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文学才开始引起批评界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作家群得到了进一步壮大。1989年, 苏珊·霍桑(Susan Hawthorne)等人主持编选了《欲望时刻:澳大利亚女权主义作家笔 下的性与色》。该书收录的三十余部作品中三分之一以上为同性恋作家所作,除了前面 已经提到的作家之外,还收入了罗斯玛丽·琼斯(Rosemary Jones)、菲诺拉·摩尔海德 (Finola Moorhead)、桑德拉·肖特兰德(Sandra Shotlander)、海伦·庖赛克(Helen
Pausacker)、玛丽·法伦(Mary Fallon)和海伦·霍杰曼(Helen Hodgman)等人的作品。 一年之后,苏珊·霍桑再次出击,她与凯西·敦斯福德(Cathie Dunsford)联袂推出一 部专门介绍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妇女同性恋文学的选集《绽放的鸡蛋花》。1991年,“坏 女人”(Wicked Women)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部全面反映澳大利亚同性恋创作的文选《粉 红墨水》。1993年,罗伯塔·斯诺(Roberta Snow)和吉尔·泰勒(Jill Taylor)更明确 以“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小说选”为副标题出版了《为优雅折服》。该书共收录包括季 娜·西恩(Gina Schien)、科斯蒂·马雄(Kirsty Machon)、艾米莉·哈格(Emily Hagg) 、苏珊·汉普顿(Susan Hampton),凯特·奥尼尔(Kate O'Neill)、安娜·塞提奥拉里( Ana Certiorari)、迪格比·邓肯(Digby Duncan)、简妮·尼克松(Jenni Nixon)、菲奥 娜·麦克格里格(Fiona McGregor)、克里姆·布鲁里(Crème Brulee)、林·修斯(Lyn Hughes)、帕米拉·布朗(Pamela Brown)、朱丽·麦克罗新(Julie McCrossin)和艾里森 ·李莎(Alison Lyssa)等在内的27位作家的30部作品。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随着一个 可观的创作队伍的形成,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文学一时蔚为大观。
在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作家中,不少人至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颇有建树,她们有 的在创作比赛中获奖,有的先后推出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集。海伦·庖赛克等人在《疯 狂》(OutRage)举办的全澳同性恋短篇小说创作竞赛中多次胜出,而苏珊·汉普顿和简 ·麦凯米什(Jan McKemmish)等人先后出版小说集,菲诺拉·摩尔海德等人则推出多部 长篇小说,她们的共同努力为妇女同性恋文学进一步拓展了生存空间。
二
澳大利亚批评家丹尼斯·阿尔特曼(Dennis Altman)在一篇题为《属于自己的壁橱》的 文章中指出,从20世纪60~90年代,澳大利亚同性恋小说走过了一个从个人到集体、从 审美到政治的路程。他认为,如果早期同性恋创作更多地把同性恋关系当做一种比喻或 象征来对待,当代同性恋作家的创作以写实为主,它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试图表现自我 的团体意识,它们的宗旨在于团结同类、扩大群体的影响[3](PP30~31)。应该说,阿 尔特曼的这一评论基本上把握了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文学的一种总体特点,一方面 ,作为一个深受主流歧视的团体,妇女同性恋作家在创作中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地记 载自己的生活,在宣传自身的同时教育异性主义者(“除了我们自己,还有谁来表现我 们”);另一方面,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作家大多执着地关注男权政治和异性社会 对于自己的双重压迫,在创作中大多直面周围环境对自身的误解和敌视,公开表达自己 对男权话语和异性主义的批评与蔑视。
直面敌对环境是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小说的一个不变主题。与以往主流文学表现 的那种怯懦形象不同,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公开的叛逆者,她 们坚定地反抗男权社会,抵制异性主义。苏珊·霍桑在一部题为《母亲/女儿》[4](PP4 3~44)的小说中刻画了一个年轻女性拒绝迎合社会对于她的性别定位,虽然母亲不断地 给她施加压力,不断地提醒她做个受人尊敬的淑女,女儿对于这样的社会智慧不以为然 ,她宣布自己不想成为母亲心目中的淑女,先后两次告诉母亲说她不喜欢缝纫,也不喜 欢让自己看上去“温柔娇嫩”。最后,她明确地告诉母亲说她是同性恋,因此她与传统 女性不一样。苏珊·韩普顿的《高个女人》[5](PP90、48)从一个变化的角度让另一个 同性恋妇女公开宣布自己的不同,叙事人告诉读者:那些上过寄宿学校的中产阶级高个 子女人个个治家有道、教子有方,说起话来娇声娇气,而她自己这样的女人从小穿着短 裤长大,长大之后连身体都跟传统女性不一样,虽然原以为晋为人母并无大难,但是, 成年之后发现,连自己也照顾不了,何以抚育后代。
对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文学中的不少女性来说,同性恋是一种天性的觉醒,当然 ,同性恋妇女并非总是天生如此,不少妇女同性恋小说描写女性曾经巨大伤痛之后勇敢 地从异性主义的婚姻中走出来,虽然她们的心中还留着痛,但是当她们最终做出决定之 后,她们对于男权社会同样毫无所惧。季娜·西恩的小说《哲学课》[6](PP182~183) 中的女主人公在发觉自己的婚姻存在严重缺陷之后果断地离开所有男性,并成功地找到 一个同性的恋人。珍·哈里森(Jen Harrison)的小说《伊莉莎白》[7](PP216~219)中 描述的一个成熟女性长期以来都认为自己愿意拥有一个异性的婚姻和一群孩子,她19岁 嫁给了本地一个学物理的男孩,可是,十年之后,丈夫在发现她不能生育之后投入另一 个女人的怀抱,打那以后,行医成了她生活的全部,55岁那年,她决定放弃职业,为自 己在女性中寻找人生伴旅。林达·德门特(Linda Dement)的小说《露的阴部》[8](PP44 ~53)叙述了另一位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受尽折磨之后走向同性恋的遭遇。露生活在一个 蛮横的男权家庭,在她还小的时候,她的兄长为了宣泄对霸道的父亲的仇恨奸污了她, 出于对父亲的愤恨,露在了解了兄长胸中的郁闷之后决定帮助他不惜以自损的方式向父 亲复仇。她要么随意与人发生两性关系,要么离家出走、吸食并倒卖毒品、四处偷窃, 直至被送往劳改学校。长大之后,出于对父亲和兄长的双重憎恨,她变本加厉地随意淫 乱直至意外受孕方使她猛醒,在多年辗转之后,她最终在同性的姐妹那里找到了情感的 救赎。
当代妇女同性恋文学中的主人公们拒绝在世人面前假装异性恋,虽然她们深知西方主 流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排斥,但是,她们大多能够坦然面对世界,哪怕受到排斥或威胁也 无怨无悔。简·普莱奥(Jan Prior)的小说《释放》[9](PP161~167)与林·修斯的小说 《我的两个朋友》[10](PP247~252)分别讲述了一位女性向自己的母亲袒露自我的故事 。在露易斯·威克林的小说《待人而租》[11](PP208~211)中,一位澳大利亚女性在英 国旅行途中不等对方询问就毫不含糊地向房东说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罗斯玛丽·琼斯 的小说《麦吉尔路》[12](PP11~13)描写了身处主流社会异样眼光的包围之中的两个女 性,她们在麦吉尔路上租下一个二楼的斗室,在自己的天地里欢乐嬉戏,过着幸福的生 活;同许多叛逆的同性恋妇女一样,她们对外界(房东和邻居)的猜测不予理会,并不隐 瞒自己的身份,每日里,她们双双将自己的衬裤与胸罩放在窗外的可口可乐牌子上晾晒 ,有时,她们骑在那闪光的广告牌上,或者靠着窗沿做爱,当房东愤愤地将她们赶走的 时候,她们从容地大笑而去,临行前她们将自己的长统丝袜挂在广告牌上,将自己的化 装品盒子丢在浴室里,而梳妆镜上涂满了口红。
当代澳大利亚同性恋妇女作家明白,在异性主义者的眼光中,敢于直面社会的同性恋 者不过是些讨厌男人的变态分子,而要真正通过文学创作来表现自我从而达到教育那些 通行恐惧者,妇女同性恋作家不能回避对于同性恋女性生活、尤其是爱情生活的描绘。 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作家告诉我们,同性恋妇女的感情生活有着和异性恋人一样的激情 和细腻,同异性恋一样,同性恋妇女在她们的情爱当中体验狂喜,也经受巨大的心灵伤 痛。例如,罗伯特·斯诺的小说《用花代言》[13](PP5~6)就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恋爱中 的同性恋女性的狂躁情绪,小说一开始,叙事人深沉地说:“我的爱像……我要给她送 花。”此后,一种无尽的不安和疑惑贯穿于整部小说,她订完了花就开始等待受花人的 回音,她担心对方或许没有收到花,于是由着自己痛苦地沉浸在对于各种可能性的想像 之中。简·穆尔斯通(Jan Moulstone)的《对着贝壳歌唱》[14](PP229~231)是一部近 乎浪漫的爱情小说,在这里,两个都曾经历过“心痛”的女性走到了一起,并在彼此的 关爱中找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情感激动,她们在一个无人的沙滩上紧紧相拥,她们手牵 着手,走进海水,让大海舔开她们曾经的苦难,从海水里出来,她们“对着贝壳歌唱” ,相拥着度过快乐的时光。凯瑟琳·贝特森的小说《我们面对面地游泳》[15](PP20~3 0)刻画了沐浴在同性爱情中的两个快乐女性,她们“身高相仿、体格一般”,两人立在 一处时感觉彼此之间是那样的爱怜,她们同在水中畅游时感到两人之间难分你我,站在 镜前,她们彼此对望,恍惚之间仿佛两人已经融为一体。在这里,同性恋的爱情不仅是 一种可以藉以抚平精神创伤的情感力量,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深刻的心灵寄托和满足。
关于爱情,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小说向人们暗示,同性恋妇女在追求爱情的过程 中与异性主义者一样会经历苦涩和痛苦。例如,苏珊·汉普顿的《妒忌》[16](P92)以 一种近乎寓言的方式表现一位女性在遭遇背叛的痛苦中的挣扎。小说形象地将女性第一 次经历的这种失落比做一种刀刺,而这位受伤的女性以骇人的勇气给自己疗伤。叙事人 告诉我们:“回到家里,她试图将匕首拔出来(显然很疼),但当她真的拔时,她身体里 的一切开始漫溢出来——陈年往事、每一根血管里流出的血、小块的面包。她来到厨房 操作台前用胶脂把伤口粘合起来……”从此以后,她仿佛经过了免疫,她的感情生活再 也没有了痛楚,有的只有平和。
除了背叛带来的绝望,妇女同性恋文学的另一类常见的爱情小说较多地表现失落爱情 之后的伤痛与怀旧,表现此类主题的作品大多感伤昔日的恋人的逝去,表达主人公对记 忆中恋情的深刻怀念。简·穆尔斯通的《在山脊上》[17](PP227~228)以一段独白的形 式记叙了叙事人在极度的悲伤中参加昔日恋人葬礼的经过。站在山坡之上,她静静地追 忆她们曾经共同度过的时光,对失去恋人之后的未来无法展望;她注视着棺椁,不知道 如何能够与亡者隔世相望,她希望看见恋人死后居住的地方,希望听一听生死两界崩裂 时夺去自己恋人的破碎之声;恋人入土时,她绝望地闭上双眼,令她欣慰的是,在她的 感觉中,恋人依然鲜活地站在山脊上微笑。罗斯玛丽·琼斯的《月亮中的女人》[18](P P64~66)中的叙事人讲述了她经历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她从前的恋人“目光怪异但 心地温柔”,她抡起斧头可以劈柴、开车、驾船、骑马、烧饭、养鸭,桩桩在行,但是 ,她心里充满了忧伤,她在梦中流出水晶般的眼泪;她温和又富有激情,她的爱如同舞 蹈,犹如歌唱。
妇女同性恋文学在表现同性爱情时并不像传统作家那样避实就虚,即便是在异性主义 最为关注也最不理解的性爱问题上也毫不掩饰,无所顾忌。例如,简妮·庖赛克的小说 《谈性》[19](PP192~194)安排了一段两位同性恋人之间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她们 谈到了包括自慰、窥视、一夜情和野合在内的许多话题,这对恋人毫不羞涩地着力突显 妇女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差别。苏珊·霍桑的《组合》[20](PP43~45)以白描手法叙 述了另一对同性恋人的性爱过程,玛丽·法伦的《趁热打铁》[21](PP139~144)运用一 系列真实和形而上的意象从不同角度描写妇女同性恋的性爱游戏,两部小说都极力渲染 了同性恋人之间的性爱给她们带来的快乐与满足。当然,妇女同性恋文学表现的性爱快 乐并不只源自性的接触,在梅里莉·默斯(Merrilee Moss)的《一样性感》[22](PP132 ~137)中,叙事人批判了传统男权社会对性的界定,因为在女性看来,不光身体的接触 可以算作性,许多非肉体的接触也可以给人带来性的快感,在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最性 感的体验随处都可以经历,它可以是一个随意的抓挠或者呵刺,它可以在卧室里,也可 以沙滩上或者丛林中,它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因此,对女性来说,独 卧一处同样可以感受性。戴安·布朗的《那好性感》[23](PP92~93)为上述界定提供了 一个极其有力的注解。小说《那好性感》中的叙事人告诉我们说,她觉得穿在身上的T 恤接触肌肤并被磨破的感觉颇为性感,而女性酒吧中的狂舞也同样给自己带来性的快乐 :“音乐在轰鸣……我们跳跃着、滑动着,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像鳗鱼一样游在一处 。她在游。她在笑。我也是……我们连碰也没碰到对方。我已觉高潮将至。”
三
在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学传统中,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女性人物一般被刻画成被动无能的 失败主义者,她们通常出现在诸如监狱、学校、医院一类的环境中,在秘密的环境中, 她们过着不为人知的“变态”生活。与这种情形相比,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文学显 然光明了许多。当代妇女同性恋文学至少从三个方面充分表现了同性恋妇女的生存状态 ,首先,当代同性恋妇女勇敢挑战男权传统权威,她们直面异性主义话语,抵制来自各 方面的压力,笑傲敌意的社会;其次,当代同性恋妇女体验着与异性主义者一样丰富的 爱情生活;第三,同性恋妇女从全新的性爱观出发体验丰富的性的冲动。通过上述三方 面的生活经验,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文学明确告诉我们,妇女同性恋文学首先是女 权主义的文学,它与人们想像中的颓废糜烂生活方式毫不相干。
当代澳大利亚妇女同性恋文学在反对男权压迫的问题上体现了一种极端的策略,这种 策略鼓励女性勇敢地抛弃对于异性主义的幻想,而接受一种全新的女性同性交往模式, 同性恋妇女主张以激进的分离主义彻底解决女权主义运动提出的众多问题。在妇女同性 恋作家的笔下,异性的婚姻给女性带来无尽的痛苦,由蛮横男权控制着的异性家庭常常 给人带来摧残,而走出异性主义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女性的世界里,虽然难免 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里有的更多的是美好的情感寄托和可靠的精神依靠;妇 女同性恋者也谈性爱,但是,她们对于性的界定同样超越了一般异性主义者的理解,她 们认为,性的感觉不仅存在于两个肉体的接触当中,同性恋妇女在生命的任何时空当中 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或体会到性的快乐,换句话说,摆脱了男权的枷锁,女性的生活无 处不给人带来激情与满足。
众所周知,20世纪的西方妇女同性恋运动与女权主义运动原本同出一源,但是,二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严格的分歧,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它们对于异性主义的不同态 度上:女权主义者反对性别歧视,而妇女同性恋者在蔑视男权的同时坚决抵制传统社会 强加于所有女性的异性婚恋制度,虽然二者都要求妇女解放,但是彼此在对待异性主义 的不同立场一度使妇女同性恋者与西方主流女权主义水火不容。1965年,美国著名女权 主义学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她的《女人性神话》一书中认为,女权运动 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而激进的同性恋主义损坏了女权运动的声誉,所 以女权运动反对同性恋行为[24](P45)。20世纪70年代之后,妇女同性恋者针对男权主 义和主流女权主义同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美国,以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理论家先后撰文指出,同性恋妇女都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 与普通女性面对同样的外部压迫,她们同所有女性一样同样面临着自我解放的任务,其 不同之处在于她们在谋求自我解放过程中处理两性关系的激进方式。她认为,所有女性 都生活在一个广义的“同性链”上,不管她们是否认同同性恋,寻求自我解放使她们的 生活或多或少都带有同性恋的性质。里奇认为,妇女同性恋者长期以来受到来自包括女 性在内的各方排斥,其原因是,人们想当然地在妇女同性恋者与男性同性恋者之间划等 号,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同性恋妇女首先是反抗男权压迫的女性,在这一点上,她们 与男同性恋者有着根本的差别[24](PP49~50)。
澳大利亚同性恋文学批评家加里·邓恩(Gary Dunne)指出,除了一些表面的相似之外 ,当代澳大利亚的妇女同性恋文学与男性同性恋文学之间鲜有相通之处,而导致这种差 异的原因是,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男女同性恋者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存在严重的分歧 [25](P299)。社会学家邓妮斯·汤普森(Denise Thompson)认为,在澳大利亚同性恋运 动史上存在一个“秘而不宣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由男性主导的同性恋运动自觉不 自觉地将妇女同性恋排除在外[26](P55)。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澳大利 亚妇女同性恋运动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希望融入到男性主导的同性恋运动当中,作为激 进的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妇女对于男性同性恋行为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她们强烈呼吁 在同性恋运动中面向女性所面临的独特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迈克尔·赫利(Michael Hurley)不无遗憾地指出,作为当代澳大利亚的一种亚文化, 同性恋运动与土著人的地权运动差不多同时出现,但是,相比之下,土著运动在社会上 得到的支持比同性恋者多得多[27](P59)。同许多男同性恋批评家一样,赫利对于男女 同性恋没有作出应有的区分,相反,他把作为女权主义一部分的妇女同性恋运动同样置 于主流大众的批判审视之下,他的呼吁很难说能赢得多少共鸣。笔者认为,把妇女同性 恋从当代澳大利亚同性恋运动中区分出来,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妇女同性恋文学的独 特个性。例如,我们注意到,除了妇女同性恋文学的主题特征之外,当代澳大利亚妇女 同性恋在政治和道德上表现出更明显的颠覆性和严肃性,在写作手段上更加倾向自觉的 文学实验,这与男同性恋文学喜用现实主义和自嘲式幽默等创作手法相比形成了鲜明的 反差。为什么妇女同性恋文学会出现这种先锋性的特征?如果我们把妇女同性恋文学置 于当代女权主义的大语境当中审视,那么,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不难找到:当代澳大利 亚妇女同性恋作家选择了激进女权主义,那就意味着她们同时选择了一种具有战斗性的 反叛话语;她们深知语言与权利的关系,为了推翻男权控制,对男权话语进行大胆刻意 的改造和颠覆便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