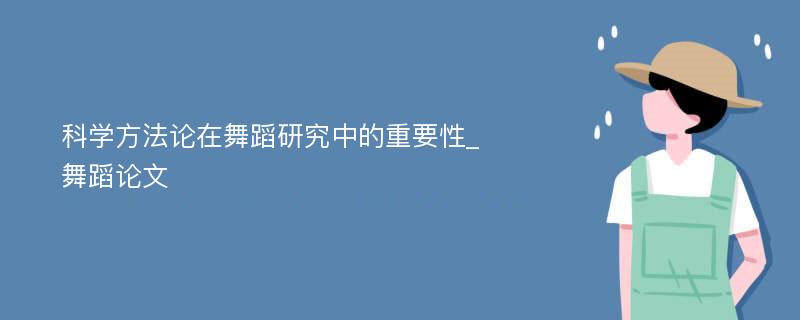
科学方法论对舞蹈研究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重要性论文,舞蹈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有幸做了资华筠老师的硕士研究生,也由此与舞蹈生态学结下不解之缘。三年的学习紧张又艰辛,有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也有些是岁月永难磨灭的。回首这几年的学习和生活,有两点让我感念颇深。一是做资老师的研究生很难,但却让你受益匪浅,导师的严格和不允许工作中出现任何可能避免的瑕疵的近乎“苛刻”的一贯作风,曾给许多与她共事过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作为她的学生,这其中的感受自然又深一层。二是舞蹈生态学追求科学、实证与系统、综合的方法论,和致力于更符合舞蹈本体特质的研究原则与研究方法,对自己理论思维的磨砺和深刻影响。这两方面在我对黄淮地域的汉族民间舞考察中,以及硕士论文“黄淮花鼓秧歌与安徽花鼓灯的同源新辨”的整个写作中体会得尤为强烈。
(一)
提起汉族民间舞,秧歌、花鼓可谓妇孺皆知,它们是汉族民间的两大体系。从地理分布上,两者呈明显的南北播布状:南方各地流行的花鼓、花灯、采茶,溯其渊源,大多与“凤阳花鼓”的传统有关,因而它们同属于花鼓的体系;秧歌则主要在北方地区流行,其中以晋、陕、豫、鲁、冀及东北较为集中和有代表性。所谓“南灯北歌”,正是人们对汉族民间舞这两大体系的总体概括。因此,廓清秧歌和花鼓的渊源与流变,将有助于从整体上考察汉族民族民间舞的历史脉络和主体框架。
然而,纵观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包括民间歌舞在内的民间艺术大都缺乏文字记载,千百年来它们主要以口传身授的方式在民间生生灭灭自然传衍;另一方面,由于秧歌、花鼓在历史上的联系与交融,它们在各地的广泛流布与影响,以及与相关播布区内其它歌舞之间的同化与被同化,形成了秧歌和花鼓错综交织的流变关系。对于这样复杂而又带有全局性的舞蹈文化现象,若仅有笼统的考察与比较,研究很难深入,且往往流于泛论;过于注重细部的考据和缺乏思维方法上的系统与联系,则又常常使研究陷入“见树不见林”的状况。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对舞蹈理论——尤其方法论的探索提出了新的课题。舞蹈生态学,把舞蹈作为人类文化行为的组成部分,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高度来考察舞蹈的民族文化特性,并由此建立的新的理论和系统方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保证。我们可以从某个局部和中观层次入手,由局部问题的解决逐渐达成对整体的把握。关于这点,我的导师曾形象地喻之为“切西瓜”和“剥橘皮”的方式。即以特定地域和具体的舞蹈(种)为对象,运用舞蹈生态学提出的“形态分析”和“历史文化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相关舞蹈(种)的形态、功能、源流及播布进行多维的研究,追溯其历史渊源,勾勒其流变轨迹。在对一系列相关舞(蹈)种的多维考察之后,我们将有可能最终确立起舞蹈源流的进化谱系。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我选择了“黄淮花鼓秧歌”作为考察对象。
黄河中游西起河南的济源、孟县,东至长垣、安阳、濮阳、风丘等豫东北一线,以及属于淮河水系的上蔡、项城、新蔡、平舆等豫东南大片地区,分布着一系列名称各异——花鼓、打花鼓、秧歌、捻伞、火伞——但却有明显共同特征的歌舞秧歌(以下简称“花鼓秧歌”)。“花鼓秧歌”与同一播布区内的其它秧歌和舞具相类的其它舞蹈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追溯其原初形态会发现,它们与淮河流域的花鼓灯具有渊源上的联系,明末清初盛极一时的“凤阳花鼓”是这两种舞蹈的同源母体。然而,由于彼此不同的舞蹈生态环境,这些渊源上原本相同的舞蹈,在日后长久的流变中渐渐拉大距离,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淮河流域传统的花鼓歌舞,经历史上凤阳人的流浪卖艺传入黄河沿线,并受当地秧歌的影响和同化,逐渐形成今日的“花鼓秧歌”。因此,对黄淮地域“花鼓秧歌”历史渊源的考察和演变轨迹的追溯,就有了超越这一特定对象的特殊意义:它将从一个具体的层面让我们看到秧歌与花鼓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有可能成为秧歌与花鼓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必要的案头准备之后, 笔者带着上述问题, 于1994年两度赴黄淮地域进行实地考察(类似人类学所说的“田野调查”FIELD STUDY)。
(二)
1994年初春首次赴河南。出郑州往南经新郑、长葛、鄢陵、西华、周口,直插豫东南方向。车在公路上急驶,举目望去,春雪初霁将晴未晴的旷野几乎没有行人。极偶尔有一辆汽车迎面驶来,擦身而过,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尤其衬出大地的寂静与寥廓。民谚曰:破五动火,初六不行初七行。这些习俗当地恪守至今,因此,春节头几天里这一带的乡村很少有城里那种熙熙攘攘的热闹。
在项城、鹿邑、上蔡、平舆等豫东南一带的调查中,除走访民间艺人,考察“花鼓秧歌”的历史沿革和文化背景外,还具体运用舞蹈生态学的相关原理和方法,对“花鼓秧歌”进行了“舞目类群”的分析与分类。整个工作大致分为两步:先从众多的“花鼓秧歌”中选择出十个典型的舞目作样本;再运用舞蹈生态学的“动作特征提取”法,从这些舞目样本中提取出典型的“舞畴”,并对之进行形态特征的归纳和综合分析。整个考察仅仅是研究的“入口”,但笔者却深深感到,舞蹈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对舞蹈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指导作用。
譬如,在动作分析上,舞蹈生态学强调精确性与模糊度辨证统一的原则,定型、定值与定序结合的方法。根据这样的原则与方法,我们通过对各种步伐性舞畴的归纳分析,找到了“花鼓秧歌”的步伐上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就是“秧歌步”为主导步伐和体现为“走步”的形态特征。步伐的长度单位和某些表面形式虽有不同,但经过还原简化后可看到它们在结构上具有同样的性质,这就是时域上二拍子的原型节奏和空域上左右交替的单步子结构。“秧歌步”形态上的走步特征和功能上的实用性质,都直接源于秧歌舞蹈“跑场”的表现需要。
又譬如,舞具有与动作之关系历来为舞蹈者所重视,但两者之间复杂的制约与互动关系,却是以往研究很难深入的;而舞具作为舞蹈特殊的“生态项”,对舞蹈文化生态分析的意义与价值,在舞蹈生态学以前,则更是缺乏理论与方法上的自觉。舞蹈生态学“因子分解”和“综合分析”的可操作性方法,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难道。我们的具体作法是:划分舞具类型,并由此观察不同舞具对动作形态的不同影响。花鼓秧歌的舞具有两类:1.响器类——花鼓小锣(镲);2.非响器类——扇巾绸。响器类舞具花鼓小锣,是与“挎鼓执锣”的原初形式相对应的原型舞具。在被考察的舞目中,一部分经历了、或正经历着由花鼓动小锣向扇巾绸的变迁,但仍有约三分之一还保留着相对原初的形态。即便已发生变化的舞目,经过形态分析仍能发现原型舞具在动作中留下的某些痕迹。通过将两类舞具及其动作形态的对比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横向地看到舞具对动作的制约和影响,还纵向地勾勒出伴随舞具变更而来的“花鼓秧歌”动作形态上的流变轨迹。
在舞蹈(种)的历史源流考辩中,舞蹈生态学除了强调舞蹈形态的核心——动作的分析和比较外,对舞蹈的组织结构、角色关系及表演方式也给予充分重视。因为结构和表演方式有时是比动作更稳定的因素,不仅可追溯舞蹈的原初形态,而且可以由此考察其原初功能,它们往往比动作本身更有价值。
“花鼓秧歌”的基本角色有三类:作为领舞的“伞”和构成群舞的“男角”与“女角”。此三类角色之间存在着内在形式上的逻辑关系,这关系包含两个递进的层次。1.“群—群”关系,由男、女角双方构成;男女之间天然对立的属性,使群舞内部只具有性别差异而没有个性区别。因此,无论男、女角在人数上如何增减,其角色关系的性质不会改变。独立于群舞之外的“伞”与之构成第二层关系,即领—群关系。领—群关系中的对立在性质上不同于前者,它是一种纯形式的对立。“领”相对于“群”而生,没有“群”是无所谓“领”的。借助逻辑我们可作如是推断:“花鼓秧歌”中作为领舞的“伞”产生于男、女角之后,是伴随其群体化发展而出现的;在领舞之“伞”出现以前的男角与女角应是一种“两小”形式,也即一锣一鼓的歌舞表演。而这,正是历史上“凤阳花鼓”的形式。
诚如舞蹈生态学所指出的:仅有舞蹈形态的分析和研究还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因为任何舞蹈的形成、发展和消亡都离不开它的历史文化环境。所以,在形态分析的基础上,还必须对与舞蹈相关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也即舞蹈的文化生态环境做更深入的考察。
比如,音乐、歌词作为舞蹈重要的“生态项”,在舞种的历史考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花鼓秧歌”中有些歌词同历史上的“凤阳歌”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前者显然是后者的变体。而有的关系则比较隐晦,但通过对相关社会背景和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仍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例如,“花鼓秧歌”和“凤阳花鼓”中都有不少吟唱“小脚”的歌词。凤阳历史上还流行过一首《恨大脚》的“凤阳歌”,歌名因江南人嘲笑凤阳艺人脚大而起。凤阳女素有“大脚婆”之称,下田劳作的传统习俗和为糊口被迫卖艺乞讨的苦难历史,在以小脚为女性理想的年代,却让心酸备尝的凤阳女连裹脚的“资本”都没有。于是,“大脚”不仅成了凤阳女在那个年代的特殊标志,它还留在了“凤阳花鼓”里,成为其中一个被反复吟咏的典型主题。此外,从“花鼓秧歌”的锣鼓音乐中也可以看到它与“凤阳花鼓”的历史联系。
在实地考查和大量参阅方志、典籍的基础上,我们还结合“凤阳花鼓”的流传年代和历史上凤阳人穿州走府打花鼓卖艺的社会文化现象,探讨了“花鼓秧歌”的形成年代和历史过程,多方面论述和应证了“花鼓秧歌”与“凤阳花鼓”的渊源关系。
(三)
实地考察和论文形成的过程,也是我对舞蹈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中间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经历了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巨大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砺。整个过程中,我的导师始终给予了我最充分的支持和最严格的要求。导师的思想方法和治学态度,也同时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记得1996年全国花鼓灯研讨会前夕(这次与我的论文有关的难得机会也是导师多方努力为我争取来的),导师要求我向大会提交一篇论文。一周后的一个早晨,我怀揣着写就的论文兴冲冲去见导师,满心想得到导师的肯定和夸奖,因为我对自己在文中的某些新观点正暗暗得意。不料导师看后对我的文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告诫我华而不实的文章,生吞活剥地滥用新术语堆砌新概念的做法是学术研究之大忌。要求我学会用朴素的语言阐述学述观点,不要唬人、吓人。对这些我当时还不能完全想通,后来在研讨会上,当听到诸位花鼓灯专家平实、中肯和言之有据的发言时,我才为自己当初的肤浅和浮躁而汗颜。当我把感受告诉导师后,她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某些论文占有材料虽丰富,却因方法论的不足造成的缺欠……我为有这样的导师而庆幸。正是靠了这种严格,我才顺利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辨,我的论文也得到了答辩委员会诸位学者的较高评价。
考察舞蹈(种)的渊源与流变,不仅是民间舞的一个基本课题,它同时也是舞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舞蹈特殊的存在与传播方式,以及长期以来缺乏有效记录手段的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使得对舞蹈(种)的历史形态及演进过程的考察,一直是舞史研究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舞蹈生态学从强调对舞蹈本体物质的研究原则与立场出发,建立起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开拓了新的思路。本文只是初步运用舞蹈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对特定舞蹈之渊源与流变的具体考察,但研究实践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方法论上的突破,必然给舞蹈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与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