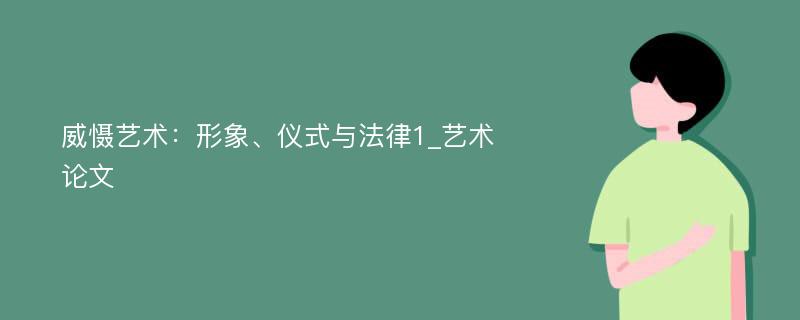
威慑艺术:形象、仪式与“法”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仪式论文,形象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214(2006)04—0034—10
过去十多年来,文艺学者增强了对于艺术人类学的兴趣,而书店里显眼的地方,也增多了写有“艺术人类学”字样的书籍。
什么是艺术人类学?
我是外行,对它备感生疏。为了给自己解惑,我翻阅相关著作,看到人类学界推崇多年的“田野工作”已深入人心,也看到在概念的跨学科传播中,我们面对着不少令人感叹的问题。对于艺术人类学,我们依旧还在寻找清晰的定义。大家也许会同意,艺术人类学指的是采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艺术。可是,什么是人类学方法呢?这些书要么语焉莫详,要么笼统论之,说它要求艺术研究者走出书斋,走入“田野”,这一出一入,为的是在摸得着看得见的乡间观察一般人民(主要包括乡民和少数民族)的文艺活动(像过去的“群众路线”说的一样)。雄心大点的作者则不满足于此,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够,因为艺术人类学的宗旨在于将艺术当成文化来研究,解析其社会性。
有不少朋友从文艺学或一般人类学转向艺术人类学,我常与他们相聚于饭桌茶座边,有不少机会向他们讨教。
朋友们对于国内现行的艺术人类学论述,也隐晦地表达出某种担忧。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年轻朋友说,这些论著停留于堆砌材料,对材料缺乏解释,对于西方新近的理论更缺乏结合——比如,对于替代了“集体表象”理论的“实践论”,他们便一无所知。另一个朋友没有在海外受系统的学术训练,但对国际“行情”了如指掌,他谦逊地说,文艺学界所做的艺术人类学对于主流的人类学是有启发的。我问:这又作何解释?他说:人类学界的艺术研究停留于“艺术文本的社会解读”,而艺术家出自天然的敏感,时常质疑人类学家的“结构—整体论”,他们能告诉我们,社会中还是存在创造力超乎常人的艺术家个人的。从艺术家眼中的艺术家个体,倒过来思考我们研究的人类学,我的那位朋友触及到了个体的“能动性”问题。他说,人类学界研究艺术的人,应当向文艺学界学习,学习他们那种对于文化物的个体创造者的注视。
文艺学家之所以借助人类学概念,是因为他们以为这门学科能使他们洞察到艺术的个体创造者之外的“社会”、“文化”对于艺术的影响;而科班的艺术人类学家则反其道而行之,认定文艺学家原来做的事儿是正当的——学者还是需要“解读文本”,还是需要承认个体艺术家的创造性(据我所知,无论是“实践”,还是“能动性”,都主要出自法国“后现代”,二者本来也是在说同一件事。“异曲同工”兴许能解释不同朋友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来的事实)。他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使我产生这样的困惑——到底是文艺学家需要向人类学家学习“社会论”,还是反过来,人类学家应当向文艺学家学习“个体能动论”?
知识界的现状把我弄得有点糊涂,而人在迷糊时,总会选择用武断的态度来拯救自己的心灵。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武断地断定,无论专家怎么说,理解艺术的社会性都应是艺术人类学家首先要做的事——至少在他们运用“实践”、“能动”这些概念之前,有必要先试试看“社会”、“文化”的观点。然而,从人类学那里借来社会或文化概念的文艺学家,有一种怪怪的倾向——他们倾向于将“社会”或“文化”简单化为某种固定化的“空间实体”。比如,一位专门研究艺术的社会性的专家就告诉我,诸如民间演戏这样的“乡民艺术活动”之社会性,在于戏是在一个“文化空间”里演出的。这个“文化空间”到底是什么?我不怎么热爱“空间”这个概念,我感到它有可能将具有活生生内涵的文化“归纳”成某种硬邦邦的“虚体”。我不反对运用“空间理论”来研究文艺现象,但我猜想,我们若是那么做,那一定会忽略活生生的文化。我总怀疑,文艺活动的社会性,相对于“空间”这个概念形容的东西,本来该来得灵活。所谓“社会性”,是使个体凝结为整体的观念形态,它可能包含知识,但其道德的因素总占上风,因为只有这样,所谓的“人人(仁)关系”才可能形成。
艺术人类学家中,有不少研究乡村(包括少数民族乡村)戏剧的,对于这些同仁来说,所谓“艺术的社会性”极其易于把握。在中国乡村看戏,我们看出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与“社会性”的演化进程息息相关。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都市里的“现代人”来说,戏大抵都要在戏院里演出(即使是在广场上演出,那也要将广场弄成临时性的“露天戏院”)。我们对于专门化表演场所的规定,体现着现代文化、现代社会的特征。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若是没有在远离生活的场合里展示,便如同失去了它的艺术性。我们似乎给了艺术某种“神圣性”,期待艺术从一个新的角度、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超脱我们的生活。这种被赋予的新的“神圣性”,是有其内在精神的。不过,这个“精神”,已不同于古代的神灵——特别在如今的中国,它必须与神灵无关才算正确。
相比而言,在现代艺术表现形态出台于历史之前,艺术并没有脱离神灵,甚至必须与之有关。
为了说明变化,让我从例子开始。我在闽南乡村做了多年调查,发现戏曲这种东西面临着一种遭际。我们的文化部门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推陈出新”,用财力支撑着剧团(如梨园剧团、高甲剧团、木偶剧团等等)。这些剧团只有在文化部门举办“文艺展演活动”时才有正式演出机会,平日没有戏演,它们必定存在生存危机,为了求得生存,它们不得已到乡村去演出,像上个世纪50年代“戏曲改革”以前那样,在乡间寻找生计。不少剧团下乡,不是为了去“慰问农民”,而是受乡村庙宇之约聘,去村庙前“娱神”。为了谋求生路,剧团派出“营销人员”,如同人类学家那样关注戏剧的“地方性知识”,细致入微地了解各地仪式日程,将之整理出来,形成地方庙宇庆典的日程表。剧团根据这个日程表,去联络庙会的组织者,跟他们形成“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易关系。在调查期间,我搭了他们的便车,看到人类学家一般都爱看的民间仪式。村庙前的戏本不是演给人看的,而是为了对于神佛表达感恩而安排的。在神佛的诞辰庆典上,村戏是“娱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村戏“娱神”,并不意味着村民不看它,他们也看,而且看的时候特别投入,边看边谈,边看边娱乐(如打牌、喝酒),将艺术与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村庙的“非政府组织”(庙管理委员会)通过在其“治理领域”征收神灵诞辰庆典经费,每年能得到数万、数十万,以至上百万的经费。演一场戏,要上千元人民币。戏是在村庙前,对着村庙内的神像演出的。观众为了看戏,只好坐在庙宇与戏台之间。在演戏之夜,神、人、戏成了“三合一”的“共同体”,相互之间不相分离。对于村民来说,神灵平日表现出的“灵验”,若是没有其诞辰庆典的“热闹”来证实,那便是空洞的;人平日生活中对于群体生活的期待,若没有庙会庆典提供的机会和场合来表达,那便是不现实的;戏台平日虽很不起眼儿,有的看起来甚至无非是个简陋的土堆,若没有被人和神观望、被戏剧充实的时刻,那便缺乏任何生气。总之,村庄里的演戏活动,不像我们现代都市的同类活动那样,疏离于生活世界之外。
剧团下乡的旅程,也是一个历史的旅程,这种历史跟史学家理解的历史不同,它的方向是逆时间的,它从现在迈向过去,从现代回归传统。参与到这个旅程中,我们能生动地体会到“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差异。
格罗塞在其《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说到不同于现代艺术的“原始艺术”,他说:
原始民族的大半艺术作品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而常同时想使它在实际的目的上有用,而且后者往往还是主要的动机,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格罗塞,1984:234)
艺术人类学家若将我们在乡间观察到的艺术,与我们在城里见到的艺术完全对照看待,那可能就会引出格罗塞的“功能解释”,而这种解释因否定了“原始人”和“乡民”的“审美欲望”,而具有某种值得批判的现代式武断。
为了避免犯格罗塞式的错误,我们最好不必对于艺术的城乡之别进行过多诠释,而将注意力集中于所谓“乡民艺术”。
研究村戏的学者,易于关注乡间演戏与乡间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从一个角度看,村戏是村落仪式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那些专门从事表演的剧团,平日可能是区分于乡村生活的,而在仪式之日,它们被一种交换的模式纳入了乡村。对于所谓“民间仪式”中的演戏活动进行研究,学者已通过细致入微的描述,呈现出它们的“宗教内涵”。我所能补充的是,就我的观察,演出活动与仪式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背后是有另一个层次、另一种力量在维持着的。这个层次,这个力量,在闽南乡村表现为仪式专家(特别是民间道士)将演出规定为仪式表演的必要点缀的做法上。
在我花了不少时间研究的溪村村庙庆典上,来自外村的、远近有名的道士根据自己拥有的道教经典来表演。在庆典举办之前,他们指挥当地村民在庙的内外立坛(祭祀空间)。接着的所有仪式,可以说都是在道士的带动下进行的。道士诵读一套套经书,因时而动,声嘶力竭,手舞足蹈,召唤着天地人神的合一。他们的表演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将神兵天将、地方神、道教神,以至帝国的正祀召唤而来,使之形成内外之分,使兵将在庙宇之外的空地上驻扎下来,在道士的号角声中演示着他们的力量,使天神和地方神进入庙宇,同管辖村子的村神一起过生日。如为了研究道教而成为道士的欧洲人类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所言,道士科仪的表演,为的是将庙宇区隔出其他空间,使之成为一种与神灵有关的“时空圈子”,(Kristofer Schipper,1982:48—54)。根据道教经典的规定,在特定的仪式时刻演奏音乐、唱颂歌谣、“以身作则”,使他们诵读的经书与他们的“行为艺术”完美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地方戏剧团被道士安排演出一系列剧目,有的戏与帝王将相有关,有的戏与伦理道德有关,而同样重要的是,演出这些剧目之后,在规定的时刻,演员被要求打扮成八仙,他们徐徐进入庙宇,一一向村神行礼。
村庙庆典的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研究艺术人类学的学者,若是要完整地用我们的“科学语言”来再现仪式可能是梦想。于我,艺术人类学家若是要研究这样的表演,兴许须同时关注以下难以同时呈现的“事实”:
1.仪式专家运用的科仪经典的内容;
2.被诵读出来的科仪经典之具体呈现方式,及与特定仪式的时间安排和空间布置之间的关系;
3.科仪表演与道士的音乐、舞蹈表演之间的“节奏对应关系”;
4.仪式专家表演的仪式,内容上表现的天、地、人、神“混融”于庙宇的面貌;
5.不同阶段的仪式表演,针对的仪式从请神到送神之间过渡的具体作用;
6.由专业剧团表演的戏剧,与仪式专家表演的科仪经典仪式之间的配合关系;
7.仪式专家与专业剧团表演,得到的庙会“头领组织”(由一般村民选举组成)与一般村民的配合。
清单还可以接着罗列下去,但到此似乎已能呈现出“乡民艺术”丰富的社会内涵。
在乡村,研究诸如演戏之类的艺术的社会内涵,人类学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有的人可以学习特纳(Victor Turner),如他那样, 将表演(如仪式)区分出日常生活之外,将其定义为超越日常时间的神圣时间,关注其与人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分化、 地位差异、 等级差异之间的不同点。有的人则可以学习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如他那样,将其看成社会生活本身,“戏演人生”。 在艺术活动内部,我们透视出社会的基本精神面貌——特别是社会中的力量观念。无论如何,走进乡间的艺术人类学家承受着一个历史负担,他们须在如此混杂的仪式中,一面埋头理出头绪,一面致力于再现仪式的多重组合。
从乡间的庙会,艺术人类学家能够透视出“艺术的社会性”得到实现的具体过程。而“社会”是什么?为了对其作解释,艺术人类学家需要关注到乡间演戏活动的“混融状态”,因为兴许恰是这种“混融状态”本身,在构成所谓的“社会”。
在乡间调查期间,我发现村民对于全村的仪式态度十分配合,个个生怕参与其中的机会从自己的身边溜过去。他们的态度,与艺术人类学应关注的另一层次的问题有关:仪式对于作为仪式主体的人有严格的要求。在仪式过程中,人们生怕自己的“行为越轨”,比如,在仪式表演期间,不做该做的事,不说该说的话,或反之,做了被认定为不该做的事,说了被认定为不该说的话。对于仪式中“行为越轨”的制裁,是众人的谴责(如怒目视之),而众人的谴责之所以常能奏效,除了因为它自身带有的“集体强制力”之外,还因为它与某种恐惧感联系在一起。至少在闽南乡村,人们总在害怕,如果自己在仪式中“行为越轨”,那便可能要承受鬼神为惩罚不端之人而施加的不幸。我们现代人所谓的“艺术”,被认为是不应带有这种神人合一的幸与不幸的观念的。然而,在我们研究的乡间,这种观念却深入人心,以一个生动的方式论证着列维—斯特劳斯用“看”、“听”、“读”三个字概括出来的艺术所具有的与自然、习俗及超自然紧密相关的品质。艺术人类学家关注的“艺术”与种种观念紧密结合,自身带有某种“威慑力”
。这一点,我们能从村庙祭祀活动中人们对于仪式规则的配合态度看出,也可以从神的形象看出。我们民间的神,形象有面善和面恶之别;面善的神与面恶的神在庙宇中往往“相互配合”,形成对人的“软硬兼施”的制约力。比如,我研究的溪村,村庙中就有面目凶恶的法主公,这个神之所以面目凶恶,据传是因为面对妖魔鬼怪怒气冲天。但在法主公的身边,还供奉着面目清秀如同文人的保生大帝,这个起源于邻近地区的神,本是医神(传说他在宋代还曾为皇后治疗乳疾)。在闽南地区的许多庙里,神有生杀之别,主生者,面容慈祥,主杀者,面目狰狞。我们说“旧社会”“神权”盛行,什么是“神权”?它就是神的这种生杀之权。神的生杀,与善恶有关。神灵的“性格类别”,相应于人的善恶感而存在。凶神恶煞的神,是惩治恶的力量;慈祥万般的神,是旌表善的力量。
对于艺术作品敏感的艺术人类学家会注意到,上面所说的善恶,在艺术中的表现是极其丰富的。戏剧中的故事是表现的一种,而我们在庙宇中去研究民间雕塑作品一样也能发现,对于我们所谓的“乡民”而言,美术是善恶故事的另一版本。我并不是说艺术是社会中伦理制度的工具,而不过是说,艺术以自己的方式,传递、表达、塑造社会的善恶观念。
为了说明问题,让我再举个例子。
在溪村的日子里,我常去村外寻访大庙。我去大庙参观,本非出于自愿。田野工作之初,在当地文史界前辈的引领下,我踩了点。受英国人类学的熏陶,我的研究方法还是社会人类学式的:我想做的,是根据村庄内部结构的综合研究,书写一部民族志作品。我急于迁入村庄居住。然而,地方文史界的前辈对于我的计划表现出不解。他们说,不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村里,更认为一个小小村子,不能算“典型”;他们认定,我需要了解的,不是那些穷乡僻壤的土农民,而是更大区域里的历史文化。为了与这些地方文化人保持良好关系,我才听从他们的指示,跟随他们去了许多古迹参观。我们所到之处,除了找庙,还是找庙,而县城不仅是“区位中心”,也是庙宇的集中地。于是,那里成了我们常去的地方。
对于溪村所属的安溪县的县城,宋儒朱熹曾于《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诗中形容说:
县郭四依山,清流下如驶。
居民烟火少,市列无行次。
岚阴常在午,阳景犹氛翳。
向夕悲风多,游子不惶寐。
……
如今,安溪县城居民烟火市井皆已繁华,但站在远处观望,人们仍可看得到朱熹当年目睹的情景。而站在县城空旷之地往北看去,我们看见凤山,在凤山山麓上,我们看见群庙宇式建筑涌出画面。金黄色的砖瓦构成它们的外观。这种颜色在闽南地区四处可见,它与绿色的丘陵相互辉映,使景色充满生机,绝无朱熹感叹的凄凉。在那片庙宇建筑里,有一座庙叫“城隍庙”。田野工作期间,地方文史界前辈曾带我进过这座庙,称那庙起源于唐代,是中国最古老的城隍庙之一。对于他们的“文化地方主义”,我有排斥之心。后来,我数次巧妙地逃脱了他们带我进庙的计划。田野工作结束后,我的书写也多集中于村庄,避免谈那大庙。然而,这些年来我有“逆反心理”,对村庄民族志越来越觉得腻烦。于是,我开始想念那些地方文史界前辈,他们带我去的大庙也不断从我脑海中涌现出来。我开始怀疑,地方文史界的前辈对于社会人类学方法的隐晦抵制实属合理。我也越来越相信,对于那些村子以外的“文化空间”的研究,意味比较浓厚——城隍庙便是如此。
城隍庙原先位于城区东部,1941年,国民党兵团派兵进驻,城隍老爷正身及副身被迫迁出,在民舍中奉祀;1990年华侨捐助重修城隍庙,择定凤山为址,两年后,庙宇竣工,城隍老爷神像才回到他的府邸。
明嘉靖版及清乾隆版《县志》没有城隍庙的内部空间结构图,但在其《城图》中,都在险要位置画出了城隍庙外貌。从《城图》看,古代县衙位于城市中轴线偏西北,而衙门外偏东处即有学宫、城隍庙等建筑。县衙建筑规模略大于城隍庙,在内部,组织相对简朴。从《县治图》看,衙门过了“门头”,进入仪门,右侧有礼、户、吏三部,左侧有工、刑、兵三部。往里走进入琴堂(左右有存放户册档案的库房和赞政厅)。再往里走,进入后堂和县衙。衙门的东西庭院有粮仓,而管理盐政的办公室位于庭院西部。
在县志中找不到城隍庙的布局图。不过,旧城隍庙建筑如今尚存,被政府充为实验小学校舍。从外观看,庙为宫殿式,五进四天井,规模宏大:
一进:戏台、古井、榕树;
二进:兵马与黑白无常,左厢稽查司、考功司、赏善司,右厢速报司、典狱司、罚恶司;
三进:正殿,城隍镇殿神像及副身;东厢,大钟、直符使者、护法韦驮、阳判官;西厢,大鼓、值日使者、主簿、阴判官;前含拜亭,后连寝宫;
四进:“城隍妈厅”,城隍与城隍夫人塑像;
五进:僧舍。
安溪城隍庙内的神像雕塑群是令我难忘的物件。这些美术作品出自艺术界的无名之辈。雕塑这些作品的艺术家没有在作品上留名,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然而,他们的美术作品,实在具有比我们看到的装腔作势的艺术品大得多的震撼力。初进城隍庙,我感到极端惊异。一进门,左右两侧,立着“黑白无常”,俗称“八爷”、“九爷”,他们一黑一白,据说是冥界专司勾摄生魂的“勾魂鬼”,黑无常一身全黑,帽子上写着“见吾即死”,白无常一身全白,帽子上写着“见吾生财”。黑白无常一矮一高、一胖一瘦,是对搭档,黑的严肃、可怕,白的嬉笑怒骂,相对幽默。他们受冥司之托,出来捉拿坏阴魂。我往左侧走进去,见有稽查、考功、赏善三司,再从右侧绕出来,见有速报、典狱、罚恶三司。左善右恶,“八爷”、“九爷”后面的这些阴间“政府部门”,分别负责对好的阴魂的表扬与对坏的阴魂的惩罚。进入庙宇的正殿,我看见城隍老爷被左右一群“副官”(如主簿、判官、值日、阴司、阳司)围绕着,他们各司其职,城隍老爷自己被叫做“显佑伯主”,是安溪县城的保护神,他老人家面目慈善,稍显棕褐色(据说是因香火旺而被熏出来的),端坐于神座之上,南面而视。
城隍庙是作为衙门的附属建筑营造起来的,如德国艺术史家雷德侯眼中的中国《地狱图》,城隍庙也是“有着难以胜计的众多衙署各司其职、协同合作而令人敬畏的模式体系”(雷德侯,2005:221)。不过, 城隍老爷在朝廷设计的品级制度上地位远高于县令,他身着皇帝钦赐的龙袍(据说他给宋代皇后医治乳疾而得到这个特殊的“礼物”),被封为伯爵,其“王宫”、属下的部门设置和等级远高于县衙之上。凌驾于县衙之上的城隍庙作为宗教式的权力,在朝廷礼仪部门的巧妙安排下,超越了衙门代表的地方行政权力。
听当地人说,城隍老爷是古代安溪人发现的。有一夜,县城外的蓝溪上有个闪光点顺溪流而下,人们看见了,知道那是神在显灵,就前去查看,结果发现,是一块有神的形象的木头在河上漂流,于是,他们将它供奉起来,后来,这块木头,就成了城隍老爷。据地方史料记载,这座庙宇确已有上千年历史,据传它建于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到明初,已历尽数百个春秋。明初, 朱元璋规定全国各地的州县都要重新改革城隍庙制度,下令将各地城隍的形象除去,代之以木主,并对官办城隍庙重新进行“内部装修”,加进些个朝廷解释的“礼法”内容。据明嘉靖版《安溪县志》,洪武三年封天下府城隍“监察司民成灵公”,县城隍“监察司民显佑伯”。不久,他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而后悔,于是,“诏革封号”,下令“止称‘城隍之神’”。当时,安溪无城池,因而,上头并没有硬要当地政府耗费钱财营造城隍庙,那里的城隍庙是由当地士绅倡建的(后来在维修时政府才出面)。县志的作者承认,安溪城隍庙是因为民间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神灵“庙以祀之,人道以处之”,实质是“沿袭前代之失而未改耳”(林有年等,2002:114—115)。
城隍老爷从灵验的化身,转化为法权与德性的化身,是信仰历史的演变脉络。这个脉络留下许多素材可资史学家叙说各自的故事(关于城隍信仰的“通史”,见郑土有、王贤淼《中国城隍信仰》,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历史素材的梳理非我强项,而我还顽固地相信,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要迎合史学研究的需要,而将灵验的化身与法权与德性的化身分割开来,使之成为时间上的前后两段,而应看到这二者,通常合而为一。
当地流传着许多城隍老爷显灵的故事,常见的故事分两类,一类是城隍老爷保障安民的传说(如显灵惊走贼兵的传说),另一类是他老人家显灵协助县官破案的传说。关于“破案传说”,乾隆版《安溪县志》之卷十(杂记)提到一个故事:
乾隆二十年正月十一日,县民陈福挟仇将田主王益让杀死于后塘陇地方,屡审,坚不承认。邑令庄成斋戒沐浴,具牒亲祷于城隍神。翌日,带犯赴庙覆讯,冤魂忽附于犯妻黄氏身上,向伊夫历历质证,并将凶器指出。福始俯首无辞。案乃定。观者无不称异。庄令题匾于庙,以纪其事(庄成等,1988:335)。
更多的民间传说将破案故事与男女关系的规范联系在一起。在闽南高甲戏中,有一出城隍老爷托梦破奇案的戏,就是根据这类故事中的一个改编的。故事梗概是,清代安溪县城一个巷子里有个姓金的生意人外出经商,他老婆忍不住寂寞,与一个举人通奸。二人相处得非常快活,以至于谋杀其夫。他们将丝蛇放在青竹管里,其夫一回家,其妻将之灌醉,将装蛇的竹管对准他的鼻孔,再用火烧蛇的尾巴,蛇滚入其夫腹中,咬死了他。出于意料之外,奸夫淫妇的凶杀过程让一个小偷看见了。后来县官也了解到有通奸害夫案存在,他开棺验尸,查无痕迹,反被诬告无端验尸。于是,便请求城隍老爷指点迷津。一夜,他果然梦见城隍老爷指点他去找小偷,将案件查了个水落石出。《安溪东岳城隍寺庙志》记述了故事的详细情节:
清道光年间,安溪县城蒲厝巷,有一姓金者外出经商,其妻与吴云梯(举人)通奸。在金氏未回之前,奸夫奸妇共议一计,把青竹丝蛇藏入竹管里,待夫回家时,借办酒洗尘之机,把金灌醉,然后将装蛇的竹管对准鼻孔,用火烧蛇尾迫[其]滚入[金氏]腹中,毒咬金氏致死。有一天金氏回家,奸夫奸妇就按此计行事。出于意料之外,凶杀过程却被小偷李彬暗地窥见……一天,县令黄宅中下乡办案回城,路经祥云渡,忽有怪风飘来一些半烧过的纸帛在黄的轿[子]四面周旋,黄疑有异,即下轿,派差役往山上周围查看。据汇报,只见一青年妇人在新墓烧纸[冥币]并哭泣着,[黄]即招回那哭墓女人,观形察色,确有可疑之处。回衙后,即派员四处查明,断定是通奸害夫。当即开棺验尸,然而查无任何伤痕。金妻受[奸夫]指使反咬一口,向上诬告“黄欺寡妇,随意开棺”。州令随即撤黄职,黄要求宽限一段时间给查明。在州官的准许下,黄便向安溪城隍拜求指点破案线索。有一夜黄梦见城隍指点“往向东方行,木子便知情”。第二天,黄宅中化装[成]一相命先生,往东行,夜宿李彬家,黄、李二人在深夜漫谈中,黄问李何为不娶妻,李叹口气说:“当今妇女真奸雄,故不敢想娶妻”。黄耐心追问,李彬终于道出金氏被青竹蛇毒死经过情况,并拿出凶具竹管给黄看,黄恍然大悟,喜形于色,对李彬说,他就是县令,为办此案,蒙城隍托梦指示而来暗访,明天你把竹管取去吴云梯典当铺当千钱,有事我做主。第二天,李彬就去当竹管,店员不理,吵闹起来,吴云梯探头一看,看是他作案工具,即叫店员取钱给李彬,李彬钱拿到手连竹管一齐带走,前往县衙呈交县令黄宅中,县令见此物证,确定[金氏为]奸害无疑,再次开棺剖尸详验,果然腹中蛇迹尚存,即于安溪城隍庙内开阴阳庭公判。罪犯二人见事已暴露,再不敢抵赖,一一交代凶杀过程。观众甚多,无不惊异敬服。黄宅中把案犯依法判罪上报,得到官复原职,并加升三级,后被人称为“黄青天”,黄深有感受,亲书一匾“是梦觉关”挂于庙内。(《安溪东岳城隍寺庙志》,安溪县,1994年印行,16—19页)
故事让我想起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提到的一件事。60多年前,有个县官告诉费先生,有个人因妻子偷汉子打伤了奸夫,结果,奸夫来县里告状。县官自己觉得很难办,一方面,在乡间殴打奸夫是理直气壮的;另一方面,通奸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但殴伤他人却有罪。怎么判?那个奸夫做了坏事,还要求法律保护。殴打他人,是犯罪,法律要管他,所以,还是要处罚打人的人。可县官心里也有道德感引起的矛盾,认为“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绝不会到衙门里来的”(费孝通,1985:58)。也许自古代开始,衙门面对众多的模糊的罪过,都与这个县官一样,知道难办。衙门一面要用法来治理地方社会,另一面却不能破坏地方社会存在的道德秩序。怎么结合?城隍老爷可能便是在衙门的两难困境中被发明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将城隍老爷破案的故事,与城隍庙内部的雕塑群之形象组合联系起来,我们能洞见艺术的“法学意义”:城隍老爷的慈祥,他手下的凶神恶煞,使城隍庙俨如法庭,这个别开生面的象征法庭,虽没有政府衙门具有的实在的政治权力,但却能从一个艺术抑或“权力美学”的角度,制造出一个令人敬畏的象征力量来。关于城隍老爷破案的传说,与城隍老爷“衙门”的形象相互配合,言说着这个“衙门”的灵验。二者都通过“承认”阴魂的实在性,促使人们对于来生产生严重的恐惧,对于今生的行为保持警惕,由此实现社会道德秩序的营造。而所有这一切,也都在一年一度城隍老爷巡行的仪式中再现出来。
明清以来(只有上个世纪50~70年代间断),每年春天,安溪都要举办城隍老爷的迎傩盛典。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立的一块石碑记载了时任县正堂的“谕事”,提到“安邑敕封显佑伯城隍尊神,理阴赞阳,每年季春,士民仿依古礼设醮迎傩”;而乾隆版《安溪县志》也提到,“二月二日,各村俱祭土地,名为做福,是月邑令内陈鼓乐,结彩棚,迎城隍神会,通衢热闹,游观者众”(庄成等,1988:112)。尽管史书说农历二月二是城隍神会的日期,但这个盛典的具体举办日,须于农历正月十六日在城隍老爷神像前占卜择定。那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安溪人按街道和村庄组合成团队,以花鼓、彩旗、舞狮队、南音清唱队等等“文艺表演团体”形式汇聚于县城。人们装扮成各式各样的戏剧人物,如梁山好汉、十八罗汉等。仪式的程序如同村落的庙会,是由仪式专家(道士和民间和尚)安排的,完成一日的祭祀,当夜12点,城隍老爷的神像衣冠一新,被抬上游神用的辇轿,他的手下“部门负责人”,也一样地被重新装扮。次日清晨5点,真人替代了神像,他们在庙里“办公”,神像被抬上街去,被沸腾的人群、热闹的“文艺团体”拥戴着,巡游县城的所有街巷和公共空间。绕城之后,仪仗队鸣锣开道,城隍老爷要南下校场(刑场),走到场子附近,他老人家要换上法衣才进入校场。一切搞定之后,主持的仪式专家突然大呼:“冤魂有冤准予前来鸣冤”。可以想见,古时在这个时候肯定有出来喊冤的。现在,这种做法没有了,一切都变成了表演。仪式专家话音刚落,城隍老爷的神像便在他的队伍的拥簇下,绕场一周,徐徐出场,再度巡行他的城池。
在校场附近,城隍老爷换法衣,成为超越官僚的官僚,入场之后,仪式主持人呼唤冤魂前来“报案”(喊冤),将城隍老爷比做真正能主张正义的“法官”。
“县有城隍,以理阴也”——这是清初《重修城隍庙碑记》采纳官方祀典给予城隍老爷“职权范围”的界定。城隍老爷是管理阴间的,他的“衙门”是阴间的“政府”,这个“政府”与阳间的“衙门”一样,“政法不分”,自身也是“法庭”。
城隍老爷的形象、传说与仪式,三种“艺术表达形式”紧密相扣,形成一套“制度”,召唤着社会的活力。如上所述,对于城隍庙进行研究,人类学家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
1.庙宇的象征空间所显示的美术威慑力及其所隐藏的城池之神到“阴间法庭”的历史脉络;
2.可从城隍老爷托梦判案透视出的道德与秩序的传说;
3.可从城隍老爷游神观察到的衙门“冤狱处理艺术”与民间驱邪仪式的结合。
从呈现阴间的种种存在方式,城隍老爷的“艺术”威慑着阳间的人。对于冤魂的恐惧,是明清政府致力于城隍庙修建的主要背景。阳间的衙门本控制在人手中,而人这种存在有其众所周知的悲哀面,要实现法制的正义,对于活生生的人而言,并不是一件轻易能做到的事。衙门是社会秩序的维持者,然而因为无能或故意,衙门也是冤魂的制造者。创造出一个对应于阳间衙门的阴间衙门,用种种所谓“文艺”的形式来营造它的真实性与灵验,为的是补充阳间衙门的力量、反省它的失误、抚慰它的潜在敌人。
城隍庙及围绕城隍象征创造出来的美术、故事与仪式让人想很多:其中一点,是它在宗教内容方面与佛教地狱和轮回观念的融合;另一点则跟“以礼入法”的传统有至为密切的关联。关于城隍的“佛教化过程”有待考证,而关于它代表的“以礼入法”,这里则可多说几句。古代中国法律制度受儒家的影响,重视礼,结合礼,形成不同于现代法的特征。对于这一法的文化特征,法社会学家瞿同祖从经典文献给予了解释。关注儒家“大传统”,使瞿同祖从中国法中看到“礼”的浓厚因素(瞿同祖,1998:361—381)。同样地,关注“小传统”的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在乡间发现“礼治秩序”的存在。在该书中,费孝通引用孔子的“克己复礼”之说,对“礼”给予定义,说“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费孝通,1985:52)。在人类学界,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之辨,向来引起广泛的关注。在瞿同祖论述的大传统与费孝通论述的“乡土小传统”之间,有什么历史性的“上下关系”?这是前辈们遗憾地没有触及的问题。不过,费孝通提到的“令人服膺”的“敬畏之感”,已为描绘城隍庙及其种种象征与仪式所可能代表的大小传统之间“礼的结合”,给予了难得的启发。
明清时期,城隍神曾担当厉坛之祭的主角,早期是将它的城隍神木主设于厉坛之上,后来改用木头雕像坐镇厉坛。明初厉坛之祭,祭文由礼部统一颁定,有抚恤孤魂野鬼、防止其作祟、宣扬因果报应、监察官吏等作用。城隍神是城池之神,但其地位介于城乡之间,沟通上下关系,通过培育费孝通所说“令人服膺”的“敬畏之感”,通过造就“阴阳关系”,来造就维持“上下关系”的“法”。一如明初的祭文所说,“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无不有人,无不有鬼神。人鬼之道,幽明虽殊,其理则一……上下之职,纲纪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上下之礼,各有等第,此事神之道如此。”(转引自上揭书:183—184)。
城隍庙内部树立的雕塑之所以如此具有威慑力,与艺术的“法律意义”有关。从一个角度看,从明初开始,城隍庙一直既是人们求取护佑的地方,又是将所有“习惯法”融入自身的空间,它如同地狱图那样,“也会说及官僚政治之错误与腐败”,并“因由无形的魂灵所监督,所以比人间的监管更频繁,更不易出纰漏”(雷德侯,2005:247)。明初的祭文提到城隍庙的作用时说:
凡我一府境内之人民,偿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上揭书:183)
用刑法、阴谴、瘟疫等等作为恐吓,祭文将城隍庙艺术的威慑力“生动地”呈现于我们面前。
而城隍庙之不同于官府,又在于它的威慑力是普遍适用的——它针对隐藏于所有角落的罪过,包括官府的罪过。祭文的最后宣誓说:
我等阖府官吏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蠧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照报,如此,则鬼神有鉴察之明……(上揭书:184)
我从艺术的社会性,延伸到法人类学,似乎离题太远。不过,为了解释何为艺术的社会性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正需要如此“离题”。
在《看·听·读》一书中,反思人类学以往存在的将艺术当作社会的“集体表象”、实现社会的组合功能的手段的观点,列维—斯特劳斯对于艺术进行了神话学“考据”,他指出,艺术与神话都同时与自然、习俗及超自然形成联系(列维—斯特劳斯,1996:148)。于我看,“礼”一样地是与自然、习俗及超自然息息相关的。作为“礼”的艺术,与作为“法”的“礼”,无论怎么理解,都与这一相关性紧密相连。
何为艺术的“社会性”?
作为“艺术人类学”的外行,我道出自己之所见,将之奉献给有志于解开这个谜团的诠释者。“种种艺术表达形式,源自于人们对于事物存在形式的种种观念型塑”(Clifford Geertz,1983:120)。无论是雕塑、诗歌、叙事、绘画、还是仪式与戏剧,艺术表达形式本身之所以值得人类学家研究,乃是因为它们为人所创造、为人所拥有,而人必须生活在与自身、自然、习俗的关系之中,对其有责任,也承受其压力。艺术的“社会性”,是一种超然的形式,它以一种超自然的诉求,激情或冷漠地表达着敬畏及同时作为敬畏的“叛逆”和内在因素的无畏之间的种种可能关系,并由此赋予人文世界以道德意义。
国内艺术人类学家(或艺术民俗学家)从“乡民艺术”,西方人类学家从“原始艺术”,各自进行着比较工作。对于我们来说,“乡民艺术”的价值,在于它对于我们都市知识分子来说,比艺术家的作品更贴近生活(特别是因为艺术家为了提升其作品的价值与价格,已变得越来越“不入群”了);对于他们(西方人类学家)来说,“原始艺术”的价值,在于它是反观近代西方思想的“个体主义”倾向的镜子。二者之间虽有不同,但更有共同点:我们都将不同于现代的艺术归结为“他者”。对象既为“他者”,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是否与现代艺术作品的分析无关?并非如此。“通观数千年历史,人类的各种激情互相交融混杂,时间没有对人类的爱和恨、对他们的诺言、他们的斗争和他们的希望增添和减少任何东西:从前到今天,一如既往。即使随意抹去10个或20个世纪的历史,也不会明显地影响我们对人类本性的认识”(列维—斯特劳斯,1996:174—175)。如我上面所形容的“传统乡民”,现代艺术也“激情或冷漠地表达着敬畏及同时作为敬畏的‘叛逆’和内在因素的无畏之间的种种可能关系”。现代艺术的“文化空间”已被区分出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艺术家的表达已越来越以其自身的个人化为形式。然而,艺术家不是非人,他们的创造即使能脱离于习俗,也难以脱离于他人,脱离于作为素材、内容和艺术表达形式的自然和超自然——艺术家所做的不是分离这些东西。因而,艺术人类学对于非传统艺术的理解也一样有启发,因为这种新的艺术之激情,也来自于某种富有启迪的敬畏,来自于非人的场景中有性别的人人关系的想象,如狄德罗所说:
伟大的风景画家有他特殊的热情,这是一种神圣的震惧。他的山洞幽暗深邃,峻峭的岩石直插天空,急流从岩石泻下……人穿越魔鬼和神的居宅。就在这里情郎把他的意中人藏匿起来,就在这里只有她听到他的叹息。就在这里哲学家或者坐下,或者放慢脚步走路,沉思冥想,假如我的眼睛停留在这种神秘的自然的模仿上面,我战栗。(狄德罗,2002:162)
人类学提供一种“语言”,使我们能从狄德罗的那段话,联系到安溪城隍老爷托梦破案传说。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它们都同时言说两性与天地之间的阴阳关系。所不同的是,在狄德罗的意境中,直插天空的岩石,急泻而下的溪流,是为情郎藏匿意中人“推波助澜”的非社会理性;而在城隍老爷托梦破案的传说里,作为激动人心的隐匿式婚外情的背景,包括小偷在内的道德监视者对于这一关系的注视,是画面上的衬托。天地的阴阳,一上一下,以其存在和表达的各种可能形式,为社会监视者提供力量与理由。后文艺复兴的艺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这个比较中得到了彰显。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将比较推到极端的对照,因为二者之间并非不可互换:城隍老爷托梦破案的传说,要转化成为浪漫史,也就是一瞬间、一闪念的事。而更重要的是,这一被推上地方戏舞台的传说,易于使观众分化为传说的不同感受者。到底他们是爱看金氏的不幸,还是爱看他那出轨的妻子与举人的“激情戏”,学者需要调查方可得出结论。从中国小说史研究者找出的“历史规律”来猜想,城隍老爷的灵力演绎出来的故事,随时可能被顺利改编为“另类故事”。妇女之所谓“有伤风化”,若带有内心的委婉与肉体的禁忌,自古以来也可以被讴歌。早在唐代,张籍《节妇吟》已为“礼法”威慑下的隐秘爱情吟唱出优美的诗篇: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褥。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持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明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诗在激情与婉约之间徘徊,微妙地透露出激情与符合礼法的婚姻的矛盾,最终用无奈的“生不逢时”,化解激情,使婚姻的誓言,成为神圣的诗篇,使激情在婚姻的压抑下,涌动于内心,而不形表于外。
经历漫长的年代,这样的叙事持续重现。无独有偶,闽籍戏剧家王仁杰著出新编梨园戏《节妇吟》,情节感人:寡妇颜氏,难捺十年冷雨青灯,夤夜叩户,向塾师沈蓉求爱,沈蓉拘于名节,阖扉拒绝,颜氏羞悔交加,断指自戒,从此洗心革面,教子成龙……
一部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古装戏,成为神话式的爱情传奇,与狄德罗的艺术论融为一体。戏里没有情人的藏匿,但有激情在内心的“悲欣交集”,寡妇内心的出轨,与因求爱遭拒而产生的羞愧与悔恨,透露出名节对于激情的压抑,而激情的压抑,可被解释为儒家节妇观念使人服膺的功效,激情本身,可被展现为对于礼法、名节的抗拒。剧作家在呈现这些矛盾时,没有如狄德罗那样,以大自然的山峰与急流来衬托“藏匿的情人”的激情,却将所有一切逼迫入内心,使身内与身外成为难以合一的存在形式,借此,将身内陈述为激情,身外陈述为礼法,使之相互否定。与城隍老爷托梦破案的故事不同,新编梨园戏《节妇吟》没有站在道德法庭的立场(城隍老爷与他保护的对象的立场)上谴责“出轨的心”,而是将之当成礼法的敌人,使二者持续处在难以解决的紧张关系之中,使“礼法”面前软弱的寡妇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古今不同形式的《节妇吟》,是明显或隐晦“自我解放艺术”,它与具有明显或隐晦威慑力的艺术一样,是社会生活道德想象的技艺,它与后者存在鲜明的差异,但因为有此鲜明的差异,而易于以种种“移情”或“颠倒”方式,实现相互的渗透与替换。我们在说艺术,也是在说礼法,因为二者都在“相反相成”的意义上构成其风格鲜明的道德叙事,相互之间的区别可能被文艺学家演绎为礼法的德行向激情解放的个人“进步”的历史。但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却是社会生活的不同道德想象不可舍弃的“双方”:无论是围绕着阴间衙门制造出来的托梦城隍对灵肉的无孔不入,还是《节妇吟》企图隐匿的内心激荡,都借助魔幻的力量使自身成为德性的言说。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人类学与法律人类学在相互启发中扬弃了结构主义,为“威慑艺术”的研究开拓了视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式文化研究”的一个局部。
[收稿日期]2006—07—02
注释:
① 本文的纲要于2006年5月9日在山东艺术学院“乡民艺术与近现代华北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过,成文后,提交同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法律与社会科学第二次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