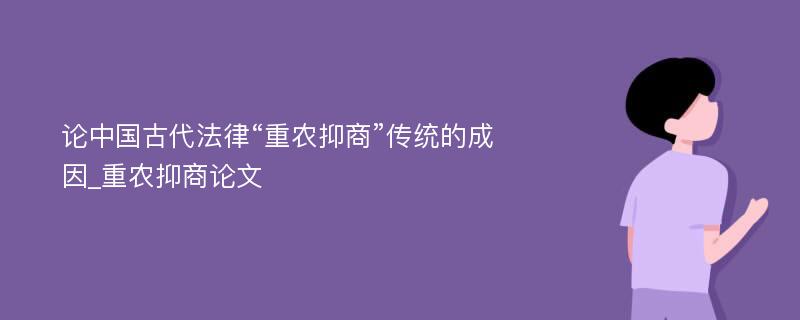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法中“重农抑商”传统的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传统论文,重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通过法律困辱工商业者,限制私人工商业发展,这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传统的形成,直接由“农”、“商”对封建国家的“利”、“害”属性所决定。从政治经济方面讲,私人工商业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结构的稳定有着经常性的危害,它常导致小农经济的瓦解。从伦理方面讲,私人工商业是对封建等级秩序、“均平”秩序、俭朴秩序的经常性破坏因素,它易导致社会尊卑贵贱关系的紊乱。这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以“重农抑商”为国策。
[关键词] 中国古代法 重农抑商 传统 成因
中国古代法中的“重农抑商”传统,人们很早以前就专门研究过它的形成原因。人们认为,其原因不外两者:一是在中国古代,商业是对作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基础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经常性威胁,故要抑商而促农;二是在亚细亚社会,商业经常威胁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行使其广泛的公共职能(如举办公共工程以抵御自然灾害、修长城抵御外族入侵等等),故要抑之。现在看来,这种结论是不全面的:只注意到了形成这种传统的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没有注意到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观念原因或精神文化方面的原因。这种原因,就是“义利之辨”、“重义轻利”观念为代表的伦理思想。
义者,宜也。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为国家之大利,为国家之最适宜者,故亦为国家之大义。重农即国家“重义”也。商为私人之利,为国家之害。抑商乃国家之“轻利”也。[①]农、商的这种利、害属性是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文明模式所决定的。这种利害,不光是经济之利害,亦有伦理之利害。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两圣之言为中国传统文化定下了基调。从此以后,“义利之辩”、“重义轻利”成了中国两千多年伦理思想的铁则。圣言即理,圣言即法,这一伦理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深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古代法。
一、以“困”“辱”为中心的古代“重农抑商”法律制度
《史记·平准书》云:“(汉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司马迁的这段记载,用“困”“辱”二字准确概括了汉代的抑商政策。自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抑商政策与立法主旨也不外“困”“辱”两途。
“困”商,即对商人实行经济打击。历代王朝用以“困”商的方式有三:
第一,官营禁榷。任何一种工商业,只要稍有利可图,就可能收归官营、禁止民营(禁榷)。管仲相齐,“管山海之利”,商鞅变法,实行“壹山泽”。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此后历朝历代官营禁榷的范围不断扩大,到明清两代已经发展到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甚至瓷、烟草、大黄等等,均统统列入官营范围。为了维护国家“专利”,历代朝廷设定了严刑峻法打击敢与朝廷争利的商人。汉代,“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②];唐法,“私盐一石至死”;五代,“私盐不计斤两皆处死”;宋代,“鬻卤盐三斤者仍坐死”;元代,“私盐一斤以上皆拟徒没产”;明清两代,“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斩。”[③]
第二,重征商税。早在秦商鞅变法时即定下国策:“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④]汉高祖对商人“重租税”以打击;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用征重税和鼓励告发漏逃税的方式对商贾进行大抄家,“得民财以亿万计”、“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⑤]。汉代征收人头税,明定“贾人倍算”[⑥](双倍征税)。自汉以后,历代王朝莫不重征商税,“寓禁于征”。
第三,不断改变币制。汉武帝时,“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⑦]仅汉一朝,改币制达六次之多。此后直至清末,朝廷进行了数十次币制改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改变铸币的金属成份、重量、发行量来使货币贬值,以搜括民财(主要是商人之财)。
为使上述三者切实有效,均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与贯彻。
“辱”商,即对商贾进行政治上的打击。历史上通过立法实施“辱”商方式有三:
第一,直接视经商为犯罪,实行人身制裁。秦始皇时,曾“发贾人以谪遣戍[⑧],”汉武帝“发七科谪”(遣七种罪犯戍边)中也有“贾人”一科[⑨]。
第二,“锢商贾不得宦为吏”[⑩]。这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抑商之法。汉初,“贾人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11)];孝惠高后时虽“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犹不得仕宦为吏”[(12)];汉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13)]。唐《选举令》规定:“身与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14)];北魏律规定:“工商皂隶不染清流。”[(15)]直到明清时代,商人子孙仍须数世以后才被允许参加科举。
第三,从服饰方面进行侮辱。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汉律明定““贾人勿得衣锦绣,……乘骑马”[(16)];”晋律:“侩卖者皆当着巾白贴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17)]”;前秦王苻坚曾下令:“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18)];明太祖亦曾下诏:“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细纱。”类似的法令史不绝书。
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法律传统的经济政治成因
历代王朝刻意“以法律贱商人”[(19)],其根本动因是什么?当然是朝廷之利害。利在重农抑商,害在弃农经商。不过,这种利害分成两个层次;一层是物质之利害,一层是精神之利害。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害大于利。
仅就物质方面的利害而言,私人工商业对国家的危害有三:一是与国家争夺“山海陂泽之利”[(20)]。在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的一切财富资源亦莫非王有。商业发达,必赖资源之开发利用,被视为盗皇家之库。二是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资源,甚而使农田荒芜,威胁国本。古时,“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市门”[(21)],“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22)]商鞅云:“农少商多贵人贫”[②③];荀子云:“工商众则国贫”[(24)];汉人贾谊谓:“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25)];汉人王符喻当时“舍农桑趋商贾”之社会风气为“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织百人衣之”[(26)],都道出了工商业对小农经济之威胁。因此,古人纷纷主张“省商贾,众农夫”[(27)],“驱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28)]”,“使农夫众多而工商之类渐以衰息”[(29)]。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为国本,民众弃农经商,则农田荒芜、粮食短缺,一遇水旱灾荒或战争,则国家危亡。三是私人工商业发展易形成对朝廷构成威胁的“叛乱”势力。汉人桑弘羊云:“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流放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30)]此语指出了富商大贾对朝廷的威胁。汉时也的确如此,如代国陈稀叛乱,吴楚七国之乱,均有私人工商业势力支持参与。
基于以上三因,朝廷采取了严厉的“困”商政策:为反对富商大贾与国家争利,朝廷实行盐铁茶酒等官营政策,禁止民营。为反对商业争夺农业劳动力及对农业的威胁,朝廷采取了重征商税、改革币制等政策,目的是“重征商税使无利自止”[(31)];“重关市之赋”,使“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使商“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32)];“更钱造币”而“摧浮淫并兼之徒”[(33)]。为反对富商大贾聚众深山穷泽成为叛逆势力,朝廷直接设官设场进行盐铁酒茶等专营制造并垄断买卖。
朝廷的物质之“利”,亦即国家之“义”;朝廷的物质之“害”,即为“非义”。在这里,“义利之辨”表现为“利害之辨”。而“利害之辨”,实际上是专制王朝之利益与民营工商业之利益的斗争:商贾之大利(擅山泽、聚徒附、私铸钱、屯积居奇、逃漏税)即国家之害,即非大义;国家之大利(壹山泽或官营禁榷、平准均输、更钱造币、重征商税)即为商贾之害,正合乎封建专制之大义。封建专制主义之大义是:一切财富应归君主统有,民富国强、民贫国富、民弱国强都可以,千万不可民富国贫、民强国弱。要让民众仰给于国家,如婴儿待哺,绝不可认民众私人厚殖财富与朝廷官府抗礼。
三、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法律传统的伦理成因
物质上的利害之争及“义利之辨”仅是形成中国重农抑商法律传统的一方面原因。还有一方面原因不可忽视:精神或伦理方面的“义利之辨”。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看来,商业及商人对传统伦理或义理(精神)的危害或威胁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商人或商业是危害封建等级秩序(君臣上下贵贱尊卑)的经常因素。
封建等级秩序要求的是:“衣服有制、宫室有度、蓄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34)]商业和商人势力是对这种静态秩序的一种天然破坏因素。例如汉时,“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人称为“素封者”[(35)]。这些靠财力而不是靠帝王诏命获得诸候般地位享受的人,“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俟于守令。”[(36)]这些工商业主,“以财力相君长”[(37)],严重地威胁着封建宗法专制秩序。工商业主因其出身多卑贱,有富无贵,故必竭力因其富厚之资僭越礼制,显示尊贵,使封建等级制度堤防日益溃坏,“制度日侈,商贩之室,饰等王候,……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38)]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捍卫者们最担心最反感的情形。富商大贾“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候之富”[(39)],此种情形,“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40)]
第二,商业和商人是对传统的“均平”伦理秩序的破坏因素。
孔子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41)]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秩序,就官民关系来讲,是贵贱尊卑等级秩序;就民众之间的秩序来讲,就是一种“均贫”或“均平”秩序。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必需的和必然致成的秩序。这也是一种伦理秩序。这种秩序使民众永远互相分散孤立而不富裕(最高愿望是温饱而非富有),使其永远无法以财力与官府抗衡。这种秩序与尊卑秩序相辅相承。此种秩序一旦破坏,贵贱尊卑秩序也难保持。私人工商业蕴藏着对这种“均平”秩序破坏的天然力量。如汉时“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42)]、“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43)]“上家累巨亿赀,斥地侔封君之王”[(44)]。这种贫富悬殊,当然不仅仅破坏了小民百姓的“生人之乐”,也破坏了朝廷之乐。朝廷之乐在于百姓“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45)],此即人伦之理。商业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势必威胁破坏着小农社会均平的、宁静停滞的生活伦理。超过了最低生活需要的财富,自古至今,必然是一种天然具有凌驾、僭越、破坏平衡的力量因素。
第三,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商业是使社会风气荒淫奢侈的一种破坏性力量。
小农社会所需要的是愚昧、寡欲、安于现状。商业的活动,必然威胁这种伦理秩序。汉人崔寔夫人之情,莫不乐于富贵荣华、美服丽饰……昼则思之,夜则梦焉,……不厚为之制度,则皆候服王食,僭至尊,逾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闭民欲。”然而,商业活动正好与王朝的这一目的相反,它在时刻开民欲,刺激物欲:“今使列肆卖侈功,高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见可欲,不能不买。……故王政一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46)]这种“多通侈靡,以淫耳目”[(47)]的风气,对国家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汉人董仲舒云:“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赢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48)]明人王夫之云:“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贱人之生为已极者也。……贾人者,暴君污吏所亟进而宠之者也,暴君非贾人无以供其声色之玩,污吏非贾人无以供不急之求。”[(49)]非独暴君污吏,小民百姓也常因商贾奇淫之货的刺激而丧失安贫素朴之性而贪求财货,使社会风气败坏。“钻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玑,设机陷求犀象,张网罗求翡翠,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交万里之财,旷日费功,无益于用,是以褐夫匹妇,劳罢(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50)]这种状况是统治者“示民以利”的恶果:“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嗜欲众而民躁。”所以,为防止此种状态,王者应该“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遏贪都之俗而醇至诚之风”。简言之,王者应“示民以义”、“教民以义”;“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工商)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51)]
第四,商业使人奸诈,农业使人厚朴,故重农抑商即抑奸诈之俗,长厚朴之风。
商鞅云:“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52)]。《吕氏春秋》云:“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53)]《盐铁论》云:“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觎而心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54)]晋人傅玄谓:“贾穷伪于市”,“其人甚可贱”[(55)]。明人王夫之谓“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贱人之生为已极者,乃其性恒与夷狄而相得,……故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56)]直到近代革命家章太炎,仍认为自农民、工人、裨贩、坐贾至职商、官吏,其道德水准有十六等之差:“农人于道德最高”,“工人稍知诈伪”,“商人是不操戈矛的大盗”![(57)]自古至近代,正统观念是“无商不奸”、“君子不入市,为其挫廉”[(58)]。所以,重农抑商非仅为物质之利害,乃“复朴素而禁巧伪”[(59)]的维护伦理之举也,乃“重义轻利”之实践也。
基于以上四因,历代王朝采取了轻重不等的“辱”商政策。直接以经商为犯罪,固可阻吓商人,使人不敢效尤经商,但毕竟太过分,故汉以后未再有此举。禁止商贾宦仕为吏、禁止其子弟参加科举,这都是历代最为有效的“辱”商措施,直到清末才有缓解。经商虽可致富,但无途致贵,无途问津政治,无途光宗耀祖,这的确让商人阶级心灰。如果让那些奸诈的商人封官晋爵,则儒家之“礼义”何存?至于从服饰车马上对商人进行侮辱,也是此理:从事下贱事业的人绝不可与从事正当事业的人平起平坐,必须使其在衣饰上有所抑屈,显其贱民身份。若让其凭富厚衣丝帛服文绣,上僭贵族(宗法血缘贵族)官僚之特权,使官贵无以显荣、无业可守,下蚀庶民百姓之美德,使百姓知商贾可以显荣、可以僭贵,则皆弃农经商,不务本业,崇尚奢侈。如此,则礼义堤防荡然无存。只有采取种种措施使“农尊而商卑”、“农逸而商劳”、“农恶商”、“商怯”、“商疑情”[(60)],作为国家基础的小农经济才能巩固。
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私人工商业与宗法制小农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宗法制小农经济国家,在于“农业立国”、“农为国本”,只要国家有库存余粮,有可战之民(农民),朝廷赋税之源充足,就不怕一切灾荒、侵略,国基就稳固。要做到这些,就要抑制私人工商业,不可让其威胁国本——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使人们弃农经商、轻迁徙而无恒心、崇尚奢侈忘记俭朴、不愿为朝廷卖命。另一方面,宗法小农之国的伦理之“义”,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于“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夫和妻顺兄友弟恭姑义妇听”,在于“尊尊亲亲长长贵贵”。这一切,只有在一个静止、愚昧、封闭的小农社会里才有可能做到,只有在子孙依赖父祖传授生产技术方可继续再生产的农业生产方式下才可做到。商业则不然,它天然要求“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天然要求“设智巧,仰机利”,要求“连车骑、游诸候”、“周流天下”[(61)]、纵横南北;也天然会以富求贵、炫耀奢靡,趋于淫佚、“(恃)财役贫”、“以财力相君长”,僭乱礼制。总之,在小农经济下,商人和商业是一种以“恶”的面目存在的经常的革命性因素。对这种革命性因素的扼杀(当然,可以允许其在一定的无害程度上——如“通有无”——的存在),是宗法小农社会专制王朝的使命,也是其大利所在。否则,就会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伦理之义仍不过是加以抽象的王朝物质之“利”。以伦理为基础的传统法律文化,自然视抑商为己任。而“抑商”也就当然成了传统法律中的应有内容,成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种传统。
注释:
① ⑤ (12) (33) 《史记·平准书》。
② 转引自沈家本:《寄簃文存·盐法考》。
③ 《大明律》、《大清律例》之《盐法》。
④ (23) (32) (52) (60) 《商君书》。
⑥ 《汉书·惠帝纪》,六年条应劭注引汉律。
⑦ (19) (21) (28) (39) (43) 《汉书·食货志》。
⑧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⑨ 《汉书·武帝纪》。
⑩ (13) (22) 《汉书·贡禹传》。
(11) 《汉书·哀帝纪》,引汉初之律。
(14) 《唐律疏议·诈伪》,“诈假官”条疏引。
(15) 《魏书·孝文帝纪》。
(16) 《汉书·高帝纪》下。
(17) 《太平御览》卷八二八。
(18) 《晋书》卷一百十三,《苻坚纪》载。
(20) (31) 李贽:《藏书》卷五十,《富国名臣总论》。
(24) (27) 《荀子》“富国”“君道”。
(25) 《新书·大政》。
(26) 《潜夫论·浮侈》。
(29) 《历史名臣奏疏》,卷二五七,苏辙语。
(30) (50) (51) (54) 《盐铁论》“禁耕”、“通有”、“本议”、“力耕”篇。
(34) (48) 《春秋繁露》“服制”、“度制”篇。
(35) (40) (42) (61) 《史记·货殖列传》。
(36) (37) 仲长统:《昌言》“理乱”、“损益”篇。
(38) 《宋书·周朗传》。
(41) 《论语·季氏》。
(44) (46) 崔寔:《政论》。
(45) 陆贾:《新语·至德》。
(47) 《后汉书·桓谭传》。
(49) 《读通鉴论》卷十四、卷二。
(53) 《吕氏春秋·上农》。
(55) 《傅子·检商贾》。
(56) 《读通鉴论》卷十四。
(57) 《章太炎政论集·革命之道德》。
(58) 《太平御览·人事部》卷六十七。
(59) 《李直讲(觏)先生文集》,卷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