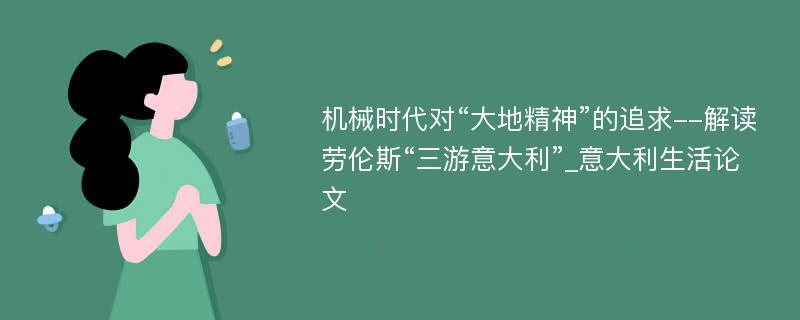
机械时代的“地之灵”追寻——解读D.H.劳伦斯的三部意大利游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伦斯论文,意大利论文,之灵论文,游记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3X(2010)06-0069-06
在现代英国作家中,D.H.劳伦斯(1885-1930)是个异数。这位出生于英格兰心脏地带——诺丁汉的矿工的儿子,几乎一辈子处在旅行、逃离或自我放逐中。正如诺丁汉大学劳伦斯专家约翰·华森教授(Prof.John Worthen)在其新著《劳伦斯传》(D.H.Lawrence:The Life of An Outsider,2005)中所说,他的生活由“一系列的逃离(escapes)”组成,逃离“闭塞和窒息的感觉”[1]44。当代旅行文学专家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则进一步指出,“对他(劳伦斯)来说,正如对大多数工业时代的旅行家一样,旅行既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追寻。在他那里,是逃避一个他讨厌的谨慎和情感退化的英国,是追寻任何一个活生生的、充满力量的、不自私的地方。”[2]475从劳伦斯身后留下的50卷小说、诗歌、散文和书信来看,这些不同类型的作品基本上是在不停地旅行、逃离或自我放逐的过程中构思,写作,或修订完成的。安东尼·伯吉斯(Antony Burgess)认为,劳伦斯的所有作品中,最迷人的(the most charming)是他写的游记作品[3]67。劳伦斯一生去过无数地方,欧洲的德国、意大利、撒丁岛、瑞士和法国,亚洲的锡兰(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和塔希提岛,北美的纽约和墨西哥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他似乎对意大利情有独钟。如所周知,劳伦斯总共写了4部游记,其中3部都与意大利有关,即《意大利的黄昏》《大海与撒丁岛》和《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我们不禁要问,意大利究竟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促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踏上这片土地,细察之,寻访之,思索之,并书写之?
一、意大利灵魂的两极
一些西方评论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劳伦斯生命中“决定性的危机”(a defining crisis),对他来说,这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的战争,而是人类依附机器犯下的一桩野蛮的大屠杀罪行[1]43。《意大利的黄昏》(Twilight in Italy)写于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出版于大战正酣的1916年。劳伦斯开始时想把它起名为《意大利岁月》(Italy Days),但他的出版商不喜欢这个标题,认为它既会引起误解,也不够醒目。改用《意大利的黄昏》之后,作家的意图和动机更加明确了。按照巴巴拉兄弟和朱丽娅·葛吉兹(Barbara Brothers and Julia M.Gergits)等人的说法,“黄昏”(Twilight)一词具有多重含义,不仅指字面上的白天与黑夜的融合,而且也是太阳与月亮,智力与心灵,理性意识与血性意识,现代工业世界与更为原始的情感世界的相交[4]182。这个标题暗示着正在描述的古老的意大利的终结,也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笼罩上一层神秘的氛围[4]187。
旅行家汤姆林森(H.M.Tomlinson)说,劳伦斯是“一个优雅而敏感的感觉器官(sensorium),对任何物理性的事实都会发出颤抖和嚷叫。”而在赫胥黎(Aldous Huxley)眼中,劳伦斯似乎属于“那种神秘的物质主义者”(a kind of mystical materialist)[5]475。这个“优雅敏感的器官”对物理性的地域和神秘的灵魂间的关系,似乎有着特别灵敏的感知和意识。
“地之灵”(the spirit of place)这个概念,是劳伦斯后来在《美国文学经典研究》(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中提出的,劳伦斯认为,“每一个大陆都有其伟大的地域之灵。每一国人都被某一特定的地域所吸引。地球上的不同地点放射着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化学气体,不同的星座放射着不同的磁力——你可以任意称呼它。但是地域之灵确是一种伟大的真实”[6]7。这个带有某种神秘的宿命意味的思想,在《意大利的黄昏》中已经初露端倪,只不过其范围尚未从旧大陆扩展到新世界。劳伦斯在这里追寻的不是一个大洲或一片大陆的灵魂,而是一个更为具体的、界限明确的地之灵。
首篇《跨越群山的十字架》记录了作家从慕尼黑穿过蒂罗尔,徒步行走在通向意大利的皇家大道途中,一路看到的乡村景观——“一座十字架接着一座十字架带着它们的篷顶渐渐地、朦胧地隐现出来,这些十字架似乎在整个乡村制造了一种新的氛围,一种黑暗,一种在空中的凝重”[7]2。在劳伦斯看来,十字架上那些由当地农民自己亲手雕刻的耶稣像,它们那或粗俗或精致的风格,或痛苦或高贵的表情,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特征和文化个性,是构成地之灵的精神内核。换言之,“地域的物理面貌与生活于其中、并被其所塑造的人们融为一体了”[4]179。
共由8章组成的《在加尔达湖上》,是整个游记的核心内容。劳伦斯通过一系列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精心的描写,刻画出了意大利民族灵魂的两极——白天与夜晚,光明与阴影,本能与理智,感官与精神,身体与心灵的矛盾与对比。年老的纺纱女代表了意大利人感性的、本能的、无意识的一极。作家着意描写了老妇人的纺线动作,那是一种无意识的、出于本能、不假思索的动作。纺纱女从身体到感官,完全沉浸于自己的劳作中,完全与自然力合为一体了。她几乎不需要费多大力气,本能地就能让自己手指的动作适应于纺车的转动,纺出一梭梭毛线来。纺纱女的本能与感官、身体与心灵完全协调一致,她甚至注意不到周围的世界,注意不到陌生人的存在。劳伦斯说:“对她来说,我只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仅此而已。她的世界是明朗的、纯粹的,没有自我意识。她没有自我意识,因为她并不知道除了她的世界以外,世界中还有任何东西。在她的世界中,我是陌生人,一个外国先生(signore)。我有一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她的世界,是她想象不出的世界。”[7]26“她似乎就像《创世纪》,就像世界的开端,就像第一次清晨。她的眼睛就像天地间的第一个清晨,永远不老。”[7]28老妇人代表的这个世界,是与机械主义相对的、前工业时代的遗存,也是一个正在无情的现代化过程中飞快消逝的世界。
与纺纱女形成对照的,是作家从教堂高处向下望的时候,看到的两位正在散步的僧侣。他们用僧侣特有的一种大而懒散的步子走着,边走边说着悄悄话。除了大而诡秘的步子和靠向一起的头,什么动作也没有。但是,作家感觉到,“他们的谈话有一种渴望。仿佛幽灵般的生物从它们寒冷、隐蔽的地方冒险跑出来一样,他们在荒凉的花园中走来走去,以为没有人能看到他们。”[7]33“他们的谈话中既没有热血也没有精神,只有法律,只是平均的抽象。阳性与阴性乃是无限的。但平均只是中庸。而这两个僧人在公允的路线上踏过来又踏过去。”[7]34这里,僧侣的神秘性、精神性、沉思性和无动作性,与纺纱女出于感官的、本能的、忘我的、无意识的动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劳伦斯看来,前者代表了夜晚的灵魂,后者代表了白昼的灵魂,两者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意大利的“地之灵”。但两者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巴巴拉兄弟和朱丽娅·葛吉兹认为,“劳伦斯的旅行写作与其说是描述了其所拜访过的人们和地方,不如说是纪录了他自己对之作出的反应。地方是物理性的存在,但读者能够进入劳伦斯的内心世界,知道他对这些地方和人群的情感。”[4]179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在许多场合,劳伦斯是在借旅行写作之便,不断地提出,印证,重述,修正或完善自己的血性意识和阴茎崇拜理论。
在《柠檬园》中,作家从他下榻的旅馆的整体空间布局、色彩搭配,以及房间内外的明暗对比等细节出发,沉思“意大利的灵魂”。他认为,意大利人之所以具有吸引力,讨人喜欢,漂亮,就在于他们崇拜肉体中的神性。这一点,他从旅馆老板这里得到了证明。旅馆老板因自己没有孩子而感到羞愧,在自己的太太面前,在前来住宿的客人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来。“他存在的理由似乎就是要有个儿子。可是他没有孩子。因此他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他是虚无,是一个消失在虚无中的阴影。他感到羞愧,他被自己的虚无消磨了。”[7]54对此,作家在惊诧之余,发了一段宏论:“于是我明白了,这就是意大利人对我们具有吸引力的秘密,这是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对意大利人而言,男性生殖器是个人创造性不朽的象征,而对每个男人而言,这是他自己的神性。孩子只是这种神性的证明。”[7]55
由此,作家反躬自问,作为一个英国人,“我们的优越在哪里呢?只因为我们在追寻神性时、在追寻创造源泉时,超越了男性生殖器。我们找到了物质的力量和科学的秘密。”[7]55但是,悖论就在于,北欧人在发展科学、发明机械、征服自然、获得财富的过程中,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变得乖张,具有破坏性,满足于在肉体的毁灭中得到快乐。机械已经使人变得不近人情,使人成为它的一些属性。“……由于这个机械化的社会是无私的,因而也是无情的。它机械地运转着,毁灭着我们,它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的上帝。”[7]56这里,作家从自己独特的生命—机械对立的哲学出发,给出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深层原因。
劳伦斯不无沮丧地看到,在机械日益统治世界的时代,旧日的秩序正在意大利急剧地消逝。土地已经被废弃,金钱取而代之。农民正在消逝,工人取而代之。那么,意大利人还能保持其与生俱来的地之灵,保持那种对肉体的崇拜,对男性生殖力的崇拜吗?在加尔达湖上的一家小酒店里,劳伦斯似乎看到了希望。那些来自荒野山中的农民、伐木者,或烧炭工,在酒酣耳热之际,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蹈。“这是一场奇妙的舞蹈,奇妙、轻快,随着乐曲的变化变化着。但是,它总有一种从容闲适的高贵,这是一种曼妙的波尔卡-华尔兹,亲切、激昂,然而绝不匆忙,它的激情中从来没有狂暴,但它却总能变得越来越紧张。”随着乐曲的弹奏越来越快,舞蹈的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男人仿佛要飞起来,仿佛在用另一种奇妙的交叉节奏的舞蹈包围着那些女人,而女人则飘舞着,浑身抖动着,似乎有一阵微风轻妙地吹拂着,掠过了她们,她们的心灵在风中颤动了、发出了回声;男人们越来越急速、越来越活泼地舞动着双脚和双腿,乐曲达到了一个几乎无法承受的高潮,舞蹈进入了如醉如痴的时刻……”[7]128这段描写性意味实足,不禁使人联想到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性描写场面。
在瑞士边境,作家遇见了一小群“背井离乡的意大利人”,他们在结束白天的打工之后,晚上还兴致勃勃在咖啡馆里排戏。“在舞台的灯光里,这个小小的剧团朗读着、排练着,映衬着空荡荡、黑黢黢的宽大房间。这似乎有些怪异和凄凉,这是一个与瑞士的荒漠不可同日而语的小巧、哀婉动人的魔幻地域。我相信在古老的神话故事中,在顽石被打开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个魔幻的地下世界。”[7]177
在劳伦斯心目中,这些业余的舞蹈家和演员在跳舞、演戏中迸发的生命活力,是夜晚对白天,酒神对日神,肉体对理智,生命对机械,混沌对秩序,南欧对北欧,意大利灵魂对英国-北欧灵魂的挑战。从这些意大利人中,劳伦斯看到了希望。“一朵新的幼小的花朵正在他们的内心之中挣扎着开放,这是一朵精神的花朵。意大利的基质一直都是非基督教的、都是感性的,都是那强劲的象征,那种性感象征。”[7]181尽管这些意大利的儿子永远也不会回去了,但他们对祖国的爱,对村庄的爱,也可以称之为乡土观念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却深深地打动了作家。劳伦斯动情地说,“每当我的记忆又触及到他们,我的整个灵魂就凝住了,麻木了,我无法再想下去。”[7]188
二、海之魂与岛之灵
《意大利的黄昏》出版3年后,劳伦斯再次离开英国,以逃避一个对他来说难以忍受的世界。他与妻子弗丽达在弗罗伦斯、罗马、卡普利作了短暂逗留,然后去了西西里,他在陶尔米纳(Taormina)租了一套农舍的顶层。1921年,他又完成了一部意大利游记:《大海与撒丁岛》(Sea and Sardinia)。
按照巴巴拉兄弟和葛吉兹等人的说法,《大海与撒丁岛》是一本比《意大利的黄昏》要阴郁得多的作品。这部分要归因于寒冷的天气、糟糕的住宿、难以下咽的食物,以及经常前来打扰的不速之客[4]189。对此,笔者提出不同看法。其实,细读整个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与《意大利的黄昏》相比,《大海与撒丁岛》更具个性化、更有抒情倾向,如诗般的语言融合了拜伦的愤世嫉俗、雪莱的浪漫气质和柯勒律治的想象力,而深层的思考又为它增添了某种理性的光辉。在这部游记中,劳伦斯不仅发展了他的“地之灵”思想,而且还引入了一个新的元素,这就是海之魂。
去撒丁岛首先要渡海。海对于劳伦斯就像对于其他英国人一样,始终有着某种不可名状的吸引力。作家充满激情地写道:
船体缓缓抬起以及它慢慢向前滑动时产生了一种使我快活得心怦怦跳动的东西。那就是自由的姿态。感受它欠起身来又慢慢滑向前方,再倾听海浪船身的声音就像在空中、在大自然的空间里骑着一匹有魔力的马狂奔。啊,上帝啊,船身这有节奏的缓缓上下摆动和像是从它鼻孔里发出的鼻息似的海浪声,这对于放荡不羁的灵魂是何等的慰藉!我终于自由了,在缓缓飘动的风风雨雨中踏着轻捷的节拍向远处飞去。啊,上帝啊,摆脱所有封闭生活的羁绊是多么好啊!那是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状态造成的恐惧,也是机器的强制作用带来的人心灵的彻底迷乱。……啊,上帝啊,自由,自由,这是最本质的自由。我打心眼里渴望这次航行一直延续下去,希望大海无边无际,这样我便可以永远飘浮在这晃动、震颤、总是波涛起伏的海面上,只要时光永驻。我希望前方没有终点,而且自己不用回头,甚至不必回头望一眼。[8]37-38
这段描写继承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使我们联想到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的某些诗句(船儿,船儿带我乘风破浪,/横渡那波澜起伏的海洋;/随你把我送到哪里,/只要不是我的故乡)。但它又超越了前者,加上了对现代性的反思。
船,一直来是旅行文学的核心意象之一。在传统的英国文学作品中,人们往往用换喻手法,用制船的材料“橡木”(oak)来代替船本身。劳伦斯也不例外,但他的出新之处在于,他将对木船的赞美与对前工业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怀旧感,以及对现代机械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了。“这块橡木没有一处不完美、不漂亮。整件作品用木铆钉套接在一起。比焊接在一起的钢铁漂亮得多,也更有生气,焕发着生命力,活生生的古老木头哟,她像血肉一样不会生锈,钢铁永远不会像她那样快活。她十分自如地航行,非常优雅自在地拥抱大海,就像在做一件很自然的事。”[8]39
劳伦斯写出了海之魂,也写出了岛之灵。他之所以选择撒丁岛作为他此次旅行的目的地,是因为在他看来,“撒丁岛与别处不同,撒丁岛没有历史,没有年代,没有门第,也不会给人什么东西。……无论是罗马人、腓尼基人还是希腊人或阿拉伯人都不曾征服撒丁岛。它处于外围,处于文明圈之外……”,远离现代工业文明,远离机械化的生活。尽管“现在它已经意大利化了,有了铁路和公共汽车。不过不可征服的撒丁岛依旧存在,它躺在这张欧洲文明之网里,尚未被人拖上岸。这张网日益破旧,许多鱼儿正从这张古老的欧洲文明之网里溜出去……也许撒丁岛也会溜走。那么就去撒丁岛好了”[8]4-5。
在撒丁岛游历时,劳伦斯特别赞赏的是南部港口城市和首府卡利亚里,因为这使他“联想到马耳他——失落于欧洲与非洲之间、不属于任何一洲的马耳他。它不属于任何一洲,也不曾归属于什么地方,对西班牙人、阿拉伯人和腓尼基人而言尤为如此。然而它遗留在时间和历史之外,仿佛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命运,从来没有”[8]77。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具有某种精神,是机械时代试图蹂躏之,践踏之,却始终没有成功的。在卡利亚里,作家观察到了当地农民的精神状态,他们从穿着、外貌到精神气质都“仍流露出传统的剽悍本色”。作者感慨地说,“同那些柔声细气的意大利人接触之后再看看裹在马裤里的小腿,轮廓清晰,充满男子气,这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人们会惊恐不安地意识到欧洲的男人已濒临绝境,只剩下基督式的英雄、崇拜女人的登徒子以及狂暴却又出身低微平凡的混血儿。往昔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男性不见了,其剽悍的特性也归于灭绝,最后几颗火花正在撒丁岛和西班牙熄灭。除了群氓式的无产阶级、凡夫俗子式的芸芸众生以及一颗充满渴求、怀有恶意、自我牺牲式的、有涵养的灵魂之外,我们已一无所有。”[8]87
在曼达斯,劳伦斯看到的景象令他沮丧,当地的农民已经不穿当地的传统服饰,而是统一穿上了士兵的伪装色,即灰绿色的意大利卡其布。甚至连孩子瘦小的身躯也被裹在这种笔挺、晦暗的长袍和外套里。在劳伦斯看来,这种布料“象征着宇宙间有灰蒙蒙迷雾,笼罩在人头上,消灭个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遮掩一切放任不羁的执着行为”[8]100。灰绿色的卡其布泯灭了人的个性差异,将一个个丰富多样的活生生的人,降格为同质化、一体化的社会大机器中的零部件。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同质化、符号化和机械化倾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劳伦斯敏感地注意到,当火车上的意大利人得知他是英国人时,马上就把他与煤、与汇率联系在一起,于是,独一无二的有血有肉的个体——“我”就成了一个“完美的抽象概念”,一个被贴上“英国人”标签的,由统计数字构成的符号。
在前往索葛洛的途中,劳伦斯遇见了一群刚刚上车、吵吵嚷嚷的农民,他们穿着古怪、举止粗鲁,自信而充满活力。作家一方面讨厌这些似乎尚生活在中世纪,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教化,自我封闭,对外界毫无兴趣的农民;另一方面又觉得,相对于世界大同化、一体化的进程,他们又成为一种对抗同质化和机械化的力量。他“喜欢撒丁岛山上的那些固执而粗俗的人们,喜欢他们的绒线帽,喜欢他们那超绝的、具有动物灵性的愚鲁。但愿世界大同的余波不会将他们那别致的头冠——他们的帽子冲刷得无影无踪”[8]127。出于对机械文明的厌恶,劳伦斯甚至把这些农民的生活理想化、乌托邦化了。他注意到,当这些农民下车时,“我们看见了远处高坡上的托那罗村,看见两个女子牵着匹小马来接那满是污垢,身穿黑白衣服的老农民。那是他的两个女儿,穿着鲜艳的玫瑰红和绿色衣服,漂漂亮亮的。男男女女的农民,男的有的穿着黑色衣服,有的穿着深棕色衣服;马裤紧贴在壮实的大腿上;女人穿着玫瑰色与白色相间的衣服。小马身上驮着褡裢,开始沿着山路慢慢向上爬去,构成一幅极为优美的剪影,爬向远处山巅上阳光灿烂的托那罗村。这是个大村子,像一个新耶路撒冷一样光芒四射。”[8]129
显然,这只是作家带着怀旧情绪和乌托邦情结描绘出来的理想共同体,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污染,保持了中世纪习俗的“新耶路撒冷”。
三、从地之灵到地下之灵
仿佛觉得光有撒丁岛的旅行尚不足以抓住整个意大利民族的大灵,劳伦斯在写作并出版了《大海与撒丁岛》之后的7年,又开始了一场更为诡秘的、真正的奥德赛之旅,这次,他从地表世界进入了地下世界,他的目标不是活生生的当代人,而是那些已经不会开口说话,却把他们的灵魂写在了坟墓的壁画上,刻画在雕像和浮雕中的古老的伊特鲁利亚人(Etruscan)。作家自述,他是在参观意大利中部小镇派拉加的博物馆时,开始第一次关注伊特鲁利亚(Etruria)文化的。伊特鲁利亚人是罗马人之前进入亚平宁半岛的一个农耕民族,他们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活动在意大利中部台伯河和亚诺河之间的托斯坎尼亚地区,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创造了地中海地区灿烂的农业文明,之后被罗马人所灭,其民族文化也随之消隐匿迹。
一个民族从崛起到消亡究竟有什么样的因素在起作用,消亡的民族中是否还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东西,渗透到其后代的灵魂或气质中?在《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Etruscan Places)中,劳伦斯试图通过自己的旅行写作,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描述了劳伦斯在1927年4月6日到11日,与布鲁斯特伯爵(Earl Brewster)两人在古老的伊特鲁利亚之地结伴而行的经历。劳伦斯将他的实地考察的体验,与他从希腊人和罗马人撰写的历史书中抽出来的不多的事实结合起来。[4]192既然伊特鲁利亚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坟墓是他们提供给后人的唯一的信息密码,那么,作家就可以任意驰骋在往昔的岁月中,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的生命哲学投射在这些逝者身上。尽管他在历史书中没有发现多少有关伊特鲁利亚人的记载,但他还是能够从他们的坟墓中找到证据,证明他们像他那样遵循着“伟大的宗教”。[4]192
像前两部意大利游记一样,劳伦斯关注的不是地表的景观,而是地域中蕴含的灵气,一个民族或族群的精神气质。他说,“我来过伊特鲁利亚人呆过的地方,每次总觉得有种奇怪的宁静感及平和的好奇感。……这些巨大的、草绒绒的、带着古代石头围墙的古墓里有种宁静和温和,走上墓中大道,我仍能感觉一种萦绕不去的家庭气氛和幸福感。”[9]15-16但是,更吸引劳伦斯的,是伊特鲁利亚人那种对生命的热爱和享受,“伊特鲁利亚人在他们平易的几个世纪中,如呼吸般自然平易地干着自己的事情,他们让心胸自然而愉快地呼吸,对生活充满了满足感,甚至连坟墓也体现了这一点。……对于伊特鲁利亚人,死亡是伴随着珠宝、美酒和伴舞的牧笛声的生命的一种愉快延续,它既非令人心醉神迷的极乐世界,既非一座天堂,亦非苦难的炼狱,它只是美满生活的一种自然延续,一切都与活着的生命、与生活本来一样。”[9]21这一点,与劳伦斯本人的生命哲学十分合拍。
在劳伦斯看来,20世纪西方世界对机器、知识和金钱的崇拜已经腐蚀了人类最深的根基;只有脱离软弱无力的理性,获得健康的“血性意识”,才能把人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拯救出来。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提出了大胆挑战,公开宣称:“我的伟大教义是对血性和肉体的信仰,它们比理智要明智。我们在头脑里可能搞错。但是,我们的血所感到,所相信,所说的事情总是真的。”[4]192他相信,一个人只有通过他的个人经历——他完全不假思索地进入其中的那些经验——才能达到同他的存在来源的结合;而通向这种经验的途径之一就是女人的身体。性是被血液所领悟的隐藏的神秘力量,身处“极端处境中的雄龟/发出的最后一声/奇异、微弱的相交的叫喊,/从遥远遥远的生命地平线的边缘/发出的微弱的叫喊,/强于我记忆中的一切声音,/弱于我记忆中的一切声音”(《乌龟》)。
在伊特鲁利亚人的坟墓中,劳伦斯似乎找到了支持自己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据。“在地下坟墓中,每个妇女之墓的通道上都有一个石室,而每个男子之墓的墓道前则都有一个阴茎石或阴茎崇拜物。由于大墓都是家庭墓,或许它们两者兼有。”[9]24劳伦斯借给他带路的男孩之口,对此现象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前者代表了子宫,用于保障生命,后者代表了阴茎,是用来创造生命的。伊特鲁利亚人的意识是十分愉快地植根于这些象征物之中的,而这也是这个民族被罗马人摧毁的原因。因为罗马人憎恨阴茎和子宫。他们想要王国和君权,更想要财富和社会成就。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统治各国又要攫取财富,于是伊特鲁利亚人在他们眼中便成了邪恶的化身,他们摧毁了这个民族,夷平了这个城市。留存下来的只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坟墓。然而,“借助这些墓冢美丽的圆顶——代表了死者伟大业绩的巨大圆顶,高高的阴茎头为死者从圆顶上升起。”[9]25
在伊特鲁利亚人的坟墓中,劳伦斯特别看重塔奎尼亚的彩绘坟墓,在这个墓葬群中,他看到了一幅幅小巧玲珑、欢快灵敏、充满生机,充满年轻生命才有的冲动的彩绘画,波浪起伏的海面、跃起的海豚、跳入纯蓝的海水中的潜水者,以及急切地尾随他爬上岩石的小男人;然后是靠在宴会床上的满脸胡子的男子,手中举着一枚代表神秘的再生与复活的鸡蛋。在这些画面中,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舞蹈画面。一个女子在疯狂而欢快地跳着舞,几乎她身上的每一部分:其柔软的靴子、滚边的斗篷、手臂上的饰物,都在舞蹈,直跳得让人想起一句古老的格言:身体的每一部分、灵魂的每一部分都该知道宗教、都该与神灵保持联系。劳伦斯认为,伊特鲁利亚人留下来的这些充满活力的彩绘坟墓,体现的是一种生命的宗教,甚至是一种生命的科学、一种宇宙观以及人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观念,即整个宇宙是个伟大的灵魂,每个人、每个动物、每棵树、每座山和每条小溪都有自己的灵魂,并有自己特有的意识。这种宇宙观和生命观使人能够利用最深的潜能而快乐完满地活着,但现代工业社会和机械文明却反对这种宇宙观,把完整的生命之流降格为单一的机械运动,使人成为僵死的机械的零部件。
显然,劳伦斯在这里借助自己的想象力,发思古之幽情,表现的是他自己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对苍白的现代文明的批判。正如罗纳德·德雷伯(Ronald P.Draper)指出的,“劳伦斯与他的朋友进入伊特鲁利亚坟墓的地下世界,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创造性地表现对衰弱的地表世界的不满。”[10]
那么,伊特鲁利亚的灵魂还活着吗,它还能超越时空的限制,依然存活于现代意大利人的灵魂中吗?劳伦斯的回答是肯定的:“当你在下午四时许的阳光下坐进邮车,一路晃悠着到达那儿的车站时,你可能会发现汽车边围着一群健美而漂亮的妇女,正在对她们的老乡说再见,在她们那丰满、黝黑、俊美、快活的脸上,你一定能够找到热爱生活的伊特鲁利亚人那沉静的、光彩四溢的影子!有些人脸上有某种程度的希腊式眼眉。但显然还有些生动、温情的脸仍闪烁着伊特鲁利亚人生命力的光彩,以及伴随处女子宫之神秘感的、由阴茎知识而来的成熟感和伴随着伊特鲁利亚式的随意而来的美丽!”[9]28
巴巴拉兄弟和朱丽娅·葛吉兹认为,《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适合作为劳伦斯的最后一本旅行书。如果说《意大利的黄昏》反映了劳伦斯第一次游历意大利时的新鲜体验,那么《伊特鲁利亚人的灵魂》则完成了他对过去、现在的观点,总结了他的生命哲学。……劳伦斯的旅行书以一种比他在小说、故事和诗歌中更随意,更无拘无束的方式,显示了劳伦斯本人。[4]192与此同时,这些旅行书也显示了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贯穿整个近代英国文学传统的“朝圣者的灵魂”对自我和他者的追寻。通过意大利—撒丁岛—伊特鲁利亚之旅,作家不仅发现了意大利的地之灵、地中海的海之魂和撒丁岛的岛之魂,以及伊特鲁利亚人遗存的生命精神,也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灵魂。
意大利不仅使我找回了许多、许多我自己的东西,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也使我发现了许多早已失去的东西,就像一个复原的奥西里斯。今天早晨,坐在公共汽车里,我意识到人必须回头重新发现自我,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完整的自我,但除此之外,还应向前迈进。还有未知的、未曾开垦的土地,那里的盐还未失去其咸味。但要涉足这些地方,得先在伟大的过去中完善自我[9]168-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