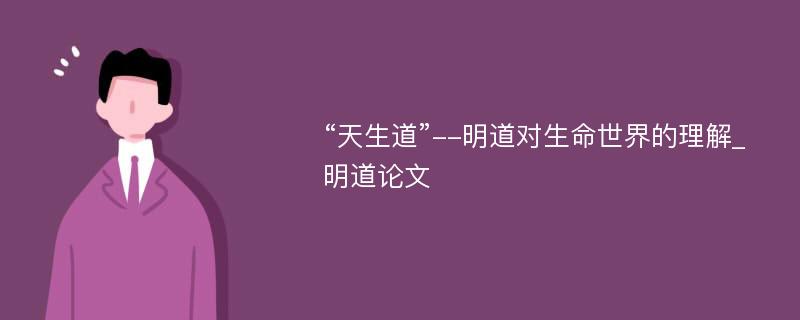
“天只是以生为道”——明道对生命世界的领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道论文,生命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论人们是否在哲学上系统地追问过深度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存有论基础,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人与整个自然万物密密涵继、相互长养的关系已愈来愈成为人类的共识。但衡诸当今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之种种论著,其问题意识却似乎无一不在果地上为之因应,乃至使尊重自然、热爱生命等口号沦为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横行后的一种补偿(注:参见戴斯·贾丁斯著《环境伦理学》一书。贾丁斯认为,西方大多数伦理学理论认为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务于人类时才有伦理价值。在这种意义上,环境伦理学事实上成为一种后果主义者的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
对生命意义的领悟不应当在生命世界残损和碎片化之后产生,而应当在人与自然万物在根源上共相牵挂的慧识中落实,这或许是我们钟情于明道的一个深层原因。
一、“学者须先识仁”
明道之学向以“识仁”一着最为醒人眼目。然而,所谓“识”者毕竟何也?而所谓“仁”之确义又是什么?我们或许可以简洁地说,明道所谓仁即是理,是道;是生生之理,是生机流行之道;而所谓“识”却非认知性的“识”,乃是对此生生流行之理、之道的感通、领悟和体贴,如明道云: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注:《二程集》《遗书》卷二,中华书局校点本1981年版,第15页。下引只注页码。)
“切脉最可体仁。”(同上,卷三,第59页)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同上,第60页)
“观鸡雏,此可观仁。”(同上,卷三,第59页)
明道以生生之机言仁,清澈简约。而其“医书”、“切脉”之喻,“观鱼”、“蓄草”之举,涵咏三味,实有诸己。然而,明道对存在界之真生命的体贴,对自然万物一体之仁的洞见,却不能由此而滑转成一单纯的美感的欣趣。牟先生云:“在明道,由麻痹无觉所指点到之‘以觉训仁’之‘觉’义,由‘切脉’所指点到之‘贯通’义,由‘观鸡雏’所指点到之‘亲和’义与‘活泼’义,由‘春意’、‘生意’所指点到之‘生’义与‘温润’义,皆是相连而生之同一义,而亦与‘一体’义为同一义。皆直指仁心、仁体、仁理、仁道而言也。”(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湾正中书局1996年,第二册,第10~11页。)果如牟先生所言,则对明道之学,如何不只就其境界而点示之、称赞之,亦且能就其义理而纲维之、条贯之,当成题中应有之义。
明道自谓“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注:《二程集》《外书》卷十二,第424页。)“天理”一词固非明道所创,但却是二程思想的核心。对明道而言,天理既是自然万物的普遍理则,亦是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明道云:
“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注:《遗书》卷十一,第131页。)
“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同上,卷四,第73页)
依明道,天理亦即是天道,它具有贯通自然万物与社会人生的普遍有效性,所谓“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同上,卷二,第20页)同时,我们尚须指出,明道言天理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自是指天理之普遍性,“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同上,第38页),如是,物之理、人之理只是天理之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其二,天理云者非玄思之物,非造作所出,而是自自然然的道理,明道云:“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同上,第121页)其三,此天理即是“生生之谓易”的“易理”。明道云:
“‘生生之谓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矣。’易毕竟是甚?又指而言曰:‘圣人于此洗心退藏于密’,圣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终无人理会。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当自得之。”(注:《遗书》卷十二,第136页。)
明道此处乃是将生生之易理关联着人而一体地说,指出人必须就此宇宙之法则默识而自得: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同上,卷一,第4页)
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明道那里,易理即是天道、天理。明道顺“易传”之思路强调人对此天理之默识。“默识”何谓?只是对此天理之体味、体贴和体验。落实地说,人之用神、率性,一切进德事业,终日乾乾,皆落于“对越在天”上。然则,所谓“对越在天”究竟是何意思?在明道,对越非对勘,更非对立。依明道,此“对越在天”之精义和了义即是依天道之自然、本然而应之、顺之,故“对越”所表现的是随顺义,于人一边说,即是显现义,亦即随顺天道并显现天道。但如此说“随顺”与“显现”似有分开之嫌,实则,人之随顺天道,即同时也就是显现天道,此又所谓一本之义,对人而言,“君子对越在天”之工夫的经典表述,则是“依天而天之”。明道云: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则无间断,体物而不可遗者,诚敬而已矣,不诚则无物也。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纯亦不已’,纯则无间断。”(同上,第118页)
此中诚敬、无间断、体物不遗,在明道,乃是兼摄天道之存有论与人之道德实践而一体地言之的说法。依明道,“易”之核心即是“生生之德”,“敬即无间断”就是随顺此天道之生生而生生,不使此“生”有任何之戕害、夭折,因而,敬只是一个自然,只是一个体贴。明道云:
“‘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它万物自成其性须得。”(注:《遗书》卷二上,第29页。)
“天只是以生为道”是存有论的宣说,亦是仁者之自我体贴,此存有论之宣说乃充满着价值意味、在人、物“共存”的一体义下所表达的人、物的“共则”。故对人而言,继此天道之“生”即是价值的最高的善,此善之实现形态便是使万物皆得其“生意”、“春意”。我们必须指出,明道以道言仁,以生言道并非建立在抽象的、观解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知性的陈言,而是实有其真生命的通感体验。故而明道以医家把脉、观鸡雏生机等等比喻,不仅要人体贴出此生命世界畅茂条达,流行不断,更要人从儒者之立场即此生机盎然中领悟出仁心常驻。审如是,我们便可理解明道何以并不讳避“生之谓性”一说。明道云:
“告子云‘生之谓性’则可。几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同上,第29页)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同上,卷一,第10页)
明道以天之自然言道,道即是性(注:同上,第1页。明道云:“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而天之自然即是天道生物、成物之自然,此即是性,性即生也。表面上看,明道在此点上与告子无别,实则告子言“生之谓性”乃落于生物学之色食之实相上,而明道在此言“生之谓性”既指向天道之创生原理,又及于儒者之仁心沁润,此亦犹如横渠以“体物不遗”说天,以“体事无不在”说仁,天道、仁心浑然一体,仁即是此天道之生生,识仁即是体验、体贴此天道之生生。
罗尔斯顿曾经指称:“如果我们想谈论自然的价值,那我们就必须主动地‘介入’(be in on)到这些价值之中;也就是说,必须要以个人体验的方式分享这些价值,这样才能对它们作出恰当的判断。”(注: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5页。)我们不知可否这样理解,罗氏就主张以“体验”的方式以分享自然的价值而言,为我们理解自然找到了一个方向,然而,相对于传统儒家的思考,罗氏的这种“体验”缺少人与自然原本融一的天道观基础,因而其所谓的“体验”仍然是“介入”式的、分隔的观照,而没有哲学的存有论奠基。明道之学示学者以“识仁”为先务,并以“切脉体仁”、“麻痹不仁”体验和领悟出仁即生、生即理即道的生命世界的原理原则。人心在天道观或存有论的意义上乃以天地好生之德以为心,故有体贴、爱惜生命之仁,此所谓“识仁”之真义,亦“识仁”之第一义也。
二、“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仁即生生一旦获得其天道观之基础,那么,此生生之仁必如天理昭融般普润于万物。然而,明道云“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究竟包涵哪些理绪?
依明道,仁之理与天之道虽“分属”天人,但其义只是一个,非二非三。《识仁》篇开篇即云:“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同体”就是一体,明道云:
“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注:《遗书》卷二上,第31页。)
“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同上,第38页)
明道此处要说明,此一体之天理具有客观性,“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时,此天理亦有普遍性,天地万物和人皆同秉此天理,故四海而准,原无少欠,亦不因人之穷通顺逆而有所加减损余。明道之意显然要指明,在天理面前,人与万物具有理的平等的地位,而此天理即是生生之理。明道云:“所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同上,第33页)“万物一体”究竟“一体”在何处?依明道,人之与物就“皆完此理”而言,皆是天道作用的表现,皆是天理之自己如此,即此而言,人与物并无任何差别,所谓“生则一时生”。如是,则我们言一体而尽仁者,其确当义便是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全人之生,全物之生。
人们常将“万物一体”、“浑然与物同体”作为明道造道而有的境界点示语而加以理会,然而我们同时想指出,假如就此而忽略明道“万物一体”所包涵的严肃的存有论的思考,则此浑然同体之仁便不免转而成一轻佻的审美情趣,盖明道所言之同体、一体实奠基在“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同上,卷六,第81页)的根源性的存有论基础之上,“天人本无二”之“本”则是一种根源性现象之“本”,其直下即可发而为仁者在其生命和生活世界中视听言动所必有的生物、成物之义,且惟生物、成物乃可尽此“天人本无二”之一体义、同体义,此即是生生之大德,生生即是天道,即是仁。明道云: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同上,卷二上,第15页)
“若不一本,则安得‘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同上,第43页)
此处“只心便是天”之意义必得在天人“同体”之“本”上来了解,职是之故,明道乃可以说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同上,卷二上,第15页)这种充满玄趣而富有智慧的言说。如是,在“一本”之意义上,心能尽此天道生生之大德,即性、天之道便皆全幅如如地彻尽其义蕴,如是,即使生者自生,成者自成,而世界皆充满和洋溢着生意与春意,此务正性命,物各付物也。此处我们要指出,从哲学上看,明道“与物同体”之一本论的形上学思考,就其根源于天道生生之实义而言,已为我们尽仁践性之一切行为给予了存有论化,此即充分地表现在,我们在说合天人时,天人早已经相合(注:在明道之思想中,所谓“合天人”之说,相对于其根源性的天道存有论而言,已只是一种“权说”,所谓“为不知者引而致之”而已,故明道云:“除了身只是理,便说合天人。合天人,已是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无间。夫不充塞则不能化育,言赞化育,已是离人而言之。”(《遗书》卷二上,第33页)),故而仁者之作为在这样一种根源性思考中已一转而成为天道生生之显现,此“显现”亦可称之为“天人本无二”之“本”的发露;另一方面,就涉及到本论题之主题而言,此“与物同体”之一本论亦为万物生存之尊严提供了形上学的存有论基础。(注: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曾言:“对人来说,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其他形式的生命的尊严,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见氏著《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2~33页))
然则,所谓万物生存之尊严的形上学基础究竟将从何处看出?假如真的象一些生态伦理学者所说的那样,从尊重生命的角度起见,伦理学乃必得为万物中的其他生命找到其应享的、恰当的位置,那么,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这样认为,明道的“同体论”或“一本论”恰当地承担了伦理学的这一重要任务。明道指称,“与物同体”之“同”即同在人、物同秉此天道生生之理,由是明道认为人之与物原无差别,原无少欠,盖人亦物也(注:明道云:“‘天地设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盖人亦物也。”(《遗书》卷十一,第118页)明道此一论点与横渠并无多大的区别,人们从横渠“人但物中之一物耳”、“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等等言说中完全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所不同者,横渠从“太虚即气”论入,而明道却不走此路,而从《易传》天道生生之理论入,兹不赘论。)。换言之,我们不得视“物”为无所足道,或为我们随意取用之对象。从“同体”、“一本”之立场而观,万物原非与吾人处于对立的地位。明道云:
“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注:《遗书》卷一,第4页。)
“‘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它底。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同上,卷二上,第33~34页)
人与物就天道之存有论的角度视之,皆是被造之物,均匀无差地参与(share)和体现着天道的创生,如是,即“自家心”与“鸟兽草木之心”亦无差别。但此“心”非人之道德实践之自觉心言,而是指人与物平等地所体现的“生意”、“春意”言。从人与物同享天道生生之理以观,在明道那里,生命世界之尊严已经获得了存有论的最后保障,这种保障是从最原始、最核心处用心和开掘出来的,移易不得,藐视不得。
从人与物之“理同”的角度看(注:明道思想既强调人与物“理同”的一面,又突显人与物“气异”的一面,待后我们将就此作出论述。),明道显然意在提醒人们,重要的是,作为人,要默识并心信此天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然而其为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测。天道默默,人却须在生活之最切近处聆听天道生生之语文诉说,并循其理,藉仁心之感应而实有地与万物为一体。明道云:
“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如何?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注:《遗书》卷四,第74页。)
照理,明道之文本并不难理解,手足疾痛而心之不觉不察,此麻木不仁之栩栩如生的写照。然而,明道却要让我们“领悟”出人之自身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在此一隐喻(metaphor)中,明道以其圆润的智慧传达出传统儒家看待万物与人之间的血脉相贯的关系:人若对于与自己共生共养的其他自然生命风顽痿痹,视若无物,此即是“不仁”、此即是“无恩”、此即是“自弃”!而不仁者,天罚之;无恩者,天惩之;自弃者,天弃之,此亦明道言“能近取譬”以观仁之同体义、一体义所必有的内在涵义。明道云: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同上,卷二上,第15页)
所谓“万物一体”,其最直接而当下的意义就是体认到世间万物都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莫非己也”。然而,这种体认却非堕体黜聪的想象和虚见,而是实有诸己地真切感受到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乃是与自己的生命具有同等之意义与地位的生命,血肉相连,气脉相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三、“患在自私而用智”
明道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乃直指人之“向上一机”的直觉领悟,但此一领悟,就其为仁者言固可表为境界上说;就其为万物一体之理上言,亦是遍摄义之实说。然则,无论是境界,还是实理实事实说,依明道,皆是依天道之自然而自然(注:此处所说的明道的所谓“自然义”,其中心意思即是无伪和无私,与那种纯全的自然主义的自然义并不相同,此亦是儒家所固有的立场。),皆是依天而天之。
如前所云,明道言天理天道极重其自然义,但此自然义是一本义之自然义,同时,明道亦藉此表明,人以及宇宙间所有的生命皆是道中之物,赋有本体论的实有与尊严。明道似乎特别注重“天人本无二”之“本”的自然义,而此义是在极高的境界上融摄天人后而言的天道流行,诚体流行。明道云:
“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说合天人。合天人,已是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无间。夫不充塞则不能化育,言赞化育,已是离人而言之。”(同上,第33页)
“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赞者,参赞之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之谓也,非谓赞助。只有一个诚,何助之有?”(同上,卷十一,第133页)
《中庸》言诚乃是天与人、本体和工夫一体而说的,其间浑无缝罅。即此而论,明道认为,“合天人”只是一种权说,换言之,“合天人”并非天人之根源义,根源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天人无间”,原本就无间,故不存在合不合的问题。明道以“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释“参赞”,其重心显然落在一个“奉”字上,“奉”即是“事奉”、“敬受”之谓,亦即不在天道生生之外有人之嗜欲的放纵。审如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明道会接着说“非谓赞助”,只一个“诚”已经参天地、赞化育了。实际上,细心体贴明道的语脉,我们大体可以揣度出明道对于人主宰万物、役取万物的欲望似乎有着敏感的警惕,盖所谓“赞”之、“助”之,难免将吾人之私意混杂其间而浑然不察,“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亦以为赞天地之化育的一部分。明道云:“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至如言‘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当如此。人几时与?与则便是私意。”(同上,第30页)此处“与”字之了解大体就是明道所谓的“非谓赞助”之意。明道此处话分两头,“循性”、“率性”、“循理”等等似乎是在圣人份上说;而“修道之谓教”,此则专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复之,则入于学。”若在圣人份上,此道与物无对,元不丧失,“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同上,第17页),“则何修之有”(同上,第30页)?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乃可进入到对明道《定性书》之了解,明道云: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注:《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第460~461页。)
《定性书》,依朱子,说的是定心工夫(注:朱子在《语类》卷九十五和《文集》卷六十七中有专文讨论“定性”之文字,学者可参看。)。依明道,从“天地之大德曰生”到“满腔子侧隐之心”似已曲折地表达了天地以生物为心(注:事实上,明道也曾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意思,明道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为心。”参见《河南程氏外书》卷三,第366页。),此处以天地之“心普万物而无心”为言,其意则在表明天地有生物之心而无自私用智之心,因而此所谓“无心”即是说无私情、私授、私爱、私欲之心;明道反对只知一味消极地、槁木死灰般地防止内心邪念和外物引诱,所谓“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主张上提一机,“大其心使开阔”以应天,应天即是前说的随物、顺物而润物。如是,我们即不难了解,圣人以物之喜怒为喜怒,了无个私之印痕,不凿偏我之阙迹,自然无烦忧郁闷,无内外动静,此即是“内外两忘,澄然无事”。所谓“内外两忘”亦是无我相,无我迹,不以私情加诸于万物,任万物各遂其生,各得其养。藉此而明道会说“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注:《遗书》卷十一,第125页。明道此说,与横渠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无我而后大,大成性而后圣”、“无我然后得正己之尽”等有极为相似之处。而明道之这一精神亦与横渠“以我视物则我大,以道体物我则道大”有神契之处。)
圣人之心情普顺万物,以有为为应迹,以明觉为自然,此是本体即工夫之境界,亦可谓之为“天心”“天情”。然而,人固然有应天顺天、应物顺物之心与情,但作为血肉之躯,此心与此情皆可以上下其讲,就芸芸之众而言,其心却常表现为经验心、习气心而有情有欲。此亦如横渠所说之“徇象亡心”。因此,明道对人情、人欲之洞察,对人之自私用智而害于生道之展开,寄予了深切的关注和深情的幽怨,故明道云: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
人情之蔽大体在自私和用智两个方面,所谓“自私”,直白而言,即是顺人之生物本能以发,依生理欲望而行,或随心理情绪而动,在明道的观念中,凡是不顺天道自然之则,而应个我之意念、目的、情绪、欲望而发的行为皆是自私的一种表现,所谓“动乎血气者,其怒必迁。”(注:《遗书》卷十一,第129页。)。所谓“用智”,大体而言,其意相当于横渠所谓的“因身发智”,亦即间隔心物、天人同体之义,以物为纯粹的外在之物,并藉心智以认识外物、役使外物(注:参见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此内外有对、物我相恃之思维便将人对天地万物之明觉感应、领悟体贴一转而为倚占、袭取之功,而不能就物之存在之迹上以天情应合之,以天常普化之。明道云: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德也。”(同上,卷十一,第123页)
“人于天理昏者,是只为嗜欲乱着他。庄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此言却最是。”(同上,卷二上,第42页)
“只著一个私意,便是馁,便是缺了它浩然之气处。‘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这里缺了它,则便这里没这物。”(同上,第29页)
“人心莫不有知”,扩充得去,便是天地变化草木蕃,此人心之知即是此天理天道,但若肆于各种欲望,即此天理天道将蔽于消亡,明道所谓“亡天德”就是亡此天道生生之德。人之欲望使人之生命纷驰散乱,导致人不辨真伪,不识真妄,而去天愈远,明道云:
“须要有所止。”(同上,卷六,第83页)
“知止则自定,万物挠不动。”(同上,卷二上,第30页)
“万物各有止”之“止”乃止于天理流行。凡动于欲,牵于物便不能安其所止,便是亡天德,“废天职”(同上,卷六,第82页),此是正面工夫之表示;另一方面,明道亦要人克制私欲,落在习心上说,明道云:“‘克’者,胜也。难胜莫如‘己’,胜己之私则能有诸己,是反身而诚者也。”(注:《外书》卷三,第367页。)人能胜己之私,当下即是天心朗现,是生生之德之流行,故而能“克”即诚,诚即克也。明道深刻认识到人之自私用智与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之境之不相容,但即其总体思想以观,明道要人用力处主要不落于消极堵绝之曲折和跌宕,主要不落于从已呈现之现象和后果上要人极力防护、补救,规规于从在手状态上限制人之私欲,此虽亦需要,然却是非得力、非根源、非究竟之一着,诚如其所谓“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其端无穷”即如前所说的人之嗜欲如沟壑难填,并与时而变,与时而进,若于此用力,即可能永远凑泊不上。因而明道要人积极地从天心即吾心的道德本性出发,“直下使吾人纯道德的心体毫无隐曲杂染地(无条件地)全部朗现”(注: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二册,第239页。),而终至其“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之境界。果若如此,我们便可说,明道之思想为我们的天人、物我关系提供的不是一种“后果法”,而是一种“根源法”。
顾视当今所谓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其源固然是人之自私用智而致,但对治之方亦必当在根源上下手,识其生则一时生,损则一时损之理,此所谓从深处悟,从大处觉。若只是规规于灾难之生,而步步为营以为逆挽堵绝,此权法之应用,其结果不灭于东而生于西倒反显奇怪。
四、“无人则无以见天地”
无庸讳言,明道思想极重天理、天道之自然义,所谓天理乃自自然然的道理,不劳人力等等,但此自然义若不通透至其道德创造之内圣一面,若不挂搭在人之德慧的感通明照上面,即此自然义之意义既无从看出,而明道亦不免被沦为一纯粹之自然主义者,此即“真成一大塌落”(同上,第12页),而根本上不合儒者之情怀。
又,即便就明道“天人无二”之一本论而论,对其了解亦有不同之进路。天人既为一本,非二非三,则将天人之间了解为一种“同属”(belonging together)(注:此处所谓“同属”乃从海德格尔那里转称而来,海氏在《同一律》一文中谈及思维与存在之同一性时,曾使用了“共属”(德文Zusammengehoren)一词。本文为适应明道之“同体”一说,故生造“同属”一词。学者可参看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446~460页,同时,亦可随附参看“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一文,第820~843页。)关系应是得当的。然而问题在于,此一本之“同属”究竟该作何理解?
在现实世界中,物我、内外、天理人心常常是或者说表象上是分而为二的。因为有此分,故须合。此明道所以说合天人乃“为不知者引而致之”,而为权说,为方便法。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先看到天与人之分别,然后将天、人两者置于“属”的关系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同属”之“属”无非是说被规整于一种“同”之中,它看到的是天、人或天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多样性的、分别的统一,思想的任务就是在此分别中完成综合。我们想指出的是,如今大部分讨论生态伦理的论著,在论述到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时基本上所取的就是这样一种进路。但显然的,这一进路似乎并不符合明道的思考,盖明道天人一本之“同属”,乃是先从“属”出发来理解“同”之意义,“属”不是分别的统一,而是说天人之“同”要从“属”来经验。换言之,天与人之“同属”是同一中的互属。此同一中之互属,人所见者则常常为异,而其根源之“同”却未得审察。《遗书》卷十四有一则门人问学记云:
“或问:‘系辞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系辞虽始从天地阴阳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弃,如此夫!’是岂不同?”(注:《遗书》卷十四,第141页。)
明道举《易》、《庸》与《诗》之诸经之“属”(“异”),而要人领悟出“纯亦不已”之“天德”之“同”,经为道言,其要在不同之道说中体贴出“天之所以为天”之“同”。故此“同”所表示的是一种内在于同一或同体的关系,此同体亦不是说二个体相同,而是说只是一体,是一本之互属;同体是表示整体,此整体先于天人之分别,如是,此天人之分别就其根源于一本或同体而言,乃是一种非分别中的分别。
明道“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所表达的一本论是根源之“合”先于表象之“分”。从天人之间共相牵挂而说,人“一本”于天,则人属于天,也是倾听着天。在这种倾听中,人的存在,人在此生存世界中的作为,乃是一种对天道之召唤的回应。明道云:
“善则理当喜,如五服自有一个次第以章显之。恶则理当恶,彼自绝于理,故五刑五用,曷尝容心喜怒于其间哉?舜举十六相,尧岂不知?只以它善未著,故不自举。舜诛四凶,尧岂不察?只为它恶未著,那诛得它?举与诛,曷尝有毫发厕于其间哉?只有一个义理,义之与比。”(同上,卷二上,第30页)
明道此段既涵有要人随顺天理,反对人为私意造作之意,但同时它又明确无误地表达了人活在此世,则回应天道之召唤乃是人之天职的观念:舜诛四凶,举十六相,如此者皆是随顺、回应天道之召唤、履行天职之行为。在明道,天道生生之大德总是需要人来“现身”,而人也纯全是一构成性之存在物,换言之,天道之如何“现身”,其主导者在人,但此主导乃是互属中的主导,天与人相互归属。审如是,在明道“天人无二”的格局中,天与人皆无独立性可言。
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明道透显的是“人亦一物”;另一方面,天与人的关系同时又表现为天道并非是一客观超越的实体,它需要通过人来加以彰显,故人必须竭尽其天道存有论之天职。无人,则天地只是此天地,块然死物,地老天荒而已,谁得其“天之所以为天”之意义?又谁见其生意、春意之盎然?故明道云: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无人则无以见天地。书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易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同上,卷十一,第117页)
假如我们将“无人则无以见天地”并合着“惟人万物之灵”一起看,其字面意义难免遭致“人为世间主宰”之误解。要解明此中缠绕,我们必得回到明道一本论中人之与物“理同”而“气异”之“气异”所包涵的天地情怀与责任意识中去。明道固重人之与物之“理同”,然则,在“气异”方面明道言之亦同样系统而真切,我们再看:
“人与物,但气有偏正耳。”(同上,卷一,第4页)
“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不得。”(同上,卷二上,第33页)
明道言人、物之别在此并无新颖独特之处,简而言之,万物同具天理,但因气禀之偏正,形气不同、本性流行也不同,而有人、物之别。此“别”在明道则被称之为“人能推”而物却不能推。然而,人之能推,在明道,即可诠释为人有自我意识,有道德之自觉,并能将此道德意识推行于万物(注:参见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第284~285页。),故“推”又包涵有实现义;物虽备此天理,但却没有此意识之自觉。然则,人与物虽有平等义,而人却更有道德意识,以及因此道德意识而有的天地情怀,因而,在明道那里,“人之能推”必进之于“人之有忧”,此道德意识一条鞭之作用所必具、必有之进路,我们亦必当说破至此,才能真正领悟到明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境界,以及在此境界中满满的忧患。明道云:
“鼓舞万物,不与圣人同忧,此天与人异处。圣人有不能为天之所为处。”(注:《遗书》卷二上,第22页。)
“‘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人,人也,故不能无忧;天则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也。”(同上,卷十一,第119页)
“‘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天理鼓动万物如此。圣人循天理而欲万物同之,所以有忧患。”(同上,卷五,第78页)
“忧”者,忧患、忧虑之谓,此忧就忧在人“不能为天之所为”。天地之中,物不能自觉,只有人能觉悟到仁(仁则生理之在人者),并推此仁及于万物。但人为血气之躯而不免“自私用智”,故不能无忧。从一本同属之意义上,“人之能推”以及“人之有忧”必转出对物之关切、关爱及人之责任,此即所谓“欲万物同之”之谓也,而能“万物同之”即是天地情怀。故而此推、此忧非冷然的理智参与,而是顺天地生物之本性。推之内容即是仁之爱,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直至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皆得其护育保任。言及于此,我们便不难看到,在明道那里,人与物之异已逻辑地转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担当和道德责任。
儒家的道德进路,在明道,表现为人之能推爱、有忧患而具天职,而此一点在明道思想中实可以以“无人则无以见天地”一句综括之。“三才”之间,人为天地之心而为最灵,但此意在明道的思想中却不能解释为人能将自身之存在(如人之意志、欲望和情绪等)加诸、投射到他人、他物中去,亦非说人在万物之中能创制一套语言用以把握外在的万物。从一本之同属的意义看,我们也决不会将人理解成一个孤零零的、寡头的道德主体,或是构成一切意义的先验我。明道强调“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所谓“见”即是彰显、呈现、实现和明照之谓。依明道,在此天地万物之中,只有人才有领会天道、天命的能力,也只有人才有开显天地万物的能力,万物之生意无人即无以实现、无以呈现。人藉其一体之仁,经由自我领会和感通,而不断地站出,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故人之尽此仁心同时就是彰显了天之所以为天的意义。
然而,“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此句更赋予人以庄严的道德责任担当,在明道,这种道德责任本质上是以天职表现出来的。在此世间万物中,只有人才有天命意识和天命感,盖明道明言,上天之载,其理谓之道,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为人之道,尽此天地生生之道为人之命(同上,卷一,第4页),故明道又云:“心具天德,心有不尽处,便是天德处未能尽。”(同上,卷五,第78页)此人之命即是人之使命、天命(注:明道也曾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见同上,卷十一,第125页。),我们亦可谓之为天职,此天职之核心内容即是天德。由是而观,“无人则无以见天地”形式上好象将人看作是万物的占有性的主宰,但在明道的思想脉络里,此人乃是以天德为天职的人,是“动以天”而“以茂对时育万物”(同上,卷十一,第121页)的人,而人的德性实践,在这里只能诠释为一种明照,以回应天地生物之德之召唤。
由一本之同属而言“无人则无以见天地”,表达的乃是一种显露根据的方式。人之本质存在于天、地、人一体的开放性之中,人之仁心的展开过程即是天地万物的见出过程、彰显过程,无始无终,即觉即化,此所以明道谓“言体天地之化,已剩一体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有天地。”(同上,卷二上,第18页)之实义,此实义传达的是根源处的运思和用心,根源处的切落下手的工夫。
如是,人已不仅仅是其“所是”,更是其“能是”(potentiality-for-being)(注:M.Heidegger:“Being and Time”Harper & Row,Publishers,1962,p183.Heidegger said:“Dasein has,as potentiality-for-Being,lies existentially in understanding.……Dasein is primarily Being-possible.”参见陈嘉映译《存在与世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75页。)。而仁心作为天地万物的一种明照和润泽的本源性动力,亦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其落实处即是成己成物,各正性命。
五、简短结语
明道之学,就涉及本主题之中心观念而论,窃以为以“对生命世界之领悟”一语似最为切当,而其对天道形而上的判言则来自《中庸》、《易传》,对此,明道以儒者仁的情怀,以“天只是以生为道”立论,以领悟和体贴生命世界的生生不息,健动不止。事实上,在北宋儒学中,明道虽为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在经典依据上明显侧重《易》、《庸》以作为形上学的奠基,故其思想中天道观的意味自是不可不寄心留意。若果以“天只是以生为道”立论,则顺生、保生、全生自是律则,不可移易和违逆,以此推演,明道亦不免于阳明所谓“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注:《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之窘境,而以一句“道理自有厚薄”作答。明道事实上不是没有意识到此类问题,故明道云:“夫天之生物也,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岂可逆哉?以天下之大,万物之多,用一心处之,必得其要,斯可矣。”(注:《遗书》卷十一,第125页。)可见,明道以高明的圆转绕过此间瓜葛,其“天理如此”与阳明的“道理合如此”意思相近,但明道显然没有去介入人们现实生活中难免会遭遇到的因“养”而“害”的矛盾和紧张,而是思以翻转提升,以指点人们向上一机达于境界,体味生之气象为鹄的。但此中的纠缠却并不因此而得以消解。
然而,话虽这么说,由明道发展的一体之仁的学说却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此意义不仅表现在人之与物为一本同属之界说,血脉交融之认定上,同时亦表现在仁者即天德以言天职,以茂对时育万物以配命于天的道德情怀和境界上。
此根源性生态伦理观念之开出,尤可使人致意再三,又岂是坊间谫谫之士所可领悟?
而我们必须马上指出,此情怀和境界,在明道,即是人之使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确定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