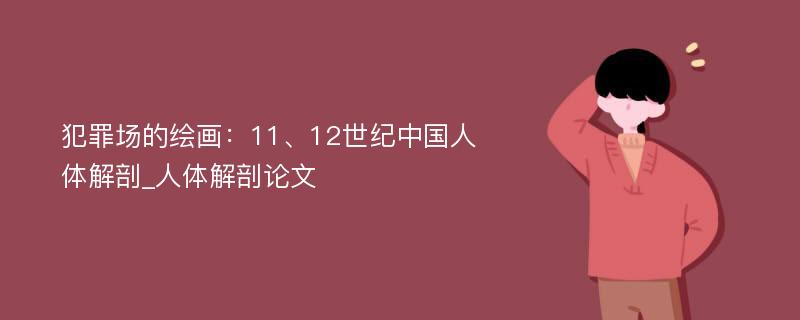
刑场画图:十一、十二世纪中国的人体解剖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场论文,画图论文,二世论文,人体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往以解剖学、解剖史为主题的研究中,有关宋代解剖的历史资料已为研究者频繁发掘。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爬梳史料去证明宋代解剖图在解剖学史上的贡献,而另一些研究者则通过宋代解剖图去阐述中国解剖学及其发展的一般状况。①基于这种主旨,这些研究的分析风格往往习惯于从散见的文献记载中抽取出“解剖”的历史,而不涉及历史事件本身的阐释。以解剖史、解剖学这一体系为基底,对整个历史的长时段予以关注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不过,如果从“中国解剖史”或者“解剖发展史”的广阔单位中转向个别事件,关注解剖事件的细节,并力图去揭示解剖事件与时代的历史环境、价值观念以及技术、知识方式之间密切而有趣的联系,如此,在宋代人体解剖事件中所阅读到的人类医学,既不是徘徊或迷失在医用术语之间,也不是简单地作“统治者残暴”之类的价值判断了。与此同时,通过观察中国人体解剖起始、中间和终结等过程的完整事件,也可略窥当时人对人体解剖的态度以及对作为知识手段的解剖的理解。
一、解剖事件及其系列:类型区分
如果不特意去强调现代解剖、解剖学的概念,②就会发现中国历代有关人体解剖的文献记载不绝如缕。20世纪以来,学者也曾以“解剖史”为题对中国历史上的人体解剖(或者说是对人体所进行的开膛剖腹)展开过讨论。③不过,虽然可以通过“解剖”这一关键词将这些事件以一种连续的方式呈现出来,但事实上,文献中相关事件在记载风格、叙述内容上均有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在讨论宋代解剖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将历史中人体解剖记载作些区分,以厘清其中的类型,概括其中的特质。大体而言,中国文献中的人体解剖记载可分为“非直接的解剖事件”与“直接的解剖事件”两类,而后者根据性质不同,又可再分为私人与公共两种。以下按这三种类型分别论述。
第一类,非直接的解剖事件。这类事件通常不涉及解剖事件本身,它们虽然不是发生在某一具体时间段中的事件,但可以将之视为解剖事件演变的产物。例如,最早出现“解剖”一词的《灵枢经》中说:“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④再如,司马迁所记上古神医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滌五藏”。⑤根据这些记载,现代学者认为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人体解剖(或“类医学解剖”),自然无可厚非,但这类“解剖”记载或是作为观察人体的一个向度、描述人体内部结构,⑥或是用以描述医生高妙的技艺,并没有涉及具体的人体解剖事件,包括解剖的组织者、执行者、解剖来源等信息,因此研究者无法根据这些零散的文本记载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对人体解剖的态度与观念。
第二类,私人解剖事件。这类事件往往直接记载解剖案例,施行解剖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探寻身体的某种秘密。例如,据《太平广记》载:后汉末,有人得“心腹瘕病”,昼夜切痛,临终时,“敕其子曰:‘吾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鎗,容数合许。”⑦又据载:
隋炀帝大业末年,洛阳人家中有传尸病,兄弟数人,相继亡殁,后有一人死,气犹未绝……其弟忽见物自死人口中出,跃入其口,自此即病……临终,谓其妻曰:“……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脑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弟子依命开视,脑中得一物,形如鱼,而并有两头,遍体悉有肉鳞。⑧这则记载还有类似的版本,不过时代为唐永徽年间(650—655),患病者为一僧人,病症为“噎病”,数年未能下食,临终时,“命其弟子云:‘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弟子依言开视胸中,得一遍体有肉鳞的两头鱼。⑨另外,据唐人笔记载:河东裴同的父亲患腹痛数年,痛不可忍,于是“嘱其子曰:‘吾死后,必出吾病。’子从之,出得一物,大如鹿条脯”。⑩
这一类解剖事件分散在正史、类书、笔记等各类文献中,其中混杂着相当多的传奇色彩,但每种故事其实都含有某些类似因素。例如,故事结尾往往以从人体中取出“两头鱼”、“铜鎗”、“状如鹿条脯的异物”等为最后的解剖结果,是因为当时人相信,人类难解的病因皆出于异物、邪物作祟。(11)同样,超出常人的长寿、体健,也与体内形成某种物体有关。据洪迈记载,太原人王超,“曾遇道人授以修真黄白之术”,年八十,仍然“精采腴润,小腹以下如铁而常暖”,后因盗罪获斩,“刽者剖其腹,得一块,非肉非骨,凝然如石”。(12)又据吴曾记载,临海县捕得一盗寇,年八十,但“筋力绝人,盛寒卧地饮冰”,盗寇自言长寿体健是因其“岁灸丹田百炷,行之盖四十余年”,为一探究竟,盗贼弃市后,县令“密使人决腹视之”,果见“白膜总于脐,若芙蕖状,披之盖数十重”。(13)这种身体观显然在一度程度上影响了某些地方风俗,例如,饶州乐平县(今属江西)吕生之妻因难产而死,其腹内死胎亦同样被视为异物,使人“沉沦幽趣,永无出期”,于是,“狃于俗说”的吕生自持刀剖妻腹,“取败胎弃之”。(14)
此外,上述解剖事件中,除了由官员秘密组织的解剖外,施行解剖之人多是被解剖者的亲人:儿子、妻子、丈夫、弟子等,几乎没有医者参与其间;故事中每每强调病人临终时的遗命、遗言,这十数字暗含着道德与法律的张力。众所周知,唐宋律令中规定,“诸残害死尸及弃尸水中者,各减斗杀罪一等”,而所谓“残害死尸”,则指焚烧、支解之类。(15)上引唐宋时期所发生的人体解剖通过被解剖者的遗言、遗命获得了合法性与合理性。(16)不过,历史上确有因解剖人体而受惩罚的案例。南朝大明元年(457),沛郡相县的唐赐往邻村饮酒后得病,“吐蛊二十余物。赐妻张从赐临终言,死后亲刳腹,五藏悉糜碎”,但唐赐的遗言并没能让张氏脱罪,“郡县以张忍行刳剖,赐子副又不禁止。论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子弃市。”不过,因为这则案例特殊,量刑“并非科例”,士大夫对此颇有争论。三公郎刘勰说:“赐妻痛遵往言,儿识谢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谓宜哀矜。”但吏部尚书顾顗之则认为:“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谓副为不孝,张同不道。”(17)可见,双方争论的焦点并非是死尸禁忌与法律条文等规定,而是儒家的伦理道德。
第三类,公共解剖事件。之所以称之为“公共”,一是因为解剖事件的组织者、执行者通常是皇帝、官员等,二是因其解剖目的通常宣称是为了“有利医家”。这类事件历史记载较少。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王莽统治时期所发生的人体解剖。王莽捕获了反抗其统治的翟义谋士王孙庆后,“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18)这则人体解剖事件记载较略,但今人对王莽组织这场解剖的目的、意义及其对中国解剖学的影响有过细致研究。(19)
本文所要讨论的两则宋代解剖事件亦属此类公共事件,分别发生在庆历五年(1045)与崇宁年间(1102—1106)。在这两起解剖中,地方官员是事件的组织者、执行者,刑死者是解剖的尸体来源,解剖现场又有画工、医家参与其间,并留下了两幅人体解剖图。由这些元素所构成的“刑场画图”的解剖场景不仅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且也使得这类事件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人体解剖记载。例如,它们的组织不再是为了特意去发现某些人的某种病症或者长寿体健的秘诀;其用于解剖的人体不再是刻意选择的病人、非同寻常之人等特殊对象;尤其重要的是,在私人解剖事件中不曾出现的医生在公共解剖事件中参与、观看了整个人体解剖过程,而画工的出现则使得这类公共解剖事件在医学史上的价值超越了其他类型的人体解剖。(20)
二、事件的细描:刑场与画图
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说:“中国古代的解剖学出现较早,从扁鹊就开始了,到王莽时代广泛采用,并持续到稍晚的三国时期。从此以后,也像欧洲一样,解剖学便绝迹了,直到中世纪晚期才再度出现。”(21)在这一段叙述中,李约瑟按时序将各个时代所出现的人体解剖记载结构化,从而推导出中国解剖史的线索。宋代的刑场画图事件是构成这一线性历史发展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今人对宋代解剖事件的描述亦是从解剖学史的立场出发,注意到了这些事件在解剖学史上的意义。(22)然而,预设的意义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研究者忽视了对事件本身的阐述与分析,甚至忽略了文献中相关记载的多样性以及关键事实的不确定性。让我们先来看看解剖事件的发生过程。
宋代的第一件刑场画图事件由时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杜杞发动。庆历年间,广西环州思恩县(今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欧(区)希范与其叔因求朝廷录用不报,反被编管全州,于是率族人伙同白崖山的蒙赶(干)等一起叛乱。庆历五年,朝廷令杜杞率军进剿。杜杞先用计假意招安欧希范等人,于会盟当日设宴时用曼陀罗酒灌醉诸人后将其处死,并令医者、画工解剖尸体绘成图。(23)此事在现存的官修史书与文集中均有记载,解剖事件中所涉及的基本事实没有太多差别,但当时所解剖的人体数目究竟有多少,则颇为扑朔迷离。从文献记载看,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24)
其一,当日共解剖70余人。如据李焘记载:当时“擒诛七十余人,画五藏为图”,其他百余人或因老病、或因是被胁迫参加叛乱的则被释放。(25)《宋史》关于此事的记载虽散见于各处,但大略无异,认为会盟当日诛杀共70余人(另一处记载明确说78人),其余老、病等百人则被释放(另一处记载说“余皆配徙”)。至于共解剖几人,落笔时则颇为隐晦,如《杜杞传》中只说,后三日,“得希范,醢之以遗诸蛮”;而《蛮夷传》中则说将欧希范处以醢刑后,“缋其五藏为图”。(26)
其二,共杀600余人,解剖10余人。如《长编》庆历五年三月甲子条下引《宋仁宗实录》称,置曼陀罗酒会盟当日一共擒杀欧希范手下600余人,三日后,才擒获欧希范等10数人,“割其腹,缋为五藏图”。(27)《宋朝事实》所载与之基本相同,《宋会要辑稿》在解剖一事的表述上略有差别,称后三日得欧希范等10数人,“醢赐诸溪峒(洞)”。(28)另一些文献中,记载了曼陀罗酒会当日戮杀600余人一事,其余事实或隐或略。有些记载从语脉上看,似乎仅希范一人受醢刑,例如,欧阳修给杜杞所修的墓志铭中,说曼陀罗酒会当日戮杀600余人,释放“尫病、胁从与其非因败而降者百余人”,后三日,擒获欧希范,“戮而醢之”。(29)范镇《东斋记事》亦载擒诛600余人一事,后三日,得希范,“醢之以赐溪洞诸蛮,取其心肝,绘为五藏图,传于世”。(30)曾巩《隆平集》与王称《东都事略》中说法相同,言曼陀罗酒会当时杀600余人,后三日,“擒希范至,并戮而醢之”。(31)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只说当时杀欧希范及降者600余人。(32)因部分内容相同,这里将上述几种说法列入同一类。
其三,解剖数十人。此说见于叶梦得《岩下放言》、郑景望《蒙斋笔谈》,称当日欧希范带数十人赴曼陀罗酒宴,醉后被执,第二天“尽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肾肠,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33)虽然文中并没有提到具体的人数,但对解剖一事颇多着墨。
其四,当日解剖56人。此说出于赵与时《宾退录》:“庆历间,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吴简皆详视之,为图以传于世。”(34)这里不仅有具体的解剖人数,而且还记载了解剖所花费的时间以及具体负责解剖官员的名字。(35)
其五,杀一千至数千余人。孔延之于庆历五年所写的《瘗宜贼首级记》中称:当日诛杀欧希范、蒙赶及其伪置官属共243人,加上之前所斩之人,总计1494人。(36)而《太平治迹统类》中说,曼陀罗酒大会中,“擒诛数千余人,画五藏为图,释虺病被胁与非因败而降者百余人”,后三日擒获欧希范,处以醢刑后送诸溪洞。(37)
一次人体解剖事件的基本情节相似,但记载的解剖尸体数量却从1人、10数人、70余人到千人、数千人的记载,着实令人眼花瞭乱。从解剖学的角度,解剖观察1人所获的人体知识与观察10数人、70余人甚至千余人以后获得的知识,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差异。然而,有趣的是,后世转录此段记载的人对解剖数字的多少以及记载的不统一性似乎从未提出疑问。换言之,人们似乎并不太关注获得精准的解剖人数(如果从现代解剖学的角度出发,这一点可能是难以容忍的)。相反,记述者对刑场、杀人、解剖、画图等几个细节的落笔并不怀疑,因此,就本文的讨论主旨而言,用“刑场画图”四字大略可以概括整个解剖事件。
宋代第二次刑场画图事件发生在崇宁年间,由泗州郡守李夷行组织。当时,“泗州刑贼于市”,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亲决膜,摘膏肓,曲折图之,尽得纤悉”,后来,当地著名的医者杨介根据古书校验此次解剖所画的图,并命名为《存真图》(一卷)出版印行。(38)此次解剖事件历史记载比较简略,刑死者是谁、参与刑场解剖与画图的医者是谁,俱无从考索。由元人孙焕所刻《玄门脉诀内照图》有“若吴简序、宋景所画希范喉中三窍者”一段文字,可知当时画工为宋景。(39)
总体而言,文献中对泗州人体解剖事件的传抄摘引并不多见,这一点与欧希范事件明显不同。尽管如此,寥寥几句,刑场画图的解剖场景实已相当生动,整个事件仍然从刑场杀人开始,继而解剖人体、画者画图,再由医者校订图画,流程之细致、清楚与上引欧希范解剖事件如出一辙。但是,与欧希范解剖事件不同的是,文献中关于此次刑场画图场面的记载一般是附着在《存真图》之后,其注意力在刑场所画的解剖图而非事件的整个过程上,医者杨介虽然不是这次解剖事件的实际组织者与执行者,(40)但成为此次解剖事件最终的主角。
三、事件的定性:“杀降”与“有利医家”
宋代两次解剖事件发生时,民众是否可以共同观摩巧屠解剖及画工画图已不得而知。按常理推测,由杜杞下令的刑杀与人体解剖虽关乎战争阴谋,但因被解剖人员乃是当时声势颇为强大的反叛者,解剖事件本身不可能是秘密的;李夷行乃是在犯人刑市后令巧屠与医工共行解剖之事,如此一来,无论解剖是当场发生、还是易地而行,(41)也不可能是一件封闭的、完全可以杜绝民众谈论的事件。因此,从当时的舆论入手去讨论宋人对人体解剖事件的态度显然是一条不错的门径。然而,吊诡的是,历史记载似乎有意无意地进行着自己的筛滤,现在所能看到的文献中只有相对简单的事件记载,对于大规模的人体解剖,当时人并没有如我们今日想象般有一番义正词严的词藻与评论。
先来看对杜杞主持解剖一事的说法。杜杞剖杀欧希范后,御史梅挚弹劾杜杞,称其“杀降”,“失朝廷所以推信远人之意”,因此要求皇帝究其罪责。(42)“杀降”本是宋代官员在对付边境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叛乱时常用的手法,比如乾德二年(964)、五年王仁瞻、王全斌伐蜀时,乾德三年剑州刺史张仁谦对付剑州叛军时,开宝二年(969)曹翰对付江州叛军时,庆历四年田况对付保州云翼军叛乱时,均使用了“杀降”手段。元祐三年(1088),张整为广西钤辖时,也曾用“杀降”来对付当地徭族。(43)通常说来,事犯“杀降”的官员往往以贬谪了事,因此,对于梅挚的上言,仁宗皇帝只是“赐诏戒谕之”,(44)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关于杜杞下令人体解剖一事的评价似乎就此止步,“杀降”成为朝廷对整个事件的性质认定。不过,一些文集中似乎对此事的处理并不满意,比如梅挚弹劾杜杞,朝廷虽下诏戒谕,但曾巩与王称仍毫不客气地指出朝廷姑且放任的态度,说仁宗皇帝于此事根本“置而不问”。(45)而杜杞46岁便过世一事,文献记载中更是在相当程度上附会了因果报应的说法。范镇《东斋记事》载:
一日,(杜杞)方据厕,见希范等前诉,叱谓曰:“若反人,于法当诛,尚何诉为!”未几而卒。杀降古人所忌,杞知之,心常自疑,及其衰,乃见为祟,无足怪也。(46)范镇虽将杜杞之死与杀欧希范导致“自疑”相联系,不过在他的记载中,杜杞犹能进行自我辩解,并义正词严地喝叱欧希范为“反人”,“于法当诛”,而叶梦得、郑景望则缺乏这种理解的态度。他们指责杜杞,欧希范“罪固不得辞,然已降矣,何至残忍而重苦之乎?”在他们笔下,杜杞从广西归来不久,“若有所睹,一夕登圊,忽卧于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欧希范以拳击我,后三日竟卒”。篇中,两人更是感叹:“因果报应之说,何必待释氏而后知也?”(47)
与杜杞不同,李夷行下令解剖刑死者尸体,并留下一幅解剖图,但历史文献中几乎鲜有对其个人谋定此事的评价。(48)而且,这一次解剖所留下的图画既非以被解剖者命名(如“欧希范五脏图”),也不是因解剖者或组织者闻名,当时及后世的记载说明一个事实:校编此图的医者杨介才是与《存真图》唯一有关联的人。那么,杨介是谁呢?历史记载说,杨介是位谦虚的医者,素以“医述(术)闻四方”,曾受召为患脾疾的徽宗诊视,在“国医药罔效”的情况下,仅用两服汤药便治愈了皇帝。(49)杨介擅长方药,他开的药方在明代仍有流传。⑧或许是因为杨介的参与,宋人在评价《欧希范五脏图》与《存真图》时,普遍认为后者比前者“过之远矣”。(50)
尽管在看待解剖事件组织者的态度上历史记载较为模糊,但在对待人体解剖这一问题上,文献中的各种记载或委婉、或直接地表达着宋人的看法。例如,关于王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同刳剥王孙庆一事,政府纂修的类书以及文人文集中均有征引。征引时,文字几近照搬全录《汉书》等前代文献相关记载,但这种相同性背后却充满着暖昧与矛盾,每一次重复陈述其实都包含着各种附加的解释。
《太平御览》将王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同刳剥王孙庆一事列为《人事部》“贪”、“虐”两类中的“虐”,《册府元龟》则列为“残虐”类。(52)也就是说,尽管编纂者对所引文献资料不做任何改动与添加,但在资料编排与分类上已表现出强烈的价值判断。《资治通鉴》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下引此条,胡三省注下则插入了多种医学术语来说明五脏与经脉,似乎有意从知识的角度进行补阙而非作道德上的判断。(53)南宋文献如《宾退录》、《郡斋读书志》等在述及《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时,行文末尾均附有王莽刳剥王孙庆一事,但从语意上看则与上述几条大相径庭。兹罗列如下。
(《存真图》)实有益医家也。王莽时,捕得翟义党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治病,是亦此意。(54)
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宜州推官吴简皆详视之,为图以传于世。王莽诛翟义之党,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说今不传。(55)此两条所引王莽刳剥王孙庆一事与上引史料一样,均是照搬《汉书》,但两书照录时,每位作者看到的都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图景与意义。前一条记载认为,李夷行下令对刑囚“决膜摘膏肓”与王莽下令刳剥王孙庆的本意是一样的,皆出于治病的需求;后一条则强调杜杞下令戮剖欧希范及其党,“为图以传于世”,实是填补了王莽时期人体解剖学说不得留传的缺憾。这样一来,不惟王莽下令刳剥王孙庆一事被追认了相应的医学价值,而且杜杞之剖欧希范、李夷行之决膜刑囚亦被置于同一种言说路径中,“为图以传于世”、“云可以治病”、“实有益医家”表达了人们对“解剖”这种知识方式的认识。
当宋人对人体解剖的叙述逐渐由道德谴责转向从医学角度进行赞美时,这种认识上的改变是否对后世医学产生过作用呢?从有益于医家的立场出发,人体解剖与观察继续存在,并成为公开表明医家医术高明的有力证据。宋代以来,强调通过观察人体来提高医术的例子非常多,例如,齐州(今山东济南)人徐遁曾讲,有一年齐州饥荒,“群丐相脔割而食”,其中有一人“皮肉尽而骨脉全”,“遁以学医故,往观其五脏。”(56)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医者张济医术甚高,他在饥荒年人相食时,曾“视一百七十人”,因此行医时用针“无不立验”。(57)明代以后,这一传统依然延续,一些医者强调人体解剖以及亲自观察人体五脏的重要性。如《医学统宗》作者何柬曾说,自己年轻时,“以医随师征南,历剖贼腹,考验腑脏”。《医林改错》作者王清任强调“亲见脏腑”的重要性,他自己曾多次至义塚、刑场看破腹露脏的尸体。(58)这里,刑场、战场、义塚等处仍然是观察尸体的主要地点,但不同的是,上述观察俱出于个人行为,而非政府有组织的解剖活动。宋代以降,有关人体解剖医学上的认识与道德上的松动并没有翻开中国医学史上新的一页,由宋代有组织的刑场解剖画图事件出发所产生的影响,也没能如欧洲那样最终将人体解剖合法化、组织化。
四、事件的重复与不连续:作为知识方式的解剖
庆历、崇宁年间所发生的两则刑场解剖事例虽然相隔约60年,但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刑场)、人物身份(州官、画工、医者)、解剖来源(刑死者)、解剖实质性效果(人体内景图)以及对解剖性质的认定(有利于医家)均有类同性。从这些因素看,我们可以暂时抛开两则事件发生经过、解剖人数等方面的差异,尽可能地将两则事件作为重复发生的案例来分析。
不仅如此,在两则事件中,刑场解剖—画图—医者校订,这一流程之细致与明确在解剖学从未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因此,分析个中原因成为很多研究者的目标。有学者提出,北宋时期皇帝对医学的提倡与贡献,尤其是庆历四年以及崇宁二年,仁宗、徽宗皇帝的兴医诏令直接促成了两次人体解剖的发生;甚至大胆假设,庆历年间的人体解剖是为了教导医学教育机构里的太医生,崇宁年间的解剖则是受北宋末年疑古思潮的影响。(59)总之,研究者相信,两起刑场解剖事件并不是出于某些州官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当时政府及社会关注医学有密切关系。
从因果关系去分析这两起由政府组织的人体解剖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事件得以发生的历史语境。不过,如果考虑到宋代解剖事件的不连续性——由地方官员下令组织的、以医学观察为目的的人体解剖没能为后代所继承,甚至没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重演,那么,试图运用因果关系去分析为什么宋代会发生人体解剖事件时,人们还得去追问这种有组织、有目的、重复发生过的人体解剖事件为什么后来销声匿迹了?那些曾经促成刑场解剖事件的所有因素为什么都不起作用了?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显然并非本文所能企及。不过,要理解解剖事件的断裂性,或许我们可以放弃寻找外缘因素,从宋人如何看待解剖图这一角度,来看他们对解剖作为一种医学基础手段的认识。
两次解剖事件中的图谱均由州官遣画工完成,原始图谱今已佚失,(60)画工之笔法,以及如何用线条来呈现人体器官结构、经络走向等绘画人体内部构造的手法、特征只能在后世转引文献中去发现,不过,《存真图》所附带的文字描述部分提供了解剖时、或至少是人们总结解剖实践时的观察角度与方法。杨介说:
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记,详得其证。吴简云:“……喉中有窃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傍则有膀胱。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类。唯希范之心,则红而硾,如所绘焉。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有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有在心之左。至若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此又别内外之应,其中黄漫者,脂也。”(61)传统中国医学以“内景(境)”来指称人体内部组织结构,这一段文字无疑很好地诠释了“内景”的观念:首先,吴简按由上至下的空间顺序来解读人体内景,由喉出发,至肺之下—胃之下—小肠下;其次,吴简按类分,将所观察到的不同人体内景特点进行归纳,心的大小形状,肝的多少,肾、脾位置的不同,一一记录;再次,吴简甚至关注到个体的特征,对蒙干之肺、欧诠之肝所代表的病症均进行了分析,(62)从疾病的类型去区分个体器官的变化,具有与分类医学思想相同的逻辑框架。当然,一些文字描述颇令人困惑,例如,关于心脏的形状,究竟是观察者观看了因解剖手法不到位所引起的心脏形状,还是作者为了强调“了无相类”而进行的举例,就不得而知了。
从今人的角度来看,人体解剖毫无疑问是现代医学的基础,但是,在11—12世纪,个别人在刑场通过解剖实践所获得的人体知识是否会有较大的说服力,沈括对此就提出过异议。由于《存真图》出现较《欧希范五脏图》晚60多年,沈括没能看到《存真图》所展示的人体内景,他的评论主要是针对《欧希范五脏图》提出的。他说:
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亦谬说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水与食同咽,岂能就口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则纳饮食,喉则通气。(63)南宋医家张杲在《医说》中曾引用此条。(64)我们无法断定沈括是否进行过人体解剖,但他在文中用以抨击“谬说”的依据似乎只是来自于日常身体的感知与经验。沈括用“验之不审”来讲明经过解剖、实证所获得的人体知识之所以错误的原因,在他看来,泛泛的目视只是承袭了当时流行的一般观点,甚至他相信知觉经验要胜于解剖观察。
或许,杨介校《存真图》时所说的一段话更能表达宋代医者对解剖实质的认识。他说:
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记,详得其状,或以书考之则未完。崇宁中,泗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观,决膜摘膏,曲折图之,得尽纤悉。介取以校之。其自喉咽而下,心肺肝脾胆胃之系属小肠,大肠腰肾膀胱之营叠其中,经络联附,水谷泌别,精血运输,源委流达,悉如古书,无少异者。(65)杨介以“详得其状”、“得尽纤悉”来盛赞解剖的进程及画工的努力,他评价《欧希范五脏图》与崇宁所画解剖图的方法是“以书考之”,《欧希范五脏图》的欠缺是“以书考之则未完”,《存真图》的价值就在于“悉如古书,无少异者”。其中所设定的前提是:解剖是为了验证古书上的医学知识,评价解剖结果的好坏是以是否与古书上的记载相一致作为标准。如此,则通过解剖实践所获得的人体知识只是对古书的还原,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切知道此处的“古书”究竟是哪些著作。(66)如此一来,杨介校图时所谓“自喉咽而下,心肺肝脾胆胃之系属小肠,大肠腰肾膀胱之营叠其中,经络联附,水谷泌别,精血运输”等知识记录的模式以及概念化方式并非来自解剖后的发现与创造。从一个医者的角度来看,解剖实践本身并不是对身体的实践解析,而是对已有知识(如“古书”)的验证与追加。(67)
这真是一种特别的认知方式。宋代解剖事件的情节——刑场杀人后解剖再请画工画图——与欧洲医学解剖兴起之初有很大的相似性。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3)从刑场上偷盗犯人尸体作为解剖之用,是解剖学史上不断被重复的历史叙述。虽然他的解剖结论仍有错误,但他通过解剖所获得的人体知识仍被后人认为是医学史上惊人的革命。在制作解剖图时,维萨留斯不仅亲自绘画(据说他非常擅长绘画),他还请著名画家提香(Vecellio Titian)的学生史蒂芬·卡尔卡(Stephen von Calcar)帮助他,并得到了提香的指点。在出版解剖图时,他又亲自选择纸张并监督雕刻图版。(68)
但是,同样是从刑场获取犯人尸体解剖,同样是解剖后绘制解剖图,“刑场画图”情景上的相似性并不意味着双方在性质上具有相同性,一些表面上的差异也未必如想象中那么简单。例如,同样是对刑死犯尸体的观察,两者也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当维萨留斯剖开人体时,他抛弃了流行千年之久的盖伦解剖学的理论体系,而完全致力于观察。但11—12世纪中国的学者与医者显然并没有摆脱旧有理论的束缚,并没有将观察作为重要的技巧。相反,沈括用“验之不审”来表达他对观察手段的不信任,杨介则用“悉如古书”来加强旧有理论、已有知识对解剖实验的引导性。如此,维萨留斯在人体解剖实践中所读到的是与旧有信息不同的人体知识,而中国医者与学者却是在人体解剖过程中找寻验证自己熟悉的信息。
从“画图”的角度看,中国11—12世纪所绘的解剖图、内景图、脏腑图与维萨留斯解剖图的区别是如此显而易见,甚至引不起人们将两者进行比较的兴趣。(69)文艺复兴时期新绘画技术的产生及其发展对维萨留斯解剖图的出版、流传是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存而不论。但就艺术风格而言,这一时期的绘画依然是线描风格,依然使用线条来表现作品,这一点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内境图、脏腑图并无区别,不过,这种同质性并不能取消每种文化的艺术风格中长久存在的民族类型的差异。(70)换言之,当维萨留斯绘制出逼真的人体结构图时,至少11—12世纪中国画工也在自己的艺术风格中表现着自己文化中的人体解剖图式。同样是解剖人体后所绘制的图画,中西方的差异显然不只是源于绘画技术的不同。当然,中国艺术风格上的民族类型是否阻碍了人们建立“逼真”认识人体的态度与方法,那将是另外的话题了。
在中国人体解剖的历史记载中,11—12世纪的两场人体解剖事件是较为特殊的例子,由政府组织的形式以及有明确的医学目的使得它们不同于中国文献中其他的人体解剖记载,当时人从有利于医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两起人体解剖事件也松开了道德束缚与观念禁忌。但是,这一时期的学者与医者并没有从两场解剖事件中得出某些显而易见的结论,比如将解剖纳入医学的范畴,将实验与观察的意涵进一步衍生等等,更没有将人体解剖实践确认为一种圭臬,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知识的可信度。相反,后人将《存真图》附刻于经络图时,虽然承认人体图是为“医家治病用”,但当儒者将之“悬之坐隅,朝夕玩焉”时,通过大规模人体解剖始形成的人体图,也不过是儒者“养身之方、穷理之学”的补充罢了。(71)
注释:
①相关研究如马继兴:《宋代的人体解剖图》,《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号;靳士英:《欧希范五脏图考》,收入《第一届国际中国医学史学术会议论文及摘要汇编》,北京: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1992年,第52—57页;靳士英、靳朴:《〈存真图〉与〈存真环中图〉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李鼎:《宋代解剖〈存真图〉的来龙去脉》,《上海中医药杂志》1998年第9期;岡野誠:《北宋の區希範叛亂事件と人體解剖圖の成立——宋代法醫學發展の要素》,《明治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紀要》第44卷第1號,2005年,第241—264頁,中译文刊于《法律文化研究》2007年第3辑,周建雄译,第185—209页;詹苡萱:《以宋代解剖图——〈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看中国解剖学的发展》,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2009年。除了上述专门研究宋代解剖图的论文之外,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90—191页)、洪焕椿《十至十三世纪中国科学的主要成就》(《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5—158页)、渡辺幸三《現存すろ中国近世まごの五蔵六府図の概說》(《本草書の研究》,大阪:杏雨書屋,1987年,第341—454頁)、祝亚平《中国最早的人体解剖图——烟萝子〈内境图〉》(《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2期)、靳士英《五脏图考》(《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2期)、于赓哲《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邱志诚《国家、社会、身体:宋代身体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12年,第13—25页)等论著中均有涉及。
②关于中国是否有现代意义上的解剖学,以及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解剖历史,可参见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7页;高晞:《“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③例如,陈垣:《中国解剖学史料》,该文1910年发表在《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第4、5期,后收入陈智超编:《陈垣早年文集》,台北: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第362—369页;侯宝璋:《中国解剖学史之检讨》,《齐大国学季刊》1940年第1期,第1—17页,该文后经增删,以《中国解剖史》为题刊在《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号,第64—73页;干祖望:《祖国医学关于解剖方面的记述》,《上海中医药杂志》1956年第10号;等等。
④《黄帝素问灵枢经》卷3《经水第十二》,《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1929年。
⑤《史记》卷105《扁鹊仓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88页。
⑥例如,宋慈《洗冤录》所记载的人体解剖即可归入此类。
⑦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18《医一·华佗》,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65页;李昉等:《太平御览》卷743《疾病部六·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99页。
⑧李昉等:《太平广记》卷474《昆虫二·传病》,第3904页。
⑨李昉等:《太平御览》卷741《疾病部四·咽痛并噎》,第3289页。
⑩张鷟:《朝野佥载》补辑,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6页。
(11)一些疑难病症中,人们观察尸体时虽然没有发现作祟的异物,但均发现了“异状”。例如,据记载,宋太祖赵匡胤随后周世宗征讨淮南时,在战场上俘获一军校,“欲全活之,而被疮已重,且自言素有瘫风病,请就戮。及斩之,因令部曲视其疾患之状。既而睹其脏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则皆青,右则无他异,中心如线直分之,不杂发毫焉。”(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张剑光、孙励整理:《全宋笔记》第1编第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65—266页)
(12)洪迈:《夷坚志·支景》卷4《王双旗》,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12—913页。
(13)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8《灸丹田之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13—514页。
(14)洪迈:《夷坚志·志补》卷18《屠光远》,第1716页。
(15)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18《贼盗律·残害死尸》,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3页;窦仪:《宋刑统》卷18《贼盗律·残害死尸》,吴翊如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6页。
(16)吕生剖妻取死胎一事,因有风俗作为依据,似乎同样也可超然于法律之外。
(17)《南史》卷35《顾顗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20—921页。
(18)《汉书》卷99中《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45—4146页。
(19)参见三上義夫:《王莽時代の人骸解剖と其當時の事情》,《日本醫史學雜誌》1943年1311號,第1—29頁;山田庆儿:《中国古代的计量解剖学》,艾素珍译,《寻根》1995年第4期;李建民:《王莽与王孙庆——记公元一世纪的人体刳剥实验》,《新史学》1999年第4期,第1—22页;等等。
(20)渡边幸三曾断言:北宋是第一个以医学为目的而解剖人体的朝代。参见氏著:《现存すろ中国近世までの五蔵六府図の概說》,《本草書の研究》,第400—401頁。
(2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卷1《总论》第2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21页。
(22)相关研究参见本文注释1所举诸例。
(23)《宋史》卷285《冯伸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613页;卷300《杜杞传》,第9962—9963页;卷495《蛮夷传三》,第14220—14221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46,仁宗庆历四年二月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41页;卷155,仁宗庆历五年三月甲子条,第3760页;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5之82、83,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807—7808页。
(24)下引不同文献资料中的记载可能因为征引时使用材料相同,因此所涉及的内容也雷同。为了避免主题涣散,本文并不着意区分文献的材料来源,只罗列宋人资料中对该段历史的叙述与记录,从另一角度看,文献中的重复传抄也可见该解剖事件的影响程度。
(25)李焘:《长编》卷155,仁宗庆历五年三月甲子条,第3760页。
(26)《宋史》卷300《杜杞传》,第9963页;卷495《蛮夷传三》,第14221页。
(27)李焘:《长编》卷155,仁宗庆历五年三月甲子条,第3760页。
(28)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5之83,第7808页。李攸:《宋朝事实》卷16《兵刑》,《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35册,第245页。
(29)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30《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杜公墓志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04页。
(30)范镇:《东斋记事》卷1,汝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页。
(31)王称:《东都事略》卷46《杜杞传》,《宋史资料萃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第691页。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13《侍从·杜杞》,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81页;卷20《妖寇·区希范》,第639页。
(32)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2,仁宗皇帝庆历四年春正月,许沛藻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5页。
(33)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63册,第744页;郑景望:《蒙斋笔谈》卷上,《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855册,第7页。
(34)赵与时:《宾退录》卷4,齐治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3页。
(35)在历史文献记载中,欧希范事件中还出现了另一吴姓人物——吴香。文献中称,在征讨欧希范的过程中,吴香与区晔、曾子华(一说“吴香、区世宏”,或“吴香等人”)曾进入五峒招降(一说招降蒙赶,或说吴香作为向导帮助杜杞攻打白崖山)。参见李焘:《长编》卷155,仁宗庆历五年三月甲子条,第3760页;李攸:《宋朝事实》卷16《兵刑》,第245页;范镇:《东斋记事》卷1,第7页;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9《仁宗平欧希范》,《适园丛书》,第262页;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30《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杜公墓志铭》,第804页。这一吴姓人物的出现,曾令学者对吴香与吴简究竟是同一人还是不同的人当作一个问题进行观察,见冈野诚:《北宋区希范叛乱事件和人体解剖图的产生——宋代法医学发展的一大要素》,《法律文化研究》2007年第3辑,第205—206页。冈野诚认为两人系同一人,不过他承认,由于历史记载中吴简与吴香官衔并不一致,两人为同一个人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设”。詹苡萱《以宋代解剖图——〈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看中国解剖学的发展》(第40—41页)也单列“吴简”条来讨论吴香与吴简的关系问题,她从宋代职务官衔与虚衔经常不一致、人物本名与字之间经常同时出现在文献两个角度来佐证冈野诚的假设是成立的。可惜文中并无引证任何资料加以说明,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假设。
(36)孔延之:《瘗宜贼首级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8册,第100页。
(37)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9《仁宗平欧希范》,第262页。
(38)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5《医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18页;又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2《经籍考·医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95页。
(39)此书手抄本藏于北京协和医院,后经彭静山整理后出版,见彭静山:《华佗先生内照图浅解》卷1《内照图·喉咙》,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5年,第27页。在引用这段史料时,不同研究者解读时看法颇为不一,例如,马继兴《宋代的人体解剖图》一文认为宋景是画工,渡辺幸三《現存すろ中国近世まごの五蔵六府図の概説》则认为宋景可能是参加解剖的医师(第396页),冈野诚在列举两人的说法后,认为画工说更为恰当,见冈野诚:《北宋区希范叛乱事件和人体解剖图的产生——宋代法医学发展的一大要素》,《法律文化研究》2007年第3辑,第206—207页。
(40)有人推测杨介为刑场画图事件中亲视解剖过程的医者,参见詹苡萱:《以宋代解剖图——〈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看中国解剖学的发展》,第32、36页。
(41)章潢《图书编》卷68《脏腑全图说》记载:崇宁五年,人体解剖在法场当场开胸剖腹,并命医官、画工详视画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1册,第22页)不过,此则记载中的刑死者为杨宗、欧希范等30多人,欧希范作恶地点为徐州而非广西。
(42)李焘:《长编》卷156,仁宗庆历五年闰五月己亥条,第3778页;《宋史》卷300《杜杞传》,第9963页;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13《侍从·杜杞》,第381页;王称:《东都事略》卷46《杜杞传》,第691页。
(43)参见《宋史》卷2《太祖本纪二》,第23、25页;卷3《太祖本纪三》,第49页;卷257《王仁瞻传》,第8957页;卷260《曹翰传》,第9014页;卷270《董枢传》,第9278页;卷292《田况传》,第9782—9783页;卷350《张整传》,第11087页。李焘:《长编》卷6,太祖乾德三年十一月戊子条,第159页;卷412,哲宗元祐三年七月丙辰条,第10026—10027页。
(44)李焘:《长编》卷156,仁宗庆历五年闰五月己亥条,第3778页;《宋史》卷300《杜杞传》,第9963页。
(45)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13《侍从·杜杞》,第381页;王称:《东都事略》卷46《杜杞传》,第691页。
(46)范镇:《东斋记事》卷1,第7页。
(47)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第744页;郑景望:《蒙斋笔谈》卷上,第7页。
(48)关于李夷行以及杨介的生平事迹考证,参见宋大仁:《宋代医学家杨介对于解剖学的贡献》,《中医杂志》1958年第4号,第283—286页;靳士英、靳朴:《〈存真图〉与〈存真环中图〉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272—273页。
(49)洪迈:《夷坚志·支景》卷8《茅山道士》,第940—941页;张杲:《医说》卷6《云母膏愈肠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何薳:《春渚纪闻》卷4《死马医》,张明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页;王明清:《挥塵录·余话》卷2《李氏医肠痈》,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08页;江瓘:《名医类案》卷5《寒中》,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第159页。
(50)朱橚:《普济方》卷116《诸风门·诸风杂治》,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0册,第754页。
(51)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5《医书类》,第718页。
(52)参见李昉等:《太平御览》卷492《人事部·虐》,第2252页;王钦若等:《宋本册府元龟》卷941《残虐》,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751页。有趣的是,上引几则人体解剖事件,如解剖噎病僧人以及瘕病之人,《太平御览》均列入《疾病部》,似乎承认私人解剖事件中的医学目的。
(53)《资治通鉴》卷38《汉纪三十》,王莽天凤三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210—1212页。
(54)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5《医书类》,第718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2《经籍考·医家》,第1795页。
(55)赵与时:《宾退录》卷4,第43—44页。
(56)苏辙:《龙川略志》卷2《医术论三焦》,俞宗宪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7页。
(57)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9,刘德权、李剑雄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7页。
(58)何柬:《医学统宗·附医书大略统体》,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日本现存中国稀观古医籍丛书》,1999年,第576页;王清任:《医林改错》上卷《医林改错叙》,道光十年(1830)刊本,第5—12页。
(59)参见詹苡萱:《以宋代解剖图——〈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看中国解剖学的发展》,第24、30—31页。关于宋代皇帝与医学的讨论,参见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3期。
(60)不著撰人《循经考穴编》中收有《欧希范五脏图》1幅(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第189页),但此图是真是伪,学者说法不一,参见是书范行准“跋”(第206页),以及靳士英:《五脏图考》,《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2期,第71—72页。梶原性全《顿医抄》、《万安方》中载有《五脏六府形》9幅,现代学者研究认为系出自《欧希范五脏图》,参见小川鼎三:《医学の暦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64年,第55頁;富士川遊:《日本医学史綱要》,柬京:平凡社,1974年,第37頁。关于《存真图》在后世的流传情况,参见马继兴:《宋代的人体解剖图》,《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号;靳士英、靳朴:《〈存真图〉与〈存真环中图〉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李鼎:《宋代解剖〈存真图〉的来龙去脉》,《上海中医药杂志》1998年第9期;牛亚华:《中日接受西方解剖学之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数学系科学技术史,2005年,第31—35页。
(61)丹波元胤编:《中国医籍考》卷16《藏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第234—235页。
(62)范镇《东斋记事》卷1在记载《欧希范五藏图》时,曾将解剖时“有眇目者,则肝缺漏”的发现特意标出。(第7页)
(63)沈括撰,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卷26《药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7页。
(64)张杲:《医说》卷8《药议》。
(65)丹波元胤编:《中国医籍考》卷16《藏象》,第235页。
(66)据政和三年(1113)贾伟节《存真环中图序》称:杨介画《存真环中图》时,“取烟萝子所画,条析而厘正之。又益之十二经。”(丹波元胤编:《中国医籍考》卷16《藏象》,第235页)杨介所取究竟是烟萝子画的什么图,以及他从何处获得烟萝子所画,参见祝亚平:《中国最早的人体解剖图——烟萝子〈内境图〉》,《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2期,第62—64页。
(67)在分析王莽刳剥王孙庆事件中,李建民从“脉如何被人看见”这一问题出发,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认为当太医、尚方、巧屠用“竹筵导其脉”时,现代人所看不到的脉,太医们之所以能看到,是因为他们先有了脉的概念。因此,王莽刳剥人体是为了证成医典已知的知识,不一定是发现新的事物。参见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8—273页。而于赓哲则认为杨介之所以要“校以古书”,是因其无法摆脱证圣法古的思想束缚,参见于赓哲:《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92页。
(68)参见 Erwin Heinz Ackerknecht,A Short History of Medicine,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pp.103-104; Albert H.Buck,A Reference Handbook of the Medical Sciences:Embracing the Entire Range of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New York:W.Wood,1900,vol.1,p.306.
(69)至少在现今关于宋代解剖图的研究中,研究者用以对比的图谱多集中于中国历代图谱,包括国外著作中所收录的中国脏腑图、内景图等,而鲜有见到中西方解剖图的对比研究。
(70)参见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潘耀昌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8、264—266页。
(71)邱濬:《重编琼台稿》卷9《明堂经络前图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8册,第190页。
责任编审:李红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