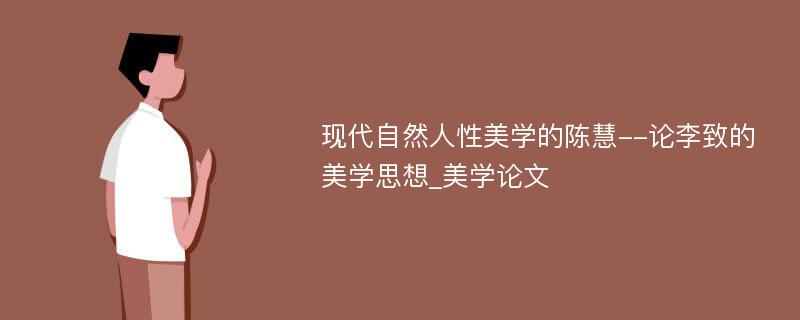
近代自然人性论美学的晨辉——评李贽的美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人性论论文,近代论文,自然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明清之际出现的近代自然人性论美学思潮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李贽是这一美学思想的先驱和主要代表。人性是李贽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童心是李贽哲学与美学的联结点;自然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李贽的美学思想对同时代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贽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他的美学思想开了中国近代自然人性论美学的先河,对同时代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性:李贽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李贽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封建制度已经走向衰落。商品经济在不少地区日趋活跃。衰竭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及其强固的上层建筑百般阻抑新的生产力的生长,使社会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空前尖锐。与政治上的衰败状况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明王朝施行严酷的专制统治。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学术。由于它对孔孟之道进行了充实加工,更加适合日益腐朽的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因此成了该时期的统治思想。理学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纲常名教和封建等级制度说成“天理”。这种“天理”是“至善”的、“永恒”的,人人必须遵守;而“人欲”是“罪恶”的、“危险”的,必须加以抑制和消灭。所谓私欲净尽则天理流行。理学家把封建的统治秩序与道德原则提到哲学的高度,其目的是要广大人民压抑人性,放弃最基本的生活要求,更加驯服地接受统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李贽勇敢地站出来,激烈地反对理学,揭露其虚伪的面目,大胆肯定人性,提倡个性解放。他的学说在当时被视为有如洪水猛兽的“异端”,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
李贽在《初潭集》第一篇《夫妇篇总作》中说:“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是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不亦惑欤!……”宋明理学家认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有一种绝对精神的“理”,“理”是世界的本原。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秩序,就是“理”在人间的体现,企图用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来论证封建统治的永恒性。李贽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夫妇是人类的开始,而天地就好比一对夫妇,天下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两个对立面即阴阳二气所产生的,而没有一个产生万物的精神性的“理”。李贽所说的“一”,就是程朱理学的“理”,即精神;所说的“二”,就是他所主张的“阴阳二气”,即物质。李贽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阴阳二气,而不是生于一,这就明确地指出了造化天地万物的,不是理学所说的那个绝对精神的“理”,而是物质的气。李贽斥责“理能生气”的论调是“妄言”,宣称“不言一”,“不言理”,根本否认了至上“天理”的存在。这样,理学家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就成了子虚乌有的东西,肯定了“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在这种基础上,李贽进一步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①“饥来吃饭,困来眠,都是自自然然的。”②肯定了人性最基本的方面。人在天性方面的要求是共同的,人的本性也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天下无一人不生知。”③“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④人性无所谓贤愚高下,强调人格的平等。李贽所说的人格平等的另一面是承认人们还有不同的个性。他说:“一物各具一乾元,是性命之各正也,不可得而同也。万物统体一乾元,是太和之保合也,不可得而异也。……然则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⑤李贽不仅指出个性的不同,承认差别的存在,而且更进一步提出要尊重人性、发展个性的主张。这就是他所说的要“任物情”,“顺其性”,而不能“强而齐之”。他说:“天下至大也,万民至众也。”“或欲经世,或欲出世;或欲隐,或欲见;或刚或柔,或可或不可,固皆吾人不齐之物情,圣人且任之矣。”⑥对于不同的个性只能顺其发展,而不能强求划一。这样就充分肯定了人,肯定了人性,人性是不能压抑,不可束缚,应该任其发展的。
李贽的自然人性论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意义,他这种张扬人性,肯定个性的思想在哲学上表现为与理学说教的尖锐对立,构成了李贽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童心:李贽哲学与美学的联结点
李贽在充分肯定人性,否定“天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童心”这一概念。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失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⑦李贽认为,不论古人还是今人,圣人还是凡人,都有一颗“童心”。所谓童心者就是童子之心,人之初之“本心”。人人都做过童子,都具有童心,这童心是人生之初最真最纯之心,是一种天赋自然之物,尚没有被世俗的虚伪矫饰所濡染,更没有被书本上的假仁假义所浸蚀,因而是“绝假纯真”之心。李贽是针对当时理学说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把社会变成“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诈骗场所而言的。
李贽是从王阳明学派发展出来的思想家,受王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较大。他的“童心说”与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以及禅宗的“心外无佛”、“本性即佛”的观点相似。王阳明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⑧“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⑨王阳明把“心”说成是超实在超道德的本体境界,与朱熹的“理”相比,毕竟更心理主义化,已经有了点人性论的味道了。此外,王阳明作为“善良意志”或“道德知识”的“良知”,也具有了感性情感的色调。到了泰州学派的王心斋,强调“任心之自然”即可致良知,或以“乐”为本,强调“乐是心之本体”,把心学向感性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后来“制欲非体仁”之类的说法不断出现,使王学日益倾向于否认用外在规范来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⑩。使王学日益走向感性化。“心即理”的“理”日益由外在的天理、规范、秩序变成内在的自然、情感甚至欲求了。这样就走向或靠近了近代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到了李贽大讲“童心”,不讳“私”、“利”,强调“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差不多完全走向了近代自然人性论了。李贽在阐明“童心”之后,便由哲学转到美学。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11)李贽认为只有摆脱儒家“闻见道理”的影响,才能护住“童心”,文艺应该表现这种“童心”,即没有受过孔孟之道毒害的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任何一种新创造出来的体裁,不管产生在什么时代,只要表现了人们的真情实感,就是好文章,好作品。李贽还认为只有“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12)感愤于心,直抒胸臆,心口一致,才能写出“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的真诗文来。因此,李贽要求文艺家必须“好察”“百姓日用之迩言”,即要注意观察、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认为老百姓谈论自己最熟悉的事是最真实的,所以李贽把“好察”“百姓日用之迩言”看成是使“童心”失而复得的根本措施。显然,李贽所一再强调的“童心”,实际上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要求摆脱封建道德的羁绊,实现人性解放的思想情绪。
此外,李贽还论述了“童心”失落的危险性:“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13)可见,“童心”不仅是李贽美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政事、德行的基本出发点,唯有从这一点出发,才有真、善、美可言。
这样,“童心”就把李贽的哲学和美学联结起来了。
李贽的“童心说”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所宣扬的“真心”、“情性”对同时代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戏剧家汤显祖进一步发挥了李贽重“情”的观点,提出“唯情说”,声称“师讲性,某讲情”,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情之至”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情”是人生的真谛,艺术家为了表现情感,为了追求“情”之解放,可以充分自由地发挥想象,创造理想世界。李贽的“童心说”对公安三袁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公安派的“性灵说”认为诗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14)。袁宗道说:“性情之发,无所不吐。”(15)都是强调作品要表现天真自然的趣味和真实的思想感情。此外,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以及后来的王士祯的“神韵说”、石涛的“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的思想、袁枚的“性灵说”、“扬州八怪”的写“真魂”、曹雪芹的《红楼梦》(曹称《红楼梦》为《情僧录》)、王国维的“意境说”等,无一不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构成了中国近代自然人性论美学的基本线索。这里无法一一详论。中国古代美学自古就十分重视情感、真心在审美与艺术中的位置和作用,突出地强调“情”与自我、个性相联系的重要意义,并且以它来冲破儒家礼法的束缚,赋予它以特定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个性解放的内涵。李贽所代表的上述自然人性论美学思潮成了近代中国美学的先声。
自然: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
“以自然之为美”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中国古代自然论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先秦之老、庄。尊崇自然本质,是道家思想的精髓(也是李贽美学思想的支撑点)。老子曾明确强调自然和谐为美,他赞美纯真无邪的“赤子之心”,赞美婴儿的哭声,认为是发自自然本性而非故意造作,强调自然之趣,以自然为宗。庄子也十分强调质朴之美,尊重个性发展,反对人为束缚,极力推崇不事人工雕饰的“天地之美”,以“自然无为”为美的最高境界。后来魏晋的阮籍、嵇康的自然论思想也是顺着这条线索发展的。李贽扬老抑孔,上承老庄阮嵇,近取阳明心学、禅宗美学,形成了自己很有特色和个性的自然论美学思想。
李贽的自然论首先表现在他的《童心说》中。李贽认为理学说教否定人性,压抑人欲,叫人说假话、干假事、做假人,是不自然的。李贽认为人人都有一颗“童心”,“童心”是人的“本心”,是不会弄虚作假的,人只有保持“本心”,表现真情,吟咏自然性情,才是自然的,不做作的,才是美的。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讲到。在文艺创作的问题上,李贽反对故弄玄虚,刻意雕琢,而极力推崇真实自然是一切文艺创作的灵魂。他说:“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16)李贽认为过分精雕细琢,一味讲求文理文法,即使工巧之极,也是难以创造出令人赞叹的优秀作品的。那么,“天下之至文”怎样才能创造出来呢?他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求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于水。”(17)李贽认为文艺创作首先应该先积聚情感,到了不可控制的时候,情感就会象火山迸发一样喷涌而出。这时作文就会下笔如有神,笔法自由,一气呵成,“天下之至文”就会产生。李贽认为这样作文才是“自然”的,才是顺乎情性的。
李贽除了论述作文要自然而发,顺乎情感,他还指出艺术家个人的性格、气质不同,其自然风格也不一样。他说,文艺作品“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18)“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19)但是不管哪一种风格的作品,均“以自然之为美耳”。李贽所说的自然,便是作者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和如实写照,而不是任何矫揉造作。他说:“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20)很明显,这与他的“童心说”是一脉相承的。
李贽还通过对《拜月亭》、《西厢记》、《琵琶记》的比较,具体阐释了文章贵在真实,纯真自然为美的思想。李贽称《拜月》、《西厢》是“化工也”,《琵琶》是“画工也”,“化工”如“造化无工”,也就是“自然”。李贽通过对《琵琶记》的分析,指出只有注意作品的真情实感,才能取得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反之,一味追求形式的雕琢,字句的奇巧,是经不起推敲的。李贽的“自然之为美”的美学观明显是对儒家“中和”美学观的叛逆。此外,李贽还对千古不易的古训“发乎情。止乎礼义”进行了否定,对束缚文艺,阻碍自然的礼义进行了批判。他说:“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而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21)
李贽的“自然”思想,渗透在他的整个美学思想的方方面面之中,“以自然之为美”是全部美学思想的概括,也是他的美学思想的核心。他的美学自然论思想突破了平淡无味的美学思想,深化了以往的文艺自然论,在美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对同时代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同时代的公安三袁,就受到李贽这一思想的影响,主张写作要自然,不拘格套,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机械拟古之风。后来的石涛、朱耷、“扬州八怪”等也都非常推崇李贽的自然美学思想,并作为他们艺术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注释:
①《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
②《顾端文公遗书》卷十四《当下绎》。
③⑥《李氏文集》卷十八,《明灯道古录》卷上。
④《焚书》卷一《答周西岩书》。
⑤《九正易因》卷上《乾为天》。
⑦(11)(12) 《童心说》。
⑧王阳明《传习录》下。
⑨王阳明《传习录》上。
⑩《明儒学案》卷三二。
(13)(16)(17)《杂说》。
(14)袁宏道《小修诗序》《袁中郎全集》卷一。
(15)袁中道《花雪赋引》。
(18)(19)(20)(21)《读律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