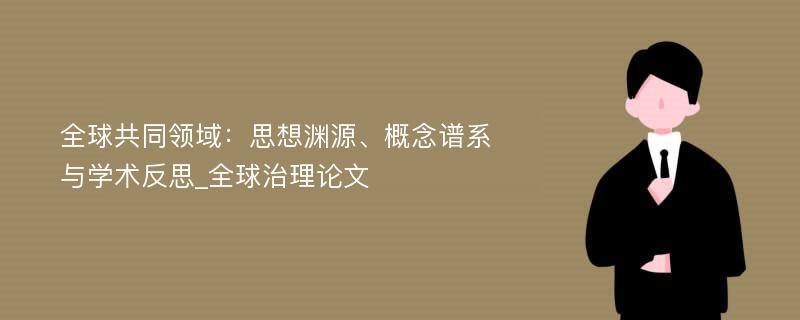
全球公域:思想渊源、概念谱系与学术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渊源论文,概念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指国家主权管辖之外为全人类利益所系的公共空间,如公海、国际空域、外层空间、极地、网络空间等。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全球公域最早出现在经济学研究中。1968年,英国经济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发表《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设想一个古老的英国村庄中存在一片向所有牧民开放的“公地”,每个牧民都可以在此自由放牧,但过度放牧会超越牧草的承受能力,最终导致牧场收益下降。此后,经济学及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将该理论推至全球范围,提出了全球公域的概念。① 步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多元化的市场竞争、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与多样性的安全威胁,全球公域内的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以及秩序与安全问题引发了多学科的关注。围绕着上述议题,经济、公共政策、生态与环境、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展开了以下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一是以苏珊·巴克(Susan J.Buck)为代表的理论建构研究。苏珊·巴克引入多学科视角,对全球公域及其治理机制进行了全景性概述,试图为全球公域的后续研究建立总纲式理论框架。②二是以约翰·沃格勒(John Vogler)、马克·瑞登(Mark Reeden)和菲利普·帕特博格(Philipp H.Pattberg)等为代表的制度研究。这批学者着眼于全球公域运行的内在机理,关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理论难题,尝试为全球公域设计、改进规则。③三是以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休·沃德(Hugh Ward)和凯瑟琳·哈里森(Kathryn Harrison)为代表的政治经济研究。这批学者运用博弈论、“国际—国内”政策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框架,对全球公域现实博弈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政策边际以及国内偏好等作出实证分析,也包括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海底区域等具体个案的对策研究。④四是以巴里·波森(Barry Posen)、斯科特·贾斯珀(Scott Jasper)和亚伯拉罕·M.登马克(Abraham M.Denmark)为代表的安全研究。这批学者普遍认为,全球公域的自由与通畅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希望通过相关研究为西方国家的全球安全战略寻找新的增长点,为应对来自全球以及新兴国家的挑战谋求对策。⑤五是以梅根·布鲁姆菲尔德(Megan Blomfield)等为代表的伦理研究。其中,主要成就集中于气候变化领域。学者们将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探讨上升至全球正义的伦理高度,试图为建立公正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机制设计方案。⑥ 在中国,学界对全球公域的研究启动较晚,著述有限。早期成果主要体现在环境治理与法律保护研究中。有学者从“一切人共有的物”的法律思想出发,论述了全球公域概念生成的合法性基础。⑦有学者在探讨“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人类共同利益”等国际法原则时,论及全球公域及其相关概念。⑧也有学者以“国际环境法”为视角,介绍全球公域的概念、范围和法律地位,并对全球公域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实践及其遇到的主权、域外效力等法律障碍进行解析。⑨ 近年来,相关研究逐步引起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有学者从国际安全的角度出发,综合分析全球公域安全议题的兴起背景、治理现状,并给出了中国的对策选择。⑩此外,多位学者还着眼于全球安全战略,提出当前全球公域具有明显的“霸权治理”特征——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全球公域名义进行全球战略部署是欲借其资金与技术优势实施对全球公域的治理与管辖。因此,欲实现全球公域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必须扩大治理的代表性,让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到其进程中来。(11) 总体上看,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介入,全球公域更多与全球秩序、国际安全及全球治理联系在一起。但与全球公域概念的广泛使用不相适应,学界的相关研究尚显不足;且现有研究多具有较强的政策冲动,国内学界的系统研究更是缺乏。本文试图在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梳理全球公域的思想渊源及其概念谱系,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索其学术意义及中国学术界应有的理论自觉。 一、全球公域的思想渊源 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全球公域经历了复杂的思想演进过程。特定的思想之源构成了全球公域发展的主要动力。 (一)全球公域思想的先导:斯多葛哲学与万民法传统 全球公域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斯多葛哲学和古罗马基于自然法的万民法传统。斯多葛哲学认为,存在一种被称为“逻各斯”的理性思维传统,即认为万物的生灭变化有其自身尺度,具有通约性的永恒事物能够解释万物的生灭。芝诺(Zeno)指出,人类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服从理性的律令,根据人类的自然法则安排其生活。换言之,宇宙之中存在着一种基于理性和具有普遍效力的自然法,它创立了一套以人人平等原则与自然法的普遍性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哲学,教导人们要超越不同城邦国家的不同正义体系,在神圣的理性指导下建立所有人和谐共处的世界国家。(12)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其著作《沉思录》中曾谈到:“若我们有共同的思考能力,则我们亦有共同的理性……若真如此,则我们也有共同的法律;若真如此,那我们大家都是公民并同属一公共之国度;若真如此,则世界便有如一国。”(13)除了主张普遍理性与世界共治,斯多葛哲学还承认世界资源的广泛共享。深受斯多葛哲学影响的罗马法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提出:“如希腊谚语所说:朋友的一切皆共有……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于我们自己毫无损失地提供给他人,那么我们就应当提供给甚至是不相识的人。”(14)不仅如此,西塞罗还指出,自然要求人们关心他人,且无论其为何人。如若每个人都将所得利益据为己有,则整个人类便会瓦解;如若只关心本国公民而不关心外邦人,则人类的共同利益纽带和由神明建立起来的人类之间的联系终将遭到破坏。(15)斯多葛哲学的自然万物之思唤起了人们对普遍理性的向往,而其世界资源分享原则更是激发了“本乎自然”的自然法,特别是万民法思想。 作为自然法的延伸,万民法虽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但其法律体系中的“人类共有物”概念,无疑具有面向世界的意味。埃流斯·马尔西安(Aelius Marcianus)在其《法学阶梯》第3卷中指出:“根据自然法,空气、流水、海洋及由此而来的海滨属于一切人所共有。”(16)查士丁尼(Flavius Petrus Sabbatius Justinianus)在其《法学导论》第2卷中提到:“依据自然法而为众所共有的物,有空气、水流、海洋,因而也包括海岸。因此不得禁止任何人走近海岸,只要他不侵入住宅、公共建筑物和其他房屋,住宅房屋不像海洋那样只属于万民法的范围。”(17)西塞罗指出,“那些被投于海洋之物与海洋一样为共有,那些扔于海岸上的东西与海岸一样也为共有的”。(18)维吉尔(Vergil)也曾提到,空气、海洋和海岸对所有人开放。(19)实际上,在罗马法中,“为公共使用的财产”一直占有重要法律地位,具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共有物,全人类共同享有之物,如空气、水流等;二是公共物,罗马的国家财产,如港口与河流等;三是市有物,罗马地方政府的共有财产,如戏院、竞技场等;四是神法物,指供奉神灵的物品。(20) 古希腊与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哲学和万民法传统为人类超越主权的世界关注提供了思想渠道,从本源上探讨了“全球公域如何可能”的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生产力水平等条件的局限,这一时期的人类共有思想及人类共有物概念并不真正具有全球意义与规模。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垄断了国家权力的政治公域和社会生活的次级公域,许多“共有物”宣称为全人类所有,实则是为城邦的统治阶层和封建帝国的统治者所有。(21)全球公域真正进入学术视野始于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 (二)全球公域思想的萌芽:“海洋自由”之争 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掀起了欧洲人环球探险、开发勘探海洋的浪潮。17世纪初,具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因不满葡萄牙的海洋扩张政策以及西、葡两国擅自吁请教皇划定海洋势力范围的做法,(22)将葡萄牙战船作为捕获物扣押,并授权当时颇负盛誉的国际法学者格劳秀斯(Hugo Grotius)阐明“海洋自由”思想,为荷兰海洋政策辩护。(23) 格劳秀斯根据自然法理论提出,大海不识主权者——广袤无垠的海洋系全人类共同财产,无法也无须为个体所占有,适用全人类自由使用原则。(24)这一思想引发了一场有关“海洋自由”的思想大辩论。英国学者约翰·塞尔顿(John Selden)提出,上帝将对海洋中鱼群的支配权交给了亚当,就意味着将海洋本身交给了亚当,英国人作为亚当的后裔自然是其海洋支配权的继承人。据此,他认为,英国及其历代君王应永享对其周边海域的排他性主权和管辖权。(25)葡萄牙法学家弗莱塔(Seraphim de Freitas)则提出了海洋“有效治理原则”。他认为,海洋与空气一样为人类所共有,但在保留海洋的人类共有属性与地位的同时,应适度引入主权国家对陆地领土的“有效管辖”原则,将部分航行与捕鱼权让渡给部分国家,以实现对海洋资源的“准占有”和“有效治理”。(26)苏格兰国际法学家威廉·威尔伍德(William Welwod)在其《海洋法摘要》中也指出,在远离各国陆地且不受海岸限制的大洋(great ocean)上,应实行航行自由,但近海海域不能与大洋相提并论,且基于苏格兰东海岸渔民的捕鱼传统,理应拥有对近海100英里的捕鱼权。(27) 关于“海洋自由”的这场思想论战最终将学者们的视野聚焦到海洋作为全球公域所具有的“排他性利益”(exclusive interests)与“包容性利益”(inclusive interests)矛盾上来。塞尔顿主张主权国家对海洋行使“排他性主权”;弗莱塔主张将海洋的治理权让渡给主权国家,以保障海洋“包容性利益”的实现;威尔伍德主张将海洋划分为“公海”与“领海”,以对“排他性利益”与“包容性利益”做出调和。这场辩论促使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对其早期理论进行反思,并最终正式提出“公海自由”与“近海主权”的双向原则。(28) 有关“海洋自由”的辩论使“全球公域”进入学者的理论研究视野。当然,上述学者的海洋思想均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对外扩张的产物,被打上了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印记,其目的都是为本国的海洋权益辩护,或对海洋所蕴含的“排他性利益”与“包容性利益”做出于己有利的暂时协调,其思想成为现代国际海洋法的重要渊源,但在当时也进一步激起了资本主义列强瓜分海洋及类似全球公域的欲望。 (三)全球公域思想的确立:生存与发展伦理 有学者指出,现代性的首要特征就是“反思”。(29)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尤其是自进入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经济的市场化与自由化达到前顶峰。但南北差距拉大、环境进一步恶化以及饥饿贫困等问题亦随之而至。在此背景下,全球公共资源如何实现分配正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如何协调?在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全球公域的概念得以提出,全球公域思想得以确立。 全球公域的最为重要、最为持久的思想动力源自生态环境学。生态环境学对全球公域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代际公平理论;二是可持续发展理论。1984年,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爱蒂丝·布朗·魏伊丝(Edith Brown Weiss)发表《地球信托:环境保护与世代间公平》一文,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其“代际公平”理论。(30)魏伊丝认为,每一代人都是人类资源的传承者,他们享有从前代人手中继承遗产的权利;同时,也负有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并将其完好地交给后代人的义务,即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谋求生存与发展方面享有均等的机会。(31)具体包括三项原则:一是“保存选择原则”,指当代人有责任为后代人保存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多样性,确保后代人和当代人有相等的选择多样性;二是“保存质量原则”,指当代人有保证地球质量的义务,确保地球资源在转交下一代时无损害;三是“保存接触和使用原则”,指当代拥有让后代人接触和了解地球共同资源和财产的权利,并引导其正当使用的义务。(32)“代际公平”理论对于全球公域中资源的存续与环境的保护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理论上可视作“代际公平”理论的继承与延展,现实中源于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思考。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描绘了一幅人类因农药污染而失去明媚春天的景象,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有关环境污染的争论。(33)10年后,在人类环境会议召开的背景下,由各领域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Only One Earth: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问世。该书将地球视作一个有机整体,旨在提高人们对“人类与地球生态环境关联性”的认识。(34)1972年,未来学研究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全球环境报告中,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理念,抛弃了自然与人类间“零和对立”的传统思维,主张改变人类线性增长状况,倡导建立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35)1987年,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36)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接受了该报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表述并赋予其国际法地位。(37)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公平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三方面全面协调的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包括三个核心原则:(1)公平性原则,包括:代内公平——同代人不分国籍、地区和种族等而同等地享有发展权利,与代际公平——人类不分代辈、时序而平等地享有生存与发展权利;(2)持续性原则,强调人类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3)共同性原则,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须以联合的方式实现。(38) “代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思想理论家们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伦理的探索,为全球公域设置了规范准绳与伦理底限,是对此前全球公域思想和理论的反思,特别对新近兴起的气候伦理研究有直接影响。 (四)全球公域思想的深化:全球主义与全球治理 随着全球化日渐深入并进入更高阶段,人类社会生活各领域不断融合,国家间相互依存日渐紧密。在此背景下,全球公域思想在全球主义理论与全球治理实践中得到深化和重构。 全球主义理论对多元行为主体、虚拟互联网络及国际规则的关注,为全球公域理论与概念的拓展提供了重要启发。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在论及国家与海洋全球公域关系时,详细论证了“国际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方面的重要作用。(39)有些学者则注意到网络在全球世界中的角色。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与约翰·厄里(John Urry)指出,网络在全球信息化时代扮演重要角色,“实物的世界”即将被“符号的世界”所取代。(40) 不仅如此,全球分配正义理论也从如何公平公正地配置全球资源及权利、利益的视角,为全球公域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源泉。针对罗尔斯(John Rawls)“既有全球资源及其配置结构无需改变”的观点,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等学者提出“全球差别原则”和“全球资源再分配原则”。(41)他指出,由于全球资源的稀缺性以及西方国家开发利用的先天技术优势,当自然资源的分配出现不公正的情形时,有必要根据各国人口、经济结构与社会需求等标准进行“再分配”,以满足不同国家的利益主张,实现全球总体发展。(42)在扭转富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和全球资源利益分配不均状况方面,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提出尝试性解决方案——“全球资源红利计划”(GRD),即向全球资源的主要消费国(往往是发达国家)征收使用税或污染税,用以缓解污染和改善穷国状况。(43) 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公域理论的发展与重塑。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全球治理理论。所谓全球治理,是指在全球范围内调和不同利益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44)在学者们列出的五类全球治理对象中,国际石油资源的开采、海洋污染、空气污染物的越境排放、臭氧衰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气候变化等,均是基于全球公域出现的生态、环境与安全问题。(45)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公域与全球治理产生了内在的联系,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为全球公域注入了新的内容,特别是引发国际关系学者从国家安全角度对全球公域的关注,如一国的太空战略与整个外太空安全秩序的协调等。(46) 追溯全球公域思想缘起与变迁的漫长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表现出不同的主题、内容与形态。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理性主宰的斯多葛主义哲学和基于自然法的万民法传统使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共有物”的存在。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海外探险扩张,海洋的归属权与管辖权问题第一次引发了学者对全球公域问题的理论思考。而现代生态危机的出现促使学者对全球公域研究中的“国家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并为全球公域研究注入了代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随着国际相互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更多学者将研究焦点转向公域秩序的维系与规则的设计。 但是,无论如何变迁,有关全球公域的思想和理论始终围绕着“公”与“私”、自由与公平、权利与义务、能力与责任、先占与后居、代内与代际等矛盾又统一的主题展开,并因此形成了全球公域概念的不同层次与体系。 二、全球公域的概念谱系 追溯全球公域的思想渊源,可以看出,随着人类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的提高,全球公域概念的范围与边界呈拓展之势,现已实现由“实体”到“虚拟”和由“有形”到“无形”的超越,形成了经济、环境、法律、安全四个维度,这些维度产生的核心理念与原则共同组成全球公域的概念谱系。 (一)全球公域概念的经济维度 全球公域概念的经济维度主要关注全球公域中资源的利用及价值产出、分配与效益问题。 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全球公域不仅是一个能够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区域,而且本身也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经济学家英吉·考尔(Inge Kaul)等学者就将大气和臭氧层定义为全球自然公共物品(natural global commons),将互联网定义为全球人造公共物品(human-made global commons)。(47)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还开创性地提出“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概念,特指全球公域中具有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48)在此基础上,鉴于全球公域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针对个体理性所导致的集体利益受损,经济学界提出四种“公域治理”的理论模型:“公地悲剧”模式,用以考察个体使用公共资源,并导致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的情况。“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用以考察信息不对称的非重复性博弈中,个人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情况,旨在说明,个体的最优选择并非集体的最优选择;即便是在对各方都有利的情况下,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49)“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旨在证明个体理性的叠加无法确保集体理性的自动生成,因为理性的个体在追逐集体目标过程中往往具有“搭便车”倾向。因为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的收益是公共性的,不管个人是否为之付出成本,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共同均等的分享它。(50)“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用以考察在小规模、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实现有效治理的可能性:由谁来设计制度或为公共资源的治理提供动力;规制设计者在推出多数人认可的治理规则情况下,如何确保多数人都如约遵守该制度;在监督成本较低,监督机制缺位的环境下,如何实现有效监督。(51) 上述理论模型集中论述了公共事务治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与困境。在全球公域研究中,这些模型常被用于分析过度捕捞、滥伐森林、过度放牧、生态退化、大气质量严重下降等因资源不合理配置而导致的经济效益下降的诸多问题。 (二)全球公域概念的生态维度 全球公域概念的生态维度是基于该区域的自然特性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所产生的,主要关注全球公域中的资源开发、利用及生态和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相关研究主要确立了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原则,指任何国家、法人或自然人不得对公海、外层空间、极地等全球公域中的资源据为己有或行使主权。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与下层土壤之原则宣言》正式宣布国际海底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52)此后,这一概念被逐步拓展到外层空间、极地等领域,并在如下条约机制中得到再确认:一是1979年的《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以下简称《月球协定》)第11条第1款规定:“月球及其自然资源均为全体人类的共同财产”。(53)二是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36条规定:“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54)“区域”及其资源由全人类共有,由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管理权;对所有国家开放,专为和平目的而使用;为全人类共同利益,其所得利益为各国公平分享。 第二,人类共同关切事项(common concern of mankind)原则,指全球公域中的资源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共同监管和保护。这一原则首次出现在1988年联合国大会43/53号决议《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中,(55)后来被正式写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56)《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在论及臭氧层的国际保护时也采用了类似的表述。“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向各主权国家提出了共同分担环境保护责任和义务的问题。(5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全球公域范畴内,诸多全球性议题有望依据超越主权的国际规制得到解决,如公海生态资源保护、公海污染治理、外层空间垃圾的处理、大气污染的防治、温室气体的限制排放、臭氧层的保护等。 (三)全球公域概念的法律维度 全球公域概念的法律维度主要关注的是全球公域中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以及国际法对于全球公域中人类活动的规制与约束。目前,这种规制与约束通过一系列国际条约及国际法律文件予以实现,它们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一系列相关全球性、地区性公海治理条约;《南极公约》及一系列相关南极动植物保护条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保护大气层和处理大气污染的条约;《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简称《外空条约》)及相关保护外层空间开发与利用的条约。(58)这些国际法文件规范为全球公域内的活动制定了以下行为准则: 第一,全人类共同利益与不得据为己有原则。此原则系国际法对全人类权利和福祉进行保全的最高原则,也是全球公域中人类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外空条约》规定,对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的探索与利用,应当以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明确规定外空活动应遵循的“整体利益”、“不得据为己有”和“自然探索和利用”三原则,正式确立了全人类共同利益与不得据为己有原则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国际法律地位。(59)此后,海洋、大气、气候等全球公共领域的国际条约与国际法律文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引用该项原则。 第二,自由探索与跨界损害责任原则。全球公域系全人类共同财产,世界各国在不违背国际法与不损害他国同等利益的情况下,享有自由介入、勘探与利用的权利。《外空条约》规定:“所有的国家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不受任何歧视,根据国际法自由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并自由进入天体的一切区域。”(60)《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则对公海自由原则做出系统阐述。(61)当然,全球公域自由并非绝对的,而是以尊重国际法与不损害他国利益为基础的。一旦一国的组织或个人在全球公域中的活动造成跨界损害,该国须担负相应赔偿责任。《空间实体造成的国际责任公约》、《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均系对此类赔偿的专项说明。(62) 第三,非军事化与和平开发利用原则。全球公域所涉资源与区域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价值,因此国际法规定相关原则以规范全球资源开发秩序,化解纠纷与冲突,防止战争发生并促进和平进程。《南极条约》率先确认了全球公域的该项原则并指出,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南极应永远专为和平目的而使用,而不应成为国际冲突的场所或目标。(63)《月球协定》规定:“月球应供全体缔约国专为和平目的而加以利用”,“在月球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或从事任何其他敌对行为或以敌对行为相威胁改在禁止之列”。(6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公海应只用于和平目的。(65) 第四,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思想一经提出,便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国际法文件中得到确认。其中,着眼于地球资源的代际托管与存续,《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保护和利用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等确立了“代际公平”原则;围绕着同代人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地区资源的公平享用,《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又确立了“代内公平”原则。(66) 第五,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此原则初步确立于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大会在其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系统地阐释了该原则的主要精神:“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行合作。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同等的但是又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它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67)这一原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斗争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全球环境正义实现的重要步骤。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较好地吸纳了这一思想。 第六,风险与损害预防原则。该原则着眼于预先防止、避免或减小对全球公域的损害,系保护全球公域的重要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相关“海洋环境的保护与保全”的条款中规定:“各国应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地采取一切符合本公约的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68)《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在论及人类对于臭氧层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义务时,也引用了该原则。《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也将其列为第15条原则,这被认为是该宣言最重要的创新之一。 第七,国际合作原则。该原则本系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全球公域处于国家主权体系之外而为全人类共同利益所系,其治理更加需要通过多边形式予以完成。《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指出:“有关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问题应当由所有的国家,不论其大小,在平等的基础上本着合作的精神来处理。”(69)此后,此原则在关于海洋、大气等一系列国际条约中都有所体现。人类新世纪发展总纲——《21世纪议程》在其序言开篇就庄严指出:人类站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面对贫困、饥饿、病痛、生态恶化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实现这个目标,但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70) 全球公域的法律维度体现了国际法对人类公共领域的持续关切,其相关规制是国际法超越“主权中心”思维的重要步骤。 (四)全球公域概念的安全维度 全球公域概念的安全维度是基于全球公域中的安全问题所产生的概念,主要关注各国针对全球公域的安全战略及其区域内的和平与秩序,涉及如下主题:海上安全,如公海航行安全、海上贸易通道(海峡)安全、深海海底区域安全以及海盗、海上恐怖主义、海上拦截等问题;航空安全,如民用航空飞机及军用航空器的“无害通过权”问题及无人操控飞机与卫星通信及定位系统安全等。此外,还有来自外层空间、极地及网络空间的资源竞争、军事科研引发的安全问题。 近年,美国、英国、日本及北约纷纷将公域安全纳入其国家全球战略或组织的整体战略部署中,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公域安全重要性的认可与关注。(71)巴里·波森认为,对全球公域的控制是美国全球时代新霸权的关键性支撑力量。(72)美国官方军事报告也明确将“确保美军在全球公域的自由进出和行动”定义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和“美军的永久使命”。(73)欧盟安全研究所(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在其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将全球公域定义为富有战略价值的开放性空间——不在任何主权国家的控制及司法管辖之内而向所有国家、企业和个人开放的世界区域,并认为欧盟是能够在多边主义框架提供价值和在这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独特角色。(74)关于北约,美欧智库相继推出报告,强调全球公域之于北约塑造新安全观、跨大西洋合作的重要性。(75) 全球公域概念的上述维度相互交融、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全球公域理论的基础。如经济维度为环境与法律维度提供分析工具与模型,环境维度为法律和安全维度提供个案支持,法律维度为环境和安全维度提供制度规范,安全维度为环境与法律维度提供保障策略。不过,全球公域的范围在不断深化拓展,关于其具体边界的划定仍存在争议。以外层空间为例,自《外空条约》出台以来,外层空间作为全球公域的国际法律地位很快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外层空间与空气空间的划界问题仍在争论之中。(76)另外,对于互联网能否纳入全球公域,学者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互联网是人类自由联络与交流的重要载体,当被纳入全球公域之列;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互联网中的信息资源虽然全球共享,但从技术上讲,网络实际是由主权国家或某些利益集团运营管理,并非真正的“无主物”。(77) 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和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全球公域的边界可能继续扩大。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总体上看,全球公域的基本特性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无主性,不为任何个人、组织或国家所单独占有或管辖,经济、环境、法律与安全各维度所涉及的资源、领域与区域均系主权国家之外的“无主物”;非排他性,任何个人、组织或国家对全球公域利益的享用不应妨碍其他个人、组织或国家的同等利益,所有国际行为主体负有同等的进入、使用与保护的权利与义务;公共性,全球公域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其所涉及的资源、区域或领域必然具有公共使用价值,与全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根本福祉紧密相连,能够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联动性,其所引起跨国的“公益问题”或“公害问题”必然要通过多边协商才能得到解决。全球公域的资源开发与污染防治等问题都要靠协商建立的国际机制网络实现有效治理。特别是包括国际条约在内的法律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被确认为全球公域,就要被纳入全球议程,受国际法约束。 三、对全球公域的学术反思 全球公域思想的兴起和发展预示了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于塑造共生共存的全球新秩序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全球公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互动沟通的广阔平台和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全球公域本质是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公共空间,它将导致全球公共资源的大量存在和全球公共性议题的大量涌现,带来人类社会中各式各类非排他性公共资源的超越国家主权界限的“全球化”,而这一过程恰恰是打破时空界限的“共在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人类共有地域、各式人类共有资源以及各类全球性公共空间交织互容,形成密切互动、相互依存的复杂议题网络。这一议题网络为全球化日程提供场域与情境,使主权国家间互动行为更为频繁,虽然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导致合作,但不同国家、地域的人们已开始在事实上结成“生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正如学者在论及全球化中的世界性社会理念建构问题时所指出的,“以人类的共生关系为纽带的世界性生产方式和人内在的求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已经把全球的共同生存与发展凸现到第一位,各国利益的联动性明显增强,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网络”。(78) 其次,全球公域的提出隐含了关于全球公共生活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的需求。通过调整行为体的成本预期、行为规则以及收益分配规范全球公域秩序。全球公域的各类公共资源与公共议题,通过国际行为体间持久的双边或多边谈判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组织、协议和条约,形成紧密联系的国际机制,有助于规范与塑造“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秩序”。简而言之,全球公域的存在隐含着无形契约机制的需求,表达了人类治理理想中的规定性,是规范与塑造“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秩序”的一个部分。正如中国学者所言,无数作为互约行为结果的无数世界性契约正以一种公共维度的力量制约和支配着这个世界,迫使行为者遵守一切涵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公共游戏规则。(79) 最后,作为一种思想和概念,全球公域的兴起标志着人类文明范式的变革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全球公域理论预设了一种世界共生的理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资源共管、制度共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这是一种可持续、非零和的关于互依互存的全球生存与发展伦理。它强调合作式竞争、开放式共建与多元利益共享;提倡共同应对挑战与风险的全球责任意识、沟通协调的国际契约精神以及合作共赢的理性发展观,并表现为“普遍但不同质”的价值理想,为超越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提供了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公域正在引领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任务不仅仅在于促进单一主权国家的利益,而在于“超越它们和它们的地方性利益,着眼于更大的人类的和行星的福利”(80)。 不仅如此,全球公域理论的发展还为全球治理开启了两种新的趋势:其一,治理的信息化、网络化特征更加突出。互联网等全球公域在全球信息化时代扮演重要角色,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提供更多全球治理的新机制。其二,治理主体更为多元。全球公域意指超越主权的人类公共地域与领域,在这一领域,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得以发挥主要的治理功能,充当重要角色。上述趋势将有助于拓展、补充既有全球化理论,推动全球治理逐渐实现由主权之治向国际法之治的转型。具体表现为从内部强化全球公域机制的结构与功能,改善全球公域治理。对此,奥斯特罗姆的“自主组织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她指出,在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环境下,人们通过密切的互动与协商而建立起相互依存、信任与合作关系。在解决新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等问题的基础上,资源的使用者们能够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主的制度设计与治理。(81)另外,针对全球公域涵盖广泛的国际议程,学者们设计了“人际关系—国际组织—非正式全球网络”三层治理网络,力图通过全方位社会动员、多渠道机制交流以及多层次全球参与等复合、灵活的举措来克服全球公域治理难题。(82) 四、余论 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公域的开放性特征与自由主义情结具有某种“自我实现”的功能,主权国家极易因无法抑制将其“异化”为国家私利的冲动,而打造出以“全球公益”为名的新型世界霸权。因此,全球公域包含了“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的理论矛盾,即全球公域内的问题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相互交织,使理论建构隐含着“异化”的危险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主权国家以“公”谋“私”,将“全球公域”异化为其“国家私利”的代表;二是部分主权国家将他国主权范围内的“私域”异化为全球公域,从而为自身的新国际干涉主义寻求合法借口;三是将公域科技异化为国家、组织或个人从事恐怖活动、跨国犯罪等非正当活动的工具。以美国为例,在海洋领域,美国制造中国“全球公域威胁论”,谋求美军在他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存在;在国际互联网领域,美国以促进开放与安全的“全球网络公域”为名,努力建立美国主导的、高技术含量的全球虚拟空间;(83)在跨大西洋关系层面,美国以“提高全球公域稳定性和确保全球公域通畅性”为由,努力推动北约拓展在打击海盗、外太空治理等领域的“新功能”,以促进北约这一冷战色彩极其浓厚的国际政治军事组织的战略转型,为其继续存在寻求合法性支持。(84)全球公域面临“异化”为美国话语霸权工具的风险。 当然,着眼于全球公域凸显了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对世界事务的共同关注增多、风险共担意识增强的时代合理性,如何在全球公域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建构起公正合理的机制与秩序也是时代赋予中国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我们要增强主动性,利用全球公域所带来的新契机参与到全球公共规则制定与秩序塑造的进程中来,充分发挥全球公域的积极潜能,推动和合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另一方面,也要保持思路清晰,看到部分国家利用全球公域的固有属性,打着“国际公意”的旗号,将对外干涉升级为“保护的责任”。 首先,顺应时势,把握机遇。西方自由主义全球公域观对既有的国际体系构成了挑战,破坏当下国际合作的法理基础,显然有利于某些经济军事实力雄厚、有能力率先探索和进入全球公域的强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公域概念的兴起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增多,隐含了世界人民和合共生的积极趋势,即便美国也承认其只能分享而无法主导全球公域,反映了西方霸权式微的现实。这为中国以全球公域为契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以及共生性国际体系开启了全新的空间。 其次,积极介入,防止异化。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不过三十余年,参与全球治理经验不足,目前对于全球公域的探索多停留在科学探索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层面。因此,中国宜以多边主义为理念基础,创造性地介入全球公域治理实践,通过法制、外交手段,捍卫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公域上的合法权益。近期,针对美国、日本在东海地区的排他性安全政策,中国以自我防御为立足点,在东海上空设立防空识别区,捍卫中国对钓鱼岛及其上空的主权权利,有效强化对钓鱼岛及其上空的有效治理,并反制美国的空中侦察和情报收集行为。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置系为钓鱼岛正名的合理举措,体现了中国遏止美国、日本将我国主权异化为“全球公域”的战略智慧。 最后,创新观念,谋话语权。美国等西方强权力图掌握全球公域的制度设计权和国际话语权,以“公域”之名行“私利”之实,是片面以自身国家利益为由,将自身理论陷于矛盾的尴尬境地。针对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全球公域观,中国应更多地关注全球公域的平等、正义与秩序,推动打造真正以全人类利益和福祉为基本关照的人类中心主义全球公域观。具体而言,中国宜超越单向度的线性思维方式,以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福祉为立足点,提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公域观,尊重全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等诸概念的内在普适性与公正性,以维护全球公域正义,捍卫全球公域的法理基础和道义准则。 全球公域概念是对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传统国际关系思维的超越,具有“公天下”的价值理性,但也存在异化为新型霸权理念的工具理性。中国应适时提出自己的全球公域观,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华文明智慧。 注释: ①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Vol.162,No.3859,1968,pp.1243-1258; John C.G.Boot,Common Globe or Global Commons:Population Reg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New York:Marcel Dekker,1974,etc. ②Susan J.Buck,The Global Commons:An Introduction,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1998. ③John Vogler,The Global Commons:Environmental and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Chichester:Wiley,2000; John Vogler,“Global Commons Revisited,” Global Policy,Vol.3,No.1 (Feb.2012),pp.61-71; Mark E.Redden and Michael P.Hughes,“Global Commons and Domain Interrelationships:Time for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Strategic Forum,No.259(Nov.2010),pp.1-11,etc. ④Todd Sandler,“After the Cold War,Secure the Global Commons,” Challenge,Vol.35,No.4(Jul./Aug.1992),pp.16-23; Hugh Ward,“Game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Global Comm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7,No.2 (Jun.1993),pp.203-235; Kathryn Harrison and Lisa McIntosh Sundstrom,eds.,Global Commons,Domestic Decisions: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0. ⑤Barry R.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1,2003,pp.5-46; Scott Jasper,ed.,Securing Freedom in the Global Commons,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Scott Jasper,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Commons: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2; Abraham M.Denmark and James Mulvenon,eds.,Contested Commons: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in a Multipolar World,Washington,D.C.: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Jan.2010. ⑥Megan Blomfield,“Global Common Resources and the Just Distribution of Emission Sha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Vol.21,No.3,2013,pp.283-304. ⑦徐国栋:《“一切人共有的物”概念的沉浮——“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法商研究》2006年第6期,第140—152页。 ⑧许健:《论国际法之“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12—116页;王秀梅:《论国际法之“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70—178页。 ⑨唐双娥:《“全球公域”的法律保护》,《世界环境》2002年第3期,第21—24页;李广兵、李国庆:《全球公域法律问题研究》,2002年10月19日,http://www.riel.whu.edu.cn/article.asp?id=24931,2013年9月5日。 ⑩张茗:《“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22—28页。 (11)曹升生、夏玉清:《“全球公域”成为新式的美国霸权主义理论——评新美国安全中心及其东北亚战略设计》,《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9期,第24—32页;王义桅:《全球公域与美国巧霸权》,《同济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49—54页;王义桅:《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以全球公域论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66—72页;杨剑:《美国“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的语境矛盾及其本质》,《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第46—52页;马建英:《美国全球公域战略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第7—13页;张茗:《全球公域:从“部分”治理到“全球”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57—77页。 (12)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3—14页。 (13)西拉·本哈比:《世界公民体制与民主:从康德到哈贝马斯》,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8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0—422页。 (14)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15)西塞罗:《论义务》,第269页。 (16)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物与物权》,范怀俊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17)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8页。 (18)转引自雨果·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马忠法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30页。 (19)转引自雨果·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第30页。 (20)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2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22)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年,第22—23页。 (23)雨果·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第8—9页。 (24)严存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5—76页。 (25)计秋枫:《格老秀斯〈海洋自由论〉与17世纪初关于海洋法律地位的争论》,《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第96—106页。 (26)W.S.M.Knight,“Seraphin de Freitas:Critic of Mare Liberum,” Transactions of the Crotius Society,Vol.11,1925,pp.1-9. (27)计秋枫:《格老秀斯〈海洋自由论〉与17世纪初关于海洋法律地位的争论》,《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第96—106页。 (28)Hugo Grotius,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Including the Law of Nature and of Nations,trans.A.C.Campbell,New York:M.Walter Dunne Publisher,1901. (2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2—40页。 (30)Edith Brown Weiss,“The Planetary Trust:Conser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Ecology Law Quarterly,Vol.11,No.4,1984,pp.495-582. (31)爱蒂丝·布朗·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衡平》,汪劲、于方、王鑫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6—17页。 (32)爱蒂丝·布朗·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衡平》,第38—49页。 (33)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62. (34)Barbara Ward and René Dubos,Only One Earth:The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a Small Planet,New York:Norton,1972. (35)Donella H.Meadows et al.,The Limits to Growth,New York:Universe Books,1972. (3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37)“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92,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sd.html,Feb.22,2014. (38)张梅:《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及全球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109—119页。 (39)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40)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1页。 (41)石斌:《秩序转型、国际分配正义与新兴大国的历史责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69—100页。 (42)Charles R.Beitz,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p.138-143. (43)Thomas Pogge,“An Egalitarian Law of Peopl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23,No.3(Summer 1994),pp.195-224. (44)英瓦尔·卡尔松、什里达特·兰法尔主编:《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组织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第2页。 (45)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第20—32页。 (46)Michael Krepon,“Setting Norms for Activities in Space,” in Scott Jasper,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Commons: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2,pp.201-214. (47)Inge Kaul,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Stern,eds.,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54. (48)Elinor Ostrom et al.,“Revisiting the Commons:Local Lessons,Global Challenges,” Science,Vol.284(Apr.1999),pp.278-282. (49)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1页。 (50)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51)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52)《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与下层土壤之原则宣言》,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海洋法资料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6—119页。 (53)《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年,第102页。 (5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刘振民编著:《海洋法基本文件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55)《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2006年3月8日,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ga/43/r43all/htm,2014年3月20日。 (56)《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第246、271页。 (57)李广兵、李国庆:《全球公域法律问题研究》,2002年10月19日,http://www.riel.whu.edu.cn/article.asp?id=24931,2013年9月5日。 (58)OHCHR,OHRLLS,UNDESA,UNEP,UNFPA,Global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of the Global Commons in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beyond 2015,Jan.2013,pp.5-6,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untaskteam_undf/thinkpieces/24_thinkpiece_global_governance.pdf,Oct.3,2013. (59)《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第17页。 (60)《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第17页。 (61)(6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刘振民编著:《海洋法基本文件集》,第43页。 (62)许健:《国际环境法学》,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6—167页。 (63)《南极条约》,位梦华、郭琨编著:《南极政治与法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89年,第404页。 (64)《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第102页。 (66)张梅:《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及全球实践》,《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109—119页。 (67)《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第678页。 (68)《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刘振民编著:《海洋法基本文件集》,第94页。 (69)《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宣言〉》,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第671页。 (70)《21世纪议程》,国家环境保护局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序言”,第1页。 (71)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The White House,May 2010; UK Ministry of Defense's Development,Concepts and Doctrine Centre,Future Character of Conflict,Feb.2,2010;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Defense of Japan2011,” http://www.mod.go.jp/e/publ/w_paper/2011.html,Oct.2,2013; Mark Barrett et al.,Assured Access to the Global Commons,Norfolk:Supreme Allied Command Transformation,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Apr.2011. (72)Barry R.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Hegemony,” pp.5-46. (73)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The White House,May 2010,pp.14,49. (74)Gerald Stang,“Global Commons:Betwee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Apr.2013,pp.1-4. (75)Mark Barrett et al.,Assured Access to the Global Commons,Norfolk:Supreme Allied Command Transformation,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Apr.2011; Michael Horowitz,“A Common Future? NATO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mons,”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Oct.2010,pp.1-14; Atlantic Council,“Protecting the Global Commons,” Security & Defence Agenda Report,Nov.2010,pp.1-10. (76)贺其治:《外层空间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77)Mark Raymond,“The Internet as a Global Commons?” Oct.26,2012,http://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2012/10/internet-global-commons,Dec.20,2013. (78)方玮:《全球化中的世界性社会理念建构问题》,《现代哲学》2001年第2期,第15—19页。 (79)袁祖社:《“公共理性”: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之人文理念的核心旨趣》,《“面向实践的当今哲学:西方应用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哈尔滨,2010年7月,第476—501页。 (80)《国际法院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案卫拉曼特雷(Weeramantry)副院长的个别意见书》,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第664页。 (81)Elinor Ostrom et al.,“Revisiting the Commons:Local Lessons,Global Challenges,” pp.278-282. (82)Sandra R.Leavitt,“Problems in Collective Action,” in Scott Jasper,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Commons: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pp.32-33. (83)Ellen Nakashima,“Obama Administration Outline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 May 17,2011,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obama-administration-outlines-international-strategy-for-cyberspace/2011/05/16/AFokL54G_story.html,Feb.22,2014. (84)Michael Horowitz,“A Common Future? NATO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mons,” Chicago Council Transatlantic Paper Series No.3,Oct.2010,pp.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