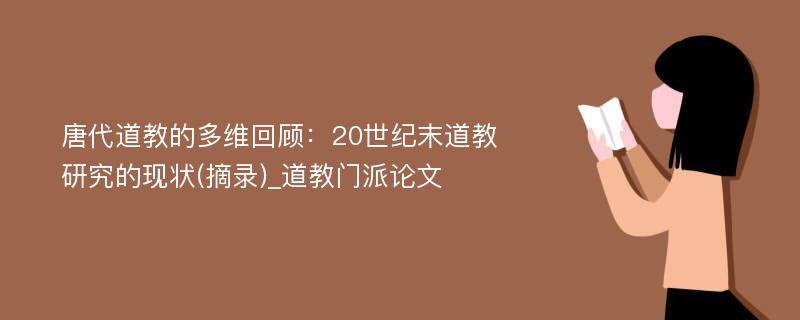
唐代道教的多维度审视:20世纪末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节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道教论文,世纪末论文,唐代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唐代的道教教团
与后来的朝代相比,唐朝在诸多方面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期。就道教来说,没有一个单一的教团模式,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来规定道教信徒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做“道士”可能意味着过修道的生活,在朝中做官或者做大学士,过着隐居的生活,写写关于神仙的诗歌、历史以及故事等。可以证明,唐代的道士如果选择以上任何一种方式都会受到尊敬。与中国历朝历代都尊崇文人学者、诗人、朝廷官员一样,在唐代,修道的生活也受到同样的尊敬,许多有成就和才华的男人和女人进入道门而没有选择追寻世俗的目标,这种做法也受到了尊崇。
唐代大多数著名的道士都受过法箓,或者至少他们在道观中都呆过相当长的时间,与道士们共同生活并拥有相同的观念。但总的来说,对唐代道教教团的研究还不够,部分原因是儒家及现代的学者们对出家修道生活的反感,另一部分原因是相关研究资料的缺乏。直到20世纪末,学者们才开始研究各种修道传统。现在已经被解读的一本唐代经书是《奉道科戒》。①此书成书年代约在7世纪20年代左右,《奉道科戒》略述了“道士修炼的概念框架和具体条件”。②其他详细记载道士女冠受箓过程的经书也开始受到注意。③但是这种制度和程序会因道观、地域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初唐时期最重要的道教中心是位于终南山的楼观台。在5、6世纪的北朝,楼观台作为首要的道教中心,慢慢地成为培养道教学者的场所。在李唐王朝的初创时期,高祖命令重修楼观台,此后直到8世纪它都一直是道教的主要中心。④那时楼观道的代表人物是尹文操(622-688)。尹据称是尹喜的后裔,自5世纪初起,尹氏都声称是尹喜的后裔。尹喜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据称老子曾传授《道德经》于他。⑤高宗皇帝任命尹文操为长安昊天观的观主,并命他编撰《玄元皇帝圣纪》。⑥调露元年(679),高宗迎请尹文操在靠近洛阳的北邙山老子庙举行斋醮仪式,在仪式上,很多人都看到老子骑一匹白马从天而降。⑦尹文操还注释了《奉道科戒》并编撰了其他的经书,包括《玉纬藏经》,这是一本关于7300余卷《道藏》的全面目录。⑧
玄宗皇帝于8世纪早期还下旨编撰了另一本类似的目录,由一位名叫史崇玄的道士负责。这本名为《一切道经音义》的著作包括了一个140章的术语表,可以让我们对那时的道教有更好的了解,但只有一些序言的材料保留了下来。⑨
唐代的皇帝们对道教教团特别重视,将其和佛教教团一起置于朝廷的保护之下。这些举措证明了唐代的统治者们认为道教在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利用得当,道教(如同佛教一样)则有益于国家;失去控制,则可能无益。乾封元年(666),高宗在全国三百余州建立了皇家资助的道观和寺院。慢慢地,他的继任者们建立了更多的道观。玄宗是支持此类活动最著名的一位皇帝,但他也对道观做了些规定,要求所有的道士和女冠注册登记以限制他们的活动。同时,玄宗还要求皇家支持的道观里的道士们举行道教斋醮仪式。⑩很明显,唐代的统治者对道观所做的制度化规定,如同“道举”制度一样,其目的不是为了促进道教在中国社会的普及,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将皇家支持与规范制度结合起来,以加强帝国的统治。
开元二十七年(739),是玄宗对道教的支持近乎巅峰之时,据说全国范围内有近1687所道观,其中550座是女冠观。尽管其中许多道观是皇家敕建的,但也有一些是传统的道教中心,这些道观与皇室和朝廷少有交往,也和那些经常被召至朝廷的道教领袖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找不到资料说明有多少善男信女在唐代的何时进入道门,关于揭示他们如何实践其宗教信仰的记载也很少。
一些名家的作品偶尔可以让我们窥视一下这种生活。其中一个例子是女冠黄灵微,她的事迹在著名学者官员颜真卿所题的两块碑文中可见。大历三年(768)左右,颜任抚州刺史,此处是黄的活动中心。早在长寿二年(693),黄就重新发现了遗失已久的魏夫人的仙坛并发掘出了一些古物。尽管黄灵微和她的女弟子维护仙坛近三十年,而且其间一直有乾道在那里做斋醮科仪,但是武后还是没收了这些物件,只不过对黄没有显示出更多的兴趣。(11)像黄这样的女冠的生活记载在一本由杜光庭所著、名为《墉城集仙录》(哈佛-燕京索引第782号)的独特选集中。(12)但是那些人物传记资料中的记载也是非常有限。
另外一位女冠,清微派的创始人祖舒(活跃于889-904年间)出现在晚唐时期。清微派因其“雷法”而闻名,在宋朝传播很广,加上正一派对其也很宽容,所以一直传承到当代。事实上,我们关于祖舒本人的事迹一无所知。后来的资料显示她结合了佛教密宗曼陀罗的修炼方法和中国本土用雷法治病的宗教仪式。(13)据说祖舒的教义在后期清微派中一直由女生修炼者传承,直到12世纪。(14)但是我们对于早期清微派的历史还是知之甚少。
二、“文人道教”——唐代道教作品以及它们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
唐代道教文学作品非常浩繁,收藏在《道藏》和其他作品集中,清代两部巨大的作品集《全唐诗》和《全唐文》收录了近70,000件唐人的著述。(15)下面我将对一些最重要的和仔细研究过的作品作一个介绍。
与六朝道教最有名的著作相比,唐代道教的文学作品从总体上说少玄谈而重实际。但这并不意味着唐代道教文学作品取材于世俗,也不意味着现代的读者容易理解。事实上,所有唐代的道教作品,不管是被收在《道藏》中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是饱学之士的成果。当时文人都很重视作品的“文雅”性,也就是说,这些作品是只有极少数受过很高教育的读者才能理解和欣赏的。唐代道教著作的作者们认为他们的读者都是博学之人,这些读者对道教本身的文化传承和世俗传统,如中国历来的编史传统和国家的祭典传统,都能驾轻就熟。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那些道教著作的作者和他们的潜在读者都是“文化人”。在中国,不论是唐代还是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轻松地去阅读此类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在唐代政治和文化的精英圈里都很有名,而且大体上是公开流通的。虽然我们对此类事情的历史知识很有限,但是也有证据显示,在唐代,即便是那些六朝时期最深奥的道教资料也经常被朝廷和民间的文人和学者们所分享,而这些人不一定是受箓道士或是任何神秘道派的初级信徒。例如,唐代的一些“世俗”诗集,诸如李白的诗,其中就饱含了道教神圣经典中的术语,这说明作者对道教传统中的种种细枝末节都十分了解。(16)9世纪早期,六朝时期的道教著作,如上清派的修炼经典《黄庭经》,在文人中已广为知晓,以至于在科举考试的答卷中被考生们引用。(17)唐代的一些官员当了道士,如贺知章;而一些道士则入朝为官,因此有很多唐代道教的著作,所呈现出道教的特点只是因为读者对道教感兴趣,而不是因为科仪的启蒙或者正式的授箓。此外,这些作品通常也没有被收藏在道观的藏经楼里,而据称是在世间流行,其抄本被收藏在皇家图书馆中。
虽然唐代道教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标准化和系统化,但唐代的各类作家写作的目的是让道教“有意义”。一些历史传记和参考书目有意地给道士和非道士们一种道教的历史感和传统感。比如:在8世纪,人们编撰与地名相关的“山志”去解释道教名胜的宗教和历史重要性。这些“山志”包括9世纪一位名叫徐灵府的道士所编的《天台山记》、李冲昭所编的《南岳小录》和杜光庭所编的《天坛王屋山圣迹记》。(18)
对现代研究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唐代道教的类书,其源于先前北周建德三年(574)奉旨编撰《无上秘要》的传统。(19)唐代最有名的类书应是由王悬河(活跃于683年前后)所编撰的《三洞珠囊》。(20)王引用了唐代以前的许多资料来综合概括个人和社会不同层次的道教修炼,包括打坐、科仪和生理上的戒律。它“看上去是用来充当道士的修炼手册”。(21)另一本由王悬河所著的重要作品是《上清道类事相》。(22)这本类书更为专业,其内容主要摘录了道教上清派的经典。但另一方面,此书提供了一个框架以理解宗教实践的整体维度:它“基本上是一部汇集了与人体内的小宇宙、自然界的大宇宙、冥府、仙界的圣地相关的道士人格、修炼和经典的语录”。(23)这两部道教类书有助于向那些没有入过道门的文人解释什么是道教。
唐代道士“阐述”他们传统的努力不仅仅囿于参考文献作品之中。像8世纪陶弘景门第的继承人——司马承祯之类的作家,就创作了有关精神修炼的手册,如已经亡佚的《修真秘旨》。此书为那些对传统神秘的上清派有些了解的修炼者提供了指导。但尽管此书名为“秘旨”,其实它不是一本神秘的作品,10世纪的一部历史传记——沈汾所写的《续仙传》中说《修真秘旨》仍然“行于世”,甚至是唐代灭亡以后都还存在。(24)如果说唐代以前的道教著作可以用“秘传”和“公开”来区分的话,那么到了唐代,这种区分不仅不明显,而且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像司马承祯那样的作家们清楚地知道道教的传统在那些出身显赫、教育良好的同辈人之中非常流行,他们还知道这些所谓的官宦贵族比其他人对道教的传统更为了解,也更感兴趣。因此,他们关于道教修行实践的著述是针对唐朝精英的不同群体。例如:司马承祯编了一本简短的名为《天隐子》的著作(也有可能就是他写的)。(25)该书避免使用天师道、上清派和灵宝派的术语和比喻,简单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成仙之道”,包括“五个渐进的途径”:(1)“斋戒”,主要是讲饮食平衡,劳作有度。(2)“安处”,意思是根据“阴阳适中”来维持平衡。(3)“存想”,即是存我之神,想我之身。(4)“坐忘”,即忘却“彼”、“我”之分。(5)达至最高目标“神解”,其特点是“入四真如”(这一概念是从大乘佛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借鉴而来)和“归于无为”(这是读者所熟悉的《道德经》中的语言)。这种道教的修炼方式很明显过滤了那些中国文人中的“一般读者”可能不熟悉的术语,使其能很容易地被司马承祯那个时代的文化人所理解。事实上,《天隐子》在中国古代和现代都一直广为流传:它被收入诸如《丛书集成》和《百部丛书》等经典丛书中,而且20世纪的气功练习者们仍然在使用该书。(26)
虽然《天隐子》从表面上看是司马承祯以前的人所写,但他的确写过一篇更长的文章——《坐忘论》(哈佛-燕京索引第1030号)。(27)这本书被科恩(Kohn)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七步得道”,此书与《天隐子》很相似,概括地指出,修道只要循序渐进,就会与道相合,得道成仙。对唐代的修炼者来说,不管其是否受过任何道教教派的入门指导,这样具体的手册都会使道教修炼更易于入手并极具吸引力。(28)很明显,《坐忘论》流传很广,或许对司马承祯下一代的吴筠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我们可以猜测此书的内容或许已经口传给了和司马承祯交往多年的某位唐朝皇帝,这也合情合理,那个时代的高道经常被召进宫中并被请求对皇帝进行精神方面的开导。遗存下来的关于这些听众的记载在某些方面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些记载总是说高道们不遗余力地去劝唐朝皇帝追求长生成仙。(29)在10世纪的《太平广记》中说像司马承祯这类高道可能给玄宗这样的皇帝口头秘传了延年度世之法。(30)虽然此类记载不能得到证实,但是毫无疑问,尽管一些唐代道士,如司马承祯的弟子李含光,不愿意秘密地给皇帝以口头指导;但是包括司马承祯、吴筠以及李含光自身在内的其他人,是非常愿意以书面的形式给皇帝一些指导的。例如,在开元十三年(725)到开元十八年(730)之间,司马承祯呈给玄宗皇帝一把神圣的宝剑、一面镜子和一份用上清派术语来阐释这两件物品的文本,玄宗皇帝自己赋诗一首,提及了此事。(31)虽然李含光想方设法避免与皇家进行口头交流,但是他和玄宗的书信交流的确十分密切,《全唐文》和《道藏》中保存了他们所交流的书信。(32)更为重要的是,天宝十三年(754),诗人学者吴筠,一位翰林院的博学之士,呈给玄宗皇帝一本《玄纲论》(哈佛-燕京索引第1046号),此书全文完整地保存在《道藏》里,《全唐文》也保存了此书的残卷。(33)韦利(Arthur Waley)将《玄纲论》称为“道教入门手册”。(34)虽然我们不能肯定玄宗究竟读了多少,但他接受此书的凭据至今尚存。
更多不确定的是《道门经法》(哈佛-燕京索引第1120号),此书据传是7世纪高宗皇帝和司马承祯的前辈潘师正之间的对话文集。(35)表面上看来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是记载高宗皇帝有关道教的问题和潘师正的回答,但其他一些章节也扼要概述了道教信仰和修炼的基本教义,并附有道教术语词汇表。我们确知,上元三年(676)到弘道元年(683)之间,高宗皇帝和武则天皇后曾多次拜访过潘师正。但《道门经法》的出处还不太清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证实此书是否真的保存了高宗和潘师正之间的对话内容。
以上提及的这些道书和吴筠的《玄纲论》,清楚地表明了初唐和盛唐时期的皇帝们对道教的强烈兴趣刺激了道门领袖以一种能够吸引皇帝、皇亲国戚和朝廷各级官员们兴趣的方式去阐明其教义。事实上,睿宗皇帝的两位女儿按照灵宝派的传统受箓做了女冠,(36)这也清楚地表明了皇家成员们对唐代道教的教义和实践也是广为了解和深表尊重的。虽然皇帝们对道教感兴趣的首要原因是出于以传统的文化和宗教来巩固皇权,但是以上的证据也表明道教传统的很多方面在唐代社会广为人知,道门领袖传播道教教义的努力在名门贵族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唐代道教思想
唐代道教思想既丰富又多元,混合了道教早期各种思想的成分,在某些条件下,还吸收了佛教的思想。总的来说,其旨在通过自我修炼从而得道成仙。追求此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保留了道门中传统的教导和实践方法,下文中将作一些具体的探讨。
初唐时期,道教思想中一直有对宇宙论思考的成分,这是继承了中古早期儒家玄学的思想,而这种“玄学”经常被误称为“新道家”。一些初唐的文人在注解《道德经》时,常常借用以往玄学中的思想。但到了7世纪晚期,人们对玄学思想的那种挥之不去的兴趣逐渐地平息下来。在那时,文人们逐渐清楚地认识到富有生机的道教传统中所蕴涵的内容比古老的玄学概念更能够提供有关生命本质的阐释。
也正是在那段时期,由皇家主持的佛道“辩论”开始了。(37)公元7世纪70年代初,像武则天这样的统治者开始逐渐意识到佛道教都有可以使其政权合乎天命:每一种宗教都有众多的信徒,他们的宗教兴趣都能够转化为统治者的政治优势,而且至少从理论上说,高僧高道通过主持宗教仪式而产生的力量能够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实际利益。此外,早期的佛道教辩论并不是因为主流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统治阶层排斥佛教或道教的思想,而是大都源于一小撮人为了获取政治上利益的考量。越来越多的唐代思想家们开始接受佛教和道教,不仅是因为它们一样有趣和有用,而是因为两教都能令人信服。由于没有敌对的氛围,那些对古代道教经典中引人深思的内容感兴趣的唐代文人发现可以通过佛教和富有生机的道教来帮助解释古代经典并理解整个世界。
在唐代最早的道教思想家中,有三个人被挑选出来代表道教参加皇家主持的辩论,他们被选中的原因现在不太清楚。其一是刘进喜(活跃于618-640年间),关于他的生平我们了解甚少,只知道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长安的一个道观中。刘进喜写过有关《道德经》的注释,一本反对佛教的论著,还可能写了《本际经》的部分章节,这在下面将会谈到。(38)蔡晃的生平我们也了解甚少,他参加过贞观十二年(638)的辩论,注释过《道德经》,还参加过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的工作。此译本早已遗佚,但或许像所有参加辩论的道教代表一样,蔡晃的参加也是奉皇帝之命,而非他认为道教就是对的,佛教就是错的。事实上,他写道:“我研究了《维摩诘经》(一本大乘佛教经书)和‘三论’(属中观学派)的理论后,我心中自然就流露出其核心的教义……尽管佛道经典不一,但其教义在本质上相同。”(39)
更为著名的是另外两人,李荣(活跃于658-683年间)和成玄英(活跃于632-650年间),他们的兴趣相似。李荣曾长住于两所道观之中,对《道德经》和《西升经》作过注解。(40)他同样也参加过三次在朝廷举行的佛道辩论,从佛教文献对他大加嘲弄的话中可以看出他非常能言善辩。成玄英更加著名,他在贞观十年(636)的那次辩论中胜出。成玄英是京城西华观的住持,道士们在那里抄写道经并将之传播天下。(41)他也参加了道教经典翻译成梵文的工作,并注疏过《道德经》、《易经》以及郭象注的《庄子》。(42)另外,他还为《灵宝度人经》作注,这说明他对玄学的兴趣并没有使其排斥富有生机的道教。他对通常被描绘为普世伦理的灵宝派深感兴趣,这与李荣不谋而合。李荣强调一个人通过自身的修炼成圣以后,有责任用自己的智慧去化度别人。这样利他的观念在唐代道教中几乎一直存在,而当代的儒家学者总是错误地宣称道教没有这样的度世观念。(43)
一些学者认为李荣和成玄英代表了一个被称为“重玄”的道教“学派”。基于杜光庭的言论,一些学者慎重地将唐代解释《道德经》的方法贴上这一标签。(44)其他人则坚持认为“重玄”是一个真正的“教派”,李荣和成玄英则是这一实际派系的创始人。(45)但证据显然不支持此种说法。(46)李荣和成玄英实际上不属于任何独立道教的教团,事实上他们使用像《道德经》这样的经典来旧瓶装新酒的做法不应该被解释为这些作者偏离了佛道的思想传统。(47)此类人物应当被认为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而那个时代思想家们研究的东西在我们今天却被错误地以完全不同的宗教传统来区分,或者甚至还要以一种宗教传统中的不同的派别来区分。对唐代的道教来说,教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不仅是对佛教、道教而言,对各教的不同宗派来说也是一样。
某些唐代的经典和其他的作品一般会和这些人扯上关系,其中之一是《本际经》(48)。《本际经》是一部广为人知的经典,约有81卷手卷在敦煌被发现,其他的道教作品也常常引用该经。或许是因为皇帝想要其广为传播。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玄宗下令全国所有道观都要抄写《本际经》,在举行斋戒仪式时,人们要背诵和讲解该经。玄宗将次年的大丰收归功于以上的活动。(49)
《本际经》以及和其同时代的其他几部经典最基本的教义是:一切众生皆有“道性”,“道性”构成了人的本真。《道教义枢》(哈佛-燕京索引第1121号)中说:“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识乃至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50)这些概念毫无疑问是受到大乘佛教“佛性”理论的影响,意在激发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士对道教的兴趣。
《道教义枢》是由7世纪的孟安排所著,关于他的生平我们了解很少。(51)该书保存了一些现在业已遗失的经典的部分章节,也可能是《云笈七签》的原型,《云笈七签》是一部宋代的大型道教选集,此书一直是20世纪晚期道经典教学者的宝贵资料。(52)编著《道教义枢》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即证明道教思想的深度和精致,并将其与大乘佛教最复杂的思想相提并论。(53)尽管这些努力在成玄英之类的思想家的著作中也可见到——其清楚地揭示了道教在面对着丰富和深奥的佛教思想面前所做的防御,但如果将这些努力视为愚蠢的模仿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如同后来儒家思想因佛教思想的挑战,促使其丰富自己的思想一样,道教在这段时期也是受到了激励并充实了自己。在唐代,对道士们来说去争论道教是否有截然不同的门派或宗派(例如: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像《道教义枢》这样的经典中,佛教“三乘”的概念被借用了,此借用不是指道教有截然不同的宗派,而是为了证明不同的道教目标和感受都是正道而使用的一种通用方法。(54)此类方法被后来几个世纪的道士们证明是有用的,并一直沿用到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如全真教中。
四、唐代道士的精神修炼——性命双修与得道成仙
受儒家和基督新教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现代偏见,使我们觉得道士应该是在读着《老子》、《庄子》的人,他们沉思着生命的细微实在及其宇宙论基础,还要对自己进行反思。对儒家学者以及后启蒙时代的西方人来说,体面的人士,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实际上都不会做任何将他们的生活同生命的细微实在结合起来的事情:他们以为,体面人士会否认任何生理上的活动含有真正的宗教上的或者精神上的意义。然而,事实上在任何时代道士们都解释了生命包含了我们的生理实体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修炼它。唐代道士既接受了斋醮科仪的功效也接受了生理上的自我修炼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在唐代,道士们从来不会因为从事此类活动而受到意识形态上的攻击,他们从来也不曾想过此类修炼会被认为与道教的神秘性或者哲学性等方面是不一致的,而现代人却通常这样认为。(55)
如同《内业》中所描绘的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道教一样,唐代道教在精神上的炼养通常被认为是不仅包含了现代人所夸赞的神秘修炼,也包含了生理上的修炼。在任何时代,鲜有道士会理解或接受当代人的假设,说身体是有别于“心”或“精神”的,更不会理解或接受这样的假设,说“精神”能够或应该被想象为独立于我们的真实生命而存在的,而生命则是物质世界中的物质存在。事实上,在任何时代,鲜有道士会理解或接受一种更为基本的假设,说物质世界在本体上是从那种更加细微精妙肉眼所看不见的世界分离而来的。(56)例如,当道医孙思邈告诫诗人卢照邻关于“养性的重要性”时,他说如果人们能够在自身体内维持平衡和秩序(这种秩序取决于精、气的适当的运行),人们便可尽享其年。(57)但对于儒、释来说,“性”这个词隐含着一个抽象的实在,此实在同人们的肉体生命的真实实在没有任何关系,但对于道士们来说,此实在总是有所关系,并且通常还很重要。(58)
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唐代两位作者值得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位是前面提及的孙思邈,他羽化后被人们供奉为神,并认为他是众多有关炼丹术经书的作者。(59)在他的真实作品中最有名的是两本现在还在流行的有关治疗学的论述,《千金方》和《千金翼方》。在前书中,孙思邈承认了佛教医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医学原理的正确有效性。(60)但道门中认为孙思邈还撰写了两本有影响的关于修炼的著作:《枕中记》和《存神炼气铭》(哈佛-燕京索引第833号)。(61)孙在《枕中记》中力荐:(1)“自慎”,即自我要控制,食、色要有节;(2)“禁忌”,关于食、色方面不合适的行为;(3)导引按摩;(4)冥想以行气;(5)“守一”以避邪。(62)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孙思邈假定精神上的成功取决于“觉心”。(63)此种说法并非是常规的道教修辞,似乎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同时,孙思邈的《存神炼气铭》(64)则介绍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完善自我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五时的心性修炼和七候的全身修炼。在第一候,人们通过使心、神、气宁静以达到“宿疾并消”,这些教导方法与从古时的《内业》到当代全真道的道教修炼相互呼应。人们通过这些修炼步骤可以逐渐地成为仙人、真人、神人和至人,最终达到终极目标“道源”。尽管在第一候,佛教的概念很明显,但是这条道路同从古代一直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道教修炼的其他概念都相一致,比如在《性命圭旨》中就是如此。
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探究其历史关系,但孙思邈的模式早在公元8世纪初期的一本通常被称为《定观经》(哈佛-燕京索引第400号)的经书中就出现了。(65)这本经书好像影响了另一个自我修炼的阐述者——伟大的司马承祯。在司马承祯的著作中有一本《服气精义论》,其中部分内容又被称为《修真精义杂论》。(66)《服气精义论》不是简单地勾画出了一些有用的生理上的修炼方法,而是系统地解释了性、命实体的性质,并附有一些指导方法来教人们如何避免负面现象、超越的不足,从而构建一个健康的、充满生气的身体。(67)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好地研究过,其牵涉到被称为“内丹”的修炼传统在唐代的根源。一些学者在8世纪初期李筌对《阴符经》(哈佛-燕京索引第125号)所做的注释里面发现了内丹思想的一个来源。(68)一本更清楚的包含“内丹的基本要素”的著作是9世纪崔希范所作的《入药镜》。(69)目前有关早期内丹传统的最为有名的人物是吕岩,通常称之为吕洞宾(后世内丹传统称吕为其始祖),现在人们认为他是崔的徒弟。但几世纪以后,有关吕洞宾生活、思想和修炼的历史事实一直都很模糊。(70)
学者们通过分析不同的唐代经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而又具体的图像,展示了唐代的一些道士,特别是在初唐和盛唐时期,道士是如何真正地练习性命双修。但是,我们还根本不清楚那时候有多少道士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或实践他们的宗教生活。这样的修炼方式,如同司马承祯《坐忘论》里呈现的一样,可能仅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对宗教生活的理解和观念。此外,孙思邈和司马承祯在不同的经典里面描述了不同的模式,这一事实说明尽管大多数唐代道士可能对生命的大致理解都相似,但是他们的修炼和传授并没有统一的模式。(71)与道门中的其他情况相似,唐代的理论家和修炼者没有正统或非正统之分,个体的差异不仅得到宽容,而且很明显地成为了一种规律而并非是例外。
[原文载于美国唐史学会会刊《唐学报》(T’ang Studies)第15-16辑,1997-1998年,第79-123页。本译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巴渝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成果。]
①巴瑞特(Barrett):《唐代道教》,伦敦:威斯威普出版社,第34页;科恩(Kohn):《〈奉道科戒〉的编撰及其时间——论宫观道教的第一本手册》,《东亚历史》第13期,第91-118页;科恩(Kohn):《奉道科戒》,在即将出版的普雷加迪奥主编的书中;常志静(Reiter):《唐初道士的理想和准则》,维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②科恩(Kohn):《奉道科戒》,在即将出版的普雷加迪奥主编的书中;科恩(Kohn)《道教体验文萃》第335-343页翻译了唐代张万福(fl.710—713)著的《法服科戒文》(哈佛-燕京索引第787号)中的摘要。关于张万福和他的作品,请参阅贝恩(Benn):《洞玄授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的一次道教授箓仪式》第137—151页和贝恩(Benn)的《张万福》。
③贝恩(Benn):《洞玄授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的一次道教授箓仪式》,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戴思博(Despeux):《唐代女冠的受箓》,《中国研究》5/1-2:第53-100页。
④参阅巴瑞特(Barrett)《唐代道教》第27—28页。虽然这些事情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现在看起来道教中心茅山,尽管其名声很响,并没有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活动中心,直到司马承祯羽化后,李含光在玄宗期间迁到茅山,才发展成中心。参阅柯锐思(Kirkland)《唐朝宫廷中的最后一位道教大法师——论李含光与唐玄宗》和《李含光》。
⑤科恩(Kohn):《尹喜——经典之初的大师》,《中国宗教学刊》第25期,第83-139页。
⑥科恩(Kohn):《道之神——历史和神化中的老君》,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中国研究中心。
⑦贝恩(benn):《玄宗皇帝时期的道教观念》,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第50-51页。
⑧见巴瑞特(Barrett):《唐代道教》第34页。尹文操还被认为是扩充了《楼观先师传》。参阅科恩(Kohn):《尹喜——经典之初的大师,《中国宗教学刊》25期,第95—100页;柏夷(Bokenkamp):《道教文献,第一部分:唐代》,第145页;鲍菊(Boltz):《道教文献通论——十至十七世纪》,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第125页。
⑨巴瑞特(Barrett):《唐代道教》,第50-52页;贝恩(Benn):《洞玄授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的一次道教授箓仪式》,第18页。
⑩劳格文(Lagerwey):《道教教团》,收入《宗教百科全书》14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第310-311页;贝恩(Benn):《玄宗皇帝时期的道教观念》,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
(11)薛爱华(Schafer):《公元八世纪临川魏华存祠的修复》,《东方文化》第15期,第124-137页;柯锐思(Kirkland):《黄令微——唐朝中国的一位女冠》,《中国宗教学刊》第19期,第47-73页;柯锐思(Kirkland):《唐朝人物传记辞典中的三则:王希夷、黄令微、贺知章》,《唐学报》10-11期,第153-165页。
(12)薛爱华(Schafer):《杜光庭》,收入倪豪士编的书中,1986年,第822页;柯素芝(Cahill):《宗教超越与神圣激情——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4-6页。
(13)鲍菊隐(Boltz):《道教文献通论——十至十七世纪》,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第38-39页。佛教密宗在唐玄宗时期渐为人知,参见温士敦(Weinstein):《唐代佛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第54-57页。
(14)常志静(Reiter):《道教的基本要素和倾向》,维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第38-51页。
(15)柯慕白(Kroll):《全唐诗》,收于倪豪士主编书中,第364-366页;《全唐文》,收于倪豪士主编书中,第366-368页。
(16)柏夷(Bokenkamp):《道教和文学:碧落问题》,《道家文献》3.1:第57-72页;柯素芝(Cahill):《宗教超越与神圣激情——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柯慕白(Kroll):《唐诗中的司马承祯》,《中国宗教研究学会会报》第6期,第16-30页;《唐代三位道士札记》,《中国宗教研究学会会报》第9期,第19-41页;《高处赋诗——登泰山》,《通报》第69期,第223-260页;《青童的宫殿》,《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105期,第75-94页;《李白的〈大鹏赋〉》,《中国宗教学刊》第12期,第1-17页;《李白的神仙风格》,《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106期,第99-117页;《李白的〈化城寺大钟铭并序〉》,《唐学报》第13期,第33-50页;《李白的紫烟》,《道家文献》第7期,第21-37页;罗素(Russell):《顾况的道教悲歌》,《唐学报》第7期,第169-195页;薛爱华(Schafer):《女神——唐代文学中的龙婆雨女》第二版,旧金山:北点出版社;《女冠子——道姑的神圣爱情诗》,《亚洲研究》第32期,第5-65页;《吴筠的“步虚词”》,《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41期,第377-415页;《“巫山云雨”词》,《亚洲研究》第36期,第102-124页;《吴筠的“游仙”诗》,《华裔学志》第35期,第1-37页;《海市蜃楼:曹唐的诗》,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以及史鸣飞(Shi,Mingfei):《李白登峨嵋山——道士眼中的圣山神化》,《道家文献》第41期,第31-45页。
(17)(41)巴瑞特(Barrett):《唐代道教》,伦敦:威斯威普出版社,第82—83页。
(18)要想了解第一和第三本《山志》,请参阅柯锐思(Kirkland):《盛唐道士》,印第安纳大学博士论文,第242—246页;想了解《南岳小录》请参阅柏夷(Bokenkamp)《道教文献,第一部分:唐代》,收入倪豪士编的书中,1986,第146页。想更全面的了解这类的《山志》,请参阅鲍菊隐(Boltz):《道教文献通论——十至十七世纪》,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第102—121页。但很奇怪,直到14世纪以后,才有人开始编著茅山志。
(19)劳格文(Lagerwey):《〈无上秘要〉——六世纪的道教大全》,巴黎:法国远东学院。
(20)常志静(Reiter):《三洞珠囊——初唐道教的工具书》,维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目前仅存留其原著30卷中的10卷。
(21)柏夷(Bokenkamp):《道教文献,第一部分:唐代》第150页。科恩(Kohn)说这篇经典“主要是针对道门行家而写的”。这可以从其简短的词条中看出:“这些词条力图使读者能突然回忆起他们已有的道教知识。”但人们很怀疑为什么“行家”会需要这样一本的“手册”。任何道教教派的初级信徒都理所当然地从其师父那里得到一些道门的主要经典或口头上的释疑。
(22)常志静(Reiter):《〈上清道类事项〉的范畴与事实》,维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
(23)巴德里安—侯赛因(Baldrian-Hussein):《道教上清派的范畴与事实》,《华裔学志》第42期,第531页;参见柏夷(Bokenkamp):《道教文献,第一部分:唐代》第150页。
(24)柯锐思(Kirkland):《盛唐道士》,印第安纳大学博士论文,第275页。
(25)科恩(Kohn):《修道七阶——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内特托:斯德瓦出版社,第145-155页;《天隐子的教导》,《中国宗教学刊》第15期,第1-28页;《道教体验文萃》,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第80-86页;《天隐子》,在即将出版的普雷加迪奥主编的书中。
(26)科恩(Kohn):《天隐子》,在即将出版的普雷加迪奥主编的书中。
(27)科恩(Kohn):《修道七阶——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内特托:斯德瓦出版社;《道教的静思——唐代的内观术》,收于孔丽维编《道教的静思和长生法门》,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中国研究中心;《道教体验文萃》,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第235-241页;《坐忘论》,在即将出版的普雷加迪奥主编的书中。
(28)科恩(Kohn)在《道教体验文萃》第235页和《坐忘论》中暗示说《坐忘论》源于司马承祯对其“弟子们”的教导。但《坐忘论》的教导是如此的含糊,如此少的涉及到道教的具体内容,而他的弟子,如李含光,对此则十分精通,因此,我认为这本书应该是专门写给那些不是他弟子的人,如:唐朝的文人学者们,这些人对上清派的传统没有任何了解、对道观的生活或仪式活动没有丝毫的兴趣、对掌握受箓道士的经典、仪式和道法也没有一点热情。
(29)(30)柯锐思(kirklaand):《盛唐道士》,印第安纳大学博士论文,第234—238页,第67—71页。
(31)贝恩(Benn):《玄宗皇帝时期的道教观念》,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第107-109页;柯慕白(Kroll):《唐诗中的司马承祯》,《中国宗教研究学会会报》第6期,第17—18页;柯锐思(Kirkland):《盛唐道士》,印第安纳大学博士论文,第247,286页。
(32)柯锐思(Kirkland):《唐朝宫廷中的最后一位道教大法师——论李含光与唐玄宗》,《唐学报》第4期,第46页。
(33)柯慕白(Kroll):《全唐文》,收于倪豪士主编书中,1986,第147页;柯锐思(Kirkland):《盛唐道士》,印第安纳大学博士论文,第104页,第109页;
(34)韦利(Waley):《李白的诗歌和生平》,伦敦:乔治安伦和昂温出版社,第106页。
(35)柯慕白(Kroll):《全唐文》,第148页;巴雷特(Barrett):《唐代道教》,伦敦:威斯威普出版社,第38-40页;柯锐思(Kirkland):《潘师正》,在即将出版的普雷加迪奥主编的书中。
(36)薛爱华(Schafer):《玉真公主》,《唐学报》第3期,第1-23页;贝恩(Benn):《洞玄授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的一次道教授箓仪式》,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37)科恩(Kohn):《笑道——中国中古佛道论辩》,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34-37页。
(38)(39)沙夫(Sharf):《〈宝藏论〉与中国八世纪时佛教的汉化》,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第36-37页,第37页。
(40)《李荣》,在即将出版的普雷加迪奥主编的书中。
(42)(47)于世谊(Yu Shiyi):《唐代的庄子解读——成玄英评注》,科罗拉多大学博士论文。
(43)柯锐思(Kirkland):《论普渡众生精神在道教传统中的根源》,《美国宗教学会会刊》第54期,第59-77页;《平衡的世界:〈太平广记〉中的整体综合》,《宋辽金元》第23期,第43-70页。
(44)贺碧来(Robinet):《道教发展史》,布鲁克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194页。
(45)藤原高男(Fujiwara):《老子解重玄学派考》,《汉魏文化》第二号,第32-48页;砂山稔(Sunayama):《道教重玄派表征——隋至初唐的道派》,《集刊东洋学》第43期,第31-44页。
(46)见沙夫(Sharf)《〈宝藏论〉与中国八世纪时佛教的汉化》,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第34—44页。沙夫(Sharf)注意到砂山稔所假定的重玄派系“传承表”只不过是将杜光庭所提及到的道士按时间顺序排列,将其姓名用线连接,然后将他们同一些特定的经典联系在一起,这些经典为了回应和尚对“玄义”的言论攻击而编写的,见上文第42页。
(48)柏夷(Bokenkamp):《道教文献,第一部分:唐代》,收入倪豪士编的书中,第142—143页;吴其昱:《本际经》介绍了敦煌文献。只有两卷被保存在了《道藏》中(哈佛-燕京索引第1103号和329号)。柏夷(Bokenkamp)同样也引用了另一本不太著名的经典《本相经》(哈佛-燕京索引第1123号),该书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49)贝恩(Benn):《玄宗皇帝时期的道教观念》,密执安大学博士论文,第248-249页;沙夫(Sharf):《〈宝藏论〉与中国八世纪时佛教的汉化》,第39页。
(50)《道教义枢》第8卷6b,沙夫(Sharf):《〈宝藏论〉与中国八世纪时佛教的汉化》第57页译。“道性”是《道教义枢》第29章的主题。
(51)柏夷(Bokenkamp):《道教文献,第一部分:唐代》,第147页;沙夫(Sharf):《〈宝藏论〉与中国八世纪时佛教的汉化》第40页,第56—60页;大渊忍尔:《〈道藏〉的形成》,尉迟酣和索安主编,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第255—256页。《道教义枢》的成书年代没有定论。柏夷(Bokenkamp)认为该书是7世纪早期的作品,但一些日本学者认为该书要晚至8世纪。
(52)《云笈七签》(哈佛-燕京索引第1026号;《道藏》677-702)是宋代张君房(进士1004-1008)受宋朝廷资助所编纂的一部122卷的宋版道藏摘要。该书编纂工作完成于天禧三年(1019),正式呈送给皇家是在天圣元年(1023)和治平元年(1064)之间。请参阅席文(Sivin):《中国炼丹术——初步的研究》,第54—56页;龙彼得(van der Loon):《宋朝图书馆中的道书》,伦敦:伊大卡出版社,第30—35页;施舟人(Kristopher Schipper)的《云笈七签》,收入倪豪士(Nienhauser)主编的书中,1986,第966—968页。
(53)参见沙夫(Sharf):《〈宝藏论〉与中国八世纪时佛教的汉化》,第56-60页;贺碧来(Robinet):《道教发展史》,布鲁克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191-192页。
(54)沙夫(Sharf)在《〈宝藏论〉与中国八世纪时佛教的汉化》第56页提到,成玄英认为,“大乘”对道士来说是“在污秽的世界里所包容的真理,与那些在山林里寻求个人心灵平静的小乘修行相对立”。但是,沙夫(Sharf)是不正确的,那样一个模式“明显的是道教挪用了在世获取解脱开悟的菩萨思想。”这个模式和早期道教“退隐山林”的观念形成对照。但是,事实上,“退隐山林”,这一儒家的陈腔滥调,现代的罗曼蒂克,在任何时期都很少成为道士的目标。从《道德经》到司马承祯,道士理想中的圣人不是一个隐士,而是帝王之师,而道门领袖在六朝、唐宋时期实际上都扮演了那样的角色。参阅柯锐思(Kirkland)的《唐朝人物传记辞典中的三则:王希夷、黄令微、贺知章》,第153—155页。
(55)在这方面很多的混淆不仅是由于当代人对道家和道教的二元对立造成的,同样也是被顾理雅(H.G.Creel)极具影响力但又非常偏见的“沉思道教”,以郭象注《庄子》的术语为代表,和“仙道”的二元对立造成的。想了解弄清这些阐述性的问题,请参阅席文(Sivin)《论产生混乱的“Taoist”一词》;柯锐思(Kirkland)《道教传统中的个人与文化》,《评孔丽维〈道教神秘哲学〉》,《中国道教的历史轮廓——对分类和术语的思考》。
(56)像当代这样的假设一直很有影响,以致许多坚持这样假说的学者们非常错误地认为“道教”的追求目标是某种“肉体成仙”。参阅柯锐思(Kirkland)在普雷加迪奥(Pregadio)主编的即将出版的书中所撰的“神仙”条目。
(57)席文(Sivin):《中国炼丹术——初步的研究》,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06-119页;关于孙思邈是天师道信徒的证明,请参阅席文(Sivin):《论产生混乱的“Taoist”一词》,《宗教史》第17期,第312页。
(58)英悟德(Engelhardt):《生命之气——唐代的养生术》,收入孔丽维编的《道教的打座和长寿法门》,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很少有现代的学者们去关注全真派的研究,全真教认为生命包含了“性”(我们生命在最深的层次上的“自然状态”)和“命”(我们日常生活的实体,由我们过去的行为而决定)和谐的融合。
(59)英悟德(Engelhardt):《生命之气——唐代的养生术》第266-267页;席文(Sivin):《中国炼丹术——初步的研究》,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
(60)另一本由孙思邈所著的经典是《会三教论》,该书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关于孙思邈是否极大地影响了后来道派,如全真教,有关三教合一的教义,似乎值得我们去研究。
(61)《道藏》中的《枕中记》看上去没有作者(哈佛-燕京索引第836号);一本较为简短的名为《摄养枕中方》的版本保存在《云笈七签》中(哈佛-燕京索引第1026号),第33章。参阅英悟德(Engelhardt)《生命之气——唐代的养生术》第288—290页。
(62)(63)英悟德(Engelhardt):《生命之气——唐代的养生术》,收入孔丽维编的《道教的打座和长寿法门》,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第279-288页,第291页。
(64)科恩(Kohn):《修道七阶——司马承祯的〈坐忘论〉》,内特托:斯德瓦出版社,第177-180页,第119-123页整理并翻译。
(65)该书的全称是《洞玄灵宝定观经注》。《云笈七签》(17.6b—13b)和司马承祯的《坐忘论》附录中也出现过该书。科恩(Kohn)《修道七阶——司马承祯的〈坐忘论〉》重新创作(181-186)并翻译了它(125-144)。同样请参阅科恩(Kohn)的《定观经》。科恩(Kohn)也于1989年翻译了《太上老君内观经》,这本书可能创作于唐朝,但具体时间不清楚。
(66)该书最全的版本有九篇,被保存在《云笈七签》第57卷中。前两篇以《服气精义论》之名单独出现在《道藏》中(哈佛-燕京索引第829号);其余的部分则被称为《修真精义杂论》。(哈佛-燕京索引第277号)
(67)英悟德(Engelhardt):《生命之气——唐代的养生术》第269-277页中概括过此书;英悟德(Engelhardt):《气功的古典传统——根据唐代司马承祯〈服气精义论〉的阐述》,以及科恩(Kohn)《服气精义论》中又更加全面地分析了此书。
(68)请参阅贺碧来(Robinet):《内丹对道教和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贡献》,收入孔丽维编的《道教的静思和长生法门》,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第303页;《道教发展史》,布鲁克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210—211页。在较早的研究当中,贺碧来(Robinet)认为《阴符经》的作者是李荃;在后来的研究中她说《阴符经》“可能追溯至6世纪中叶,直到李荃编辑了该书之后,才被人们广泛阅读”。
(69)请参阅贺碧来(Robinet):《内丹对道教和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贡献》第305页和《道教发展史》第221页。其1997年的参考书目中给出了崔的日期为“活跃于940年”和鲍菊隐(Boltz)《道教文献通论——十至十七世纪》第234页中的一样。贺碧来(Robinet)在别处标明崔的弟子吕岩为9世纪的人物,这与她在以前的研究中认为崔的年代是一样的。
(70)鲍菊隐(Boltz):《道教文献通论——十至十七世纪》第139-143页中详细地分析了据称是吕所作的很多诗文,但无一是唐代的真实作品。
(71)在1998年于罗浮山召开的第二届国际道家学术研讨会上,许抗生教授认为司马承祯的性功思想是从他早期作品中对气的合理保养逐渐发展而来,在他的晚期作品中获得了“道性”。对此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标签:道教门派论文; 文化论文; 道教传播论文; 道德经论文; 读书论文; 道藏论文; 道士论文; 司马承祯论文; 国学论文; 全唐文论文; 道教义枢论文; 玄纲论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