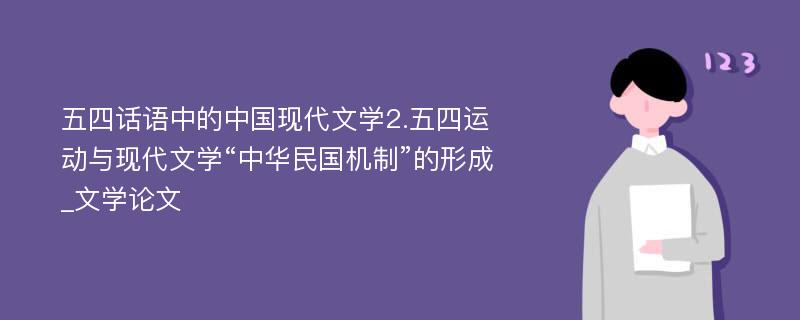
五四话语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笔谈)——2.“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笔谈论文,中国论文,民国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一直是各种思想潮流(乃至各种党派、各种政治力量)谈论现代中国文化历史的起点,对所谓“五四”的理解和认识,更是人们分析、评价和判断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成就和局限的主要“根据”。政治革命家早有“新民主主义开端”之说,保守的政治独裁者(如蒋介石)也曾指责“自由主义”的“五四”是背弃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给予许多的“启蒙”期待,而西方汉学(尤其美国汉学)更有“激进”、“偏激”的种种忧虑……今天,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一点都不能减少围绕它的种种争论。问题是: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五四”吗?“五四”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构成”的?在总体上实现了什么功能?
“五四”之所以常常令我们陷入到一种没有结论的争议,乃是因为后人把太多注意力花在了对“运动”之中诸多激烈言论的关注当中,所谓的“激进”也好,“偏激”也吧,都不过是这些言论的组成部分,对五四的责难似乎认定就是这些言论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构成了关键性的影响。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观察现代中国的历史,却应当承认:不管五四新文化派的主张有多么的激进,现代中国文化都没有顺着那样一种单一狭隘的方向发展,至少是直到1949年为止,中国的现代文化在融会古今中外的宽阔的道路上自信地走着:外来文化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整理、阐述和发挥,而“整理国故”的中坚并不是为历史淘汰的前清文人,而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建设者。以文学为例,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诞生的白话文学不仅延续了中国文学的现代生存,而且出现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思想追求的新的繁盛景象。也不仅是五四新文化派所倡导的那种文学形式的一花独放,包括新文化派质疑和批评的旧派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也依然生存着,发展着。被称做“现代”的这个时期,中国文学获得了来自社会体制、文化环境、文学氛围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保证和推动力量。这些事实都启发我们:需要对“五四遗产”作一番新的检点和梳理了,除了激情论战的“造势”效应外,它真正积淀下来的、融入社会历史的“坚硬”的本质是什么?
在我看来,五四遗产中被人们有意无意遗忘掉的而在如今最需要我们正视和总结的东西便是一种能够促进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健康稳定发展的坚实的力量,因为与民国之后若干的社会体制因素的密切结合,我们不妨将这种坚实的结合了社会体制的东西称作“民国机制”。
在推动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之中,“民国机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空间的基本保障,作为现代知识文化传播渠道的基本保障以及作为精神创造、精神对话的基本文化氛围。正是在五四,初步形成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对现代中国至关重要的积极推动性力量。
科举制度结束之后,现代学校和出版传媒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基础。前者容纳了数量众多的知识群体,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生存空间,尤其是高等院校更成为大量富有创造力的知识精英栖身之所。如教育部于1912年-1913年制定颁布的民国第一个学校制度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其中的《大学令》、《大学规程》等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已经包含了若干废除了忠君、尊孔等旧教育宗旨的内容。同时如校内设评议会、教授会等机构,则开始效仿英美大学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思想。“五四”时期在教育界更开展了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倡行教育独立的运动,“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现代公民教育思想成为全国教育联合会太原年会的决议。自1917-1927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所谓“教育无宗旨”的十年中[1],现代中国的教育理念从师从德日转向仿效英美,从而为民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校园注入了思想独立的重要因子。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生存基础的最早创立者便是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其推动下,北京大学率先践行“研究高深学问”、“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等办学理念,于“五四”前后完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转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蔡元培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努力将北京大学营造成诸种思想倾向并立的知识分子的殿堂,这里既有新文化派的《新青年》、《新潮》,又有研究传统文化的《国故》,以及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的新旧派都能够接受的《国民》。这些刊物对内号称尊重同人的个性,《新青年》宣言谓:“社人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新潮》发刊旨趣书称:“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对外则透过论争形成思想的互动,从而推进社会文化的发展。没有这样的生存基础,就根本没有思想交锋的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就是“民国机制”的第一次显现。
出版传媒既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直接谋生之所,又为更多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传播思想的基本渠道,因此,围绕出版传媒而形成的体制性运营方式,又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现代知识的生产和扩散。随着近代出版传播方式的出现和发展,清政府与后来的军阀政府都试图通过各种条律加以钳制,不过,种种的钳制努力都无法扭转一个更大的历史格局:内忧外困的清政府日益衰弱,而军阀政权的频繁更迭也自有它穷于应付的社会政治乱局,专制的本质遭遇到了无序的社会。从1906年《大清印刷物专律》到1914年袁世凯颁布的《出版法》,一方面是中央政权不断试图实施的出版传媒控制,另一方面却常常无法解决其间出现较多的“空隙”。除此之外,民国法律在“法理”上对民权的保护,以及近代以后中国逐渐形成的出版传媒的民营体制格局,都不断扩大着这些出版限制的缝隙。最终,在五四时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言论自由得到了基本实现的宽松的舆论环境,它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五四开始构制的思想的自由与多元,营造了民国文化的基本面。尽管后来国民党独裁政权总是以各种方式侵犯和压制思想自由,但都无法从根本上封堵知识分子精神自由的追求,更没有能够将主要的知识创造与思想表达纳入到专制政治的精密机器当中,或迫使它们沦为专制独裁的完全的附庸。
从五四新文化到左翼文化,这是我们现代文化史与文学史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国民党血腥的“清党”之后,左翼文化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且努力抵抗了专制独裁势力的绞杀迫害。左翼文化能够获得基本的生存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自五四时代就开创出来的“民国机制”。
也是在五四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个人思想表达如何介入公共话题,个人的话语权力与他者的话语权力如何对话与互动,如何在彼此的砥砺中构建更大的话语空间的全面训练。哈贝马斯曾经将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公共领域”的出现视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鉴于历史文化的深刻差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那种“公共领域”显然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具体情形有不小的错位。不过,知识分子如何走出一己的闲情雅致,彼此呼应,为一系列现代文化的公共性话题展开探讨却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标志。问题在于,个人的话语权力如何得到保证,又如何与他人形成整体的配合,更有甚者,当不同的话语产生彼此的矛盾、分歧乃至冲突的时候,需要在怎样的容忍中尊重对方且不丧失自己的文化立场,这种种的“原则”都需要细细的掂量、揣摩,需要更多的实际话语抵牾中的磨合,而最后的“和而不同”则是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所急需的“氛围”,一种在传统中国社会所不曾有过的多元个性的共生“氛围”。过去我们对五四的认识,把主要的焦点都集中于进步如何压倒落后、新文化如何战胜旧传统之类你死我活的命题上,其实,在我看来,除了五四新文化倡导者那些理论激情之外,五四遗产更“坚实”的部分就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话语空间,或者说文化争鸣的“氛围”。在这种氛围背后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彼此分歧却又相互尊重的有一定认同度的“文化圈”的存在。
在这个圈子当中,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各自有着并不相同的思想倾向,有过程度不同的文化论争,但又在总体上形成了推动文化发展的有效力量。在当时,宣扬“西方文明破产”的梁启超常常被人们视做“思想保守”,但他却对新文化运动抱有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甚至认为它们从总体上符合了他心目中的“进化”理想。学衡派也竭力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支持,并且并不拒绝“新文化”这一概念本身。“东方文化派”与《新青年》展开东西方文化的大论战,但“东方文化派”杜亚泉等人同样具有现代文化的知识背景,同样是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甲寅派一直被简单目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其实当年《甲寅》月刊的努力恰恰奠定了《新青年》出现的重要基础。后来章士钊任职北洋政府,《甲寅》以周刊形式在京复刊,与新文化倡导者激烈论争,但论战却没有妨碍对手双方的基本交谊和彼此容忍。论战之余,胡适与章士钊各自以撰写对方擅长文体唱和打趣,章士钊云:“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反对白话文学的章士钊将白话诗题写在照片上送给胡适,还附言道:“适之吾兄左右:相片四张奉上,账已算过,请勿烦心。”主张白话文学的胡适却以旧体诗歌作答:“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只有走出了传统的意气之争的私人领域,共同体认到了某种公共领域存在的必要,才会有胡适章士钊二人的这段佳话。一个巨大的存在某种文化同约性的文化圈营造的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十分宝贵的思想“氛围”——它在根本上保证了现代中国文化从思想基础到制度建设的相对稳定和顺畅。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把这种对中国20世纪上半叶影响深远的遗产称为“民国机制”,并不是为民国时期的专制独裁与黑暗辩护,因为,民国机制并不属于那些专制独裁者,而是根植于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根植于这一群体对共和国文化环境与国家体制的种种开创和建设,根植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贤的现代理想,它的雏形便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是我们需要珍惜的五四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签:文学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新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读书论文; 新青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