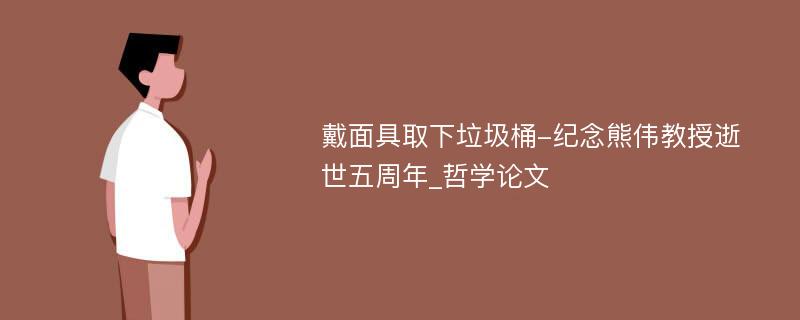
戴着口罩掏垃圾箱——纪念熊伟教授逝世五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垃圾箱论文,口罩论文,戴着论文,五周年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0)03—0374—04
“戴着口罩掏垃圾箱”,这是1952年上半年,我在南京大学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中,听熊伟教授在自我批判中讲过的一句名言。
当然,“名言”一说是我的评价。因为我觉得以此来形容当时从事西方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教师的工作,既生动又深刻。虽然我们(我和同学们)当时还没有学过多少哲学,却已经非常明确地接受了如下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现代西方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都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表现。这些腐朽没落的思想犹如一堆发臭了的垃圾,仍然要去研究它,岂不是戴了口罩掏垃圾箱吗!后来,当我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警醒过来时,我才体会到了这一“名言”的真正的深刻的含义。即以此来描述那些学有专长的教授们在当年的命运,不是更深刻吗?掏垃圾箱的环卫工人,工作时戴着口罩是自然的。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从事别的职业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对环卫工人的惩罚。但是,对于那些学有专长的教授们来说,戴着口罩去掏垃圾箱时,却实实在在是一种惩罚,而且是荣誉性的惩罚。即形式上不是惩罚,而是发挥其专长;不过这种“发挥”同时是(甚至主要是)自我批评。因为他们不仅是这些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受害者”,同时亦是这些思想的“散布者”。所以,他们的批判性研究,如不触动自己,一定就会被认为仍然在坚持反动阵地。那末后果便不难设想了。这样一来发挥其专长,不实际上是一种惩罚吗?而我们这些只知道一点马列,别的一无所知的青年,一般来说是没有这种荣誉的。
熊伟教授是1951年我进南京大学哲学系时的系主任。他亲耳聆听过海德格尔的讲课,是三四十年代国内仅有的极少几个专攻存在主义的专家之一。他对存在主义有独到的理解。例如,在刚看他的存在主义译作时,我总觉得他把海德格尔的Dasein一词译为“亲在”,读起来有点别扭。后来他的学生将其改译为“此生”时,念起来是顺畅一些了,但存在主义的味淡了。所以又不能不承认,“亲在”一译的确有其独到的体会。在思想改造运动以前,我没有听到过熊先生谈起过存在主义,更没有听到过他对存在主义的情感性评语(如一位我尊敬的前辈在自我批判中曾提到,他可以和夫人离婚,也不能和黑格尔哲学分离)。我想,即使如此,要说出重新去研究存在主义便是去掏发臭了的垃圾箱,无论如何不会是由衷的、愉快的。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前,他似乎真的不再研究存在主义了。偶尔因为教学或政治运动的需要,要他批判存在主义时,他上纲上线比青年人都狠,什么“死亡哲学”、“帝国主义的哲学”等等,别的内容似乎就没有了。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报告,我既看过、也听过。但我既没有看懂,也没有听懂。因此我也曾产生过怀疑,是不是熊先生自己也有些不甚了了。但是,连续不断的所谓学术批判,使我很快明白了,既然他是专攻存在主义的,领导上要他批判存在主义时,如果上纲上线不比别人狠一点,一定会被人指责为:还没有从存在主义的反动立场上转变过来。熊先生十分清楚地知道,与其授人以柄,不如自己批判得狠一点。所谓上纲上线高一点,批判得狠一点,说穿了恰恰便是空一点。因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便不可能胡乱上纲上线了。但是,我们有的领导和专家,便喜欢这种胡乱上纲,其无知程度,可见一斑。正是这种胡乱上纲,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象,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那些自以为这样就是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罪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要对十年动乱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冷遇负责。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们打破了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状况,实行了改革开放。因此西方的哲学思想也随之而进入了中国。原来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存在主义,一时间成了国内的一种时髦的流派。这事引起了共青团上海市委的警觉,把它称之为“第二次冲击波”。并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因此,各地各级领导都对存在主义的“入侵”重视了起来。北大作为高等学府,更应提高警惕,防范存在主义对青年学子的毒害。但是大家弄不清楚存在主义是怎么回事。所以学校领导要求我为他们介绍一次存在主义思想。对此,我犯了难。因为我对存在主义没有研究,批判肯定不够格,介绍也不称职。所以,我不得不临渴挖井,赶紧看书。并就一些弄不清楚的问题去向熊先生请教。再次体会到了熊先生对此有独特的研究,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平时和熊先生聊天,常常发现他妙语惊人。这是和一些青年朋友谈起熊先生时,大家共有的印象。不过有些妙语,听完一笑,没有往深处想。所以时间一长,也就忘了。但是,这次我去请教,又听他说了一段出乎常人意料的妙语。我说,海德格尔的书这么难念,听课时怎么能听得懂呢?看书看不懂还可回过头来重看,听课则一听即过去了,没有时间来反复,岂非更难懂了。他立即给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回答:“就是去听那个听不懂的。不仅我们这些外国人是如此,德国人也是如此。”大家都听说过,海德格尔的课堂,像上世纪黑格尔的课堂似的,常常是爆满。这么多人都是去听“那个听不懂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不久,我便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哲学课。很多人听哲学课,就像听物理课或历史课一样,以为是去听知识的。即以前不知道,听了老师的课便知道了。以前不懂得,现在懂了。这就是所谓长了知识。而哲学课的主要任务恰恰不在传授知识,而在启发智慧。通俗点说,即启发你去想问题。例如,以前你认为理所当然的道理,老师在课堂说,这不对。并说出一套“歪理”来,弄得你莫名其妙,迫使你不得不反复思量,这是为什么呢?由此,你可能就会发现很多新的道理。如果一个哲学老师在台上讲课,说得一清二楚,同学们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再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了,听完课一身轻松,那就失败了。如此传习,一定是一代不如一代,犹如俗语所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有时我想,不仅哲学教育要注意这个特点,甚至整个大学教育,也应有这样的特点。打个不确切的比方,小学、中学的基本任务是传授知识,凭着这些知识,原来无知的小青年,就有了独立思考的初步能力。大学教育的重点就在于发展这种能力。所以,我们在评论一个青年学生学术上有没有发展前途时,总是把他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发现新问题,才能提出新思想,才能有创造性。这就是所谓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发现问题的能力,虽在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但是它却不能当作知识来传授。40年代初,我在初中时,便听讲过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受到启发发现了万有引力。这大概是个故事,但它是一个富有哲理性的故事。苹果从树上掉下,在牛顿以前,肯定有无数的人看到过了,为什么没有人发现万有引力呢?这可能是因为知识发展的水平和实践发展的水平,还不足以使人们提出万有引力的假设。但是我以为,更重要的是在思维方式上,人们被理所当然束缚住了。重的东西往下掉,一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反之,如果要是有人假设它往上飞,岂不要让人讥笑为大脑不正常吗?怎么才能突破理所当然呢,不就是要有一种全新的自然观,全新的思维方式吗?这就是个哲学问题。在我看来,如果用漫画的方式来概括科学发展史的话,就是一部不断突破理所当然的历史。
当然,我没有就这些体会再次向熊先生请教,这是件憾事。现在才觉悟到已经晚了。不过,更为遗憾的是熊先生的才智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我在南京大学上学时,他不仅是哲学系的主任,同时还是全校政治课的负责人。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孙叔平同志任组长,熊先生任副组长。这可能也是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尽可能给自己高高上纲上线的原因。
在南京大学这一年,我不记得熊先生给我们开过什么课。我只记得宗白华先生为我们讲过《共产党宣言》。讲了什么,现在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一年后,我们由南京到了北京。似乎更没有人注意要发挥熊先生的特长了。我觉得与旧中国哲学界的派性有关。如果说熊先生没有得到重视,因为还不算旧中国的名教授,而且系里有一些人还是他的老师,那末,宗白华教授应是名教授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似乎就证明的确存在这种情况。关于宗老的情况,别处再说。现在仍回到熊先生的话题上来。教学基本上没有熊先生的份,他的工作似乎主要是搞翻译。
我觉得最为不妥的是把他变成了专职翻译。60年代,历史系请了位德国专家来讲德国史,需要找几位德语翻译,结果把熊先生也调去了。新中国的一位哲学教授,成了比他年轻的德国历史学教授的翻译,这对他本人、对国家都是不合适的。不过他本人却似乎因祸得福,避开了对他轻视的眼光,在受人尊敬的环境中工作了几年。80年代,他被选为全国德国史学会会长,显然也与此有关。不过,他关于翻译工作的题外之话,却启发过我的哲学思考。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要搞同声传译。所以从全国抽调了一批专家去翻译大会文件。熊先生和德国专家洛赫亦去了。熊先生回来后,给我谈了一件趣事。他们为了保证译稿的高质量,把同一语种的人员按两个人一个小组,分成若干组。各小组都要独立完成整个文件的翻译。然后把自己的译稿交到本语种的大组长那里,由他综合各译稿的优长,修改出定稿。熊先生和洛赫两人是一组,洛赫不会中文,故先由熊先生把中文稿的内容讲给他听,由洛赫斟酌落笔为德文。当熊先生将此稿交组长后,组长认为此稿不规范,表达常不符合语法,所以他没有与熊先生商量便将此稿改了。当熊先生告诉他,此稿是洛赫的稿子时,弄得这位老朋友哭笑不得,他只能半开玩笑地说,你这家伙,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件趣事,告诉我们,同是德语,中国人(即使德语专家)的表达,与德国人的表达仍然有鲜明的不同,仍然是中国人的德语。我觉得,这个例子在哲学上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以往我们总是把语言表达和语言内容的关系了解为直接的。这就大大简化了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这一复杂问题。而这里的事实却表明,不仅不同的语言对同一内容的表达是不同的,而且同一语言对同一内容的表达也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在认识理论的研究中,思维形式是如何表达思维内容的,应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思维与对象的二级关系(不过,我仍然对所谓“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一说,有极大的保留),了解成思维、语言和对象的三极关系,显然会大大有利于认识理论的深化。同时,上述事实还说明,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人的认识活动,起着一种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来说,这不仅是主观的条件,而是客观性的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不是认识活动的辩证本性的又一深刻表现吗?……总之,由此事可引起的联想很多。
由此,我想起了哲学著作的翻译问题,不同语言的翻译实在是件难事。文学著作翻译得好,人们常说是再创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哲学著作的翻译也是如此。逐字逐句的翻译一定传达不了原作的精神。既貌似而难神似。反之,神似了,可能貌便不似了。总之,对于真正的研究者,任何好的翻译也替代不了对原作的研究。同时,又要体谅别的译者的苦衷,不可苛求。你看了别人的译稿不满意,你自己来译也不可能尽善尽美。
熊先生在翻译上是有贡献的,不仅因为他译了一些西方重要的哲学著作,而且还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
当然,作为一个哲学家,熊先生对自己翻译上的贡献一定是不会满足的,而是要在哲学上作出贡献来。十年动乱后,他抛弃了“戴着口罩掏垃圾箱”的精神枷锁,重新开始了对存在的教学与研究,而且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学生。
在教学中,我觉得他颇有点存在主义的味道。有一次,他跟我说,他上午九点多钟到学生宿舍去找研究生,一敲门,那位同学在里面说:“谁?我还没有起床。”他一听,什么也没有说便回来了。我说,您为什么不批评他,九点多了还不起床?他却说,生活小节,不必苛求。
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不仅培养了一批很有才气的学生,还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为推进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在他离开我们已经五周年了,但愿他是带着“听那个听不懂”的愉快心情离开的。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因为30年代,在他取得博士学位后,曾取得了柏林大学的终身教席,但因发表文章断言“光明从东方来”而不能见容于纳粹党人,(注:这是在南京大学时, 熊先生讲的。 2000年3月8日,我向靳希平教授提及此事时,靳说希特勒也说此语,怎么会不见容。我只得存疑了,已无法考证。)在当时的驻德大使桂永清(他们似乎是同乡)的帮助下,才回到了祖国。但随后的几十年间,他似乎并没有能全力投入存在主义的研究。但改革开放以来,使他得展平生所志,能不快哉!
熊先生并不是只关心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他真正关心的是:在学习西方哲学中来发展中国哲学,可惜老天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使他没有把这一方面的才智全贡献出来。这便是他留给后人的一项历史任务!
收稿日期:1999—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