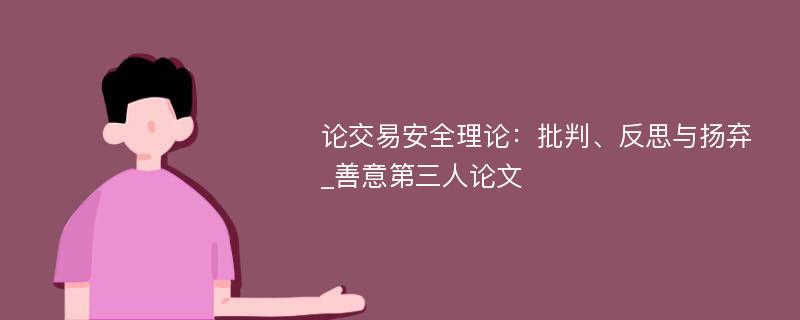
关于“交易安全理论”:批判、反思与扬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415/j.cnki.fxpl.2014.04.010 一、引论:流传已久的“交易安全” 交易安全一直被视为物权法(甚至整个民法)至为神圣的法理念,它频繁地出现在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之中:前者包括一物一权、物权法定以及公示公信;后者诸如物权变动和善意取得。上述制度构成了传统物权体系的核心支柱,在法学论著和各种教材中反复出现。长此以往,交易安全和物权法呈现出俱损俱荣的局面:一方面,交易安全是制度具有合理性的最佳证据,比如支持物权行为的学者就不断提及物权行为理论对交易安全的重要意义;①另一方面,既然物权法的原则和制度都在维护交易安全,那么对物权法的研习就意味着不断认同和强调交易安全理念。当一个概念得到了结构性的支持,它很容易陷入套套逻辑(tautology)的循环论证——永远为真且无需证明,并且成为证实(或证伪)各种观点屡试不爽的万能武器。交易安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每个法学本科生都无比熟悉的术语,也是几乎所有民法学者都信手拈来的理论,但很少有人考虑传统物权法中的交易安全究竟是什么意思,遑论“保护交易安全”的说法是否真的成立。 本文希望反思并揭破“交易安全”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物权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体现为两方面:第一,它强调保护善意第三人;第二,它设计了一系列强制性规范。但这两点实际都不成立。根本原因在于,交易安全理论忽视了很多重要的制度成本,片面保护交易安全并不是物权法乃至整个民法的真正宗旨。我们在完成对上述两方面“交易安全”的批评之后,这一结论将更加明显。 二、保护善意第三人,就是保护交易安全? 善意第三人是两大法系都着力加以保护的目标,大陆法系的物权法将它与交易安全紧密相连。通说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归纳为两种合法利益的取舍:一方是无辜的善意第三人,另一方则是遇人不淑的原权利人(所有权人)。当二者无法共存时,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正义——也就是交易安全,物权法将物权归属的天平倾向了善意第三人,制度代表是善意取得以及公信力。但此论述却忽视了如下问题:原权利人和无权处分人之间同样存在着“交易”。②换句话说,交易安全理论不只是利益的取舍,更是两种交易之间的取舍。可见虽然物权法声称保护“交易”安全,但它并不保护一切交易的安全:原所有权人与无权处分人“交易”的安全就劣后于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借用逻辑学的术语,所谓“保护交易安全”实际是个特称命题(只保护特定交易),但它却伪装成一个全称命题(物权法更重视一切交易的安全);明明是在几项交易中进行取舍,但传统物权法却将其作为重视交易的证据,并且得出了(我们熟知的)如下推论:保护交易安全意味着“动态利益”(善意第三人)优先于“静态利益”(原所有权人)。这就使“交易安全”从一个事实命题幻化为价值命题,拥有了自身本不该拥有的抽象价值判断。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交易安全的身边总是矗立着诸如公平与正义之类的宏大叙事,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道德印象凌驾于客观经济分析的非理性局面。 上述弱点集中地体现在传统物权法关于“交易安全”的论证中。传统物权法认为,原物权人和第三人的权利固均值保护,但从社会的角度看,如果不将第三人的交易优先,就容易“引起怀疑和担忧交易的公众效应,影响和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利益。”③这个论证的核心采取了目的论与功利主义的模式:即认为与原权利人的物权相比,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更重要。不过这一结论要想成立,物权法必须考察保护善意第三人能增加多少社会福利,随后再考察放弃原所有权人的权利会造成多少福利减损,然后比较这两种福利的量化值之和是否为正。很可惜,量化分析意味着大量的归纳推理与实证数据,后者从来不是传统物权法的风格。相反地,它更喜欢从社会公义之类的一般结论进行演绎推理,试图给出必然性结论。在复杂的经济现实面前,放弃归纳推理而使用演绎推理是很幼稚、也很不负责任的态度,但传统物权法仍然拒绝对具体的交易进行实证调查和细节比较,而是选择闭目塞听,固执于“交易安全”的幻象之中,沉溺在源自罗马法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体系建构传统,无视“传统并不能使命题为真”这一简单而有力的逻辑学结论。 即便是演绎推理,传统物权法仍然无法自圆其说。它希望用社会公共利益为交易安全提供支持,但这实际非常苍白。事实上,从公共利益的基础出发,我们同样能得出“应当保护原所有权人”的结论:如果立法选择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原权利人将自行调整交易预期;为了防止无权处分引发善意取得,除非对相对人达到相当信任的程度,否则原权利人就不会进行交易。这意味着信赖危机以及大量的调查成本,将极大减少交易的发生,而交易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样看来,(无权处分中)保护原权利人同样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利益。由于缺乏实证数据比较,问题陷入了无解的僵局。笔者并不反对诸如善意取得之类的制度,④但它们需要更好的理由,交易安全显然难堪其任。深层原因就在于,传统物权法将一个技术问题(两个交易的比较)上升为价值问题(静态与动态的比较),希望用过度概括(over generalization)的不当方法来维护价值命题,是一种注定失败的理论尝试。 综上所述,保护善意第三人就等于保护交易安全的说法严重缺乏科学性。善意第三人及其交易固值保护,但这只是因其属于可保护之法益,它并非先验地优先于其他交易(权利),更不能以交易安全作为理论基础。 三、谁之“交易”?何种“安全”? 与合同法不同,物权法中充满了强制性原则和制度。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交易安全是物权法最常用的理由:由于物权具有排他性与对世性,故须采用强制性规范以保证物权清晰且为外人所知,否则不利于交易安全。比如为何物权须公示?原因是物权具排他性,须公示令他人认知;否则变动频繁的物权容易造成困扰与混乱,无以保障交易安全。⑤与公示制度一脉相通的是我们熟知的物权变动,尽管德瑞在物权移转的原因与效果是否连带的问题上有所差异,但都要求物权的移转需完成公示(登记或交付),否则不发生移转效果,⑥原因还是维护交易安全。类似的论证同样可见于物权法定原则和一物一权原则。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些论证全部不成立。究其根源,传统物权法无法回答本节标题提出的问题:保护交易安全,究竟要保护谁的交易安全?又要保护到何种程度? 交易安全不是一个抽象的指标,而是因人而异的个体性判断:确保交易安全最终仍然要落实到具体交易的每个物和每个交易者,而每个人对交易安全的预期、保护方式以及愿意花费的成本都不一样,抽象地讨论交易安全毫无意义。进一步讲,绝对的交易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倒是交易风险是永存的事实:一方面,风险是物权人和其他主体保持社会性接触的必然衍生品;⑦另一方面,风险会带来经济利益(交换的收益)与非经济利益(比如因“担风险”而结成的友谊与其他社会关系),更不用说有时风险本身就是当事人追求的目标(比如赌博带来的刺激感)。要言之,交易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交易安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标准,每个交易者在不同场景中需要的交易安全都有所不同。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难看出,传统物权法的强制公示制度⑧是越俎代庖:对财产采取何种公示方法,本应取决于当事人自己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和判断。公示本身必然包含成本,因此是否公示、采取何种公示都应取决于当事人对未来风险的预期:即便是房屋,物权人打算再不搬家终老于此,占有公示就已足够;一个更极端的例子,黑帮老大的房子就算不登记也没人敢侵犯。事实上,公示与物权的紧密联系完全是臆造出来的。我们对他人物权的了解并不单纯取决于公示,而是包括市场认知、道德规范以及文化归属的综合判断。同样是一本书放在桌子上,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很可能是占座;但如果在饭店里则往往是遗忘或者丢失。公示对于交易安全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强制物权的取得和移转必须满足公示,意味着不同交易风险预期的当事人都要满足单一的立法标准,是一种陈旧而低效的立法模式。 传统物权法从未考虑这一点,它无谓地希望用立法强制来建构稳定而单一的交易世界,不太相信私主体能自己预见、处理和承担交易的风险,相反过分相信公权力介入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典型的家长主义:为了实现立法者心中的交易安全,它不惜扭曲当事人的市场判断,不惜付出高昂的法成本,甚至不惜与意思自治和自由背道而驰。这集中地体现在物权法定和一物一权之上。这两个原则源自19世纪私法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即用纯粹所有权取代纷繁复杂的中世纪地产权,目的是降低当事人的调查成本和交易成本,⑨时代意义毋庸置疑。但发挥了时代作用的东西不见得要继续存在。或许传统物权法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它试图用交易安全作为这一路径依赖的经济理由:物权仅能成立于特定的单个物之上,以确保权利明晰,从而保护交易安全;⑩物权之排他性和对世性要求公示,这样才能确保交易安全和便捷;但公示技术有限(尤其是土地登记)故需法定。(11)但这些论证同样不成立。 公示技术有限就要求物权法定,等于用法律技术来否定经济需求,颇似路窄就禁止开车的霸王逻辑。一个颇具反讽的事实是,“一物二卖”一直是物权法竭力防止的风险,但此时恰恰仅有一种财产权!可见物权法定是典型的“防君子不防小人”。事实上,允许权利类型的多样化,不意味着当事人会在一个物上设定无限的对世性权利,否则会影响该物权(所有权)的行使与价格。对物权人而言,物上权利(至少)涉及物权人的监督和协调成本以及物权人交易的涤除成本(要终结负担)与欺诈风险(比如忘记负担存在而引发的纠纷);而对物上权利人而言,除了要关注其他负担权利人的冲突,还要关心善意购买人对自己负担的超越和清除。(12)这将导致边际权利人的权利效用以几何级数骤减,可以想见,物上的权利不会超过难以想象的局面。这样看来,物权法定固然可以降低调查成本,但牺牲意思自治的代价太过高昂。反观一物一权也绝非必须:物上存在两个甚至多个物权完全有可能,欧陆封建时代多重所有权的长期维持恰堪为证;而现代社会同样存在“多重所有权”的经济现实(比如公司),以至于德国学者要再给多重所有权“一个新的机会”。(13)与物权法定类似,一个物上存在若干物权会影响权利的行使;但对具体交易者而言,如果在制度(比如公司)、收益考虑(比如高风险高收益的激励)以及其他规范(比如道德规约)之下,形成了对交易安全的个体化判断,一物一权就必成具文。 要言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要求立法尊重具体交易场景中的具体判断;硬性的强制性规则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极易沦为公权力寡头垄断。法律不保护当事人对权利对抗力的自主安排,除非其采取了法律规定的权利形式。(14)而否定自由又往往打着保护交易安全的旗号,这种不光彩的角色更值反思。归根结底,传统的交易安全理论完全忽视了自己包含的制度成本。 四、交易安全的制度成本 当法律试图保护某种法益或者法观念,就一定存在成本。这里的成本既包括显性成本,也包括隐性成本。其中,显性成本包括制度设计、机构运行以及人员维系,还包括培训以及学习成本,包括编写和发行教材、学术研究以及法学院系的课程学习等等。不过对交易安全而言,显性成本并不大:首先,它并不需要太多额外支出,大部分成本都可以划归于一般性的法律制度和机构(包括法院、律所以及行政机关);其次,它的学习成本并不高,交易安全并不难理解,本科二年级的水平就足以熟练掌握。因此我们更关注的是交易安全的隐性成本,这个成本就是对交易自由的限制甚至损害。 当一项制度或观念成立之后,它并不仅为既有的纠纷提供解决方案,更将作为未来当事人行为的一项参考。笔者将其称为前瞻性原理。(15)当我们考察某项制度的合理性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其是否有助于解决眼下的纠纷,而是要考察一旦该制度成立,当事人的行为在给定制度之下会发生何种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后果。这有点类似牛顿第一定律,外力并不保持物的运动状态,它只改变物的运动状态;民事立法并不创造或决定当事人的市场行为,它只能通过激励来调整和改变当事人的行为。作为财产法的核心之一,物权法规范是当事人进行市场行为的重要参考因素,而传统物权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会对交易造成负面激励。本节希望证明这一点。 交易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交易者的利益预期。这一事实决定了交易安全仅仅是考虑因素之一。交易者最关心的是价格(而不是交易安全),(16)因此风险的降低并不必然带来交易,后者取决于当事人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巴泽尔的洞见,市场参与者除了(狭义)价格和数量之外,还有许多可供调整的边际。(17)它说明交易(合同)不是一个单独的线性结构,而是双方在变化的情境之下不断调整策略的动态进程。这是交易安全呈现个体化局面的根本原因,当事人可以用各种策略来弥补交易安全。在正常的竞争市场中,当权利的风险高出预期,出售方可以选择降低风险,可以选择降低价格,还可以选择其他途径来努力消除对方的顾虑(比如提供担保或者求诸熟人说情),或者干脆选择退出市场;而购买方除了可以选择拒绝购买之外,也可以接受对方的降价(即用价金收益来抵充风险),或者选择其他途径来降低风险。(18)反过来,买受人的压价甚至拒绝购买会推动出售人对权利的改进与完善;而出售方的交易风险也为买受人提供了风险套利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牢记,市场竞争意味着当事人存在各种选择与磋商的权力与可能性;面对交易风险,当事人拥有多种多样的市场手段加以自发调节,这种调节将集中地反映在价格之上。正如马克思援引的“利润300%就敢上断头台”(19)的生动说明,高交易风险完全可以被高价格所弥补,交易安全会和各种市场因素综合反映在交易价格之中。这样看来,管控交易安全最有效的机制并不是立法,而是市场竞争之下的价格机制;后者是对交易安全最有效、最直接也最具体的市场反馈。 反观传统物权法,它希望对交易安全提供强制性的统一保护。但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这等于用立法标准否定个体交易,必然是低效的:(20)首先,不同交易者对风险的预期和敏感程度完全不同。每个人能够预期和承受的风险都不一样:正如有人喜欢冒生命危险从事高危行为(比如飙车、攀岩以及极限运动等等)一样,(21)交易者的性格(谨慎还是鲁莽)、交易财产价值、(22)对交易者的效用以及未来是否再次交易的预期等事实,都将综合影响交易人对风险的认知程度;其次,交易安全的维护手段呈现多元化,其中大部分都可归为市场行为,包括情感纽带(父母与子女的交易)、情谊与交情(朋友之间的交易)或者对未来工作利益的预期(比如上级与下属的交易)等等,我们甚至可以预期,关系联系越紧密,或者权力差距越大(试想普通公民与国家领导人的交易!),立法的交易安全保护就越无意义。再次,高风险高收益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如果当事人甘愿承担交易风险,立法为何要予以干涉?这不仅会导致资源浪费——因为当事人要额外花费成本满足立法设定的门槛(比如购买不动产必须进行登记),还意味着立法阻碍了当事人对市场利润的合法追逐。忽视乃至否定这些事实,意味着对交易自由的阻碍:在并无违法事由的前提下,仅以“有损交易安全”就否认当事人对财产的设权、处分与保全方式,这完全不是现代财产法应有的做派。 归根结底,传统物权法看不到市场竞争的存在,也没有看到价格机制对交易安全的自发调节。无论是出售方还是购买方,他们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时刻要与其他主体构成竞争。(23)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风险都可以通过市场渠道解决,因为风险结合其他信息最终会反馈形成市场价格。 或许有学者会以市场有时缺乏竞争质疑本文的结论。垄断是普遍存在的市场现实,(24)不过,物权法客体一般均为可替代品——即便是国人最关心的住房(不动产),也很少出现非此房不可的局面。既然具体物品的垄断非常少见,市场足以发挥调整作用。退一步讲,垄断有时反而会降低交易风险,因为垄断者往往希望风险尽可能低以便更快地攫取垄断租金;(25)另一方面,垄断很可能导致当事人根本没有风险救济途径,这在政府垄断中尤其明显(也就是所谓“没处说理”),此时侈谈交易安全纯属空话。总而言之,无论是竞争还是垄断,价格都足以作为风险控制的基本机制。还有学者会担心本文的意见会助长欺诈,但一方面,法律对欺诈的控制(26)应当体现为结构性激励而不是个案性管制,即明确不同行为的不同风险水准供当事人自行选择,最终目标在于培养健康而负责任的市场主体。(27)在传统物权法的家长主义之下,正常交易者的合法诉求受到了严重限制,而违法者仍然会绕开物权法追求各种违法利益。前文提到的“一物二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本文无意否认交易安全值得保护,也不甚认同诸如哈耶克对市场和自生自发规则的极端化信赖。我们赞同如下结论,政府以及国家的规则对财产结构的影响和降低交易成本至关重要,(28)因此保护交易安全亦为必需。但这种保护并不是立法的目标,而是一种手段。对民法而言,交易安全必须与其他手段一并指向更高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促进交易。 五、交易安全:促进交易的手段之一 交易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历史上看,交易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皮雷纳认为,商业是改变欧洲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29)布洛赫同样认为,欧洲中世纪的贸易通货缺乏且流通缓慢,甚至只是作为对封建权力的承认甚至感谢。(30)一旦商品和货币流通得到加强,“欧洲封建主义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入了“靠买卖而生存”的现代社会。(31)从微观的角度看,正如主流经济学指出,交易会提高对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改善每个人的处境;(32)而从宏观的角度看,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专门化进程,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交易成本的降低。(33)总而言之,交易推动并且标志着对现代社会,促进和激励交易就理应成为民法的核心旨归。 从理论上讲,对交易的激励机制保护有如下两种方式:一种是积极层面,激发当事人进行交易的欲望;另一种则是消极层面,祛除交易的障碍,使当事人在交易时不会太麻烦或太担心。保护交易安全的论证就是后一种。它通过限制单一物上有限的对世性权利类型和数量,配套强制公示制度,希望降低包括搜寻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34)但前文已经指出,就算交易毫无风险(这是不可能的),也不必然会带来交易。正如美国学者克里斯特曼曾指出,私有财产权在激发当事人交易的愿望方面并无先天的优势,因为“有权做什么”与“受激做什么”并非一回事,(35)这一洞见告诉我们,对权利的承认和保护固然重要,但在积极层面激励交易的关键之一是当事人的交易意愿:只有能够激发交易意愿的机制才能最直接地促进交易。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到,物权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将市场自发调节的事项纳入立法,固然借助强制性的立法降低了(包括调查成本在内的)交易成本,但同时也会减损交易自由:民事主体只能在有限的物权种类中选择(否则就不承认构成物权,也不具有对世效力),剥夺了当事人自由决定权利内容的权利。这会对交易意愿造成重大挫伤:当事人不能依靠自己的意志决定利益,而必须遵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充满了令人反感的恩赐与施舍味道,与现代社会的基调格格不入。 此处有一个事实需要澄清:如果说物权法的强制性规范并不合理,那么为什么两大法系会存在类似的实践?(36)首先必须看到,根据逻辑学的基本认识,经验事实并不能保证一个命题为真。更重要的是,相似的现象在基础不同的时候就不宜加以等同:普通法系的产权和大陆法系的纯粹所有权完全不同,美国的产权本身就是相对性产权;英国在保留两种普通法地产的同时,还承认了大量衡平法利益,而这些利益都具有对抗力。而且还要看到普通法系存在非常灵活的信托规范与实践,借助信托可以创设各种具有对抗力的利益和权利。这样看来,普通法对财产权利形式的削减与大陆法系形同神异。(37)而关于强制性登记,虽然英国自1925年改革之后,产权登记的强制性逐步加强,但采托伦斯登记制的英国仍然保留着大量无须登记的利益以及衡平法利益,并且针对已登记土地和非登记土地设计了不同的规范。(38)而且学者通过考察指出,这一进程有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以及利益诉求,绝非单纯为了满足概念逻辑。(39)正因如此,上述经验不能作为强制性登记的充分证据。 事实上,传统物权法出于家长主义硬性安置强行性规范,名为保护交易安全,实质是在扭曲市场:首先,它意味着风险预期低和不敏感的人要为预期高的人支出额外成本,等于被强制保险;其次,它限制了交易物种类——只有符合法定类型和内容的权利才能对世,并且提高了权利标准——必须满足法定的权利外观否则失权,人为增大权利成本,造成供应的短缺并带来无谓损失;再次,它有便利公权力寻租之嫌,这一点在不动产登记上最为明显。不动产登记伴随着高额税费,理由是国家对市场的促进和保障需要财政支持。(40)但如果当事人自担风险或者有其他渠道自保安全,物权法的强制登记意味着强制当事人接受本不需要的服务并且被征收税费,这本身非常可疑——毕竟保护当事人权利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义务。 本文认为,促进交易才是民法的核心旨归,保护交易安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判断,而只是为了促进交易的一种手段。同一目标之下的各种手段性原则往往会呈现出紧张关系,因此就必须加以协调和平衡。由此看来,传统物权法(乃至整个民法)都需要加以反思和变革。 六、结语:待进行的物权法变革 本文希望证明如下观点:保护交易安全不是物权法的核心,也不是证明一切制度合法性的完美理由。交易安全不是一个抽象的价值判断,它涉及非常复杂和具体的实证调查和数据分析,需要法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空泛地讨论毫无意义。因此物权法必须反思一切以交易安全为基础的制度:其中,诸如物权法定和一物一权之类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放弃,现有的强制公示制度须大幅革新,而善意第三人的价值判断也要被祛除……由于交易安全与物权法的联系如此紧密,改变交易安全基本等同于改变物权法,这当然不是一篇论文能够说完的大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浅尝辄止。从立法理念上,物权法要放弃“替当事人着想”的倾向,将利益与风险的决定权交由当事人自己判断和承担,最大限度地承认并且保护当事人对利益的自主处分和安排。这意味着物权法要放弃设权性的强制规范,着重形塑多元化的激励方式,提供不同层次的保护方式供当事人选择。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交易安全的保护方式,包括立法保护或者市场保护;物权法不否认当事人的权利本身,但不同权利在证据和证明责任的层面会有所差异,对抗力也会有所不同。在此仅试举一例:在新的物权法中,登记不再是不动产物权唯一的公示方式,但登记最为可靠和有效;然而当事人若自信不会发生纠纷,占有同样可以公示不动产物权。只是一旦发生纠纷,采取占有公示的当事人要负担更重的证明责任,包括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 进一步讲,物权法变革的核心是物权对抗力的多元化。传统物权法认为物权是对世权,但“对世性”本身是个逻辑悖论:既然只有经过司法判定才能决定权利归属,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先验地声称自己的权利可以对世;“对世性”缺乏司法意义,“对抗一切人”的隐喻终究要落实到具体的权利主张对抗中。(41)在现实世界复杂而多元的财产关系之中,物权的效力并非呈现单一和抽象的对世性,而必然在具体的情况下呈现出不同的对抗力。正确的做法是承认主观权利的对抗力源自当事人的约定,但这种对抗力是否能变现,取决于司法进程中的举证与对抗。反观传统物权法选择了一条错误的绝对主义进路:它将物权对抗力抽象为单一的对世性,并且设计一些僵化而过时的标准作为物权成立与生效的前置条件(典型的代表就是公示制度与物权法定),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交易安全。既然这个最重要的理由根本不成立,那么举重以明轻,物权法还有不改变的道理吗?尽管工程浩大,但物权法的变革总要从反驳某个流传许久的谬误开始,我们希望交易安全理论就是这个谬误。从这个角度讲,本文希望能够推动物权法真正的现代化变革。 注释: ①参见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以下;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页。有意思的是,物权行为理论的反对者同样强调交易安全:比如王利明先生在批评萨维尼“违法的交付亦为有效”时,理由就是这“有害于交易安全”。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再如孟勤国教授明确反对物权行为,但他同样认为物权的排他效力要止于交易安全。参见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当某个概念能同时为截然对立的方案提供支持,它很可能具有过分笼统和不明晰的弱点,交易安全恰为例证。 ②一个佐证是,传统民法认为,在无交易的情况下(比如盗赃物与脱手物)不存在善意取得。 ③前注①,孟勤国书,第114页。 ④维护善意第三人的结果完全可以基于其他理由:比如原权利人更容易控制无权处分引发的风险,因此由此带来的利益损失风险亦应由其承担。 ⑤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⑥比较特殊的是法国的意思主义,它并未延续罗马法中合同不包含所有权移转义务的法学传统,而是径直要求合同成立权利即移转。正如刘家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中,买受人取得的所有权并非抽象的对世所有权,而是效力有限、能够对抗第三人但无法彻底对抗出卖人的所有权。参见刘家安:《买卖的法律结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以下。因此意思主义并不能反驳本文的结论。 ⑦正如贝克和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一切风险事件几乎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是不可消除的副作用。参见[英]斯蒂尔:《风险与法律理论》,韩永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54页。 ⑧公示的强制性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原则上,不同物理性质的财产权公示方式不同;物权变动必须完成公示否则无效;而且公权力支撑的公示(登记)效力要高于私权形式的占有,等等。 ⑨参见[德]维甘德:《物权类型法定原则》,迟颖译,载《中德私法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105页。 ⑩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页。 (11)参见前注⑩,王泽鉴书,第44页;陈本寒、陈英:《也论物权法定原则——兼评我国〈物权法〉第5条之规定》,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4期。 (12)两大法系都设计了当事人无需受到物上负担约束的制度,大陆法系是善意取得和公示公信;而英美法系则是善意购买人(Bona fide purchaser)制度以及对信托利益的超越(Overreach)等制度规范。正如前文所言,此类制度不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而是为了明确风险分配:如果当事人的权利未能达到使其他人知悉的程度(比如缺乏实际占有),则要承担失权的风险。 (13)参见[德]赫尔鲍特:《封建法:欧洲真正的财产共同法——我们应当重新引入双重所有权?》,张彤译,载《中德私法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141页。也有中国学者主张建构相对所有权制度,参见李国强:《相对所有权观念的形成》,载《金陵法律评论》2009年春季卷。 (14)参见张凇纶:《论财产权利的对抗力规范——从继承中的财产法规则谈起》,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1期。 (15)关于这一原理的详细论述与历史材料,参见孟勤国、张凇纶:《财产法的权力经济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5期。 (16)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当价格足够低(也就是所谓“性价比”高)的时候,消费者很可能购买自己并不需要的产品。当然劣质产品除外(实际上劣质产品的本质是消费成本太高,因为有可能危害其他财产甚至人身,同样可以纳入价格之中),但劣质产品的“交易安全”并不是民法中的交易安全。 (17)类似的一个观点,可以参见麦克尼尔的关系契约理论。契约除了传统的交易合意,还包括命令、身份、社会功能、血缘关系、官僚体系、宗教义务以及习惯等多种社会因素和社会关系。参见刘承韪:《契约法理论的历史嬗迭与现代发展:以英美契约法为核心的考察》,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4期。我国学者对类似的想法亦有相当深入的考察,例如李力:《清代民间土地契约对于典的表达及其意义》,载《金陵法律评论》2006年春季卷。 (18)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算一个房屋上设定了100个抵押,但如果该房屋仅出售1元,正常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大不了就赔一块钱。另一个颇为现实的例子是,尽管不动产物权必须登记,但在现实中,有产权证、未办产权证以及无法办理产权证的房屋同时存在于房地产市场,在大小、位置以及其他因素相似的情况下,价格会相差甚远。由此看来,市场价格反映了当事人对不同公示方式的态度。 (19)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 (20)一个更极端的观点来自英国哲学家雅赛,其认为国家对权利的执行既无“内在的”必要性,也无“内在的”效率,并且以中世纪国家商业发展为证。参见[英]雅赛:《重申自由主义》,陈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21)而定价低的原因则有很多,比如更看重其他效用(如家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非理性(如对风险不敏感)等等。 (22)这尤其要考虑价值和自身资产相比较:对普通学生而言一个iPhone或许无比珍贵;但对亿万富翁而言仅仅是九牛一毛。这就可以想象二者对相同iPhone的风险敏感程度会完全不同。 (23)康芒斯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在设计交易结构的时候除了买主、卖主以及监督机构(如法院)之外,他指出买主和卖主双方都存在“下一个最佳替代者”,也就是竞争者。参见[美]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寿勉成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5-89、113-114页。 (24)事实上仍然有学者认为,除去自然垄断与政府垄断之外,基于市场的人为垄断基本不可能实现。参见[美]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杨欣欣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页。 (25)一个佐证是大型企业往往更重视声誉以及交易渠道的畅通。 (26)之所以说是控制而不是消除,是因为立法只能作为当事人行为的激励,而不可能彻底决定当事人的一切行为。这是现代法律人必须承认的现实:即便施加再重的制裁与惩罚,仍然不可能杜绝一切违法乃至犯罪行为,欺诈亦然。一个类似的精辟见解,可参见[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8-90页。 (27)这一方面包括民众对风险的理性认识,目前我国存在将风险一味归咎于政府的倾向,原因就在于政府承担一切风险分散成本的政治传统(背后就是包括高税收在内的家长主义)。这是非常不良的实践方式:一方面政府疲于奔命;另一方面民众日益对风险不敏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立法者的本意是为了维护出资父母利益,但忽视了一切出资都有风险。这一条规定实质是利用公共资源(立法)分散了(本该由婚姻当事人自行承担的)婚姻风险,加剧了当事人对婚姻风险的不敏感。另一方面包括市场对风险机制的完善,如美国学者希勒所言,应借助以保险、贷款、宏观市场以及国际协议等金融创新来分散和管理风险。参见[美]希勒:《金融新秩序》,陈雨露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28)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一编。 (29)参见[比]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5-137页。 (30)参见[法]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册),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3-139页。 (31)参见前注(30),[法]布洛赫书,第139页。 (32)参见[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33)类似的观点可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一章;[英]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91页;前注(28),[美]道格拉斯·C.诺斯书,第175页。 (34)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以下。苏先生援引并批评了Merrill和Smith对物权法定的维护,也即是估量成本和挫折成本(因无法交易而带来的成本)之间的函数关系。 (35)参见[美]克里斯特曼:《财产的神话,走向平等主义的所有权理论》,张绍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6、185页。 (36)普通法系的Numerus Clausus很类似物权法定,参见张鹏:《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载《法学》2003年第10期。自1290年《完全保有法》开始,普通法一直在削减地产和保有的种类和数量,到了1925年财产法改革之后,英国仅承认两种普通法地产利益(即非限嗣继承不动产与租赁),其余的地产利益一概被括入衡平法利益,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美国亦然,如霍姆斯在Johnson v.Whiton一案中指出,美国人已经不能创设新型地产,美国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财产权的标准化进程:通过限定财产权(地产)的形式,增加财产的可交易性(Transferability)。因为太过独特的“财产权”会增加调查成本(Measurement Cost)。参见[美]杜克米尼尔、克里尔:《财产法》,第5版,中信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第215页。 (37)参见张凇纶:《论物上负担制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95页。 (38)关于这一点的详细阐述,参见Riddall,Introduction to Land Law,3rd ed,Butterworths & Co.Ltd,1983.pp.438-440. (39)比如事务律师和土地登记处之间的矛盾以及英国对财政收入的追求等等。参见于霄:《1925年英国财产立法改革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68-169页、第182页等处。我们至少应当承认,强制性登记或许更多源自政府权力扩张的大趋势,其必要性仍有反思的余地。 (40)这是税法学的基本认识,参见葛克昌:《所得税与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2~13页。 (41)参见前注(14),张凇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