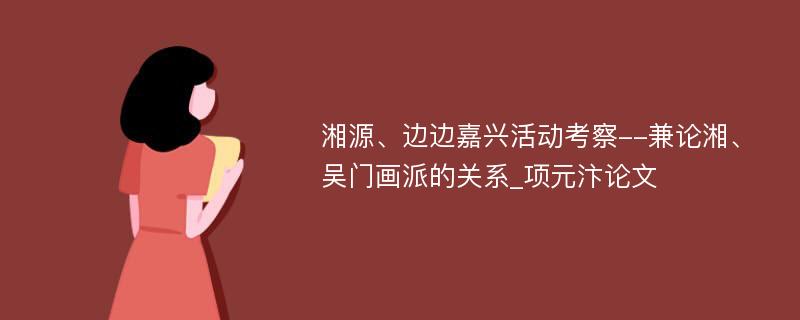
项元汴嘉兴活动散考——兼论项氏与吴门画派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兴论文,画派论文,关系论文,项元汴论文,兼论项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国书画史上最大的私人鉴藏家,嘉兴项元汴历来引人关注。但由于史料分散,钩玄不易,我们对他的生平还了解甚少。近些年,随着一些学者的努力,有关他的家系已获得了较为准确的考证,此外,亦有学者对其藏品进行了编目的尝试,它对于我们了解项元汴书画收藏的规模,进而研究明代书画鉴藏的趣味与风尚,都是大有帮助的。从项元汴的一生看,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嘉兴,有关他在嘉兴的活动及交游,研究者似乎还较少涉猎,本文试图就项元汴与嘉兴,及至与吴门画派的一些关系,作初步探讨。
直至今日,在嘉兴的民间,还流传着“三麻子收古董”的乡谚。“三麻子”即项子京,清代沈季友在《槜李诗系》中,明确记载到:“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时人多艳称‘项三麻子’云。”①又据其同乡陈懿典《太学生墨庵严公暨元配仲孺人合葬墓志铭》“余每谓公,短小精悍颇似项子京”②之语可知,项元汴身材矮小。由此看来,项元汴实属长相平庸,貌不惊人之辈。嘉兴庄一佛先生旧藏《项墨林先生像》,与文献记载较为吻合,③比对台北故宫博物院王世华先生藏清代贾瑞龄摹本《墨林山人小像》,④尽管动态各异,但二者形象高度一致,看来应有可靠的祖本,足为我们想见其音容之一斑。
宣德五年(1430),嘉兴府析嘉兴县西北境为秀水县,东北境为嘉善县,此后的四五百年间,嘉兴长期保持着“一府七县”的体制。项元汴家族被归为秀水籍,据明嘉靖《嘉兴府图记》,秀水县“东西广三十八里,南北袤四十五里界”。⑤著名的天籁阁即位于秀水县南的项家漾附近,上个世纪80年代初,嘉兴市的建设路北首东侧,曾被命名为“天籁里”(现已更名),⑥足以见项氏天籁阁的影响。天籁阁是项家的附属建筑,早已湮没无存,所幸海盐徐定夫尚遗有《游禾城项园》一首,足资后世想象其奢华:“名家园林城郭间,侧径逶迤廻石阑。亭亭高云下土阜,飒飒清画鸣风湍。潭涡地接三江脉,竹柏阴连五月寒。繁华回首俱陈迹,金谷平原此重看。”⑦
除天籁阁为我们熟知外,项园还有供项元汴雅集的“双树楼”,据项元淇《少岳诗集》,此楼主要用于项氏与僧侣的聚会。⑧同时,还有专用于兄弟间交流的“花萼亭”。⑨规模甚大,难怪时人比之为“扬雄宅”⑩和“金谷园”。
天籁阁毁于乙酉兵变,具体形制尚不见文献记载,诚为憾事。但当日阁中陈设,还有不少流入民间。项元汴把玩书画的石桌,后来成为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物,供其批校缥缃万椠,黄丕烈这样欣喜地记录下:“余家向收大理石画桌,亦其家(陆西屏)旧藏,……此桌出墨林山堂,石背镌此四字,并镌云:‘其值四十金。’自余收得后,吴中豪家喜蓄大理石器具者,皆来议让,卒以未谐而止。岁丁丑(1817)大除,晤一博闻往事之人,谈及墨林当日,有数十万金之书画,皆于此桌上展阅,故项氏甚重之,而此时光泽可鉴,盖有无数古人精神所寄也。余虽不讲书画,而古书堆积,实在此桌间,安知非此石有灵,恋恋于此冷淡生活耶。今而后当谨护持之,勿轻去焉,庶足以慰此古物之精灵乎。戊寅(1818)元旦,坐雪百宋一廛,复翁记。”(11)
另有道光间嘉兴收藏家郭季人,因得项墨林铁如意,故号其斋“如意馆”。其上铭错金文二十四字:“非竹非玉,出自昆吾。指挥三军,张我令图。毋或骄溢,逞表珊瑚。”银错“项墨林”三字。此如意传为文天祥故物。(12)
作为嘉兴的望族,项家还拥有多处房产。嘉兴金明寺后的景范庐,也曾为项元汴家族的别墅,此地原为纪念范蠡而建。《嘉禾项氏清芬录》载:“景范庐,金明寺后,宋淳熙戊戌状元姚颖筑圃范蠡侧,颜其庐曰‘景范’,又有水亭,额曰‘铁舟母家’,项氏别业也。”(13)清代,该别墅又归项圣谟密友曹溶。(14)项家资力之雄,确非寻常!陈继儒曾记载其密友——项元汴侄孙项鼎铉,为获得苏轼《书庐山宝书》,不惜以一座庄园进行交换的史实,而不久之后,该法书即归于祝融,诚令人扼腕。(15)可以想见,对于书画收藏,项氏家族的确做到了不遗余力!
在项元汴研究过程中,我们应同时观照作为整体的项氏家族。他的兄长项元淇和项笃寿,对项元汴有着深远的影响。项元汴作为吴门趣味在嘉兴的传播者和代言人,其奠基工作却与两位兄长密切相关。项元淇与苏州集团接触很早,项元汴与陈淳的短暂交往即是由于项元淇的缘故,笔者已在另一篇论文中有所论述,(16)我们在此着重探讨项笃寿与吴门关系的开展。项笃寿系万历壬戌(1562)进士,他的书画收藏活动主要集中在他在嘉兴期间。《珊瑚网》显示他曾与谢樗仙有密切交往,(17)在此之前,他即主动与吴门画派的核心——文徵明家族进行了接触。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最初往来,其中间人却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柯律格[Craig Clunas]首先注意到这点,史料十分珍贵:
One work of calligraphy executed for Xiang Dushou by Wen Zhengming in 1545(when Xiang was only in his mid-twenties) is apparently extant,and it may possibly be that which is referred to in the only letter from Wen addressed to him,dated by internal evidenced to 1545 or 1546.In the letter Wen writes that the two men were not previously acquainted,but that Li Zicheng,none other than the recipient of Wintry Trees in 1542,′had travelled to Suzhou in past years,and spoke to me of your lofty elegance.′ Wen now acknowledges receipt of some Xiang′s writings,which he praised suitably (again remarking ′how have I deserved this consolation′) before going on:
I am now seventy-six years old,beset by illness,older and feebler every day.My insignificant old occupation is daily decayed and forgotten,and I am often ashamed(in the face of) those about me.As to the handscroll that you commissioned,due to a combination of illness and indolence I have not yet managed to write it; when I have a spare moment it shall be promptly delivered very shortly....I thank you for excellent silk I have received.
[据我所知,文徵明在1545年为项笃寿所作的一件书法尚存于世(项笃寿那时年仅二十五岁),它很可能与仅有的一封文征明写给他的书信有关,时间在1545年或1546年之内。信中文徵明表示他此前与二位(项笃寿、项元汴兄弟)并不相识,但正是由于李子成,也就是那位在1542年获赠《寒林图》的人,他“比岁薄游苏州,每谈高雅(指项氏兄弟)”,文徵明于是见到了项笃寿的手迹,并得体地对之表示赞扬(又云“审问起候安胜为慰”),然后文征明说:
“征明今年七十有六,病疾侵夺,日老日憊。区区旧业,日益废忘,媿于左右多矣。向委手卷,病嬾因循,至今不曾写得。旦晚稍闲,当课上也。使还,且此奉复,再领佳币,就此附谢。(未间,惟若时自爱。徵明顿首,再拜少谿尊兄侍史。)”](18)
该尺牍著录于《经训堂法帖》,柯律格只引用了后半部分,前半段的内容是:“徵明久不闻问,颇切驰系。比岁李子成薄游吴门,每谈高雅,尤用企竢。适承惠教,兼示佳文,词旨明润,命意严正。捧读之余,益深健羡。首夏清和,审闻起候安胜为慰。……”(19)
文徵明提到的那位介绍人叫李子成,武原人。他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二月前往苏州,吊唁文徵明妻子吴氏。(20)文徵明为他作《仿李营丘寒林图》,柯律格曾对之进行过研究,该图现藏大英博物馆。所幸《式古堂书画汇考》留下了文徵明的跋语:“武原李子成,以余有内子之戚,不远数百里过慰吴门。因谈李营丘寒林之妙,遂为作此。时虽岁暮,而天气和煦,意兴颇佳。篝灯涂抹,不觉满纸。比成,漏下四十刻矣。时嘉靖壬寅腊月廿又一日,徵明识,时年七十又三矣。”(21)
据《文徵明年谱》,李子成只留下这次与文氏的交往记录,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柯律格因此将李推荐项笃寿的时间定在嘉靖二十一年,这应属柯律格的推测(是年项笃寿二十二岁,项元汴十八岁),当然我们也不应排除另有时间的可能,毕竟文徵明写给项笃寿的这封信已是三年之后,如此长的间隔,似有悖常理。
项笃寿奉上作品请文徵明指正,并向他索书。柯律格从信中语气判断,他们此前并不相识。不过细细分析,文徵明也许对项笃寿略有所知,或许还有过极浅的交往,但可以肯定的是绝无深交,毕竟项笃寿还过于年轻。叶梅女士在《晚明嘉兴项氏法书鉴藏研究》中指出,项家与文徵明的来往,应从项元汴父亲项诠开始,(22)但叶梅还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而柯律格上文所引《文徵明致少谿》,足以证明两家的交往,很可能与项笃寿密切相关。只是柯律格说李子成向文征明推荐了项家两兄弟(two men),信中似乎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不知柯律格何以认为。文徵明在该年十月,为项笃寿作《行书春兴二首卷》,现藏北京市文物商店,(23)或许,这正意味着他们深入交往的开端。此后,他还收藏过文徵明的《松阴高士图》,彭年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月三日为之题跋,(24)也正是这年,项笃寿荣登进士榜。
文徵明致项元汴的尺牍,目前仅知一封。文徵明应墨林之请,为书《北山移文》相赠。写作时间不详,从内中语气判断,他们已建立了一定的交谊:“昨承惠访,病中多慢。别后方窃愧念,而诲帖荐临,糕果加币,珍异稠叠。祇辱之余,益深惭感。即审还舍,跋涉无恙,起居□□为慰。区区衰病如昨,无足道者。委书《北山移文》并二绫轴,草草居上,拙劣芜谬,不足以副盛意也。使还,率尔奉复。徵明肃拜,上覆墨林太学茂才。”(25)
项元汴鉴藏活动的后面,有着一个庞大的复杂网络。其间有职业古董商,也有和他一样的职业收藏家,还有僧人及装裱匠。在鉴藏之风盛行的明代,甚至许多地位卑微的文人,也或多或少的拥有几件藏品。透过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丰富图景。而在项元汴时代,这种景象更是显得极为迷人。
嘉靖三十八年(1559),当三十五岁的项元汴得到元代揭傒斯《揭文安公杂诗卷》时,他在退密斋中自负地写下一段题跋,流露出雄视江南的气概:
昔唐宋之韩柳欧苏以文擅名,时称四大家。元有虞杨范揭以诗鸣世,人亦谓之云。余近日颓荣进,闭门却扫,倦则游艺,雅好博古,展卷品评。至视文安公手书己作,词格清丽,笔法婉媚,似得晋唐人逸韵,由其心志非力可勉,若困而学之终不能入,岂可与庸鄙罔习共鉴定其甲乙,若斯人者,当时罕有与之俦匹。余特宝重是卷,独叹其高处不必世论之同也,赏音者自以余言为然,予何言哉!嘉靖己未岁仲夏十又一日在北窗下书,退密斋主人项元汴力疾饶舌。(26)
毫无疑问,此时的项元汴对自己的目光和品位十分自信,这种自信源于他身后的宏富收藏。
由于项元汴的存在,嘉兴成为古董商的纷至沓来之地。不要小觑那些鬻古者,对于项元汴,他们是愿意拿出真品和精品的:“……昔闻先宗伯云,有古董陈海泉者,将成国书画、庐鸿草堂图、虞世南庙堂真迹、宋拓定武兰亭、怀素自叙真迹等共九卷至嘉兴售项墨林,酬价八百金之语。今阅是卷尾有墨林手迹并题识,定价及印章历历俱存,确为九卷之一也。……”(27)
这是韩逢禧跋《宋拓定武兰亭》时所记,此段掌故由韩世能处得知。不过那位叫陈海泉的古董商,我们还无法知道更多的情况。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交易,档次极高,其中尚有几件流传至今,为各大博物馆所珍。遗憾的是,项元汴没有记录下收藏的时间,留下了史料的缺憾。
除职业古董商外,项元汴还有不少藏品来自吴门名流,如文彭、文嘉,当然也包括文徵明。文氏二兄弟与项元汴的关系已为大家所熟知,他们经常性的充当项元汴的顾问,并为其掌眼。文彭与项元汴关系的黄金时期应在他担任秀水训导期间,现存旅顺博物馆的《文彭致项墨林札》,其中有大部分应写作于他在嘉兴的时段。(28)万历十年(1582)文嘉逝世以后,项元汴的收藏活动逐渐进入低潮,(29)可见文氏集团对他收藏活动的帮助非比寻常。除文彭、文嘉外,顾从义与项氏家族的交往也值得一提,他曾转让部分收藏给项元汴。而顾从义正是项元淇的好友。
嘉靖三十三年(1554)春,顾从义拜访嘉兴项氏,并盘桓数日,项元淇书诗作相赠,从项元淇跋语看,二人有较长的交往历史:
嘉靖甲寅春,研山留此信宿,乘暇为书旧作数首。盖往常遗寄,纸墨不啻十数,辄复为好事者持去,而研山又获此为重,是诚俗下语,岂足为大好耶。项元淇。(30)
项元汴一直与顾氏兄弟保持有书画交易,宋赵士雷《湘乡小景图》即是项元汴从顾从德手上获得,顾氏于嘉靖二十年(1541)买下此卷,项元汴后以原价购归。(31)顾氏后来又转让了《蜀素帖》给项,它一度被文徵明视为有“神物呵护”。(32)此外,昆山也是项元汴时常造访的地方,他和著名的吴中富豪周于凤(周六观)有过交情,他曾经是仇英的重要艺术赞助人。项元汴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和嘉靖三十二年分别从他手上买下了李唐《夷齐像》(33)和张即之书《李珩墓志铭》,(34)这段时间正是他与仇英交往的高峰,不知项元汴和周六观的交往是否与仇英有关。
在嘉兴地区,项元汴也拥有一张巨大的收藏网络。分析项元汴书画题跋的记语,我们不难观察到这点。其间,嘉兴的池湾沈氏和乌镇王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关池湾沈氏,史料上尚未有更多发现,唯有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有过记录,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三日,“同汤慧珠、许叔重、亨儿拏舟至池湾,访沈尔侯、仲贞兄弟,留集北山草堂”。(35)李日华当日夜宿沈尔侯园亭,直到第二天中午离开。李日华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所阅书画,计有夏圭、倪瓒、吴镇及赵孟頫夫妇等人的画作与书札若干。期间沈尔侯还向李日华“出观其父贞石公讳士立者手书数通”,李日华云“贞石年三十余而早世”。(36)池湾地处嘉兴城东北约10公里处,古称麟湖,也叫池溪,那里有著名的栖真寺。项元汴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在池湾沈氏手中买下王宠书《离骚并太史公赞卷》,笔者推测,与项元汴进行交易的,应该就是沈尔侯的父亲沈贞石。项元汴对王氏的书法十分喜爱,王宠曾于嘉靖五年手抄宋周必大《玉堂类稿》,该稿本后为“天籁阁”所有,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项氏诸印俱存。(37)项元汴本与沈氏谈好价格为十五两,但由于沈氏知道项元汴十分喜爱该法书,又加价五两,最后以二十两成交。项元汴把此事忠实地记录于跋尾。这一定价已超出项元汴收藏宋代石延年《古松诗》的价格,(38)项氏对王宠的钟爱可见一斑。
乌镇王氏较为著名,项元汴在他那买过不少书画,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神龙本《兰亭序》,文嘉为之题跋,至今为诸多学者广泛引用。项元汴获得这一稀世之珍是在万历五年(1577),时年五十三岁,我们在今天仍把它定为冯承素摹本,即是根据项元汴的鉴定意见。(39)万历三十八年四月九日,李日华在树荫浓绿的“淅沥小雨”中,无限感慨地追忆此事,并再次抄录文嘉题跋。(40)乌镇王氏见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氏“名济,字伯雨。以资为横州判官,富而好客,……所居有长吟阁、宝岘楼,图史鼎彝,夺目满栋”,(41)看来也是位资力雄厚的藏家。文嘉认识王济,是否在其中起过中间人的作用,还需史料的进一步发现。
文氏集团对项元汴的支持不仅在于为之鉴定和收罗书画,同时也为他进行技术人才输出。现藏旅顺博物馆的《文彭致项墨林札》,有一封引人注目:“汤淮之艺,犹有乃父遗风,有中等生活,可发与装潢,幸勿孤其远来之望。……”(42)
明代装潢名手辈出,据《茶余客话》载:“王弇州藏古迹最多,尤重装潢。有强氏者精此艺,延为上宾,居于家园。又汤氏者,亦擅此艺。时有汪景纯在白门,得右军真迹,往聘汤氏,厚遗仪币,张筵下拜,景纯朝夕不离左右,阅五旬始成。……”(43)汤姓装裱匠在文献中时有出现,《珊瑚网》中还时常能看到叫一位“汤玉林”的裱工。(44)谢稚柳先生在谈及上述文彭信札时说:“汤翰在嘉靖时为装潢名手,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卷,当时即为汤所装。又尚有一装手名汤臣者,《清明上河图》之事,即为其所起,亦当时吴中名手。此汤淮装潢有父风,不知是汤翰,抑或汤臣?”(45)
谢稚柳提到的“汤臣”,也即汤勤,人称“汤裱褙”,传说中臭名昭著。而他后来的家就在嘉兴,并且紧靠项元汴天籁阁。至今嘉兴还有“汤家巷”,就是以汤勤命名的。(46)作为大收藏家,项元汴显然需要大量书画修复及装裱人才,汤勤应该为项元汴服务过,此后就在嘉兴定居。汤姓裱工是一个家族,但由于地位不高,文献中极少留下他们的确切字号,信中提到的汤淮,与汤勤是否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还有王雅宾复元,他的学生朱肖海是嘉兴知名的作伪专家,徐邦达等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他。王复元的传记见于李日华《紫桃轩又缀》,(47)他早年“得事文徵仲先生,稔其议论风旨,因精鉴古”,(48)后因文徵明去世,来到嘉兴,转投项元汴门下。万木春先生对他有过仔细的观察,这里不再重复。(49)除了在项元汴门下从事古画修补,王复元也为项元汴收集字画,目的是换得金钱,平日“每独行阅市,遇奇物佳玩与缣素之迹,即潜购之”,陈继儒有载:“赵子昂亭林碑,其真迹曾粘村民屋壁上,王野宾买之以转售项氏。”(50)王复元生活放荡,又较为拮据,李日华说他与豪贵易金钱,“资未尽不轻鬻一物也”。(51)而替项元汴收罗古物,他可以完全不必有上述担心。
这是一个由吴门集团形成的自上而下的网络,它使项元汴的收藏活动有了强有力的保障。但同时,项元汴本人也极善于吸纳来自各路的民间高手。
作为一位职业鉴藏家,项元汴有着敏锐的嗅觉。只要是他看中的人才,他总会不遗余力地揽至门下。万历中名手张鸣岐,“住谢洞(今嘉兴新塍一带),善治铜炉,无不精绝,项墨林见而异之,招居城中,名遂大著”。(52)宜兴制壶高手,时大彬弟子李茂林、蒋伯荂,(53)以及浙中名匠阎望云,(54)甚至更远的新疆人蒋少川,(55)都曾经在项元汴门下为其服务。项元汴通过他们,既满足了自己的收藏欲,客观上也扮演了艺术赞助人的角色,实现了利益的互惠与互补。
在嘉兴,项元汴过着极为悠闲的生活。显赫的家族背景以及雄厚的财力,决定了他在里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其长兄项元淇,素与嘉兴地方官员保持有不错的交情,项元汴经营的典当业,在吃了官司之后,亦是由项元淇通过官府平息事端。(56)项家有殷实的地产,(57)项元汴亦时常亲自收取地租,盛百二《柚堂续笔谈》载:“项子京索租田家,见阶下一石,遂免其租,载石而归。”(58)可见,收藏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项元汴死后,李维桢为其书写行状,沈思孝则为他作传,(59)后来又由董其昌替他撰写墓志铭,可谓荣极一时。他的六个儿子继承了项元汴的收藏,也就是所谓的“六大房物”。此外他还有几个女儿,其中长女嫁到海盐的刘仲方家,不过不久便失去了丈夫,一直寡居。(60)三子项德新,在后来又与著名的焦竑结为亲家,实是艺林佳话。(61)
除了收藏,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文人一样,项元汴也醉心青楼。项元淇在《少岳诗集》中提到过一位叫杜苇的女子,她是嘉兴地区的名妓,(62)素与元淇相善。项元汴交游圈里的屠隆,(63)更是此道的著名人物。而项元汴的长子项穆,就是因寄情声色,在《书法雅言》成书后的不久,便盛年凋零。(64)见于钮琇《觚賸》中的项墨林狎妓一事广为流传,为他略显刻板的生平平添了一笔风流的色彩,(65)梅里诗人禇凤翔以诗进行了概括:“水沉床载莫愁城,千古风流有子京。不道青楼偏忘旧,香焚十里擅豪名。”(66)周履靖《闲云稿》亦有《春日项墨林夜集观妓》一首,其间这样写道:“舞袖摇银烛,歌声绕画栏。月浮杯乍白,漏促夜将阑。倒着接离兴,山翁醉笑看。”(67)细腻地为我们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项元汴生前应留下为数不少的画像。仇英、文嘉,以及后来的曾鲸都曾应邀为他作肖像画,遗憾的是均未得以流传。仇英的项墨林小像,至少在清代还能得见,王翚曾说:“时下谓仇君画,大抵以《墨林高士》为最。”(68)可见品位不低,当属仇英精心所作。项元汴对人物画创作也有相当的兴趣,从其《善财顶礼图》看,人物刻画极为不俗。李日华族兄李培在《水西集》中曾记录同乡吴东洲先生寿辰,项墨林为之写照,李培的赋诗中有“项公未已言外传,且为洒墨伸长笺”之语。(69)嘉兴本地著名肖像画家唐凤(号岐山),亦和项元汴有过合作,唐曾为冯梦祯及屠隆留有写真。(70)项元汴嘱唐岐山画脸,躯干部分则自己完成。项的友人智舷《题项子京小像》云:“倩人图面自图身,面或随人作喜嗔。只有此身偏倔强,诎信未肯暂随人。”(71)吴门画派中的人物画高手并不多,他的启蒙老师或许就是仇英。现藏上海博物馆、项元汴作于二十九岁的《双树楼图》(正确的名字应是《双树图》或《山水图》),(72)其间有一高士,刻画较为细腻,不过造型平庸,但已能说明他早年有过人物画训练的经历,这是一般吴门画家所没有的。
李培在《祭墨林先生文》中这样写道:“座上客常满,而衲子居半,无日不憩息于梵林,至或酣睡于香积,若不知有家也。”(73)黄承玄在《墨林项公暨配钱孺人墓表》中也说:“公……时从黄面白足辈说偈拈宗,机锋勃发,若夙契者。方外名僧飞锡至,靡不参印三乘,即老瞿昙不是过。”(74)可见项元汴与方外往来密切,但与他交往的有哪些僧人,这些僧人与他的书画鉴藏及创作活动有无关联,似鲜有涉及,兹就笔者所知,作一探讨。
著录于庞元济《虚斋名画录》,现藏南京博物院的《梵林图》,是项元汴现存作品中的一件佳作。徐邦达认为该图可能由项元汴三子项德新代笔,(75)理由是该画较为“工能”,不似其接近文嘉风格的墨笔小轴,似可商榷。该作品系纸本设色,据项元汴跋尾,创作于诸友双树楼雅集之时,“余之拙笔固不足以起时目,僧主当存之箧笥,以俟后之名人词翰品题。余楮切不可委诸俗陋,使有续貂之叹”。(76)清楚地表明是赠与僧友,但跋文没有说明受画者何人。所幸《少岳诗集》亦有载:“冬初过渊上人居,以子京弟图画梵林卷索题,时残阳明窗,木叶堕几,为书二绝”(诗不录)。(77)渊上人是龙渊上人的简称,他法号慧空。当年汪砢玉的父亲汪继美就是通过慧空等僧人的引见,方才得以结识项元汴——“先子爱荆,字世贤,别号荆筠山人。弱冠时,与慧空、慧鉴、大洲、竹堂、定湖诸方外游,因识子京公。”(78)而请项元汴为汪爱荆作《荆筠图》的,也正是慧空和尚。《珊瑚网》著录的该作品留有项元汴题识:“龙渊慧空上人,持素索绘《荆筠图》,为友人世贤汪君而徵其别号者,遂并题一联,以呈手眼云。”(79)正是由于慧空的关系,才使嘉兴这两大收藏家族建立起联系。
龙渊地处嘉兴城外以西,旧为白龙潭。唐代于此建立三塔,塔旁有龙渊寺,后改名茶禅寺,即“嘉禾八景”之“茶禅夕照”。宋以后更名为景德寺,也叫三塔寺。(80)传说苏轼曾到此汲水煮茶,故寺中建有“煮茶亭”。项元汴有枚鉴藏印曰“煮茶亭长”,即源于此。龙渊景德寺是项元汴与诸亲友时常雅集的地方,在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81)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项圣谟《山水图》(《三塔寺图》),便是他在顺治五年(1648)于陡门拜祭项元汴后(从三塔往西南约18公里,便是陡门寒字圩项元汴墓),路经此地,“喜雪”而作的。(82)
《珊瑚网》对慧空还有详细的记录,他叫彬公,一字化仪。旁通文墨,后归梓里,汪爱荆供其白璨灯油十余年。与他一起的慧鉴亦擅博古,其游峨眉有诸名宿送行卷,宋旭、文嘉、项元汴为之图,焦竑、陈继儒为之记,该图后来亦归汪砢玉。遗憾的是这件册页在汪继美去世后被盗,汪砢玉惋惜不已。(83)
项元淇卒于隆庆六年(1572),他记录《梵林图》的下限应在此年,而项德新还不满两岁,没有替项元汴代笔的可能。
定湖老人真谧,亦是项元汴交游圈的一位僧人。据《槜李诗系》,他乃“隆万间秀水真如寺僧冬谿之门人也,有学行。参方归后构室三楹于长水法师墓侧,绕屋四五亩,细竹翠烟,碧雾笼密,……王百谷至,每信宿不去”。(84)他的师父冬谿,陈麦青先生有过介绍,名方泽,字云望,嘉善人。他是项元淇密友,自然也与项元汴有一定交情。(85)精严寺与项家相隔不远,平日走动十分方便。项元汴在与元淇祭扫长水大师墓的时候,为真谧作过别号图——《定湖图》,真谧有诗为记。(86)万历三十七年三月九日,他的门孙牧隐曾谒见李日华,求作定湖诗集序。(87)
真谧与慧空都是嘉兴书画世界里的重要人物。因为与项元汴家族的密切关系,他们拥有令我们艳羡不已的学习条件。著录于《式古堂书画汇考》的项元淇“与二上人札”,为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兰亭》禊帖乃赵松雪所跋定武佳本,奉定湖上人。又赵魏公书纨扇《咏史诗赋帖》,此奉慧空者。兹审好尚,故致左右。须当手摹心追,方得此中三昧。昔赵文敏欲与独孤结一重翰墨缘,余亦尔耳。顷过西丘,余留面指。项元淇拜,二上人足下。(88)
此外,项元淇从苏州得到赵孟頫《简中峰帖》一册,亦借与真谧学习,并告诉他“此书学人不可无者,……字中有笔,如禅句中有眼,须一毫头上下功夫始得”。(89)看来项元淇还是他们的书法老师。
嘉兴丛林遍布,名僧大德与士人交往频繁。在嘉兴的地方文献中,时常可以看到一位智舷和尚的身影,频率极高,引人注目。智舷字苇如,号秋潭。他与项元汴家三代人都有过从,尤与项圣谟相善。在项圣谟的《尚友图》中,智舷即赫然在列。(90)智舷十七岁开始居秀水金明寺,那是项元汴的别墅所在地,他在项元汴家见过王绂《江山万里图》,(91)因受项元汴之请作《题项子京小像》而“名日盛”。(92)晚居黄叶庵,李日华为他作《秋潭禅师传》,其《黄叶庵诗草》残卷尚存于世。崇祯庚午(1630)卒,年七十四,(93)可知他与项元汴的交往是在青年时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项元汴致竹园上人札》,历来未见著录,兹录如下:
久不会,殊想。昨专人奉问南山长老所藏赵子昂手迹,已承指示去路,即往彼询之。自然和尚有云,直待秋后七月方上来。今若迟迟,恐不能待他,乞为我再作一柬,促此僧持来看,当出高价,不然,遂持银去见买。兹此进求一纸字去,以为执托,千万详细写下,容谢不一。外扇一柄,奉敬竹园上人。即日。项元汴顿首。(94)
此竹园上人未知是谁,待考。其间不难想见项元汴迫切的心情,反映了他对收藏赵孟頫法书的喜爱和重视。仅在万历三年(1575),他就先后获得了赵孟頫的《大洞玉经卷》和小楷《汲黯传册》二十二板。其中《汲黯传》有文徵明题跋,项元汴又进行了重新装裱,可见重视之程度。(95)叶梅女士长期从事项元汴藏品的编目研究,她指出,项氏收藏的赵孟頫法书至少67件。(96)这通珍贵的尺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项元汴寻访赵书的真实记录,殊为难得!
项元汴的出行情况,史料记载较少。张岱《陶庵梦忆》有他在杭州的片语描写。(97)与晚明社会的普遍风尚一样,他喜去无锡惠泉取水,到虎丘天池采茶,若逗留时间稍长,他还不忘寄些给在嘉兴的长兄项元淇。(98)在水运发达的江南,项元汴亦拥有豪华的船只,那是他出行的重要工具。《觚賸》中就提到他去南京是“巨舰访之”,(99)而其密友彭年因受到项元汴虎丘采茶的邀请,对他的书画舫亦留有深刻印象,并写下“画舸乘春渺若仙,笔床茶窖布帆悬”的诗句。(100)不过项元汴的出游,主要还是与书画鉴藏活动相关,邀请吴门名流题咏或向他们索书,是他的主要目的。我们上文提到过的《文徵明致墨林札》就是一例,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彭年致项墨林一通》,也是同样的情况:
雅意稠叠,感荷无任。饱德之余,加悚加悚。经赋略皆试写,然遇亲友葬事,山行三四次,登顿困惫,僵卧累日,未能卒业以复。半月后当课完驰纳馆下,并请罪也。伏枕草草,并希鉴恕。廿五日彭年顿首再拜复。墨林先生大元道契侍史。(101)
董其昌给项元汴圈子列出的名单中,彭孔嘉是其中一位,但向来未见具体史料,上述两例聊作补充。彭年与项笃寿亦有不错的交谊,这点前文已有论述。
《嘉禾徵献录》在介绍项元汴时曾说:“海内风雅之士,取道嘉禾必访元汴,而登其所谓天籁阁者。”(102)可见他在当时的极高知名度。天籁阁的客人中既有丰坊(103)、周天球(104)这样的名流,也有像吴孺子那样的寒士,(105)当然也会有不少江湖掮客。詹景凤万历四年过嘉兴时与项元汴的那段对话十分著名,那年项元汴五十二岁,此前不久他得到了法常的《花卉翎毛卷》及宋本《北山录》,(106)项元汴在欣喜间毫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作为江东巨眼的自信,对话颇令人想起《三国演义》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情景。
天籁阁宏富的收藏不仅滋养了董其昌,也滋养了不少嘉兴籍书画家。周履靖正是在项元汴的支持下“遂得尽其披览”,(107)终有所成。在与项元汴的交往过程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履靖所编《九畹遗容》与《春谷嘤翔》便是由项元汴为其校订的,(108)丁羲元甚至认为项元汴收藏的千文编号即是以周履靖的《初广千文》为依据,(109)但笔者目前还未发现其史料来源。李日华家族因与项家乃世交,加上其族兄李培获侍项元汴近四十年,(110)故李日华亦得以“纵观书绘名迹、鼎彝法物”,(111)为今后成为博物君子奠定下坚实基础。饱受天籁阁滋养的还不只是他们,活跃于崇祯年间的嘉兴画家戴晋亦是一例。戴晋字康侯,号松厂,幼孤,因与其叔至项氏天籁,遂工画。(112)后来加入汪砢玉的画社,曾作《摩诘诗意图》。董其昌也认识戴晋,著名的《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就是在他的手上,董其昌在戴晋这里留下题跋,进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鉴定。在今天的大阪市立美术馆,我们还能看到这幅作品上董其昌的观画题语。(113)更令人惊奇的是,天籁阁中还有一位叫吴氏的女画家,“居墨林山人天籁阁,琴榻销然,有林下风”。(114)实是令人艳羡!在项元汴离世后,他散落的藏品成为众人竞相争购的对象,嘉兴金鄂严所藏的大部分书画即天籁阁故物,方薰从中获益匪浅,(115)他充满真知灼见的《山静居画论》,若没有他早年的这段经历实是无法想象。
在项元汴子孙手中,他庞大的收藏逐渐分崩离析。四子项德明(字晦夫,号鑑台),由于祖宅之东“清和堂两遭回禄”,(116)部分书画毁于火中,他亦因此家道中落,此后更是大量出售项元汴收藏。(117)明清易代之际,天籁阁灰飞烟灭,累世收藏遭灭顶之灾,徒余后人嗟叹!
客观地看,项元汴是较为低调的。在他留下的书画题跋中,几乎看不到他对于自己收藏的吹嘘,对于自身的艺术水平,他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我们在阅读其题跋时不难感受到这一点。项元汴双亲去世后,他在所作《竹石小山图轴》中,曾经这样表达了他的情感:
汴以不才困处丘隅,踌躇世故凄恻家艰。惜哉运命受物汶汶,思无自释,援翰宅心。盖取夫岩岭高则云霞之气鲜,林薮深则萧飋之音微,其可以藻玄莹素疵其浩然者乎,舍此遂无以泄孤愤之叹,以舒抑郁之怀矣,人能观画畴知斯意。(118)
尽管项元汴画名不著,但由于影响甚大,后世对他的作品仍十分重视。朱彝尊就提到过与他同时的著名书画家程邃(字穆倩),家虽贫而尤嗜古,曾以所藏项元汴画作请他题跋。朱彝尊感喟道:“子京之画,世人知之者罕,程子独加珍惜,俾予跋尾。夫程子且然,况生同里而数过其庐如予者耶!”(119)或许,他又回忆起少年时代屡登天籁阁的历历往事。
万历十八年(1590),项元汴在“家衅陡作”中离开人世,(120)葬于嘉兴城外陡门寒字圩。这位大收藏家的遗体不幸于文革被盗,(121)1975年春,项墓进行了发掘,里面有其妻妾的棺木,从项元汴二、三房陪葬器物看,他的家族已经衰败。(122)另据项映薇《古禾杂识》,清道光年间的项家,已“凋丧殆尽”。(123)
注释:
①[清]沈季友《槜李诗系》,载《四库全书》14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325页。
②[明]陈懿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十二,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79册,北京出版社,1998,第192页。陈懿典,字孟常,万历二十一年进士。
③见嘉兴庄逸庐、庄一拂先生藏《嘉兴历代先贤像传》。山阴冯悦轩、秀水陈贤林写照,郭蔗亭补景。承嘉兴图书馆范笑我先生惠赠照片,特此感谢。
④见郑银淑《项元汴之书画收藏与艺术》附图,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第253页。
⑤[明]赵瀛、赵文华纂修嘉靖《嘉兴府图记》卷二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91册,齐鲁书社,1997,第330页。
⑥参[清]许瑶光修、吴仰贤纂光绪《嘉兴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与《嘉兴市地名志》(嘉兴市地名办公室编,1982)的记载。
⑦[明]罗炌修、黄承昊纂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九,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第771页。此外,[明]释方泽《冬谿集》中亦见类似记载,陈麦青先生已有引用,《关于项元汴之家系及其他》第四节,载《随兴居谈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102页。
⑧见[明]项元淇《少岳诗集·初秋双树楼》的记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43册,齐鲁书社,1997,第505页。另见方泽《冬谿集》外集上《夏日过西丘双树楼》,载陆光祖《禅门逸书》初编第七册,台湾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据隆庆辛未刊本影印。双树楼也可能位于嘉兴城西。
⑨花萼者,取《诗经·小雅·棠棣》“棠棣之华,鄂(萼)不韡韡”之意。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十七《棠棣》,中华书局,1989,第502页。唐代有《李氏花萼集》。《少岳诗集》中,每每兄弟相聚,都于(子京弟)花萼亭中。
⑩[明]释方泽《冬谿集》外集卷上《立秋日过项墨林》有云“每过扬雄宅,令人心晏如”。载陆光祖《禅门逸书》初编第七册,台湾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据隆庆辛未刊本影印。
(11)见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240页。
(12)吴藕汀著《郭家与我》,未刊本。王世华所藏《墨林山人像》,项元汴身旁置有一如意,不知是否为此件。
(13)项乃斌《嘉禾项氏清芬录》第一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14)同注(13)。
(15)[明]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五十《书庐山宝书》,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16)见笔者《项元汴家系再考》,未刊稿,第12-13页。
(17)[明]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六《谢樗仙山水长卷》,载《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第1148页。
(18)Craig Clunas,Elegant Debts: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1470-1559,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td,2004,p124,信札翻译依原始文献,括弧内的内容是笔者补加的,以便完整阅读。
(19)转引自周道振、张月尊辑《文徵明集》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473页。
(20)见周道振、张月尊辑《文徵明年谱》卷六,百家出版社,1998,第530页。
(21)[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二十八《徵仲仿李营丘寒林图并识》,载《中国书画全书》第7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第209页。
(22)叶梅《晚明嘉兴项氏法书鉴藏研究》,首都师大2006届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欧阳中石。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第20页。
(23)见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第207页。
(24)[清]吴升《大观录》卷二十,载《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第575页。
(25)见周道振辑《文徵明集续辑》卷下,自印本,第102页。
(26)[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卷之十七,载《中国书画全书》第6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第432页。
(27)[清]吴荣光《辛丑消夏录》卷一,见《中国书画全书》第1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第830页。
(28)从这些信札中的语气看,他们之间的距离应该非常近,如旅顺卷项元汴编号第四十九札:“适有人持蔡君谟《茶录》在此,能枉驾过此一看否?”又如编号第五十一札:“……在敝寓,屈过一赏,幸即命驾。”见《中国古代书画图录》第十六册,文物出版社,2000,第38页。
(29)笔者《项元汴年谱》(未刊稿)可见其收藏的清晰历程,文氏家族对他的帮助亦时有体现,这与以往项元汴研究者的结论是一致的。
(30)[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二《项伯子诗卷》,见《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第1034页。
(31)同注(24),卷十三《赵公震湘乡小景卷》,第409页。
(32)同注(26),书卷之十一,第317页。
(33)同注(27),第860页。
(34)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书法一下,文物出版社,1999。
(35)[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八年十一年三月条,《嘉业堂丛书》本,文物出版社,1982。
(36)同注(35)。
(37)见李宗焜《“傅图”收藏的“项子京旧藏”古籍》,载《古今论衡》第十期,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2003,第25-38页。
(38)据《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五[宋]石延年《古松诗》项元汴记语,该卷原价“十五金”。《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第762页。
(39)见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上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第53页。文嘉只是称“唐摹”,项氏的鉴定不知何据。
(40)同注(35),万历三十八年四月九日条。
(41)[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477页。
(42)见《中国古代书画图录》第十六册,文物出版社,2000,第37页。
(43)转引自邓之诚《古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第388页。
(44)同注(17),名画题跋卷十九,第1164页。董其昌提到李成的《晴峦萧寺图》即是“以汤生重装潢而得之”,汪随后指出汤生名“汤玉林”,这件作品此前正是由“文三桥售之项子京”的。《晴峦萧寺图》原系《宋元宝绘册》第一板,董其昌曾于万历丁巳(1617)春仲携至嘉兴,汪砢玉与项又新、项圣谟在舟中得阅,次日董又携至沈商臣家(沈亦嘉兴名流,《呼桓日记》有载),1619年,汪再见到它时,面貌已发生变化,原因是董换掉了两幅元画,而代之以王蒙画作,并增王维《雪溪图》于册页之首,《晴》遂为第二板,董其昌于是命名为《唐宋元宝绘册》。汪曾指出《晴》装裱于万历戊午(1618)春,裱工为汤玉林,汪同时对该卷提出质疑。王霖先生则推断装裱时间应在万历丁巳(1617)春仲以前,也就是说董氏在携至嘉兴前即已装裱完成,而后来的改头换面,其装裱人亦是汤玉林,确为的见。此册的成因较为复杂,冯梦祯曾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项家见过《唐宋元画册》(见《快雪堂日记》),或与此册有关,不知是否后来为董氏购走,并重新组装。该册在清代归安岐所有,但面貌又发生了变化(见《墨缘汇观》名画下卷,载《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第394-397页)。前面提到的这位汤玉林不但裱画,而且鬻古,他与嘉兴的渊源可能颇深,天启辛酉(1621)春,他还向汪砢玉兜售过文征明家族的画作(见《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八,第1157页),这位汤玉林,不知是否就是汤勤的后人。
(45)谢稚柳《北行所见书画琐记》,载《文物》第8期,1963,第33页。
(46)《嘉兴市地名志》,嘉兴市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2,第43页。
(47)[明]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108册,第8-9页。
(48)同注(47)。
(49)见万木春《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的嘉兴书画世界》第四章第三节的相关论述,中国美院出版社,2008,第136-144页。
(50)[明]陈继儒《妮古录》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美术丛书》本,1997,第621页。“王野宾”即“王雅宾”,见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条:“徐润卿来,出亡友王野宾诗稿草一卷相示……。”另见《珊瑚网》名画卷十八“野宾王复元”的诗作,第1159页。
(51)同注(43)。
(52)[清]许瑶光修、吴仰贤纂光绪《嘉兴府志》卷五十一《艺术》,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第1383页。张鸣岐知名海内,见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七的记载,中华书局,1982,第404页。
(53)见[清]吴骞《阳羡名陶录》的记载,《续修四库全书》11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327页。李茂林名“养心”,蒋伯荂字“时英”。
(54)见[清]张廷济《清仪阁题跋·项墨林棐几》的记载,《中国书画全书》第11册,第733页。另,《蕉窗小牍》云:“严望云浙中巧匠,善攻木,有般尔之能,项墨林最赏重之。望云为‘天籁阁’制诸器……至今流传。……‘阎’或作‘严’。”转引自邓之诚《古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第205页。
(55)同注(35),万历三十七年九月三日条:“蒋向游项子京门下,修古琴破砚古鼎彝之属,泯然无痕,实一时绝技。”另见崇祯《嘉兴县志》卷十六,蒋少川名蒋汝成,又称“蒋回回”,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第644页。
(56)项元淇与龚勉等嘉兴官员相善。官司一事见[清]盛枫《嘉禾徵献录》卷十三的记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25册,齐鲁书社,1997,第355页。笔者在《项元汴家系再考》中已有引用,此略。
(57)方泽在《寿近谿项翁八十》谈到项家不置田产,陈继儒在《槜李太学鑑台项君墓志铭》中也有同样说法,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项家田产不多。朱国祚《沈窦项三公孝义祠记》就有项元汴长子项穆“割亩七百”的记载(崇祯《嘉兴县志》卷二十三,书目文献出版社,第951页)。万历十八年,项穆又“捐学田百亩”(光绪《嘉兴府志》卷八,台北成文出版社,第222页)。由此可见,项家的田产绝不是小数字。
(58)[清]盛百二《柚堂续笔谈》卷三,载《槜李遗书》,浙江图书馆藏秀水望云仙馆清光绪四年刻本。
(59)李维桢行状见董其昌所作《明故墨林项公墓志铭》“具京山先生行状”一语。沈思孝作传见祝廷锡《竹林八圩志》卷六《项宗义》条。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卷,据民国二十一年石印本影印,第493页。项宗义系项增钰孙,他后来曾请嘉兴沈铭彝重书沈思孝《项子京传》与陈懿典《项仲子天籁阁草引》,同上,第493页。
(60)同注(13)。
(61)现藏故宫博物院,项德新作于万历四十年癸丑(1613)的《乔岳丹霞图》跋语“癸丑孟秋,项德新写赠澹园尊亲家初度”。见《中国古代书画图录》第21册,文物出版社,2000,第217页。项笃寿的墓志铭就是收录在焦竑的《国朝献徵录》。
(62)见项元淇《少岳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43册,齐鲁书社,1997,第539页。
(63)[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万历十七年年八月二十八日,项元汴宴请屠隆,冯梦祯作陪。可知项元汴与屠隆有交谊。
(64)见笔者《项元汴家系再考》有关项穆的论述。
(65)见[清]钮琇《觚賸》卷二《吴觚》中,“沉香街”条,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11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9页。
(66)载[清]许燦衡编《梅里诗系》卷十五,嘉兴图书馆藏清道光三十年刻本。
(67)[明]周履靖《闲云稿》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9页。
(68)同注(24),第580页。
(69)[明]李培《水西集》,载《四库未收书辑刊》6辑24册,北京出版社,第70页。
(70)事见《快雪堂日记》万历十五年九月八日条。唐岐山,见崇祯《嘉兴县志》卷十四:“描写真照,颇得其神,擅一时绝技。”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第612-613页。
(71)[明]释智舷《黄叶庵诗草》,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82册,北京出版社,1998,第304页。
(72)“双树楼”是项元汴楼阁名,此图与此无涉,故名《双树楼图》似不妥。该卷款云“项子京写于双树楼”,可知双树楼只是作画地点。卷中有“双树楼阁主□□为方外交,日还笑晤,时一杂翰戏游,……(万历十年再跋)”等记语,为项元汴念及当日楼中故友(僧侣)所题。见《中国古代书画图录》第3册,第188页。
(73)同注(69),《祭墨林先生文》,第238-239页。
(74)[明]黄承玄《墨林项公暨配钱孺人墓表》,载《盟鸥堂集》卷十,上海图书馆藏明天启四年刻本。
(75)徐邦达《嘉兴项氏书画鉴藏家谱系略》,载《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第45页。
(76)[清]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四,载《中国书画全书》第12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第430页。
(77)同注(62),第551页。
(78)同注(17),卷十八,第1158页。
(79)同注(17),卷十八,第1157页。
(80)[明]罗炌修、黄承昊纂崇祯《嘉兴县志》卷八,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第336-337页。
(81)见《少岳诗集》、《冬谿集》、《冲溪先生集》等文献,项元汴时常与诸亲友于此雅集。
(82)见《中国古代书画图录》第四册,文物出版社,2000,第99页。项圣谟到陡门是为了“相地”,从诗作及题跋看,他应前往拜祭了项元汴,而他的父亲项德达也很有可能就葬在陡门。
(83)同注(17),卷十八,第1151页。他与宋旭、皇甫汸均有不错的情谊。
(84)同注(1),第755页。这段记载实际上出自李日华《紫桃轩又缀》的相关文字,有删改。
(85)见笔者《项元汴家系再考》的相关考证。
(86)同注(79)。
(87)同注(35),万历三十七年三月九日条。
(88)同注(26),书卷之二十八,《少岳山人与二上人札》,第631页。
(89)同注(88),《项元淇致定湖札》,第632页。
(90)见上海博物馆藏项圣谟《尚友图》,载《中国古代书画图录》第4册,第98页。
(91)同注(17),卷十二,第1103页。
(92)[清]盛枫《嘉禾徵献录》,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25册,齐鲁书社,1997年。
(93)卒年见李日华《秋潭禅师传》,载《恬致堂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64册,北京出版社,1998,第599页。
(94)见张鲁全主编《故宫藏明清名人书札墨迹选》,荣宝斋出版社,1993,第92页。
(95)见笔者《项元汴年谱》,未刊稿。
(96)叶梅《嘉兴项氏家藏法书统计补正》,载《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66页。这与她在博士论文中的统计是相同的。
(97)见张岱《陶庵梦忆·仲叔古董》条,中华书局,2007,第77页。
(98)同注(62),第534页。
(99)同注(65),第19页。
(100)[明]彭年《隆池山樵诗集》,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46册,齐鲁书社,1997,第135页。
(101)见《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第三册,上海图书馆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第138-139页。
(102)同注(92),第357页。
(103)《宋吴允文自书诗卷》后丰坊跋曰:“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四日,南禹世史丰道生借观于墨林项子京天籁阁因题。”见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书法一下册,文物出版社,1999,第610页。
(104)见吴升《大观录》元贤四大家名画卷十七,周天球隆庆辛未《黄大痴富春山居图卷》的观款。载《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第485页。徐邦达认为该卷可靠,见《古书画伪讹考辨》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第69页。
(105)见汪砢玉《珊瑚网》法书题跋卷十八,国朝名公词翰卷吴孺子跋“题项子京楼”。吴孺子,字少君,号玄铁,又号“破瓢道人”。另见《槜李诗系》第346页及《嘉禾徵献录》第726页的记载。
(106)法常卷见《石渠宝笈初编》下,《北山录》见袁克文《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民国影印本。
(107)见周履靖《梅坞遗琼》卷六周天球跋《黄庭经》(周履靖藏)。载《夷门广牍》卷八十八,第三十三册,上海涵芬楼《景印元明善本丛书》本。
(108)《九畹遗容》、《春谷嘤翔》均见《夷门广牍》第十四册,上海涵芬楼《景印元明善本丛书》本。
(109)见丁羲元《鹊华秋色图再考》,载《国宝鉴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第363页。《初广千文》见《夷门广牍》卷十,第四册。
(110)同注(69),《疑雨斋诗集序》,第193页。
(111)见谭贞墨《明太仆少卿李九疑先生行状》,载《恬致堂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64册,北京出版社,第22页。
(112)同注(13)。
(113)见[日]铃木敬《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第三册,东京大学出版社,第132页。
(114)同注(80)。
(115)见[清]胡昌基《续槜李诗系》卷三十三“金德舆”(金鄂严)的相关记载。嘉兴图书馆藏清宣统三年刻本。
(116)[明]陈继儒《槜李太学鑑台项君墓志铭》,载《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十三,湖北省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117)在项德明手上卖掉的如: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卖与项玄度)、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米元晖《潇湘白云图》(卖与董其昌)、《卢鸿草堂十志图》(卖与京口张修羽,见《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五十一的记载)、赵大年《江乡雪意图》(托嘉兴盛龙生为中介,卖与李日华,见《六研斋三笔》)……。但陈继儒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仍讲他“虽贫,敢不作古人金汤”。见《槜李太学鑑台项君墓志铭》,这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
(118)同注(77),第651页。
(119)[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四《项子京画卷跋》,《四部丛刊》本。程穆倩是安徽黄山人,别号垢道人,著有《垢道人集》,与一时名贤如冒襄、吴山涛、宋曹、龚贤、戴本孝等皆有往来。
(120)同注(74)。项元汴的去世可能较为突然,原因或许与家庭发生的变故有关,否则不会有“家衅陡作”一说,陈麦青先生以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郑心材《郑京兆文集》卷七《祭姻家项贞玄先生文》中的部分内容,认为其中“隐约触及项氏家族在德纯一代时的矛盾纠纷”。见《关于项元汴之家世与其它》第三节,载《随兴居谈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99页。
(121)顾国华《文坛杂忆》初编沈侗廔《文革期间盗墓》曾载:“文革祸及泉壤,……西门发掘一明代古墓,棺木完好,其尸面目如生,微髯,官服未腐,有云系项元汴墓,墓中遗物皆被盗走。又……明朱国祚及清初朱彝尊等墓,亦于是时被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12页。陆耀华在《浙江嘉兴明项氏墓》一文提到,项元汴尸体亦于发掘前被盗走,载《文物》,1982年第8期,第40页。
(122)见陆耀华《浙江嘉兴明项氏墓》考古报告,载《文物》,1982,第40页。
(123)见《古禾杂识》吴受福跋,“项姓凋丧殆尽,仅有一二不肖者,往往侵毁襄毅公赐茔,始则盗伐宰术,继则货其翁仲、石羊、石马、石檯诸物;凡可易钱者,窃卖罄尽。傍茔祠宇久毁,门前石狮,亦售予人矣。……可胜嘅载!”据嘉兴图书馆藏民国廿五年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