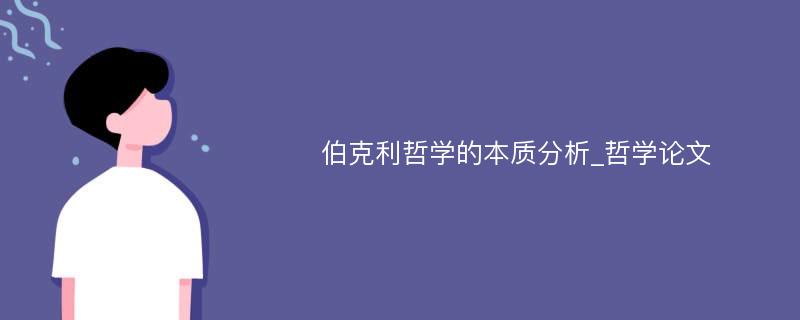
贝克莱哲学性质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克论文,性质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是西欧近代哲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的哲学代表着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个转折点。在他之前,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基本上保持着唯物主义的性质。从贝克莱开始,经验主义就转向了唯心主义。正因为如此,哲学史上往往把贝克莱称为西方哲学史中近代唯心主义的一个创始人。然而他的唯心主义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呢?当前我国的哲学史界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贝克莱是西欧近代主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这种定性可以说是承袭了前苏联五十年代的哲学史教科书中的观点。然而,笔者在学习研究中发现,贝克莱哲学性质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应当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哲学史界把贝克莱的哲学性质,误解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重要依据,是他的著名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与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的有关论述相关。我们具体分析贝克莱的命题本意,及列宁在书中有关论述的本来意图,以此来对贝克莱哲学性质加以澄清。
首先,现在通用西方哲学史教材中认为。贝克莱只承认观念的唯一存在,这样,观念也就成了知识的唯一对象。然后把“观念”与“存在”等同起来,这样,“观念的存在,就在于被感知”(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39页。)演变成了“存在就是被感知”。
这是否合乎贝克莱的本意呢?笔者是否定的。因为,贝克莱说过,“我认为,观念,精神和关系,在它们各自的种类中,都是人类知识的对象和话题;观念一词的意义不应当不适当地扩大到指我们所知道的或所理会到的任何东西。”(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65页。)在他的论述中,只是强调观念的存在在于被感知,而不是泛泛地讲什么“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谈观念的真意,在于强调隐藏在观念背后的,创造观念、支配观念的上帝。他认为,能感知事物(观念)的心灵,绝不仅仅是我的心灵,也不限于其他人的心灵,而是“一切心灵”,特别是那个永恒的,崇高的“无限的心灵”,即上帝。因此,如果有某事物没有被我所感知,它可能被别人所感知,如果不被一切人所感知,那一定被上帝这个“无限的心灵”所感知,存在于这个“无限的心灵”之中。这样,事物或观念可以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可以不存在于“我”的心灵中,可以不随“我”感知与否而忽生忽灭;但它最终要存在于无限心灵之中,被无限心灵所感知。
贝克莱模仿了托马斯,通过上帝的创造物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办法,用上帝赋予人类的、为人类“明确而直接认识”的观念,去“推知”仁慈睿智的上帝的存在。他说:“在一切我们视线所得到的任何处所,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感知神灵的明显标志;我们看到、听到、触到或无论从何种方法由感官感知到的每一种东西,都是上帝的权力的记号或结果。”(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39页。)毫无疑问,上帝确是存在的。贝克莱哲学议论的宗旨就是去歌颂上帝,他的整个哲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以从感觉出发,用唯心主义感觉论来论证上帝。所以,用贝克莱只承认观念的唯一存在来给他的哲学下个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未免太简单化了。罗素也曾经说过:“不管怎样,总之,贝克莱认为存在不被感知的东西这件事照逻辑讲是可能的,因为他认为某些实在的东西,即精神实体,是不被感知的。”(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191页。)
其次,人们常引用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的有关论述,来证明贝克莱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列宁这样说的,“由此可见,不能把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解为:似乎他忽视个人的知觉和集体的知觉的区别。恰恰相反,他企图靠这个区别来确立实在性的标准。贝克莱从神对人心的作用中引出‘观念’,这样他就接近了客观唯心主义……。”(注:《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6页。)笔者认为,准确理解列宁的原意,就需要了解哲学史的实际,以及列宁论述贝克莱哲学的目的,切不可断章取义。
在西欧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中,贝克莱对后世哲学的影响,并不是贝克莱哲学思想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贝克莱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休漠实现的。休漠用贝克莱的剑,即“存在就是被感知”的思想,砍掉了贝克莱的头颅,即上帝。这样,在休漠之后,贝克莱的本体论中多元的精神,就被看作是他那“独断唯心主义”(康德语)中的独断成份而被抛弃了。在贝克莱哲学中去掉它的本体论独断成份之后,剩下的是什么东西呢?有两种可能,一是不可知论,一是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与唯我论之间的区别乃是本体论上的区别。正是这种本体论上的不同,使唯我论显得比不可知论更接近于贝克莱的哲学。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说贝克莱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或唯我论的渊源。马赫所接受的贝克莱哲学是经过休漠批判之后的贝克莱哲学。马赫接受的是他的认识论而不是他的本体论。由于此,马赫不承认自己的哲学是贝克莱主义。
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针对马赫主义及其变种的战斗性著作。列宁论述贝克莱是为了揭示马赫认识论中的唯心主义,列宁著作的这一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根本不需要也根本没有打算要对贝克莱的哲学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注:傅有德《贝克莱哲学研究》(序一,陈修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页。)很显然,列宁所说的“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指的是贝克莱哲学中被马赫所接受的那个部分,即没有上帝的贝克莱认识论。也就是说,贝克莱的认识论一旦与他的本体论割裂开来,就成为主观唯心主义,而这也正好就是贝克莱对后世哲学的实际影响。
列宁指出,不能认为贝克莱忽视个人知觉与集体知觉之间的区别;又指出,贝克莱的上帝使他接近了客观唯心主义。这就说明列宁在提醒读者,当读到贝克莱本人的哲学时,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本来意义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更不能把列宁的意思理解为贝克莱哲学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加上客观唯心主义,或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达到了客观唯心主义。
在观念来源问题上,贝克莱明确指出:观念起源于上帝。贝克莱认为,感知者,即心灵、自我、精神不仅仅是人类的,而且主要的不是人类的,因为人类的心灵、自我、精神毕竟是有限的、特殊的,它既不能感知那无数的观念,更不能永恒地感知观念,如果观念依赖于这样的感知者,岂不是说,观念以及由观念构成的万物就会随感知者的间断性忽生忽灭了吗?因此,要保证世界的永恒性,只能承认有一个我们人类的心灵所无法比拟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永恒的心灵,这个心灵就是上帝。一切观念盖源于它,这个上帝是观念、万物的实体或基质。在贝克莱那里,人的心灵、精神并不是观念以及由它构成的万物的本原,因为人类的精神与上帝相比是次等的,它是“再造的精神”,它本身并不能创造观念,只能感知观念。就观念的起源来讲,“不是由心灵自己从内部产生的,而是由异入感知它们的那个心灵的精神印入的。”(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66页。)
贝克莱在谈到观念的起源问题时,明确指出了三点:一种是由实在印入感官的,一种是由心灵的各种情感和作用产生的,第三种是在记忆和想象的帮助下形成的。其中“造物主在我们感官上所印下的观念,叫做真实的事物。”(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53页。)没有上帝,当然也就没有观念,也就没有观念所构成的世界。这种理论不过是“天赋观念论”和上帝创世说的变种罢了。
贝克莱的著作中,常把客观事物与人类的感觉混为一淡,把人类通过感觉所了解到的事物归结为感觉本身,从而证明人们的认识对象不能离开感知者而独立存在。他企图用这种论证方式取消房屋、山岳、河流等物质现象的实在性,进而达到消灭唯物论、无神论的目的。在贝克莱看来,观念产生的最后原因是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一切事物都依存于他”,“他创造一切”。(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70页。)
贝克莱认为,上帝为自然界立法。贝克莱承认有自然法则,人们正是依据这些法则来规范自己的行动,趋乐避苦,否则会“陷入混乱之中”。他认为自然法则实际上是人们感知到的观念之间有秩序的互相联结和融合,以致一定的观念常会伴随着另一些观念而出现;这种联结和秩序并不表明事物或观念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而“只是表示一个记号或符号同用符号标志的事物的关系。”(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60页。)他举例说,我看见的火,并不是在我靠近它时感到疼痛的原因;我看到的太阳,也并不是使我感到热的原因,而只是对我发生警告的标记或符号,人们正是根据这种符合的联接才发现“自然法则”并用来规范自己的行动。
那么,自然法则或标记、符号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只能来自上帝。上帝建立了自然法则,才使宇宙间万事万物处于“和谐的有规律”的状态,才使它们相互间有了奇妙的联系,仁慈的上帝创造了自然法则,为人类造福,使人们合乎法则地安排生活。这些符号或法则就好像一种“自然的语言”,上帝用它们来向人们发出“通知”和“预报”。因此,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研究并力求了解造物主的这种语言……而不是借有形体的原因来妄图解释事物。”(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60页。)人们对自然法则认识愈深,就愈能领会和证明上帝的明智、仁慈和伟大。他声称自己是主张研究自然及其历史的,是主张观察和实验的,“不过这些观察和实验所以能有利于人类,所以能使我们得到普遍的结论,那并不是各种事物的固有的性质(或关系)的结果,乃是上帝在管理世界时所本的仁慈心肠的结果。”(注: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69页。)贝克莱这些神谕式的语言,充分说明了他的确是“英国哲学中神秘唯心主义的代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9页。)
列宁针对贝克莱企图调和经验与上帝、科学与宗教的做法,深刻地揭露说,“让我们把外部世界看作是神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感觉组合’吧!承认这一点吧!不要在意识之外,在人之外去探求这些感觉的‘基础’吧!这样我将在我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内承认全部自然科学,承认他的结论的全部意义和可靠性。为了我的结论有利于‘和平和宗教’,我需要的正是这个范围,而且只是这个范围,这就是贝克莱的思想。”(注:《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4页。)
贝克莱的这种上帝为自然立法的思想能算作主观唯心主义的吗?
研究贝克莱的哲学,必须抓住他的各种议论的内在联系;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在他的哲学议论的宗旨上,来把握其哲学的性质。在贝克莱的哲学中,认识的主体是人类,它并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人在认识过程中并不创造世界,只能是通过对创造主的创造物的认识达到对造物主的真诚信仰。人类的认识只有达到与上帝的意志的合一,才能进入到真理的境界。正是这些想法,促使他在晚年又到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中去寻找出路。贝克莱在他的《人类知识原理》一书的结尾,把他的实践和理论追求作了一个概括:“在我们的研究中应占首要位置的,乃是对于上帝和我们天职的研究,我这些辛劳的主要旨趣和目的就是要提倡这一点,假如我不能借我所说的话来激动我的读者对于上帝的存在有一种虔诚的意识,那我认为这些辛劳是完全无用和无结果的。”他要求人们必须正确地理解上帝,因为“崇敬并信奉造福人类的福音真理,认识和实行这些真理,乃是人性的最高完善。”(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60页。)由此可见,贝克莱是把上帝的实在作为它的哲学体系的核心的。
笔者认为,贝克莱的哲学思想是否可以作这样简单的概括:上帝创造了无数能构成现实世界的感觉、观念,又把这些感觉、观念印在人们的各种感官上,让人们去感知它。上帝以自己无所不在的才能支持它们的存在,人类也以上帝赋予自己的方法支持和证明这些观念的存在,从而就勾通了人与上帝的联系,使人类获得了知识,完善了人性。上帝既是贝克莱哲学的出发点,又是它的归宿。
笔者认为,贝克莱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这样定性,更加客观地认识了贝克莱哲学的本质;同时,对正确分析与认识贝克莱时代的特点也将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