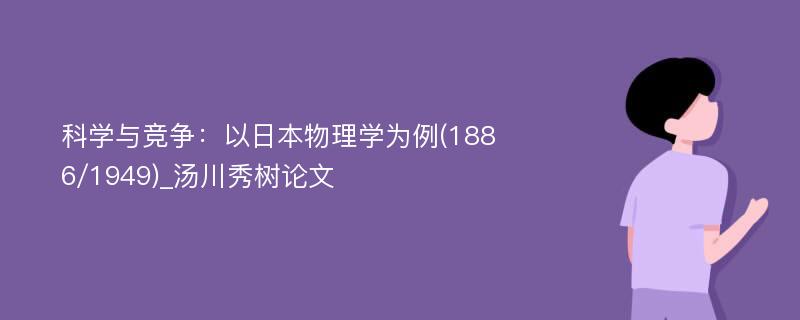
科学与竞争:以日本物理学为例(1886—194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为例论文,物理学论文,竞争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1947年,应战争部长的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将负责科学技术改革的科学顾问团派往日本。顾问团此行目的是希望盟军最高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官员对日本的科学计划有一个适当估计, 这个计划由日本科学家团体以促进日本国内科学研究的民主化为名而提出。在顾问团1948年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日本研究人员的奇特动机令美国科学家们感到不安:
大学里的很多研究,其内容都深奥晦涩。相比数学分析或者应用数学,数学家们更喜欢数论这一类的研究。造就一个文化阶层,维护日本的尊严,证明其文化优越于世界上其它文化,这似乎是很多大学教研人员心目中最主要的动机。①
日本科学家在抽象理论的研究上花大力气而轻视实用科学,想以此证明自己国家的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越,这一点让科学顾问团感到奇怪。
科学史家已经指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家目标——“富国强兵”或多或少都影响了日本科学研究的特点,并使国家的研究方向指向工业和军事上的应用。但是,如果仔细审视日本科学家的实际科研活动,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好几个反例,说明他们在研究中并未遵从这一国家目标:日本的第一、第二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是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在战前就已经开始着手的研究工作与工业应用并无多大关系;20世纪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日本建立公共卫生协会时,他们就发现相比于临床应用,日本的医生更热衷于理论研究。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详细分析日本物理学家学术活动的几个方面,并通过这种分析来说明战前的日本科学家如何把研究兴趣转向了纯科学研究。
一 长冈半太郎(Nagaoka Hantaro)的担忧
山川健次郎(Yamakawa Kenjiro,1854—1931),田中馆爱橘(Tanakadate Aikitsu,1856—1952),长冈半太郎(1865—1950),这三位明治早期著名物理学家的经历告诉我们,日本的第一代物理学家都是在江户时代封建儒教传统影响下接受的启蒙教育,然后转向现代物理学的教育和研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决定抛弃传统文化,投入完全陌生的新领域时,都难免会产生疑问、会犹豫不决。长冈半太郎的故事几乎众所周知。
在进入东京大学物理系之前,长冈半太郎研究了古代中国的科学史,目的是要弄清东亚人是否也有能力在科学上做出原创性贡献。对于一个生活在明治时代早期的年轻的中学毕业生来说,他即将要投身于其中的自然科学是彻头彻尾的西方的东西。如果他(作为东亚人)注定无法完成原创性工作,长冈半太郎不会愿意把生命耗费在此。
但是仔细研究中国的经典著作之后,长冈半太郎确信亚洲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有天赋的。古代的中国人研究过北极光,精确记录了天体的运动,还发明了指南针,这些都使得长冈半太郎自信自己也能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有所突破。此外,长冈半太郎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是衡量文化的标准,东西方可以共用;或者是一组竞赛规则,亚洲人和欧洲人在同一竞技场上竞争。很明显,长冈半太郎把中国人视为共同拥有东亚传统的文化同胞,而非西方人那样的竞争对手。[板倉聖宣、木村东作、八木江里1973,页39—44]
在给他的学长田中馆爱橘的一封信中,长冈半太郎要与西方人(或者确切的说是白种人)一比高低的想法表露无疑,当时的田中馆爱橘正在欧洲求学(1888年6月7日):
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有广阔的视野、敏锐的判断力和对事物的透彻理解,不能屈服,不能有一丝的松懈。那些看似专心工作,实则心不在焉,任何小事情都会让他们停下来去看、去听、去议论,甚至跑出去买东西的人,不要让他们在我们的工作间打扰我们的工作。没有理由让白人在每个方面都如此超前,如你所说,我希望我们能在10或20年之内打败那些白人:我才不想在地狱里用望远镜去看我们后代的胜利。②
田中馆爱橘和长冈半太郎都相信亚洲人在道德操守上胜于西方人,尽管他们的国家在物质上仍然贫弱。他们互相鼓励,决心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他们真的能够在知识上击败“白人”。
好战的情绪不仅在年轻的学生中、也在明治中期的知识分子圈子中弥漫开来,曾经受益于西方教育制度的政治领导人也深受感染。1885年,文部大臣森有礼这样解释他为何要在师范院校中引入军事体操:
我引入军事体操不仅仅是为国家紧急备战。我们无法精确告知战争会何时爆发,这只能指望专家。但是战争决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而是关乎我们的日常行为。国际贸易是工业和商业的战争;我们要凭知识上的优越取胜;通过我们的发展和努力来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也是一种战争。如果你心安理得日本永远受别国领导,那么无需为这些战争费神。这个国家会日复一日地堕落下去,直至瘫软无力、无可救药。日本的少年能接受吗?不,不能……③
森有礼认为未来的教师应该关注与其他国家的在知识、文化层面上的竞争。
一位日本博物学家甚至试图说服另一位东亚知识分子赞同对西方人采取斗争的态度。1897年,当时在伦敦工作的博物学家南方熊楠(Minakata Kumagusu)告诉孙逸仙,亚洲人有望把西方人驱逐出去。南方熊楠在大英博物馆里的一个房间里大声地说这些话让孙逸仙不免有些担心。南方后来回忆说孙逸仙听了他的话极为震恐④。南方负笈海外,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希望亚洲人最终能够把这些西方的野蛮人从自己的国家驱赶出去[神坂次郎1987,页116]。而孙逸仙追求的目标则有点不同。
如果科学是竞争,其规则又形成于欧洲,那么,这一仗,就很有可能是西方的科学家打得比日本科学家好。要参与竞争,成为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日本科学家们就必须掌握西方的规则和策略。第一代日本科学家们狂热地学习欧洲语言,前面所引的长冈半太郎的信就都是用英语写成。文化教育部部长森有礼曾建议日本政府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但是要想掌握技巧赢得胜利,只学习语言恐怕是不够的,为了深入理解西方的文化,一些人开始信仰基督教。另外一些人则建议日本男人娶白种女人为妻,这样他们的后代就能比其父辈更智慧、更强壮。
但是西方科学家却并未太在意日本人所投入的热情和精力。长冈半太郎和田中馆爱橘都发现他们的研究没有引起西方科学家的注意。长冈半太郎最著名的工作可能是他的土星型原子模型(Saturnian atomic model),这个系统包括“大量相同质量的以等角度间隔排在圆周内的粒子,这些粒子之间的斥力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以及“以相同平方反比定律吸引着周围其他粒子的一个大质量粒子”[Nagaoka 1904,pp.445—455]。在1904年的《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上,长冈半太郎公布了他的模型。7年以后,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公布了他更为著名的原子模型,其核心理论与长冈半太郎的极为相似。但是在卢瑟福关于他原子模型的首次报告中对长冈半太郎却只字未提。
1911年,在给长冈半太郎的信中(1911年3月20日), 卢瑟福说他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土星模型:“你将会看到我所采纳的原子模型结构与你在几年前的一篇论文里提到的结构有些相似。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查阅到你的文章,但是我记得你确实写过这方面的文章。”⑤ 也是这一年,卢瑟福在他《哲学杂志》上的专论里第一次提到了长冈半太郎的早期工作[Rutherford 1911,pp.669—688]。直到40年以后,在庆祝日本获得第一个诺贝尔奖的时候,长冈半太郎还很奇怪为什么在论文发表之后长达7年的时间里,卢瑟福都没有看到他关于土星模型的专论呢? 实际上,剑桥附近的许多科学家都没有对长冈半太郎模型给予重视。1911年3月11 日的信里,布拉格(W.H.Bragg 1862—1942)曾要卢瑟福查阅长冈半太郎的论文,但是卢瑟福认为不过是一个“小日本”的工作,忽略掉了⑥。
二 量子力学:新的规则
知识的较量并没有因为日本在1904—1905年与俄国的较量中取胜而终止。虽然这场胜利展示了日本在军事和经济上的竞争力,但是日本科学家的目的远不止此。在癌研究会(1908年)的落成典礼上,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大学校长青山胤通(Aoyama Tanemichi)认为,既然能够胜俄国,那就不用再对欧洲同行的邀请感到羞怯,日本的医学家们已经决定要参加国际癌症会议:
今天,我们不要指望仅仅依靠军事实力或者经济实力就能得到别的国家的尊重,只有当这个国家对文化的进步有较大贡献,她才有资格得到国际上的尊重和支持。我想,如果在这个癌症研究会里,我们国家的医学家们能够取得比欧洲的研究者们更多、更好的成绩,这将比我们投入几十亿日圆和上十万人力更能赢得支持和尊重。[青山胤通1908,页275—279]
青山胤通不像一心梦想打败“白人”的长冈半太郎那样好战,取而代之的是,青山胤通更希望得到西方同行的尊重。对他和他的同胞来说,科学是为了赢得国际尊重的文化之战。因此,当癌症研究在日本开始后,肺结核和脚气病,这两个大拦路虎在日本的医生看来仍然是对公众健康的可怕威胁。然而,为了赢得国际尊重,日本的医学家心甘情愿为此呕心沥血。
1910年代,日本的科学家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地谈到知识战争。1915年,曾经相信过亚洲人道德高于欧洲人的田中馆爱橘在上议院中坦言正是那些在自然科学领域为真理而战的西方的先驱们促进了西方文明,他警告说我们不应该把西方文明仅仅理解为唯物论的或者机械论的⑦。
一战以后,日本知识分子不再像以前那样毫无顾忌地彰显他们对文化竞争的狂热。他们开始很放心自己的文化在世界上的威望,毕竟两场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证明,日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地位都是与那些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的,尽管在文化上还不是如此。
同时,自然科学在欧洲为后来者提供了机会。1925—1926年,机械量子力学的出现为研究物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而且改变了竞赛规则。受过如力学、电磁学、热力学等传统训练的物理学家们不得不学习新的规则以跟上当前发展。新的研究阵线的领军人物有许多都是出生在世纪之交。年轻的日本物理学家们通过阅读登载在外国科学期刊上的论文学习量子力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和欧洲同行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1928年,两名理化学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分别在日本和欧洲做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菊池正士(Kikuchi Seishi 1902—1974)成功地记录了高能量电子通过云母晶体的折射图案,这就是后来的“菊池正士图案”(Kikuchi patterns)[Kikuchi1928,pp.83—96]。按照量子力学的推论,晶体对电子的折射是电子具有波的特征的一个重要证据。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在1930年出版的量子力学初级读本里提到了菊池正士的工作[Heisenberg 1930,p.57]。1937年,G.P.汤姆逊凭借一项与菊池正士类似的发现,和C.J.戴维森(C.J.Davisson,1881—1958)共同获得诺贝尔奖,后者在实验中采用了低能量的电子束。汤姆逊完成他的论文[Thomson and Reid 1927,p.890][Thomson 1927,p.802]在菊池正士之前不过几个月。
也是在这一年,当时工作于哥本哈根的日本物理学家仁科芳雄(Nishina Yoshio,1890—1951)获得了以其姓氏命名的用相对论处理散射的公式,就是后来的“克莱因—仁科公式”[Klein; Nishina 1929,pp.853—868]。1928年底回到日本以后,仁科芳雄开始指导他年轻的同事们如何用新的方法从事物理研究。
三 介子理论
由量子力学引发的这场革命,其产物之一就是物理学领域出现了一项新职业,即理论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之前,物理学家著名的理论工作都集中在实验领域内。但是量子力学出现之后,实验物理学家们都发现继续以前的实验研究是跟不上理论发展的。理论研究对数学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迫切需要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新专业。
纯理论研究的出现对日本的年轻物理学家来说意味着另一个机会。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物理学、数学知识,掌握了欧洲的主要语言,又怀有对新理论的热情,他们就能从事理论研究。当然,为了跟上理论研究的发展潮流,他们必须通览外国科学期刊上的专题论文。不过,他们不用去购置那些主要从欧洲和美国进口的昂贵的实验设备。
20世纪20年代,当朝永振一郎(Tomonaga Sin-itiro,1906—1979)和汤川秀树(Yukawa Hideki,1907—1981)开始自学量子力学的时候, 他们都还只是京都帝国大学尚未毕业的学生,他们不能指望能有老师指导他们学习量子力学。他们不得不花大量的功夫去译解有关量子力学的新报道,但是他们乐此不疲,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走进了物理学研究的前沿阵地。
但是年轻的学子们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地怀疑他们对游戏规则的理解是否正确。外国学者的演讲对于学习欧洲科学家如何从事物理学研究是难得的机会。于是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怀着极大兴趣听取了海森堡和狄拉克(P.A.M.Dirac,1902—1984)1929年在京都大学的演讲,还有长冈半太郎那场极受欢迎的演讲,后者肯定了两名欧洲物理学家在他们还不到三十岁时就做出的成就,责备日本科学家同行们只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却不能超越。1931年,仁科芳雄也在京都做了一场报告,这场报告使得京都的年轻学子们都确信他们从事物理学研究的路走对了。
汤川秀树在1934年提出介子理论之前,还没有在海外求学、与外国学者交流的经验。他是大阪帝国大学(Osaka Imperial University )一个新建成的系里的青年讲师,他和他的助手们都仅是理论物理学家。这种知识上的离群状态很可能促使了汤川秀树去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中子和质子之间的力。1932年以来,物理学家已经发现核子包括质子和中子,但是他们还不能对是什么力将这些粒子结合起来给出一个比较能说得过去的解释。一些人坚持,微中子和电子这种粒子的存在经过了实验的证明,它们平衡了质子和中子之间的力并且将二者结合起来,但是他们却不能合理解释这种力的特征。汤川秀树则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平衡质子和中子所需要的力来确定起到调节作用的粒子的特征。因此他预言了一种新的平衡粒子的存在,这就是“介子”[Yukawa 1935,pp.48—57]。
尽管汤川秀树没有违反新的游戏规则,但介子理论在他的许多同行们看来还是太标新立异了。只有时任大阪帝国大学物理系主任的菊池正士和仁科芳雄鼓励他继续追踪物理学的前沿。1937年,玻尔(Niels Bohr,1885—1962)访日,当玻尔结束在理化学研究所(RIKEN)的演讲之后, 汤川秀树呈上自己有关介子理论的论文单印本,不料玻尔只是不屑地说道:“你似乎很喜欢新粒子啊。”看来那个时候的物理学界还不习惯有人提出新粒子。
但是1937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物理学家都报道在宇宙射线中发现了新的粒子,并确定这就是汤川秀树曾预言过的粒子⑧。汤川秀树曾提出过的核子间力的新解释突然间被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们视为大有前途。理论物理学家们涌进“介子产业”,尽力把这个理论打造得更加精致完美。实验物理学家们试图确定介子的质量、生命周期以及其他物理特征。1937—1939年在莱比锡与海森堡共事期间,朝永振一郎说:“汤川秀树”和“介子”占据了他老师的大脑。与以前的同班同学相比,自己能在国外学习却没有出色的成就,这一点经常让朝永振一郎感到沮丧。1939年,汤川秀树应邀参加第八届索尔韦研讨会,他才第一次离开日本,参观了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中心。
1940年的诺贝尔奖,有两名物理学家提名汤川秀树:一个是荷兰化学家D.科斯特(Dirk Coster,1889—1950),他曾经和仁科芳雄在哥本哈根共事过一段时间;另一位就是长冈半太郎。长冈半太郎多年来都受诺贝尔奖物理委员会之邀提名候选人,因此他有机会在提名汤川秀树之前就推荐一些自己的同胞。长冈半太郎很清楚地知道菊池正士和仁科芳雄的工作,但是在长冈半太郎早先的几封推荐信中对他俩都只字不提。尽管长冈半太郎长久以来都希望日本能够在科学上胜过西方,但是他从不降低对国人在理论贡献上的标准。他不能接受一场表面上的胜利。
只有汤川秀树所享有的国际声誉能够最终说服长冈半太郎推荐他。1913年,在第一封推荐信中,长冈半太郎悲痛地写到:
我非常遗憾没有写下我的国人的名字。日本的科学研究还处于其幼年时期,但是正如大量的调查研究都必须忍受枯燥的常规工作一样,很有可能在下一代科学家中,一定会有人获得诺贝尔奖。
他的预言没有错。大约25年之后,他在他的下一代科学家中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在汤川秀树的推荐信中,长冈半太郎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这是我第一次满怀信心地推荐我的同胞作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正如1888年给田中馆爱橘的信中所期望的那样,他果然亲眼看到他的同胞在科学上取得了压倒西方人的成就。
四 物理学家与战争
汤川秀树原计划要去参加的索尔韦研讨会因1939年欧洲战争的爆发而取消了。这场战争也使得朝永振一郎不能继续留在德国。因为1941年12月7 日珍珠港事件之后,这场战争明显地影响到了日本物理学家的活动。
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的重要物理学家在理化学研究所每半年召开一次研讨会,讨论科学家在战时的责任。仁科芳雄大力鼓吹理论研究的价值,认为不应放松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努力,这样才不会在战争结束之后因为基础研究工作被国外同行超越而丢脸。而菊池正士则被同行间民族危机感的缺失所激怒,他坚持当国家处于战争期间时,科学家应该暂时放弃学术上的目标,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工作。在这种爱国情绪的引导下,菊池正士在战争期间成为了一名海军工程师,改进了雷达系统。
仁科芳雄也卷入了战时研究。二战期间,他领导了几项检测能否将核力用于军事目的的工程。京都的物理学家,包括汤川秀树,也独自开始了对核力的研究。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菊池正士除外,对防御系统的研究并无多大热情。至少在战争的前半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很怀疑日本能否在战争结束前造出原子弹,因此也没有为达到工程目的而十分努力。而且,从战争前期开始,就有几个研究课题一直牵扯着这些科学家的精力、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
经过越来越多物理学家的彻底审查,汤川秀树尚还不太成熟的介子理论被认为容易从多方面受到攻击:它不能适当解释质子和中子之间力的属性;宇宙射线中发现的粒子,其特征也不能满足核力之间的理论需求。即便在战争期间,解决这些问题对大部分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来说也是意义重大。1941年,坂田昌一(Sakata Shoichi,1911—1970)、井上健(Inoue Takeshi)和谷川安孝(Tanikawa Yasutaka)修改了最初的介子理论,提出了“双介子理论”[Sakata; Inoue 1946,pp.143—149][Tanikawa,1947,pp.220—221],他们的改动使得介子理论重又焕发出光彩,在理论界引起轰动。
实验物理学家们忙着自己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的主要科学家们,比如仁科芳雄,就一直致力于有着空前经济规模和物理学意义的事业:回旋加速器的建构和使用。即便是战争期间,理化学研究所、京都帝国大学、大阪帝国大学,三个物理学研究中心的实验家们仍然继续着他们在核物理上的研究。
五 原子弹
对日本物理学家以及其他大部分民众来说,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是个天大的震惊。他们原先估计即使美国也不能在战争结束之前造出原子弹的。日本科学家不能明确回答军方关于原子弹特征的询问。军队于是要求参加防御系统研究的科学家们去调查广岛和长崎,以弄清原子弹的属性特征。
在前往广岛调查原子弹之前,仁科芳雄给他的年轻同事们写了一封信:“如果杜鲁门没有撒谎,那么现在便是参加仁科工程(仁科芳雄的核力工程)的人切腹自尽的时候了。……到达总参谋部(the general headquarter )的报告有力证实了杜鲁门的话。”⑨ 直到1943年底,仁科芳雄对原子弹工程都还不是很热情,但是他的态度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开始转变。随着日本丢掉一个又一个战役,他开始意识到这项工程的胜利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虽然他仍然怀疑这项工程能否成功。
为一项没有希望的工程投入大量金钱和资源,这时常让仁科芳雄感到不安。然而这并未让他停止为这项事业继续努力。除了对国家的责任感,还有其他原因使他坚持这项工程。他可以使用军队提供的经费和其他资源从事他在物理化学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研究。当美国物理学家围绕着制造原子弹的目的改进他们的回旋加速器时,仁科芳雄几乎是反其道而行。此外,通过参加军事研究的工程,年轻又有潜质的物理学家就能够避开征兵。这样一来,仁科芳雄就为战后科学的促进保证了人力资源。
广岛原子弹事件后,仁科芳雄感到责任重大,他意识到美国人已经超越了他的工作。他可能还会因为他没有对这项工程投入足够的热情、因为他曾向军队报告说美国在战争结束前不会造出原子弹、因为他使用过军队的机会和资源来从事自己的理论科学研究等等而怀有负罪感。在这件事之前,甚至日本一些高级小学的学生们都相信这些聪明能干的日本科学家在研制一种新型炸弹,能够最终扭转日益恶化的局面。因此,仁科芳雄决定用切腹的方式来履行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同样有意思、甚至更有趣的是这封信中的下一句话:“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如果美国和英国成功地研制出了原子弹),那么美国和英国便击败了物理化学研究所49号楼(从事核力研究的大楼)里的科学家,这表明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在人格上也超越了49号楼里的科学家。”[Ito 2002,p.82]仁科芳雄意识到,在这场发展核力的国际竞争中,他已经败给了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虽然研制炸弹的事业是工程和技术性质的,许多科学家、包括工程师,也都这样认为。但是在仁科芳雄看来,科学竞争上的胜利则意味着人格上的优越。
六 战后的岁月
从广岛回来之后,仁科芳雄突然发生大的改变。看到军官们如此严肃地考虑投降的事情,仁科芳雄意识到他将很快能够像战前那样做一名“理论科学家”。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要切腹自杀。甚至菊池正士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一旦战争结束,物理学家就应该回去从事理论研究。
利用军队的项目,仁科芳雄可以保护年轻的物理学家,使得他们能够在战后继续从事并促进科学研究。虽然日本急迫地需要食物、燃料和其他供应品,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他们在核物理和宇宙射线物理学方面的研究。不过日本人要从事理论科学研究的倾向却让美国人感到疑惑,科学顾问团在1947年写到:
在大学毕业生和研究人员当中,至少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相比于应用科学研究,对理论科学研究的强调似乎有些过分。这种强调可以被合理地怀疑是因为考虑到日本当前经济令人绝望的状态以及恢复经济的迫切需要。日本在这个阶段对理论研究的适当强调与美国是正好相反的,在美国可能会被认为过分强调了科学对工业的应用。除了理论科学领域里一些更为浪漫的研究,日本在生产方式,产品质量控制、设计和结构改进,安全维护的方法,以及对机器、电路和仪器有效使用的事前检测等等方面,看来需要更多的学习和指导。⑩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日本都有许多物理学家在理论科学领域继续着他们的“浪漫”的研究,而不去理会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到底需要他们做什么。他们的努力渐渐导致了他们国际声誉的提升。1947—1948年,实验家们报道了证实“双介子理论”的发现,该理论由日本科学家团体于1942年提出,然后由R.E.Marshak和Hans Bethe独立发表(11)。这个发现引起了战后的一番轰动, 汤川秀树因此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在此之前一年,朝永振一郎开始了他对量子重整性的研究,最终获得1965年的诺贝尔奖。1950年,菊池正士前往美国,他要追随核物理领域实验研究的前沿。
长冈半太郎于1950年去世,一年后,仁科芳雄也去世了。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年,改造科学研究所的诸多管理事务让他们分身乏术,他们再也不能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继续理论科学的研究。但是,战后科学研究工作的恢复和重新开始一定会让他们感到欣慰,因为年轻的物理学家们会在战后的科学研究中继承他们重视纯科学的传统。
注释:
① Report of the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Reorga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apan”pp.7—8.
② 1888年6月7日长冈半太郎给田中馆爱橘的信,《长冈半太郎传》第113页。
③ 森有礼:“Saitama jinjo shihan gakko ni okeru enzetsu”森有礼「埼玉县寻常师范学校にぉける演说」(在埼玉县寻常师范学校的演说)(明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Dec.19,1885)、大久保利谦编《森有礼全集第一卷》(东京:宣文堂书店、1972年)、481—486页、the quotation is in pp.485—486.在埼玉县寻常师范学校的演说.1886年1月31日。
④ Yanagida Kunio Minakata Kumagusu ofuku shokanshu (the Yanagida Kunio-Minakata Kumagusu correspondence)(Tokyo:Heibonsha,1976),p.162.《柳田国男 南方熊楠 往复书简集》.东京:平凡社,1976年.162页。
⑤ 卢瑟福给长冈半太郎的信,1911年3月20日。《长冈半太郎论文集》,国家科学博物馆,东京。
⑥ 《长冈半太郎传》第340—341页。
⑦ 田中馆爱橘:《航空机讲话》,1915。《航空机讲话末章》重印于田中馆爱橘《葛の根》(东京:日本の口一マ字社),Kuzu no Ne 1938.Tokyo:Nippon-no-Romazi-Sya.126—128页。
⑧ 参见:J.F.Carlson and J.R.Oppenheimer 1937; H.Yukawa 1937; E.C.G.Stueckelberg 1937。
⑨ 参见:Kenji Ito 2002; Keiko Nagase-Reimer; Walter E.Grunden; Masakatsu Yamazaki 2005.
⑩ Report of the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to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Reorga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Japan,”1947,p.68.
(11) 这些内容参见M.Conversi,E.pancini,and O.Piccioni 1947; C.M.G.Lattes,H.Muirhead,G.P.S.Occhialini,and C.F.Powell 1947; C.M.G.Lattes,G.P.S.Occhialini,and C.F.Powell 1947; E.Gardner and C.M.G.Lattes 1948; W.H.Barkas,E.Gardner,and C.M.G.Lattes 19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