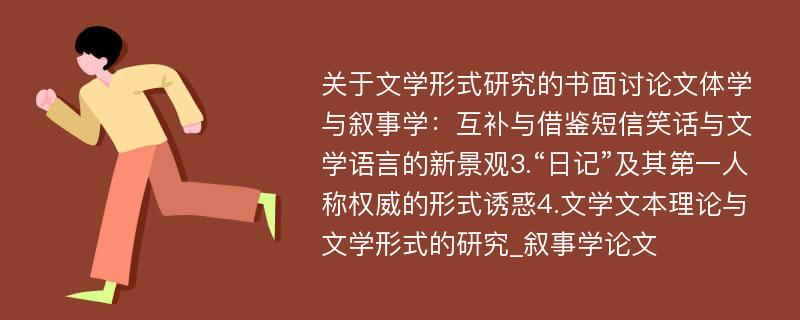
文学形式研究笔谈——1.文体学和叙事学:互补与借鉴——2.短信笑话与文学语言的新景观——3.日记的形式诱惑及其第一人称权威——4.文学文本理论与文学形式研究——5.金圣叹文学形式批评的现代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论文,文学论文,文学语言论文,笔谈论文,人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体学和叙事学:互补与借鉴
□申丹(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1)
文体学和叙事学(叙述学)① 都属于生命力较强的交叉学科。1960年代以来在西方,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两者均可谓同步发展,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引起中外学界的足够重视。我曾在有关论著中探讨了这两个学科的互补性②。这次我想集中谈谈西方文体学对叙事学的借鉴。这种讨论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认清文体学与叙事学之间的互补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为国内文体学的跨学科发展提供参考。
首先,我简要说明文体学借鉴叙事学的必要性。文体学家一般将小说分为“内容”与“文体”这两个层次,叙事学家则一般将小说分为“故事”与“话语”这两个层次。从表面上看,文体学的“文体”和叙事学的“话语”相似相通,但实际上两者相去甚远。英国学者迈克尔·图伦(Michael Toolan)在《文学中的语言:文体学导论》一书中说:
文体学所做的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具有共识的基础上来探讨文本的效果和技巧……如果我们都认为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印第安帐篷》或者叶芝的诗歌《驶向拜占庭》是突出的文学成就的话,那么构成其杰出性的又有哪些语言成分呢?为何选择了这些词语、小句模式、节奏、语调、对话含义、句间衔接方式、语气、眼光、小句的及物性等等,而没有选择另外那些可以想到的语言成分呢?……在文体学看来,通过仔细考察文本的语言特征,我们应该可以了解语言的结构和作用。③
不难看出,文体学所关注的“文体技巧”涉及的是作者的遣词造句。这与叙事学所关注的“话语技巧”大相径庭。让我们再看看图伦在《叙事:批评性语言学导论》一书中,对“话语技巧”的界定:
如果我们将故事视为分析的第一层次,那么在话语这一范畴,又会出现另外两个组织层次:一个是文本,一个是叙述。在文本这一层次,讲故事的人选定创造事件的一个特定序列,选定用多少时间和空间来表达这些事件,选定话语中(变换的)节奏和速度。此外,还需选择用什么细节、什么顺序来表现不同人物的个性,采用什么人的视角来观察和报道事件、场景和人物……在叙述这一层次,需要探讨的是叙述者和其所述事件之间的关系。由小说中的人物讲述的一段嵌入性质的故事与故事外超然旁观的全知叙述者讲述的故事就构成一种明显的对照。④
这些“话语技巧”涉及的是结构安排,而非遣词造句。虽然在两段引语中,都出现了“节奏”一词,但该词在这两段文字中的所指实际上迥然相异。在第一段引语中,“节奏”指的是文字的节奏,其决定因素包括韵律、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之间的交替、标点符号、词语或句子的长短等等。与此相对照,在第二段引语中,“节奏”指的是叙述运动的节奏:对事件究竟是简要概述还是详细叙述,究竟是略去不提还是像电影慢镜头似的缓慢描述等等。第一种“节奏”是对语言的选择,第二种“节奏”则是对叙述方式的选择。也就是说,两者在关注面上都有其局限性。
为了克服文体学的局限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文体学家采用了不同方式来借鉴叙事学。我们不妨将这些研究大体分为三类:温和的方式,激进的方式,并行的方式。下面我将逐一探讨这三种方式的所长所短。
一、温和的方式
西方文体学家对叙事学的借鉴大多采用“温和的”方式,即采用叙事学的概念或模式作为文体分析的框架。下面以“视角”、“时序”及“人物塑造”为例。先谈谈“视角”,传统上的“视角”(point of view)一词至少有两个所指,一为结构上的,即叙述时所采用的视觉或感知角度,它直接作用于所述事件:另一为文体上的,即文字表达或流露出来的叙述者的立场观点、语气口吻,它间接地作用于事件。叙事学一般不关注后者,而文体学传统上也忽略前者。虽然结构上的视角属于非语言问题,但在文本中往往只能通过语言特征反映出来,加上叙事学的影响,文体学家后来也对这一方面产生了兴趣。然而,在具体分析中,他们明显地更为关注语言特征本身。近来文体学家较为注重借鉴叙事学的视角结构分类,将之作为文体分析的框架。就“时序”而言,叙事学关注的是倒叙、预叙等安排事件的结构顺序,而文体学则聚焦于动词时态变化或句子内部的文字顺序。但有的文体学家在探讨动词时态的文体效果时,借鉴了叙事学的结构顺序作为分析框架。就“人物塑造”而言,叙事学关注塑造人物的不同方式,譬如究竟是直接界定人物特征,还是通过人物言行来间接反映;究竟是采用哪一种行动来刻画人物,或人物究竟是由哪些特征构成的。文体学则关注作者究竟采用了什么词句来描写人物。有的文体学家采用了叙事学的人物分析模式作为语言分析的框架,使分析更有系统性。
文体学对叙事学的“温和”借鉴是克服文体学之局限性的一种较好的做法,但容易受到文体分析本身的限制。文体学聚焦于语言特征,即便借鉴叙事学模式,也往往只起辅助性作用,为语言分析铺路搭桥,这必然导致对一些重要结构技巧的忽略。
二、激进的方式
与“温和”的方式相对照,有的西方文体学家采用了较为“激进”的方式来“吸纳”叙事学。保罗·辛普森(Paul Simpson)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2004年面世的《文体学》⑤ 这部新作中,辛普森采用了“叙事文体学”这一名称来同时涵盖对语言特征和叙事结构的研究。这是克服文体学之局限性的一种大胆创举,但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在理论界定中,辛普森有时将文体学与叙事学混为一谈,从而失去了文体学自身的特性。他在书中写道:“很多文体学和叙事学的论著都首先区分叙事的两个基本成分:叙事情节和叙述话语。”实际上这是叙事学而非文体学的区分。文体学区分的是“内容”与“文体”,而如前所述,“话语”与“文体”大相径庭。辛普森在将“话语”纳入文体学之后,将各种叙事媒介均视为文体学的分析对象之一,声称“两个常用的叙事媒介是电影和小说。诚然,还有各种其他媒介,譬如芭蕾舞、音乐剧或连环漫画”。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下面所引辛普森的两段文字:
我们为何要研究文体学呢?研究文体学是为了探索语言,更具体地说,是为了探索语言使用中的创造性……也就是说,除非对语言感兴趣,否则就不要研究文体学。(第3页)
语言系统广阔的覆盖面使得作者技巧的方方面面都与文体分析相关。(第3页)
不难看出,辛普森在此仅考虑了文字媒介。值得注意的是,上面这两段引语互为矛盾:第一段将文体分析限定在语言层面,第二段则将其拓展到“作者技巧的方方面面”。以往文体学家认为作品中重要的就是语言,但身处新世纪的辛普森已认识到文体学仅关注语言的局限性(如第一段引语所暗示的),因此有意识地借鉴叙事学。然而,也许是“本位主义作祟”,他不是强调文体学与叙事学的相互结合,而是试图通过拓展文体学来“吞并”叙事学。其实,无论如何拓展“语言系统”,都难以涵盖“芭蕾舞、音乐剧或连环漫画”。
此外,就文字性叙事作品而言,辛普森在探讨“话语”时,有时也将语言结构(文体学的分析对象)和叙事结构(叙事学的关注对象)相提并论。他举了下面这一实例来说明“话语”对事件顺序的安排:“约翰手中的盘子掉地,珍妮特突然大笑”。这两个小句的顺序决定了两点:约翰的事故发生在珍妮特的反应之前;约翰的事故引起了珍妮特的反应。倘若颠倒这两个小句的顺序(珍妮特突然大笑,约翰手中的盘子掉地),则会导致截然不同的阐释:珍妮特的笑发生在约翰的事故之前,而且是造成这一事故的原因。辛普森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话语”对事件的“倒叙”和“预叙”。在我看来,语言层面上的句法顺序与“话语”安排事件的顺序只是表面相似,实际上迥然相异。后者仅仅作用于形式层面,譬如,究竟是先叙述“他今天的成功”再叙述“他过去的创业”,还是按正常时间顺序来讲述,都不会改变事件的因果关系和时间进程,而只会在修辞效果上有所不同。这与辛普森所举的例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照。此外,句法顺序需要符合事件的实际顺序。就辛普森所举的例子而言,如果是约翰的失手引起了珍妮特的大笑,就不能颠倒这两个小句的顺序(除非另加词语对因果关系予以说明,但那样也不会产生美学效果)。与此相对照,在超出语言的“话语”层面,不仅可以用“倒叙”、“预叙”等来打破事件的自然顺序,而且这些手法具有艺术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切不可将文体学关心的句法顺序与叙事学关心的“话语”顺序混为一谈。
在说明“叙事文体学”对“情节”或“故事”的研究时,辛普森采用了我国读者所熟悉的普罗普的行为功能模式来分析两部电影的情节:一为迪斯尼的动画片,另一为故事片《哈里·波特和哲学家的魔石》。辛普森从情节发展中,抽绎出普罗普的模式所涉及的种种行为功能,譬如第二种功能“主人公收到禁令”(德斯利斯夫妇不让哈里上霍格沃特的魔法学校);第三种功能“违反禁令”(哈里上了霍格沃特的魔法学校)。辛普森成功地将普罗普的结构模式用于对这两部电影情节的分析,但这种“叙事文体学”分析既脱离了语言,又脱离了语言学。辛普森的本意是用“叙事文体学”来涵盖叙事学,而这种分析实际上是叙事学取代了文体学。
在论述“叙事文体学”时,辛普森提出了“文体学领域”可分析的六个维度:文本媒介:电影、小说、芭蕾舞、音乐等;社会语言学框架:通过语言表达的社会文化语境;人物塑造之一:行动与事件;人物塑造之二:视角;文本结构;互文性。这一“六维度模式”的长处在于涵盖面很宽,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我已经探讨了涉及第一个维度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近来有些文体学家注重将文字作品与根据该作品改编的戏剧和电影相比较。若旨在以戏剧和电影为参照来分析文字作品的语言,则是拓展文体分析的一种良好途径;但若聚焦于戏剧和电影,只是以文字作品为参照,则基本上是一种叙事学的研究。有的电影研究者近来倾向于采用“文体学”、“文体分析”这样的术语,但分析对象则是与语言无关的各种电影镜头或拍摄技巧,这种对“文体学”的用法有违中外学界对“文体学”的界定。就第三个维度而言,辛普森仅仅关注了小句语言的及物性(主要涉及对动词类型的选择),而没有借鉴叙事学对人物塑造之结构技巧的探讨。就第五个维度而言,辛普森说:“对文本结构的文体学研究可聚焦于大范围的情节成分,也可聚焦于局部的故事结构特征。”前者指的就是普洛普那样的情节结构分析,那种分析超出了语言层面,也无法应用语言学。由于文体学和叙事学各有其特性,旨在“吞并”叙事学的文体学论著难免片面展示,甚或曲解叙事学(辛普森用句法结构来说明叙述事件的顺序就造成了这种后果)。从另一角度来看,由于要照顾到叙事学,辛普森主要按叙事学的路子提出的“六维度模式”相对于文体分析而言,也失之片面,而且还失去了文体学关注语言的本质特性。
正如“叙事文体学”这一名称所体现的,文体学与叙事学相结合在西方已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这固然有利于对叙事作品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但若处理不当,则可能会造成新的问题。文体学和叙事学各有其关注对象和分析原则。既然文体学关心的是“语言”,就难以用任何名义的文体学来涵盖或吞并叙事学。在实际分析中,若想克服两者各自的局限性,不妨将两种方法交织贯通,综合采纳⑥。
三、并行的方式
为了克服文体学和叙事学各自的局限性,有的文体学家不仅两方面著书,而且也两方面开课。迈克尔·图伦就是其中之一。他身为著名文体学家,却也写出了简介叙事学的书。本文开头之处的两段引语就分别出自他的文体学著作和叙事学著作。诚然,图伦的那部文体学著作有一章题为“叙事结构”,但该章避开了叙事学,仅仅涉及了社会语言学家拉博夫的口头叙事模式。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是因为在探讨文体学时,仅愿意接纳属于语言学范畴的模式,而且那一章的实例分析也聚焦于语言细节和会话话轮等文体研究对象。
有的文体学家在同一论著中,既进行叙事学分析,又进行文体学分析。譬如,米克·肖特(Mick Short)在探讨一部小说时,先专辟一节分析作品的结构技巧,然后再聚焦于语言特征,旨在说明作品的“叙事学创新”和“语言创新”如何交互作用⑦。凯蒂·威尔士(Katie Wales)在她主编的《文体学辞典》中,也收入了不少叙事学的概念,有的是独立词条(如“行动素”、“受述者”、“叙事语法”),有的则与文体学的概念一起出现在同一词条中,譬如“mood”和“anachronism; anachrony”这样的词条, 均同时给出了文体学和叙事学大相径庭的定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者各自的局限性和相互之间的互补性。
与“激进的”方法形成对照,“并行的”方法没有试图用文体学来“吞并”叙事学,而是保持了两者之间清晰的界限。但采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往往未注意说明文体学和叙事学各自的局限性和两者之间的互补性,而是让它们分别以独立而全面的面目出现,这从本文开头所引图伦的两段文字就可窥见一斑。在我看来,鉴于目前的学科分野,无论是在文体学还是在叙事学的论著和教材中,都有必要明确说明小说的艺术形式包含文字技巧和结构技巧这两个不同层面,文体学聚焦于前者,叙事学则聚焦于后者。倘若在文体学的书中像图伦那样借鉴拉博夫这位社会语言学家(或其他语言学家)的叙事结构模式,则有必要说明这种结构模式与叙事学的模式有何异同,阐明在“话语”层次上,还有哪些主要叙述技巧未被涵盖。威尔士在《文体学辞典》中将“文体”界定为“对形式的选择”或“写作或口语中有特色的表达方式”。这是文体学界对“文体”通常加以的界定。如前所示,这种笼统的界定掩盖了“文体”和“话语”之间的差别,很容易造成对小说艺术形式的片面看法。我们不妨将之改为:“文体”是“对语言形式的选择”,是“写作或口语中有特色的文字表达方式”。至于叙事学的“话语”,我们可以沿用以往的定义,如“表达故事的方式”,但必须说明,叙事学在研究“话语”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文体”这一层次,而“文体”也是“表达故事的方式”的重要组成成分。
总的来说,西方文体学对叙事学的借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⑧。在国内,文体学界和叙事学界互不通气的情况十分严重,这难免给研究带来一定的片面性,对于小说的表达层面来说更是如此。在新世纪里,我们希望在国内看到更多的既借鉴西方经验,又有中国特色的跨学科研究,以克服单一学科的局限性。
注释:
① 国内将法文的“narratologie”或英文的“narratology”译为“叙事学”或“叙述学”,在我看来,两者并非完全同义。“叙事”一词为动宾结构,同时指涉讲述行为(叙)和所述对象(事);而“叙述”一词为并列结构,重复指涉讲述行为(叙+述)。“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连,宜指话语表达层,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表达这两个层面。西方文体学的跨学科借鉴既涉及了叙述表达,又涉及了故事结构,因此本文采用“叙事学”这一译法。
② 参见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第8章)、《小说艺术形式的两个不同层面》(《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Dan Shen(申丹)“What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Can Do for Each Other”,in James Phelan & Peter J.Rabinowitz eds.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Oxford:Blackwell 2005,pp.136—149。
③ Michael J.Toolan,Language i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Stylistics,London:Arnold,1998,p.6.
④ Michael J.Toolan,Narrative:A Critical Linguistic Introduction,2nd edition,London:Routledge,2001,pp.11—12.
⑤ Paul Simpson,Stylistic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4,笔者在《外国语》2005年第2期上较为全面地评介了这部书。
⑥ 笔者最近综合采用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方法,分析了一系列作品(申丹:《平淡无味后面的多重象征意义》,《国外文学》2005年第2期;《深层对表层的颠覆和反讽对象的置换》,《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选择性全知、人物有限视角与潜文本》,《外国文学》2005年第6期)。
⑦ Mick Short,“Graphological Deviation,Style Variation and Point of View in Marabou Stork Nightmares by Irvine Welsh”,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15 (1999):305—23.
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一直是国际文体学研究的中心,因此本文的探讨聚焦于英国文体学家。叙事学很少借鉴文体学,因此本文聚焦于文体学如何借鉴叙事学。
短信笑话与文学语言的新景观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5)
短信笑话有什么好谈的?笑过就忘啊,还谈什么?诚然,短信笑话在大量普通人群间发送和传看,似乎不登大雅之堂,低俗不堪,何足挂齿,但我以为,这却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学或文化现象,它可以让我们从中见出为我们的传统偏见所忽略的一些有意味的东西。例如,要了解近来文学中语言及其形式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揭示的社群情感等变化,短信笑话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对象。这并不等于说通常的严肃写作、畅销书、影视剧本、网上文学等在语言上的进展就变得不重要了,而只是表明,正是在短信笑话这种当今影响公众最广泛的移动网络媒体形式中,文学语言形式的新变化及其社会修辞功能表现得最为集中、鲜明且最具公众号召力,因此值得做一番考量。
短信笑话又称幽默短信,可以视为短信文学的一种形式。它主要在手机这种移动网络上传输,同时也可在互联网上传送。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到2005年8月底,全国手机用户已超过3.7亿户,比上年底增长3795.2万户;手机普及率为每百人28部,手机短信发送量已达1906.2亿条,比上年同期增长39.8%①。如果以每个手机用户平均每周传播短信笑话2条(次)计算,他一年可以传播短信笑话104条(次),而全国手机用户一年传送短信笑话可达384.8亿条(次)。如果每个手机用户每周传送仅1条(次),则全国用户一年也可发收短信笑话192.4亿条(次)。但就这个数字看,短信笑话的影响面之广泛应是不言而喻的,其超过通常的杂志文学、报纸连载文学甚至影视文学的巨大传播力量就可想而知了。就我个人的有限观察和体会看,每到逢年过节时,短信笑话的收发数量可谓滔滔而来,应接不暇。
公众之所以喜欢发送和收看一些短信笑话,原因很多,探索途径也应多样,但从语言形式来看,语言的修辞性组合不能不引起重视。具体说来,短信笑话的感染效果是通过种种语言修辞手段实现的。下面不妨看看一些文本实例。大量的短信笑话是用来传达爱情、友情的。“蓝蓝的天空白云飘,白云下面我傻跑,背着LOVE行囊把你追,直到天荒地老,灵魂出窍。看见你精神百倍,梦见你忘却疲惫,想你想得无法入睡,别说你还无所谓,收下我的红玫瑰,你不爱我是你不对!”“玫瑰开在九月里,我的心中只有你,好想和你在一起,没有什么送给你,只有一句我爱你!”轻松诙谐的语句传达出爱情的真挚。“夏日高温不退,生活枯橾无味,革命工作太累,个人身体宝贵,多吃瓜果才对。”这属于韵文达情,即以整齐的押韵文字传达夏日炎炎中的朋友关爱。“茶,要喝浓的,直到淡而无味。酒,要喝醉的,永远不想醒来。人,要深爱的,要下辈子还要接着爱的那种。朋友,要永远的,就是看手机的这个!”依次以“茶”、“酒”、“人”起兴,直到推出“看手机”的“朋友”,体现了起兴赞友这一设计理念。“一个人能走多远,看他与谁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看他有什么人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看他与什么相伴。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身边,很高兴认识你!”这里通过列数不同侧面而赞美朋友的重要作用。
讽刺、调侃或针砭时弊在短信笑话中也不在少数。“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诗歌之美,在于煽动男女出轨;女人之美,在于蠢得无怨无悔;男人之美,在于说谎说得白日见鬼”,这显然是以整齐对称的语句讽刺或调侃当下一种时髦学问、诗歌、男女的品行。
去年传诵很广的《这年头》这样说:“这年头,警察横行乡里,参黑涉黄,越来越像流氓;流氓各霸一方,敢作敢当,越来越像警察。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教授摇唇鼓舌,周游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频上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明星风情万种,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谣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夸大其词,越来越像谣言……”这则短信以角色对换的方式把当前社会中影响广泛的几个社会群体的一种普遍恶习揭露了出来。警察与流氓、医生与杀手、教授与商人、明星与妓女、谣言与新闻等,一股脑地成了嘲讽的对象。虽然有着把所涉人物都绝对化的偏颇,但毕竟对于当前的几种流弊给予了空前辛辣的讽刺。可以说,这则短信笑话具有不可多得的当代“经典”意义。
常常可见到以俗露真的手法。“我是一棵葱,站在风雨中,谁要拿我蘸大酱,我操他老祖宗!走过南闯过北,厕所后面喝过水,火车道上压过腿,还和傻子亲过嘴。操!啥也不拒,就是想你!”粗鄙语言或脏话换个语境可能会有伤大雅,但在这里却颇为得体——不粗不足以显示亲密程度,不亲不粗,越亲越粗。正是这里的粗,也只能是粗,才可以更直接地袒露对话者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大海啊全他妈是水,蜘蛛啊全他妈是腿,辣椒啊真他妈辣嘴,认识你啊真他妈不后悔。祝快乐,天天开怀合不拢嘴!”“国骂”的运用同样拆散了朋友之间的社会礼仪屏障,造成了真情得以尽情流露的独特效果。
“了”字也可以显示其特殊的修辞力量:“恋爱了吧!高兴了吧!从此花钱大了吧!结婚了吧!爽了吧!从此有人管了吧!离婚了吧!自由了吧!做爱要花钱了吧!艾滋了吧!傻了吧!躺在床上等死吧!”
正反同体也效果奇特:“祝身体健康,牙齿掉光;一路顺风,半路失踪;一路走好,半路摔倒;天天愉快,经常变态;笑口常开,笑死活该!”还有名人效应:“听说你最近很牛B,普京扶你下飞机,布什给你当司机,麦当娜陪你上楼梯,金喜善给你烤烧鸡,刘德华帮你倒垃圾,连我都要给你发短信息!”名烟缀联也得到应用:“祝愿你致富踏上万宝路,事业登上红塔山,情人赛过阿诗玛,财源遍布大中华。”还有叠辞传情:“许一个美好的心愿,祝你快乐连连。送一份美妙的感觉,祝你万事圆圆。发一条短短的信息,祝你微笑甜甜。”
上面只是一些简要列举,目的是见出短信笑话的修辞状况之一斑。如何把握这些修辞状况?俄裔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的言语沟通六要素模型可以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基础。他认为任何言语沟通行为verbal communication)都有其基本的构成要素(the constitutive factors):发信人(the addresser)发送一个信息(message)给收信人(the addressee);这个信息有其据以解读的参照语境(context);为发信人和收信人都共通的代码(code);最后,使得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可能的物理渠道——触媒(contact)②。这六要素确实是任何言语沟通都必不可少的,短信笑话也不例外。限于篇幅和论题,我这里只谈短信笑话中的“信息”要素,而且只是它的语言形式方面。
从语言形式看,短信笑话在实际的社会交际中往往体现出自身的特点。不妨看看这则短信笑话:“你被通缉了……以下是你的罪行……对朋友太好,又够义气,善良纯真贴心又可爱……本庭宣判……一辈子做我的好朋友。”先是以法律语言如“通缉”和“罪行”等造成“吓唬”效果,继而转说原因是一贯可亲可爱,最后回到法律语言,做出令人突兀而又兴奋的“一辈子做我的好朋友”这一庄严“宣判”。这则短信笑话显示出两个特点:一是短语性,即短信笑话的篇幅必须短小,通常不足百字,而这则短到只49字。这是要适应手机的屏幕尺寸,可以说是由手机媒体(触媒)的媒体特性所决定的。二是速笑性,即它必须在半分钟左右这个超短时间内迅速引起收看人发笑。具体到这则短信笑话,它引发的不是一般的大笑,而是好友之间的会心的微笑。这就是说,不短不足以成短信,而不笑不足以成短信笑话。由此可见短语和速笑对于短信笑话有多重要了。
不过,光凭这两个特点还不足以造成短信笑话的传播在社会公众中的具体实现。我凭什么要发送或收看这条短信?难道不是白白浪费时间、白花冤枉钱?这里肯定有送看的主体间条件和动机在。在这里不能只谈单一主体,而必须谈主体间,也就是必须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社会关联出发去谈。短信笑话总是发生在人群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间,不能脱离这种主体间去对单一主体做单方面考察。因此考虑短信笑话的主体间性是必要的。从主体间条件看,发送者和收看者必须相识或相熟,具有沟通的社群基础。“知道我在做什么吗?给你五个选择:A:想你 B:很想你 C:非常想你 D:不想你不可能。”如果两人彼此不相识、甚至不熟悉,怎么可以随便送看这则情人间或好友间才可以发送的短信笑话?发送和收看上面的短信笑话的两个人之间,肯定有着情人或好友这一层特殊关系。从主体间动机看,发送者和收看者一个愿发、一个愿收,两厢情愿,导源于共同的社群沟通、同感、同情、关爱或传情等需要。如果缺乏这种社群需要,短信笑话的传播就可以免了。这种导致短信笑话得以传播的主体间条件和动机可以合称为主体间社群同感性,简称同感性。同感性在这里是说,短信笑话必须依赖于主体间的社群沟通基础,并导源于其同感需要。在这里,同感性体现出短信笑话在语言形式上对于主体间社群生存的依存性:笑话总是对主体间的社群生活具有某种用途,而正是这种实际用途制约着笑话的语言组织方式。“我一直都守在你身边,也一再为你担心,今天你吃得饱吗?睡得好吗?深夜会冷吗?我向来都知道你就是不会照顾自己,每当我一走开,你就会从猪栏跳出去。”前面几句都是在描述人间温情,但最后一句中以“猪栏”形成突转,由人转向猪,从而引人发笑。这种笑声有助于让朋友、同事从轻快、幽默的语言游戏中获得一种日常解脱。可以说,笑话正是依据主体间的社群需要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在主体间造成实际感染效果,满足他们的社群生活需要。
综合上面的短语性、速笑性和同感性这三个特点看,短信笑话具有不容置疑的美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丰富意义。也就是说,它所可能包含的意义往往可以超出我们的通常想象或者纠正我们的传统偏见。在这个意义上,短信笑话不能简单地从通常的语言学角度去理解,而应当更合理地从超语言学或修辞学的意义上去理解;同时,这种“修辞”又不能仅仅从传统修辞学意义上去领会,而应当同人的现实生活形式的调适紧密联系起来考虑。这样,短信笑话可以被约略地定义为一种在社会公众间展开的以笑去调节社群状况、主体间关系及个体生存方式的短语修辞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短信笑话具有短语博笑修辞的特点。
短语博笑修辞,是说短信笑话总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旨在传达日常生活同感和引发笑声的短语组织及行为。传达同感和博取笑声是短信笑话的两大最显著的社会功能。与传统和经典的文学文类如诗歌、小说、散文等悉心追求意义深度、历史关怀相比,短信笑话更多地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同感的传递,把这种同感加以平面化,服务于有时十分廉价的笑声的激发。短信笑话当然也有其意义、有其历史感,这在上面列举的《这年头》这则短信笑话中有比较鲜明的展现,但是,它的短语性和速笑性限制了它,既使本来就有限的意义竟变得扁平,同时又使跳动的历史感显得轻飘了。
我想追问的是,短信笑话凭借其短语博笑修辞已经和正在随处博取数量庞大的公众(手机用户)的群体笑声,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具体地说,当越来越多的公众或手机用户正满足于从短信笑话中阅读或谈论“文学”而对诗歌、小说和散文等经典文学文类不屑一顾时,一种怎样的新的文学现象正在兴起?我不禁联想到宋词、元曲先后在各自时代兴起及其对传统权威文类如诗歌构成冲击时的情形。短信笑话这一语言形式是否会对目前的现成主流文学语言形式构成强力挑战?公众对短语博笑修辞的重视和喜爱,是否会意味着淡化或者已经和正在淡化他们对主流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喜爱?随着当今信息技术和媒介技术正努力把生活中的全能信息终端聚集到技术越来越复杂和精巧、功能越来越多而全的复合手机而不是人们原来设想的电脑系统上,那么,短信笑话的语言形式是在对目前及未来的文学语言形式的基本范型提供新的预设、启迪或感召,还是只是在构成昙花一现的无序的过渡式狂欢?谁也不能轻易否认信息技术和媒介技术在生活变化和文学变化中的巨大能量。需要辨明的只是,这种能量其实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与它们所身处于其中的特定社会情境整体一同发挥作用的。随着短信笑话的日渐深入人心,作家们或如今还不被看成是作家的年轻写手们是否会“穷则思变”地呕心沥血,认真研究短信笑话的奥秘,尤其是它的语言形式的奥秘及其启示,直到从中转化出一种专门适合于手机人群传播的语言短而新奇、表述面窄而又兴味深长的新的文学文类或样式来?手机短信笑话的兴盛(以及本文未及谈论的手机小说或手机诗歌的出现),使我不能不产生一种预感、期待或警惕。但这是否会出现,或者具体以何种方式出现,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注释:
① http://news.hexun.com/detail.aspx.1m=1748&id=1349065.
② Roman Jakobson,Linguistics and Poetics,Language in Literature,Krystyna Pomorska and Stephen Rudy,ed.,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66.
日记的形式诱惑及其第一人称权威
□赵宪章(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南京 210093)
日记作为最具民间性的文体,“私语言说”是其存在的理由;而这一理由同语言之交流功能的悖论,又决定了日记存在的不可能。于是,日记文体的蜕变也就不可避免,各种日记名义下的“假体日记”也就大行其道①。
日记文体蜕变的主要标识在于它的听者是“隐身”的还是“现实”的,这是“真体日记”和“假体日记”的分水岭——由于后者的言说对手已经从“自我”转向“他者”,使原本“隐身”的听者“显形”,孤寂的自我倾诉及其私密性不再是日记书写的真实动力及其语体特征,于是,这类所谓的“日记”,也就只剩下“被时间格式化了的记忆”这一纯粹的文本形式②。也就是说,日记被形式化了。
换言之,包括日记体散文、日记体小说在内的“假体日记”的大量涌现,一方面说明日记溢出了它的本义而泛化为广义的“文学”,是日记文体的消解;另一方面也说明日记本身具有文体的魅力,具有能被其他文体所转借的形式诱惑,诱惑出各种假借日记文体形式的“假体日记”层出不穷。其中,“第一人称权威”当是其形式诱惑之肯綮。
第一人称“我”是日记的法定叙述者。相对第二或第三人称而言,第一人称“我”毫无疑问具有法定的权威性,这就是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所说的“第一人称权威”(first person authority)。“在直觉上,一个人关于自己的心的状态的第一人称陈述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而他关于他人的心的状态的第二或第三人称陈述则不具有这样的权威性。……如戴维森所言:‘当一个说话者声称他具有一个信念、希望、欲求或意向时,有假定认为他是没有错的,这个假定并不适用于他关于类似的心的状态的他人归结。’”理由很简单:“心的状态的自我归结并不需要行为观察或其他方面的证据来支持,但心的状态的他人归结则必须以对他人行为的观察以及相关证据为依据。”③ 于是,人们便可以假定一个人具有了解并陈述自己的心的状态的“优先通道”。以小说为代表的日记体文学之所以假借日记展开叙说,首先看中的便是日记的这一形式诱惑。
韦恩·布思曾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用“讲述”和“展示”区别文学史上不同的小说叙事方式:“讲述”即作家或其可靠叙述者直接在作品中呈现,对作品中的人和事进行评论或判断;“展示”则客观地将故事展示给读者,如同戏剧演出,作家或其可靠叙述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也不对作品中的人和事流露倾向或发表评论。布思认为,前者是传统小说的主要叙述方式,后者则是现代小说的主要叙述方式。如果说这一判断大体符合文学史的实际,从某一角度揭示了小说叙事方式的现代转换,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就可以发现,日记体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出现和兴盛④,恰恰同现代小说叙事视角偏向“展示”是同步的。这是因为,现代小说以强调叙事的客观性为由而主张清除作家存在的一切痕迹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实现,特别是涉及“内心透视”(布思语)的人物心理描写,其实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视点:“在生活中,我们通过完全可靠的内省方式来了解自己,而对他人的内心世界却不能把握……在文学中则有点奇怪,作品一开始就直接地用权威式的语气把人物的动机讲述出来,而不必根据人物的外部行动去推断其内在动机。”传统小说的叙述者实际上就是这样强制读者相信未经证实的情况,否则就不能接受和认同他所讲述的故事。这种被布思称之为“人为的权威式的讲述故事的方法”⑤,尽管从福楼拜之后有了很大改变,作家及其可靠叙述者退隐了,不再充任直接的干预者,客观性、非个人或戏剧式的“展示”成为小说的主流,但是,一旦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现代小说所推崇的所谓“展示”也就显得力不从心和难以服人,经不起细心的旁观者的冷静拷问。于是,第一人称叙述也就在这一特定语境中凸现出无可代替的优势——只有“我”讲述“我的内心”才具有无需他人证实的、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就此而言,日记体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兴盛,既和整个现代小说强调客观性、非个人和戏剧性相敌对,也是其“展示”倾向的有效补充。它作为一种最典型的“讲述”,一方面在叙述视角上和现代小说的“展示”倾向两相对峙,一方面又作为“第一人称权威”之“内心透视”的自我陈述,有效地“展示”出无需任何旁证和毋庸置疑的内心世界。
事实是,中外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日记体小说无不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见长。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⑥ 的情节十分简单,讲述的就是主人公维特对绿蒂姑娘一见钟情却不能相爱而苦恼万分最终用手枪结束自己生命的故事。它之所以成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时代号角,并使德国文学产生世界性影响,显然不是以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而在于对主人公“苦恼”内心世界的精细刻画。例如,维特在一次乡村舞会上首次结识绿蒂便暗自认定“这是我心爱的姑娘,我要她除了我永远不许和别人跳华尔兹,哪怕我不得不因此沦入地狱!……我们在大厅里缓步转了几圈,喘一口气。然后她便坐下,我把特意摆在一旁、现在已所剩无几的橘子取来,这倒很起作用,她出于礼貌,一片又一片分给邻座一位不知趣的女士,每分一片,我的心像被刺了一针”(5月30日),“从那时起,尽管日月星辰静悄悄地沿着它们的轨迹奔波,我既不知白天,也不知黑夜,整个世界统统在我周围消失了”(6月19日),“我过得多快活,就好像上帝给他的圣徒们保留的日子一样:今后不管我的命运如何,我永远不能说我没有领略过欢乐的滋味,生命的最纯洁的欢乐”(6月21日)。这种情爱的冲动及其妒忌和苦乐完全发自维特的内心,只有第一人称“我”的自白才有“全知”的特权,才能承担如此细腻和隐秘的情感诉说。现代小说所张扬的客观性、非个人和戏剧式“展示”对于这类“内心透视”肯定无能为力。
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这样。这篇带有浓烈象征意味的小说显然是“主题先行”⑦,即为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⑧,作者臆想出一个深受其害的“迫害狂”,试图假借这“狂人”的“荒唐之言”,“惊起”一直呆在“铁屋子”里“昏睡”、“不久都要闷死”的人们,呼吁他们醒来,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⑨。这“狂人”的“日记”13篇,“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也就是说,这日记首先在格式上就呈现出非常人的混乱,名为“日记”,实则并无正常人的时间概念。全篇所记“狂人”所患“迫害狂”的全部病症是对“人吃人”的猜疑,尽管他那呓语式的假想和感受像“意识流”一样颠三倒四,不合常规逻辑,但是通篇所表达的意向非常清楚:赵贵翁、古久先生、陈老五、大哥、何医生等都是吃人的人;“我”一方面被他们合伙算计着如何吃,也曾无意中吃过“我妹子的几片肉”!为了弄明白其中的缘由,“我”夜读史书,却看不出年代,每页上的“仁义道德”几个字,“歪歪斜斜”,终于从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这就是《狂人日记》的主题,即作者假借“错杂无伦次”的“荒唐之言”所要表达的思想,非常明确。试想,这种“呐喊”式的思想表达如果不是第一人称“讲述”,将大大削弱小说的震撼力和鼓动性。韦恩·布思所说的“展示”只能引发“思考”而不是“呐喊”,因此,只有作为第一人称“讲述”的“日记”,才是“呐喊”“救救孩子”最便捷的文体,并能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还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都非无源之水和纯粹虚构,日记体小说往往有一创作原型或现实因由:《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青年歌德的一段情感经历有关,《狂人日记》和鲁迅的姨表兄患“迫害狂”病有关。可见,日记体小说尽管是文学“虚构”,但是往往和日记的“纪实性”难脱干系。换言之,与一般小说相对而言,以精雕细刻心理世界为主要优长的日记体小说,更多地渗透着现实的因由或作家的体验。再联想到这两部日记体小说分别是两位作者的成名作这一事实,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就像许多家长和教师将日记看作写作训练的启蒙途径那样,日记体小说作为日记和小说的胶合,同时也是“纪实”和“虚构”的交界;既是纪实性文体的虚拟化,也是虚构性文体的初步与雏形。小说钟情于日记文体,正在于小说可以方便地假借日记形式的可信度,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艺术真实的雾瘴⑩。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还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都在正文之前冠一“小序”。其他如萨特的《厌恶》、茅盾的《腐蚀》等,很多日记体小说都采用这类格式。“小序”无非是简要地交待“日记”的背景或来龙去脉,有时还会略加点评,目的是拉开小说作者及其可靠叙述者和日记言说者的时空距离。进一步说,“小序”最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叙述人称的转换,将日记文体的第一人称“讲述”转换成了第三人称“展示”,将“我”的私语言说转换成“他人”私语言说的展示。这一叙述策略显然是为了弥补日记体小说专注于主观“讲述”的缺憾,为个人内心世界的“展示”预设客观性、非个人化和戏剧式的平台。由此可见,小说的“讲述”和“展示”并不是绝对的,韦恩·布思的理论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以第一人称“讲述”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日记体小说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对隐秘的心理世界的客观“展示”。
现实的因由和体验使日记体小说的“讲述”具有真情实感,这是没有任何“中介”的动情力;对于心理世界的客观“展示”则使日记体小说具有无可置疑的可信性。这就是日记体小说“第一人称权威”的形式魅力。它用日记形式所营造的内心独白是一个真切而诱人的雾瘴,以其“格式化了的记忆”诱惑读者的艺术想象。
注释:
① 参见拙文《日记的私语言说与解构》,《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本文系该文的续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② 当然,在“写给自己看”还是“写给他人看”之间还有大量的“不妨给他人看”之类,即可“隐”可“显”之类日记作者的存在。但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只能就其两大极端而言,处于中间部位的听者必须付之阙如,就像康德关于“美在形式”还是“美是道德的象征”的辨析那样。参见赵宪章《文体与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6页。
③ 唐热风:《第一人称权威的本质》,《哲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④ 西方最早的日记体小说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年)最为著名,此前虽有文学性日记面世,或在小说中插入日记文体(如《鲁滨逊漂流记》等),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日记体小说。中国第一部日记体小说是徐枕亚的《雪鸿泪史》(1914年),影响最大的当然是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年)。总体看来,日记体小说的大量出现,当在19世纪之后,是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文体创新,和韦恩·布思将法国作家福楼拜作为小说叙事视角现代转换的标志是一致的(参见韦恩·布思《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⑤ 韦恩·布思:《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⑥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很多篇章都使用了第二人称“你”,以“我对你倾诉”的语调表达主人公维特对绿蒂的爱恋及其复杂的内心世界,但是不能由此认定这小说是“书信体”而不是“日记体”(见侯浚吉《歌德与〈少年维特的烦恼〉》,《少年维特的烦恼》,侯浚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页)。尽管作者在作品中也使用过“这封信”之类的字眼,但是,那完全是一种修辞手法(更真切地表达对绿蒂的爱恋),而不是一种真实的称谓。这不仅因为构成这部小说的每一篇章均有日期标识,即日记的“排日记述”格式, 更在于维特的“倾诉”只是“自言自语”,没有也无须他人回应,“我”和“你”并未构成“对话”关系,何况“你”在作品中并非特指绿蒂一人。
⑦ “主题先行”即在创作之前就有了比较明确的主题思想。参见顾农《读鲁迅对〈狂人日记〉的自评》,《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⑧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
⑨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⑩ 至于日记体散文,则是纪实的虚拟化和文学化。如陆游的《入蜀日记》和郁达夫的《日记九种》等。
文学文本理论与文学形式研究
□董希文(烟台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山东 烟台 264025)
一
“文本”概念在人文科学领域使用频繁,但对其内涵却很少做出明确界定。“文本”是一个西方文论概念,其被引入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它被稳定接受和大量运用并直接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观念的转变。当然,这一方面固然是由国人摆脱“文艺为政治服务”主流理论、渴求新的理论转型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学者探求文艺自身规律的必然结果。其流行之广、影响之大,令国人始料未及,“文本分析”、“文本阐释”、“文本解读”、“泛文本”等概念一时之间遍地开花,但对于什么是“文本”却很少做出明确解释,仿佛它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事实上“文本”这一个范畴内涵颇为复杂,从词源学上看,“它的词根texere表示编织的东西,如在纺织品(textile)一词中;还表示制造的东西,如在‘建筑师’(architect)一类的词中”(霍兰德);但在一般意义上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利科)①。从语言学角度看,“文本指的是文本表层结构,即作品‘可见、可感’的一面,因此对文本的分析可以从语音结构、叙事句法和语言功能等三个层面展开;从符号学角度看,文本表示以一种符码或一套符码通过某种媒介从发话人传递到接受者那里的一套记号”②。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特娃则认为:“我们将文本定义如下:一个超越语言的工具,它通过使用一种通讯性的言辞来重新分配语言的秩序,目的在于直接地传递信息,这些言辞是与那些先于其而存在的和与其并存的言辞相互联系的。”③ 而在当代有些批评家那里,文本则超出了语言学界限,既可以用于电影、音乐、绘画等艺术种类,“也可以指一切具有语言——符号性质的构成物,如服装、饮食、仪式乃至于历史等等”④。法国现象学符号理论家让—克罗德·高概更是将文本归结为一种表达方式:“说文本分析的时候,应该把文本理解成一个社会中可以找到的任何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是某些书写的、人们通常称作文本的东西,也可以是广告或某一位宗教人士或政界人物所做的口头讲话,这些都是文本。”⑤ 由此可以想到,文本概念人言言殊,“新批评”理论将其视为特殊的语言表达机制,符号理论认为它是超越语言的符号体系,后结构主义则认为文本具有互文性,而当代批评家更是将其内涵无限扩大,认为生活中具有表意功能的语言符号以及类语言符号都是文本。中国当代文本理论来源于西方,“文本”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中国,最初有人将其翻译为“本文”,后改译为“文本”。有人认为其含义就是“以文为本”⑥;有人以为其含义是与“作品”相对而言的,是指作者创作完成,但未经读者解读并实现其价值的客观存在物,总之众说纷纭。
文学文本理论是一种立足文本客观形式而展开的文学批评、阐释方法。文本理论与文学形式研究关系极为密切。
二
20世纪整个西方文学理论之所以关注作品本身,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对此前理论界忽视作品研究的反拨与矫正。因为文学要想具有科学形态,就必须对其客观存在做出科学解释,并弄清自身的构成与规律。就如艾亨鲍姆所言:“我们和象征派之间发生了冲突,目的是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诗学,使诗学摆脱他们的美学和哲学主观主义理论,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⑦ 另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然而,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有多少学者研究语言学及其相关问题,取得了多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与发现,而在于他们驾轻就熟自觉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去解释其他人文学科,因研究角度的别样而发现了许多被历史和传统遮蔽了的问题,因此而具有了研究方法上的“转向”之意。语言学是20世纪的“显学”,其研究方法已渗透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盛宁先生所言:“语言学已经跃居西方人文科学的领导地位,这门科学的高度理论性使它成为任何思考的出发点。……语言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⑧
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对文本理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个由各类词语按照一定规律编织而成的语言复合体,对其分析、研究必然涉及语言问题和语言学方法。语言学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从直接的较浅显层次而言,语言学的兴起引起了研究者对文本语言乃至表达技巧的重视,将文论研究核心定位在语言本身及其组合规律。在这方面,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其始作俑者,也是直接受益者。从较深层次上讲,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文本研究很有启发,人们可以用语言哲学方法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语言能指本身与指称对象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能指与所指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本身是一个具有层级区别的逻辑结构体系,语言的意义产生于能指层面与所指层面体系内部存在的区别与差异;语言区别于言语,具有转换生成功能。上述认识促发了人文科学研究的革命,结构主义方法风行一时。更进一步讲,语言学转向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形而下的技术操作方面和研究视角的转变,而且还直接导致了对文学本质的重新定位:文学不是传达作者情感与认识的载体,不是读者随意填充主观内容的释义对象,更不是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的耳目与喉舌;它是一个客观存在、自足封闭的语言编织物。文本观念与文本理论由此得以形成。
三
文学文本理论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文本的客观性及其阐释、解读问题。20世纪人文科学处于一个重视语言阐释和意义生成的时代,文学文本分析自然是意义诠释的一个重要领域。就一般情况而言,文学文本阐释需要经过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渐次递进过程:最先是辨析语言,接着是体察结构布局,然后是寻找文本间的联系,最后才是对文本文化意义的揭示。而语言、结构、互文(文本间的联系)又恰恰是分析文学文本客观性的依据,而其文化意义虽属于主观阐释的东西,但必须立足文本之上,否则成为无稽之谈,因为文学文本的文化意义不同于一般社会事件的文化含义。
文学文本分析的第一个层次是辨析语言,对作品进行语言结构分析与描述。从语言功能上看,文学文本语言到底是工具、载体还是本体?从语言本质上讲,文学文本语言到底具有确指性还是具有歧义性?所有这些困惑着整个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集中表现于对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区别的理解中。文学文本是语言的艺术,但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这并不是说文学语言在词语的选择方面迥异于日常语言,而是指词语在文学功能体系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文学语言充满了反讽与悖论,是一种张力语,只能放在一定的语境中理解。与日常语言相比较,文学文本语言具有自指性和曲指性。
文学文本分析的第二个层次是体察结构。通常的理解是,结构就是对事物内容的组织与安排,属于形式要素;但事实上,结构涵义颇为复杂,需要重新审视。就结构的地位来看,结构不仅仅是技巧与手段,它本身就渗透在文本有机体中,具有本体地位。就结构层次来说,结构有表层结构、深层结构之分,前者类似叙事句法,通过化约文本可以得出;而后者则是深藏不露的叙事模式,只有运用结构功能逻辑推演才能获得。就结构的本质来讲,结构并不具有永久稳固性,它徘徊于稳固与颠覆之间,既支撑着文本大厦,又不断挖掘其根基。惟其如此,才使得文本既具有意义的相对稳定性,又具有释义的无限多样性。
文学文本分析的第三个层次是剖析文本间的联系,即揭示互文性。互文意味着此在文本与前在文本之间存在着可征实的文字术语或不可征实的精神意念上的多样联系,它是理解文本意义必然涉及的因素。这种理念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已将文本视为一种开放体系,而不仅仅是封闭的语言、结构及其由此构成的有机体。但互文不同于影响,互文是文本间的共时横向渗透,立足文本形式因素;影响则是文本间的历时纵向承传,侧重文本思想与意义的挖掘。以高科技和网络为载体的网络文学最突出地展示了互文的特性与价值,是有史以来互文本的最高典范形态。
此外,文学文本分析还需揭示其文化价值,因此历史、意识形态因素也是理解文本必定涉及的方面,它虽不直接进入文本,但时刻对文本产生着影响。20世纪后期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对此表现出尤其浓厚的兴趣。这些因素主要以两种形式与文本发生着联系:一是历史因素的介入,一是意识形态权利关系的干扰。新历史主义使人们认识到历史事件也以文本形式存在,历史叙事与文学文本之间具有互文关系。而以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詹姆逊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则将文学活动视为一种独特的文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在他们看来,文学文本活动本身作为一种表意实践方式执行着文化与政治职能。“泛文本”是对上述文本观念的最恰当描述。
文学文本理论所关注的正是上述文本分析与批评问题。
四
研究文学文本理论,不能不谈到20世纪西方文论。特雷·伊格尔顿对近代以来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曾有准确论述:“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阶段。”⑨ 此言不虚,精当而准确。文本理论贯穿于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全过程,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也相应地出现了两次转折与飞跃;即由作品到文本,从自在到建构。相比较而言,前者更关注文本分析的语言、结构层面,而后者则在立足语言、结构探讨基础上深入挖掘文本互文关系和文本阐释与文化制约的互动影响。而就历史发展状况来看,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由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等主流批评理论依次关注了文学文本中的语言、结构、互文、文化等问题。
文本理论肇始于俄国形式主义,历经新批评,至结构主义,终于蔚为大观。由作品到文本观念的转变就历经这一过程。对文本自身细究深讨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法捷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特色所在。俄国形式主义提倡陌生化理论,重点探讨文学语言表达技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而完整的形式主义理论体系。英美新批评对文本语言本身尤为关注,在他们看来文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文本语言的悖论、反讽、含混特性使作品既复杂、充满矛盾对立又统一和谐。在文本中感知的具体性与逻辑的抽象性做到了有机融合。文学批评就是研究文本自身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因此,他们将自己的批评方法命名为“细读法”。而细读批评最为担心的就是“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在批评过程中的无意识出现。如果说上述两种批评方式侧重文本语言特色的话,那么结构主义批评则更倾心于将文本视为一个封闭体系,着力挖掘文本深层结构模式;如果说前者突出单个文本的特色及其为读者带来的具有个性化色彩的独特体验,那么后者则更关注文本深层结构所具有的普遍性、客观性,更乐意寻求结构模式的科学性与普遍性。
从根本上讲,自在的文本观是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而建构的文本观则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后诸多理论派别的文本理论。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认为文本是一个自足的语言符号系统,它由能指排列组合,并形成一个共时的总体结构,文学研究就是分析文本的语言、表现技巧以及支配文本成型的深层结构。文本只有一个确定的意义与结构,文本与作者及现实世界没有必然联系。建构的文本观则持相反认识。一方面,文本虽然是封闭的语言客体,但其意义并不确定与唯一,因为语言本身具有隐喻性,语言的这一本质特征使得文本与其指涉物保持着一定张力,既指向外物,但又总不与其完全一致,文本的意义是多重的。另一方面,就文本构成而言,语言符号是其物质基础,但语言符号意义的无限延宕造成文本意义并不固定,而是时时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因为构成语言符号的每一个能指和所指的内涵只能依靠更下一级的能指和所指来区分;而从理论上讲,这种区分是无限的,因此意义和内涵只能处于无限的延宕与推延过程之中。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建构的文本观并不是某一种文学观点或理论流派,而是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文学批评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整体倾向。从其内部构成来看,派别众多,并且各自有着不同的理论渊源。大致来说,建构的文本观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批评方略和旨趣。另一种是立足文本内部,从语言与结构的不稳定性出发,揭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建构生成过程。美国“耶鲁”学派及德里达、巴特的理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一是立足文本自身,但更侧重文本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广泛联系及互动关系,从这种联系中揭示文本的开放性、多元性和生成性。新历史主义及詹姆逊、伊格尔顿等人的观点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在每一种批评策略内部又因理论背景的不同,运用着不同的批评原则,呈现出多样理论形态。它们交相呼应,互相启发与借鉴,彼此互补,共同促进与发展。
综观文学文本理论内涵、研究核心问题及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文本理论是一种立足作品客观存在形式而展开的解读、批评方法,对于文学形式研究具有启发价值和借鉴意义。
文本观念不断变化,多元的时代应有多元的文本观。但无论如何,文本分析必须立足其客观性,同时注意其意义的生成性。这一点,对于新世纪文艺研究至关重要。忽视了前者,文艺批评就会成为子虚乌有的痴人说梦;忽视了后者,文艺研究就会众口一词、呆板机械,丧失其应有的人文性质。只有立足文本客观存在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
注释:
① 董学文等《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297页。
②③④ 参见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68、168页。
⑤ [法]让—克罗德·高概:《范式·文本·述体》,《国外文学》1997年第2期。
⑥ 王一川:《杂语沟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⑦ [俄]艾亨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托多洛夫主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⑧ 盛宁:《人文的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9页。
⑨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金圣叹文学形式批评的现代思考
□樊宝英(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 山东 聊城 252000)
一、文学批评性解读应该始终透过形式把握寓意
对金圣叹批评意图的把握既不能仅仅从外在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直接去求得,也不能从作者的意图方面直接求解,同时也不能从金圣叹的世界观中直接见出。在这方面,金圣叹对宋江的解读很有典型性。金圣叹在批点《水浒》时,独恨宋江,视为狡诈奸猾之徒:“一路写宋江使权诈处,必紧接李逵粗言直叫,此又是画家所谓反衬法。读者但见李逵粗直,便知宋江权诈,则孰几得知矣。”① “此书写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径心地,然曾未有宋江之权诈不定者也。”② 诸如此类的评语还很多,金圣叹由此概括出宋江的性格是一种权诈奸猾,可以说超出了一般评点家视为“忠”的看法。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金圣叹何以能总结出宋江的如此性格?关键在于金圣叹能沉浸文学文本之中,以形式文法为中介,细细玩味于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细细追索于情节的跌宕曲折、前呼后应。在充分的审美判断的基础上,对宋江施之以道德判断,进而折射出自己的批评意图。金圣叹深知文学文本的寓意绝非显在之物,而是“深文隐蔚,余味曲包”③。金圣叹说:“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斯真天下之至乐也。”④ 文学文本的意图实不易追寻,对此,金圣叹认为必须“理会文字”,解读形式,透过字里行间,触摸行文脉络,才能深识鉴奥。他说:“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夫读宋江一传,而至于再,而至于又再,而至于又卒,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然吾又谓由全好之宋江而读至于全劣也犹易,由全劣之宋江而写至于全好也实难。乃今读其传,迹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笃敬君子也?篇则无累于篇耳,节则无累于节耳,句则无累于句耳,字则无累于字耳。虽然,诚如是者,岂将以宋江真遂为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记汉武,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也,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⑤ 金圣叹对宋江的解读并非是演绎自己的主观意图,先入为主,也决不是径直获得作品的意义,而是通过枝枝节节的审美判断,求得一种言外之意。
在金圣叹看来,对文学作品思想意图的揭示,是建立在文学文本基础之上的。批评家应该结合具体的形式分析,从而引发出他对社会人生的看法。金圣叹的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文学解读学的建构来说,不无启发。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道胜于文、质胜于文的强势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里,形式冲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低迷状态,致使我们的文学解读忽略了形式的中介,思想先行,直奔主题。这一点引起了现代学人的关注,并强烈呼吁文学批评“不要绕过形式”的思想:“一方面注重文学思想史研究,一方面又能避免‘思想史取替文学史’,实现‘思想’与‘文学’的有机统一,也就成了我们所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实现二者有机统一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形式阐发意义,即通过文学文本的审美分析阐发文学的思想,相对于‘思想优先’式的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姑且将这样一种方法称之为‘形式美学方法’。”⑥ 这种看法颇富见地。无论怎样,文学创作总要遭遇意识形态,思想意图之于文学文本的存在可谓如影随形。但意识形态的存在已被文学符码化,被移置、呈现为幻化的形式,并非通体透明。因此,文学文本不是意图、主题、创作经验的存在,不是意义或效用的存在,而是一种形式的存在。正如马拉美所说:“诗不是用思想而是用语言写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姿态,即文学批评性解读,必须从形式出发。文学解读“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⑦,所以只谈内容不谈形式,不叫现代批评,现代批评必须以形式代码中介,来触摸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
二、文学批评应该寻求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张力
金圣叹的文学评点常常遇到才与法的纠葛,但是金圣叹却能较好地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对于创作来说,金圣叹一方面要求性情抒发,自然无迹,无“印板文字”,强调“文无定格,随手可造”,另一方面又要求“文成于难”,无不精严,强调“临文无法,便成狗嗥”,意在追求自然与精严的统一,达到至法无法的“化境”。那么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一方面采用八股式的文法解读,另一方面要求自我阐释的“适来自造”;一方面要求“不是圣叹文字”,另一方面又要求“是圣叹文字”⑧。具体来说便涉及到文学评点中分解细读与感悟之间的矛盾问题。文学批评犹如美人照镜,既是映照自己,又是映照他人。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首先应该会用心灵去感受文学作品,体验出美感的深度,甚至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据此金圣叹特别张扬文学批评中的主体意识,要求独创性。他评点《西厢记》时说:“《西厢记》不是姓王字实甫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敛气读之,便使我适来自造。亲见其一字一句,都是我心里恰正欲如此写,《西厢记》便如此写。”⑨ 文学解读是读者通过纵心想象,积极和作者共同参与的活动,但这种活动并不是重复作者已有的发现,而是接受者“每有心会”、“贵乎自得”的结果。但是文学批评并不能一味地止于妙悟感叹,“只可意会不可言谈”,必须把这种美感予以分解,予以证实化、科学化。为此,金圣叹一方面否定“妙处可解不可解”之语,另一方面强调“鸳鸯既已绣出,金针亦尽度”,声言“愚意且重分解”。在金圣叹看来,真正的批评家应该是金针度人,给读者指点迷津。他在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中曾说:“观鸳鸯而知金针,读古今书而视其经营。”⑩ 其《杜诗解》也说:“看诗全要在笔尖上追出当时神理来。”(11) 所谓“经营”,就是一种匠心独运的叙事笔法;所谓“神理”就是在运笔之中所体现的诗之精髓。这些东西的获得必须依靠“分解”之“金针”才能完成。金圣叹的“金针”之喻表明作品所内涵的审美之秘可通过对其语言、结构等形式的分解来加以透视。金圣叹一方面要求“条分而节解之”,讲究分解数、分节数,走向细化,另一方面,又要求“解分而诗合”。他在解杜甫《秋兴八首》时认为。“道他是连,却每首断;道他是断,却每首连……分明八首诗,直可作一首诗读”。每首诗都是一个整体,自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对于它的分解我们不能绕过它内在的意象和气脉,而直接抽取它的内涵。“圣叹所以不辞饶舌,特为分解。罪我者,谓本是一诗,如何分为二解;知我者,谓圣叹之分解,解分而诗合,世人之溷解,解合而诗分。解分前后,而一气混行;诗分起结,而臃肿累赘”(12)。“解分而诗合”就是可以进行分析分解,但这分析分解最终要符合诗歌自身的艺术特性,强化它的整体效应。正如布鲁克斯所说:“一首诗应当被视作各种关系组成的有机系统,诗的品质决不在于某一可单独取出的成分之中。”(13) 从这样的诗学观出发,金圣叹的“解分而诗合”的批评方法,找到了自身的批评话语,带有文学本体批评的味道。金圣叹的这种“解分而诗合”与“新批评”强调的“细读”有极大的相通性。解读文学文本,应该审慎地关注其中的每一个词句,细细加以体会它的本意和言外意,详加推敲语气、音律、意象以及词语搭配、句型选择等方面的微妙之处。同时在注意它们之间的微妙联系之中,又紧紧扣住文本的整体篇章布局,见出整体的意蕴。金圣叹的这种分解论,因精细的阅读,使批评家对艺术的价值判断变得不再那么飘浮不定,从而给以较有说服力的明证。金圣叹的这种细读批评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注入了理性分析的血液,是对长期以来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谈”、“妙处不必可解”批评模式的一种反拨。对文本意蕴的美学感受和理解不再只是点到即止,心领意会,而是可以做精密的推理和详细的论证。
由此可知,金圣叹进行文学批评追求的是精细透彻,一方面对文学文本有自己的深刻领悟与体验,既能契合作家之心,又能创生读者之意,构成了一种双向对话与交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以科学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让人能感到它实实在在的美之存在。30年代的范烟桥先生对金圣叹的批评的精神予以高度赞扬,认为“第一有科学头脑”、“第二能体会”(14),这可以说颇得金圣叹文学评点的真谛。文学批评首先面对的是文学文本,必须灌注一种理性精神,对艺术的神理精髓,进行细密的透视。只有以文法的方式加以介入,才能驾驭作品的艺术真谛。唯有这样,才可以防止它成为一种“过度的诠释”(15)。但是这种理性细密的分析,还必须依靠批评者自身的体验感悟和生发创造。否则,文学批评将会成为没有审美意味的理性审判,同时它的生机也就会停止了。文学批评既需要感受美感,领悟美感,同时还要传达美感,确证美感,做到艺术化和科学化的统一。布迪厄说得好:“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是空洞的。”(16) 就金圣叹而言,他既是一个欣赏家,又是一个分析家,是一个复合型的文学评点家。他的细读批评实现了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这不仅对于许多空头的理论家或印象式的鉴赏家是一种警醒,而且对我们目前危机四伏的文学批评也具有一种纠偏化弊的作用。
三、文学批评在文化研究中应确立自己的位置
金圣叹是一个悟性极高的才子,他对中国文化中的儒、道、释均有涉及,并且使它们之间互识互证,杂糅一体。金圣叹本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源,使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时,难免用文化批评的方式加以观照。但金圣叹文化批评的路径却别具一格。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按照宾主(17) 关系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大致不外乎四种:主中主:从文学到文学;主中宾:从文学到文化;宾中主:从文化到文学;宾中宾:从文化到文化。对金圣叹来说,除了采用从文学到文学的方式之外,最主要的文化批评形式就是从文化到文学。特别是他能借用文化的分析,导向文学形式的印证,呈现文法的总结。由《周易》中的阴阳互补到“相间”式的解读,由老庄的“有无”到作品结局的删削,都落实到文学形式的层面。特别是佛教文化诸多用语,诸如用“因缘生法”、“极微”、“那辗”来说明文学的道理,达到以佛理证文理的目的。金圣叹的文化批评所遵循的是从文化到文学,再从文学到形式的理路。在他那里,文化只是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策略,文学的本根依然是坚固的,有着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疆界。金圣叹的这种文学研究方法论对于我们目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者,无疑是一种启悟,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研究与文化的关系,并在这种反思中对我们自身的角色加以定位。“无论是对某一对象的综合研究,还是选取一定的视角切入特定对象的个别研究,文化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方法,而不在于文化学的‘学科’性质。文化和文化学的内涵至今仍被认为大而无当,没有确定的疆界和知识域,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目前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学’学科”(18)。文化研究虽然隐含着极为广阔的空间,但它对于文学的研究“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视野,一种范式,或一种策略”(19)。因而,当我们面临文化转向的今天,文学虽然走向了边缘化,但是文学性的领域不但不会消失,而且更加宽广了,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它的寻觅依然是文学批评的根本所在。
文学批评的深度表现在于从形式出发,抓住艺术形式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释艺术的秘密。对于一个文学批评家来说,应该依据一种审美的立场,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美学客体,去感受文学文本的形貌,从而评定文学文本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这可以说是金批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
注释:
①②⑤ 林乾主编《金圣叹评点才子全书》第4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34、659、644页。
③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下册,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61页。
④⑧⑨ 林乾主编《金圣叹评点才子全书》第2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19、19页。
⑥ 赵宪章:《也谈思想史与文学史》,《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8日。
⑦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⑩ 林乾主编《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3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11) 陈德芳校点《金圣叹评唐诗全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页。
(12) 林乾主编《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1卷,1999年版,第774页。
(13) 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14) 范烟桥:《金圣叹的治学精神》,《新闻报》1935年8月20日。
(15) 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3页。
(16) 布迪厄:《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17) 此处借鉴了佛教关于宾主关系的论述,如《洞山大师语录》所论“主宾”就有“主中主”、“主中宾”、“宾中主”等关系。
(18) 赵宪章:《文艺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及其发展趋向》,《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
(19) 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