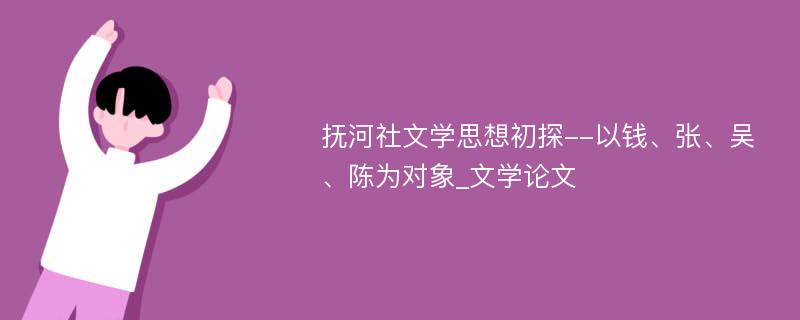
复社的文学思想初探——以钱、张、吴、陈等为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象论文,思想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4)02-003-06
兴起于明末的复社,是我国历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的文人社团。过去,人们对于它的了解和研究多限于政治运动方面,有关文学方面的专门探讨甚为少见。其实,虽说复社不是纯粹的文学社团,但它的文学活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在当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而其文学思想尤其值得引人关注。
从思想史和文学史的角度看,复社的文学思想不仅是其“兴复古学”(卷一)[1]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是明清之际文学思想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其要点大体包括如下的内容:(一)从“兴复古学”的思想宗旨出发,并受其文学使命感的影响,复社主张取法七子,继李、何、王、李之后掀起了文学复古主义的第三次高潮;(二)与尊经复古思想相联系,复社文学思想的最终指归是“力返风雅”(卷二五《仿佛楼诗稿序》)[2],《诗经》为其文学上最高的典范;(三)在文学审美追求方面,复社认为“温柔和平”是最高的审美准则,体现了对诗教传统的继承;(四)主观方面讲究“学问”和“性情”,客观方面讲究“世运”,是复社创作论的基本内容;(五)复社文学思想吸收了先秦以降直到明代的一些重要文学理论学说,并融入自身文学创作的实感真悟以及结合了时代的因素,故已非前后七子复古思想的沿袭照搬,而是有了较大的涵盖面和兼容性;(六)就其影响而论,因复社人数众多,地域甚广,影响久远,加之复社作家创造了杰出的文学实绩,所以复社文学思想在当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响应,至清初有的被直接接收下来,有的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由此成为清代文学思想中的合理成份。
(一)渊源论:绍绪七子,宗法汉唐
明代文学自复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出现以后,其发展体现了门户对立、路向各异的趋势。启、祯以后的文论诗论,一般来说都免不了要涉入派别之辩,扬此抑彼,各立营垒。结果,各派都有承继者,同时又都受到他派的攻击和批判。这是当时文学发展的基本状况,复社的文学思想正是形成于这样的背景之下。
在文学上,复社既没有自辟蹊径,也没有选择唐宋、公安、竟陵中的任何一派,而是态度鲜明的表示要取法七子,不遗余力地捍卫复古派在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崇祯四年,张溥、吴伟业、陈子龙等十一位复社重要成员聚于京师,明确表示“拟立燕台之社,以继七子之迹”(卷三十《壬申文选凡例》)[2]。自此,复社高扬七子的旗帜,掀起了明代文学的第三次复古浪潮。令人值得思索的是,前后七子自嘉靖以后就先后受到唐宋派、公安派和竟陵派的批判和否定,复古派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的种种弊端早有充分的暴露,此连复古派自身都有一定的认识和悔悟。那么,复社何以要重树七子的旧帜呢?而且,在这一复古旗帜下为什么还能得到极为广泛的响应呢?
此需先从地域因素说起。复社领袖张溥在《王文肃课孙稿序》中指出:“嘉靖之季,文尚弘邈,吾娄相国起而昌大其事,观斯备矣。当时称述大家者,咸云:‘琅邪探放六艺,太原综切义理。’两家岳岳儒林间,四方车盖辐辏其乡,童子歌谣,丈人播说,未能先也。(《古文近稿》卷一)”[3]《王子彦稿序》复云:“予生时晚,不及从琅邪王氏两先生游,则闻之长老云:‘元美先生广大,敬美先生方严。’辄私心想见之。”[3]琅邪王氏指王世贞、世懋兄弟,太原王氏指王锡爵,或文为宗主,或位居相国,皆为太仓人。这两段文字说明,太仓二王之文对张溥有着深刻的影响。此外,复社干将、张溥门徒吴伟业在《太仓十子诗序》中还详细地考察了太仓文学的渊源和五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指出:太仓之文“至于琅邪、太原两王公而后大,两王既没,雅道澌灭,吾党出,相率通经学古为高,然或不屑於声律。”(卷三十)[4]张溥、吴伟业和复古派另一位中坚人物张采都是太仓人,所以无论从地域情结还是从文学源流来说,他们宗法王氏,倡导文学复古思想,都在情理之中。
但地域因素还不是最根本的方面。最根本的方面在于,复社的文学复古思想是其兴复古学思想的一部分,亦或说,取法复古派,实乃复社依其思想内在理路的必然选择。复社兴复古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比隆三代”(卷二四《复社纪事》)[4]的理想社会。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复社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即复古主义的文学观。复古派的文学观源于他们的社会史观,是古非今是其思想的共同特点。故单就文学方面看,他们的观点似乎是倒退的,但他们并不单纯地看待文学,对现实大胆的批判精神、对社会强烈的使命感、对士人独立品格的追求,皆不可避免地表现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由张溥、吴伟业、陈子龙上溯到李攀龙、王世贞再上溯到李梦阳、何景阳,与其说他们在主张文学复古方面有着一致性,倒不如说他们在思想气质和处世精神方面属于同路人。从李梦阳提倡“三代之学”(《论学上编》)[5]到张溥以兴复古学为己任,从李梦阳批判士人“病在元气”(卷三九《上孝宗皇帝书稿》)[6]到张溥激励复社诸子“明生死之大”(《古文近稿》卷三《五人墓碑记》)[3],从李梦阳疏劾刘瑾等“八虎”、不避势要到张溥承绪东林、反对阉党,复古派取舍同趣,血脉相通。陈子龙谓:“国家景命累叶,文且三盛:敬皇帝时,李献吉起北地为盛;肃皇帝时,王元美起吴又盛;今五十年矣,有能继大雅、修微言、绍明古绪,意在斯乎?天如勉乎哉!”(卷二五《七录斋集序》)[2]明文三盛实与“国家景命”息息相关,文学复古的宗旨在于“继大雅、修微言、绍明古绪”。陈氏之言,此意甚明。
复社取法七子,还有一层因素。这涉及到复古派为何皆主“汉唐说”的问题。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卷二八六《李梦阳传》)[7],李攀龙“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卷二八七《李攀龙传》)[7],复社中主张文学复古的重要旗手陈子龙亦云:“文当规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卷三十《壬申文选凡例》)[2]。复社与前后七子的论调几乎如出一辙。依理说,“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经唐宋派、公安派的有力批驳似已很难立足,但为什么像陈子龙这种才识超卓不让古人的大家还要把前后七子的旧训条再次抛出来呢?此中必有一定的原因,概言之可为三个方面:其一,与复社远绍汉唐、比隆三代的政治理想有关;其二,与复社提倡之文乃“国家之文”有关;其三,与复社张扬“元气”、“元音”有关。
从政治上讲,明代是“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8]。太祖开创基业,成祖励精图治,至永乐后期出现了“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幅员之广,远迈汉唐”(卷七《成祖本纪三》)[7]的局面,而明兴以前则是“曩宋失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余年,移风易俗,华夏腥膻”[9]的时代。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变对明人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士人尤其如此。一方面,疆域的扩张、国力的增强,使不少人自然萌发了“远绍汉唐”、“比隆三代”的政治理想,此种思想又自然地反映到一些士人对于文学的认识上。吴伟业说:“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以为之重”(卷二七《陈百史文集序》)[4]。依此观念,政治上“远迈汉唐”的明王朝,文学上所要取法的自然当属汉唐,而不会是宋元;或者说,文学上规摹秦汉文章和盛唐诗歌,是明代在政治上出现“远迈汉唐”之势后文化上追求与政治对等以使明帝国能全面地再现汉唐盛世的辉煌的需要。再一方面,伴随明帝国的强盛而增长起来的民族主义情感,不仅渗透于明代士人的政治心理,而且也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心理上。换言之,“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旨有为了树立起正统的华夏文学典范的一方面。兴复古学、尊尚汉唐,实与强化华夏民族的文化正统不无关联。这种思想在满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明末,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如陈子龙不屑于“胡服胡语”(卷二《宣城蔡大美古诗序》)[10],而崇尚“当大汉之隆,宣导盛美,文词玮丽”(卷二六《白云草自序》)[10]的诗文。这是复古派尊“汉唐说”的一种深层因素,以前的论者却很少看到这一点。
与“比隆三代”的思想相联,陈子龙提出了“国家之文”的说法。所谓“国家之文”,即指“睹山川都邑之盛,典文礼乐之华,宜有雍容歌颂之业揄扬圣朝”之文、“润色鸿业”之文(卷二六《白云草自序》)[10]。他在另一篇文章所说明代“文且三盛”,讲的其实也就是“国家之文”。振兴“国家之文”,是从前后七子到复社一以贯之的思想。陈子龙认为,由于“讙呶之者申申起,卒难夺其众且久”(卷二六《白云草自序》)[10]的原因,“国家之文”虽经弘治、嘉靖两度振起却未能臻于极盛。为此,前后七子的未竟之业需要有后继者加以光大,才能使“国家之文”可望“灿然与三代比隆”(卷二六《白云草自序》)[10]。这可以说是明代文学之所以到复社时出现第三次复古思潮的重要原因,而且,“国家之文”与“文人之文”之异也是复古派与唐宋派、公安派之争的焦点。
复古派提倡“国家之文”之同时,还主张文学应张扬“元气”和“元音”。李梦阳以为天下有二病,“元气之病“居其首,此病体现在士风上则为“口呐呐不吐词”、“不喜人直,遇事圆巧而委曲”,体现在文风上则为淫靡萎弱(卷三九《上孝宗皇帝书稿》)[6]。他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实有起衰救弊的用意。很显然,论气之雄,莫过于秦汉之大块文章;论格之高,莫过于盛唐之李杜诗歌。故提倡汉文唐诗,不仅可以起到文学自救的作用,而且一定程度上还会收到疗救“元气之病”的效用。到了党争激烈、士习日偷的明末,复社倡导“元气说”尤力。陈子龙认为,元气不张,致使“小人以文章杀人也日益甚(卷二一《诗论》)”[2];他批判,“近世以来,浅陋靡薄,浸淫于衰乱”,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元音之寂寥”,主张须有一种“长育之气”灌注于篇章之中,以致“文章足以动耳,音节足以竦神,王者乘之以致其治(卷二五《皇明,诗选序》)”[2]。他的盟友吴伟业也主张,“诗之为道”应当“养一代之元音”,应当“追国初之元音,还盛明之大雅”。陈、吴所言“元音”,指的是元始、雅正之音,充盈着元气之音,能体现“国家之文”正大博雅气格之音。此,远一点说,则是诗、骚之音,其后为汉魏之音、盛唐之音,在明则为国初、弘治、嘉靖之音。以此看来,复社取法七子和尊尚汉唐、远祧诗骚完全是一致的。
当然,对于取法七子的做法,复社成员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分歧,钱谦益、黄宗羲等人反对七子复古派甚力,但总体上看来,绍绪七子、宗法汉唐的倾向在复社中占有主流地位。在复古派重要基地南直、山东、河南、广东等地发展起来的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松江几社、山左大社、雪园诗社、南园诗社皆归属复社,成为复古派的主要势力,张溥、张采、吴伟业、吴应箕、陈子龙、侯方域、宋继澄、陈子壮、黎遂球等人则为其中坚。即使钱谦益、黄宗羲,他们在倡导“天地元气”、“国家之文”以及主张崇经返雅方面也与复社其他重要人物的观点极为一致。
(二)宗旨论:祖述六经,力返风雅
上文着重言复社与前后七子的继承性,侧重的是复社取法七子的深层原因的探析。若进一步看,则不难发现,复社的文学思想与前后七子相比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总的来说,复社文学复古的最终指向是“力返风雅”,文学审美的最高追求是“和平温厚”(卷二八《程翼苍诗序》)[4],在前后七子的基础上向前再推进了一步,落到了祖述六经、推崇诗骚的根本上。因此说,复社的复古可谓是“复元古”了。
张溥极为推崇“诗三百”和屈原,对诗骚之后的诗歌则有所否定。《宋九青诗序》指出:“以予观之,《三百首》之后,作诗而不愚者,独屈大夫原耳。下此拘音病者,愚于法;工体貌者,愚于理;唐人之失,愚而野;宋人之失,愚而谚。愚而野,才士所或累也;愚而谚,虽儒者不免焉。夫谚可以为诗,则天下无非诗人矣”(《古文近稿》卷三)[3]。古人奉诗、骚为正途,不惟张溥一人,但他对汉以后诗歌史作如此观却不免失之偏颇,不过,在下文中他同时承认“剥穷则复”、“穷极而变”的文学发展规律,表明对诗之“变”也有一定程度的肯定。而且从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来看,对汉魏文学有很高的评价,而非以一“愚”字一概抹杀。关于唐、宋之诗,张溥在此两皆非之,与“诗必盛唐”大相异趣。但细加琢磨起来,唐、宋诗人之优劣在他眼中依然是存在的:唐诗之“野”,尚不免为才士之诗;宋诗之“谚”,则根本不能再算诗了,否则,天下人人皆可称诗人。两相比较,他还是崇唐抑宋的。
张溥以《诗经》为诗歌的最高典范,是由其兴复古学的基本思想决定的。而所谓古学,说到底指的就是经学,他指出:“今右文之世,学始五经”(《古文近稿》卷三《皇明诗经文征序》》[3]。此带有在思想上正本清源的意图,在文学上推崇《诗经》则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他批评了当时一些不尊经、不宗圣的妄说:“近有妄人,轻议周、孔不能诗,闻者笑之。周公之诗见于《三百篇》中;孔子《龟山》、《临河》诸操,学者讽焉。”又说:“周公相成王,制礼乐,首以诗为端”,“孔子续以《春秋》,……《春秋》据事直书,无声律可言,举以续诗,则何昉乎?”(《古文近稿》卷三《宗九青诗序》)[3]看来,张溥言诗,并非纯粹的声律之诗,而是体现儒家文化精髓和古代圣贤思想灵魂的政教德化之诗。这大约便是他认为“《三百首》之后,作诗而不愚者,独屈大夫原耳”的立足点。而这种尊经宗圣思想支配下的文学观与崇祯年间经学复兴的背景实有一定的联系。
钱谦益虽然在对待前后七子的问题上与张溥、吴伟业、陈子龙等复社巨子有着明显的分歧,但若只看到他们的对立面显然不够。作为东林魁目和复社领袖,钱谦益的政治思想与张溥等人是相同的,个人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这就决定他与张溥等人对文学的认识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必然彼此相通,比如说他论诗以《三百篇》为祖,论文以六经为祖,即与张溥等人并无二致。他的《袁祈年字田祖说》一文以“祖”、“宗、“小宗”论文学源流,没有像张溥那样对六经以后的诗文几乎持否定的态度,但他提出“各本其祖”、“尊祖敬宗”、“六经其坛墠”的观点,无疑与张溥以《三百首》为最高典范的看法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同时,他反对“必秦必汉必唐”的七子派,但也并不赞成“自我作古”的公安派,讥前者为“以人之祖祢而祭于己之寝”、后者为“被发而祭于野”,认为二者在“不识其祖”一点上本质是相同的。在他看来,欲“驰骋于文章”先必由“求其祖”始,而“祖”就是六经;“求祖”的办法则是“等而上之”、“反而求之”,沿波溯源,殊途同归(卷二六)[11]。“反经求祖”是钱谦益重要的方法论,也是他学术思想的一贯主张,其文学思想受其影响。
复社“尊经”的思想,从文学目的而言,最终是为了“力返风雅”,特别是为了继承《诗经》以来的美刺传统和抒情精神。陈子龙论诗持“美刺说”最力。周立勋、徐孚远等人在几社中同为陈子龙诗友,同时亦为复社成员,子龙为其诗作序力倡“诗之本”:“盖忧时托志之所作也。苟比兴道备,而褒刺义合,虽途歌巷语,亦有取焉。……夫作诗而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联类而见其志,是则《风》不必列十五国,而雅不必分大小也。虽工而余不好也。”(卷二五《六诗序》)[2]《白云草自序》亦云:“诗者,非仅以适己,将以施诸远也。《诗三百篇》,虽愁喜之言不一,而大约必极其治乱盛衰之际。远则怨,怨则爱;近则颂,颂则规。怨之与颂,其文异也;爱之与规,其情均也。”(卷二六)[10]在《佩月堂诗稿序》中,他高度肯定了情真辞丽的《风》诗:“盖古者民间之诗,多出于絍织井臼之余,劳苦怨慕之语,动于情之不容己耳。至其文辞,何其婉丽而隽永也,得非经太史之采,欲以谱之管弦,登之燕享,而有所润饰其间情欤?”(卷二五)[2]
陈、钱之外,复社代表作家吴伟业亦奉风雅为宗。他在给陈名夏、彭宾、宋存楠等复社成员的诗文作序时一直宣扬这种观点。《陈百史文集序》开宗明义地“正告天下”:“俾知大雅复作,斯文不坠。”(卷二七)[4]《彭燕又偶存草序》充分肯定:“云间之以诗闻天下也,三四君子实以力还大雅为己任,遭逢世故,投渊蹈海,其英风毅魄,流炳天壤,可以弗憾。”(卷二八)[4]《致孚社诸子书》则称道王世贞“专主盛唐,力还大雅”(卷三二)[4]此外,还有:扬扢风雅”(卷二九《白林九古柏堂诗序》)[4]、“还盛明乎大雅”(卷三二《与宗尚木论诗书》)[4]等说法。综合起来看,吴伟业力主风雅,体现了很强的文学使命感,而且包含了忠臣志士人格精神的内涵。强调诗歌的抒情本质,也是吴伟业提倡风雅的内容,《宋辕生诗序》云:“古来诗人自负其才,往往纵情于倡乐,放意于山水,淋漓潦倒,汗漫而不收,……决焉自放,以至于此也。”(卷二八)[4]这种基于对诗人悲剧命运的深刻剖析而得出的对诗歌精神本质的认识,是明末清初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在诗歌审美方面,复社代表作家继承“诗教说”,崇尚“和平温厚”之美。值得思考的是,复社时处亡国之际,身罹党争的政治旋涡,谈诗论文为何却要提倡“和平温厚”?诸如“诗教”、“声教”、“和平温厚”、“温柔敦厚”、“垂教易俗”、“和平深婉”、“温远”、“德和”、“发于哀乐而止于礼旨”、“温柔之音”、“中和之极”、“意存温厚”、“风旨深永”、“和平淳至”、“和而能壮”、“怨而不伤”、“颂而不谀”、“和平”、“穆如清风”、“不比于怨”等语词为何频频出现于吴伟业、陈子龙、钱谦益等人的文论中呢?有论者以为提倡温柔之旨是钱谦益入清后诗论的一种转变[12],这其实有所误解。其原因一是忽视了钱谦益与陈子龙、吴伟业等人的文学思想的共同处,二是忽视了他们之所以提倡“温柔敦厚”诗风的时代因素。按照《牧斋初学集》卷三十《徐司寇画溪诗集序》说法,由于受到兵燹和党祸的直接影响,明末的文学创作有两种气息随之滋生蔓延:一曰“兵象”,二曰“鬼趣”,其表现特征是“噍音促节”、“凄声寒魄”、充满“幽阴鬼杀之气”,这种诗风、文风不仅与雅正传统相悖,而且已显露某种“亡国气象”,不免令“有识者”深以为惧。所以,必将其“荡为和风”、“化为清尘”,才能既救文弊,亦救世弊。
有趣的是,陈子龙《皇明诗选序》与钱谦益的《答司寇画溪诗集序》几乎对同样的文学现象表示了完全相同的关注,其文曰:“世之盛也,君子忠爱以事上,敦厚以取友,是以温柔之音作,而长育之气油然于中,文章足以动耳,音节足以竦神,王者乘之以致其治。其衰也,非辟之心生,而亢厉微末之声著,粗者可逆,细者可没,而兵戎之象见矣。王者识之,以挽其乱,故盛衰之际,作者不可不慎也。圣天子方汇中和之极,金声而玉振之,移风易俗,返于醇古。是编也,采在遵人哉。”(卷二五)[2]比较一下,“兵戎之象”与“兵象”,“亢厉微末之声”与“幽阴鬼杀之气”,“盛衰之际,作者不可不慎也”与“有识者审音歌风,岌岌乎有衰晚之惧焉”,“金声玉振”、“移风易俗”与“荡为和风”、“化为清尘”——立言、立意,陈、钱二人皆何其似也。再如,吴伟业《白林九古柏堂诗序》亦云:“曾未百年,而其俗伤于呰窳,其地逼于舄卤,愁苦焦萃之声作,而休风不可复见矣。”(卷二八)[4]他们的批判态度和所提倡的文风在此竟然如此一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复社社会观、政治观在文学方面的反映。
概括言之,复社核心作家之所以倡导温柔敦厚、和而能壮的诗风和文风,从思想渊源来说,无疑是对儒家传统诗学、美学精神的继承;从时代因素来说,则是复社兴复古学、振兴“国家之文”、培育“天地元气”、挽救明王朝“岌岌乎有衰晚之惧”的需要,所以,这种文学审美的追求,不是对“诗教说”的照搬,而是有着重要的时代内容和现实价值的。
(三)创作论:性情、学问与世运
一般认为,灵心、世运和学问“三者相值”(卷四九《题杜苍略自评诗文》)[3][13]是钱谦益有关创作论的最基本的命题。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钱谦益这种文学观点的深刻内涵与他作为东林、复社的重要角色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同时,这种文学观点是否为钱氏独具,与他同时的其他复社作家是否有类似的看法。而这两个问题,也就是本文有关复社文学思想需要弄清的第三点。
(1)灵心(性情):“灵心”的提出,受到了哲学上阳明心学和文学上公安派“性灵说”的影响,但钱谦益“灵心说”有了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灵心为统一于学问和世运的灵心,二是灵心与“元气”、性情与“言志”不可分。这是因为钱谦益为东林和复社的重要魁目,他的诗学不能脱离其思想的倾向性,他所讲的“灵心”和“性情”包含了“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来,政治之污隆,道术之醇驳”(卷三五《瑞芝山房初集序》)[11]等丰富的内容,尤其包括“忠君爱友忧时怀古之志意”(卷三二《王元昭集序》)[11]的时代精神。
(2)学问:钱谦益讲的“学问”、“学殖”,是与灵心、世运统一于一体的:与灵心不可分,强调的是活学问;与世运不可分,强调的是真学问。为此,钱氏既批判王世贞“《四部》之书……即而视之,枵然无所有也”(卷三一《汤义仍先生文集序》)[11],也指责“卓吾之删割,使人呰耳剽目,不见古书之大全(卷四三《颐志堂记》)”[11],故其谓学问突出了以经史为本和经世致用的特点。
(3)世运:简单地说,“世运”指的是“政治之污隆”、国家之兴衰的时代气运。钱谦益强调灵心(性情)、学问与世运的统一,反映了他对作家与时代、文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高度重视。“世运”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文学应当弘扬“天地间之元气”。其次,文学应当指陈“时政之疾病”,以起到“救世之针药”(卷四二《王侍御遗诗赞》)[13]的作用。
钱氏上述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是带有一定普遍性质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复社核心作家多作此观。现罗列几例以作比较:
钱谦益《胡致果诗序》:“(诗)其征兆在性情,在学问,其根柢则在乎天地运世。”(卷十八)[13]又《题杜苍略自评诗文》:“夫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卷四九)[13]
吴伟业《宋尚木抱真堂诗序》:“君子之于诗也,知人,论其世,固已;参其性情,考其为学,而后论诗之道乃全。”(卷二八)[4]《龚芝麓诗序》亦云:“夫诗人之为道,不徒以其才也,有性情焉,有学识焉,其浅深正变之故,不于此考之,不足以言诗之大也。”(卷二八)[4]
陈子龙《吴次尾己卯诗集序》:“要之,读次尾诗,其学问可考而知也,即其性情亦不能外,然岂可与今之人同日语哉!”[14]
张溥《宋九青诗序》:“无才之人,不可与言诗,恶其无文也;无情之人,无可与言诗,恶其非质也。虽然,才至矣,其学不行;情至矣,非诗不立。”(《古文近稿》卷三)[3]
此外,吴伟业在《沈伊在诗序》中还直接用“世运”一词论诗(卷三十)[4],有时则采用“时”这一与“世运”相近的提法。张溥与黄宗羲亦以“世运之升降”论文风之变化[15]。
综合看来,钱谦益、张溥、吴伟业、陈子龙等人论诗强调性情、学问和世运几种因素是相同的,而之所以如此,则与明末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背景有关,与东林、复社的思想、学术和文学倾向亦有关。首先,明末的社会现实使文人的角色、处境发生了变化,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也显得更为密切。具体来说,明末处国家衰亡之时、朝野多事之秋,天下兴废,人际沧桑,情状千端,发为文章,故论文学不能不重视“性情”;国家兴衰系于人才,关乎学术,东林、复社从救世精神出发,力辟空疏之弊,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经经纬史,正本清源,故论文学亦不能不重视“学问”;明末是内外斗争最复杂、价值观冲突最激烈、人格分野最明显、人生处境最险恶的特定历史时期,文学需要匡护正气,讴歌忠臣义士的不朽精神,鞭挞邪恶,担负文学自救和救世的使命,同时,文人的生存境遇趋于恶劣,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以及作品流传无不受到时代因素的制约,故论文学更不能不重视“世运”。其次,明末后期文学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在明中期以后文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三种基本的倾向:一是“法古”与“师心”(卷二一“侯泓”条)[16]、“体法”与“性情”[14]的合流。二是“文人之文章”与“豪杰之文章”(卷三十《顾太史文集序》)[11]的合流。三是“文人之诗”与“儒者之诗”(卷十九《顾麟士诗集序》)[13]的合流。此几种合流,即意味性情、学问、世运三种因素的统一。性情、学问、世运合一说,在我国古代诗论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揭示了诗歌创作过程中主、客相统一的基本规律。它对清代文学理论的影响也很明显。
[收镐日期]:2004-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