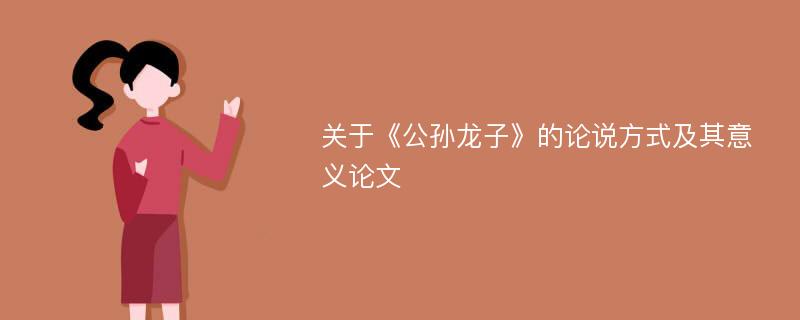
关于 《公孙龙子 》的论说方式及其意义 *
张长明 肖中云 曾祥云
摘 要 “假物取譬”是指假借某具体事物作比喻来说明和揭示一个道理。在《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三篇中,公孙龙都采用了这一独特的论说方式。因此,具体掌握并切实遵循“假物取譬”的论说特征,不仅是我们开启《公孙龙子》“潘多拉盒子”的一把钥匙,而且是正确理解公孙龙名学思想,准确把握其理论特质和研究风格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公孙龙 《公孙龙子》 论说方式 假物取譬
在我国先秦典籍中,《公孙龙子》素称难读。在我们看来,这其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对《公孙龙子》独特的论说方式,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必要的重视。对《公孙龙子》的诸多争议及误解,也与不了解其论说方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因此,了解和把握公孙龙独特的论说方式,既是研读《公孙龙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揭开《公孙龙子》“神秘”面纱、深化公孙龙名学思想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假物取譬”在《公孙龙子》中的运用
现存《公孙龙子》一书共六篇。一般认为,其中的《迹府》篇系公孙龙弟子记录公孙龙言行的材料,并非公孙龙本人作品。也正因为此,许多《公孙龙子》研究者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其它五篇上。这本是十分正常、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作为公孙龙弟子记录公孙龙言行的材料,《迹府》篇所述并非就不重要。实际上,从史料来源的真实性上来说,《迹府》中所载有关公孙龙的言行,较之历史上散见的一些有关公孙龙的传闻,在真实性程度上或许更为可靠,可信度更高。这虽然是我们的一种推测,已无从确考,但《迹府》篇中的某些记载,确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某些“提示”,也许正是我们开启通读、通解和研究《公孙龙子》的一把金色钥匙。
《迹府》云:“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这段话透露出的某些信息,如公孙龙是一位“辩者”,并且以“善辩”著称,这些描述已获得我国研究者的普遍认可。但是,对于其中的“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是置之不理,个别研究者虽稍有提及,也是一笔带过,而未将其与《公孙龙子》一书联系起来,实质性地贯彻到自己的实际研究中去。在我们看来,上引《迹府》中那段文字所透露的更重要的信息,还在于“假物取譬”,它揭示的是《公孙龙子》书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论说方式,直接关系到对公孙龙名学的理解及其思想特质的把握。可以说,如果不把握公孙龙的这一论说特点,那么,对于公孙龙思想的认识、理解,就必定是流于表面,沦入误解、强解,与公孙龙本意将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所谓“假物取譬”,是指借用某具体事物作比喻来说明和揭示一个道理。与先秦诸子一样,公孙龙也是“疾名实之散乱”而展开其名学研究的。《公孙龙子·名实论》云:“夫名,实谓也。”又《墨子·经说上》云:“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又《经说下》“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谓”即称谓、谓述。不难理解,“名”即事物的名称,“实”即客观具体事物,名的功能、作用即在于称谓或者说指称具体事物,而客观具体事物则是名所谓述或者说指称的对象。因此,公孙龙对“名”的认知、理解,与墨家及其他先秦诸子都是完全一致、没有区别的。作为事物的名称、标记,名的存在形式即是汉语言系统中的名词,表诸于文就是汉字。从现代符号学理论来说,我国先秦名学即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语词符号理论。而作为一种语词符号理论,先秦诸子所论述的名实关系,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名与具体事物之间的指称或者说代表关系;先秦名学所探讨的名与名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指不同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不同事物名称之间的关系。显然,在两千多年前的我国先秦时期,我们的先人还不可能有当代人这种符号意识,更重要的是,从汉语言文字的生成特征来说,在当时也很难找出一种合适的表达形式或者说话语体系,专门用来阐述名学问题,而对于如名与名之间关系等名学问题,如果没有专门的话语表达体系,即使是现代人来表述也会有难度的。正因为此,公孙龙、尹文子和后期墨家学者等先秦名学家,便采取了一种“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来阐发其名学思想。
《迹府》篇说,公孙龙“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这就告诉我们, 公孙龙《白马论》中的“白”、“马”、“白马”诸名的使用,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物之色白性征、马和白马类事物,而是指“白”名、“马”名、“白马”名自身。而所谓“白马非马”,并不是指白马与马这两类事物之间的相非关系,而是指“白马”这个兼名与单名“马”之间的相非关系。换句话说,公孙龙是假借白马和马这两类事物,即借白马类事物以喻兼名“白马”、借马这类事物以喻单名“马”,来阐明兼名“白马”与单名“马”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兼名、单名,即《荀子·正名》所说:“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名是指由一个音节或字表示的名,如“白”、“马”等就是单名。兼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名组合而成的名,如,“白马”就是一个兼名,它是由“白”和“马”这两个单名组合而成的。因此,公孙龙之论“白马非马”,实质是通过“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来阐明兼名与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
《白马论》云:“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这是公孙龙为阐述其“白马非马”之论而作的第一层、也是最重要的论证。显然,如果仅从字面上,即不按照“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去理解,则必然引发如下两个问题:其一,“白马非马”只能被理解为“白马不是马”。许多研究者都将这种理解看作是诡辩,而在我们看来,这根本就是一个误会。白马不是马,就像说“上海人不是人”一样,这完全不是什么诡辩,纯粹是乡间泼妇之间吵架损人的一种脏话。实际上,当有研究者说“白马不是马”是诡辩时,该研究者似乎并不明白什么叫诡辩。在我国古代有“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论,在古希腊有“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之说,这是公认的诡辩之论,因为其中既有“诡”、更有“辩”,那无穷无尽的“一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只不过是论者将其绝对化了,从而沦于诡辩。我们很想请教将“白马不是马”视为诡辩的研究者,它究竟“诡”在哪里?又“辩”在何处?而正如公孙龙本人所言,“白马非马”之论,乃是他得以成名的资本。试想:如果公孙龙本人所理解的“白马非马”即是“白马不是马”之义,他在孔穿面前还敢如此得意洋洋、豪气冲天吗?绝无可能!因此,如果仅从字面上去理解《白马论》,必将造成对其中心论题“白马非马”的误解,并引发更多的困惑而难以自圆其说。其二,如果不按照“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而仅从字面上理解,那么,对于公孙龙提出的论据“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我们无法圆融其义。“形”即事物之形,先秦诸子多有“名者,名形者也”之说,这无疑是与汉文字的象形特征密切相关。因此,“命形”即是命名事物形状之意。然而,作为客观存在的马类动物,它如何去命名事物之形呢?这明显是义理不通。同样,“命色”即命名事物颜色之意,作为事物的一种性征,白色本身又如何去命名物之色征呢?这同样是义理不通。可见,简单地从字面上、而不依照“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去解读《白马论》,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很难想像、也无法理解,我们的许多研究者究竟是如何通解《白马论》的。
在先秦诸子中,采用“假物取譬”论说方式探讨名学问题的,并非公孙龙一人。尹文子以“好”、“牛”、“马”、“人”分别喻指不同的单名,而用“好牛”、“好马”、“好人”分别喻指不同的兼名,具体探讨了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合成规则,并指出了不同单名以及兼名与单名之间的“相离”关系。后期墨家学者也采用了“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具体探讨兼名与构成它的单名之间的关系。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世界上决不存在什么非牛非马的牛马之物,在我国汉语言文字系统中也决找不出“牛马”这样的名。实际上,与公孙龙一样,后期墨家学者也是采取了“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即借“牛马”以喻“白马”、“坚石”这样的兼名,而构成“牛马”的“牛”、“马”则是单名之喻。由此可见,“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既非公孙龙所独创,也非《公孙龙子》一书所特有。
我们知道,《名实论》是公孙龙名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也是《公孙龙子》其它各篇立论的根本依据。正因为此,有研究者将《名实论》看作是公孙龙名学的纲领性篇章,当作《公孙龙子》全书的绪论。这种理解与认识是正确的,完全符合《名实论》在《公孙龙子》思想体系中所占据的实际地位。在《名实论》中,公孙龙对“物”、“实”、“名”等基本术语作出了明确的界说,探讨了名实关系,提出了“正名”的原则和方法。《指物论》篇名的基本涵义是论对事物的指称,其核心内容即是对名物关系的探讨。公孙龙由《名实论》对于名与具体事物之间关系的讨论,进入到《指物论》关于名与物之间关系的一般性阐发,这是对名与指称对象之间关系的一种更高概括,因此,可以将这两篇看作是“姊妹”篇。《坚白论》的核心是探讨兼名的合成问题。公孙龙认为,坚、白两种性征各有其质的规定性,是各自独立分离的;人们对它们的感知,也是通过不同的感知方式获得的,因此,表征事物质坚的“坚”名与表征事物色白的“白”名,也是各自分离的,二者不能结合。这样,由“坚”、“白”、“石”三个单名只能结合成“坚石”、“白石”这两个兼名,这即“坚白石二”这一中心论题的基本涵义。正如上面所分析,《白马论》之论“白马非马”,主要是揭示兼名“白马”与构成它的单名“马”之间的关系。从《通变论》所论及的具体内容来说,既有对兼名合成规则的详细分析,也有对兼名与单名之间关系的探讨;它既是对《坚白论》和《白马论》所研究问题的一种综合,同时在具体研究内容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延伸与拓展,作了更为深入的具体分析⑦。
(二)论说方式对于研读《公孙龙子》的意义
既然《公孙龙子》书中采用了“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那么,我们在研读《公孙龙子》时,就应遵循这一论说方式来理解公孙龙名学思想,才能把握其思想的实质与本意,否则,就会造成对公孙龙及其思想的误解乃至曲解。研究《尹文子》名学和后期墨家名学,也同样如此。
公孙龙不仅在其《白马论》中“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而且在他的《坚白论》和《通变论》中,同样也采取了“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在《坚白论》中,公孙龙假物之质坚、物之色白以喻表征事物性征的名称“坚”名和“白”名,并以视、拊异任及坚、白二性各有自身规定性为依据,推断出“坚白石二”这一中心论题。在《通变论》中,公孙龙用“一”、“左”、“右”、“羊”、“牛”等喻指单名,而以“二”、“左与右”、“羊合牛”、“青以白”等喻指兼名,深刻揭举了兼名的独立符号性质,科学阐发了他的“通变”思想。
既然公孙龙在《白马论》中采取了“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那么,遵照其论说方式来解读《白马论》,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也是必须如此而没有其它选择的。《公孙龙子》原文本没有标点符号,现有的标点符号是后来的研究者加补上的。而依“假物取譬”之义,上引《白马论》一段的严格文字表达应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需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里的“‘白马’非‘马’”与前述引文中的“白马非马”,实际上是表述两种完全不同的命题。“白马非马”是一个综合命题,而“‘白马’非‘马’”属于分析命题。艾耶尔指出:“当一个命题的标准仅依据它所包括的那些符号的定义,我们称之为分析命题;当一个命题的标准决定于经验事实,我们就称之为综合命题”①。作为一个综合命题,“白马非马”命题的真假,是通过对白马与马这两类事物关系的实际观察,即凭经验事实来确定的。而作为一个分析命题,“‘白马’非‘马’”命题的真假,不是依赖于经验事实来确定,而是依据于对它所包括的那些符号的定义来确定,即根据对“马”、“白”和“白马”三个名称的定义或规定来确定该命题的真假。如此一来,上述增补单引号的这段引文就变得很好理解了,其语义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马”名是命名事物形状的,“白”名是命名事物颜色的,命名事物颜色的名不是命名事物形状的名,所以说,“白马”名不是“马”名。《白马论》进一步指出:“‘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白马’者,‘马’与‘白’也。”为帮助读者理解,我们在引文中增补了单引号。“与”即结合;“未与”即没有结合。在这里,公孙龙已说得非常清楚了:“马”在与“白”名结合之前,它就是“马”名自身,“白”在与“马”结合之前,它就是“白”名自身;而当“马”与“白”相结合,就生成了一个新的名即“白马”;因此,“白马”名是由“白”和“马”两名组合而成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论的思想实质,并不是探讨“白马”与“马”这两个名称符号之间的关系,而是假“白马”以喻兼名,借“白”、“马”以喻单名,因此,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论的本意,是揭示兼名(如“白马”)与构成它的单名(即“白”、“马”)之间的关系。在公孙龙看来,兼名“白马”虽由单名“白”和“马”相结合而成,但兼名“白马”中的“白”和“马”已不再具有独立单名的性质,而只是作为构成兼名“白马”中的组成部分存在,换言之,兼名“白马”与其它单名一样,也具有独立符号性质,用公孙龙《白马论》的话来说,就是“白马”既不是“白”,也不是“马”。而用他在《通变论》中的话来表述,那就是“二无左”、“二无右”即“二无一”。并且,很明显,按照上述解释,令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与不解的《通变论》篇名的涵义也由此而得解。因为,构成兼名的两个单名原本是具有独立性质的事物名称,而当它们结合成兼名之后,就只是作为兼名的组成部分而存在,都不再具有独立名称符号性质了,这就是“通变”的本来涵义。公孙龙“白马非马”,在后期墨家学者那里,就是“牛马非牛非马”之论。需要指出的是,后期墨家完全是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来展开其分析论证的,即《经说下》:“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数‘牛’数‘马’,则‘牛’、‘马’二,数‘牛马’则‘牛马’一,若数指,指五而五一。这就是说,上述论题虽然在表述上用词不同,甚至公孙龙与后期墨家的分析思路也不一样,但殊途同归,它们的思想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换言之,“假物”虽不同,所取之“譬”即它们所揭示的道理却是相同的。在《坚白论》中,公孙龙同样采取了“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因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展开分析了。总之,在我们看来,由于公孙龙等先秦思想家采取了“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因此,在研读《白马论》、《坚白论》、《通变论》诸篇时,必须撩开其假借的那一层面纱,深入到它所喻示的实质性思想内容中去加以领悟和把握,否则,就会不明其所以,难得其要领。
如果我们将《公孙龙子》各篇的思想内容、写作文体和论说方式作一简单的对照分析,就可发现,实际上公孙龙在这三者之间做了一种精心的设计、巧妙的布局和刻意的安排。这就是,《名实论》和《指物论》两篇都是关于名实关系、名物关系的一般原则性的讨论,并不涉及到对具体事物名称的使用与提及问题,因此,这两篇都没有采用“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在写作文体上也都不是客问主答式对辩体;而《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三篇,⑧则都是对兼名合成规则、兼名与单名之间关系等较为具体问题的探讨,也都涉及到了对“白马”、“马”等具体事物名称的提及与使用,因此,这三篇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并且也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对辩体这种文体。公孙龙对《公孙龙子》五篇这种巧妙而精致的设计、安排,可谓用心良苦,它对于我们整体把握其思想脉络与体系特征,深刻理解其思想内核与理论特质,具体领略其研究风格与个性魅力,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②Р·苏佩斯:《逻辑导论》,宋文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85页。
标定系统主要由加载系统、信号放大电路、数据采集卡组成,通过将标准的标定力和力矩加载到传感器上,经过信号放大电路进行放大和滤波,最后经数据采集卡将电压信号采集到计算机中,从而得到对应的输出电压值。
苏佩斯指出:“通常在使用语言时,是不可能混淆事物和它的名称的。我们使用名称谈论事物,而看来真的只有白痴才会比如说把威廉沙士比亚和他的名字搞错了。然而,当我们想要一般地提及名称或者表达式,而不只是使用它们时,我们不必是白痴也会发生混乱。那就是,当被命名的事物本身是语言表达式时,就会引起某些特殊的问题。给表达式命名的标准方式是使用单引号或双引号”②。不难理解,在我国先秦尚无标点符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像“白马非马”和“‘白马’非‘马’”这两个语言表达式,无论在言语表述上、还是在文字表达上,要像现代人这样严格区分名称的提及与使用,实际是非常困难。也就是说,就当时的特定条件来说,不论是“说”出来、还是“写”出来,“白马非马”和“‘白马’非‘马’”的表达方式,都是完全一样的,即:白马非马,而不能从表达形式上将二者加以甄别与区分。由此看来,公孙龙等先秦思想家之所以采取“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也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而这同时表明,两千多年前的公孙龙等先秦诸子,就能将名称的提及与使用作严格的区分,充分体现了他们思考的严谨和分析的缜密,这也正是公孙龙《名实论》所说“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真实写照。③
最为关键的是,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如果不遵循“假物取譬”的论说特点去作解,我们就无法把握《白马论》、《坚白论》和《通变论》诸篇的思想实质和核心要义。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说公孙龙有“诡”的话,那决不是“诡”在他的“白马非马”、“坚白石二”、“二无一”这类中心论题上,而是“诡”在先秦尚无标点符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十分机智地采取了“假物取譬”这种论说方式,并且他本人不做任何解释或说明,让人们为之“揣度”了两千多年仍不得其要领,一直处于猜测之中。这不仅契合了历史上有关公孙龙擅长论辩的传说,同时也印证了其弟子对公孙龙“因资材之所长”的描述与评价,的确不失客观与公正,他们对自己的老师似乎并没有丝毫的抬捧与夸耀之意。
(三)论说方式与《公孙龙子》体系的关系
③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5页。
我国学界一般认为,在《公孙龙子》五篇中,《名实论》是全书的理论基础,在写作方式上,没有采取客问主答式对辩体,而其它四篇则都是由对辩体写成。在我们看来,学界有关《名实论》、《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四篇的普遍性看法,⑤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完全可信的,因为其相应的特征表现十分清楚、明了。但是,对于《指物论》也为对辩体一说,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从《坚白论》、《白马论》和《通变论》三篇所呈现的对辩体写作特征来看,《指物论》的写作风格明显不符。前三篇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客难主答、主客针锋相对的对诤特点,在《指物论》中却荡然无存,而且前三篇都是以客方对各篇中心论题的质问作开篇,而在《指物论》中,则是以论主提出中心论题为开篇,且全篇都不见有客方对主论的质疑或否证⑥。因此,在我们看来,《指物论》的文体并不是对辩体,而有关它的对辩体之说,实是一种误解、误会,是经不起推敲和不可信的。
梨花的声音怯怯的,好像是谁家的童养媳,小李的眼神却有些热,轻声对着梨花:别有什么顾虑,这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梨花对着小李点了点头,脸色依然沉重。老邓狠狠地瞪了小李一眼:什么过场,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是需要人坐牢的大事。小李对梨花伸了伸舌头,再次温和地笑笑。
采用PDCA循环管理方法干预小袋包装中药配方颗粒调剂的效果分析 …………………………………… 卢 兴等(11):1466
①A ·J ·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85页。
前15天给予匹多莫德颗粒(天津金世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30225)400mg/次,2次/d,然后减少至1次/d,共持续治疗1个月。期间同时应用抗生素、抗病毒药物进行对症治疗。
无论是智力阈限假设还是行为遗传学的研究,都为自杀的适应器理论提供了某种间接支持。不过,两个领域的研究都没有涉及适应器理论的具体内容,没有对内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不少研究者开始对影响自杀的进化线索和当前机制进行探讨(Brown, Dahlen, Mills, Rick, & Biblarz, 1999; Joiner & Silva, 2012)。
上述分析表明,“假物取譬”虽是公孙龙惯用的一种论说方式,但其真正的目的则正如《迹府》所说,“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④因此,公孙龙研究名学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为了成名,更不是为了“辩胜”,而纯粹是出于对名实问题的深入思考,甚至在《公孙龙子》全书中,我们都看不到公孙龙将名学问题与政治伦理等其它问题纠缠到一起的丝毫痕迹。“专决于名”的《公孙龙子》,无疑是我国先秦名学史上唯一一部专门探讨名学问题的专著,其历史地位不可低估。而如果我们将公孙龙“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与《公孙龙子》各篇的思想内容作些对照与分析,就会发现,“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与《公孙龙子》思想体系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颇有意义的关联。
⑯爱新觉罗·弘历:《汲惠泉烹竹炉歌叠旧作韵》,裴大中、倪咸生修,秦缃业等纂:《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4册,第26页。
④庞朴:《公孙龙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6页。
⑤林铭钧、曾祥云:《名辩学新探》,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0~168页。
⑥曾祥云:《先秦哲学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指物论〉新探》,台北:《哲学与文化》,1997年第2期,第140~111页。
⑦张长明:《〈公孙龙子·通变论〉的现代解读—从语词符号的角度》,湖南湘潭:《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第107~111页
我们可以认为,学科话语生产是隐藏在体系建构后的另一条发展线索。话语生产是知识生产的上位概念,知识、规则及价值都是学科话语的重要体现方面。米歇尔福柯认为:任何学科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社会规范。他强调一个学科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属于知识生产的范畴。目的是为了实现知识的新旧更替和知识的一体化、理论化、系统化与再系统化;而学科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意指学科的知识成为规定人们行为的规范,学科构成的话语产生了一个控制系统,它通过统一性来设置其边界。因此,学科话语的生产的关键在于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与规范养成、价值认同之间的一致性。
⑧张长明、李后生:《中国古代辩学论略》,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 B 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19)02-0065-06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公孙龙子 》的符号学解读 ”(项目号 18ZDB 007)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张长明,湖南工学院教授,博士;肖中云,湖南工学院副教授。湖南衡阳 421001;曾祥云,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 200433
[责任编辑 刘慧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