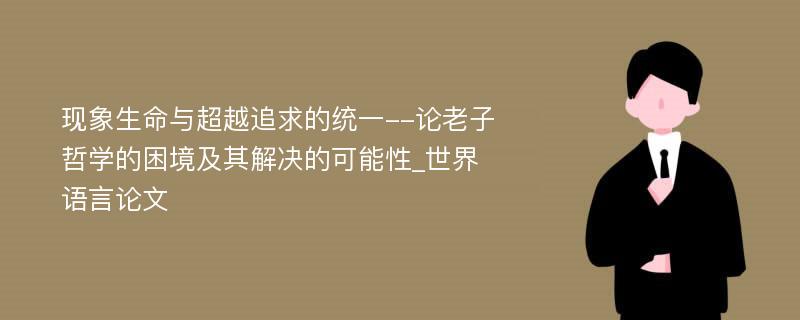
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追求的统一——论老子哲学的两难及其解决之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生活论文,老子论文,哲学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秦思想家普遍认为人应该依据对于真理的认识来行为,但对于究竟什么是人应当据以行为的真理,不同的思想家则有不同的回答。道家鼻祖老子强调在道本体论上的自然无为,认为真理即道,据道的行为则是自然无为。然而,这恰恰与老子提出这一看法的形式——“言”是相矛盾的。因为言作为辩诘,作为表达,是人之社会化的表现,是一种人文、一种有为。人文有为的“言”与自然无为的“道”,显然有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在“言”与“道”的关系上,老子的处境是两难的。本文希望通过对老子重要命题“不言之教”的分析,来论述其两难解决之可能,以印证真理通过实践而最终达到与现实世界一致的合理性。
一、“行不言之教”——现象世界中的两难与矛盾
关于老子处境的两难,我们可以在《老子》成书的传说本身得到启示:老聃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欲去践道,但是守关官员要他留下几句话,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可以把握得住的“人为”,只留下五千言便不知所终了。这一带有神话意味的见首不见尾的传说,至少表明《老子》的成书,是基于一种“被迫”、“强迫”或“勉强”。《老子》的五千言是勉强之言。我们只要细细阅读就能发现,这种勉强在《老子》书中非常明显,从书的开篇强调的“道可道非常道”(第1章)至中间的“绳绳不可名”(第14章)和“强为之名”(第25章),以及篇末的“道常无名” (第32章)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勉强之言一旦说出,就成了具有某种目的的施教,成了在现象世界中倡导某种行为的理论。勉强施言行教,又与道之自然无为相左,于是就有了“不言之教”。
“言”作为人的社会化存在方式,总是关联着四个方面:言者,言述者之主体;所欲言者,言所指称的对象;所言出者,主体所出之语言;言所欲者,主体语言之目的。
《老子》第2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章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在这里,立言的主体是圣人,所言出者就是这段文字,言所欲者即立言之目的就是倡导“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从文字表面看,仅用一个“是以”将前后文连缀起来,以说明两者间具有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且“圣人”被描述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被决定者。如果真是如此,那立言者呢?如果立言者就是“行不言之教”的圣人,那他为什么还要立言呢?有必要自己为自己立言吗?抑或真的像传说那样,“五千言”仅仅是为了骗取出关护照的一派胡言?如果立言以教人去“行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那么,立言者与被教者之间谁是圣人呢?实际上,老子在这里是把立言者放在立言之目的当中,使“是以”的上下文显得像是自然的因果关系,于是就巧妙地隐匿了立言的主体,从而在表面上回避了“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是自己为自己立言、自己对自己施教的两难悖论。
当然,以为老子有意运用文字技巧来回避两难悖论,这种看法似乎太肤浅了。应该说,人在一般言说时,主体总是隐匿不见的,正像人用眼睛看东西时,自己是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一样。因此,任何理论,其言所欲者如果返回言说者即主体自身,都会出现悖论。“行不言之教”当然也不例外。然而一般人的思维和言说由于主体隐匿,就避免了其思维和言说陷入悖论的危险。而《老子》则不然,它一口气说出了那么多的两难与矛盾,其目的显然不是要掩盖或回避矛盾,而是有意要把“行不言之教”的勉强和两难非常明显地烘托出来。
这个烘托,我们还可以通过“是以”前的一部分文字分析来展现,如美恶、善不善、有无、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等。这些都是现象世界的相对事象。它们作为事象的相对性,通过语言与概念而得到表达。而语言与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人为,一种置身于现象世界的相对事象。作为相对事象的言语与概念,通过特殊的“正言若反”(第78章)方式,即通过否定相对事象的实在性,来反衬出超越的绝对实在,以揭示现象世界的矛盾和悖论之性质,其目的则是以此引导人们的思维指向那超越事象的绝对实在及其自身的运动规律。这不能不认为是老子的一种苦心安排,这种苦心与古希腊“在论辩中证明真理”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如此,《老子》一书的写作,常常表现为使用自相矛盾的一些论断,诸如“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之类的说法。通过这样一些论断,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超越现象世界的绝对实在。这个引导过程与指向,亦可以理解为“道”;道者,实为导之者也。
那么这个“道”怎么又是“行不言之教”呢?这是因为,在老子那里,绝对实在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述的,这相当于康德哲学中那个不可以认识的“物自体”,但却又要求人们的思维指向它,要求由它来范导人的思维与行为,于是就只能是一种“不言之教”。这种“不言之教”,其实又是《老子》的“所欲言者”,即语言指称的对象或认识对象。有了指向的和认识的对象,就必然要认识对象中所包含的内在的必然的规律,而对象作为客体,它的自然无为性与人所认识的对象之表述的人文目的性是有差异的。在这种差异中老子必然陷入矛盾,为了解决或调和这种矛盾,老子采用了“不言之教”和“行不言之教”的方式。其实“言所欲者”才是老子所谓的“道”,这才是人生之大义。
本来,在《老子》中,“所欲言者”与“言所欲者”的区别并不明显,但我们把它们区别开来,目的在于说明“所欲言者”还不是“道”,只是主体指向的对象;这种对象往往是现象世界中的具体事物,而“道”更多的是隐身于“所欲言者”即对象之中(或背后)的一般的规律的东西,这就是所谓:“道隐无名”(第41章)。正因为这样,“所欲言者”本身是超越了言语置身的现象世界的。所以《老子》也只能通过勉强之言,把它以“不言之教”的方式说出来,这样,“所欲言者”也就由绝对实在即彼岸世界而进入到了现象世界,从而使“不言之教”与“行不言之教”的两难矛盾,即“言”与“道”的两难矛盾,由彼岸实在与此岸现象的对立,转变为同一现象世界之中的矛盾对立。按常理来说,这个转变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老子通过特殊的“正言若反”方式实现了这个转变,这似乎把客观世界中存在的对立与矛盾更加凸显了出来,但实际上却为本来无法解决的悖论提供了化解之可能。其最大的意义在于把两个不同层次即绝对实在与现存事象之间的对立,外化为同一层次即现实世界之中的矛盾,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二、所欲言者与所言出者之间的矛盾
在老子那里,所欲言者即言所指称的对象,或道或绝对实在本是超越现象世界的,但在老子的精神体验中,它还是有迹可循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21章)因为精神体验也属于现象世界,这说明作为绝对实在的道,在现象世界中有其真实的迹象可循,所以,所欲言者才可以当作所言出者。
本来,在《老子》的“不言之教”中,言之为言所关涉的几个方面关系是暖昧不清的,言所欲者与所欲言者都作为道,区别更为模糊;现在,把所言出者当作所欲言者,也当作道,情况就更加复杂了。显然,言者作为主体,所言出者是其所言,言者自身的样貌没有得到说明,那么言者所言如何达致言之所欲?即所言出者与所欲言者二者如何同一呢?
所欲言者即绝对实在,作为道是超越语言界限的,所以其践行的方式只能是“不言之教”。然而“不言之教”一旦推出,事实上又成了所言出者,由于所言出者也可被理解为道,这就与不言之教及道的本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1章)发生了矛盾。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所言出者。不言之教作为所言出者,它先隐匿了立言者(圣人),同时又遮蔽了所欲言者(绝对实在即道)。由于语言是人的社会化存在方式,不言者就只是一种失却社会性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一种人本自然,于是不言者就回归成绝对实在的一个部分。这说明所言出者作为道是与作为彼岸世界的人本自然和绝对实在对立的,这种内在的对立又不符合《老子》的本意。因为老子本体论上的道,是自然无为的,它是制约一切的主宰力量,同样也制约着人自身的言说行为及名言。言不是人最终的存在根基,只是一种方式,它存有所依,出有所指。言自身的有效性,也同样取决于自身生存的有效性。《老子》对此有明确的界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所以,在所言出者与人本自然和绝对实在之间,道在后者而不在前者。然而,若果真言之无道,那么何以为言?教者何名?人类生存所依赖者,就是道;人持生存,就要遵从绝对实在即道之要求。在这一点上,《老子》肯定所欲言者对于言所欲者的直接决定作用,并用“是以”来表示这种决定关系。但若是言之无道,如何能让人懂得“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第37章)、“孔德之容,唯道是从”的道理?是不是这两句话本身也是无道之言、碍道之言?当然不是,不然《老子》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自然无为的道既然决定一切,那么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语言也同样被决定。于是问题又产生了:被自然无为的道所决定的言,何以用与道自身规定性相反的方式来表现?自然无为的道作为超越性的绝对实在,是万物之始基,实为“一”。《庄子·齐物论》说:“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所以,道一经言语表达,本身就退隐为现象世界的相对事象。这样在庄子那里就有了第二个道,这种道就是语言,就是所言出者。这就是“一与言为二”。而把这第二种道付诸实践,即行不言之教。不言之教一旦推行,于是就产生一个五花八门的人为世界,这就是“二与一为三”。但从此以后,在人为世界里人们被言和现象世界所迷惑,原本意义上的道即绝对实在就更加难以得到。
可见,不但所言出者与所欲言者的关系会陷入两难的矛盾境地,而且与言所欲者的关系同样也会陷入两难的矛盾。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里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取消绝对实在(包括作为本然的人),即取消作为道的决定作用;要么取消人的言语行为。前者是老子所反对的,相对而言,他更倾向于后者。但是,人是现象世界中的言者,他只有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获得其生存发展,就是老子所认定的“道”,也只有通过语言表述才能为人所把握,才能对人的行为起作用。也就是说,“言”是“道”成立和表述的前提条件。可是这样一来,为言所传达的道已经是“此道”而非“彼道”了——它不再隐身于本然世界的超越性之内,而是显形于相对事象的现实性之中。这样,隐匿在现象世界之中的道(绝对实在)地位就被逆转了:不再是道决定人的行为(包括言语行为),而是人的行为决定道。这与老子的初衷——寻找正确行为的绝对根据背道而驰了。所以,所欲言者和言所欲者作为“道”,与所言出者(言语)的尖锐对立,在老子那里是没有得到解决的。
老子没法解决的矛盾,实际上也是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对立,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观点来看,这种对立原本就是无法解决的。这是一种人类硬要追求隐藏在现象世界背后的绝对实在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二律背反”,是人类现象性生活(实践)与超越性追求(真理)之间的矛盾。老子和庄子对这个矛盾的解决是企图通过言说者(主体)的隐匿把隐身于本然世界之中的道转移到现实的事象世界之中,使“言”与“道”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但事实上,人的认识与认识对象之间没有绝对的一致与同一,即使在理性思辨逐步完善的今天,同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本然的真理(道)与其认知表达(言)之间的矛盾。
三、解决两难对立的可能性
道不能言而又不得不言,言不能达道而又不得不用以达道。陷入这样的困难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人类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追求之间的矛盾关系。老子可能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将是人类认识的永恒难题,而人类生存之社会只有在不断地解决这个难题的努力中才能前进。但是,为什么语言只能是道的表现方式(且往往是碍道的或蔽道的方式)而不是道本身呢?原因在于语言所具有的双重性质:它作为一种物质现象(不考虑其所表达的意义),如山风呼啸、流水细语,是一种声波,是一种自然无为的道;而它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系统(所言出者),则是一种人文现象,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这种方式正是绝对实在之对立面,于是它就不可能是道。然而道既存在于一切当中,当然也存在于语言,因此语言也可以是道,条件则是语言要超越概念系统——不是退回到无意义之声波,而是指向它的目的——言所欲者,引导人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去“无不为”,用现代哲学语言表达,就是应该指向实践。所以,“道”与“言”的矛盾,其原因不在于“道”,也不在于“言”,而在于怎样去“践道”。
《老子》中关键的命题之一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而”字两边,连接了两个行为,这两个行为的主体初看似乎是同一的,但仔细分析却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主体。请看《老子》第57章深入阐释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具体含义:“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这里,所谓的“无为”是指“我”这个主体,所谓的“无不为”是指作为他者的“民”。因此,“无为而无不为”的立论,是从两个主体即两种人之间的关系着眼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当时的社会关系(阶级社会)在《老子》中的反映:“我”指统治阶级,“民”指被统治阶级,“我”为言者,即立言者;而“民自化”则为言所欲者。显然,言所欲者指向作为他者的民,而不是指向“我”自身,这样,“无为而无不为”的立论,就又由两个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转化为主体与对象物之间的关系了,它立足于解决“我”与“他者”即与民的共在问题。由于主体与他者共在的问题只能在现象世界里面才能展开,因而不会陷入自相矛盾的悖论陷井。如果说,我无为民也无为,我好静民也好静,我无事民也无事,我无欲民也无欲,那么,整个社会及其生活就会死气沉沉、趋向消亡。所以,“无为而无不为”只能落实到两种不同的主体身上才是合理的,即“我”无为而“民”无不为。其实,封建社会长期认定的“君子有所不为而小人无所不为”也正是这种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若用20世纪西方外在形而上学所关注的人类围绕对象意识以探索外在于人的物质对象或精神对象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无为”和“无不为”两个行为主体,只有一个才是真正的主体,另一个只能算是客体。这样当然是言者“我”为主体,言所指向的“民”为客体,所以,“无为”是主体行为,而“无不为”只能是一种客体的行为。因此,老子偷梁换柱式的转化实在有无可替代之理论妙用,这其实是老子解决其哲学两难之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命题。“处无为之事”就是立言(只说不做);所立之言,即所言出者,就是“无为”、“不言之教”;言所欲者就是使民“无不为”,即“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这样,言者和所言出者与言所欲者的界线清清楚楚,言所欲者也不会返回言说者自身,两难悖论自然也不会发生了。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因为圣人立言而化民,需要有个中间环节,即需要有人把圣人的言教传达给民众并促使民众按圣人的意图去行事——行不言之教。这个行不言之教的人《老子》也称其为圣人,那么,作为言说者(立言者)的圣人与作为施教者的圣人,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主体?或是两个人但又同属一个主体?抑或一个是主体一个是客体?这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是必须分辨清楚,也能分辨清楚的。但在古代东方哲学中则未必,因为东方哲学的基础或精髓恰恰是超越主客体两者的“天人合一”论。然而这种主客体不分的观点,既为陷入两难矛盾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也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土壤和养料。
在《老子》中,言说者即立言的主体是隐匿的;传道施教者又称为圣人;传道施教的对象则是民;施教的内容是“不言之教”;言说的目的即言所欲者则是用“不言之教”去教化民众。假如我们依次把传道施教的对象、内容、目的都分别称之为“道”,则这些所谓的“道”都是不能返回言说者即主体自身的。如果传道施教的对象是言说者自己,自己给自己传道没有必要;如果用“不言之教”要求自己,则他又没有必要立言;如果目的不是化民而是化自己,则自己原本就不是圣人了。这样的两难、如此的悖论如何化解呢?实际上,传道施教者与立言者的确可以是同一个人,如老聃、孔丘即是。但问题在于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不等于说两者同是主体或同是客体。前面说过,无论“道”作为绝对自然还是作为“所言出者”,其含义都是“不言之教”,都是“无为”;而“行不言之教”则是有为,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言说者与施教者是同一个人,则就是他想的与做的刚好相反:想无为而行有为,行施教而又不言,就具有了人格分裂的危险。所以,中国古代的传道者都把“道”称为“天道”,“先天之道”,绝不承认此道是自己创立的。老子隐匿了立言的圣人而把施教者称为圣人;孔子则强调他所传的是“先王之道”,自己是“述而不作”等等,其实质均是回避两难。只有把立言者与施教者分离与对立起来,隐匿一个凸显另一个,才能为解决——确切地说是为避免陷入两难矛盾提供可能。
言与道的两难困境避免了,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因为“行不言之教”的圣人,其说教的目的是化民,而民又自化自己。其实圣人在这里仅仅是个传道者,是个信差,可以不必为自己的言说负责。如果他自以为是立言的圣人,身体力行自己的理论与言说,这样反而会因理论返回主体自身而陷入困境。所以圣人的说教是教别人去遵从而不是自己去实行。但这个秘密一旦被人发现,则会被说成是“伪君子”、“假道学”、“说假话”等等,所幸的是,伪君子、假道学们所传之“道”不是自己发明之小道而是“天道”,这又证明立言者与传道施教者不能同一,不然就会因“伪君子、假道学”而危及道本身的价值。
总之,老子的道,意指着“绝对自然”,然而其本身又是在对“绝对自然”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对人之行为的一种导向,这就是“不言之教”与“行不言之教”之间的关系。而这两者间究竟何者为“道”,这在老子那里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如《老子》中“常使民无知无欲”(第3章),既可解释为对“绝对自然”与客观规律的尊崇,又可解释为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愚民政策。所以,老子陷入了“不言无道,可言也无道”的困境,自己也只能叹息;“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稀,则我者贵矣,是以圣人被褐怀玉。”(第70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稀及之。”(第43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56章)。所以,天道无言,人也无言。而无言又何以传道?不传之道又何以知之其为“道”?言者又何以能言?所言出者如何与所欲言者契合?如何达成言所欲者?这些问题似乎根本无法解决。而“道”的存在与发展,又必须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过程中才有可能。出路当然不在《老子》本身,而在于后来的人,包括当代人对于《老子》的不同理解。因此,要继承和发扬《老子》的合理内核,首先是要把“道”引入现象世界(不是把道引向绝对自然),用以规范人的思维与行为,这就是“行不言之教”;其次是把“道”归之于实践,从而走出理论返回主体、自我缠绕的怪圈。这个实践,不是哲学家的自我精神体验,更不是统治者的“无为而无不为”,而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实践运动,主要由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实际生活所组成。把老子哲学引向实践论哲学,这也可说是继承发展老子学说的一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