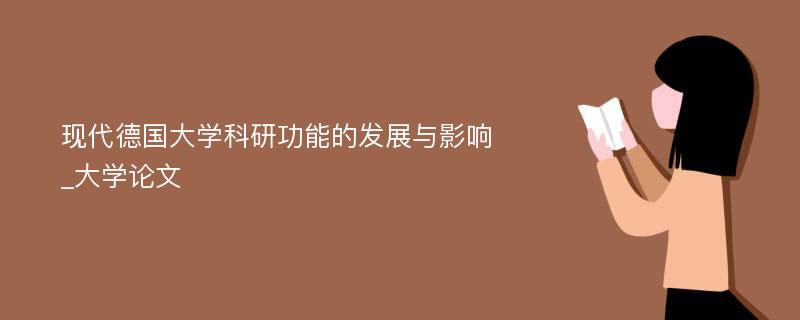
近代德国大学科学研究职能的发展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近代论文,科学研究论文,职能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衡量大学水平的重要尺度。从历史上看,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已历经八百多年的沧桑变迁,但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正式职能仅有一二百年。近代德国大学是世界上最早确立科学研究职能的大学,“为科学而生活”成为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意志诸大学的理想目标。正是科学研究以及科研和教学的统一,使德成为近代大学最发达的地方。其一流的大学,吸引了来自各国的成千上万名求学者,通过他们,德国大学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科学研究原则,更是为各国大学所普遍接受。本文主要探讨科学研究职能在近代德国大学起源、确立、发展和传播的历史。
一、德国大学科学研究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长期以来,科学研究不属于大学的职能,大学的作用仅限于保存和传授已有的传统文化。无论是赫赫有名的牛桥大学(牛津、剑桥的简称),还是古老的巴黎大学,无一例外,德国大学同样如此。大学对新的科学持排斥的态度,大学教授不是科学家和发明家,不必从事科学研究,甚至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从未进过大学校门。就德国而言,经过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大学不再处于进步的状态,被看成是过时的和逐渐衰亡的机构。德国著名科学家莱布尼兹甚至以自己侧身于这样的学校感到耻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大学于18世纪率先进行了改革运动。
德国最早提倡现代科学和研究的大学是哈勒大学和稍后的哥廷根大学。哈勒大学创办于1694年,被称为“欧洲的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其主要特征:一是采纳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二是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原则。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者是哈勒现代化倾向的发起者和促进者。理性主义哲学家托马西乌斯(Christian Thomasius )是“哈勒大学的第一位教师”和新大学学术的奠基人,他废弃了中世纪大学传下来的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他强调实际知识和现实生活,重视对生活有用的科学的运用,使大学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他最早采用德语教学,而不是用传统的拉丁语。虔敬派神学家弗兰克(A·H、Francke)在哈勒大学任教三十多年, 他的目标是培养具有虔敬信仰和实际生活所必需的智能的基督教徒,正是他突破了盛行的神学正统观念。启蒙哲学大师沃尔弗(Christian von wolff)除1723年到1740年在马尔堡大学任教外,一生大部分时间任教于哈勒,主要讲授数学、物理学和哲学,他是创建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哲学体系的第一人。象托马西乌斯一样,沃尔弗用德语而不是用拉丁语讲课。他一生写了67本著作,影响十分深远。
正是以上三人的努力,哈勒大学成为学术自由的第一个发祥地,成为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最早基地,成为18世纪德国境内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大学之一。
哥廷根大学创办于1737年,它既是效仿哈勒大学的产物,又是哈勒大学的对手,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哈勒大学,因此有人认为哥廷根比哈勒更有资格享有欧洲“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头衔。德国教育史学者鲍尔生(Fricdrich Paulsen)说:“哥廷根大学不同于别校的优点,是该校使真正的科学研究受到大力的鼓励和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它有经济充裕的设备和富丽的图书馆,还有专门从事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研究所。”〔2〕哥廷根大学的创办人闵希豪生(Cerlach Adolf von Munchhausen)曾在哈勒大学学习法学,长期担任汉诺威政府官员。他终生关心大学的发展,亲自创办了大学图书馆和科学学会。他大大削弱了神学家在大学的地位,反对宗教上无休止的争吵,重视任用教义上保持中立的神学教授,这实际上已显露学术自由的萌芽。他倡导自由的学术讨论和自由发表的风气,并重视那些著述丰富的学者,他用高薪和优良的条件吸引了许多第一流的学者来校任教。在短短的时间里,哥廷根大学获得了极大的声誉,成为中欧主要的学术和科学中心之一。虽然不足以证明闵希豪生对著述丰富的学者的偏爱导致了19世纪德国大学科学研究和出版的风气,但结果是鼓舞了发表著作的教师,他们的著作有助于世人对著作者所在机构的认识和重视。被誉为德国“国家法之父”的皮特(Johann Stephan Putter)在哥廷根的60年中,共写了126本书,其声望吸引了大批学生来哥廷根专修法律,其中包括后来普鲁士非凡的政治家哈登贝格(karl von Hardenberg )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
大学哲学院与其他三个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始于哥廷根。在此之前,哲学院在欧洲大学一直行使着预备职能,闵希豪生通过增加哲学学科的份量表明自己对哲学院的重视,他尤其看重历史、语言和数学学科。实际上,哥廷根大学哲学院的课程在1760年代时已远远超出纯粹的初级预备目的的范围。
哥廷根大学建立了大量优良的物质条件,包括装备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植物园、古物博物馆、医院等,其图书馆是当时欧洲最好的。如此优越的条件,使学生进行了更多的独立阅读,更使教授进行了较多的有独创性的研究。格斯纳(J.M.Gesner)在哥廷根举办了德国大学第一个习明纳(Seminar)——哲学习明纳。海涅(C.G.Heyne)的语言学习明纳培养了许多古典学者。教授们大量发表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获得了全欧洲的赞扬。
哈勒和哥廷根大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到18世纪末,几乎所有德国大学都按照哈勒和哥廷根的模式进行了改革。学术自由、注重科学研究等现代大学所具有的特征都已现端倪。然而从整体上看,德国大学仍远离时代的要求,科学研究充其量只是大学的副业而已,并非对每个教授的要求,更非大学的正式职能,大部分大学仍处在衰退之中。真正使德国大学焕发勃勃生机的改革完成于19世纪。
二、科学研究职能在德国大学的确立
18世纪末19世纪初,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冲击着德意志这块古老和封建的土地,一些开明的统治者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开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酝酿改革。最初的改革是缓慢的、 效率低的, 直到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大败于法国后,迅速而全面的改革才在施泰因(H.F.K.Stein)等人的领导下得以实施。 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相信:普鲁士必须用精神力量来补偿物质上的损失,于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被当作重要的精神力量得以重建。重建的指导思想是新人文主义,孕育的最大成果是柏林大学。
在18世纪末的大学危机中,出现了三种对大学改革的主张。第一种主张以许多大学教授为代表,墨守古老的和保守的思想,认为教育目的是通过运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来传递具有正确信仰的知识。这种观点常常在大学神学院拥有市场,因为采用偏重实际的方法威胁了神学在大学的首要地位。第二种主张以源于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思想为代表,用一种实际的方式解释教育目的,极力强调以对职业、邦和教会有用的技能训练青年。功利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是邦政府官员、大学法学院和医学院。第三种主张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代表,用一种更主观的方式解释教育目的,认为教育目的是帮助发展和实现个人全部的潜力,强调语言学、古典学科、历史、自然科学和哲学。
显然,第一种主张是守旧的,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遂遭到后两种主张的反对。但由于在教育目的上的不同见解,新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有关大学改革的方法是大相径庭的,在实践中分别对德国各邦大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最终新人文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
新人文主义崇尚古希腊文化,要求在德国思想中复兴古希腊的理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席勒、赫尔德和歌德等。而将新人文主义的理想贯穿到大学改革中,是由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完成的。新人文主义领导了19世纪初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正是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科学研究在大学的重要地位。
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费希特(J.G.Fichte )和洪堡三人是创办柏林大学的先驱和功臣,前二人被誉为柏林大学精神的缔造者,而担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的洪堡,则是柏林大学的实际创办人。
施莱尔马赫曾受业于新人文主义的先驱沃尔夫(F.A.Wolf)门下,1804年担任了哈勒大学神学教授。耶拿失利后,在柏林参加创办新大学的讨论,成为柏林大学思想的先驱。1808年,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一文中,阐明了自己的大学思想。首先,他要求大学完全独立于国家。其次,他认为哲学院是大学的核心,这是因为大学的所有成员,不论他是哪个学院的,都必须把根扎在哲学院。再次,他主张思想自由和思想独立,要求大学必须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使他们独立地深入到科学当中去。为此,大学需有一种精神上完全自由的气氛,科学要从对任何一种外来权威的屈从状态中解放出来。上述思想对洪堡建立柏林大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新大学开办后,施莱尔马赫被聘为神学教授和第一任神学院院长,这使他有机会进一步实施自己的大学理想。
费希特曾在耶拿、莱比锡、维滕堡大学学习,1794年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后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失去教职并移居柏林。1806年受聘于埃尔兰根大学,讲授知识学和逻辑学,并开始对大学组织问题进行思考,撰写了《关于埃尔兰根大学的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一文。他主张大学应该是“一个科学地运用理智的艺术学校”。他对传统的让听众在其中完全持消极态度的教学实践提出批评,要求“把阐述的、解释的内容转变到生动的、活泼的认识中去”。几年前,著名哲学家康德曾主张大学较高级的学院是用来进行职业教育的,即是用来培养牧师、医生和律师的。只有低一级的哲学院才是进行与任何社会实用目的无关的“自由的科学反思”的场所。费希特不以为然,他将对“自由的科学反思”的要求提高到大学课程的一切专业之上。费希特的文章被呈送给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后者又转给柏林首席财政枢密顾问阿尔滕施泰因(Karl Altenstein),受到高度重视。不久,普鲁士政府决定建立一所旨在扩大和介绍科学认识而不是旨在进行职业教育的新型大学,这就是柏林大学。无疑,柏林大学吸取了费希特的思想。当柏林大学于1810年开学时,费希特担任了哲学院院长,不久当选为第一任校长。
洪堡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后又结识歌德和席勒等人,深受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1809年,他担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在为期仅16个月的任职中,终于将柏林大学的新理想付诸实施。他不仅参与筹办了这所新大学,更根据新人文主义思想,确立了新大学的主旨和方向。
洪堡大学思想的核心一是学术自由,二是教学与研究的统一。他反对传统大学将传授知识作为主要职能的做法,主张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在教育史上,洪堡是提出大学教育应当与科研相结合的第一人。他认为只有教师在创造性活动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只有这种教学才真正够称大学水平。洪堡反对大学传授实用的专门化的知识,而要求传授不含任何目的的所谓“纯粹科学”,这种思想支配了德国大学达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久。
柏林大学一开办,即体现了与传统大学不同的新风新貌,尊重自由的学术研究成为柏林大学的精神主旨,洪堡提出的“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柏林大学的新校风。
大学教师应该在他们从事的领域具有专长并具有向听众传递自己的知识的能力,这是各地大学早已达到共识的起码要求,大学教师常常被视为有学问的博学之士。启蒙时代哥廷根大学改革家闵希豪生提出了第二种要求,即至少某些教授应该是能够发表著作的学者。18世纪末,新人文主义形成了第三种要求,即把科学研究当作学者的最高职责,也当作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有用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职责。无疑,这种要求和理想最先是在柏林大学实现的。柏林大学的独特之处在于科学研究成为教授的正式职责,甚至是第一位的职责,鲍尔生说:“柏林大学从最初就把致力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为次要的问题来考虑;更恰当地说,该校认为在科学方面有卓著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的最有能力的教师。在这种理解下,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乃是取得新颖的知识,于是大学不再以博览群经和熟读百家为能事,却要求学生掌握科学原理,提高思考能力和从事创见性的科学研究。”〔3〕为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新大学采用了开设讲座的制度。为鼓励高深研究,重视习明纳方法,即高年级学生和优秀生在教授指导下,组成小组研究高深的科学课题。习明纳成为“科学研究的养成所”,成为培养优秀学术人才的摇篮。
柏林大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将哲学院变成大学的中心。从前,哲学院被看作是低一级的学院,主要实施普通教育,为学生升入其他三个学院打好基础。如今,洪堡、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等人反复强调的哲学院在柏林大学终于第一次成为与其他三个学院平等和并列的学院。不仅如此,在科学知识和教学方法方面,新的哲学院甚至处于领先地位,成为其他学院效法的榜样。从前那些所谓的高级学院不再是单纯训练开业律师、牧师和医生的功利主义机构。教授如何起草辩护状、写一篇优秀的布道文或治疗一名病人,不再是大学的中心任务。语言科学和历史科学成为神学和法学的理论基础;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成为医学的理论基础。最先源于哲学院的学术讲授和习明纳也为其他三个学院所采纳。
洪堡为柏林大学聘请了第一流的教授,除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以外,还有语言学家沃尔夫、历史学家尼布尔(B.G.Niebuhr)、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萨维尼(F.K.von Savigny)、医学家胡费兰德(C.W.Hufeland)、农学家塔埃尔(A.D.Thaer)、化学家克拉普罗特(M.H.Klaproth)等一大批卓越的学者,正是由于他们,柏林大学很快在德国达到第一流的科学水平。
柏林大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所开创的新的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精神,成为德国大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也对许多国家的大学产生了影响。在科学研究上,最初是语言学和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后是自然科学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
三、德国大学科学研究的发达。
拿破仑失败后,德国进入政治上反动的时期。1819年保守作家柯茨毕(A.von Kotzebue)被一名大学生刺杀促使惊恐的德国政府同意梅特涅对大学进行严格控制的要求,德意志各邦议会通过卡尔斯巴德决议,查禁学生组织,建立遍及德国联盟的大学严密监督网,该决议标志着改革时代的结束。从1819年到德意志统一战争前,德国大学进入相对沉寂时期,许多方面呈现出停滞不前的状态。尽管如此,大学科学研究仍在艰难地向前发展,并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德意志统一后大学的突飞猛进,科学研究最终成为德国大学最重要的职能和最庞大的事业,并对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819年以后,尽管洪堡等人的新人文主义理想遭到了严重挫折,但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仍获得了进一步的确立。在1819-1840年间,大学一方面受到当局的政治监视,一方面却诞生了一批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兰克(L.von Ranke)、黑格尔、马克思、俾斯麦、李比希(J.v.Liebig)、亥姆霍兹(H.v.Helmholtz)、施莱登(M.J.Schleiden )等人的名字都是与这一时期连在一起的。1840—1866年间,尽管这是一个被史家称之为大学停滞不前的时期,但“正是在这一时期,科学的理想突破几所变革的大学的范围,成为德国大学的主要原则。”〔4 〕在大学里,创造性的研究以及发表新知识的理想逐渐形成,这种理想日益成为衡量教授和优秀学生荣誉的尺度。一小批教授和学生聚集在一起,根据洪堡的精神,共同探索新的知识领域。到19世纪中期,科学研究精神已在德国大学稳固地扎下根来。许多伟大的发现者和学者认真而热情地从事研究活动,如历史学术的开创者柏林大学教授兰克,实验化学的创立者吉森大学教授李比希,著名地理学家洪堡(A.von Humboldt)等等。有趣的是以上三人都是拙劣的讲课者或不善表达者,但他们以其对科学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年轻一代。
具体而言,1820年代到1870年代德国大学科学的新精神是通过习明纳和研究所而体现的。在1820年后,习明纳仅少量存在于神学和语言学学科,而且其预备功能多于研究功能。1820年前,特别是1850年后,习明纳数量迅速增长。以前习明纳多由个人举办,并未经邦政府承认,往往随着举办者的去留而废存,19世纪中叶以后,由邦官员支持设立的永久性习明纳和研究所成为主流。从规模上看,由于得到政府的承认和资助,习明纳和研究所的形式日益正规,规模日趋扩大。从前在由个人举办的习明纳和研究所中,课程由个别教授开设。经过挑选的少数学生,将定期集中在一起(地点常常就设在教授家中),解释难度较大的课文,承担和报告独立研究的课题,从中得到教授和其他同学的鼓励及批评。如今,得到政府支持的习明纳,不仅有了专门的指导者,还有了固定的场所、独立的图书馆和稳定的经费来源。1840年前,许多教授不得不自己支付研究经费,如吉森大学李比希就曾自己花钱购买实验室的设备,1840年以后,政府大大增加了对习明纳和研究所的投入。1820年柏林大学用于习明纳和研究所的经费为37,500塔勒(德国当时的一种银币名),1870年达到375,500塔勒,50年增加了10倍。毫无疑问,可靠的经济保障是科学研究之风在大学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
德国大学科学研究的发达昌盛是在德意志帝国时期(1870-1914)。这一时期大学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19世纪中叶以来形成的趋势和路线,一方面力求适应德意志朝着强大的工业化的现代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除了大学入学人数成倍增长,习明纳和研究所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仅在1880—1907年间,由普鲁士文化部高等教育处负责人阿尔特霍夫(F.Althoff)在9所普鲁士大学帮助建立的习明纳和研究所就多达176个,其中法学9个,神学4个,医学86个,哲学77个。〔5〕
这一时期习明纳和研究所发展最快的是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 如1860-1914年间各大学医学院至少创办了173个研究所, 其中许多是为新的学科开设的。这种快速增长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历史学家说:“如果说在19世纪早期的科学史中,哲学体系和人文科学的新的观察方式以及工作方法的发展还处于中心位置的话,那么19世纪中期以后科学的发展首先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认识范围的扩大,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自然科学的专业范围,而深入到哲学、人文科学和文学之中”。〔6〕
德意志帝国时期大学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日益服务于社会和国家的需要。例如:普鲁士大学开办的诊疗所和分科医院,不仅通过提供大量的病人供教授和学生研究及学习之用,而且也对大学所在城镇的健康管理和卫生质量有直接的影响。有些研究所和习明纳完全是针对当时德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而设立的,如医学院的公共卫生学、传染病、皮肤和性病、肺病、神经错乱和法医学研究所,法学院的犯罪学和安全保障习明纳。这些研究机构的发展,都得到了邦的鼓励和支持,因为政府日益相信:现代社会问题必须用科学来处理。甚至神学院也开始适应德意志发展的需要,如哈勒大学1897年创办“传教学”习明纳,就是为了满足德意志帝国海外扩张的要求。
哲学院对德意志社会和政治发展也作出了贡献。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和文学的学术研究,不仅是与欧洲其他民族竞争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适应殖民世界发展的需要。例如,为了培养德意志未来新的“海外”官员,大学开始雇用非洲语言和亚洲语言的教师,并创办海洋学研究所、东欧研究习明纳等。
大学也没有完全忽略德国工业的需要,除新兴的技术学院担任应用科学研究的任务外,大学也被迫适应时势创办应用科学研究所。应用电工学、数学、化学和物理学研究所的创办是工程学和纯科学相结合的尝试;新的农学研究所则反映了科学和农业之间必不可少的关系。德国商人也在莱比锡大学创办了倾向经济学自由经营观点的习明纳。然而,应用科学研究在洪堡“纯粹科学”占主导地位的大学里,一直是较薄弱的环节。
习明纳和研究所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大学成员的生活方式,如今教授的大部分时间在研究所工作,而不是象从前那样坐在家里的书斋里。虽然他们仍到课堂讲课,但大多数工作是在研究所完成的。研究所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对优秀学生也是如此,研究所有专门的图书馆和设备供他们使用,在这里他们能够获得在课堂上得不到的与教授交流的机会,并避免了外界的各种干扰而专心从事学习和研究。对博士学位申请者来说,研究所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博士论文就是在习明纳和研究所完成的。
习明纳和研究所成为德国大学科学研究的摇篮和中心,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美国教育史家麦克莱兰(C.E.McClellan)说:“作为学术和发现中心的德国大学的荣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大学古老的躯干里所包括的这些有生气的机构。”〔7 〕德意志帝国时期大学科学研究的发达,也使德国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获得者中,有14名是德国学者,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0名和5名,美国仅2名。值得注意的是,德国14名获奖者全部是大学教师,仅柏林大学就占8人。在纳粹统治前, 柏林大学可以自豪地说:该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数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机构。这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德国的科学水平在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第二,大学是德国科学研究的中心。
四、德国大学科学研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近代大学科学研究职能是在德国起源、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正是科学研究的发达,使德国大学拥有了世界性的声誉。
对美国的影响:
近代德国大学对美国的影响是教育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从1814年起第一批四名美国学生赴德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一万名美国青年和学者到德国大学学习,仅柏林大学前后接纳的美国学生就超过五千人。这些留德人员回国后,大多成为美国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成为传播德国大学思想的主要力量。美国学生在德国发现了他们自己国家所没有的东西,包括最先进的科学方法,思想和调查研究的独立怀,尤其是德国学者对科学和知识的热爱和无私奉献精神。他们回国后,便把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和方法介绍到美国,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创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该校1876年一开办,就体现了与传统英式学院不同的特征:重视研究生教育而不是本科教育;重视科学研究面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象德国大学一样,霍普金斯大学成为一所自由自在地寻求真理的非教派机构。科学研究成为每个教授的职责,教授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把教学和创造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为了鼓励高深研究,霍普金斯大学引入了德国大学的讲授法和习明纳制度。此外,大学注重实验室方法,重视图书馆的功能。学生来去自由,选择并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学术气氛是自由放任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约翰·霍普金斯的名字逐渐有了一种享誉世界的意义,它象征着美国高深的学术和教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卡特尔(J.M.Cattell)1926年调查发现, 在当时1,000名卓越的美国科学家中,有243人是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在它成立的20年内,美国60多所学院和大学各有三名或更多的在霍普金斯取得学位的教师。〔8〕有人称霍普金斯大学为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这是不无道理的。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带动下,美国大学开始朝着高深的学术研究方向迈进。
对英国的影响:
自中世纪以来,英国高等教育为牛桥两校所垄断,而两校恪守传统,崇尚古典学科,拒绝新科学和科学研究,以致培根、洛克、达尔文、斯宾塞和穆勒(J.S.Mill)等著名学者和科学家都非大学出身。有人说:在1830年以前,“英格兰没有科学专业,也没有任何从事科学事业的机构。”〔9〕还有人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 所有伟大的科学家就其科学知识而言都是自学而来的:尽管有了波义尔和牛顿的先例,科学并没有在较老的大学中生根,诗人坎贝尔(Thomas Campbell)1820 年赴德访问后,倡导在伦敦设一所新大学,八年后,伦敦大学学院诞生。该校完全世俗化,开设多种课程,注重现代科学和技术。1830年代,新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会发动了一场促使大学承认自然科学的运动。1839年,英国学生普莱费尔(Lyon Playfair)来到德国吉森大学, 随李比希学习,正是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多地将德国的学术生活方式介绍到英国。1845年,李比希的学生、德国化学家霍夫曼(A.W.von Hofmann)被聘为皇家化学学院首任院长, 他将德国大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英国。1860年代,曾在德国留学的英国人成立了学术研究机构协会,协会组织者之一牛津林肯学院院长帕蒂森(Mark Pattison)于1860 年代后期发表了两篇引起广泛讨论的论文,号召按照德国的模式改革英国大学。他呼吁重视研究和培养科学态度,并严厉批评英国将大学仅仅看作一所供成年的学生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的补习学校的做法。著名科学家赫胥黎(T.H.Huxley)十分推崇德国大学,认为德国大学是献身于科学研究和学术教育的学者团体,是真正的大学,他甚至说德国一所财力不足的三流大学在一年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比财力充足的英国大学在十年中取得的成果还要多。他认为改变英国大学落后局面的关键是扩大大学的职能,开科学研究之风。诗人和评论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曾用七个月的时间考察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的教育状况。1868年发表《大陆的学校和大学》,其中有关德国的部分1874年冠以《德国高等学校和大学》的书名重新发表。他认为德国大学的最高目的是“鼓励对研究和科学的热爱”,德国大学制度的基本思想是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和科学研究,而英国最需要从德国大学借鉴的正是科学。他断言:“法国大学缺乏自由,英国大学缺乏科学,德国大学则两者兼而有之。”〔10〕
在德国大学的冲击下,英国新成立的大学最先引入科学学科和研究,曾经顽固地反对培养学生的研究精神的牛桥也被迫改制。1855—1860年间,牛津建立了许多现代科学实验室;剑桥于1871年建成驰名世界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一批卓越的物理学家曾在此工作,使英国的实验物理学执世界之牛耳。到1880年代,科学研究之风已盛行于英国大学之中。19世纪后期数以千计的英国学生赴德学习,其人数不少于同一时期的美国。著名律师、哲学家和政治家霍尔丹(R.B.Haldane )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称德国是他“精神上的故乡”,足见德国大学的魅力。后来,英国也依照德国的榜样,设立了哲学博士学位,而取得这一学位的必要条件是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贝尔纳在30年代曾说,在英国完成的基本科研工作约有五分之四是在大学试验室里进行的。人们日益认识到,对大学说来,科研工作即使不比教学更为重要,起码也是同样重要。
对法国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革命政权于1793年关闭了全部22所旧大学,巴黎多科性工艺学院、高等师范学校相继开办,这类学校体现了功利主义倾向,主要面向实际。拿破仑执政后,进一步按照功利主义原则,将原来的大学学院改造成为独立的造就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这类学校主要体现了实用的功能,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注重严格和可靠的教学而缺乏科学精神。这种措施从短期看可能一时满足了一些部门对某种专业人才的需求,但从长远看,是不利于科学和学术发展的。数十年后,它终于使法国丧失了在欧洲科学方面的领先地位,取而代之的恰恰是注重大学科学研究精神的邻邦德国。
法国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发现本国高等教育的缺陷。1864年,哲学家、历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撰文尖锐地批评了法国高等教育。他说:“与德国大学相比,法国的学院处于一种低劣的有失脸面的状况。”〔11〕1860年代后期,拿破仑三世的教育部长迪律伊(Victor Duruy)创办一所高级研究和实验学校,作为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及教学中心,该校鼓励学者进行科学研究,最早引进德国大学的习明纳方法。
1870年普法战争以法国在色当的惨败告终,人们分析了法国失败的各种原因,其中一种观点将战败的原因归于高等教育。勒南更直截了当地说:“赢得战争的正是德国大学。〔12〕当时一句流行的警句是“柏林大学报了耶拿失利的一箭之仇。”〔13〕许多人赞成著名科学家巴斯德(L.Pasteur)的观点,法国在半个世纪中忽略了智力的培养, 特别是在科学上。目前迫切需要对高等教育各学院的教学和研究进行全面的改革。〔14〕一些访问过德国大学的人,亲眼目睹德国大学的优良和法国大学科学研究的落后,要求按照德国的榜样改革法国大学。经过多年的努力,这种改革终于在1896年完成了。在从前独立的专业学院的基础上,17所大学宣告成立,科学研究在大学获得了应有地位。巴黎大学更是鹤立鸡群,这里汇集了许多一流的教授和学者,所有的研究领域都采取科学方法。到20世纪初,巴黎大学再度成为有名的科学和知识中心,为法国大学和国家重新赢得了荣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有10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仅次于德国,其中绝大多数获奖者是大学教授,而巴黎大学一校就占5人之多,足见法国大学尤其是巴黎大学科学研究的发达。
近代德国大学的影响是世界性的,除对上述三国外,还对日本、希腊、荷兰、比利时、俄国、丹麦、挪威、瑞典等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曾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也大量吸取了德国的经验。他将大学看作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主张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并在北京大学首创文、理、法三科研究所;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最早在北大采用选科制,实行教授治校。短短的时间,蔡元培就把北大改造成为一所中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
总之,近代德国大学以其对科学研究的重视而闻名于世,它有第一流的教授、学者,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这就决定了德国大学的水平也是第一流的。其他国家只能望其项背、步其后尘,至少在近代是如此。虽然在两次大战中德国大学被拖入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泥潭,但它在世界近代大学史上留下的辉煌篇章是不容忽视的,是值得追述和借鉴的。
注释:
〔1〕Willis Rudy,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1100-1914,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4,P.87.
〔2〕鲍尔生著,滕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3〕同〔2〕,第125页。
〔4〕C.E.McClelland,State,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980,P.152.
〔5〕同〔4〕,P.281.
〔6〕卡尔.艾利希·博思等著《德意志史》第三卷上册第323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7〕同〔4〕,P.286。
〔8〕Hohn S.Brubacher,Willi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1636-1976,Harper & Row,Publishers,1976,P.176.
〔9〕同〔1〕P.128.
〔10〕Matthew Arnold,Higher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in Germany,Macmillan and Co.,1892,P.152
〔11〕Paul Monroe,A Cyclopedia of Edacation,Volum Two,The Macmillan Company,1911,P.669.
〔12〕同〔1〕,P127.
〔13〕Joseph N.Moody,French Education Since Napoleon,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78,P.88.
〔14〕同〔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