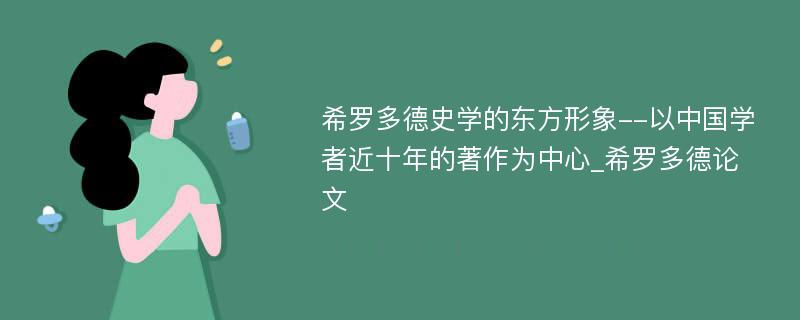
希罗多德史学的东方形象——以近十年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著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著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近十年论文,多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4)02-0083-06
在西方,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年)的名字是和历史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传世之作《历史》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自罗马时代西塞罗称其为“史学之父”之后,这个美名就一直在西方沿用了下来。
其实,对希罗多德的史学,仍是褒贬不一的。大体说来,在古代,贬多于褒,至近世,情况才为之一变,直至18世纪“回到希罗多德”之声随理性主义史学思潮而风行。现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希罗多德史学日众,出现了各派争雄,诸说纷起的史学景观。在此不容赘说。
以此反观中国学界,新世纪以来亦成就出众,给这位西方“史学之父”涂上了浓重的“东方形象”,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化。本文侧重探讨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但笔者还是要作一点回溯,作一点历史的铺垫,这是必须的。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对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中国史,亦是如此。
有史料证明,早在20世纪初就有文介绍过希罗多德①。周作人在1918年问世的《欧洲文学史》中,对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西方古典史家留下笔墨。20年代初,李大钊在《史学要论》及演讲中也屡屡提到希罗多德。1929年,陈训慈刊发《希腊四大史家小传》,其文曰:“希罗多德氏著《史记》九卷,荡涤旧识,自树新帜,希腊史学自兹始昌。”[1]30至40年代,在我国学者编纂的关于史学概论之类书籍中,希罗多德多有涉及,如卢绍稷的《史学概要》、胡秋原的《历史哲学概论》、常乃德的《历史哲学论丛》、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等书。综观这一阶段关于希罗多德的介绍,仍是简要的、不全面的,遑论作出深入的探索与具体的研究了。
5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总体来说,此时中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完全被冷落,其引进也是在“夹缝”中求生。所幸在困难的条件下,西方古典史学名著的翻译仍蹒跚前行,1959年出版了王以铸翻译的希罗多德《历史》的首部中译本。此时,笔者已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就学,在校图书馆开架书库内第一次读到了这部名闻遐迩的西方史学名著,初步领略了古希腊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风采。从此时刊发的犹如寥若晨星的相关文章②,也会留下国人关于希罗多德史学的蛛丝马迹,但集中与专门的论述尚付阙如。
希罗多德史学研究伴随中国“科学的春天”的来临,也乘着这和煦的春风,蔚然成气候。80年代伊始,郭圣铭率先发表《古希腊的史学遗产》一文,文中对希罗多德及其所著《历史》多有评述,这位前辈历史学家的大作,揭开了中国新时期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序幕。
接着,1981年出版了张广智的《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③,又于是年发表了《希罗多德:西方史学的创立者》一文。顺便提及,张广智也就由撰写希罗多德一书一文的个案为突破口,自此出发,开始了他个人学术生涯中悠长的西方史学史研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张广智在上述一书一文中,除论述希罗多德的史学贡献外,还提到要把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作比较,指出:“如果对这两位史学巨人做一番比较研究,一定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史学发展的规律性。”此后竟引出了不少相关作品,比如有:林青、蒋颖贤的《希罗多德与司马迁》、杨俊明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之比较研究》、阎崇东的《司马迁之〈史记〉与希罗多德之〈历史〉》、房晓红的《中西“史学之父”著史的共同特色》、凌峰的《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等文。此外,黄新亚的《司马迁评传》一书,在“东方与西方”这一节中,作者对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也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希罗多德的《历史》仅仅包含了我们所说的历史科学的因素,而司马迁的《史记》却奠定了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也奠定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科学的基础。”[2]
据知,这一工作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中,有不少学术成果面世。比如邓嗣禹的论文《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之比较》,从两者的时代背景与传记、撰史的动机与目的、史书之组织与范围、史学方法与史观、优点与劣点等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比较。以比较史学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名家杜维运在《比较史学的困境》一文中,说希罗多德史学与司马迁史学作比较是一种“附会”[3],因为两者史学成就相差悬殊,称司马迁“在史学成就上,远超过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4]。不过,杜氏之说,充满了悖论,倘未对两人作过实质性的比较研究,怎能得出两人史学成就极为悬殊的结论。在我看来,存疑的应当是杜先生的“附会说”,而不是他后来的实践,即他对两者曾进行过的实质性比较。此外,侨居巴黎的左景权已出版《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比较研究》(法文版),此书尚未见闻,恐难以评说。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从80年代初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一书到最近问世的于沛等人合著的《西方史学史》,在中国新时期出版20多本通贯性的西方史学史作品中,都会在叙述西方史学的源头时提到希罗多德,各有轻重,也各有特色,在此不再逐一评说了。
总括以上所述,中国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20世纪前期还说不上有什么成绩;五六十年代成果亦微,直至中国新时期,才发出了中国学人的东方声音。不过,迄至20世纪末,这种“研究”,就总体而言,还缺乏深度,对希罗多德史学底蕴的揭示。还欠功力,比如一个很显著的方面,即在八九十年代一度热闹的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比较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平面的、形式上的对比,此后也就日渐冷落了。中国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深化,需要耐心,更需要足够的时间。然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后来者,并疏通与撑起后继者的研究,并成了后人新的出发点。没有传承,何来创新,中国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史,也可作如是观。
二、新的世纪,新的形象
中国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林新风,史界活跃,给希罗多德的“东方形象”抹上一片亮色④。
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中国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不仅成果丰硕,质量上乘,且新人辈出,以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为例,从跨世纪的吴少梅学位论文《论古希腊史学的两种范型: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讨论中心》,犹如一支春梅,揭开了新世纪中国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序幕,至2013年阮芬的学位论文《神谕与希罗多德的叙事》,其间以希罗多德为传主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或成品竟“扎堆”地出来。又,吴晓群在为复旦历史系研究生开设《西方古典史学》一课,选课者近10人,历史系选课者竟有3人痴迷希罗多德,以研究这位西方“史学之父”为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这充分显示了希罗多德史学的无穷魅力。
以下,笔者对近十余年来我国希罗多德史学的研究,用下列十二个字,即三个“关键词”:词义阐释、多重视野与历史语境作点归纳,难免挂一漏万,失之偏颇,祈望识者赐正为盼。
(一)词义阐释
词义于史学研究之重要,则不言自明,尤其于希腊文(或拉丁文)的西方古典史学原著,更要精心找准相对应的现代汉语词汇,切磋再三,否则,词不达意,还谈什么深入的研究。在近十余年的希罗多德研究中,研究者对《历史》文本很关注,于是就有了徐松岩的新译本⑤。这里不作徐译本与王译本的“对照研究”,仅就《历史》的“序言”之多种版本为个案,以显中国学界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变化,这一点在过去是不曾出现过的。
在这里,晒一下《历史》序言的各种版本,不仅饶有兴味,更在意它引领我们通读全书、解读希罗多德史学,却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5]。这是首译《历史》的王以铸译本。(下以姓氏简称某译本,如这里的王译本)。
以下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的成果,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着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6]。这是新译《历史》全书的徐松岩译本。与王译本对照,差别不大。差别的是,在“调查研究”与“异族人”之后,徐译本分别加了长篇的“译者注”,当自有价值。通古希腊文的希腊史专家黄洋,在《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对话》一文中,将《历史》序言自译为: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在此发表其研究(historia),以使人类过去的事迹不致因时间而流逝,使希腊人和蛮族人(barbaroi)伟大而令人惊叹的成就不致变得湮没无闻,尤其是他们相互爆发战争的原因[7]。
上述译文,我看不出与王译本有多大的差异,唯一明显的是黄译本将王译本的“异邦人”译成了“蛮族人”,这一词义的差异当为其论旨服务的(下述)。
关于《历史》序言的各种中译本,我注目的是张巍在《希罗多德的“探究”——〈历史〉序言的思想史释读》一文中的版本。哈利卡那索斯人希罗多德所做的探究展示(historiēs apodexis)于此,目的是使人类的作为(ta genomena ex anthrōpōn)不致因时光流逝而黯然失色(exitela),使一部分由希腊人、另一部分由异族人展示(apodekhthenta)的令人惊异的伟业(erga megala te kai thōmasta)不致失去荣耀(aklea),(探究涉及的)除了其它,特别是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aitiē)[8]。这是张译本。倘与王译本相比较,两者在于语义上差别甚大。熟谙古希腊文的张巍,为学界奉献了一则与王译本不一样的《历史》序言,不仅于此,译者还通过这段序言的新译,进而分析希罗多德与荷马的关系,力图阐明希罗多德正是凭借这种关系,以构建其historia的独特的“语义场”。综观全文,张译本不同于王译本的语义,始终是与阐述其文主题密切相关连的,那就是:希罗多德通过“叙事”(logos)来展示自己的“探究”,就实现保存“荣耀”的目的而言,既是史诗诗人的竞争者,亦是他的追随者。
这种由《历史》序言引发,由此可以说明,词义关乎史学论题之宏旨,不可小觑。推衍开来,另做文章,还可再举一例,比如张广智的《论古代西方的历史理论——由希罗多德(历史)之“引言”说开去》一文,引申出以下几个可以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发展变化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兴衰成败的经济因素等,藉以考察古代西方历史理论的基本特征。
关于《历史》序言之中译,有一例颇令人玩味。通古希腊文的学者刘小枫,在《略论希罗多德的叙事笔法》一文中,不仅把《历史》改译为《原史》⑥,文中引文,均从古希腊原文重译,且中希文对照,让识者验证。但在引用《历史》序言时,仍沿用了王译本。这颇令人蹊跷,也许在刘小枫看来,王译本这段畅达的文字,准确传神,与自己译出的各段文字,均古朴典雅,风格较为贴近吧。这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测,不足为据。
必须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部分学者在引用包括《历史》序言在内的希罗多德的原文,有的也称“自译”,但与王译本两相对照,多是王译本的“改头换面”,学术意义不大,还不如直接且老实地标出王译本的页码,这不丢脸,倘弄巧成拙,那就贻笑大方了。
(二)多重视野
这里所谓的“多重视野”,即是指从不同的角度(或侧面)来对希罗多德史学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文章,见世的不少,大体可归纳为如下一些方面:
对《历史》个别卷次作出分析研究的。《历史》卷II,内容独立,颇具一格,这自然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比如蒋保的《论希罗多德的埃及观》、杨扬的《希罗多德“埃及卷”释读》等文即是。对《历史》文本的结构作出分析研究的,比如杨俊明、付静的《评希罗多德〈历史〉的结尾——兼论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文章认为:《历史》的结尾符合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是相当圆满、无懈可击的。
对《历史》叙事作出分析研究的。由论叙事理念的,也有论叙事笔法的,如上文论及的刘小枫的《略论希罗多德的叙事笔法》。分析希罗多德的“叙事理念”也好,探究他的“叙事笔法”也罢,都意在去接近希罗多德,进而阐明他的写作目的,还原为一个“真实的”过去。对神谕与希罗多德叙事之间关系作出分析研究的。这是对上述的进一步研究,因视角不同,其探讨又出新意了。比如郭海良的论文《关于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作品中对神谕的描述》一文,因其比较的视角,相关论述自然颇具深义。有用《历史》中的某一故事撰文,如阮芬的论文《神谕与希罗多德式叙事——以吕底亚故事为例》;由此,进而讨论希罗多德的“人神史观”,比如冯金明的《历史:另一种神话——谈希罗多德的人神史观》,又如杨俊明的《试析希罗多德的宗教迷信思想》一文,则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他的《历史》其中心是人事而非神事,他的历史观是宗教迷信思想掩盖下的人本史观,这与前引《论古代西方的历史理论——由希罗多德〈历史〉之“引言”说开去》一文中的观点是相吻合的。对希罗多德与波斯的关系作出分析研究的。从这一视角,即希罗多德以其历史书写,通过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战争的“探究”,寻求“蛮我两分”的“话语体系”和“他者形象”。这种研究,视角独特,与传统习见大异其趣,黄洋的两篇文章《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像》和《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可为代表。这两文刊发相隔两年,就写作者而言,多是同一时期的产物,虽则前文没有标出希罗多德,但“史学之父”却是该文描述的“重头戏”。因此,两文在近十年中国希罗多德史学的研究中,可视为“姊妹篇”,或可一并予以评述。
《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给人突出的“印象”是时贤萨义德所津津乐道的“东方主义”,在黄洋看来,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该文自点出荷马之后,重点阐述了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以共和与帝制之交,罗马人接受希腊人“东方主义话语”终篇。黄洋的结论这样说,“至此似乎也可以说,东方主义的思想和话语在西方之所以经久不衰,乃是因为它根深蒂固,有着悠久的传统”。至于说到希罗多德,笔者要饶舌的是,他对非希腊人的“异邦人”不存偏见,一视同仁,表现出了他那个时代希腊人鲜有的“开明”与“公正”,只要细读《历史》,便可知也,那不是一种“想象”[9]。现在要切磋的是,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西方人,是否在邈远的古代那种“历史语境”下,会有现代理论家这种过度解读的“东方主义”的“想象”,这还是一个问题,一个颇可商榷的问题。不是吗?
《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对话》一文,发展了上文希罗多德“蛮我两分”的历史书写,通过对异域文明的描述,希罗多德向希腊人展示了一个由“希腊人和蛮族人”这相互对立的两部分所组成的世界,奠定了影响至今的东西方两分的世界史书写传统。这当然是“黄氏之见”,不过,我很赞同该文作者文末所言:
最后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提出的仅仅是阅读希罗多德的一个视角,也许并不能涵盖和解读其《历史》中的全部内容。因其内容的丰富性,其它方式的解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为不同的学者所采用。例如,《黑色雅典娜》的作者伯纳尔就认为,希罗多德提供了一个不带种族偏见,将希腊文明源头追溯到西亚和埃及的解释模式。也许丰富的内涵和多种阅读的可能性正是希罗多德的恒久魅力之所在。
需要补白一点的是,上文作者在张广智主编的《世界文化史》(古代卷)里,提及并赞同奥斯文·穆瑞提出的“东方化时代”的论点,录此也许可给伯纳尔的希罗多德东方观作注⑦。
此外,对希罗多德与波斯的关系作出分析研究的,还有一些,比如:倪学德的《古希腊文化传统与希罗多德对波斯的态度》;李隽旸、时殷弘合撰的《帝国的冲动、惯性和极限——基于希罗多德波斯史撰的帝国战争考察》一文,值得关注。该文与我们上面所说到的所有文章不同,它是历史I的研究,也就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思考。那么,我们在前面所评述的,皆是历史II的研究,即对历史学(希罗多德史学)发展进程的思考⑧。该文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视角与话语出发,借助希罗多德笔下关于古代波斯帝国历程的描述,以史为鉴,从中总结了帝国和帝国战争的某些重要教训,回顾历史,省思现实,颇为可取。
总之,在多重视野下的希罗多德史学,不再是乏善可陈的“一元论”,在学者们多样性与独特性的眼光里,它展现的是“史学之父”的多重面相,于繁花似锦中开辟出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显示了与西方学界不尽相同的“东方形象”。
(三)历史语境
笔者在上文评论黄洋的希罗多德史学观时,首次用了“历史语境”这个词语。本子节企图以“历史语境”这一“关键词”,继续探究中国新世纪希罗多德史学的研究。那么何谓“历史语境”?我查了中国首部由蒋大椿、陈启能主编的《史学理论大辞典》,只有“历史语词”而无“历史语境”。我无力为“历史语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为行文计,只能于此说个大概。
“历史语境”,由“历史”与“语境”这两个词汇构成,在汉语中属于偏正结构一类,在这里“历史”作为定语,用来界定所指“语境”的范畴。那么,何谓“语境”(context)?《辞海》给出的解释是“语言环境”的简称,即指说话的现实情境,即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具体场合,一般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时间地点、听读对象、作(或说)者心境、词句的上下文等项因素⑨。倘如是,所谓“历史语境”就是回到说话者(或撰文者)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环境中作出分析,进行“探究”,如斯金那所说的,“我们需要去还原作者在提出某一特定论点时所可能具有的意图”,即回到这种“原初语境”中。进言之,广义的“历史语境”可泛指社会文化背景,即回到蕴藏于某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层面,“历史语境”的深刻底蕴即在于此;又言之,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语境”,它或许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主义”近义,研究者的研究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不能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再言之,“历史语境”的目标是研究者在多样性与独特性的解读中,寻求统一性,寻求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最终是为了寻求历史学的真谛。
在这里,必须再次提到吴少梅博士在2000年答辩通过的学位论文:《论古希腊史学的两种范型——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讨论中心》。为写本文,这次找出来重读,顿有一种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惊讶的快乐”。尤其是论文作者说到她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施林普顿教授的大作《古希腊德史学与记忆》的深刻影响。是的,正如施林普顿所言,不管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现代史家的“经验的真实”不同,它们是“记忆的真实”。“记忆的真实”与“经验的真实”在表面上毫无共同之处,但内在的情感则是一致的[10]。以施氏这个视角与方法去理解古希腊史学,总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或许与笔者所述“历史语境”之底蕴不谋而合。如此,倘用来研究希罗多德史学,一些疑难问题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不管怎么说,施林普顿新见以及对吴少梅的影响,我以为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人的研究。后人的研究总是在前人的成就上起步,在传承中创新,不是吗?
本子节着重评述的是吴晓群近年来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吴晓群早些时候,关注点是希腊宗教与仪式文化,专注于古希腊史学,那是接受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古代卷)的写作任务之后,尤陶醉于希罗多德史学的“探究”,成果甚丰:张广智主著的《西方史学史》(第三版)一书希罗多德篇的执笔者;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古代卷一书的执笔者;2009年发表的论文《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2010年发表论文《公众记忆与口述传统——再论〈历史〉的真实性问题》;2013年发表论文《论希罗多德的“探究”是何以成为“历史”的》等等。笔者通读这些篇什,从中察觉出论文作者的“历史语境”这一“关键词”贯穿其中,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显示出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新意。
吴晓群是如何看待“历史语境”的呢?她说:“在研究古人及其经典时,首先需要尊重研究对象并秉持客观性,不应完全以今人的知识架构来看待古人,而更应该思考其本身的问题意识以及问题产生的历史语境,从而就其自身的特点来理解古典著作。”[11]由此一端,她对“历史语境”的“还原说”“古今观”“个性与共性论”等与笔者上述之浅见是相吻合的。
我们注意到,“城邦语境”一词一再出现在她的论著中,这自然是“历史语境”的“希腊版”。试想,希罗多德生活时的古希腊,是一个城邦林立的大千世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发达的奴隶制经济,及璀璨的古典文化,自然会对希罗多德史学产生难以磨灭的影响,这不同于“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更不同于“帝国语境”下造就的塔西佗史学,在她看来,“只有将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放在古代希腊城邦的特定语境下加以解读,才是合理的解读。”[12]我赞同这样的见解。
希罗多德史学研究中的一大难点是,“史学之父”的历史叙述多以口述资料为主,于是其史实的“真实性”倍受后人质疑。由于口述史料来自于记忆,如何判断记忆的真实性,如何判断公众记忆与口述传统,这就构成了我们理解希罗多德史学真实性之关键所在。吴晓群在汲取前人与西儒之新说(比如加拿大历史学家施林普顿《古希腊史学与记忆》一书中的新见)基础上,潜心研究,颇有个人心得。她在《公众记忆与口述传统——再论〈历史〉的真实性问题》作了阐发,这种阐发的理念和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回到古典史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去,避免以自我为中心、以现时代为中心去解读他人和他时代,忘掉现代学科分类的严格标准,也不要以进步观去衡量古人。”[13]此见是与历史主义同道,也是符合“历史语境”之旨趣的。在上述这段引文处,吴晓群又加了一个长注,算作“余论”。在笔者看来,这个“注”不只是为正文铺陈,也颇具深义,值得在这里重引,以引起研究者更多的关注。她说:
实际上,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既不在于简单地求同而为自己的言行找寻一个“古已有之”的证据;也不在于纯粹的求异,以表明今人所谓的“进步”之处。我们认为,对经典的研读首先应该是将古人的思想平等地视作一种可供借鉴、参照的精神资源,研究者彰显古人与今人思维的异同,是要以此与现时代形成对照或批判,从而使人们对自己身处的时代及思潮进行反思[13]。
说得好。其实,吴晓群对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历史语境”说,在新世纪中国学人中并不孤立,前述张巍的“语义场”说以及其他学者的识见,也多有流露,只不过没有吴晓群那样明显罢了。总之,在“历史语境”的映照下,我们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真的不能为自己的“新论”与“想像”,找寻一个“古已有之”的证据,而要像吴晓群们所希望的那样,“尽可能多地关注古典时代所处的时代与语境,认识到他们与现代史家在目的和方法上的差异,不要纯粹以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古人……”[14]。
诚然,希罗多德乃“西方史学之父”,中国学者的研究自然离不开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真知灼见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但是,从近十年来中国学者关于希罗多德史学的研究中,我们不是跟在译人评说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充分了解与认识西儒相关论说的基础上,以自己的“话语”,研讨省思,终发出了东方学者的声音,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现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进步。
三、几点想法,一个愿望
随着时代与社会的不断进步,历史学将继续前行,中国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也将伴随着我国西方史学研究的深化继续前行。
曾记得1961年,耿淡如师在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笔者时为该系大二学生)上《西方史学史》(《外国史学史》)一课时,在“导论”课开宗明义说道,希罗多德是西方史学的开山祖师,后世的西方史学繁衍多变,但都离不开这位“老祖宗”。希罗多德,“老祖宗”,此后这两者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而难以忘却。个人就是从读《历史》(王以铸译本)起步,在这块被西方人视为“世袭领地”的西方史学史中,沉潜耕耘了数十年。在这里,笔者以中国希罗多德史学研究“过来人”的角色,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前述诸多时彦,也就教于这里未曾提及的才俊,总之,就教于中国希罗多德史学的研究者们。
我初步想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历史》文本的翻译。
如今,我们虽已有了广为学者征引的王译本,也有了新的徐译本,但我还是希望能出一个比上述两个版本为优的新译本。在广袤的汉语学术圈,不说一个,就是再出几个《历史》汉译本,也不嫌多。笔者不是最近又见到了一个“新译本”(见前注释)。诸版纷行,也可各显其长,让读者择优而从。这让我想起,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从最初的《霸术》到《君王论》,再到如今还在新出的各种中译本《君主论》,林林总总,我也弄不清到底出了几个新译本。至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从1997年首译至今,已有将近30个译本了。暂且不说这是否就是被学术界批评的“翻译乱象”,但我十分赞同“研究型翻译”,倘如是,则多多益善了。至于《历史》新译本,个人的想法是:需要全面理解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从古希腊原文直译,而不是以英译本为主、对照希腊文来译的传统路数,更忌以王译本为蓝本的“改头换面”。当然,西方学者经过了多年的学术积累,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历史》现代英译本,这当然可以借鉴。这里强调从古希腊文原典出发,是为了如上文张巍所说的,不致因译词的疏失考辨而忘却“语义场”的独特性,以致造成对《历史》一书深义的掩盖和了解。从时下来看,这个条件完全成熟了。对此,我个人、研究希罗多德史学的学界同仁们都很期待。
第二,关于历史观与史学观。
这里所谓的“历史观”是指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即在前面说到的对历史I的研究。史学观是指对历史学自身的思考,即是对历史II的研究。综观国人对希罗多德及其《历史》的研究,对历史II(史学观)的兴趣胜过对历史I(历史观)的研究。近十年来的情况,笔者在前面的列举,都可证明。我觉得,希罗多德史学研究应兼备历史观与史学观,当然这两者也不是不可逾越的,我们需要研究希罗多德的历史观,那是为了研究他的史学观作铺垫,而研究希罗多德的史学观,那是为了深化对他的历史观的进一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我个人总觉得像上面举例的李隽旸、时殷弘这类研究希罗多德历史观的文章还是太少了。
第三,关于比较研究。
上文提到,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比较,一度曾很“热”。但近十年来,却冷落了。对此,我们应该反思。2007年台湾学者戴晋新撰《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中西比较研究的一个焦点与线索》一文指出,此前这类研究,“新意不多,且时有谬论与浮泛之言”[15]。该文侧重从史学方法的角度,对两者的比较研究的“对当性”、如何比较、比较意义等问题发表新见,颇具深意。他希望希罗多德与司马迁的比较研究,能更上一层楼,以“获得更多跨文化与世界性的了解,他们在人类历史意识与历史思维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与价值也将不断地被诠释和被公平对待。”在我看来,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希罗多德史学的比较研究,将大有作为。从横向来看,希罗多德的比较对象不只是司马迁一人,也不仅仅限于我国古代历史学家;从纵向来看,希罗多德可比的不只是后来者(包括信从者和批评者),也更有史学文化深层的与时代的等方面的因子,故可深掘,当见新义。总之,在多重视野的研究者眼中,这类比较研究的深入会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希罗多德观,将会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第四,关于“影响研究”。
这里的“影响研究”,说的是在史学史研究中,不应只局限于各自史学自身发展历程的研究,还应当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史学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我个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文即是一种“影响研究”,说的是希罗多德在当代中国学者眼中的一种“东方形象”。历来的史学研究,只关注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这就使史学研究的路径变得越来越狭隘。因此,为了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开拓创新,我们还须重视希罗多德史学的域外史,尤其是他的东传史,重视希罗多德史学对我国史学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我国的新史学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总之,希罗多德之外传,不仅是东传,亦即这位西方“史学之父”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或如上文戴晋彬所说的“世界性了解”,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上的几点想法,旨在深化中国的希罗多德史学研究,并由此推进我国的西方史学研究,共同为发展与繁荣中国的史学,开辟中国史学的新天地,这就是一位多年来专注希罗多德史学研究的东方学者的一个愿望。
注释:
①参见李长林:《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②例如齐思和的《〈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等,自然会对希罗多德与中西史学作一点比较,但多语焉不详,尚缺深论。
③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本书乃是“外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种。这套丛书自1961年起,先后由吴晗和陈翰笙任主编,选题广泛,内容丰富,是专为普及外国史而出版的通俗读物,是史学工作者将历史知识交给广大民众的一种自觉性的表现,丛书虽“小”,却承担着史学服务社会的“大”功能。此后,张广智又于1983年、1993年在商务印书馆相继推出了《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佗》等小书。
④笔者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的硕士、博士课程“西方史学史专题研究”,曾连续进行“民调”,希罗多德均以高票折桂,稳居首席之宝座。
⑤徐松岩重译的《历史》,附有大量的“译注”,甚见功力,此书由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又,徐松岩与黄贤宝重译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早于《历史》新译本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徐松岩又译色诺芬《希腊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出版。至此,古希腊三大史学名著,皆由徐松岩重译或新译,在中国的西方古典史学之史中,应当记上一笔。此外,这次本文成稿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路过上海书城,又发现了一个“新译本”:《历史》上下两册,译者周永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我很想知道这个“新译本”所据何种外文版本,是否参考、借鉴了其他译本,但在简短的“译者序”中没有交代,很遗憾。又连忙看了周译本所译的《历史》序言,当即抄录译文如下:“这是哈利卡尔那索斯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把这些研究成果予以发表,是为了使人类的事业保留在记忆中,使之不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被人们遗忘,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英雄史诗不至于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录下来。”(周译本第3页)。说来也巧,一旁就摆放着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2013年1月第12次印刷(1959年6月第1版)的《历史》,王以铸译本,即把周氏新译的《历史》序言与前者相对照,也就毋需我再饶舌了。
⑥无独有偶,吴小锋在《希罗多德笔下的爱欲与礼法》(《浙江学刊》2011年第2期)一文中,也称希罗多德的《历史》为《原史》。
⑦参见张广智主编的《世界文化史》(古代卷),黄洋执笔的“东方化时代”一节,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89页。
⑧这里所谓的历史I、历史II,即指“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参见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西方史学文化的历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新版,第10页。
⑨《辞海》缩印本(199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481页。西方学者对“语境”理解不一,诸说繁冗,在此略举一例,比如:伯克霍夫(Robert F.Berkhofer)认为历史研究中有三类九种定义“语境”的方法,即从传统历史、从语境主义以及从文本主义这三类出发的方式。参见:Robert F.Berkhofer,Beyond the Great Story: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0。
标签:希罗多德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西方史学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史学史论文; 希腊人论文; 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