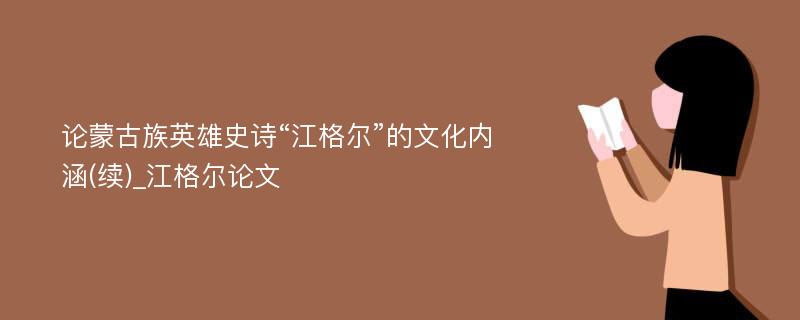
论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文化内涵(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史诗论文,格尔论文,内涵论文,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政治制度内涵
政治制度的范畴,诸如官制、社会等级等在史诗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是说唱者们对所观察到的正在趋于成熟的政治制度的一种艺术性的反映。
对官制的反映主要体现在对主要勇士的描绘上。从史诗中所反映的整个官制来看,除了江格尔这个最高首领以外,其余的主要勇士都被归入左手席或右手席。这种设置方式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国家官制的一大普遍特征,从匈奴人的国家一直到成吉思汗时代都是如此。因此卫拉特蒙古人将这种古老的自己非常熟悉的官制用史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们看到,这些勇士们除了都是战场上的勇士以外,有些人还担任了其他的职务,如左手头名勇士阿拉谭策吉,他扮演的是国家主要谋士的角色,负责处理和调解许多重要的国家事务,人称其为千里眼:“千里眼阿拉谭策吉,/人间的阴谋诡计,/他都能洞察不误;/大千世界上,/他最有智慧。”(第29页)“他掌管宝木巴七十个属国的政教大权”(第10页)。美男子明彦,是江格尔的颂其,负责酒宴上款待宾客的礼节,因为如果乱了章法,上饭上菜时漏掉某位赴宴的贵客,就可能引起不良的后果,可见这个职务的职责是很重大的。勇士凯·吉拉干,是位舌士,能说会道,掌握数种语言,经常充任翻译官。
首先,从官制的结构来看。处于这个官制核心的自然是江格尔,从史诗中可以看到,江格尔除了具有承及天命、无可怀疑的绝对权力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具体职务,但我们认为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一种三重性的特征:江格尔要担负古代勇士们所担负的那种保卫家乡、保卫亲人,与蟒古斯殊死斗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还要担负一种古代氏族、部落首领所担负的责任,即负责宗教方面的事物,这从第九章“西拉·胡鲁库败北记”里对江格尔入地救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因为根据传统,只有萨满才有这样的技能,而在古代萨满往往也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首领。对江格尔具体职务描绘方面的模糊性,表明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只是期望能有一位象江格尔这样的人来担任那种综合性的、能对全民族负责的重大的职务,而在当时,这一职务——全体卫拉特人统一的大汗还没有产生。在这个官制中还有一个职务是很重要的,即阿拉谭策吉所担任的职务。从整体来看,这一职务同古代氏族部落里的长老很相象,他们大都是些德高望重,有经验、有智慧的长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有军事的、行政的、司法的和宗教的,他们可能亲自参加战斗,其中某些人起着“总参谋长”的作用,组织并给军队提供建议。而史诗中的阿拉谭策吉起的正是这样一种作用。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官职是雄狮洪古尔所担任的右手头名勇士,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是战场上的佼佼者,必须要异常勇敢、忠诚。史诗中有大量篇幅描述洪古尔,可以说他是史诗中人们重点刻画的人物,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江格尔,在洪古尔身上,集中了古代勇士所有典型的英雄品质及特征。承担这一职务的英雄是如此之出众,可见这一职务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在这一官制的内部,各官职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江格尔与其周围人的关系,基本上有两种形式。第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史诗中可以看出,由于江格尔权力的承及天命无可怀疑,因此他可以指挥任何人做任何事,他周围的人也认可并服从了这种权力,他可以派某个勇士单独出征,也可以率领大队勇士集体去征战,甚至雄狮洪古尔的婚礼也要由他亲自操办。第二,平级或平等的关系。这一点在史诗中不时地被体现出来,如第五章“萨布尔的功绩”中,萨布尔因一点小事就愤然离开江格尔投奔沙拉·裕固三汗,并发誓“让我们挑起战争,/夺取江格尔的国土”(第104页)。在第八章“江格尔和暴君芒乃决战”中,当江格尔命令勇士们将洪古尔捆起来的时候萨纳拉公然违抗江格尔的命令,勇敢地出来阻拦(第183页)。在第九章“西拉·胡鲁库败北记”中,当江格尔坐在那里沉思默想不回答勇士们的问话时,凯·吉拉干说道:“‘我们三十五个勇士都可和你比并,/我们和你一样都是可汗之子’。/凯·吉拉干说完,拉开银门走出宫殿。勇士们一个跟着一个哗然离座,/纷纷离开了江格尔可汗。”(第228页)可以看出,一方面人们认可并服从江格尔的领导,另一方面又不时地反映出与江格尔的平级或平等关系,这种矛盾现象我们认为主要反映了一种变化的痕迹,即由军事民主制时代向集权时代变化的痕迹,前者来自于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对史诗最终成型的那个时代的观察与思考,而后者则是人们对古代民主传统的一种回忆与继承。
其次,从这一官制中官职的特点来看。这些官职的设置带有浓郁的游牧社会色彩,从史诗中可以看到,它们是在非常有效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战争在游牧社会中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因此,在其官职的设置中这是被优先考虑到的。在《江格尔》中我们看到,所有的官职,无论其具体职责是什么,首先必须是为战争服务,担任这些官职的人也首先必须是个勇士,不仅能随军参战,而且还能单独出征。至于江格尔本人,他的首要职责就是率领勇士们东征西讨,为保卫、发展宝木巴尽职尽责。从史诗中可以看出,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按照江格尔的命令去进行的,并且几乎每次都是由江格尔亲自出战来最后决定胜利。江格尔作为一名最出色的勇士的那种无与伦比的风采是与他那承及天命、至高无上的权力及地位相辅相成的,二者缺一不可。因此我们认为,征战应该算是这些官职的一大特征。虽然这是由承及传统而来的,但又明显带有史诗最终成型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即由于征战的范围有所扩大,性质有所改变,因此这些官职的征战特征也有所改变,由原来的为氏族、部落的局部利益,为血亲复仇而战,到现在的“愿为宝木巴建立伟大的业绩,/我听从你的吩咐,/不论何时何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第30页)为征战服务的目的有所改变;从为征战服务的方式上来看,由原来的单打独斗,一对一厮杀,到现在带领自己属下的勇士集体作战;从为征战服务的直接结果上来看,由原来的将对手打败直至消灭,到现在的将对手征服,纳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所有这些改变,都表现出了一种国家的、集权的意识,表现出了某种趋于成熟的倾向,时代变了,这些官职的内涵也在变。一方面这是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在对传统继承的基础上的一种艺术创造,另一方面又是他们基于现实观察的一种艺术再现。
松散性可以说是这些官职的又一大特征,这主要是针对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种集中化管理而言的,亦即担任这些官职的人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担任这些职务。这一点在史诗中被多次地表现出来,如在第九章“西拉·胡鲁库败北记”中,分别着重墨对西克锡力克老人、阿拉谭策吉、库恩伯诺颜、洪古尔的宫殿及属民领地进行了描绘,他们都是各自领有一方土地人民的首领,一旦宝木巴或江格尔需要他们时,他们便来到江格尔身边,担负起各自的职责:“马蹄哒哒敲击大地,/惊动了江格尔的三十五个勇士,/惊动了七十二个可汗,/他们争先恐后飞向江格尔的宫殿。”(第206页)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这是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对古老传统的继承,即一旦需要时相关部落结成临时性的联盟;另一方面,这又是他们对史诗最终成型的那个时代的观察思考,即当时的卫拉特社会各大小汗国之间正在努力进行着联合统一的过程。
对社会分层的反映在史诗中虽然是间接的,但从整体上看,我们认为,整个社会是被分为三大阶层的,即统治阶层,以江格尔为首,包括“左手十七名勇士”和“右手十七名勇士”甚至更多一些;属民阶层,就是史诗中所说的“五百万人民”、“七百万人民”、“万千属民”等;奴隶阶层。其中属民阶层我们认为还可细分为两部分,即各汗国原有的属民及后来新征服的属民。
社会分层是与社会平等相对照的,而社会平等只有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才能办到,因此社会分层是除狩猎采集社会以外其它一切社会形态所具有的一种普遍而有影响的现象。对于《江格尔》中所反映出来的卫拉特蒙古人的社会而言,既然产生了社会分层,那么在这些群体之间就必然要有相对的高低等级之分,其间就必然要有较明显的差别。我们认为,从史诗中看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特权方面来看。统治阶层的人自然比其它阶层的人拥有更多的特权,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的“专利”。第一,他们掌管着军队、法律、税收等。如:江格尔统领着六千又十二名勇士,其他重要勇士也都各自有自己的伊勒登(亲信、卫士):“库恩伯鞴好乌龙驹最先出发,/他的三千名伊勒登都跨上骏马,/携带奶食飞向英雄江格尔的宫殿。”(第205页)他们统领着这些英勇无比的军队,跟宝木巴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千里眼阿拉谭策吉端坐在黑缎垫上,/他掌管宝木巴七十个属国的政教大权。/无论遇到什么疑难的案件,/他都能迅速无误地勘破、裁断。”(第10页)“让他们发誓保证:/缴五十年的贡品,/一千零一年的税金,/永远作宝木巴的属民。”(第10页)第二,他们可以单独承担任务,出征作战。在盛行英雄崇拜的社会里,这对于一名勇士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誉,难怪在第十章“黑纳斯全军覆灭记”中,当江格尔建议“六千又十二名勇士一同去,/一同去消灭那野心勃勃的魔王”时,“雄狮洪古尔说:/不能这样,千万不能这样!/这会给我带来世人的诽谤,/会说洪古尔惧怕厚和查干,/出征应战还拉上江格尔可汗,/六千又十二名勇士陪他上沙场。/这不光彩的名声一旦传扬,/我就无颜活在卫拉特家乡。”(第318页)这种机会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他们的一种特权。第三,他们都住在富丽堂皇的豪华宫殿里。江格尔的宫殿自不必说,史诗中还对西克锡力克老人、阿拉谭策吉、库恩伯诺颜、洪古尔的宫殿进行了描绘。第四,他们都有广阔的领地的众多的属民。象阿拉谭策吉:“宫殿北面湖水清澈,/流水潺潺,山泉淙淙,/美丽的草场四季常青。这里住着五百万人民,/人们相亲相爱,彼此不分。/在主人的洪福照耀下,/吉祥如意,欣欣向荣。”(第202页)第五,他们大都是可汗之子,有着高贵的出身及非凡的才干。他们的特权及地位一般都是世袭的,象江格尔是塔海兆拉可汗的后裔,唐克苏·宝木巴可汗的孙子,乌琼·阿拉达尔可汗的儿子;阿拉谭策吉是达赉扎木巴可汗的孙儿,嘎吉嘎·阿拉达尔可汗的独生子;萨布尔的父亲是大无畏的英雄,母亲是海洋般富有的女人等。
其次,从义务方面来看。从史诗中可以看出,统治阶层的义务主要有两项,即为宝木巴和江格尔尽义务,这从勇士们纷纷归附江格尔及向江格尔频频表示的誓言中可以看出,也可以从江格尔对勇士们的赞美中看出。对于属民阶层来说,那些宝木巴原有的属民,他们除进行正常的生产外,主要义务就是服兵役,除去那些主要的勇士,其余众勇士大概就出自这一阶层;而那些后来新征服的属民,从史诗中来看,其主要义务就是为宝木巴、为江格尔纳税进贡。至于奴隶阶层,他们要无条件地为主人尽那些主人所要求的一切义务。从史诗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经常被主人用来交换物品,如,洪古尔的一块手帕是用一户奴隶交换的(第213页),萨布尔的那匹栗色马,是他用一万户奴隶换来的(第400页),明彦的一副肩甲,是用一万户奴隶换来的(第410页)。另外,奴隶们还要为主人从事家务劳动,如拾粪砍柴(第181页)、守门(第222页)等。
我们认为,这种社会分层是宝木巴国政治制度的基础。由于战争的频繁,统治阶层作为国家的核心,自然而然地成为战争的领导者,而人数众多的属民阶层甚至于奴隶阶层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可靠的兵力及物质来源,这样国家战争所需要的基本东西都可以得到满足。我们看到,虽然这种社会分层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化的不平等,但在人们看来这种不平等却是天经地义的,人们对此并没任何抱怨。相反,从史诗中处处洋溢着的赞美之情来看,人们认为只有有效地维护并发展这一切,才是国家强盛发展的出路。处于社会低阶层中的人们无条件地相信统治阶层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并且无条件地去服从这种权力,因为他们认为统治阶层的这些权力都是承及天命的,只要怀着积极的期望去承认、服从它,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在承认并服从这种权力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承认了自己的地位,默认了这种社会划分,他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政治制度观念上的基础。
四、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法律制度内涵
这里所涉及到的法律同我们日常理解的那种被有意识地加以系统化的、独特的、完整的法律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比一般意义上的法更狭义、更特殊的某种东西,可以称其为“法律秩序”,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社会习惯、政治制度等并无差别。没有人试图将当时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组成为一种独特的结构,法律没有被自觉地加以系统化,它还没有从整个社会的母体中“挖掘”出来,而仍然是其一部分。从史诗中可以看出,这种“法律秩序”更多地是通过某种精神,某种努力趋势表现出来的。
从整体上看,我们认为史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法律秩序基本上呈现出了家庭的及国家的(封建的)两大特征。
虽然在前面我们曾论及过在《江格尔》中呈现出了氏族部落意识及血缘关系的淡漠,但是家庭内部的那种血缘亲情联系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存在的,可以说这种亲情联系是社会存在稳定的基础,因此史诗《江格尔》所反映出的法律秩序表现出家庭性的特征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我们认为这种家庭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血亲复仇。虽然整部史诗描述的是以江格尔为首的众勇士捍卫发展宝木巴的英雄业绩,背景是广阔的,气势是宏大的,但血亲复仇的痕迹仍可以看出来。如在第十二章“美男子明彦活捉昆莫”中,活捉昆莫的理由是,由于宝木巴的强盛,江格尔的声名,使昆莫恼羞成怒,便想前来征讨,因此江格尔认为只有派人去将昆莫活捉,才能免除这场灾祸。表面上看理由是如此,但实际上真正的理由是血亲复仇,即很早以前昆莫曾打败过江格尔的父亲乌琼·阿拉达尔。在第十四章“三位小勇士擒大敌”中,出征的理由也是:“今天我占有辽阔的东方,/我的名字遐迩传扬,/他要派两名使者前来侵犯。/他们一旦来到我们的家园,/我们就要遭受涂炭。/先派人去活捉巴达玛·乌兰,/就能免去这场灾难。”(第447页)但我们从这背后仍然看到了另一个理由:“这魔鬼力量巨大把我压倒,/举刀要把我杀掉,/这时,他向我问道:/‘你有什么夙愿未了,/可对我讲明才好’。我没有隐瞒真情,/吐露了年轻人的三点夙愿/……/巴达玛·乌兰听了我的陈述,/他说:‘快去实现你的志愿/然后再来较量!’/他遂把我释放。”(第446页)江格尔出征实际上是为了报当年的受辱之仇。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实际上是一种变了形的血亲复仇。在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的脑海中,古老的血亲复仇依然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模糊而已。当国家的、民族的意识产生之后,他们便将些融于其中,使之有了新的面目,原先是以血缘亲情为借口去复仇,现在却是以国家民族为借口去出征,外在的形式变了,可内在的精神却依然如故:珍惜荣誉,赢得光荣。这同时也说明在史诗最终成型的那个时代,卫拉特蒙古人社会的法律秩序正在朝着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另外我们还看到,不论是表面上的理由,还是实际上的理由,亦即不论是以国家民族为借口还是以血缘亲情为借口,解决的方法都是暴力,而这恰恰是这种法律秩序所具有的英雄的一面:为了荣誉,仇人间进行殊死的搏斗,难分难解,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决定接受命运的挑战及安排,随时准备赴汤蹈火,而不管这可能有多么残酷,多么痛苦。
第二,家庭保护。在古代,家庭成员之间不仅有血亲复仇的责任,更有互相保护、互相帮助的责任。这一点在《江格尔》中也是以一种变了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如在第四章“萨纳拉远征胡德里·扎嘎尔国”中,当江格尔派萨纳拉去向扎干泰吉可汗传达命令时,萨纳拉哭着说了一番话,意思是:你派我去执行这么艰巨的任务,是不是因为我远离汗国、父母家庭孤身一人的缘故。在第十一章“美男子明彦偷袭托尔浒国阿拉坦可汗的马群”中,当江格尔派明彦前去把马群赶回来时,明彦同样是哭着说道:“我放弃了雄伟的明山,/抛弃了千万属民,/离开端庄的夫人,/扔下可爱的儿女,/只骑了金银马投靠您。/……今天,为何叫我匹马单身/奔赴他乡异地?/是惧怕强大的故人;/还是因为我孤单一人?”(第379页)在第十章“黑那斯全军覆灭记”中,当西克锡力克得知洪古尔要单身匹马出征时,他老泪纵横,悲痛万分:“洪古尔不是没有飞翔的双翼,/他是我手中的弹丸!/洪古尔是温暖我晚年的太阳呵,/他是滋润我心灵的甘泉!/洪古尔不是生长在高山岩间/一裸纤细孤单的红柳,/洪古尔象凤凰象雕鹰,/他是盘旋在空中捕捉猎物的雄鹰!/洪古尔不是牙齿不全的野猪,/他是我的独生子呵!/你怎能把他推向火海刀山,/你怎能让他单骑奔向苦难?”(第324页)在这三个例子中虽然表达的方式不同,但意思只有一个,即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家庭作后盾,如果离开家庭,失去家庭的保护,那么就会在社会上遭到岐视,甚至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的心目中,家庭保护这一古老的习俗一直没有被彻底忘却,虽然他们在《江格尔》中主要想表现对英雄的赞美及对时代的责任,但这一习俗还是被无意地表露出来,那种变了形的表达方式即是证明。同时这种“无意”也表明在史诗最终成型的那个时代,这一习俗已不起太大的作用了,已经让位于另外一种(或一些)更有效、更合理的法律规范了。
至于国家性的(封建性的)特征,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纵观整部史诗我们看到,宝木巴从整体上呈现出的是一种井然有序的景象。全国上下除了遭到敌人入侵外,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都很正常,有江格尔这样非凡的领袖在领导,有阿拉谭策吉、洪古尔等这样的勇士在辅佐,有八千名宝通、六千又十二名勇士这样强大的军队在保卫,国土辽阔,牲畜遍地,千百万属民和奴隶们在安宁幸福地生活。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一种有力、有效的社会控制(法律控制),这一切是很难达到并维持下去的。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创作出如此完整有序的政治、社会结构及生活画面,我们认为,一方面这是他们基于现实观察的结果。在史诗最终成型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已经产生了某种法律控制形式,其作用和目的在于监督和调整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使其能够融洽和谐,从而构成一个整体,有效地进行运作。从宝木巴的这种井然有序中我们看到,这种通行的法律控制形式主要不是为了决定犯罪和确定审判,不是为了将人们相互区分,而是为了将人们维系在一起,使人们和解。在此,它首先是一种调解过程,一种交流方式。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相反,那么结果则是处处充满了紧张、压抑、敌视甚至暴力,绝不可能有什么融洽和谐,井然有序。而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能以一种不超出习俗规定范围内的、被全体人员所接受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以解决,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冲突的发生,从而也就保住了融洽和谐,井然有序的局面。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受英雄主义的熏陶内化控制的结果。我们知道,英雄崇拜在游牧社会中一直是兴盛不衰的,英雄精神已经成为其共同体共有价值的一部分,而这种共有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一种“活的法律”。人们对英雄精神的认同就是对“活的法律”的认同,因此人们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自觉地遵守这种“法律”,从而使自己符合社会的要求。在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的心目中,这种英雄精神的主要体现就是忠诚、勇敢。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英雄一定要做到忠诚与勇敢,要忠于国家,忠于自己的首领,要勇敢地为了这一切去拼杀,他们将此表现于史诗的创作中,因此我们看到,宝木巴的井然有序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忠诚勇敢的结果:有了勇士们的忠诚,宝木巴才能团结一致,保持完整;有了勇士们的勇敢,宝木巴才能安宁,才能幸福。史诗中的勇士们个个充满了英雄精神,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忠诚勇敢,自觉自愿地去为国杀敌:“荣耀的江格尔,我的圣主,/……愿为宝木巴建立伟大的业绩,/我听从你的吩咐,/不论何时何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第30页)而这一切正是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所期望达到的。另外,由于宝木巴整体上是人们基于现实的一种幻想,因此宝木巴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井然有序一定程度上也是人们的一种期望,人们期望现实社会能变得和宝木巴一样井然有序,实际上在这种期望的背后表现出的是一种对秩序、对法律的期望,同时这再一次说明了当时卫拉特社会中的法律秩序正在朝着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
第二,我们知道,宝木巴的基础是江格尔的汗国与其他勇士的汗国之间的联合。那么是什么保证了这种联合呢?
首先,从史诗中看,人们之所以聚集在江格尔的周围是出于对江格尔的崇拜,我们认为,这种崇拜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江格尔的统治的合法性。这里的“法”指的是判定一位英雄兼大汗的标准,这种标准的产生是以当时社会所公认的最主要的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即作为一名真正的英雄,他要有非凡的技能,作为一位大汗,他要有承及天命的绝对权力。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活的法律”,人们认同服从了江格尔,就是认定江格尔符合了这两项标准,也就是在遵从这一“活的法律”,这是宝木巴各部之间联合的一个法的观念上的基础。
其次,其他勇士通过向江格尔、宝木巴宣誓、尽义务的方式来巩固他们之间的联合,而这种誓言与义务就具有法律效力。作为习惯的一部分,这种誓言与义务是神圣的,以致于它还可以不仅是神圣的,而且简直受到了绝对的和不容置疑的尊重。它是以对宝木巴、对江格尔的忠诚为基础的,并且与勇士们为了荣誉而英勇斗争交织在一起。从史诗中看,虽然它被淹没在其它社会制度中,但它仍是一种“法律”,仍是一种法律秩序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尺度,人们承认其权威性,并服从其约束。
从这种誓言与义务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两部分,即对江格尔所发的誓言及为宝木巴所尽的义务。
首先,从史诗中可以看到,勇士们在向江格尔宣誓的时候,大都使用了如下字眼,如做江格尔的战马、号角、铁衣、坐骑、皮外套、盔甲、骏马、野兔、雕鹰等。这种描述很传统,也很形象生动,体现了勇士们对江格尔的忠心赤诚,也体现了史诗的创作者与欣赏者们对习惯、民俗的一种不折不扣的遵从。我们看到,当勇士们将自己的人身与江格尔紧紧地联系起来的时候,其实已在将自己的领地和属民与江格尔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且一旦有人违背了誓言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如:“宁愿今生违背江格尔的法纪,/被处死,/……。”(第510页)在第十章“洪古尔出征西拉·蟒古斯”中,当魔王前来挑衅时,江格尔说道:“……谁打退恶魔的进攻,/三次赦免他的死罪!”(第477页)可见江格尔对违背他的人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那么与勇士们的这种忠诚、誓言相联系的是什么呢?我们从史诗中看到,表面上勇士们得到了荣誉,实践了作为一名勇士所应具有的人格价值,而实际上与此相联的是江格尔会给勇士们一定的特权及授予他们一定的领地,如:“谁能打退入侵的魔鬼,/我将满足他的十三种要求,/……谁打退恶魔的入侵,/送给他善巴山做领地!”(第477页)同时勇士们还可以得到江格尔政治上的庇护,关于这一点史诗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在第三章“洪古尔和萨布尔的战斗”中却体现了出来。萨布尔的父母临终前对他叮嘱道:“我们一旦离开人世,/你赶快奔向宝木巴乐土。/白天不要停步,/黑夜不要住宿,/你要找到江格尔与他会晤!”/(第51页)萨布尔的父母去世后“他无依无靠,形影孤单”,只有投奔一个强大的首领——江格尔,他及他的汗国才能保存下来。因此我们认为,这种相互间的关系,实际上已有了相当多的封建成份在里面。一方面是传统习俗的绝对、神圣,另一方面则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忠诚与誓言。
同时我们还看到,这种对个人之间忠诚关系的描述在《江格尔》之前的蒙古英雄史诗中是不存在的。在《江格尔》之前的史诗中,体现出的是一种生存意识,即个人的生存、家庭的生存、氏族部落的生存,人们需要的是能够勇敢、顽强,战胜自然、战胜敌人的人,人们认为只有靠这样一位非凡英雄的勇敢斗争,生存才能维持下去,因此这时的英雄们所具有的品质大体不超过个人勇敢、对亲人忠诚等范畴。这实际上是氏族部落意识的一种体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英雄史诗所反映的自然是英雄们个人的冒险活动及其英雄业绩,说唱者及听众们所感兴趣的也自然是这些。那么之所以在《江格尔》中才出现了对这种忠诚关系的描述,我们认为:在《江格尔》中所体现出来的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生存意识了,而是具有了更高层次的发展意识,即整个社会要结为一体,要战胜一切困难,繁荣、稳定、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而要实现这一切,秩序、结构、机制是必不可少的,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就更是必要的了,在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的心目中,这种古老的关系便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熟悉也是最简单的方法了,他们幻想通过英雄个人所具有的这种忠诚品质来使社会成为一体。因此他们便在史诗中塑造出不仅具有个人勇敢及对亲人的忠诚,更具有对朋友、对首领、甚至对更大范围内的人们保持忠诚的英雄形象,同时不惜笔墨,在史诗中对这种忠诚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描绘和赞美。这种忠诚范围的扩大,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思想意识内涵的扩大,这已是氏族部落意识所容纳不了的了。
其次,史诗中在提到为宝木巴尽义务时,大都是用“为宝木巴建立伟大的业绩”、“为宝木巴披肝沥胆”,“把赤心献给宝木巴”等方式表达的,从中体现了对宝木巴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我们知道,任何政治共同体,不论是氏族、部落还是国家,其成员对该共同体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是该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每个成员的一种“天赋权力”。不论该共同体是否有相关的明确的法律规定,这种责任与义务是其每个成员必须无条件遵守的,他们必须把这种责任感与义务感认同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尺度,这样做对该共同体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具体到史诗《江格尔》也是这样。从《江格尔》中我们看到,这种责任感与义务感是同勇士们的英雄性格联系在一起的,就象他们的英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一样,这种责任感与义务感也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的一种“天赋权力”,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在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看来,正是英雄们的这种“天赋”的强烈责任感与义务感,才使得宝木巴得以生存发展,欣欣向荣。赞美之余,也表达了他们对这种责任感与义务感的认同,在他们看来,这种责任与义务既是对古老传统的继承,又是时代发展所必须的,是不容怀疑,不容推卸的,就象过去对家庭、对氏族部落忠诚负责一样,现在必须对国家,对民族尽职尽责。当他们面对着崛起的机遇与挑战时,这种对社会、国家乃至全民族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就显得更加重要和更有意义了。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就一定能够把握住机遇顺利地迎接挑战。
五、英雄史诗《江格尔》的经济制度内涵
史诗《江格尔》中所反映出来的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大致有经济形态、所有制形态、劳动分工等三项。
第一,经济形态。从史诗中我们看到主要的经济形态是畜牧业,因为史诗中曾多次提到过马群、羊群、牛、骆驼,还有人们经常吃的奶食(奶酪)及喝的马奶酒等,这一切都是一个畜牧业社会所具有的。如:“阿拉谭策吉的马群/把草原填满,/从善巴山到吉兰河畔,/油亮的铁青马约有八万。”(第17页)“当他们经过一个丰美的草场,/惊动了一千只紫头白绵羊,/……。”(第340页)“象角斗的公牛威武雄壮。/……象发怒的公驼凶猛异常。”(第32页)“这儿是甘美的食品和奶酪”(第76页),“……携带着纯洁的奶食,/要敬献给江格尔可汗。”(第205页)另一种经济形态即狩猎业,在史诗中也被以不同的方式或明或暗地表现了出来,如:“我们什么时候遇到较量的对手?/我们什么时候遇到猎获的野羊?”(第14页)“蒙根·西克锡力克/背好弓箭要去狩猎,/……。”(第19页)等。我们看到,狩猎业显然只是一种辅助经济形态。另外,在史诗中还有个别地方提到了农业现象,如:“……象田野里恐吓鸟兽的草人,/……。”(第43页)“江格尔的宝木巴地方,/……粮食堆满田野,/……。”(第30页)虽然还难以断定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史诗最终成型的那个时代,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对农业已不太陌生。
第二,所有制形态。在此我们主要指的是牧场的相对公有制和牲畜私有制。首先,就牧场公有制而言,在史诗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我们看到,史诗中在提到领土或牧场时,通常冠以“某某汗”或“某某魔王”的“宫殿”、“国家”、“国土”,虽然这些领土被认为是这些首领所有,但我们认为,这些人所代表的是一个政治实体而非仅仅是他个人,仅管他们对牧场有领有权和支配权,但为游牧生产所计,他们是将这些牧场在属民中间分配使用的,因此在他们所统治的这一实体内牧场是按一定规则共同使用的。史诗中有一处暗示了这一点,即在第六章“雄狮洪古尔的婚礼”中,当洪古尔变为秃头儿后,一对身为奴隶的老夫妇收留了他,这对老夫妇非常穷,住的是破毡房,没有足够的牲畜,连日常饮食之用的酪浆也要向别人乞求。当秃头儿得到奖赏的绵羊、骆驼和新毡房后,“秃头儿对父母说:/爸爸,我们有了两千只绵羊,/再不能住在村边的这所破旧的毡房,/我们到湖畔挑选芬芳的牧场!”(第154页)这里的关键在于“挑选牧场”,表面上看,这对老夫妇有了牲畜和新毡房,就可以自由挑选牧场(当然,这种“挑选”是有一定规则的,并不真的就是自由挑选),实际上我们认为,这里表现出的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现象或制度:那些有一定的牲畜,并且有人身自由的人对牧场有使用权。老夫妇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一是身为奴隶,饮食起居无着,地位低下;一是有自己的牲畜、毡房,并且还可以使用牧场。这两种人在社会中的处境显然是不同的,别的且不说,单就对牧场的使用权这一点来讲,从史诗中看,前者是没有这种权利的;而后者,既然有了足够的牲畜及自己的新毡房,那就肯定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从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正是这部分人对牧场有使用权,并且如前所述,这部分人在社会中是占绝大多数的,因此我们认为,牧场的相对公有是存在的。其次,就牲畜私有制而言,也表现在这个例子中,老夫妇用黄金买的四种牲畜及秃头儿得到的两千只绵羊、七峰骆驼都属于他们的私有财产,因此他们才衣食有了保障,地位有了变化,才有了“挑选”及使用牧场的权利。
第三,劳动分工。首先我们在史诗中看到的是性别分工,如妇女们负责缝缝补补、挤奶等家务劳动:“江格尔披着黑缎外衣,/这外衣是阿盖夫人用金剪细心剪裁,/众勇士的夫人精心缝制。”(第8页)“姗丹对洪古尔说:/……‘我去挤马奶来到草原,/……’。”(第20页)而男人们则负责放牧及征战,征战的例子在史诗中比比皆是,在此不复举,至于放牧的例子,在第十三章“雄狮洪古尔酒醉出征记”中有详细的描绘(第430——432页)。这些牧马人、牧牛人、牧驼人、牧羊人都是男人、好汉。史诗的创作者及欣赏者们虽意在赞美歌颂这些好汉,但实际上在他们看来,这些放牧的工作都是由男人来承担的。其次,我们在史诗中看到的是工艺的专门化。如,史诗中有好几处提到了“能工巧匠”这一名词:“最好的日子,/最好的时辰,/四十二位可汗,/率领六千又十二名能工巧匠,/破土动工。”(第6页)众勇士那些精美雄奇的宫殿都是这些“能工巧匠”精心修造的。我们知道,众勇士大都有自己得心应手威力无比的武器,如,阿拉谭策吉的宝剑、洪古尔的钢鞭。如此精致的武器如没有相当的专门技术是制造不出来的。史诗中唯一提到专门称呼的是铁匠,如:“那里有个国家,可汗名叫杜尔本,/有一位手艺超群的呼和铁匠,/……。”(第359页)并且提到有许多铁匠一同协作工作:“江格尔取来长枪,/铁匠们一齐奔忙,/将它按住,又烧又打,/转眼间修好了长枪。”(第360页)另外,史诗中还提到了造酒能手:“奴隶们为主子酿造美酒,/巴岩·双合尔酿造的酒最醇最浓郁;/……。”(第469页)所有这些人,无论是“能工巧匠”,还是铁匠、造酒能手,他们都是有一定专门技术的人,虽不能肯定他们已是专职的,以此为业,但其工艺的专门化已具一定的规模。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有一些根植于其文化当中的风俗与规则,决定着该社会经济行为的运作,游牧社会也不例外。从我们由史诗中所抽出的这些经济行为来看,无不与游牧社会及游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由于史诗本身所限,这些联系不可能在其中一一展现,但其确实存在则是勿庸置疑的。例如:我们看到在史诗中描绘了二种(或三种)经济类型,这几种经济类型在游牧社会都是确实存在的。据学者们的研究,实际上没有纯粹的畜牧业社会,牲畜可以提供人们的主要所需,但不能提供全部,人们往往以狩猎(或小规模的农业)及交换来补充所缺的部分。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古代的蒙古人是游牧狩猎民,可见狩猎在蒙古人的经济生活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仅管后来比例日渐减少,但蒙古人对它的印象还是相当深刻的,成吉思汗就经常用狩猎的方法来训练自己的士兵。就牧场公有制来说,据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研究:“古代蒙古氏族,当全族有可能在一个地区共同放牧,全体亲属或者共同居住在一个古列延,或者虽然分散居于各个阿寅勒而相隔不远时,他们就自然认识到牧地的公有。”(《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92页)在蒙古帝国时期,牧地的领有者是领主、那颜、可卜温,他们掌管着隶属于他们的百姓的游牧,随意指挥他们,分配牧地。鲁不鲁克指出:“……每一个首领(capitaneus)根据自己管理下人数的多少,都知道自己牧地境界,以及春、夏、秋、冬应该在何处放自己的畜群。”(转引自上书第178页)这时,牧地由氏族公有变为封建领主个人领有,但实际上仍是由属民们共有同使用。14—17世纪时,蒙古人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单位,是一种阿寅勒集团——鄂托克,它是以地域单位为基础的,亦即共同使用一块牧地的、数量不等的阿寅勒集团组成了鄂托克。可见,在14—17世纪之间,牧地公有仍然是存在的。就牲畜私有制来说,同样根据符氏的研究:在古代的蒙古氏族社会里,每一家族,每一阿寅勒都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主要是牲畜);各类财产如牲畜、帐幕、幌车、简单生产工具等都归氏族成员个体所有;牲畜的所有权以特殊的烙印标志来表明。在帝国时代,自由民、普通战士、庶民、家臣等都拥有用以从事游牧的私有牲畜。14—17世纪时,牲畜归阿拉特(平民)占有,阿拉特能经营个体畜牧经济。由此可见,牧场的公有及牲畜的私有是蒙古人畜牧业经济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蒙古人的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的。之所以在《江格尔》中对此没有过多的反映,我们认为,对于史诗的创作者们及欣赏者们来说,这是一件勿庸置疑、无须多言的事情,他们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责任编辑注:《论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文化内涵》(上) 见本专题1995年第10期313~3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