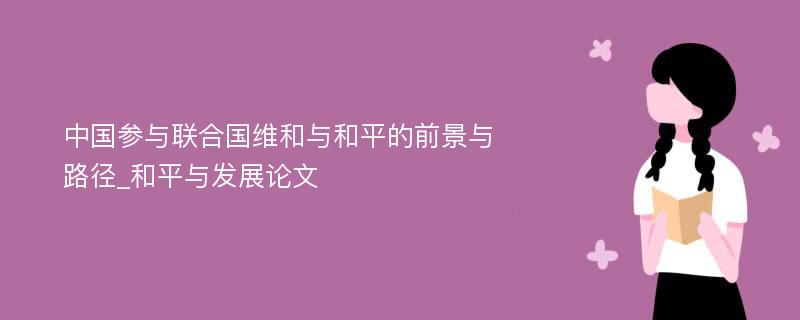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前景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和论文,联合国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持和平”(简称“维和”,Peacekeeping)与“建设和平”(简称“建和”,Peacebuilding)是联合国两项既不相同又密切相关的和平使命。从机构设置看,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任务分属两套不同机构。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1948年开始的传统项目,“建设和平”的概念虽早已提出,但有关机构设置的决议2005年才在联合国得到正式通过,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Peacebuilding Commission)是一个相对新的机构。从任务授权看,维持和平行动授权主要包括监督停火、维持当地的和平与安全、促进民族和解与对话、制止武装冲突、战斗人员的复员、遣返与重返社会,以及法治建设、行政机构重建、组织和监督选举、保护平民、保障人权、打击暴力犯罪等。建设和平的主要任务是支持冲突后国家的和平进程,包括协调各行为体筹集资源,关注冲突后国家的复原和重建工作,提供建议和信息,在政治、安全、法治、人权、人道主义和社会发展方面提出综合性战略等,其目的是防止冲突后国家再度陷入冲突,“以期实现可持续和平”。从资金来源看,维持和平行动经费来自会员国所缴纳的维和费,大会根据既定的分摊比额表向会员国分摊维和费用,并考虑会员国的经济状况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建设和平委员会则依靠会员国及各方面捐助的“建设和平基金”(Peacebuilding Fund)支助建设和平议程上的国家以及秘书长所指定的其他国家。
虽然在机构设置、资金来源及任务授权方面有所不同,但这两项使命共同关注和平、安全、政治、法治、人权等相互关联的任务,是联合国多维度、综合性和平行动的组成部分,联合国试图通过这两个领域的行动推动冲突中国家和冲突后国家走向可持续和平。迄今为止,联合国已经在全球实施了66项维和行动,有15项行动正在进行中。参加维和的人员总数达到98548人,还有文职人员17771人(截至2011年11月30日),以及联合国志愿人员2323人(截至2012年2月)。②目前,有22个国家在联合国建设和平项目议程之上,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截至2012年3月)。③
随着冷战的结束,联合国维和行动活跃起来,相关的学术讨论也明显增多,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间,国际学术期刊上有关维和方面的文章数量增长超过了350%。④《国际组织》这类权威期刊也开始增加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讨论,更有《全球治理》、《国际维持和平》等新兴刊物大量刊载有关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方面的论文。无论是在学术讨论层面还是在联合国的实践中,狭义的、传统的“维和行动”概念逐步扩大为包含“缔造和平”(Peacemaking)与“建设和平”、“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及“机构建设”(Institution-building)内容的综合性或“混合型”维持和平(Hybrid peacekeeping)。⑤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的扩大和参与角色的变化,国际、国内对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注和讨论也日益增多,季北慈、沈大伟等中国问题专家也就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撰写了相关文章。⑥
已有讨论提出了许多与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形成了很多争论热点和焦点,如联合国目前的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框架是否正确,以组织选举为“第一优先”的思路是否正确,西方主导的“国家建设”、“机构建设”是否能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成功地移植到非洲国家,⑦联合国维和部队能否担负“化解国家内部冲突”的重任,⑧以及中国是否应该派遣作战部队参与维和,是否应该派遣更大规模的维和部队,如何处理不干涉内政原则与维和干预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履行维和中的“公正”、“中立”等原则。⑨无论从发展和改革联合国维和建和机制看,还是从中国外交政策角度看,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尤其是随着利比亚、叙利亚这类问题的发生,“保护责任干预”、“选举干预”及国家重建、机构重建等已经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建设和平行动的重要内容,再一次降低了联合国干预的门槛,也使维和与建和行动的政治性更加明显,这无疑使中国在扩大参与维和和坚持不干涉原则之间面临更大挑战与调整。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一个影响和作用不断扩大并被期待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建设和平行动显然是无法回避的责任。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联合国维和建和内容和性质的变化,中国的参与不应再是当初的简单参与和简单扩大,从参与原则、参与理念到参与战略和政策,都应该有新的调整和磨合。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在对联合国维和建和变化趋势及中国参与的评估之上,对中国如何进一步改善和扩大参与维和建和提出自己的看法。
2011年4月,本文作者应邀参加了由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驻东北亚代表和奎克联合国办公室(the Quaker United Nations Office)组织的“中国学者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考察团”,对联合国在布隆迪、刚果(金)等国的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项目进行了考察,与当地政府官员、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当地媒体、联合国机构、联合国维和部队等进行了交流,包括对中国驻刚果(金)维和部队的访问。本文内容也基于此次对非洲维和建和的实地考察和访谈。
一、中国参与维和建和面临新的磨合期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以来,无论从联合国维和建和行动的变化趋势看,还是从中国参与角色的变化趋势看,中国的进一步参与需要经历一个新的磨合期。
(一)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基本评价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参与可以概括为积极支持、慎重选择、适度参与。尽管中国的参与相对比较晚,但中国在维和经费、人员派遣、参与范围等方面都在不断扩大,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就对待参与维和的态度而言,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中国坚定支持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⑩媒体及民众的态度也是基本支持的。(11)在参与政策和原则上,中国强调传统维和基本原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安理会授权、所在国同意、慎用武力、中立等原则。(12)
中国派遣的维和部队以工程兵、医疗队及其他后勤支持人员为主,也派遣观察员、民事警察等参与联合国维和。尽管联合国方面对中国派遣成建制作战部队有需求,但迄今除警卫分队外,中国尚未派出成建制作战部队。中国对维和建和中涉及政治、法治、机构重建等方面的事务参与很少,一直被认为是注重“硬”参与,缺乏“软”参与。再有,除政府行为外,中国其他行为体缺少参与,也缺乏与东道国及其他国际非政府行为体之间的联系。这也是已有研究中经常被提到的一点。(13)另外,中国对维和行动的参与比较多,对建设和平项目的参与相对比较少。
从联合国2011年底的统计情况看,中国应缴纳联合国常规会费分摊比为3.189%,排第八位。应缴纳的维和费分摊比为3.93%,排第七位。根据2011年12月31日统计,中国派遣的维和人员人数为1924名,排第十六位。在维和人员派遣方面,中国的贡献比发达国家和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贡献更大。在新兴发展大国中,中国的贡献远不如维和派兵大国印度,略少于巴西、南非。(14)在建设和平方面,目前建设和平基金的主要捐款来自欧洲国家及加拿大、日本等国,排名在前的国家是瑞典、英国、荷兰、挪威、日本、加拿大、德国、爱尔兰、芬兰和丹麦等。根据2006年到2011年建设和平基金捐款统计,排列第一位的瑞典捐款额为8444万美元,英国为6193万美元,荷兰为4646万美元。中国的捐款为400万美元,排列第十六位,与印度、韩国相同。(15)
总体来看,中国对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参与和贡献是积极的,也是慎重的。比较而言,中国目前的参与不算落后,但中国的参与模式和路径比较单一,参与的任务范围有限,存在适当扩大的空间,也面临进一步调整和改进的紧迫性。
(二)中国参与维和建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及联合国维和建和性质和内容的变化,中国的参与面临日益增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经常要面对参与还是不参与、有限参与还是扩大参与、强制干预还是非强制干预、武力干预还是非武力干预等两难选择。
首先,中国面临的矛盾困境来自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被期待发挥作用和被制约、被怀疑、被挤压的处境。一方面,中国面临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和国际责任的期待,联合国方面及会员国期待中国作出更大贡献,提供更多人力和财力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一些会员国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不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甚至视中国为潜在的威胁,对中国扩大影响保持警惕。这种国际大环境并不鼓励中国扩大参与国际多边军事与安全合作,导致中国对扩大参与维和建和选择慎重,保持低调。因此,中国的扩大参与需要经历与联合国会员国尤其是大国之间新的磨合,以增加相互信任。
挑战也来自联合国维和建和内容和性质的变化,这些变化冲击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传统的维和基本原则,也超出了中国熟悉的维和议题和领域,即和平与发展。这需要中国在今后的维和实践中进一步适应与调整,探索新的参与路径和模式。
涉及“保护责任”、“国家建设”、“机构建设”及“善治”等内容的干预给中国带来了难题。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一直困扰着联合国维和。自“保护责任”被提出后,在科特迪瓦、海地、几内亚比绍等案例中已得到部分应用。“利比亚式干预”是最典型的一例“保护责任干预”,预示着“保护责任干预”可能被越来越频繁地采用,包括在传统维和行动中授权“保护责任干预”,以及由“利比亚式干预”开始然后转向维和与建和的授权。作为联合国干预手段之一的维和与建和,更纵深地卷入所在国内政。在很多情况下,政治干预内容已经超出了人道主义干预内容。鉴于这种趋势,中国必须面对维和干预与不干涉内政之间更加紧张的关系,中国的参与面临更加复杂的环境。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这样描述中国面临的挑战:远在地球另一边发生的事情,动乱、内战、政权更迭等等,过去与我无直接关联,中国可以持超脱态度,以后就不再如此了。(16)
尽管国家建设、机构建设和善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是存在很多争议的概念,但显然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与建和的时尚话语和优先内容,被联合国自上而下地推行着。例如,2011年7月9日启动的“联合国南苏丹共和国特派团”,其授权包括:“围绕政治过渡、治理和建立国家问题”,“促进民众参与政治进程,包括就启动一个包容各方的制宪进程、根据宪法举行选举、推动建立独立的媒体和确保妇女参加决策论坛等事宜”,“支持制订有关安全部门改革”,以及“支持南苏丹共和国政府建立一个起辅助文职司法制度作用的军事司法制度”等内容。(17)在联合国启动的维和与建和项目中,除维持和平与安全外,从发动、组织、监督选举,到法治建设、行政能力建设、公安与警察系统改革、保护平民、人权、言论自由、媒体独立、反腐败等,也都在授权范围之内。很多方面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中国所熟悉的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多边合作。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调整和适应日益复杂的维和建和任务需求,也包括维和人员选拔、培训方面的改革。
还有一点是,联合国维和建和所涉及的行为体增多,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等不同行为体都参与到联合国维和建和行动中,成为联合国的维和建和全球伙伴。例如,北约、欧盟、非盟、阿盟、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维和建和行动,联合国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动员和组织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方面,尤其在建设和平领域。例如,联合国在非洲国家的维和建和任务也包括协助建立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反暴力组织以及新闻机构和媒体等,并为这些组织提供专门的培训。建设和平委员会“承认包括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在内的民间社会”在建设和平各个阶段的重要作用,也鼓励建设和平项目相关国家的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到建设和平的协商中。(18)
(三)有必要磨合的“西方思路”与“中国思路”
在维和建和实践中,西方国家的思路与中国的思路有所不同。
首先,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强调人道主义干预和国家政治重建干预,将国家机构重建、选举、善治等内容作为优先事项,如出资建立法律援助中心、法院、警察学校、“善治办公室”等。中国则强调尊重所在国的选择权和话语权,关注所在国的能力建设,重视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和平与安全的促进作用。中国的参与以提供道路和场地建设、派遣医疗队及提供其他后勤支持为主。
第二,如前面提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行动,也注重在东道国自下而上地动员、组织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国家重建和机构重建,如资助、培训当地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扶持独立媒体等。中国则缺少与所在国民间社会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在此次对非洲的考察中,我们也目睹了西方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宗教人员及其他志愿人员如何参与与联合国维和相关的活动,建立与当地民间社会的联系,并为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提供政策建议。在对联合国维和建和提出的建议中,呼声最强的也是关注微观层面“地方冲突解决”,听取“民间社会声音”,重视“地方机构”和当地民众在国家重建进程中的作用。(19)
第三,在冲突解决方式上,中国的传统思路和价值观是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西方思路则倾向于通过分裂、分离来“遏制和缓和暴力”,“使和平得以恢复”。(20)这类案例包括厄立特里亚问题、科索沃问题及南苏丹问题,目前也有通过分离手段解决刚果(金)境内战乱和冲突的主张。
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工作主要是按西方思路进行的。其目的是“改造国家的安全力量、政治机构和经济部署”,而这种改造“实际上就是执行和输出西方的自由主义方法”。(21)这些年来,建设和平基金的主要去向是和平协议的执行,包括安全部门、司法部门、行政机构的建设,以及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善政等,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只占很小一部分。例如在布隆迪,联合国帮助布隆迪组织选举,支持行政管理机构建设,包括建立善治办公室,发展和就业等问题排列其后。发达国家的资助项目也体现了“西方思路”,如德国政府出资支持联合国开发署和联合国中非乍得特派团建立法律援助所,荷兰、美国政府出资支持联合国在塞拉利昂建立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小组,日本、英国等国家资助联合国在刚果(金)建立警察培训学校等。
在非洲考察期间,考察小组与中国驻布隆迪大使进行了座谈,大使强调善治的确重要,但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等问题同样也很重要,应该给予关注。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审议建设和平委员会报告时也经常强调,建设和平应该重视当事国的优先地位,尊重当事国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应该优先关注引发冲突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包括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22)上述看法体现了中国的维和建和思路,也体现了对冲突根源及冲突解决方式的不同理解。支持在维和建和中“政治第一”的观点相信政治和解是和平的基础,解决因土地、资源、矿藏和选举等问题发生的冲突是建设和平的关键,而“发展本身会使这些冲突恶化”。(23)
目前的维和建和项目符合西方主流价值理念,具有比较完整的设计思路和方案,也建立了相应的报告、审核、监督和评价制度。但从中国思路和中国经验看,一些维和建和项目起点高、标准高,但收效小,且过于西化,与当地条件脱节,普遍存在重理念轻效果、重形式轻内容、重自由轻稳定、重选举轻安全与发展的现象。
当然,关于维和建和模式与思路的争论并不局限于中国与西方国家思路之间。一些研究也对具有“自由偏好”的“国家建设”模式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种带有“自由偏好”的建设和平努力并没有消除冲突的根源,也没有带来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反而再度诱发了冲突。持“安全第一”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建设和平不应在缺乏安全、信任或稳定机构的不成熟条件下开启竞争,他们主张一种更有秩序的、渐进式的、更具策略性的建设和平方案,强调“在争获自由与民主奖章之前应先建立起安全与稳定的机构”。(24)有关联合国维和建和的争论表明,在这一领域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各种思路和模式都需要实践的检验。
鉴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发展趋势及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中国有必要加大对参与政策和战略的调整,而不是一味延续过去的路径。促进不同维和建和思路之间的学习与互补是必要的,这也包括中国积极参与维和建和的项目创新,以及推动联合国维和建和思路的拓展。
二、中国扩大参与维和建和需要考虑的因素
中国参与维和建和并不是简单地扩大规模和增加捐助的问题,也不是中国单方面能决定的,中国的参与程度和方式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中国参与战略的调整应该基于对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主要包括:联合国维和建和的作用和效果如何,联合国维和建和目标与中国基本利益和原则是否一致,东道国及多数会员国是否支持。
(一)联合国维和建和是否必要
中国的参与应该考虑联合国维和建和的效果和前景,即维和建和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必要的,是值得中国扩大支持的。在此次考察中,我们听取了当地政府官员、民间社会组织对联合国维和建和作用的评价。我们显然听到了两方面的意见:一方面,无论在布隆迪还是在刚果(金),人们大都肯定联合国维和建和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联合国的表现也受到批评和抱怨。受访者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联合国的存在,当地治安情况会更不稳定,会有更多人死亡。在发展方面,联合国机构也提供了一些援助项目,有助于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布隆迪已举行了多次选举,没有爆发大规模暴力,被联合国视为成功的典型。在民主刚果东部地区,我们也看到了联合国援建的地方政府办公楼、法院、警察局、监狱等,这些设施为当地的民主和法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但联合国的不足与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布隆迪这样的小国,联合国相对容易取得成效,而在刚果(金)这样的非洲大国,联合国的作用十分有限,成效也不显著。联合国虽然帮助刚果(金)建立了地方法院、警察局和监狱,但这些设施目前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仅仅是一些建筑而已。在刚果(金),有罪不罚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大规模强暴妇女事件不断发生,要求联合国撤出、袭击联合国人员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联合国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还抱怨对联合国的援助项目不知晓。总之,当地人对联合国的看法只是有限肯定,而且是矛盾的。在一些案例中,东道国仅仅是勉强接受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存在,并带有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这种情况使联合国的维和建和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作为外部干预力量,联合国所制定的战略和方案在当地存在水土不服现象,作用十分有限,并面临各种矛盾困境。支持联合国维和建和的主张也承认,联合国在非洲“失败国家”所开展的国家重建、机构重建存在缺陷,如联合国建设和平战略所推行的选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地冲突,西方的国家制度无法被成功地移植到非洲大陆,外来援助国和非洲国家对“失败国家”、“冲突后国家”的认同无法一致,以及国际行为体不具备重建非洲国家的能力等。(25)联合国维和建和战略的优先项目与东道国需求之间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矛盾。联合国一方面强调“东道国的持续赞同和有效合作”是维和建和成功的关键,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决不能为获得东道国的赞同而“侵蚀本组织的各项原则”。(26)还有前面提到的各种矛盾,如重政府还是重民间,重选举还是重安全,重分离还是重统一。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联合国在维和建和实践中经常左右摇摆、进展艰难。
虽然有大力支持和推动维和建和的力量存在,对联合国维和建和的需求也有上升的趋势,但总体看,各方面对联合国维和建和作用和效果的评价褒贬参半、看法不一。无论是大国还是东道国,其态度都是非常慎重的。在理论上、政治上和技术上都没有出现对联合国维和建和压倒性的支持。鉴于上述情况,中国显然应该继续采取慎重和选择性的参与立场。联合国方面和中国都应为改进维和建和作出努力,而不是为效果不佳的项目一味简单地扩大投入。
(二)中国是否具有进一步扩大参与的利益需求与可能条件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维和与建和是中国的责任,从能力、财力和人力资源方面看,进一步扩大参与也是完全可能的。加之中国政府和民众对维和的支持,以及中国维和部队、警察在维和中已经树立的良好信誉。在此次非洲考察中,所到之处都能听到来自联合国方面和当地民众对中国维和人员的赞誉。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扩大参与维和建和与中国的自身利益和基本原则是否一致。
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经总结出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若干利益需求,包括: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的需求;提高国际声誉和国际形象的需求;锻炼国际型、开放型人才队伍的需求;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需求;维护中国海外利益的需求等。(27)毫无疑问,通过进一步扩大和改善中国的参与,中国的维和部队、警察及其他参与人员能得到在国际舞台上的锻炼机会,也有助于加强中国与联合国、地区组织、所在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中国的参与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的地区和全球安全环境,包括为国际海域提供护航,开展反恐、反海盗及反其他跨国犯罪的国际合作。总体看,中国不仅具有扩大参与维和建和的能力和资源,也具有扩大参与的利益驱动。
(三)联合国及会员国在多大程度上鼓励中国扩大参与
从相关学术文献到联合国官员和其他会员国,都乐于表达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期待。联合国长期积累的一条经验是“无论从政治、军事和财政方面看,大国对维和的投入都是至关重要的”。(28)联合国倡导建立全球维和建和伙伴关系,也非常期待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能提供更大的支持,认为中国的扩大参与对联合国是非常重要的,相信中国可以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并借助迅速发展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帮助消除南北双方在维和问题上的分歧,为建立一个“包容的全球维和联盟”贡献力量。(29)2007年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盖埃诺曾表示,期望中国派遣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包括空中运输、空中战术力量,“乐意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这方面的支持”。(30)
斯德哥尔摩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季北慈在撰写的关于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报告中认为,中国参与联合国多边安全合作应该受到鼓励,西方国家也应该加强与中国在维和研讨、培训及其他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相信中国扩大参与维和,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与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安全领域的密切接触,有助于促进中国为地区稳定和有效的国际维持和平行动作出更大的贡献和承诺。(31)在非洲考察过程中,我们也得到同样的信息,联合国方面、维和建和所在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学术机构,都希望能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期望中国更多投入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项目。
但如前所述,一些会员国对中国扩大国际影响的态度是矛盾的,鼓励中国扩大参与和限制中国扩大参与的想法同时存在。美国国防部2009年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中提到,中国参与远距离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使命的能力,也能够让中国用于保卫资源、获取通道和强化对有争议领土的要求。(32)“中国思路”与“西方思路”的差异以及“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削弱了中国扩大参与的积极性,是中国选择慎重参与或回避参与的理由。中国显然不会单方面扩大参与,同时又被迫接受一套中国不赞成、不熟悉的维和建和模式。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参与,这要取决于中国与联合国机构、东道国以及其他会员国之间的合作程度。
三、中国扩大参与的领域和路径选择
对中国来说,改进参与和扩大参与不仅仅是参与规模或捐助数额的扩大问题,拓展参与领域、创新参与模式、提升参与质量与效果更为重要。从这一意义来看,中国在许多方面存在改进和扩大的空间。
(一)参与《联合国宪章》及维和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合法、公正、必要干预
中国对维和建和的参与应该考虑合法、公正、必要、可能和适度。《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基本原则以及相关的维和基本原则,是中国参与维和建和的指导原则,坚持联合国授权、东道国同意以及反对过度干预、武力干预,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上,都不支持联合国维和建和的过度扩大,也没有任何国家在政策上和实践上支持这种扩大。
中国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参与了联合国框架内的维和建和干预,从中国强调的联合国立场来看,指导中国参与维和建和的依据应该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前面提到的《联合国宪章》原则和传统维和原则,其二是相关的国际法准则、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及会员国认同的共同价值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解、包容等原则,其三是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等原则。(33)中国依据这些原则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参与合法、必要的国际干预,是履行联合国会员国的共同责任,不存在是否“背叛”不干涉内政原则问题,也不应该因为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坚持而在维和建和问题上停滞不前。
(二)发挥传统领域优势,拓展非传统领域参与
中国的传统参与领域是工程兵、医疗队及后勤支持,这些方面的参与是中国的特长,是优势项目,赢得了广泛的信誉,值得发扬光大。但在一些对中国来说的非传统领域,中国也具有扩大参与的必要和潜力。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如行政机构、法治机构建设及重返社会、难民安置等方面,中国可以加强与联合国方面的合作,提供相关的培训支持,包括基础设施、设备、技术、人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也可与联合国合作,资助诸如“行政人员培训中心”、“警察能力培训班”、“复员重返人员培训站”、“妇女儿童救助站”、“民事纠纷调解室”等项目。
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不是维和建和的重点项目,但青年就业、性别平等、儿童保护等项目也在维和建和的关注范围之内。中国在这些方面既具有扩大参与的资源和能力,也具有扩大参与的可能。中国可以扩大对青年就业和青年培训项目的支持,包括资助文化活动中心、体育活动中心等相关项目。吸引青年人参与工作与文体活动,有助于使青年人脱离暴力,扩大团结和交往。在对非洲的访问中,我们看到中国援建的学校、医院、道路深受当地人民欢迎。中国也应该更多地尝试“以小见大”的项目,上面提到的这些项目在技术和资金方面要求不高,一两间砖木平房加上简单维修即可达到效果,容易操作且便于维持,也符合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宗旨和任务。
(三)扩大非传统行为体参与,加强与当地民间社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传统维持和平行动基本上属于“高政治”领域,是政府部门主导的事务。但随着维和建和授权范围和伙伴关系的扩大,更多非政府行为体也参与其中。
重视非政府行为体的参与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发展与当地民间社会及国际非政府行为体的合作关系,二是扩大中国参与人员的多样化,包括非政府行为体的参与。当地民间社会、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等是当地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协助联合国完成维和建和任务方面也试图发挥积极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如诊所、妇女救助中心、艾滋病检查中心、和平教育培训、技能培训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对象是当地民间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宗教人士。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历史悠久,一直参与国际和平行动,并与联合国建立了合作关系。组织和资助此次非洲考察的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就属于这一类,该机构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全面咨商地位”,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建和工作,与联合国方面保持密切联系,为联合国提供相关的咨询和政策建议。
相比之下,中国参与维和建和的人员构成有限,也缺少与当地民间社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一方面,中国应该不断拓展不同行为体的参与路径,使民间组织、慈善机构、志愿者、企业等可以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相关项目。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加强与当地不同行为体的联系与互动,考察东道国不同方面对维和建和的需求。在维和建和问题上,中国还应扩大与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等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可适当扩大中国警察的参与。从2005年1月到2011年1月的数据看,对联合国维和警察的需求不断上升,维和警察人数从6765人增加到14377人,增长了一倍多。同一时期,维和军事人员的总数从56197人增加到82196人,增长了约46%。(34)尽管联合国方面有要求中国派遣作战部队的需求,但作战部队的参与有更苛刻的条件限制,只能根据情况慎重派遣。此外,中国的司法人员、行政人员、技术培训人员等也可加入维和队伍,使中国的参与人员更趋多样化。
(四)从传统参与模式向多种参与模式扩大
中国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参与形式。例如,可以选择简单的附和型参与,对已有项目进行人员和捐助数量上的简单扩大。也可选择主动型参与,包括主动倡议、策划,主动开辟联合国维和建和新项目、新类型和新领域,即从理念、设计、操作到资金支持的主导参与。这意味着以中国思路、中国经验和中国资源推进联合国维和建和的发展,也包含了“中国思路”与“联合国思路”或“西方思路”的创新结合。因为在联合国框架内,中国主导的项目也需要得到其他会员国包括东道国的支持。
在建设和平方面,一个切入点是“可持续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结合。从可持续和平走向可持续发展,这是联合国的维和建和思路。考虑到目前建设和平基金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基金的主要去向是冲突后国家的政治与法治重建。除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扩大支持外,作为对联合国“善治和平”的补充,中国可以推进建设和平中的“发展和平”部分,将遣返安置、重返社会、稳定治安、青年就业、性别平等、消除贫困等建设和平关注的内容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
总之,中国的参与应该超出“修路筑桥建医院”模式,尝试新思路与新模式,尤其是探索在非传统领域的参与,包括更多参与维和建和政策与项目的创新,寻求中国思路与西方思路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小结: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建和的未来角色
中国以何种身份、何种模式参与维和建和,是国内外都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例如,围绕中国是否应派遣成建制作战部队参与维和这一问题,国内各方面存在不同看法。关注中国维和参与的国外学者也在研究未来中国的参与模式:是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成为维和“兵力派遣国”,还是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成为“经费贡献国”或“政策制定和后台谈判贡献国”。(35)此外,也有研究提出,如果中国放弃传统方式,则可能失去“硬”优势,并陷入与发达国家的“软”竞争;如果继续坚持传统方式,发达国家则将用“软”规则批评和制约中国,迫使中国就范。(36)
各方面的推测和分析反映出对中国未来参与角色的密切关注。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对中国参与维和建和的基本判断是:
第一,中国将继续以积极的态度支持联合国维和建和,并探索进一步的改进和扩大。中国的参与是对联合国维护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贡献,是履行联合国会员国共同的国际责任,也符合中国的利益需求。但中国的参与将仍然是十分慎重的。
第二,作为国际多边和平行动领域的合作,中国的参与和贡献需要中国方面的主动适应和调整,也需要中国同联合国方面及其他相关国家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扩大交流、增进信任与合作关系。
第三,中国不走“兵力派遣大国”道路,目前也还难以成为“政策制定和后台谈判”的贡献大国,但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参与都会有所扩大,并为此作出更多的贡献。除坚持中国传统维和优势外,中国的参与范围会更加广泛,参与人员也会逐渐多样化。
注释:
①见联合国大会决议《建设和平委员会》(A/RES/60/180)。
②见“联合国维持和平概况”,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zh/peacekeeping/resources/,2012年2月29日登录。
③见“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联合国网站,http://www.unpbf.org/countries/。
④Oldrich Bures,“Wanted:A Mid-Rang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9,No.3,Fall 2007,p.407.
⑤Chetan Kumar and Jos De la Haye,“Hybrid Peacemaking:Building National‘Infrastructures for Peace’”,Global Governance,Vol.18,No.1,January-March 2012,pp.13-20.
⑥见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China's Expanding Peacekeeping Role: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SIPRI,Policy Paper 25,November 2009,http://books.sipri.org/files/PP/SIPRIPP25.pdf;沈大伟:《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大有可为》,“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http://unpanl.un.org/intradoc/groups/public/。
⑦相关研究可见Séverine Autesserre,“Hobbes and the Congo:Frames,Local Violence,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3,No.2,Spring 2009,pp.249-280; Pierre Englebert and Denis M.Tull,“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Africa:Flawed Ideas about Failed Sta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4,Spring 2008,pp.106-139。
⑧〔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王忠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⑨李康云(Courtney J.Richardson):《对中国作为兵力派遣国的对比研究》,载赵磊、高心满等:《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年,第467—487页;广野美和(Miwa Hirono):《在当地民众中建立信任——维和中的公正性原则》,载赵磊、高心满等:《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第488—512页。
⑩见《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中国立场文件》,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2010年9月13日。
(11)2004年“零点指标数据网”(www.Horizonkey.com)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七成中国人支持政府参与国际维和行动,表示反对的约占一成。其中25.3%表示非常赞成中国更积极地参与维和行动,45.4%表示比较赞同中国更积极参与,11.1%表示比较反对更积极参与,2.5%的人表示非常反对。该机构2010年公布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7.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扩大对国际维和行动的投入,46.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维持参与现状,主张减少投入的占4.3%。见马丽:《七成居民赞成中国更积极参与维和行动》,零点研究集团,www.Horizonkey.com;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委托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所做的《中国公众和在华外国人士眼中的中国国家地位观调查》,http://www.horizonkey.com/tongqi.pdf。
(12)见《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中国立场文件》。
(13)克里斯·阿尔登、张春、贝尔纳多·马里亚尼、丹尼尔·拉吉:《非洲冲突后重建:中国日益增长的作用》,《国际展望》,2011年第6期,第100—115页。
(14)数据来源:“2012年会员国应缴纳的会费”,联合国网,http://www.un.org/zh/members/contribution.shtml;“维持和平的经费筹措”,联合国网,http://www.un.org/zh/peacekeeping/operations/financing.shtml;“Ranking of Military and Police Contributions to UN Operation”,2011-12-31,联合国网,www.un.org/en/peacekeeping/contributors/。
(15)数据来源:“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联合国网,http://www.unpbf.org/donors/contributions/。
(16)陈健:《中国多边外交面临新课题》,《解放日报》,2010年10月25日。
(17)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96(2011)号决议,2011年7月8日。
(18)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文件,“主席在非正式协商基础上提交的民间社会参加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暂行准则”(PBC/I/OC/12),2007年6月6日。
(19)Séverine Autesserre,“Hobbes and the Congo:Frames,Local Violence,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pp.249—280.
(20)〔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第274页。
(21)同上书,第288页。
(22)“李保东大使在安理会审议建设和平委员会年度报告时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网,http://www.china-un.org/chn/gdxw/t809098.htm,2011年3月23日。
(23)Chetan Kumar and Jos De la Haye,“Hybrid Peacemaking:Building National‘Infrastructures for Peace’”,p.14.
(24)相关争论见:Jens Meierhenrich,“Forming States after Failure”,in Robert Rotberg,ed.,When States Fail:Causes and Consequenc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155—156; Michael Barnett,Hunjoon Kim,Madalene O'Donnell,and Laura Sitea,“Peacebuilding:What Is in a Name?” Global Governance,Vol.13,No.1,January-March 2007,p.51。
(25)Pierre Englebert and Denis M.Tull,“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Africa:Flawed Ideas about Failed States”.
(26)见《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的报告》,联合国安理会文件(S/2010/611)。
(27)赵磊、高心满等所著《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一书分析了中国参与维和的各种利益需求,包括履行大国责任、提高国际形象、提升国家实力、加速军队现代化、维护海外利益、建设和谐世界等。见赵磊、高心满等:《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沿问题》。
(28)Fred Tanner,“Addressing the Perils of Peace Operations:Toward a Global Peacekeeping System”,Global Governance,Vol.16,No.2,April-June 2010,p.213.
(29)Ibid.,pp.213—214.
(30)“联合国维和事务主管访问中国”,联合国电台网,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2007年11月19日。
(31)Bates Gill and Chin-hao Huang,“China's Expanding Peacekeeping Role:Prospe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32)“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09”,http://www.cfr.org/china/annual-report-congress.
(33)可参考《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中国立场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http://www.fmprc.gov.cn/chn/。
(34)Monthly Summary of Contributions(Police,UN Military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roops),As of 31 December2011,http://www.un.org/en/peacekeeping/resources/statistics/.
(35)相关讨论可参阅李康云《对中国作为兵力派遣国的对比研究》,第487页。
(36)[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第111-112页。
标签:和平与发展论文; 联合国秘书长论文; 中国重返联合国论文; 联合国会员国论文;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