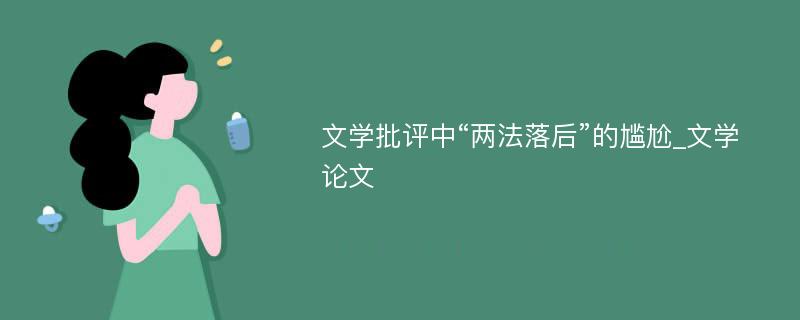
文学批评中的“二律背反”困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困窘论文,二律背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性与感性的夹缝:批评的位置困窘
批评是回答作者是谁、他的作品怎么样、读者对作品解读的途径又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但当批评自问批评是什么时,批评就会显出一种困窘。一方面它是站在理论的立场来评说文学现象的,这使得它具有理性的面孔;另一方面它又是站在切近文学现象的立场来感悟其魅力与价值的,这并不能靠说理的方式来体会并传达给他人,因此批评又有感性的一面。
批评处在理性与感性二者的夹缝中,这或许就可安定了批评的位置。但是这种安定在理论的分类上显得有些悖理。这就暴露出一种位置的困窘。事实上,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划分是始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或苏格拉底),柏拉图在假苏格拉底之口所撰写的一系列对话录中,首开了理性感性二分法的记录。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怀特海曾说:“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稳定的一般特征,就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①这话或许有些夸张,但考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曾说亚理斯多德思想“在欧洲雄霸了两千年”,而亚氏作为柏拉图一个判逆的弟子,他的所有重大成就都是在对其老师针锋相对的批驳中提出的,这样来看,欧洲哲学传统中柏拉图的影响就确实涵盖了几乎全部的欧洲传统的哲学问题。
在柏拉图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划分中,他是厚理性薄感性的,而且二者似乎永远不能调和。他在《国家篇》中引出了一个洞穴比喻,意思是说,一般的缺乏哲学修养的人可以比做关在洞穴壁里的囚犯,他们被铁链锁着,只能面朝洞壁。他们的身后远远地燃上一堆火,面前则是洞穴壁墙。这样,他们就只能看到身后物体与自己在洞壁上的投影,不可避免地也就以为这就是真实世界的样子。囚犯中某个人有次意外地逃到了阳光明媚、视野开阔的洞外,他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真实的世界,这个人也就成为哲学家。他自感有责任回去开导洞中同伴,但回去后他的说服工作异常困难,因为别人并未看过他所知道的东西,更为严重的是,他现在回洞中后由于早先阳光刺激,此刻他对洞中影子的辨析还不如同伴们清楚。在同伴们看来,这个哲学家从洞外回来后变蠢了。在这里,洞穴中囚犯们的认识就类比感性认识,哲学家认识类比理性认识,柏拉图本意是说明感性认识的极不可靠,但我们从中也可见出在理性与感性的二维中双方的一种矛盾和对立。理性应该是能引导感性的,但这一“应该”在现实的“实际”面前往往也无能为力。
在对柏拉图理性与感性二元划分的理论作了一番回顾与梳理后,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划分的基础就是在二者的相互矛盾上面,因此我们就很难说批评是处在文论理性与创作感性之间的一个中点的位置上,在矛和盾之间大概难以说出刚好能够调和二者的东西,或者在一张纸的两面能说出刚好既是这面又是那面的中点的位置,如果它处在两面之间,裹在中间则它就不是“面”了。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批评是作为一种寓于感性的理性或寓于理性的感性而呈现的,理性与感性的矛盾就孕含于批评之中而不是批评处在二者之间,其实这样来认识已抓住了批评的要害。但在这时重新又面临的症结就成为它是怎样“寓于”的了,因为在人的认识之中其实并没有二者的截然分离。人的理性认识的内容是在大量感性认识的升华中提取的,而反过来感性的认识也不能完全离开理性去做纯粹的感觉,当我们感觉某样物体是如何时,我们大都是抱以某一目的来进行感性体验的,否则这种感觉就难以进入人的精神世界,当一个人吃一颗糖时,他会感到甜味,但那是在他剥去糖纸时就有明确的尝甜味的理性目的蕴含其中才出现的,如他在品味时又去注意其它事情,则糖虽在口也会淡味许多。对此,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一个值得玩味的见解,即在性质上感性与理性是二分的,但在活动上二者却是合一的。“我所主张的是,没有一组观察不同与一组典型境况即规则性相联系的,观察试图在其中发现某种结果,我认为,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在感觉器官中,预期的理论都是遗传地体现的。”②从理性与感性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的活动的状况来看,简单地认为批评包含了此二者的认识虽则可以接受,但离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它并未能揭示批评包含感性理性的特殊性之所在。
我们只能说,当批评面临着更具理性色彩的文艺理论时,它是作为一种感性的东西呈现的,而这种感性可以为理性的文艺理论提供具体的经验实证材料;反之,当批评面临着更具感性特征的文艺现象时,它是作为一种理性的东西存在的,起着弥补抽象化的文艺理论在解答文艺现象时的“隔”的状态,能使文艺现象更充分地显示出其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在这里,每当批评面临一方就相似于另一方,总站在另一方的立场来同面临的对象对话,起到了沟通二者的作用。批评没有一个稳定的位置,它是在矛盾着的双方中随时调整、变幻着自己的位置。
在文艺理论与文艺现象这一对矛盾之间,批评不处在二者中任何一方的位置,但是批评作为一种活动总应有它存在的位置,它就只好在二者之间来回变动,又可说它处在两者中任何一方的位置。这就体现出它的位置的困窘,这种位置对它来讲只是“借住”而并不真正归它所有。
二、整一与杂多的平衡:批评的操作困窘
与批评的位置困窘相关,批评又面临在整一理论与杂多现象间的操作困窘。
这种操作上的困窘可以作如下概述:在面临众多作品或面临同一作品开放性的多种理解的可能性时,批评总是力图将这些不同作品以及作品更为纷纭的意义统合到某一理论的平面上,使之各各在同一理论的平面上得到解释。换句话说,批评是以某种相对固定的理论座标系统来看待也许本来就不处在同一座标平面的作品及在深度层次上不同的各种作品含义的。在作品方面体现为杂多,在理论方面体现为整一,批评操作的困窘就在于,它要么是牺牲了作品世界的丰富性来迁就理论的明晰、严整,要么则可能伤害了理论的明晰、严整来切入作品的世界。
对此问题,著名的文论家阿诺德·豪塞尔曾指出,当人们用艺术社会学的方法来对作品加以社会学的分析,找出其创作背景与写作内容的社会内含时,它往往可能把艺术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某一社会政治状况的对照物,从而使得作品的独特含义和读者对它的独特体验丧失殆尽。它的用语诸如“宫庭的”、“资产阶级的”、“保守的”、“乌托邦的”等等,每个范畴的对象太多,以至于很难明确其确切含义,作品的丰富性在这种单一化的分析下搞得面目全非。③其实,批评对于作品的可能伤害也并不仅限于社会学批评一条路子,而是普遍地存在的。前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曾指出在文学课程的作品分析中。“‘按层次’分放它的所有成分(确定它的人物是什么社会力量的代表,拆开情节安排,分析结构组成,阐明用什么语言手段描绘肖像和风景),那么生动的艺术感知还有什么可剩下呢?几乎一无所有!这就是有时连世界文学的杰作也在学校中‘失之交臂’,使学生无动于衷,甚至引起他们反感的原因之一。”④而我们知道文学教学中涉及到的有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语言学批评、文化学批评、风格学批评等多种批评模式,这里对作品魅力的消解就不只是哪一类型的批评的过失,而是采用整一的批评目标来面对杂多的文学现象造成的错位。
同样道理,文学理论在直接面对文学现象时也可能受到损伤。每种理论都是针对某一类型文学现象作出的反应,它的有效性都只能在针对特定对象时才有可能成立。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在医术上体现为擅长敷治创伤和手术技艺精湛,一个好的内科医生则是诊断准确和用药合理,超过了这个范围则都可能显得平庸甚至较差。对于文学来说,文学包含的方面是相当广阔的,不同模式、类型的文学理论往往是只就某一方面来作研究,其它方面则阙而不论。如俄国形式主义宣称只以作品为研究对象,而读者反应理论又只以读者的感受为审视目标,精神分析文论和原型批评兼及作家论和作品论重点是挖掘作家创作中的“潜意识”和“原始心象”。各种文学研究的方面不同,这使得各自确立的对象有别。如俄国形式主义因认为“陌生化”是文学的特质,就特别注重对诗歌语言的研究;结构主义认为文学的意义取决于对其深层结构的揭示,他们就尤其注重叙事作品结构尤其是小说结构的分析。由这些文论派别的差异可以看出,当我们力图将繁杂的文学现象整合到划一的理论规范中时是多么的困难,它使得任何一种理论面对整体的文学现象时都会力不从心,要么是它不能面面俱到,有些理论表述失之简陋粗糙;要么则是都显得论述周全,但也就失去了该理论的特色,成为大而无当、内容空洞无物的理论。
也许,人们会设想一种解决操作困窘的方法,那就是整一与杂多之间不要绝对化,对不同文学现象应该用不同文论来作解剖的武器,对同一文学现象,也应允许有不同理论的切入点来作多方位多层次的扫描定位。这种态度看来是解决困窘的良方,但是想一想,各种文学理论之间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形式主义、新批评认为只有作品才有资格作为文学研究对象,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又认为现在应把读者阅读作为研究重点,文学社会学理论认为作品的意义应该在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系统中才能科学地认识,结构主义、原型理论又认为作品的真正意义就在作品字里行间包孕着的深层结构中,毋需再向作品之外的世界询问,分歧和对立层出不穷,其间的矛盾与差异根本无法谐调。在人文学科领域中,某种方法同某种理论系统是有着联系的,以为可以单把各种理论系统的方法统合起来而不触及到各个理论系统本身,这只是一种天真的设想。
三、恒久原则与短暂体验间的选择:批评的取值困窘
批评活动既处于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和作品等文学现象之间,那么批评就面临着是主要靠拢理论来描绘文学现象,还是主要切近文学现象再充实文学理论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面临着充实文学理论的恒久原则还是强化、扩大文学现象的短暂体验间的矛盾。
对此,我们先来看一下清代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评论。金圣叹说:“《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⑤在这段话中,一方面金叹对《西厢记》作出了“妙文”的论断,另一方面又指出若有他人作“妙文”或“淫书”的论断都不再做理会。这就表明他作出“妙文”的判定是原则性的,而一般读者公众的见解则多只是体验的,这种体验人言言殊,殊无定准。作为原则应有普遍性恒久性,而作为体验则相当短暂。
在批评活动中恒久原则与短暂体验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区分也多少带有人为的痕迹,如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论断作为评价该书的原则也就源于他自己对该书的体验,而别人的体验由于缺乏理论支柱和体验的深入,或者干脆就离开了作品自身意义构成的规律性,不能上升到原则来认识。从这个道理来看,原则必然是体验的升华,体验则未必都能上升到原则。
伽达默尔曾从阐释学批评的角度对“体验”进行过探究。他指出,人的“一切经历物不是很快被忘却的,对它的吸收是一个长久的过程,而且它的真正存在以及意义就恰恰存在于这个过程中,而不只是存在于这样的原初经验到的内容中,因而,我们专门称之为一种体验的东西,就是指一些未忘却的和不可替代的东西,这些东西对领悟其意义规定来说,在根本上是不会枯竭的。”⑥这里还显露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体验作为过程,它在历时上是延伸的,同人的生命活动相伴相随;它在共时态上又是“不会枯竭的”多义复合体,可作多重理解和解释,而反之从体验中提取的原则却只有那么单纯的几条。原则作为恒久的道理呈现,但它本身不过是一段体验过程的产物;体验作为即刻的、瞬间的感悟,但体验的过程则是永无终止之日的劳作。
批评取值的困窘主要就在于,它如是力图从作品中擢升出几条有权威性的规则,那么某种意义上它就背叛了作品,就相对地封闭了对于作品新的体验的生成;它如是力图丰富和发掘对于作品的新的有价值的体验,则这一活动的代价就是永远没有一个结果,这对文艺批评作为文艺理论在现象层上的衍伸又是悖离。在如此两难境地中,批评要顾及其中一方就势必伤害到另外一方。
恒久原则和短暂体验的差异还在于,恒久原则是以对普遍性的关注和揭橥为要务,短暂体验则是以独特性的感受和体味为宗旨,恒久原则是在超越文学作品内部差异的前提下实验的,短暂体验则要在深入这种内部差异中来完成。这种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关系在科学中可以较好地处理,但在艺术领域中,每个作品的个别性是在反对挪入一般性的理解中来展示的,文艺的一般就在于文艺现象个个都是个别。卡西尔对文艺与科学的这种差异曾作出说明:“科学意味着抽象,而抽象总是使实在变得贫乏。事物的各种形式在用科学的概念来表述时趋向于越来越成为若干简单的公式……但是一当我们接近艺术的领域,这就被证明是一种错觉。”“画家路德维希·李希特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他年轻时在蒂沃利和三个朋友打算画一幅相同的风景的情形。他们都坚持不背离自然,尽可能精确地复写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然而结果是画出了四幅完全不同的画,彼此之间的差别正像这些艺术家的个性一样。”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学批评要想成为一种“科学”,就应借鉴科学综合的方法,侧重于对恒久原则的发现、验证和应用,具体操作上多从理论原理出发来解剖作品;但同时它又应采取科学的实证态度,需多从具体的个别的作品来深入体验,发现作品的不能被简单挪入到任何抽象条理的独特感人的东西,在操作上就应从作品体验出发来完善和修正理论。回溯中西批评史上的状况,西方一般是采用的第一条途径,中国传统上是履行第二条途径。真正的理想则是综合两方面而来的第三条途径,但这是相当困难的。
四、描述与评价的中和:批评的方法困窘
批评这一概念的含义可以在过宽或过狭的范围中交替作用,而这些词义都可被人接受。从过宽的方面来说,它可以同整个文艺理论、文艺研究的范围等同,甚至更为宽泛,如韦勒克所指出,批评这一术语,在17世纪时外延扩大起来,它可以“既包括整个文学理论体系,也包括了今天称之为实践批评的活动和每日评论。”⑧这种宽泛意义上对批评一词的用法,在对二十世纪出现的各种新兴的文学研究学派均可冠以“××批评”上也可见出。从过狭的方面来说,它仅指一种评判或判断的意思,古希腊语中“krites”是后来批评的原型,它意为“判断者”,以之与文学艺术的创作相对应。在这宽狭两种意思之间,批评可以被视为一种探讨文艺的活动,它与创作有别,也与文艺理论对文艺一般性的关注有别。
我们暂时把批评的对象聚焦在作品上,而将作者、文艺思潮与运动等对象撇开,那么可以说批评的任务有三条,即对作品的描述、解释和评价。⑨这三条任务的核心是解释,即批评是意在把作品意义通过另一种语言形式昭示出来,使得多义的或不确定的艺术语言转换为另一种意义相对明确和确定的科学性语言,同时它也可以把文艺理论抽象的一般性的表述转译为针对特定作品的批评话语。在批评的解释这一活动中,它必须深入到作品的内部关系,并对作品的内蕴表白某种情感的和思想的态度,这也就是说,批评作为解释是在对作品加以描述和评价的工作中来进行的,批评的任务实际上可以具体化为描述与评价两方面,至于解释则不过是这两方面的综合。它既有较为客观的描述也有倾向于主观的评价。但就在这一综合中,批评在方法选择上具有困难。
从思维的层次上来说,对作品的描述是力图站在作品的立场来勾画出作品脉络,它是站在作品中的思考;对作品的评价则是试图站在作品之外的立场,是退一步来检视作品及其对作品描述的思考。描述是对艺术创作思维结果的思维,评价又是对描述结果的思维,也即是对创作思维结果进行思维后的思维,每一环节都是思维向后退一步的检视。在形而上的立场看,它实际上是将那曾经进行过思维的主体加以客体化认识的方式,思维主体是以外在于它的客体作为思维对象的,这样,它可以昭示出客体的一些性质。但是思维主体自身不过是思维过程中的一个“黑箱”,当一些问题纳入思维主体后,得出了思维结果,问题本身与思维结果都是明确的,但思维过程则永远是一个迷。现在将思维主体客体化后,就是力图表明思维主体的合理性,而不仅仅作为对思维结果的检视。不过这种追问的结果如何呢?正如阿部正雄指出:“但在这个回答中,却出现了两个‘我’:一个发问的‘我’:和一个被问的‘我’。那么,这两个‘我’究竟是同一的,还是相异的?它们必然的同一的,但又相互区别的,因为发问的‘我’是问的主体,而被问的‘我’,则是问的客体。”“但是,真我却因我们反复询问自己而逐步后退。这一过程永无止境──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后退。然而,在不断被迫从事这一无穷尽的抓捕过程中,我们同时也被迫认识到:这个可能被抓到的东西,无非是一个客体化的、僵死的自我而已,”⑩就是说,每后退一步的思维都是为了抓住前一步的思维,但在后退中早先前一步的思维已被客体化了,它已失去了思维自身的活性。
批评方法选择的困窘主要就在于,它如作为描述是站在一个层次,它如作为评价又是站在另一个层次,在前一层次时评价还未出现,在后一层次时描述又被客体化了,从而失去了其真实的存在。在描述这一层次中,批评是力图从作品的个别性中进行有价值的发掘;而在评价这一层次中,批评则又是力图对于作品的一般性加以关注,把个别化的作品放置在金字塔式的艺术价值图系中加以衡量。我们不能贸然说这两个方面就注定了无法调和,但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在对此矛盾中的关系还根本未加梳理的情况下就平列式地将二者都作为批评的要务提出,确实就使得批评在二者中难以兼顾,使具体批评在操作上要么是顾此失彼,要么则是模棱两可,问题未能说透。
五、批评的自觉与批评的困窘
我们在上文提出并分析了批评的若干困窘之处,在这样的一个分析中,我们并不是否定批评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而是认为批评的正常运行及发展都必须要有对自身短处的自觉,而这种认识就正是在批评已成为人的自觉活动的前提下来认识的。
在古代,批评并不作为一种专门性的活动,它与文艺创作作为一种展示学问和创造能力的工作的声誉形成鲜明对比。在那种情况下,批评的任务就在于阐释作品和评价作品,而从一般艺术欣赏的角度看,做到这一点似乎是并不困难的。因此,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可以有桂冠诗人或相当于此类称号的艺术家,但绝难找出有此类称号的批评家。当然,也并非说批评的难处无人知晓,如中国刘勰就指出:“知音实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但在这种知晓中,我们只需指出两点关键之处,一是批评作为“知音”来理解,这毕竟要比创作能“造音”的价值低下;二是批评的困难似并不在它工作本身的艰巨,而是多数批评家的蹩脚和拙劣,优秀者仅“千载其一”,这与其作为对批评工作的夸赞,倒不如理解为多数批评家的拙劣与艺术家的优秀形成反差。从这一角度认识,事实上批评的困窘还未被人自觉。
西方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批评家是法国的圣·佩韦(1804-1869),从那时起批评有了很快的发展,由于圣·佩韦及其后继者的工作,十九世纪在文艺学上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十九世纪在批评上的贡献在于,批评也已不只作简单地评判或阐释作品的工作,而是一门独立的研究文艺的学问。到了二十世纪,情况有了进一步发展,如美国批评家韦勒克指出的:“十八、十九世纪曾被人们称作‘批评的时代’。实际上,二十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在二十世纪不仅有一股名符其实的洪流向我们汹涌袭来,而且文学批评也已获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在公众心目中占有了比往昔高得多的地位。”(11)二十世纪产生的文艺学诸学派,从二十世纪初发轫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文论,到二十世纪中期红极一时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权主义批评,再到二十世纪已近尾声中登场的新历史主义等无不可以以“批评”来称谓之。它表明,批评已逐渐深入到文艺理论的范围。在二十世纪,文艺学上的主潮已不再是由某一哲学理论体系为核心来构筑文艺理论体系,而由一系列的批评理论来扩展为文艺理论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批评反省到自身的困窘其实也就意味着批评的真正自觉。批评的困窘正是批评的独立带来的创痛。
在文学批评面临的位置困窘、操作困窘,取值困窘和方法困窘等一系列的困窘中,作为一个“困窘”的课题是我们今天才能够较清晰地意识到的,但是它的存在却是批评从最初诞生之日起就有了,只是它采取了一种文学理论的附庸或文学创作的附庸的形式,结果这种矛盾被消解在文论与创作之间,成为文论与创作之间矛盾的表征,批评则并不直接面对“困窘”的难题。那么,从早已有之的症结到了今天才予诊断出这一角度来说,我们揭示出文学批评包含着的“困窘”并不意味着批评的受挫,而恰应被视为批评的成熟。
从更大的范围看,批评包含的一系列“二律背反”式的困窘其实并不是批评所独有的,康德提出的哲学二律背反命题中就已普遍地涉及到了人们二律背反的活动与观念,或者也可说是在更为久远的辩证法的思想中对事物的两面性的认识中就已普遍地涉及。批评困窘的意义在于揭示出了批评并不是一种固然之物,而是一种生成之物,批评所包含的一系列的矛盾正是批评在向前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因,而我们对这些动因的分析揭示,正是把握批评性质流向的研究工作。当然,我们在本文还只是揭示出了这些文学批评中的困窘,而更为艰巨的工作是具体解释和解决这些困窘,这有待于笔者另文来述及。
注释:
①引自《外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72。
②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P.76。
③《艺术社会学的范围与局限》,见《美学文摘》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
④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282。
⑤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之二》。
⑥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95-96。
⑦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P.183-185。
⑧(11)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P.32,P.326。
⑨有关批评的具体任务的分类,可以参见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P.156。奥尔德里奇《艺术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P.111。
⑩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P.10,P.12。
标签:文学论文; 二律背反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西厢记论文; 康德论文; 文艺论文; 文艺理论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