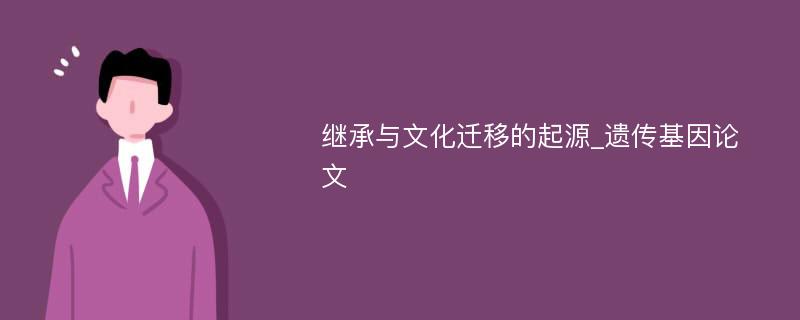
遗传与文化转移之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洛尔·弗林通过神经学技术给华盛顿的立法者们以极大的启发。作为全国精神病联合会的执行主席,她历数包括费用分析到道德教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力争通过一项禁止歧视精神病人的立法,但是到目前为止,她最强有力的鼓动工具只是光电变换器(PET)扫描仪。 她携带一组色彩纷呈的大脑图片到国会展出,为那些立法者们了解“破碎”大脑的行为提供了一个“窗口”。“当他们看见这并不只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模糊不清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理状况时,他们就理解了,并说‘不错,问题是在大脑里’。”
把精神病看作一种大脑疾病,对于分清什么是精神分裂症,什么是精神抑郁症是至为关键的。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对美国文化进行生物解读的一个更为广泛的例证而已。这种解读分析已持续了10多年。基于政治和科学两个方面的原因,要想把这二者区分开来总是不可能的。包括犯罪行为,由吸毒上瘾而产生的精神错乱及性指向等每一件事,在今天更多地被看作是遗传因素决定而非自我选择的结果。甚至人的基本性格看起来也越来越像是遗传因素的结果。几乎是每一个星期都有一篇有关发现决定某一性格特征的新遗传基因的报道。根据新的研究,猎奇、宗教狂、羞怯,以及离婚倾向甚至幸福感(或者缺乏幸福感)等性格特征的形成,部分原因是一种基因影响的结果。
这种文化转移有政治和个人双重涵义。就个人而言,一旦相信基因的强大力量,就必然会削弱个人品质的潜在作用——如意愿、选择能力,以及对上述选择的责任感等等。如果罪在你的基因里,那么你自己完全可以不负责任。举例说,酗酒者把自己看做是自己生物性的一个可怜的牺牲品,而不是一个对自己行为有控制能力的明知故犯者。遗传决定论可以释去这些所谓的受害者和他们家属心头的罪恶感,或者说把他们永远禁锢在痛苦中而不得翻身。
从政治角度来说,生物决定论使各种问题诸如同性恋权利、医疗保健、青少年犯罪审理和福利改革等公共政策的辩论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先天后天之争中的后天论者们认为,政府的干预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而社会又无法为每一个不幸公民的坏运气进行补偿等。在此种种认识的参与下,企图消解社会作用的力量显得更加猖狂起来了。这种对文化的生物化阐释现象一直伴随着国家在政治上的右倾化的转移,因为在传统上保守派对人的自我完善能力比自由派更持怀疑态度,这一点也许并不是巧合。所以,东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利昂·卡明认为,要想发现某个人的政治倾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问他对遗传学的看法。
即使如此,遗传决定论有时还会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果,给那些受害者带来的更多的是蔑视而不是同情,是排斥而不是包容。文化批评家们现在正在筛选出那些无法预见的生物学政治化现象,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暴力、精神病、酗酒和性指向。
1.暴力的性质
要想了解文化生物化已经进行得多么深入及多么政治化,只需看一下在今天业已形成的城市团伙暴力问题。几年前,当时的政府最高心理保健机构主席弗雷德里克·古德温和所谓的“联邦暴力起源”协作来确定贫民区里有暴力犯罪倾向的孩子的身份,目的在于对这些据推测是神经系统错乱而犯罪的青少年进行药物治疗。古德温自己遭到解雇,原因是他把具有侵略性的青年男性与生活在热带地区的灵长类动物相提并论。随之,这种暴力起源的说法以触犯众怒而自取灭亡。但是能够提出这样一个生物医学方法本身,就表明了知识界的钟摆已经偏向生物学到了何种程度。
20世纪30年代的优生学运动至少部分反映了人们盼望消灭惯犯的愿望。许多年来,人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找到侵略、暴力以及犯罪行为的遗传根源。比如,196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囚犯比其他人多一个Y 染色体(意味着有更多的男性基因)的可能性要大。在当时,将染色体缺陷与犯罪联系在一起的证据显然是不够的,不充分的。但政治总是比证据更加捷足先登。随后不久,波士顿的一家医院开始着手调查那些有缺陷的婴儿,一旦这些孩子的人格问题变得明显的话,可以早一点进行干预。这项调查后来停止了,原因是研究表明这些XYY孩子, 除了智力稍有点迟钝外,并无表现出超常的侵略性。
和许多精神病理学的现象一样,犯罪性侵略行为实在难以准确界定,因而研究也十分艰难。的确,犯罪和酗酒经常是交织在一起,所以很难知道遗传标记和酗酒及犯罪动机之间是否有关系,或者和人格特征等其它方面完全有联系。比如说,在1993年“全国调查委员会”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已发现充分证据证明遗传基因对个人的反社会性人格错乱有影响。但是同时它又称,与此有关不止一种基因,上述不确定的基因和破坏性行为或攻击性行为的实际实施,或者一个充满野蛮和暴力人生的生成,两者之间鸿沟之巨实需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信念飞跃。
这是一次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飞跃。当遗传学家XANDRA BREAKEFIELD几年前宣布找到了一个暴力犯罪和遗传基因之间的联系后,她立刻接到许多询问电话,打电话的律师们代表囚犯进行咨询,他们希望这种遗传发现会使这些人所犯的罪行得到赦免。
2.突变和感情
早在20年前,美国“心理健康全国委员会”曾资助系列研究,包括经济萧条、失业及城市病等诸项对人的感情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精神病学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分支:“社会精神病学”。通过铲除诸如贫困和种族主义等社会病源来帮助病人康复,今天看来,这项工作的可行性值得商榷。现在“心理健康全国委员会”已将研究重点全部放在大脑研究和感情障碍的遗传作用上。
重新调整联邦研究重心的决定是基于科学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在神经科学研究方法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为新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这在上一代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项研究的结果是推出了新的药物,可有效治疗某些神经错乱症。不仅如此,还出现一个要求重新解释精神病病因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在上一代人那里,有关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理论认为:这种摧毁性的感情和精神分裂症是由母子关系冷漠和疏远所致,是母亲那种无意识的不愿意生出她的孩子的愿望的直接结果。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游说运动,抨击这种无中生有的母亲过失论。直到20年后,这种弗罗伊德时代的荒唐理论才寿终正寝。今天,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心理疾病是大脑的毛病,或许与遗传因素有关。
然而,这个神经遗传理论的胜利并不是最后的胜利。举个例子来说,家庭和消费者团体一直在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辩护说:精神分裂症象癫痫症一样同属大脑疾病,证据之一是它可以通过大剂量的镇静类药物来治疗。但是,一些盈利性的医疗公司已经抓住这个病例不放,他们只容许药物治疗,除此之外的任何方法都不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因为药物治疗见效快,而且得到了生物精神病理专业论点的验证。“美国精神病治疗协会”今年发布了治疗精神错乱症的详细指导说明,其中不仅包括各类药物,还有一系列的社会心理治疗,当然这些治疗不会得到保险业一分钱的资助。
对造成严重精神紊乱的遗传基因的探索并不能够说明一切。对一些家庭、被收养者及在出生后就分开的双胞胎几年的调查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和癫狂与抑郁交替出现的疾病都是在家庭范围发作的。但是如果这种家庭模式是遗传基因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这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因为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兄弟姐妹(包括一半具有完全一样基因的双胞胎)并没有得精神分裂症。由此,行为遗传学家们怀疑,在这种疾病后面有几种基因在起作用,某种环境压力,也许还有一种病毒或出生并发症,也有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
在过去有那么几次, 研究者们报道过严重的精神病和一种特殊的DNA(脱氧核糖核酸)间的“联系”。比如阿们宗派(AMISH)一项很有名的研究声称找到了癫狂与抑郁交替发作型精神病和11号染色体异常间的联系。但是当其他研究者试图重复这些试验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新发现中没有一项经得住检验。
尽管有人同意严重的妄想症有其遗传根源,批评家们所关心的还是对其它精神病的生物化解析。据精神治疗师报告说,一些患者来向他们求药,并声称他们是生物学悲剧的受害者,其中有一个患者说他能够“感觉到他的神经细胞在失效”;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它说明了文化与生物学之间的充分渗透。
一些精神病理学家正在从精神病严格的生物模式中退出来。精神病理学家基思·拉塞尔·阿布娄已经将“性格”概念重新引入他的医学实践中,他告诉那些情绪抑郁的病人他们不仅有责任也有能力摆脱这种疾病。正如阿布娄所看到的那样,懦弱的性格会使患者的病情加重。这种看法在精神病理学领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在精神病理学这一领域,那怕暗示病人要为他们自己的某些痛苦负责都是忌讳的。
3.诱发酗酒的遗传基因
有关酗酒的遗传学研究的最佳说法是:它尚无任何定论。但这并未阻止人们将遗传学论点用于政治目的。酒精中毒的病例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精神病理学和大部分治疗机构,(也许最重要的是)被民间戒酒组织AA所认可,这意味着应该告诉那些企图通过过量饮酒来获得某种解脱的人:他们有病(虽然这种病的确切性质尚不清楚)——也许是遗传原因引起;治疗的唯一办法就是戒酒。
不过,证据还未充足到非得提出上述要求的地步。对于遗传基因究竟是如何导致过量饮酒,存在着好几种理论。比如说,天生对酒精反应不敏感可能会造成一些人饮酒过量;也有人以为,不同的酗酒者对酒精的消化能力不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可能是因为酗酒者继承了某种易导致冒险和寻求刺激的性格。一些研究家族血统和被收养者的人士曾指出:一种酒精中毒方式往往和某一种特定的家庭模式(如男性精神分裂症的早期发作)相对应,但他们又无法确定这种模式,这种情况也不足为怪,因为给酒精中毒下一个定义本来就很难。有些研究人员通过酒后驾驶记录来确认某人是酗酒者,而另外一些研究人员则凭藉上瘾症状或每天的饮酒量为标准。这就是遗传学家所称的“肮脏显型”,人们以如此不同的方式过量饮酒,以至于特征本身变得十分难以辨别,而家庭模式不仅各不相同,而且还相互冲突。
面对以上这些研究方法中出现的难题,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找到一种(或数种)或许和酒精中毒有关系的具体遗传基因。199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神经紊乱最严重的一种形式和一种基因有关,此种基因可解释为神经传感器所必需的化学受体多巴宁(一种治疗脑神经病的药物)。研究人员甚至研制并获得了一项遗传突变试验的专利,但是接下来进行的证实多巴宁和该基因关系的努力却失败了。
在探讨有关酒精中毒和其它可导致上瘾的神经紊乱症状的过程中,选择和责任感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即使科学家们能够发现一种或几种导致人体酒精中毒的基因,也很难知道这种遗传基因“负荷”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一种对饮酒决不宽容的文化环境如阿们宗派里,这个基因当然不会导致酗酒,所以严格地说,它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即使在饮酒比较普遍的文化中,一生饮酒也是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在里头,实在很难一下子从核糖核酸跳到道德堕落的表现或是性格瑕疵而予以严厉的谴责。如今,许多人担心,这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酒精中毒的疾病模式,事实上为一些人的自我毁灭行为提供了一种借口。正如心理学家斯坦顿·皮尔所言:“给青年人灌输这样的观点,即他们有可能成为酗酒者,可能恰恰就把他们变成了酗酒者,而且速度极快,……”
4.欲望的突破
把注意力仅集中在对精神病理学的生物解释上是会犯错误的。文化演变的意义却要广泛得多。在上一代人那里,同性恋组织在和有组织的精神病学的战斗中,曾成功地为自己辩护,称性指向是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应该将其从精神分裂症的范畴中删除。最近,该组织又在找到同性恋是生物特征(或遗传性特征)而非生活方式的选择的新证据而大肆庆祝。
有三条证据可证明遗传因素在同性恋的形成中起着作用,但没有一条有决定性意义。一项对双胞胎和被收养的兄弟姐妹的研究发现,男同性恋者中大约有一半人是完全相同的孪生子, 而非孪生子占的比例是22%,被收养的人占的比例是11%;在女同性恋中也发现类似的分布模式,而且这个模式与决定人类性指向的某种遗传因素相吻合。批评家们争论说,这也可以从许多孪生子共有的相似经历来解释。当然,有一半完全相同的孪生子并没有变成同性恋者……这就说明,除了基因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起作用。
1991年发表的一项受人瞩目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同性恋者身体里发现了一种清晰的解剖学特征,西蒙·勒韦在分别解剖了男同性恋者和异性爱者的大脑后发现:人体视丘下部的某个细胞核在异性爱者身上比在男同性恋者和女异性爱者身上要大两倍多。虽然勒韦无法解释这种神经性差异是如何演变为同性恋的,不过据他猜测,这个细胞核和人的性指向是有关系的;众所周知,视丘下部和性反应是相联系的。
迄今为止,发现遗传因素和同性恋之间确实有联系的唯一一项研究是由“全国健康协会”的生物学家迪安·哈默先生进行并于1993年公布于世的。他在75%的同性恋兄弟的X染色体内找到了一种遗传标记。 这片DNA的作用和意义目前尚不知晓, 而且后来的研究并没有能够再现哈默先生的结果。
就自我选择和生物决定论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而言,同性恋代表了一个矛盾体。当哈默报告了他的遗传发现后,同性恋者中许多人为之庆贺,认为社会对一种源于生物学和DNA 的行为要比对自我选择的行为可能会更加宽容一些。勒韦本人就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说自己开展这样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同性恋事业。在发生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桩十分重要的有关同性恋权利的案件里,哈默曾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当时,有点阴差阳错的是,自由派人士发现自己站在遗传决定论的立场上讲话,而保守派坚持同性恋是一种自我选择的生活。赞成同性恋权利的人认为,生物特征决定了同性恋者的法律权利应该得到法律保护。
5.历史的警钟
据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加兰·艾伦的观点,历史告诉我们相反的情况。在二三十年代的优生学运动中,在美国和欧洲,社会对人类的变异和恶运愈加苛刻而不是越来越宽容。基于东欧人比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低劣的种族理论,美国国会通过了由总统签署的1924年限制移民法案。到1940年,有30多个州制订了相关法律,允许对所谓弱智儿童和精神病患者等一类人进行强制清除。在欧洲,优生学狂潮的最终结果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在德国第三帝国发起的净化种族血统的狂热运动中,同性恋者没有得到额外的同情或保护。
艾伦担心可能会出现一场新的优生运动。虽然可能不叫这个名字或采取同样的方式,它更有可能对那些不幸的人采取医疗定额限制的方式。今天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与两次大战期间的社会经济状况十分相似,都为优生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有甚者, 艾伦认为, 加利福尼亚的第187号倡议使人想起20 年代对有限资源的剧烈竞争(最终导致了美国社会对外来移民的仇视)。而且,他还提醒我们,优生学过去在欧洲和美国并不是一次边缘性的、一成不变的运动,它是一次“进步”运动,旨在利用科学,使之在减少人类痛苦和不幸以及提高社会效益上发挥作用。
艾伦的忧虑应该有其道理。不过,也有迹象表明,我们正处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转移的颠峰。越来越多的专家,包括那些富于牺牲精神的生物学家们感到,遗传学的威力被夸大了,该到纠正的时候了。而且,也有迹象表明,真正的美国人也许对它并不那么认真。根据最近的“美国新闻博泽尔民意测验”,在5个美国人里,只有不到1人相信遗传基因在控制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有3/4的人认为环境和社会对人的影响更加巨大。至于这里所说的行为是否象吸毒成瘾、精神病、暴力或者同性恋特征等一样同属精神分裂症,大部分人以为遗传起了某些作用,但并不是主要作用。相反,有40%的人认为在同性恋的形成中,遗传不起任何作用。还有相同比例的人认为,遗传和吸毒成瘾及犯罪之间并无瓜葛,在所有接受测验的人当中,大部分人相信人的生活完全受本人选择的影响。
上述这些数字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解释为神经遗传决定论已经变成了“知识阶层的宗教”,但它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美国人的共识。也可以说是我们正在目睹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校正。在经历了一系列没完没了的神经科学和遗传学方面的喧嚣之后,公众不但已兴趣索然,甚至对批评家们所描述的那些社会控制的种种方式变得忧心忡忡起来。
不论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对遗传威力的新怀疑和科学所要揭示出的实质是相呼应的。的确,“成为……的遗传基因”这个说法据哲学家菲力普·基奇看来会给人以误导。基奇是《未来的生命》一书的作者,他批评了那些“基因之谈”——即那种谈论遗传学进展时所采用的过于简洁的缩略语。它导致了大众对DNA的真正作用的广泛误解。 他建议说,在公开谈话中理应包括更多的专业术语,不需太多,但起码的一些还应该有,这样就不会导致大众对遗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过于简单化的理解了。
对先天与后天之争的深刻反思,其意义之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大多数人一想到遗传,总是从古典的孟德尔学派的遗传学角度去理解它,即:一种基因总是对照着一种性格特征。但是把多数复杂的人类行为和最近研究成果所揭示的内容相比较,两者相去甚远。要想得出一个较为准确的观点,很可能得把许多不同种类的基因考虑进来。这些不同的基因受来自环境的各种标志的制约。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的是,环境本身复杂之极,涉及到我们所称的后天的东西(如双亲、家族史、教育、安全住房等)和诸如病毒、出生并发症甚至细胞核内发生的生化反应等在内的生物性特征。
遗传基因和环境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相加。在人的一生里,基因在不同的环境下不断产生蛋白质,或者不产生蛋白质,只取决于环境的丰富、恶劣或贫瘠。先天和后天的相互作用是如此深刻彻底,如此天长地久,以至于心理学家威廉·格力诺说道:“要问先天后天孰轻孰重,就如问一个长方形的长与宽哪个更重要一样。”
关于先天与后天的议题,新出现的观点是:许多复杂的人类行为可能和某种使人对精神分裂或侵略等变得敏感的遗传因素有关。但是行为或病理的发展所需要的并不止这些,“全国精神病研究所”主任斯蒂芬·海曼认为还需要一次来自环境的“二次打击”。这个“二次打击”的实施是反直觉的,是通过遗传基因来“塑造”人的大脑。以情绪低落为例,它看上去好象是一件坏事,比如说是一个摧毁一切的损失,事实上却能够在人体内产生影响某些遗传基因的化学物质,而这些遗传基因反过来会影响那些使一个人对将来的情绪低潮变得更为敏感的某些脑蛋白质,是先天还是后天?同样,海曼的研究还表明:服用易上瘾的物质能够导致人体在遗传和分子层次上的生化变化,使得人脑内的网络,包括意志力,受到影响。这样一来,便会瓦解一个人控制其破坏性行为所必需的内在动力。有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去吸毒或酗酒,结果是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上瘾性神经错乱的生物基质。生物学与人类经历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了。
6.后天的潜力
正如坏的经历会诱发某些脆弱的遗传基因,丰富且富于挑战性的经历往往具有加强生命力的功效,当然仍然要通过遗传基因这个渠道。格力诺在老鼠身上的试验表明,通过提供装满玩具和不停地进行位置变换的复杂布置的笼子……“相当于模拟动物大脑起源”,他可以使老鼠大脑中的突触数量增加25%,血液流量增加58%。聪明和智力的可塑程度看来大得惊人。
儿童智力开发专家通常把能够加强(或瓦解)基因形成的生活环境称为“近身过程”。这个术语是由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创造的。从活泼的谈话到游戏、阅读故事等每一件事都可能激活一种基因,并产生一种有可能成为一个与思维或心情有关的神经元感受器或信使化合物的蛋白质。布朗芬布伦纳说道:“没有一种可能的基因会成为现实,除非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允许这种基因形成的程度。”不幸的是,正如他在他的新书《美国人的状态》中详细阐述的那样,许多美国孩子生活的环境一年一年变得越来越贫瘠单调。
如果说在当今的遗传学家当中有一句口头禅的话,那就是:我们越是努力工作去显示遗传的巨大力量,便越难摆脱后天经验的影响力。这很有点悖论的意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努力总是以重复50年代前的结论而告终,只不过我们的手段比起从前来要无限复杂而已。的确,干预人类生命以提高生命质量,消灭精神疾病、吸毒和犯罪行为的根本办法就是丰富人类贫困的生活环境,改善人类家庭和社会生活条件。目前,已经发生改变的是左倾社会学家们的观点,而不是那些最熟知人类遗传基因活动规律的人的观点。社会心理干预的目标乃是找到遗传基因发挥作用的最佳形式。
因此,不妨让我们假设一下存在一连串和青少年暴力有关的遗传基因。带有这些基因的那个孩子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拥有父母之爱、正常的营养膳食、大量的书籍和安全的学校,也可能生活在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屋兼之周围枪声不断的世界里。那么在哪种环境里上述的遗传基因可能会制造出犯罪行为所需要的生化基础呢?或者说,是形成幸福的蛋白质和神经突触呢?
(赵亚莉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