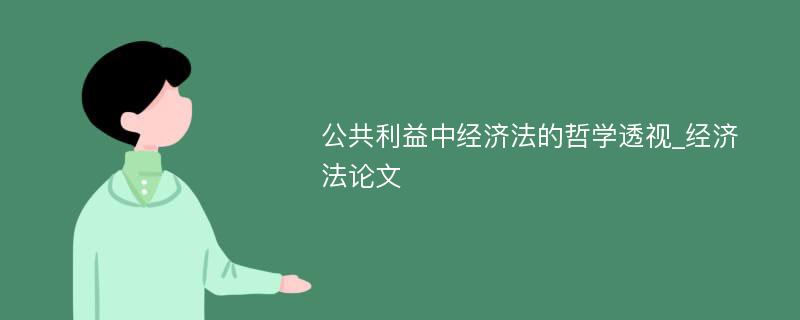
公共利益的经济法哲学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利益论文,经济法论文,透视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利益层面的不确定性
《辞源》和《现代汉语词典》都将利益释义为“好处”或“功用”。然而,将“利益”这一哲学与法学上极为重要的概念运用类比的方式简单地解释为好处或功用,即算不是循环定义,也是失之严谨的。正是因为利益是这样一种异常直观的现象和概念,因而人们在对其进行深入剖析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奥古斯丁式的困惑之中。
在艰难的探索中,人们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庞德教授认为利益不外是主体对客体的渴求,周旺生教授认为利益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而孙国华教授则认为利益表征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在任何时候利益都离不开主体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及所形成利益概念是不确定的,因而也就不限于物质上的利益,也包括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式利益,如文化、风俗及宗教等利益。这样,利益的形成及利益价值的认定,恒为当时客观事实所左右,公益内容的认定及维护也必将随着变动不居的社会情形而有所不同。
公共层面的不确定性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一词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意思。它们源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一同运用到建立在工业进步和社会福利国家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关系当中时,相互之间的联系会变得模糊起来。同样是这些社会关系,一方面反对传统用法,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它作为术语加以使用。不仅日常语言如此,官方用语和大众传媒也是如此。即便是科学,尤其是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显然也未能对“公”、“私”以及“公共领域”、“公共舆论”等传统范畴作出明确的定义。
一般而言,人们将公益及相关概念如大众福祉、社会利益等统统概括为公众享有的利益,然而享有利益的对象既然是公众,那么公众又如何定义呢?倘若将公众定义为全体社会所有成员,那么公益即可理解为全体社会某种共享的利益。然而,由于现代社会是利益多元化的,就几乎难以存在一个为社会所共有的“公益”。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存在利益分化的情形,并且双方都可能援用公益话语证明自身要求的正当性。
如何描述公共利益
亚里士多德把国家视为最高的社团,其目的就是实现“最高的善”,这种最高的善在现实社会中的物化形式就是公共利益。亨廷顿认为很难给公共利益下一个普遍而具体的定义,这个问题只能部分地解决,部分解决的办法就是从统治机构的具体方面着眼给其下定义。他认为公共利益既非存在于自然法规之中,亦非存在于人民意志之中,也非政治过程所产生的任何一种结果,相反,它是一种增强统治机构的东西。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哈贝马斯认为事实上公益、公共利益都是历史的概念。公共领域借助公共舆论使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发生接触,这种利益就是当时的公共利益。
对利益的分类及描述最为经典的当属庞德教授。庞德根据耶林的学说,将利益分为三大类: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将公共利益分为两类,一是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二是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又将社会利益分为六类,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满的体系。
在这些力尽完美而并非一致、甚而大相迥异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找出它们的最大公约数,这是本文所称的公共利益界定一般进路最大的也是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最基本的共同点表现为:社会公共利益能给社会公众带来好处,是人们认可的共同的善;公共利益是客观的;公共利益的客观内容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公共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区别在于社会性和共有性;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公共利益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主体是多元的。
经济法中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典型与理想类型
无数法理学家和部门法学家试图抽象与概括出各种部门法中形态各异的公共利益之共同特征,构建出“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因为大多数人相信,既然不同的对象运用一个共名,那么,对象之间就必定有共同的内涵,否则就不会分享同一个名称,其具体路径便是上文介绍的由“公共”、“利益”而及“公共利益”的传统组合方法。但在“不确定性”成为这种进路的几乎是不可逾越的最大障碍时,我们必须反思的是在目前的法律与语言之情境下,是否真如本质主义者所言的那样任何事物的本质都具有本体论上的不变性和揭示方法上惟一性。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与韦伯的“理想类型”正是在不同层面对本质主义的反动。沿着两位先贤的思路继续前进,我们不禁怀疑以下命题的正确性:即当我们用“公共利益”这一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部门法中作不同指称的时候,我们毫不怀疑这些被指称的对象一定有一个本质特征,并且可以运用概念对这种本质特征进行抽象概括。无数中外法学家在这一抽象概括的过程中对他们发现的“不确性”的惊愕和向描述性定义的退却也证明了这种怀疑的合理性。
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中的公共利益作为公共利益大家庭中的不同家庭成员,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共同的特征是不得而知的,或者说是目前的研究方法尚不能探知的,在这样的情境中试图用“公共利益”这样的具体概念自然只能是水中探月。这时“家族类似”中的典型与韦伯的“理想类型”便成为跳出公共利益本质主义樊篱的有力武器。既然作为家族类似的公共利益的法律向度是无法确定和抽象概括的,那么从中摘取“典型”或者说是“理想类型”以达到对公共利益理解的片面深刻便显得至关重要。维特根斯坦针对斯宾格勒的文化类型强调过典型与对象的区别,韦伯曾用“资本主义精神”、“西方城市”作为理想类型去解释特定历史现象,用社会行动类型、合法性统治类型去解释普遍社会现象。
经济公益之表征:自由与秩序
经济秩序始终是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追求的价值。一般认为,市场条件下的经济秩序是市场经济中规范交易主体、中介主体和政府监管主体的法律和道德约束体系。所谓市场有序是指各类市场和各市场主体的约束体系健全并得到尊重,各市场主体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相互之间达成的共同规则以及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合法利益得到维护、非法行为受到惩罚和社会谴责,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最大可能的实现。市场有序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市场实现产品交易必须遵守客观的一般经济规律,如等价交换规律、价格规律和竞争规律等;二是经济交易各方必须遵守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其重点必须维护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和主体秩序。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是指交易实现的条件和规则,交易实现的核心是价格,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因而,交易秩序的核心问题便转化为由谁定价和怎样定价:是生产者、消费者还是政府定价?是自由定价、垄断定价还是由政府行政定价?一般说来只有通过竞争定价、市场定价才能形成比较真实的价格,真实的价格才能传递真实的信息,才能解决信息的不对称问题,才能实现合理的分配机制,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而,必须反对和制裁价格垄断、价格歧视。市场经济的主体秩序是回应谁在交易,即什么样的主体可以进入市场,承担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市场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其中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因而从现实出发从法律规制的角度解决政企不分、企业的破产制度、普遍存在的第三方付款等问题是当务之急。
为什么选择经济法
一般认为,民法为私法,乃市民社会之法,有异于政治国家之法。民法乃权利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以个人利益作为出发点,强调人的个性的充分发挥,注重机会均等和机会公平。高度发达的民商法秩序的建构以实现以经济自律为基础的平等的自然的经济秩序、保障微观经济安全、实现竞争机会的均等和形式上的分配公平、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理想状态,在这种秩序中凸现了民商法的个人本位利益观。然而,近代以降,这个曾经被视为完美的民商法秩序受到新时代的挑战。倡导个人本位的民商法秩序与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矛盾。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阻制的追求和对他人、社会利益的漠视导致了对后者的损害,从而造成了经济学上所称的外部负效应。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危机昭示人们,个体主义的无节制发展与人类固有的社会属性产生了矛盾,如果任由个体主义无限发展下去,人类便有“礼崩乐坏”、自取灭亡的危险。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民商法学家也曾试图努力修正,然而民商法的利益观的先天不足并非能为内部的局部修正所解消,新的利益撞击、孕育着新的部门法的产生,经济法的出现拓宽了民商法利益观视野的局限。
19世纪末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日益加剧粉碎了“看不见的手”的万能神化,近代自由经济的充分发展,垄断也作为自由竞争的副产品而出现反过来严重限制的自由竞争,使得完全竞争只得虚化为一种理论形态,由于消费者在个人利益本位的驱使下而产生的“搭便车”心理,使得具有消费时非排他性和非对抗性的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社会分工的发展、个别劳动的日益片面化,使得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越发尖锐,有效需求不足与私人盲目行为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之间所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私人利益无限膨胀的结果使社会资源大量浪费和社会经济的衰退。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竞争性也更增加了社会的风险性因素,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问题、劳动者问题、产品责任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等等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威胁。上述种种阻断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也使得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相对于个人利益的独立利益彰显出来。这一切反映在政治层面上,一如哈贝马斯所言,当市场主体的利益冲突无法继续在私人领域内部得到解决时,冲突便会向政治层面转化,从而使干预主义得以产生,而随着资本集中和国家干预的加强,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过程中,便产生了不能完全归于传统私法或公法领域的一个新领域,这是对古典的私法制度的突破。这不仅证明了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都是受一定的物质条件支配的,而且表现出法哲学的发展对现代经济法产生的间接铺垫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