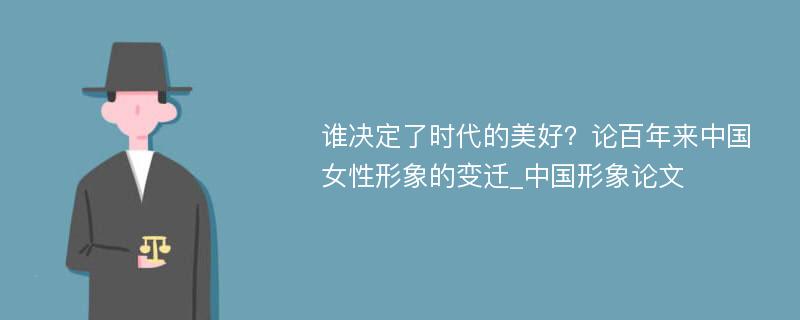
谁决定了时代美女?——关于百年中国女性形象之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形象论文,女性论文,决定了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女性的生活和外在形象发生鲜明而巨大变化的时代。张爱玲曾经感慨说: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其实,迂缓、呆板、没有变化可言的不仅是服装,也是那一时代女性整体的生活和形象。中国女性的生活和精神都曾长期处于沉闷和凝滞的状态中,然而,在20世纪的风云变迁中,中国女性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视觉形象上,都已不复为传统的女性可比拟。简言之,在已然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女性不但在社会生活中,而且在外在的形象上也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代、世纪都更为纷繁、重要而本质的变化。
然而,由于既往的文化有意无意地把外在形象看作是个体与生俱来的特征,或女性个人在装扮上的爱好,人们很少清晰地意识到,女性形象的变迁其实正是一部形象撰成的历史,那装扮、变化于时代,形神兼备的“真实的一人”、女性,乃是一定时空所捕获的“人质”。(注:“人质”一词为刘心武语,见《时空所捕获的人质》,《读书》1995年第1期。)恰如西蒙·波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社会女性的外在形象也不是“天然”的。常常“流行”似乎只是在女性的内部进行,然而,真正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令女性趋之如鹜的却是时代那只“看不见的手”。女性并不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形象和变化,在她们那“独立”的、“自成一格”的形象和够“酷”的装扮背后,是时代更为有力而隐蔽的想象和要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郎士的话颇有启悟:“如果我获准从我死后的一百年出版的那些书中进行选择,你知道我会挑选些什么?……不,在未来的图书中,我既不会选择小说,也不会选择历史著作,当历史给人带来某种趣味的时候,它也不过是另一种小说……。为了看看我死后一百年的妇女将如何打扮自己,我会直接挑选一本时装杂志。她们的想象力所告诉我的有关未来人类的知识将比所有哲学家、小说家、传教士或者科学家的还要多。”(注:《服饰——人的第二皮肤》,P34。)
作为“人的第二皮肤”,服饰传达着心灵的消息,奠定了形象的基础;而对于“时代女性”来说,有时,“生活”几乎就是穿戴什么——或者说允许你穿戴些什么。和满清三百年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不同,20世纪是女性着装的黄金时代,各式时装风起云涌,中国女性的外在形象也在时装的衬托和刺激下一变再变。然而,形象不仅仅决定于衣著,由特定时代的服饰装扮、举手投足和神情气质等等所构成的时代女性的整体形象是一系列传达复杂信息的重要符号,它所表述的将不仅是“形象本身的历史”,也是时代和社会变迁的历史。
毋庸置疑,摄影在“形象的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变迁”是形象之成为“历史”的关键所在,那么恰是摄影,使这一切的变迁得以“凝固”和保存。和历史上无数个“失落”的女性相比,20世纪女性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方面,便是生逢摄影这一现代技术的发明。正是由于摄影术的发明,她们的面目才免于湮没而得以留存,其喜怒哀乐也才有了直观的记录,而不仅仅是凭藉于文字的描摹和揣测。中国女性的形象在摄像镜头中的出现是和摄影术在中国的传入几乎同时发生的。然而,我们发现,虽然同处于一个摄影发明的时代,女性在镜头前的命运和遭际却很不一样。当晚清的后妃们频频地在摄影机前“梳头、净面穿衣服”,(注:1903年,慈禧为了次年的70寿庆,曾照相30种共786张,其中“梳头、穿净面衣服、拿团扇圣容”一式的现今尚存103张,见《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1月版。)恣意地享受和尝试这一最新的文明成果时,底层女性大多只是被动地落入了猎奇者的镜头之中。
事实上百年来中国女性在镜头前的这种差异是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当都市女性的形象成为时尚的代表时,小城和乡村妇女对时尚的追随和复制却可能只是显出了一种更为突出的“乡气”。差异其实远不止此,在“美”和“美的追随”的背后,地缘本身——都市和乡村的差别即已造成了一种权力的等级。20世纪的20-30年代以来,在时代一系列的动作之下,中国社会已经日益分裂成了两大板块:一块是新的都市系列,另一块是广袤而古老的乡土农村。有人曾这样描述了作为都会代表的上海与乡村的“联系”和“隔阂”:“即使在1941年,仍旧可以在三四小时内从外滩中段跑到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农村地区。乡村相距不到十英里;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为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边界之一……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迹象。”(注: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P81、P5。)都市是文明的象征,代表了时代发展的前锋,在都市,女性被推上了社会生活的前沿舞台,都市的经济活动中融入了她们的人力资源,都市的公共空间里活跃着她们的身影,“理所当然”地,都市女性成了引领时代风尚的代表。以至今天,当我们回首百年中国女性的形象时,最多地映入眼帘的便是这些都市女性的形象。她们的身姿和面影曾经最多地进入了当年的摄影镜头,但这与其说是掌握镜头人的“偏见”,毋宁说是历史的“偏爱”。
几乎同样令人瞩目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工农兵女性的形象逐渐成了时代女性唯一的主角。时代的摄影室里,早年尚有旗袍、列宁装和布拉吉并存,尚有共和国女性的“青春之歌”,到后来则变成“蓝灰黑”的天下。
70年代末,在蓬勃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伴随着社会对长久以来所忽视、甚或有意抑制的自我意识和个性的重新认可,女性的特点也重新受到了关注,“女性”开始从服饰、发式、言谈笑语和举手投足中重又“浮现”出来;转瞬间,已汇入到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洪流之中……
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是“谁”塑造了女性的形象、决定了时代的“美女”?
综观历史,我们发现,女性形象和社会政治的变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常常,其变迁不仅透露出变革的消息,而且某种程度上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相伴而行,“时髦女性”对于社会政治和时尚的变化往往有着双重的敏感和“悟性”。辛亥前后的状况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为口号推翻了满清政权,于是,不仅“达拉翅”、“花盆底”等旗女装束在一夜间销声匿迹,而且,“三百年来没有什么变化”的汉族妇女也乘机一改以往的面貌和规矩,一时间,去头饰、放缠足蔚然成风。“时髦女性”对于政治和时尚的双重“敏感”,在20世纪的下半叶里也屡有表现。1949年,随着秧歌队进入城市,以“上海滩美女”为代表的都市女性们很快便脱下旗袍换上了列宁装。杨绛小说《洗澡》中回国投奔光明的“标准美人”杜丽琳,虽然一时还未能将身上的西装套裙爽快地脱下,可也早已添置了两套制服,一俟革命群众提出:“为什么杜先生和我们中间总存在着一些距离”时,她便把簇新的列宁装制服“用热肥皂水泡上两次,看似穿旧的,穿上自在些”。至于文革时期流行的“不爱红装爱武装”,更是直接的政治影响的结果。
政治的影响之外,女性解放的思想无疑也是造成20世纪中国女性形象变迁的动因之一。《吴友如画宝·海上百艳图》中,一幅数名闺阁女子手持望远镜窥视租界的风情画,便生动地传达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女性,在风气渐开的时代里,冀望突破既定命运的心曲。尤其重要的是,辛亥前后,西方教会和革命党人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在全国各大城市竞办女校,掀起了一股女性解放的热潮,著名的上海中西女塾、桂墅里大学堂等等都是在此时开办,女子教育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及至20年代中期,随着女子教育的日渐发展,社会上出现了第一批以自己的能力服务于社会和为稻粱谋的职业女性。这一切,毫无疑问地都为女性地位乃至外在形象的改变提供了基础。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女性改变旧身份象征的革命中,走在前列的却是晚清的妓女。由于她们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她们是其时仅有的能够无所顾忌地出入茶楼、戏院、公园等各种公共场合的女性,广泛的社交活动和较少礼教的束缚,使得她们往往能够率先发出对于旧规则的冲击。事实上晚清妓女对于社会服饰等级的僭越和淆乱早在“革命”前即已发生,《点石斋画报》中一幅描绘妓女应召的出行图,其中的着装便全无规矩:旗装、日装、男装、道姑装、西装、女式洋装,无所不有。清末民初,曾流行一种叫“元宝领”的抵颊高领,也是在妓女中最为风行。晚清妓女的“奇装异服”对普通女性的衣饰妆扮造成了广泛影响。1898年《申报》的有关文章曾记载说,19世纪的60-70年代,普通妇女和妓女在装扮上尚有区别,而到了90年代,由于社会上流行“女衣悉听娼妓翻新,大家亦随之”,人们已经不能从装扮上简单区分两者。(注:《申报》1898年6月24日,《上海通史·晚清社会》P4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晚清上海妓女对于明尚变化的追求可说是既敏感又大胆,这种敏感和大胆为社会的动荡提供了一个富于象征性的指数。服装文化史家曾经指出:如果妇女的服装如晚礼服突然变为紧身裤或显露出抛弃以往的礼仪标准时,清配的社会观察家就可以把它当作一次真正的社会动乱的标志。(注:《服饰——人的第二皮肤》,P135。)辛亥前后的中国社会及其女性的服饰状况,虽然不是完全如其所言,却也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说法。跟在军阀的马蹄后跌跌撞撞地赶上去的女性时装,不仅是时代审美的变化,也是社会变动、骚乱的标志。
然而,20世纪中国女性形象变迁的一个至为重要的方面,并不在于是普通女性还是地位特殊的妓女充当了变革的“先锋”,而在于一切的变化皆是在一个新的格局中产生。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在坚炮利舰的“先导”下,如惊涛拍岸,步步逼来。随着海禁的打开和上海等通商口岸的相继建立,西方的各种货物源源而来,冲击和占领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晚清上海妓女在服饰妆扮上的标新立异很大程度上便是源自其对洋货的率先使用。清光绪中叶以后,她们中的好修饰者戴眼镜、佩“小表”的已相当普遍;至民初,妓女们制衣用洋纱布绸呢绒更是普通平常,饰物也多由传统的金银翡翠而扩为钻石、烧料及各种仿真品,丝袜、洋伞、香水、围巾,也皆如影随形……(注:《上海通史·晚清社会》。)
确实也是,百年中国的女性形象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女权思想的驱动和鼓舞,而且得到了现代文明的有力支持和“怂恿”。自海禁打开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渗入已经十分便利。19世纪末,一位来华为英国皇家园艺学会作茶叶引进的植物学家曾这样报告他对于上海的观察:“上海是中华帝国的大门,广大的土产贸易市场”,“上海港内各式大小船只云集,从事于内陆运输。自从港口开放以来,这些船舶运来大批茶叶和蚕丝,并且满载着他们交换所得的欧美工艺制品回去……”,“上海距汉口、苏州、南京等大市镇的地点相近,构成一个有利条件”。(注: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P81、P5。)事实上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进入中国的路线。由于地理的原因,上海客观上成了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第一站。1854年,上海就有了外商在华经营的第一间百货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着欧美各国忙于战事,中国的民族资本也开始发展起来。1913年,澳洲华侨黄焕南和郭乐回国投资经营原先都是由外商经营的巨型百货公司。1917年,黄焕南的先施公司首先揭幕,第二年,郭乐的永安公司也随之开张。耸立于南京路上的这两家百货公司的先后建立,不仅揭开了华人经营环球百货的序幕,而且使上海的工商各业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1925年和1936年,上海又有两家巨型百货公司——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开张,而外商经营的著名的惠罗公司也早已于1913年创立。从此,上海开始了各大百货公司争奇斗艳的局面。至3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远东第一大都市,一本英文版的“上海大全”类书籍(AllAbout Shanghai)更是以赞叹的口气写道:置身于上海的繁华中,几乎要使人不知道该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还是巴黎是西方的上海好了。以至初来乍到的西方冒险家或观光客要发出这样的惊叹:
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驶过南京路,停在堪与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巴黎大道上的百货公司媲美的商店门前!游客一上埠,就会发现他们家乡的所有商品在上海的百货大楼里都有广告有销售。猎装和BVD内衣陈列在一起,"HOUBIGANT"香水下面,"FLORSHEIM"鞋又紧紧地吸引着顾客的视线,上海百货公司里的这种世界格局足以在中外商店前夸口它是“环球供应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时空里,“摩登女性”产生了。摩登女性的产生显然和正在兴起的社会消费以及商业的发展密切有关。其时,在上海的各大公司里,人们几乎可以买到世界上所有最新最时髦的商品,而欧美最新物品在上海的及时登场,则使得上海的时髦女性在时尚的追赶上没有丝毫的焦虑,她们流行的节拍永远踩在点上。但这一切与其说是摩登女性们的“先进”和灵敏,却不如说是资本的“魔力”和胜利。
据经济学家的有关研究,中国社会在1928至1936年间,尽管战事频仍,而现代工业的平均增长率却仍然高于8.4%。(注:小科布尔《上海资本与国民政府》P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茅盾长篇小说《子夜》中致力于民族工业发展的吴荪甫就曾发出这样的宏愿:“他们将他们的灯泡,热水瓶,阳伞,肥皂,橡胶套鞋,走遍了全中国的穷乡僻壤!”换言之,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的中国,无论外来资本还是本土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都迫切地需要一大批具有都市“韵味”的女性来作为它的社会基础和消费的“代表”。由于女性在社会和家庭消费中的特殊地位,不仅她们本身成为商家重点跟踪和“包装”的对象,而且被赋予了消费的“形象代表”的使命:从柯达软片到永备电池、菲力浦无线电、可口可乐、天厨味精、桂格麦片到美丽牌香烟,以及高露洁牙膏、力士香皂、四七一一佳古龙香水,这些代表着最新文明的商品,哪一样不曾为当年的摩登女性所“消费”和展示过呢?(注:以上商品广告均可从当时的月份牌及其他报刊见到。)
消费以女性为代表的过程,也即是资本和各种社会力量“塑造”时代美女的过程。清末民初,女性形象已渐为日益兴盛的商业文化所关注,月份牌广告则是其中一个鲜明而有趣的例子。月份牌广告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流行,最初由外商在境外印制后运来,而不久即改变了制作方式。1911年,英美烟草公司率先引进了胶版印刷机,以便能够在中国就地印制月份牌广告;1915年,该公司又在上海浦东设立了颇具规模的美术学校,以训练专门的广告制作人材。不仅如此,公司还专门设立了广告部延请各式人员,进行月份牌广告的设计,其中便有中国的画家和设计人员,从而改变了以往月份牌广告上西洋风土人物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月份牌广告真正重要的改革并不在于它的“本土化”,而在于其日益发展的“时尚化”。思想开放的海派画家们从最初加盟月份牌广告的创作起,便不仅用传统的中国美女来取代遥远的异域美女,而且很快把目光投诸到了时代的新潮上。其时不少的月份牌广告都以时髦女性的精美妆饰为描摹的重点,而这些美女的原型不少是妓女。此外,变动时期新的社会礼仪和风尚也在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如开派对、跳交谊舞等等,都是月份牌广告的好题材。有趣的是,在那个西风吹动的时刻,派对上相拥而舞的往往是两个女子。20年代前后,靓妆倩服曾领风骚的晚清妓女很快为更为新潮的女学生们所刷新,女学生成了引领时代风尚的代表,于是,海派的月份牌画家们便开始以女学生为创作的题材和“灵感”。画面上的中国,女学生们像当年西方的女性一样裸露着双腿,进行着各类时髦活动,如游泳、骑马、射箭,间或也露出胸脯。显然,女学生运动图所绘的并非全是写实之作,相当部分只是画家们的想象和对西方美术的模仿,但却异常生动地表明了社会风尚的转变和艺术的“引导”作用。一如王尔德所说,生活模仿艺术常常多于艺术模仿生活,时代女性的“经典”形象很多时候就这样被“造成”了。到了30年代,出现于月份牌广告上的美女已不是昔日风华正茂的女学生,而换作了丰满性感的摩登太太。究其原因盖在于,此时此刻,从发展消费的需要来看,具有相对自主权的太太显然比女学生们更有消费的能力,她们成熟的形象也更适合于作为一系列新式产品的代表。有意思的是,摩登太太们虽是摩登的代表,在月份牌画家的笔下,相夫教子却仍然是她们的重要职责。这或许也不仅是月份牌画家的想象,而是社会的期许和定位。(注:张燕凤《老月份牌广告》。)如果我们意识到时代美女的塑造乃是一个多种因素合力的复杂过程,那么,技术——月份牌广告特有的擦笔淡彩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所谓擦笔淡彩法,即是用炭精粉先在纸上擦出一个底子,好比打下一个素描的架子,然后涂以不同层次的水彩。此法10年代初由画家郑曼陀率先发明使用,然而却根本上是时代的产物,是海派的商业画家在过渡的时代里,孜孜地向西方学习“明暗、立体、色彩”的结果。海派画家的月份牌广告于是虽还留有明显的从传统年画脱胎而来的痕迹,然而他们“揉合”了西洋画法的擦笔淡彩却使笔下的美女鲜明柔和细腻可触,和所代表的都市的声光色影相得益彰。由于月份牌广告的踪迹遍及了广袤的大小城乡,其中的形象也成为小城或更为广大的乡村女性模仿的对象,其影响可谓历久而弥深。
如果说月份牌美女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海派画家的知识背景和审美想象,那么,电影则提供了更为“洋气”的关于时代美女的样板。电影在中国的传入是和它的发明几乎同时发生的。1895年,法国人卢米埃尔发明了电影,一年后,1896年的8月,上海徐园的又一村便首次放映了“西洋影戏”,之后,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了既可演戏又可放映电影的影戏院。20年代末,在世界电影发展的影响下,上海等大城市的影戏院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1927年,一个有关的统计曾报告说,“中国目前有106家电影院,共68000个座位。它们分布在18个大城市,这些大城市大都是通商口岸。”(注: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第3章。)这106家中,上海就占了26家。而到了30年代的末期,上海的电影院已经发展到了36家左右,其中既有以亚洲“洛克赛”(ROXY,当时美国最豪华的影院)著称的南京大戏院,也有投资100多万改建的新大光明电影院,以及国泰、夏林匹克、恩派亚等其他一流电影院,上海成了电影的“天堂”,拥有着最为先进的设备。(注:《中国电影图志》,珠海出版社1995年10月版。)与此密切相连,美国好莱坞和英法的电影大量进入了上海,其时,几乎“欧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发行人”,(注: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第3章。)这些影院里,每年放映的西方电影大约要在400部左右。
作为一种时新的艺术与娱乐样式,电影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新奇感,而且它还是一种宣传摩登生活的最好工具,西方的流行风尚不少便是通过电影而传入的。而在这一风尚的“流传”中,中国的女明星们显然“功莫大焉”。她们对于西方时尚的刻意模仿和追求,某种程度上成了她们个人声誉的组成部分之一。事实上,明星形象的很大一部分也正是在她们关于时装、发式、生活趣味和休闲娱乐等等的日常私事上建立起来的。然而,一如对流行“心有灵犀”的不仅是女明星们,形形色色的都市女性们也是风尚的追逐者和推波助澜者;给予女性形象的变迁以“灵感”、以效仿的“样板”和可能的,除了欧美影片外,中国本土的电影也是重要的来源之一。30年代,正是中国电影的发展时期,天一、明星、联华等中国重要的电影公司都已相继建立。尤有时代意义的是,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剧,一些有影响的电影公司打破了一个时期来影坛对于武侠、古装片的热情,纷纷改拍都市片,以适应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兴趣,掀起了一波都市影片热。这些影片中的女性和女明星,连同着欧美、好莱坞女星的风采,为上海摩登女性的“美的构建”提供了一份具有“谱系性”的资源,并经由她们的融会吸收、效仿改造,进而影响到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女性,天津、北京、汉口、广州……以至香港、东南亚等海外各地。与此同时,当红的中国女明星则被称作了“东方的嘉宝”抑或“东方的琼·克劳馥”。
事实上也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女性的形象“建构”,很大一部分的参照是来自西方,3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女性标准服装的旗袍,其在20年代末的出现,和欧美当时的流行风尚其实也有莫大的关系。20年代初,西方最为流行的女性形体是和男性相接近的流线型身材,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妇女担负了以往由男性担当的工作和岗位,角色和审美眼光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也是正在兴起的现代艺术的影响所致,当时的汽车、摩天大楼等都无不显示出流线型的审美倾向,西方女性于是竭力地使自己的体型呈现为流线型,与之相应,服式亦以管状为时尚。在西方流行女装的“启发”下,本为满清帝国象征的旗袍由于它的“管状”基础而得以化腐朽为神奇,从一片混乱中脱颖而出,世纪初的中国女性在十几年的花样翻新和多种尝试后,终于获得了一种能代表这个时代重要价值和自我身份象征的基本的服装样式。然而,“借鉴”并未就此结束,“新生”的旗袍在西方不断变化的时尚影响下又一次次地发生“改良”。20年代,西方女性裸露着大腿,充满了活力,但是并没有裸露出脊背和胸部,而到了30年代,西方女性的无背晚礼服却袒露了过去从没有袒露过的部位;与此相连,中国女性身上的旗袍腰身更紧了,胸省开始出现,叉则几乎开到了臀下。有关研究表明,20世纪20年代的中叶,西方女性裙子的长度在以往的历史中是最短的,从1929年到1932年,裙子的长度一英寸一英寸地逐渐变长,从膝盖以上加长到了小腿以下,在以后的三四年中保持着一种稳定。从1936年到1939年,裙子的长度重又收缩到膝盖,三年以后,人们本来预测裙子又会加长,但这时巴黎被德国占领了,欧美的时尚由于战时织物的短缺而受到限制,时尚的变化于是突然中止(注:《服饰——人的第二皮肤》,P215。)——而这几乎也就是中国女装——旗袍在30年代变化的节奏和“旋律”,不同的只是稍稍的“时间差”。(注:《良友》画报1940年1号(总150期)以“旗袍的旋律”为题记载摄影了历年旗袍的长短变化。)
不难发现,自国门在上世纪中叶被打开以来,随着和世界关系的日趋紧密以及都市化的加剧,社会塑造时代美女的机制已经十分丰富和成熟,环球百货、月份牌广告、好莱坞电影、欧美时尚等等,无不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构造着中国女性的“崭新”形象。除此而外,先锋艺术、流行画报等等也在有意无意中参与了这一构造。1915年,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专第一次使用人体模特儿,引起轩然大波,1920年,美专的西画系又一次雇佣人体模特儿且为女性,招致了更为强烈的攻讦,甚至引起法律诉讼,女性裸体从此不仅作为艺术探索的对象而为人瞩目,也成为一种时髦而进入社会生活的视野。20年代中期,著名的杭穉英画室等月份牌画家就曾应广告商的要求而制作过裸体美女画。1926年,作为“中产”和流行代表的《良友》画报创刊。《良友》辟有世界新闻、社会时事、欧美最新时尚、好莱坞影星介绍等专栏或专题报导,内容丰富且印刷精良,每期以电影女明星、名媛名太等摩登女性作为封面女郎,在一派的关于富足、文明、进步等等的宣示中,也有力地建构起一种新的社会认同和期望的女性形象。为此,画报除展示女明星等摩登女性的形象外,还专门开辟“小家庭学”,登载有关的知识技巧,以教导普通的中产阶级女性如何学习做一个有见识有情调、落落大方、既入得厨房又上得厅堂的“标准女性”。在这一过程中,“名媛”这一新的身份和称呼产生了。20年代末的《良友》画报上,名人之女尚被称作“女公子”,而到了30年代,则改作了“名媛”。“媛”字虽然古已有之,然而被用来特指为现代商业文明所包装的中产阶级的女性,却是时代的创造。事实上,此时的名媛们亦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中佳人,而是更多地担当起社交明星以至时装模特的角色,30年代流行于各大城市的时装表演,很多便是由电影明星和所谓名媛共同担当。顾名思义,“名媛”的要件之一是出身“名门”,然而,此时此刻,充当着这一角色的,大都是正在兴起的资产或中产阶级之女。于是,仿佛正是为了要给予她们一个更为“合法”而确定的地位,1930年,上海举行了一场规模颇大的名媛选举,夺冠的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大小姐同时被冠以“上海小姐”的称号(注:《良好》画报1930年第2月号P26。)——至此,不仅资产阶级之女得以真正成为“名媛”而活跃于各种社交场合,一时间,汉口名媛、天津名媛等等纷纷登场亮相,占据了各种流行画报的封面封底,而且新一轮的都市选美风也开始兴起。自清末民初以来上海曾举行过多次选举“花界状元”的选举,而如果说此前所开的“花榜”,散发的是旧文人的酸腐气息,那么,“上海小姐”的选举则带有了更多的“都会摩登”和“殖民”的色彩。1933年,《明星日报》发起评选“电影皇后”活动,胡蝶以21334票当选。这一风气和机制甚至影响到了女学生,此前,上海的女校里最为盛大的节日是运动会,现在则添了选“皇后”,而那一款款“皇后照”上的姿势和眉眼神情像极了画报上的某个名媛或明星。(注:《良好》画报。)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那本著名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里,曾经富有洞见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变革,像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一样,在黄浦江边,充分地生长出现代的根苗……它的成长促使不断扩大的变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就现代商业、金融、工业都市的最后成熟阶段而论,上海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物的锁钥”。(注: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P81、P5。)同样,上海摩登女性的兴起和衰落,对于20世纪中国女性形象的变迁也是一个甚为重要的解说。以选举“XX小姐”为例,上海的“示范”作用就十分明显,自“上海小姐”诞生后,“天津小姐”、“汉口小姐”等也应运而生。有意思的是,1932年选出的“天津小姐”,是一位白俄后裔。而“上海小姐”的发明,说到底也无非是“美国小姐”的翻版和启发。现代化在中国的开展,乃是一个无限的权力网络,表现在女性的形象上,便呈现为如下的图像或“等级”:一方面,上海的摩登女性以西方为楷模,欧美时尚的每一次流变都在她们中间引起了“飓风”般的反应,一如当代物理学分支混沌学的“蝴蝶效应”所显示的:亚马逊森林中的一只蝴蝶只是振动了一下翅膀,却引来了北美大洋上的一次飓风;而另一方面,“飓风”之余绪或“翻版”却成了本土其他大中城市或小城女性模仿的对象。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再一次在女性形象的变迁上得到了印证和显现。
或许,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现代性话语和时代美女的关系。20世纪中国女性的形象变迁,在受到物质文明的支持和怂恿的同时,事实上也和现代性话语紧紧缠绕在一起,并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的一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外来冲击的刺激下,女性形象的变革在维新的忧国之士的意识里首次被与“强种保国”的神圣目标联系在一起,“女子为国民之母,欲列其国势于优等,必先跻入人种于优等,种族进步之权基于妇女,吾愿为人母妻者,俱以体健貌美为万国先”,(注:《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转引自《女性与中国近代社会》。)凡此等等,一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女子教育、女子体育以及女子社交等等的新事物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兴盛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了以五四女学生为代表的一代崭新形象。然而,自2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风尚发生了新的变化,关于女性的话语也有了新的意味和发展。我们看到,随着“现代化”等一类词汇在中国的流行,英语中的MODERN一词被音译为“摩登”来特别地表示具有时代特色和“先进性”的事物,与此同时,在消费的促动下,“摩登女性”这一最新提法出现了。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摩登女性特指那些站在时代生活风尚的前列,代表了文明的最新成果,同时具有时髦外表的都市女性,是摩登中的“摩登”。她们的出现,为“现代性”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作出了生动而“有力”的“注解”,形形色色的时代美女,无不在“摩登”的名义下闪亮登场。有意思的是,摩登女性作为“现代性”的“能指”,不仅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同时也是资本运作的符码之一。20、30年代铺天而来的香烟广告即是突出的一例。这些形形色色的香烟广告,无论产自“本土”,还是源自“外来”,大多有着一个吞云吐雾的时髦女性,哈德门牌的广告上更是赫然写着:“她俩说,吸来吸去还是他好”。是“他好”而不是“它好”,一字之差,却渲示出一种甚为“现代”的意识:从来“被看”被品评的是女性,而现在却轮到女性来评判男性,社会女权的张扬似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如果我们同时注意到,在20世纪的前半叶里,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所获的利润曾达四亿美元之巨,(注:张燕凤《老月份牌广告》。)那么便不难发现,所谓“摩登”,所谓“女权”,不过是资本运作的另一种表达。
仿佛正是对于既往时代过分“女性化”的反拨,抑或一个“必然”的结果,在中国之后的革命年代里,女性外在的性别特征被逐渐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女性不仅在行为规范上、社会功能上,而且在衣着、体力上往往也被要求和男性一样。而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换言之,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女性的形象变迁相当程度上得自于物质文明的支持和“怂恿”,而在它的下半叶里,其形象的建构则更多地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所整合。新中国在催生了一批健康明朗的女性之后,有关的“女性美”的标准很快便转向了中性化乃至无性化,简朴粗糙的女性日渐被作为“革命性”鲜明的代表,而富有“女性美”的好修饰的女性则往往被钉在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耻辱柱上。然而,如果说在极左政治盛行的时期,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着鲜明的性别特征的群体曾经不复存在,那么,随着时代的变革,现代化号角的再次吹响,浪漫、迷人、风姿绰约的MODERN女性在隔了30年的烟云后再一次“浮出地表”。自80年代中期以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几乎占据了传媒和社会视觉中心的“公关小姐”、“住别墅的女人”、“洋行里的中国小姐”、“深圳的女人们”,(注:所举均有同名的电视剧。)以及最新出现的“新新人类”,这些或存身于屏幕上,或活跃于现实中的“现代女性”,都无不在成就着一种颇富“感召力”的关于“现代化”的叙事和想象。
时至今日,适逢新世纪的到来,时代女性和现代化的关系再一次受到了世人的关注和言说:怎样的姿态和面貌才不辜负女性的自我和新世纪的来临?才跟得上“全球化”的脚步和流行?新世纪的中国女性将再一次经受时代的洗礼和“塑造”。
某种程度而言,百年中国女性形象变迁的过程,也即是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在时代的发展中由传统而现代的过程。是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身心体格、神情面貌以及心灵历史发生鲜明而曲折变化的过程,也是各种社会权力塑时代美女的过程,其变迁、演进,昭示的不是社会风尚、审美眼光的简单改变,而是资本、物质文明与技术、现代性叙事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种权力进行微观运作的生动历史和符号体现。是女性的“变异”史,也是时代的变迁史。
历史不仅存在于社会的风云变幻中,也留存在小女子的一颦一笑和衣袖的折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