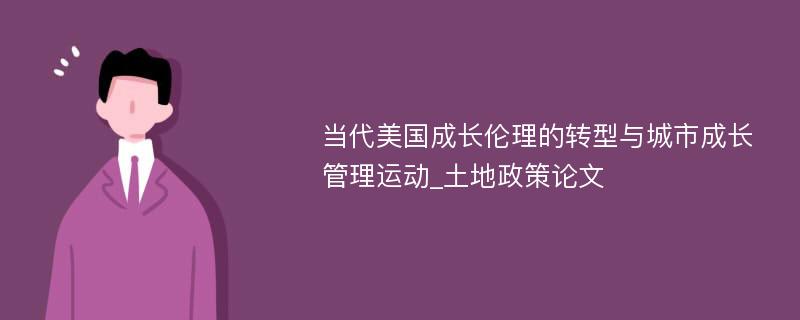
当代美国增长伦理的转变与城市增长管理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伦理论文,当代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美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与大都市区的低密度蔓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比如中心城市的衰落、环境的恶化、能源的消耗、开放空间和农田的流失、交通拥堵、种族隔离、基础设施的浪费、财政负担的加重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等。①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末,美国学术界、规划机构、政府部门、地产集团,乃至普通市民都对美国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改革尝试,先后经历了城市更新、新镇开发、绅士化运动、新城市主义、增长管理(growth management)和精明增长(smart growth)运动等。②其中,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城市主义、增长管理和精明增长运动,对美国的增长伦理进行了根本性的反思,一直延续至今且正在产生重大影响。新城市主义主要是美国城市规划界的改革运动,它更加注重城市的空间形体规划;而增长管理和精明增长则主要是各级政府的增长政策,内容更加广泛。增长管理和精明增长是一个运动的不同阶段,增长管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被精明增长所取代,且两者的特点有所不同。前者更强调对增长的规范和控制;而后者则更强调管理与增长或发展的平衡,强调理性地增长,理论性更强,内容更加广泛,组织更加系统。限于篇幅,本文只对增长管理运动进行探讨,精明增长运动需另文撰述。
一、美国“增长伦理”的转变
增长或发展是美国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的一个核心主题,这一主题在早期最显著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对西部边疆的拓殖,二战后的表现形式是人们向郊区的大举搬迁和郊区的大规模蔓延式开发。为了开拓西部,19世纪的美国人怀着兴奋躁动的心情浩浩荡荡地涌向西部,在那里发掘矿藏、开垦土地、放牧牛羊、设州置县和建立城镇,昔日古老沉寂的大地瞬间繁忙兴旺起来。边疆成为上帝赐予美国人的“迦南”、新的“应许之地”。边疆一词也成为美国征服新领域的一个象征性词语,每当美国出现新的发展机遇之时,他们总是以“边疆”一词进行比喻和描述。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一个丰裕的社会,经济发展空前繁荣,人们的增长狂热又达到一个新的高潮。与19世纪不同的是,这次增长狂热的目标不是西部边疆,而是新的“马唐草边疆”——大都市区的郊区。许多郊区官员对此拍手称快,因为他们认为,增长意味着扩大税收基础,减少人均基础设施负担,从而稳定甚至改善地方税收状况。新的增长可以“自我支付”,即新的基础设施可以由新的税收自行支付。新开发会为社区带来更规范的物资和服务。新增长可以提高地方工资水平,增加就业机会;新增长还可以带来更多的住宅类型和更宽泛的住宅选址,改善社区基础设施,比如消防、健康服务、公路、学校等。③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积极推动本社区的增长,包括税收刺激、广告宣传、建造工业园区以吸引新产业的到来等。
然而,增长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它不能超过某一区域的自然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自然承载力主要包括水、土地、大气等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社会承载力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的规划能力、管理水平、提供服务的能力、法律制度、机构建制等社会能力。如果增长速度超过自然的和社会的承载力,就会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果然,战后美国城市和郊区的增长狂热导致了城市蔓延式的开发,所谓城市蔓延就是“未经规划的、不受控制的或不协调的单一功能的开发模式,它不能提供富有魅力的和土地利用方面的功能混合,与周围的土地利用功能没有关联,其各种表现形式就是低密度的、带状或长条状的、分散的、蛙跳式的或孤立的开发模式”④。这种低密度蔓延导致了前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严重后果。
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长伦理”受到人们的质疑,一种反对增长的“新态度”迸发出来。学者们著书立说阐明增长带来的危害,众多的报纸杂志登载文章进行宣传。此外,在有关开发问题的听证会上,在地方官员的选举中,在发行公债的公民表决中,人们越来越明确地反对没有限制的增长。许多社区对发展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州和联邦政府也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土地利用和增长管理法规,以协调州、区域和地方社区的增长。对此,美国学者兰德尔·W.斯科特(Randall W.Scott)写道:“美国的增长伦理越来越受到挑战,它不再作为一个进步的前提条件而被人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它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正经受着广泛的讨论,而对它的管理和控制则被许多人视为现代土地利用政策的根本内容。”⑤
有些人甚至提出了“零增长”、“停止增长”和“非增长”等概念,试图对增长的全部或部分叫停。他们对地方官员说,“停止”,“够了”,“在我们制定规划——真正的规划——之前先停顿下来”⑥。他们组织了许多地方团体以抵制增长。许多地方辖区开始排斥外来居民,抵制增长压力。零增长的倡导者一般是那些已经迁居郊区良好生活环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主张势必遭到尚未迁移到郊区或生活在郊区衰败社区的人们的批评。批评最激烈的莫过于黑人领袖,因为黑人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蜗居于中心城市和衰败的内层郊区。他们指责倡导零增长的规划人员和地方官员试图“使恶毒的种族灭绝合法化”,“呼唤种族大屠杀的幽灵”。他们揭露零增长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和维护本国的富人与穷人、白人与黑人的鸿沟。1972年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他们的方法就是在原则上敌视增长,对于普通民众的需要漠不关心。它具有明显的阶级偏见,反映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价值判断。它的倡导者往往是一些善良而富于奉献精神的人们。但他们是一些富足的人们,并且希望踢翻他们身后的梯子,虽然他们并非有意识地这样做,但他们的基本目标却是如此。”⑦与此同时,这种零增长的观点也遭到了来自商业利益集团、地产主、建筑商、广告商等与土地开发相关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其原因自不待言。
另外,零增长的观点和措施也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零增长政策也许能够控制那些实施该政策的社区的蔓延式开发,从而保护其自然环境,提高其生活质量,但它也会把开发活动转移到其他不实行零增长政策的社区,从而导致其蔓延式开发,损害其自然环境和资源,降低其生活质量。零增长不是克服大都市区蔓延和解决各类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良方,而且在市场经济体制中,零增长就等于自取灭亡。可见,这种零增长的政策是不现实的,“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州和地方政府应该尽快地建立有序和有效的机制,以便做出理性的土地利用抉择”⑧;也就是要对增长加以规范,即实施“有规范的增长”(managed growth)。所谓“有规范的增长”就是政府利用各种技术、方法、政策、规划和行为,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模式,包括开发的方式、地点、速度和性质等方面。⑨这种新的“有规范的增长”观念及其政策措施被称为“静悄悄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
“静悄悄的革命”的内容首先是关于土地伦理的革命。在19世纪,美国人把土地仅仅视为一种商品,一种发财的工具。但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各种土地利用是相互影响的,整个自然界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土地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而不仅仅是一种任意挥霍的商品。同时,静悄悄的革命也是一次土地利用政策的革命,增长管理政策逐渐在地方、区域和州等各个层次上实施并扩大开来,联邦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予以支持。弗雷德·P.博塞尔曼(Fred P.Bosselman)和戴维·L.考利斯(David L.Callies)于1971年在《静悄悄的土地利用控制革命》一文中写道:“在我们的土地管理方式上,我国正处于一场革命的进程之中。这是一次和平的革命,完全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的革命。这是一次悄然进行的革命,其支持者既包括保守人士,也包括自由主义者。这是一次没有组织的革命,没有中央领导阶层,但它仍然是一次革命。”⑩革命的手段就是新的土地利用政策和法规,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形式各异,但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州政府和区域机构直接介入土地利用的管理之中。
关于增长管理的概念,杰伊·M.斯坦(Jay M.Stein)精确地概括道:尽管“增长管理规划存在各种形式,但基本都要求利用政府的规制权力,以一种综合的、理性的和经济的方式,来达到经济发展与保护和保留我们的自然的和人造的系统相平衡的目标。其理想信念就是要求政府建立和加强制度机制,以便有效地运用税收、开支和规制权力来系统地影响社区行为的空间分布”(11)。简单地说,增长管理的核心是通过政府的政策和干预,对缺乏管理的土地市场的弊端进行规范,其最终目标是通过良好的规划来保护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
二、地方政府的增长管理举措
最早对无序增长做出反应的是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最早感受到增长所带来的压力和危害。地方政府的增长管理措施是多种多样的,最直接的一种方法是对开发活动的总量进行控制,即限制住宅供应的总数,从而限制该社区的人口增长。比如1972年佛罗里达州的博卡拉顿(Boca Raton)进行公民投票,通过了一条宪章修正案,规定了该镇的人口限额,方法是将该镇的住宅总数限制在4万套以内,包括独户住宅和多户住宅。如果平均每户人口为2.5人,那么该镇的人口上限就是10万人。当该镇达到这一人口限额时,该镇将拒绝任何住宅开发。(12)旧金山湾区的佩塔卢马(Petaluma)也对住宅的数量进行了限制,但与博卡拉顿稍有不同的是,佩塔卢马不是限定该社区住宅的总数,而是对住宅的建筑进度进行了限制,即将每年的住宅建筑限制在500套以内。(13)到20世纪70年代末,加州的其他许多城市也实施了建筑限额制度,而且这种限制还扩大到工业、商业和多户住宅的开发方面。该措施的一个变种是对增长的百分比进行限制,而不是数量。
第二种控制增长的方法是限制用于住宅建筑的土地供应量和降低住宅建筑密度。方法之一是地方政府将潜在的可开发的土地买断用作娱乐用地或开放空间。马萨诸塞州的林肯镇就采取了这种政策,该镇购买了800英亩的土地用于开放空间。这种方法最适合于那些财力雄厚的地方政府,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Aspen)采取各种财政手段购买土地。加州的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等社区的顾问认为,购买土地比在它们开发后提供服务设施更划算(14)。方法之二是直接利用政府的规划权力,减少住宅建筑用地,降低住宅建筑密度。实行这一政策最著名的地方政府是加州海边一个5万人的城镇圣克鲁斯(Santa Cruz)。1975年,该镇制定了一个新的住房政策,对住宅的密度、式样和地点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1978年,该镇又通过了一个更加严格的增长控制议案,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其一是将某些原规划中的住宅用地改为绿带,从而减少住宅用地的供应;其二是限制该镇每年住宅的增长率。这一计划关闭了两个城市“扩展区域”(expansion areas),大约占地1000英亩,从此,这两个区域不能建造任何类型的住宅。此外,该镇还将大约占地500英亩的15个较小的“特殊区域”(special areas)的住宅密度降低了一半。在上述两种区域内,规划中的住宅用地总共大约减少了一半,而住宅数量大约减少了2/3。该镇只能满足原规划新增家庭1/5的住宅需求,将有5000个家庭不能在该市寻求住宅。(15)
第三种控制增长的方法是通过控制基础设施的供应控制开发进度,这种方法被称为基础设施“同步要求”(concurrency requirement)。比如纽约州的拉马波镇(Ramapo)于1969年制订了一个为期18年的基础设施改进计划,规定只有在某项住宅开发项目预计完成之时,并在该开发区所规划的基础设施也恰好完成的情况下,才允许项目的开发,从而能够为该居民区提供适当的服务;或者是,如果该开发项目完成之时,市政基础设施不能预期完成,但开发商自己同意提供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可以进行开发。1972年,纽约上诉法院在一次判决中维护了该镇对开发进度进行控制的增长管理法规。加州的马林县(Marin County)在1970年代初期举行公民投票,拒绝发行公债扩大供水设施,虽然该县需要新的供水设施,但担心更多的服务会吸引更多的新居民。1973年,加州圣何塞的一项公民提案规定,如果开发区没有足够的学校教育设施,而建筑商自己又不能提供这些设施,那么就不允许住宅项目的开发。(16)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实施了类似的增长管理措施,1973年,该县议会制定了“充足公共服务设施法令”(APFO),要求开发项目必须同时跟进相关的基础设施,否则不能进行开发。1986年又通过了一个修正案,明确了县政府在确定充足的基础设施方面的职责,这些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公共学校、给排水设施、警察、消防和医疗卫生等。到1995年,马里兰州实施APFO的县多达18个。实施APFO的结果就是土地开发获批的难度和开支更大了,开发强度下降了,从而对开发进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控制。(17)
第四种控制增长的办法是对城市开发的空间范围进行限制。加州的圣何塞市是实施这种增长管理方法的一个典范。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圣何塞市居民开始反对没有限制的增长。1968年,该市的行政部门制定了一项城市开发政策,该政策将该市划分为三种服务区,即城市服务区、土地保护区和城市过渡区。城市服务区就是现在拥有基础设施和在未来5年内将要建立服务设施的区域,它拥有5年开发所需要的土地,如果5年后土地使用完毕,其边界可以扩展,但是,扩展只能在该市基础设施改进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土地保护区就是当前没有服务设施,而且将来也不会提供服务设施的区域。该区域不允许进行开发活动,除非得到特别审批,而且该区域内的某些地区将永远禁止开发。城市过渡区介于前两者之间,将来可以成为城市服务区。圣何塞市的这一城市开发政策于1972年被其所在的圣克拉拉县所采纳。(18)然而,最著名的限制城市开发空间的举措,莫过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大都市区的城市增长边界(UGB),后文将详加论述。
地方政府的增长管理措施往往是对增长的控制或排斥,把自己不想要的开发活动转移到其他社区,比如住宅开发尤其是低档住宅开发,从而把民生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开支和穷人与少数族裔转移到其他社区。这种地方性的增长管理措施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大都市区的蔓延及其危害。正如某位学者所指出:“地方政策主要会影响大都市区的内部结构和发展的分布,而且,如果这一政策是由地方政府自私自利的人员制定的,它还会是低效的和不公平的。”(19)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至少应该在区域的范围内进行增长管理。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区域机构不是具有实权的政治实体,其活动必须有州政府的推动和权威保障,只有州政府才具有足够的权威对地方和区域的增长管理进行宏观指导与协调。因此,州政府的增长管理政策法规才是实施有效增长管理的关键。
三、州政府和区域机构的增长管理政策
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注意到地方性增长管理的弊端,主张由州政府承担更广泛的责任,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社会需求,缓和社会冲突。增长管理由地方政府向州政府转移,是“静悄悄的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
州政府的增长管理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强调环境和生活质量问题。当时有6个州制定了增长管理法规,要求州、区域和地方政府采取行动,避免无序开发造成的负面影响。这6个州分别是佛蒙特州(1970)、佛罗里达州(1972)、加州(1972)、俄勒冈州(1973)、科罗拉多州(1974)、北卡罗来纳州(1974)。而夏威夷州早在1961年就制定了土地利用法规,1978年又制订了夏威夷州发展规划。(20)除了这些已经制定了增长管理政策的州以外,还有很多州开始着手制定相关的政策,到1975年,至少有21个州正在着手制定开发目标。南部的15个州组成了“南部增长政策委员会”,来制定该地区的增长管理备选方案,以规范未来几十年内的开发模式。(21)
在这一时期,许多州还成立了州一级的和区域性的规划和管理机构,以便协调全州和区域范围内的规划活动。在联邦政府政策(比如A—95联邦援助资金,见下文)的推动之下,许多州通过了相关立法,成立了区域性的增长管理和规划机构。比如在1970—1975年间,有47个州建立了A—95区域性信息交流处,超过一半的州建立了由多个地方政府构成的次州级的区域规划机构。一般而言,由州政府的相关机构确立全州范围的发展目标和管理政策,并责成地方政府制定综合性的发展规划,然后由州和区域性规划机构来负责审核和协调地方规划,以确保地方规划与州和区域规划目标一致,从而加强了州政府和区域机构对土地利用的管理。(22)但州和区域机构的这种介入也常常在州、区域、地方政府之间产生紧张关系,所涉及的问题包括:第一,每一层政府机构的权限分配问题;第二,这些权力如何实施;第三,州政府和区域机构如何控制地方政府。(23)
1974—1975年美国的经济衰退使城市开发压力减小,而且人们也希望通过开发活动来刺激经济活力,于是州级政府的增长管理活动势头减弱。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过后,开发活动的恢复又造成了新的增长压力,于是80年代中期出现了州增长管理立法的“第二次高潮”。在第二次高潮中,制定增长管理政策的州的数量激增,出现了“增长管理热”,而且“增长管理”一词正式而明确地出现在一些州的相关立法中。佛罗里达州的增长管理法案于1984年、1985年和1986年通过,成为第二次高潮的开端,到90年代初期,俄勒冈、佛罗里达、佐治亚、新泽西、科罗拉多、加州、夏威夷、缅因、佛蒙特、罗得岛、华盛顿等州都通过了某种形式的增长管理立法。(24)而到了90年代中期,美国有19个州制定了全州范围的增长管理法规,或建立了研究团队探究开发对于开放空间和农田的影响等问题。(25)第二次增长管理高潮所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和生活质量,而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更加注重“平衡”问题,即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需求,并且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强调基础设施必须能够支撑开发所导致的影响,尤其是交通设施;此外,还增加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比如满足对廉价住宅的需求问题等。(26)
州政府的增长管理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可称为自上而下的增长管理,即州政府在增长管理规划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州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和规划方案,确立全州性的发展目标。地方政府制定的规划要经过州和区域有关机构的审核,从而确保其与州规划目标和政策的一致。凡是与州规划目标不一致的地方规划就不能获得批准和付诸实施,或者扣留州政府给予该地方政府的规划援助基金。在更严格的情况下,州政府会将原来下放给地方政府的规划权或称警察权(police power)收回,由州政府或区域机构代替地方政府制订发展规划。实施这种增长管理方法的主要代表是俄勒冈州和佛罗里达州;缅因、新泽西、罗得岛、华盛顿等州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这种方法。(27)
第二类州增长管理方式可称为自下而上的增长管理,即州政府虽然也同样制定长远发展目标和增长管理法规,但它们一般只具有咨询性质,而不具有强制力。州政府的规划目标要通过地方政府实施,州政府责成地方政府制订综合性发展规划,由区域规划机构审核这些规划是否与州规划目标相一致。即使地方规划与州政府规划目标不一致,州政府也无权去阻止地方规划的实施。实施这种增长管理的州一般是一些草根民主比较发达,或公民的环保意识薄弱,而公民权意识尤其是财产权意识却十分浓厚的州,比如加州、佛蒙特和佐治亚等州。(28)
四、州政府增长管理的案例分析
前文指出,美国各州的增长管理方式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从总体而言可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本文仅以两个州为案例,来分析这两种方式的不同效果。
俄勒冈州是典型的实施自上而下增长管理的州,而该州的波特兰大都市区的增长管理最为著名,效果最佳。1973年俄勒冈州议会通过了“俄勒冈土地利用法”,成为该州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增长管理方面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该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确立了该州的19项总体规划目标,作为州政府各机构和各地方政府的规划标准,并且规定了州和区域规划机构对地方政府规划的制定、修改和实施过程的审批和监督。最关键的是,这19项规划目标具有强制力,而不仅仅具有咨询性质,如果地方规划没有达到州政府的有关目标,该州政府有权责令其进行修改,拒绝修改或修改不善者将受到处罚。州政府的权威不仅体现在对地方规划的审批上,更体现在州政府还对其实施进行跟踪监督,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州规划目标能够真正得到贯彻,这是其他许多州的增长管理措施所不能企及的。(29)
在规划内容方面,俄勒冈州的土地利用法确立了19项规划目标,建立了一个全州范围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其中第3项(Goal 3)和第14项目标(Goal 14)所规定的内容。第14项目标规定,各个城镇和大都市区周围建立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UGB),“以确定和区分用于城市化的土地和乡村土地”;第3项目标规定城市增长边界以外的地区为“排他性农业用地”(EFU),并成立“土地保护署”对这里的土地进行分类和保护。(30)在机构建设方面,该法授权州政府成立了一个州级的“土地保护开发委员会”(LCDC)及其行政机构“土地保护开发部”(DLCD)。这两个机构是该法的执行和监督机构,是保证该法得到实施的制度保障。此外,1979年该州还建立了“土地利用上诉委员会”(LUBA),它是一个具有司法性质的仲裁机构,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有关发展规划方面的争端,可以通过该委员会进行仲裁。(31)然后可以上诉到州上诉法院,最后可上诉到州最高法院。
波特兰大都市区的增长管理鲜明地体现了俄勒冈州增长管理的效果。1979年,波特兰大都市区成立了一个综合性的大都市区政府(Metro),它有权制订整个大都市区的综合发展规划,有权对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进行审查,并要求其与区域规划相符合。波特兰大都市区政府拥有民选产生的议会和民选的行政官员,它代表选民而非地方政府,所以具有更大的权威。这也是何以使该大都市区的增长管理最有成效的根本原因。
1979年波特兰大都市区政府制订了增长管理规划,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划定了城市增长边界,规定所有的城市开发都必须位于该边界之内。与美国其他地方的城市增长边界不同,波特兰的城市增长边界是“大都市区的增长边界”(Metro GB),而不仅仅是“城市的增长边界”(Muni GB),它为整个大都市区确立了一个区域性的增长边界。该边界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土地资源,限制城市蔓延。(32)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着扩大城市增长边界的冲突与斗争,但波特兰大都市区的城市增长边界还是比较稳固的。1998年12月,俄勒冈州议会做出折中性决定,先将3500英亩的土地划入城市增长边界以内,并在不久的将来再增加1900英亩。(33)在20年的时间里仅仅增加几千英亩的土地用作开发,这在美国大都市区的增长管理中已经是一个奇迹般的成果了。城市增长边界的存在提高了新建住宅的密度,节约了城市用地,限制了大都市区的蔓延,对于保护农用地和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紧凑的开发模式可以使居民住宅与就业地相互接近,便于提供公共交通,还可以节约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等。可见,俄勒冈州尤其是波特兰大都市区的增长管理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俄勒冈州相比,加州的增长管理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增长管理模式,由于州政府和区域机构在增长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大,因而其增长管理的效果相对而言并不十分理想。
1965年加州议会通过的土地保护法(威廉森法)是最早试图限制土地开发、保护农用地和开放空间的立法之一。该法规定,通过削减农业用地的财产税来阻止将农用地和开放空间转变为城市用地。但该法是由县政府负责执行,而不是由州政府的有关机构监督执行,而且县政府和农场主的参加也是自愿的。土地所有者要与参加该计划的城市或县政府签订为期10年的合同。在土地合同的有效期内,这些土地只能用于农业生产,而不能用于其他方面。当土地保护合同期限届满时,农场主可以解除合同。(34)
1976年,加州议会对威廉森法进行了修订,州政府对参加该计划的县进行拨款,以弥补县政府由于农场主参加该计划而蒙受的财产税损失,并资助参与该计划的县在有关方面的行政开支,从而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参与该计划。1987—1988财政年度,加州政府为补偿各县签订土地保护合同的开支而进行的拨款达到1450万美元。(35)该计划的实施对于保护加州的农业用地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加州大约有1500万英亩的农田加入该计划,占加州农田总数的一半。(36)
但是,威廉森法的自愿性注定了该计划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这是因为:第一,该法不能保护城市周边地区的农田,因为农场主认为他们有机会高价出售其土地,他们就不愿参加这一计划。第二,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因为农场主参加了这一计划,土地的价格评估就会受到限制,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就会遭受损失。第三,如果地方政府参与了该计划,为了弥补财政税收的不足,也可能会修改其土地利用规划或分区制规划,进行税收较高的工商业开发活动,从而导致地方政府间在土地利用方面的无序竞争,进而导致蔓延式开发。事实确实如此,比如在中央谷地县,从该计划的实施到1988年底,大约有5295英亩的土地退出了该计划;而在1989—1990年间,竟有2.5万英亩的土地退出该计划。就整个加州而言,每年竟有5万英亩的农田用于城市开发。(37)由此可见,仅仅依靠自愿性是不能很好地进行增长管理和保护农田等自然资源的。
加州增长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依靠地方政府进行增长管理,或者说地方政府是实施增长管理的主体。从数量上讲,加州地方政府的增长管理措施确实多得令人惊叹,许多增长管理方法,比如建筑限额制,也是由加州地方政府所首创的。根据一项调查,仅1989年加州、各县和各城市就采取了850多项增长控制和增长管理措施。但是,加州不像其他许多州那样制定了范围广泛的州增长管理法规,也没有制定全州范围的综合性规划和区域规划,增长管理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而这些地方政府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毫不顾及其增长管理措施对其他地方政府的负面影响。另外,加州也没有一个全州性的行政机构来监督和审核地方规划。在一般情况下,加州的规划法律不是由州政府监督执行,而是由该州的公民或公民团体监督执行,并通过司法程序对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这种增长管理被威廉·富尔敦称为“公民执法”。这种公民执法不能起到事先防范的作用,属于事后纠偏,而且诉讼过程繁琐拖沓,不能起到及时纠正的作用,效果很差。因此,加州在增长管理方面虽然曾经在实施时间上领先,但在深度和强度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各州,结果使该州的增长管理问题更加恶化。(38)总之,加州的增长管理更体现了美国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
五、联邦政府对增长管理的推动作用
总体而言,联邦政府的政策不利于增长的有效管理。与英国等欧洲国家不同,美国联邦政府从来没有制定过全国性的土地利用政策和综合发展规划,也没有全国性的土地利用规划机构来对各州和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进行规范,这也许是美国大都市区的蔓延程度远远比欧洲国家严重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鲜明地体现在1956年联邦高速公路法的影响上。由于美国不存在全国性综合土地利用规划,因此当高速公路系统穿越美国各个大都市区时,在公路位置的选择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从而造成高速公路布局混乱,不能有效地服务于现有的社区和合理地引导城市增长模式。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的某些立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州、区域和地方政府的增长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1954年国会制定了联邦住宅法,该法第七条第701款规定,为了推动小型城市(人口在2.5万人以下)、大都市区规划团体、区域规划机构制定增长管理规划,联邦政府对这些规划活动提供援助资金,而由州政府机构负责执行。该法还规定对各州的各种规划机构的规划活动提供指导。在该法的推动之下,全国市政联盟于1955年发表了一个“州和区域示范法”,推动了各州政府的规划活动。在1960年到1968年间,积极进行规划活动的州的数量从13个增加到39个。1964年各州规划机构成立了“州规划机构联合会”。更重要的是,州的规划机构的地位大大提高,它们大多直属于州长办公室,受州长的直接领导。对州规划影响最大的是联邦援助资金的增加。在1959—1969年间,联邦援助资金从60亿美元增加到200亿美元。到1967年,这一援助囊括了399次拨款和大约162个主要的州规划项目。这些拨款的1/3直接拨给各州,1/6直接拨给地方政府,1/2则通过州政府提供给地方政府。(39)随着联邦援助的增加,各州的规划能力大大提高。
在各项联邦政策中,对各州和地方政府增长管理活动影响最大的是联邦“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A—5通函(Circular No.A—95)援助项目。A—95援助项目源于两项联邦立法:第一项立法是1966年的“示范城市和大都市区发展法”(Model Cities and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Act)。该法第204款授权大都市区内各种公共设施的开发项目可以申请联邦援助,而每项申请书都必须得到大都市区规划机构的审批,且必须符合大都市区的综合性发展规划,大都市区审批机构的评语要与申请书一起提交给联邦拨款机构进行评估。第二项立法是1968年的“政府合作法”。该法第四条第401(c)款规定,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要“在最大可能的限度内与国家目标保持一致,所有联邦援助的开发目标应该符合并推进州、区域和地方综合规划”。这两项立法都授权“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制定和实施这两项法律的规章和细则,于是该办公室发布了“第A—95号通函”,根据该通函对地方和大都市区综合规划项目所进行的援助称为A—95援助。这些细则成为推动联邦援助的地方项目之间协调一致的一个有效的举措。(40)然而,A—95计划并不是全国性的综合发展规划和综合性的土地利用规划,它只是依靠区域机构对开发项目进行逐一的审查。
联邦政府的增长管理措施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功能的单一性,即通过单功能立法而不是综合立法推进增长管理。这一特点鲜明地体现在国会通过的一系列环境立法当中,它们都在某一方面对土地利用产生了某些影响,但没有一项立法是专门针对土地利用问题的。比如1965年的“水资源规划法”授权联邦政府向各州发放配套拨款,帮助各州制订综合性的水资源和相关土地资源的规划。同年的《土地和水资源保护基金法》授权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配套拨款,帮助制订全州范围的综合性的户外娱乐空间规划。(41)
在所有的联邦环境立法中,对增长管理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969年国会通过的《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该法要求重大公共项目必须提交“环境影响声明”(EIS),所谓“环境影响声明”,就是一项关于拟议中的土地利用开发项目对环境的潜在影响的评估报告。这里的“环境”一词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而且还包括对经济活动和公共设施、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和税收、对住宅和其他开发活动等方面的影响。该法通过后仅5年,就有17个州制定了类似的环境政策立法,规定重大公共开发项目必须提交环境影响声明,其中7个州还要求重大的私人开发项目也要提交环境影响声明。许多重要的公私开发项目由于不能达到声明的要求而被迫推迟,有些项目甚至永久性地冻结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大都市区空间蔓延的速度。(42)后来,联邦政府通过的其他一系列环境立法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比如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1972年的《滨水地区管理法》和《联邦水污染控制法》等。但是这些环境立法没有一项是针对增长管理的核心即土地利用问题的,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功能的立法,不能有力地确保在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方面的整体机制。比如水资源管理法虽然暂时禁止了某些郊区的排水管道的铺设,但由于没有土地利用综合规划,开发商可以到更远的有排水管道的地方进行住宅开发,结果导致了蛙跳式的开发和更严重的郊区蔓延。(43)
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静悄悄的土地利用革命,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性,一些州和地方政府制订了综合性的土地利用规划。在这种氛围之下,国会也开始考虑制定全国性的土地利用规划。尼克松总统在其第一次国情咨文中宣称:“我承诺,在这些问题尚未严重到不可挽回之前,本国将制定一个全国性的增长政策。”(44)他在1972年2月关于环境的国情咨文中再次宣布:“一种成熟的新的思想正在孕育一种新的土地伦理,这种伦理认识到,滥用土地会影响公众利益,并且会限制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的选择机会。现在,我们必须授权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使之能够履行这种新观念所包含的职责。我们必须建立必要的行政及管制机构,保证土地能够被明智利用,并制止无计划的、浪费的及破坏环境的开发。”(45)
在这种鼓舞人心的形势下,1970年1月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土地利用政策法》的议案,揭开了一场关于土地利用政策的全国性大辩论。杰克逊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就是要力图保证“将来所有的开发”都将“符合合理的生态法则”。他在议案中提出:联邦政府将为各州的综合土地利用规划提供援助资金;各州政府收集有关其土地生态特征的数据,并提出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方向。1971年冬,尼克松政府提出了由国家环境质量委员会起草的另一个替代方案。这两项议案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不要求联邦政府采取直接行动,而是通过联邦援助资金来鼓励各州制定相关的土地利用法规。经过妥协,1972年国会出台了一个折中法案,即《土地利用政策和规划援助法》,其主要条款是:只要州政府愿意清查其土地并建立土地利用管理系统,联邦政府就将对其进行资金援助。(46)经过几番周折之后,法案终于在1974年1月获得国会两院的通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尼克松总统突然撤回了对法案的支持,拒绝签署。随后,国会也未能凑足2/3的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47)这样,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制定增长管理法规的尝试就彻底失败了。事实上,尼克松总统的否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因为在为期两年的法案辩论中,大多数选民反对这一法案,因为它威胁了美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民权,即财产权。这说明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威胁公民基本权利的土地利用法规是难以成功的。
总之,当代美国的高速增长和大都市区的低密度蔓延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危害。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的增长伦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所谓的“静悄悄的土地利用革命”,美国各级政府都实施了某些增长管理的措施,并在不同程度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美国的增长管理和精明增长运动尘埃未定,尚难以对其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与此同时,增长管理和精明增长运动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一,美国联邦政府不能像英国等欧洲国家那样可以制定全国性的发展法规和土地利用法规,不能有力地指导和规范各州的开发模式和发展进程。第二,以加州为代表的一些“草根民主”和地方自治传统浓厚的州,州政府无法制定全州性和综合性的增长管理法规和土地利用政策,更不能成立强有力的州和区域规划机构。地方政府在制定增长管理法规和土地利用规划方面自由度太大,因而州政府不能有效地实施增长管理政策。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公民对财产权的保护已经形成一场政治运动。在法院和立法机构中,保护财产权的倡导者已经对美国的环境和土地利用政策构成了巨大挑战。美国的增长管理运动以及后来的精明增长运动仍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关于美国城市或大都市区蔓延所产生的危害,参见孙群郎:《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孙群郎:《当代美国郊区的蔓延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世界历史》2006年第5期;孙群郎:《当代美国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特征与交通困境》,《世界历史》2009年第5期;孙群郎:《美国郊区化进程中的黑人种族隔离》,《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
②关于这些城市改造运动,参见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旭、罗思东:《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孙群郎:《美国内城街区的绅士化运动与城市空间的重构》,《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孙群郎:《美国新城市主义运动的兴起及其面临的困境》,《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③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Randall W.Scott,ed.,Management & Control of Growth:Issues,Techniques,Problems,Trends)第1卷,华盛顿1975年版,第5页。
④阿瑟·C.纳尔逊、詹姆斯·B.邓肯:《增长管理的原则与实践》(Arthur C.Nelson,AICP,James B.Duncan,AICP,Growth Manage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华盛顿1995年版,第1页。
⑤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1卷,第2页。
⑥威廉·K.赖利:《关于美国土地利用的六个神话》(William K.Reilly,"Six Myths:About Land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1卷,第100页。
⑦厄尔·芬克勒:《作为规划另案的非增长——当前争议初探》(Earl Finkler,"Nongrowth as a Planning Alternative: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an Emerging Issue"),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1卷,第120—121页。
⑧拉塞尔·E.特雷恩:《增长与环境质量》(Russell E.Train,"Growth with Environmental Quality"),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1卷,第44页。
⑨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1卷,第4页。
⑩弗雷德·P.博塞尔曼、戴维·L.考利斯:《静悄悄的土地利用控制革命》(Fred P.Bosselman and David L.Callies,"The Quiet Revolution in Land Use Control"),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1卷,第245—248页。
(11)杰伊·M.斯坦主编:《增长管理——20世纪90年代的规划挑战》(Jay M.Stein,ed.,Growth Management:The Planning Challenge of the 1990s),纽波利帕克1993年版,第VII页。
(12)罗伯特·卡恩:《我们的增长由此走向何方?》(Robert Cahn,"Where do We Grow from Here?"),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1卷,第70页。
(13)迈克尔·A.安琪拉斯托:《非增长与穷人——增长控制政策中的平等思考》(Michael A.Agelasto,"No-Growth and the Poor:Equity Considerations in Controlled Growth Policies"),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1卷,第431页。
(14)迈克尔·A.安琪拉斯托:《非增长与穷人——增长控制政策中的平等思考》,第430页。
(15)保罗·L.尼班奇:《增长控制和不平等的产生》(Paul L.Niebanck,"Growth Controls and the Production of Inequality"),戴维·J.布劳尔等主编:《理解增长管理——关键问题与研究议程》(David J.Brower,et al.,eds.,Understanding Growth Management:Critical Issues and a Research Agenda),华盛顿1989年版,第109—110页。
(16)欧文·希夫曼:《增长管理的备用技术》(Irving Schiffman,Alternative Techniques for Managing Growth),伯克利1999年版,第6页。
(17)道格拉斯·R.波特主编:《增长管理的行动标准——一份PAS报告》(Douglas R.Porter,AICP,ed.,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Growth Management,a PAS Report),华盛顿:1996年版,第19—24页。
(18)美国规划协会:《地方融资与发展管理——分析与个案研究》(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Local Capital Improvements 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华盛顿1980年版,第142—143页。
(19)威廉·阿朗索:《城市的零人口增长》(William Alonso,"Urban Zero Population Growth|),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1卷,第408页。
(20)约翰·M.德格罗夫:《增长管理与治理》(John M.De Grove,"Growth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戴维·J.布劳尔等主编:《理解增长管理——关键问题与研究议程》,第23页。
(21)生态学家:《生存蓝图——摘录》(The Ecologist,"A Blueprint For Survival:Excerpts"),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3卷,第320页。
(22)弗兰克·施尼德曼等主编:《增长管理与增长控制——技术的应用》(Frank Schnidman,et al.,eds.,Management & Control of Growth:Techniques in Application)第4卷,华盛顿1978年版,第254页。
(23)阿瑟·C.纳尔逊、詹姆斯·B.邓肯:《增长管理的原则与实践》,第19页。
(24)杰伊·M.斯坦主编:《增长管理——20世纪90年代的规划挑战》,第Ⅶ页。
(25)兰德尔·G.霍尔库姆、塞缪尔·R.斯坦利:《土地利用规划概论》(Randall G.Holcombe and Samuel R.Stanley,"Land-Use Planning: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兰德尔·G.霍尔库姆、塞缪尔·R.斯坦利主编:《精明增长——21世纪土地利用规划的市场战略》(Randall G.Holcombe and Samuel R.Stanley,eds.,Smarter Growth:Market-Based Strategies for Land-Use Planning in the 21[st] Century),韦斯特波特2001年版,第2页。
(26)约翰·M.德格罗夫:《增长管理与治理》,第32页。
(27)阿瑟·C.纳尔逊、詹姆斯·B.邓肯:《增长管理的原则与实践》,第22页。
(28)阿瑟·C.纳尔逊、詹姆斯·B.邓肯:《增长管理的原则与实践》,第26页。
(29)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在城市边缘耕作——农田保护的备选方法评估》(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Plowing the Urban,Fringe:An Assessment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Farmland Preservation),劳德代尔堡1989年版,第52页。
(30)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在城市边缘耕作——农田保护的备选方法评估》,第53页。
(31)康斯坦斯·E.博蒙特:《精明的州,更好的社区——州政府如何帮助其公民保护其社区》(Constance E.Beaumont,Smart States,Better Communities:How State Governments Can Help Citizens Preserve Their Communities),华盛顿1996年版,第290页。
(32)罗伯特·T.邓菲:《摆脱困境——交通与开发》(Robert T.Dunphy,Moving beyond Gridlock:Traffic and Development),华盛顿1997年版,第48页。
(33)卡尔·艾博特:《可持续城市的规划——波特兰城市增长边界的诺言和成就》(Carl Abbott,"Planning a Sustainable City:The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of Portland's Urban Growth Boundary"),格雷戈里·D.斯夸尔斯主编:《城市蔓延——原因、结果与政策反应》(Gregory D.Squires,ed.,Urban Sprawl:Causes,Consequences & Policy Responses),华盛顿2002年版,第219页。
(34)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在城市边缘耕作——农田保护的备选方法评估》,第25—26页。
(35)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在城市边缘耕作——农田保护的备选方法评估》,第24页。
(36)蒂姆·帕尔默主编:《加州环境危机——恢复梦想》(Tim Palmer,ed.,California's Threatened Environment:Restoring the Dream),华盛顿1993年版,第150页。
(37)蒂姆·帕尔默主编:《加州环境危机——恢复梦想》,第150页。
(38)威廉·富尔敦:《走在最前列——加州的增长管理和增长控制》(William Fulton,"Sliced on the Cutting Edge:Growth Management and Growth Control in California"),杰伊·M.斯坦主编:《增长管理——20世纪90年代的规划挑战》,第114—115页。
(39)弗兰克·施尼德曼等主编:《增长管理与增长控制——技术的应用》第4卷,第252—253页。
(40)威廉·K.布鲁萨特:《A—95审核制——能否成为一种有用的制度?》(William K.Brussat,"A-95 Review System:Can Be an Asset?"),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第3卷,第298—299页。
(41)弗兰克·施尼德曼等主编:《增长管理与增长控制——技术的应用》第4卷,第253页。
(42)罗伯特·格拉德斯通、罗伯特·威瑟斯庞:《环境影响声明与开发——起源、演进及其影响》(Robert Gladstone and Robert Witherspoon,"EISs & Development:Origins,Evolution,Impact"),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3卷,第142页。
(43)帕梅拉·C.麦克:《联邦环境立法——零碎的土地利用模式》(Pamela C.Mack,"Federal Environmental Laws:Piecemeal Land Use"),兰德尔·W.斯科特主编:《增长的管理和控制——争议、技术、问题和趋势》第3卷,第422页。
(44)帕梅拉·C.麦克:《联邦环境立法——零碎的土地利用模式》,第411页。
(45)亚当·罗姆著,高国荣、孙群郎、耿晓明译:《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46)亚当·罗姆著,高国荣、孙群郎、耿晓明译:《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195—196页。
(47)亚当·罗姆著,高国荣、孙群郎、耿晓明译:《乡村里的推土机——郊区住宅开发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第2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