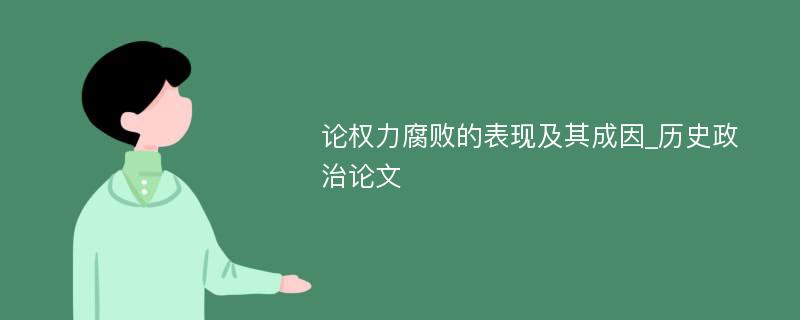
论权力腐败的表现及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腐败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1)03-0053-06
腐败,这一当今社会的毒瘤,从不同角度我们可以给出不同的定义。从经济学角度看,其实质是一种权力寻租和出租活动,即权力客体和权力主体以私利为中心和目的进行交换,前者以较低成本和代价租用后者所持有的公众权力而获取其中的利益差额,后者则出租自己所持有但本身并不属于自己的公众权力而获取法外私利。从政治学角度看,其实质是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在各自私利驱使下,共同改变公众权力性质,使公众权力蜕化成自己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社会学角度看,它又是一种违法乱纪行为,是一种与社会道德相背离行为,具有损他人、利自己、践法纪、乱社会的特点。
然而不管怎样给腐败下定义,我们都会看到,权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权力腐败是诸多腐败的根源、轴心和实质。我们要反对腐败,首要的、根本的、长期的就是要反对权力腐败。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权力腐败的“中国特色”表现及成因做一探析。
表现:目的变异;指向错位;构成“四化”
权力腐败,不是中国的特产,但却具有浓浓的“中国特色”。应该指出,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其做过探讨和论析。这些探讨和论析无疑是有益的,推动了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然而笔者认为,当前就权力腐败问题的研究,对其“中国特色”却揭示不够。我们反对权力腐败,要真正取得实效,则必须深刻剖析,揭示出其“中国特色”,以权力为轴心来提出和认识问题,方能对症下药,有效施治。关于权力腐败的“中国特色”表现,笔者认为关键有如下几条:
(一)权力获取目的变异
权力,就其本义而言,是一种社会公众的委托,只能用来为社会公众办事。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党纲党章更是明确规定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权力持有者——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革命战争年代,对于我们党来说,有的只是危险、风险和困难,到党的队伍里来找个人出路的人是很少的,即使有也很难经得起生死考验。所以,那时候入党、当干部的人基本上都是为穷人打天下,他们追求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其目的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谋得个人的一官半职。即使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也基本都能为社会公众办事,为人民服务。然而建国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我们党从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作为她的成员和干部,不仅没有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危险、风险和磨难,而且还可以享受到其他一些人所不能享受的法定待遇,还有了以权谋私的机会,这就导致一些人入党、当官的目的与公众权力的性质和党的宗旨发生背离和变异,由为社会、为大众蜕变为为个人、为私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领导干部更是力图使自己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转换为经济财富,利用党和人民的权力疯狂地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填充和实现自己的私欲。这种权力获取目的的背离和变异,埋下了权力腐败的祸根,是权力腐败的起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当官”是为人民、为社会的思想观念在某些单位和局部已经越来越少,而为自己、为私利的腐败观念则在那里越来越占上风;尽管在客观上许多人也能为党和人民做一些事情,但从目的上讲仍然是在为自己。这种权力获取目的的变异和背离,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治理和制止,那么我们反对权力腐败就可能如同割韭菜那样,割了一茬再生一茬,割不胜割,直至变质。
(二)权力指向错位
目的决定手段,这是一条铁律。某些权力持有者
“当官”目的的私利性和反人民性,必然导致他们在权力指向上的错位和倒置。其主要表现:
1.在政治上,将权力公有转化为私有。一些领导干部世界观已经变质,他们利用所窃取或掌管的党和人民的权力,媚上:力图使自己的权力升值,谋取更大的权力资本,因为他们的第一步“投资”已经获益;压下:权力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嫉贤妒能,压制正义。在他们眼里,权力完全变成了他们个人的私有物,应该而且必须为构筑自己的权力上升通道和维持自己的权力地位服务。这种权力指向在政治上的错位,直接后果就是家天下、帮天下、私天上。对于下属,极力培植奴化思想和绝对服从观念;对于上级,又极力阿谀奉承,不讲原则,不讲党性。这就会在党和干部队伍内形成一个个与党的纲领和党的宗旨不能相容的利益集团。
2.在经济上,将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资产阶级时曾这样指出:掌握着经济权力的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论述向某些人身上一套,就会发现,现在一些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总是千方百计使自己的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资本。一些贪污、受贿几百万、上千万之巨的大案、要案,不都是出在握有重要政治权力者的身上吗?“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说过这样一句话: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毛泽东关于党内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论断未必得当,但是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资产阶级权力已经侵入到我们的党和政治制度内,却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从贵州省的“第一夫人”到北京市的“第一书记”,再到成克杰这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我们党内和领导层内的部分权力腐败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一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实际上他们是既握有政治权力,又拥有经济资本的披着“红色外衣”的资本家——帮凭借权力掠夺增殖而发达起来的“中国特色”新贵。
3.在生活作风上,腐朽糜烂,霸道专断。现在在一些机关和领导层中,奢侈浪费、大吃大喝等违纪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司空见惯,这已不是那一个人的过错和罪过,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对此我们姑且不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党的某些干部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挥金如土,声色犬马,群众戏称为“灯红酒绿桑拿浴,游山玩水带小蜜”,对此我们恐怕不能一概斥之为望风捕影。在工作作风上,家天下,帮天下,一言堂,一人堂,用人唯亲唯派,办事根据上钱多少……不一而足。权力笼罩下的某些人,生活已经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作风已经货真价实“老爷”化了。
(三)权力构成“四化”
首先申明,这里所说的权力构成“四化”,仍就部分而非整体而言。我们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仍然不容置疑。但是权力构成存在某种程度的“四化”现象——亲缘化、嫡系化、商品化和互相转化,也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
1.亲缘化。亲缘化,又可做裙带关系解释。我国封建社会有世袭制之说,即老子死后其官位可以由儿子承袭。一人当官,三亲六故沾光。当官者永世当官,为民者永世为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随着他们的血统延续而延续。这种状况势必阻碍社会前进,造成社会黑暗,引起人民群众的极端不满和强烈反抗。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时甚至喊出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尽管这种腐朽东西已被彻底否定,但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仍屡屡出现。一个人在重要部门或岗位任职,他的老婆、孩子及其他亲属统统容易受到特殊关照,得到一定提拔,尽管他们的德才比照他人可能逊色许多。结果往往出现这种现象:当官是一家子一家子的、一窝子一窝子的,家庭亲友聚会成了个“三级干部会”。在当前的干部选拔制度下,一些地方和部门当官者的老婆、子女及其亲属进入权力层(尽管官职可能有大有小之别)的比例,可能要远远高于平民百姓及其子女亲属进入权力层的比例。在我们国家,亲缘关系恐怕占有了权力资源的相当一部分,甚至在有些机关连称呼也由称同志或官衔改为叫“叔叔”或“阿姨”。如此这般,党的原则何以还能得到贯彻执行!
2.嫡系化。孔子曾提出“君子群而不党”。孔子是把“党”作为帮派意义而言的。毛泽东一贯提倡搞“五湖四海”,反对搞帮派、搞小圈子,反对“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知道,过去国民党的军队有嫡系和非嫡系之分,嫡系的待遇、地位都要高于非嫡系。我们共产党历来是反对这一套的。然而,我们的某些掌握着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却重拾历史沉渣,对人以自己为中心,搞帮帮伙伙。入了他们圈子的,才可能得到提拔重用,否则只能坐冷板凳。他们指鹿为马,圈内的人,有门、有根子的人,对于他们维持和发展权力有用的人,明明是庸才也当成人才;圈外的人,没有门、没有根子的人,对于他们维持和发展权力没有用的人,则根本不放在眼里,甚至给以排斥打击。这就导致人们要当官不走正道走邪道,先去找后台、找根子。从而,使正直和有本事的人,心里没了底,造成凭关系、凭钻营,不凭本事当官的风气。
3.商品化。权力,本来是社会公众的一种委托,不是商品,不能交换。然而,现在某些权力持有者却把权力变成了一种商品,使其具有了商品特征,甚至可以标上价码,进行出售,形成权力交易市场。大量事实说明,出卖官职和权力,在我国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是典型一例。“副科提正科,需要一万多”,“副县提正县,需要四五万”,就是其卖官丑恶行为的真实写照。人民群众中还流传着什么“要得富,动干部”的顺口溜,就是指卖官者通过动干部来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促使干部为保住或取得理想的官位争相进贡,这样卖官者就能够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现在盛行于权力场的出卖官职行为,比之于旧社会出卖官爵更加恶劣:后者出卖的是封建国家机器的职位,前者出卖的是人民的权力;后者是把职位出卖给社会的有钱人,前者则是把权力出卖给投机者;后者把卖官所得充实了国库,前者卖官所得则中饱了私囊。两相比较,使我们看到,21世纪的今天,我国带有“黑金政治”色彩的权力腐败和权力交易,是多么腐朽落后而又与时代格格不入。
4.互相转化。权力按其特性来说,一般可能有三个:一是其地域性,即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有效,超出其范围则失效;二是其行业性,即在一定条件内有效,超出此条条则失效;三是其时效性,即在职在位时有效,反之则失效或无效。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使权力的三个特征界限消失,权权置换,使此地的权力转化为彼地的权力,使此条条的权力转化为彼条条的权力,使此时的权力转化为彼时的权力。我们看到,有的人明明是甲地的“父母官”,而在乙地私事却照样办;有的人明明是管干部的,但对于财政、文教等其他部门的事宜却照样能干预;有的人明明已改换岗位或退休,然而在原岗位上的利益却照样有人维护。我们可千万不能小看了这种转化和置换,它会使权力腐败得以超时空、超范围滋生和蔓延,在权力结构内部形成利益集团和利益阶层,从而交叉感染,为祸国民,使权力腐败呈几何级增长和繁殖。
成因:自蚀作用;环境影响;体制弊端使然
权力腐败作为诸种腐败的根源和集中表现,从韩国的两任前总统被推上审判席,到中国的那个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案件,再到我们身边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何以肆虐政坛,屡反不绝,甚至蔓延泛滥?我认为,这其中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权力的自蚀作用
权力不是不锈钢,而是一块易生锈的铁。这是由权力的自身性质决定的。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我们知道,阶级社会里的权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并超然于其上的一种特殊力量,是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支配、服从关系。权力性质的这种超然性和支配性,决定了权力持有者容易脱离权力产生的初衷,成为谋私利、危及他人甚至社会的工具。这种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权力的自蚀作用。权力自蚀作用既存在于历史上,也存在于现实中。历史上的统治者,在他们夺取权力之前可能是革命者,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一旦获得政权,往往很快就会蜕变为反对革命者,蜕变为历史前进的反动力,这里面就有权力自蚀在发生作用。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些人没当官以前,为人处事都不错,当了官后很快就变了:手伸长了,嘴吃馋了,腿变短了,爱摆官架子,好拿官调子,甚至走向犯罪……这里面也有权力的自蚀作用。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谁在判决总统》一书揭示了前韩国总统卢泰愚从“民主斗士”到当上大总统后日益腐败的轨迹,也告诉我们: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一把手”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和制约,其自蚀作用是何等剧烈!也正是如此,文明国家无不力求对权力进行全方位监督,或采取分权制,或设有专门监督机构,履行这一使命。
权力的自蚀作用,具体可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在政治权力方面。我们知道,政治权力是由政治资本和政治资源所产生的支配力量,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甚至残酷性。这种强制性和残酷性固然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然而正像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各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一样,它有时又往往与民主、民意、(人)民(利)益相背离和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持有者为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往往本能地、自觉不自觉地镇压和反对民主、民意,损害人民利益。二是在经济权力方面。我们知道,经济权力是由经济资本和经济资源所产生的经济支配力量。以往社会统治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代表,由于他们占有生产资料而对人民群众形成支配力量姑且不论。在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每一个单位的领导(或曰权力持有者),他们也都要掌握一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力。这种支配权力往往形成一些人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贪污受贿、排斥异己的工具,从而使公众权力走向异化和自蚀。三是精神权力。我们知道,精神权力是由精神资本和精神资源所产生的精神支配力。现代心理学认为,人们除了具有物质的需要外,还具有精神的需要。尤其在现代社会,这种精神需要甚至更为重要。而作为组织成员,这种精神需要很大一部分要在领导者那里获得,诸如信任、荣誉、自由、理想等等。而领导者由于拥有这种精神权力,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控制和左右被领导者的思想和行为。这样,从一方面讲,一些领导者能够按照组织目标和规则行使这种权力;从另一方面讲,一些领导者或者由于水平问题,或者由于思想意识问题,又不能正确地行使这种权力,甚至歪曲地、错误地行使这种权力。例如,违背真理原则,强迫下属接受和支持自己的错误主张;如荣誉授予不当,工作评价不公等等,这些都属于领导者精神权力的滥用和自蚀。有时他们也明知这种做法和行为是错误的,但因为自己拥有权力,为了自己的私利、地位甚至“官面子”等东西,也往往强制推行。可见,权力的自蚀作用在精神领域同样顽强存在。
(二)环境的影响作用
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是欧洲哲学史上“环境论”者的著名观点。这话虽然不全面,但就其强调环境对人的巨大作用来说,其真理性却是不容怀疑的。今天,我们国家一些地方,权力腐败之所以达到一定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环境的产物和表现。我们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论述:
1.外部环境影响。权力腐败,已成为世界性、世纪性话题。这一人类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正在不分国别、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制度地在全球范围内恶性滋生、蔓延,吞噬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和平等。近二三十年以来揭露出的大量事实说明,权力腐败不仅存在于下层、中层,而且更存在于上层、最高层。韩国两任前总统被推上审判席,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贪污公款1亿多美元,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几乎把整个国民收入的几分之一据为己有,并存于国外银行……整个世界政坛,就像得了瘟疫,权力持有者们似乎在进行着一场权力腐败的竞赛,并且已经昂首阔步地跨入了新的世纪。
我国的权力腐败,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国际大环境下权力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最腐朽思想毒素,无不被某些权力持有者拿来惟我所用。只不过我国的权力腐败更具有中国特色罢了:极少数变了质的政府官员更贪婪、更自私、更赤裸裸的。
2.内部环境影响。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无疑是一项伟大战略决策。然而,它又必然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应当承认,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还是很不成熟、很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我国的政治权力规则还是很不成熟、很不完善的政治权力规则。一方面,法律真空大量存在,在许多方面无法可依;另一方面,法律虚置现象严重,在许多方面有法不依。改革开放活跃了社会的经济、政治和人们的思想,也激活和诱发了腐败行为。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不正之风的话,那么今天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腐败成风了。由于腐败现象司空见惯,所以人们由气愤、反对逐渐到麻木、习惯。由于原来腐败的人看到搞腐败风险很小、代价很小,而收益却极大,所以在屡屡得手之后,胆子变得更大,手段变得更毒,腐败者变得更加腐败。原本廉洁自律的领导者,看到腐败现象大量滋生、恶性蔓延,且得不到有效治理,自觉再不与之合流,就会吃亏、碰壁、孤立,于是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所操守的官德发生了逆转,这样,不腐败者也可能变得腐败了。对于普通社会成员来说,感到自己无权无势,既搞不了腐败,也治不得腐败,旧社会都说“官贪民偷”,现在“偷”不行,那么也就学乖点,利用腐败机制和权力办点私事、捞点实惠!这样,腐败者又成了某些普通社会成员的依靠对象,某些普通社会成员又成了腐败者的社会基础。总之,权力腐败和社会环境的这种交叉感染,使权力腐败这一顽疾久治不愈,越发严重。在中国,从上到下,可以说人人都说存在腐败,人人都说应该惩治腐败。然而许多人又可能本身就在搞腐败,又可能本身就是腐败的社会基础。“中国特色”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已经达到了一个仅凭说教难以改变的程度,这种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顽疾须猛药,要改变这种权力内部环境,非来狠招不可。
3.历史环境影响。历史环境,又可称之为历史基础。历史环境的影响,我们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首先从我国的历史环境看。我国历史悠久,科技文化曾一度领先于世界,这是好事。但同样不可不论的是:悠久历史积淀下来的一些东西却是惰性的、阻止历史前进的,其中对权力腐败起支撑和基础作用的就有:一是人治观念。人治有利于治人者,这是治人者总是崇尚人治而废弃法治的根本原因。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在中国总有那么一些人,谁当了官,谁就想人治。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延续的原因之一。尽管在春秋时我国就有了法家并大肆宣传法治,然而至今法治却仍未能真正建立和实行起来,在许多方面和有的时候仍然是人治。人治就是治人者说了算,这就为人治者随意治人提供了基础,为权力腐败埋下了种子。二是“重官”观念。一个社会是崇尚官职,还是崇尚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判定这个社会是先进还是落后的重要尺度之一。据出国考察人员回来讲,在西方国家,一个教授往往很被社会看重,而一个处长则没有这份荣耀,因而有些出国人员以在名片上印上“教授”为荣。在我国则相反。据有关资料介绍,在美国年轻人中最有才能的人大都流入商界和法律界,后来进入政界担当大任的也大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和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从政则是年轻人最热门的职业。近几年虽然被市场经济冲掉了一些,但仍然严重存在。一个社会,大家都争相去当“官”,这很难同大家都去争相为人民服务画等号,实际上是法外利益诱使人们去挤抢这条道。三是依赖德性观念。对干部过分依赖德性,也容易出现偏差。人们公认,我们现在的官员队伍存在着严重腐败,然而哪一个又不是在“重德性”的前提下选择出来的?实际上人人都有人性和德性两方面。对于政府官员,我们也只能通过法制促其克服人性弱点,光大德性优点。反之,过多的依赖觉悟、德性而不靠法治监管,使一些表面看似德性好,实际上却是私心大而且隐蔽的人进入干部队伍,并得不到有效治理和监管。我国官员队伍的腐败现象,应当说与我们重德性、轻法制不无关系。正确的办法应该是重才学、重法制、重监管。
其次,从我们党的历史环境看。我们党有着伟大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有着很好的宗旨——为人民服务。这些也都鼓励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人民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我们党实行的基本上是感召式权威领导,即领袖振臂一呼,万众一齐奋勇前进。应当肯定,这种领导方式在革命战争年代是非常必要的,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再过多地依赖这种方式则会受到很大限制。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向是由感召权威向法理权威过渡。我们在这种过渡中尚有不适应、不赶趟的情况。为什么治理腐败问题中央决心大,而下面行动缓、收效微?这里面与法理权威尚未安位、感召权威又鞭长莫及不无关系。在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真正确立起法理的权威,适当削弱个人影响。这样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过多地依赖于个人总不是个办法。
再次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偏差看。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对待这一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做法:一是把指导思想等同于工作方针,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指导思想,顾名思义是专门指导思想的,是为思想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而工作方针才是指导工作的。我们用指导思想去指导工作,实际上是把指导思想庸俗化、低级化。体现在干部工作中,就是用定性的、模糊的思想觉悟去处理有关干部工作的各种具体问题,结果造成随意性过大,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精确把握和运用,从而给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缝隙。二是把相对真理当成绝对真理,使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各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于他们的那个时代和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真理。长期以来,我们却把这种相对性加以绝对化、凝固化、教条化和惟一化,使马克思主义失去生机和活力,不能随着变化了的世界而变化,从而使人们对其真理性发生了怀疑。在国际共运史上,许多人长期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向世人灌输他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当历史过了几十年回过头来看,一些人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东欧、苏联剧变,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遭损,就是对这种假马克思主义主观性和随意性曲解的注脚。在我国,其直接政治后果就是导致了包括某些干部在内的许多人的信仰危机,导致了剥削阶级思想乘虚而入、腐败加剧。
(三)权力体制弊端使然
权力体制,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权力产生、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应当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具体到体制上,则弊端不少,后果严重。就权力体制而言,我认为至少存在下述严重弊端:
1.重“德性”轻才能。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几年前我在《新华文摘》上看了一个“观点摘要”:选拔干部要重才轻德。当时我的心头为之一震,这能行吗?然而细读文章,却发现极有道理。社会是靠人才支撑的。对有才的人在起用的同时应加强监管,从而使其既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又不能跑偏走歪。然而,从“文革”前的“白专道路”,到现在某些人的用“政治眼光”看人,在重“德”轻才的传统偏见下,我们压抑了多少人才,给事业造成了多少损失?时至今日,那种有才的人坐冷板凳、平庸的人滥其岗位的现象,仍不鲜见。这种现象在事业单位、国企部门其表现尤为严重。这里还应指出,一些人的所谓“德”,实际上是一个被歪曲、偷换了概念,与江泽民谈的“以德治国”风马牛不相及。回首过去,我们所推崇的那些所谓“德”,有多少还能立得住?又有多少根本立不住?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是到了该抛这些东西的时候了。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西方管理理论借鉴较多,取得了良好效果。而目前西方管理理论又已经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不仅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和前提的“物本”管理,过渡到了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和前提的“人本”管理,而且正向着以“能力人”假设为基础和前提的“能本”管理迈进,实行“人的革命”,挖掘人的潜力,发挥人的创造性,把人塑造成“能力人”。而我们却要倒退起来,再去玩“空手道”,靠嘴皮子吃饭,显然是一种误国行为,应该铲除。
2.重人治轻法治。人治与法治,历来是相互对立的。纵观当今世界,发达的国家、开明的国家,无一不是法治国家。相反,那些死硬、落后、僵化的国家,才容易出现人治和独裁。我们国家封建的家底历来很厚,厚到令世界民主潮流都无可奈何的程度。这些年,应当说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不行,人治色彩还是太浓。例如,对领导人的讲话重视程度远远胜过法律,这就不正常。我们应该研究、借鉴、学习别国权力制衡的先进经验,在依法治权方面弃旧图新、有所作为,使权力体制真正运行到法制轨道上来。不能老强调历史原因,不能老说人民群众还不会行使民主权力。历史障碍要靠我们去消除,人民群众要靠我们去推动。古今中外,有作为的政治家无不因在这两方面做出贡献而彪炳千秋的。老坐在历史的椅子上哀叹,老怨人民群众不行,从而不能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庸人的一种典型表现。
3.重选拔轻监管。我们的干部选拔,是有一套制度的,政治关,思想关,那一关都得过。以前还要搞政审外调,查个八辈祖宗。按说如此选出来的干部,应该是根正苗红,人民就可以放心了。然而,不幸的却是贪官污吏照样出,权力腐败照样有,并且呈越来越严重之势。原因何在?固然,选拔制度本身存在问题,一些素质差、能力低的人被选了上来。这些人上来以后,能力低不会干事,素质差胡乱干事,贻误甚至损害了人民事业。但疏于监管不能不说是一个极重要原因。一是监管者权力太小。人大、纪委、监察部门权力太少,受制于同级党委和地方太多,监管难以有效施展。监督者必须拥有比被监督者更大的权力,监督才会奏效,这应该是常识。最低也须二者权力相等。否则,说得直白一点,这种监督只能是让“耗子”去监督“猫”——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的各级权力监管部门,人权、财权受地方制约那么严重,处处受制于人又要去监督人,这个监督又怎么能够奏效?更不待说高效了。所以,我们要加强权力监管,首先要在监管体制上入手,给监督者以必要的权力,给监督者创造优良的条件和环境。应从理论上探讨、法律上明晰监督者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二是监管者素质不行。连续几届人代会,不少代表对高检、高法的工作报告投了弃权票或反对票,反映了社会对这些部门工作的不满意。事实也正是如此。司法公正,在我国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重要的一条是要解决人的问题,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进出制度。司法队伍素质低,光靠“提高”是不行的,还有一条就是要换人,通过让素质低的人下来、素质高的人上去来解决。三是监管力度不够。权力腐败,也有个风险和成本问题。当着权力持有者的腐败风险系数和成本支出都极低甚至为零,而其效益却翻着跟头上涨时,必然你行我效、上行下效,权力腐败终成风气。按说,权力持有者是社会的中坚,对其要求应比普通社会成员更高更严。然而,在我国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做一个比较,小偷偷了1000元,要蹲拘留,而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了1000元的私利,恐怕没人管,事发都不够处理,这怎么能行。应比照刑法来制定打击权力腐败犯罪,要求要严,措施要“酷”,打击要狠,学一学新加坡对官员的管理和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给权力腐败者以威慑和恐惧,使他们不敢再越雷池半步。否则,权力腐败将很难遏制。
收稿日期:2001-03-10
